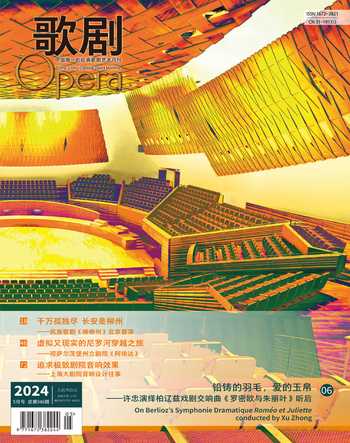以丑扬美的喜歌剧:听上海音乐学院和意大利科莫歌剧院联合制作《塞维利亚理发师》

2024年4月13日—16日,由上海音乐学院和意大利科莫歌剧院联袂制作的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连演4场。我聆赏了15日B组的演出。该制作的看点,除了音乐本身所塑造的人物表情、动作及暗讽外,突出的亮点是舞台设计所带有的哥特式精神现象的梦境符号,以至于我走出剧院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巴尔托洛变成了一个疯狂的科学家,他在古堡内囚禁着罗西娜,仆人也不再做着洗衣做饭的家务,而是拿着一把斧头横冲直撞;还有机智与滑头的费加罗帮助被爱勒住心弦的伯爵阿尔卡维瓦,在巴尔托洛眼皮底下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示爱罗西娜的情节;配合着耳边蒸汽机式的罗西尼渐强,展开的故事就像打怪、闯关、升级的游戏,可批判可娱乐,可走耳可走心。
众所周知,19世纪初在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状况悲惨,催生了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孕育了一种新的艺术思想和爱国主义情绪。喜歌剧在罗西尼手上,以带有现代生活气息和现实性的面貌重新复苏。这部《塞维利亚理发师》,以费加罗通过机智滑头和幽默风趣帮助伯爵阿尔卡维瓦,从违背伦常的巴尔托洛医生手里夺走美丽的罗西娜的故事,展示了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也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典范。
此次新版制作,在当代的演绎中没有回避这一历史状况,而是以隐秘的、符号性的指射,将历史的情绪,转喻、凝置、浓缩为了一系列弗洛伊德式的梦境,即剧中的疯狂的科学家(巴尔托洛医生),还有哥特古堡、黑猫、恶龙浮雕等中世纪符号。这些看似“不合时宜”的设计,实则是希望为观众带入更多的历史情绪。

每一次不同的舞台制作,都是一次感官上的全新实现,而歌剧中的音乐,在增强喜剧效果上更是喜剧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总监廖昌永院长与导演伊凡·思泰法努蒂(Ivan Stefanutti)的合作下,该版制作中音乐喜剧元素有着独具匠心的人物动作呈现,动作与音乐之间也有着全新的配合。笔者了解到,在排练的过程中,大到舞台调度、形体行动,小到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眼神,导演都会引导演员往音乐文本靠近。除国际组演员外,此次担纲演出的乐团、合唱团、主要演员,全部由上音优秀校友及在校师生们组成。
“快给大忙人让路”:一首让男中音大放异彩的咏叹调

罗西尼以现实主义的音乐和精确鲜明的音乐形象,将博马舍所嘲笑的人物缺点——假仁假义、愚蠢、贪婪——以讽刺又带有锋芒的方式传达。角色设计上,罗西尼让所有角色像现实生活那样的说话,从而刻画人物的喜剧性。比如在第一幕,费加罗的咏叹调“快给大忙人让路”(Largo al factotum)里,费加罗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如何为这座城市的孩子、女士和绅士提供各种服务,以及为人们带来巨大乐趣,又如何被人们所喜爱,一副第三阶级生活里的趣味。而音乐上则通过密集的语调、极速狂飙式的乐句、上下乱窜的音型与收放的节奏,以急口令式的歌唱等完成人物塑造。这些属于喜剧节奏的最大特点,在音乐中统统可以听见,在欢快紧凑的气氛当中,带给观众一个灵敏圆滑、精通世事、幽默、诙谐的费加罗。
费加罗的扮演者胡斯豪,上音声乐博士,曾获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对分句的各种不同表情处理,有着精湛的意大利语吐字基本功:铁花飞溅的元音、辅音,流畅地从一个单词过渡到另一个单词,带着可玩味的艺术处理,在前半段语气长长的强制性连线性上,给人微妙且十足的生活情趣。当他唱到每个人都喊着他的名字而制造的混乱场景时,可以感受到他驾驭着乐队原本就利索的速度,让听众感到这个唱段在歌剧的早期阶段是多么的大放异彩。

费加罗有着丰富的情感,很多重唱段落,也都需要在巧妙中完成与不同角色间的交流。譬如在伯爵请求费加罗帮助追求罗西娜的场景中,费加罗唱到“奶酪正好落在你的通心粉上”(sui maccheroni, il cacio vè cascato)这句,胡斯豪以一种主人似的语调与伯爵交流,将上升的第三阶级的自信与尊严予以凸显;而在与同样第三阶级的罗西娜的重唱时,胡斯豪又以一种戏弄的和充满生活一面的交流方式,一本正经的语调,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副假装的担忧,故意告知罗西娜明天要被嫁出去,如这句“(巴尔托洛)明天成为你的丈夫”(esser dentro doman vostro marito),语气轻快地落在“你的丈夫”(vostro marito)上;而“明天”(esser dentro doman)一词,又是一副严肃的表情。让置身事外的观众看足了他在罗西娜面前的表演。
巴尔托洛:疯狂科学家诙谐性的自我指涉
将角色性格中的某个缺陷无限放大,并以此定性角色形象,通常是喜剧的创作手法之一。这一版的一个亮点,就是将巴尔托洛某一缺陷的无限放大——把他塑造为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一个疯狂的科学家。这种形象在影视作品里通常有着刻板印象,类似科幻情景喜剧动画片中的科学家瑞克·桑切斯的形象。
这一版的巴尔托洛,被符号化为一个疯狂的科学家,一个与道德无关的理性主义者,就像19世纪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社会等级;他培育出的名为安布罗焦(Ambrogio)的怪物,满身暗红色的疤痕和粗糙的缝线,在舞台上时不时地出入,与情节却毫无关联;那游荡的黑猫符号则暗合《塞维利亚理发师》当年首演时对手为捣乱而放进舞台的猫。疯狂科学家的符号本身也有着诙谐性的自我指涉,作为被讽刺的对象,在费加罗、伯爵、林多罗(伯爵的变装)和罗西娜的戏弄下,便更显得不谐调与风趣,讽刺感十足。但巴尔托洛同时也有邪魅的一面,疯狂科学家为这个角色也带来了更多隐秘的力量,能更直观地体验到所有角色被卷入一种不断加剧的无法挣脱的力量中。

在第一幕第二场——二重唱到六重唱巨大的重唱终场中,所有的人物统一在了一个单一的音乐连续体所制造的情境变化之中,每个人物的感情也将在新的人物加入后而随之改变。个别角色一会儿喘息着听不见声音,一会儿又充满激情地吼着,此起彼伏,夸张的语言音调在整个舞台上充满了喜剧性,巨大的讽刺力量也呼之欲出,每个人物就像是在夜路里宣泄或狂奔实现各自欲望的马车。
巴尔托洛的扮演者是奥玛尔·蒙塔纳里(Omar Montanari),他对这个具有诙谐指射的角色是这样刻画的:舞台上行走时用的是较为缓慢的八字步,手部不时运用绕手腕、绕手指的小动作彰显科学家的怪癖,形体上时而刻板僵硬时而扭捏造作,夸张而顿挫……所有这些细节,越是表现得高贵就越虚伪。
在这一幕的终场合唱下,从阿尔玛维瓦扮演一名醉酒士兵寻求住宿开始,到巴尔托洛在混乱中像一座雕像一样僵硬地站着。这期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喜剧事件:巴尔托洛要赶走士兵(伯爵)——罗西娜为自己的定局哀叹——醉酒的士兵向巴尔托洛发起决斗——费加罗要求众人冷静又故意搅动局势——巴西利奥和贝尔塔稳定秩序——军队在混乱一发而不可收时突然敲门,逮捕了所有人。整段音乐有着活泼生动的管弦乐音响,具有生活气息的现实性,流畅轻巧的旋律以及率直畅快的节奏感,无数巧思皆汇聚于精妙的充满讽刺的愉快情节中。随着喜剧动作不断升级,人物也不断展示着各种诙谐、反差、趣味,妙趣横生,喜剧味道十足。
伯爵与罗西娜:充满感情的言谈语气
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仍然很低,没有工作可言,唯一能够做的便是嫁人,婚姻是她们最终的归宿。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阐述道:“女人只要抛头露面就是惊世骇俗的丑闻,隐忍克制的观念早已融入女性的血液里,使得她们无法抵制淡泊隐居的冲动。”

罗西娜在剧中是一个纯真善良、果敢刚毅、追求平等自由的女性形象,被高雅、勇敢、有魅力的男性形象所深深迷恋。她并没有讨好他人,也会对巴尔托洛进行反抗,她的“我心中的声音”(Una voce poco fa),是一首可以令所有男人在脑海里放烟花的花腔咏叹调。此次罗西娜的饰演者是意大利莫科剧院的齐亚娜·蒂洛塔(Chiara Tirotta),这位活泼的年轻姑娘俏皮感十足,还有着华丽的声音、流畅而舒服的花腔,展现出罗西娜沉溺于想象中的爱情,穿梭于希望与现实的不确定中。后半段她一改倾慕的歌声,又展现出罗西娜狡黠而泼辣的另一面。
阿尔玛维瓦伯爵,通过伪装三个不同身份——变装的穷小子、军官和家庭教师——来骗过巴尔托洛,以便接近罗西娜。阿尔玛维瓦伯爵时而正直、睿智,时而凌然正气、沉稳勇敢,时而谦逊,与巴尔托洛那一副高贵而不可一世、工于算计的样子形成强烈反差。他的开场咏叹调“黎明披上曙光”(Ecco Ridente in cielo)是阿玛维瓦伯爵唱给罗西娜的情歌。当时他正站在罗西娜居住的楼下,对着她房间的窗口深情吟唱,同时给他伴奏的还有他花重金聘请的乐队。随后在咏叹调“如果你知道我的名字”(se il mio nome saper voi bramate)中,伯爵自称林多罗,半曲吟尽,罗西娜给出了回应。扮演阿尔玛维瓦伯爵的安德列斯·阿古德洛(Andres Agudelo),在这首爱情咏叹调中,将这一人物的温暖、关怀与顺从,融合为一种人格的和谐状态。而在军人身份中他表现出高大、刚强、高贵,在家庭教师身份中则展示了情操高尚、道德完善,每个身份都有着款款爱意,全方位展示出一个渴望爱情到来的伯爵形象。

巴西里奥:以急口令演绎狡猾诡秘的性格
第一幕第二场,巴尔托洛向巴西里奥说明了目前的紧急情况,巴西里奥决定用诽谤赶走伯爵,使出了老狐狸般的奸计唱出这首地震般爆发的咏叹调“造谣像微风般”(La calunnia)。这首咏叹调的歌词大意是:谣言如温柔的微风般开始,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增强而扩散开来,最后就会像大炮和巨雷一般爆发。这首咏叹调的音乐,有着极端化的力度对比,不仅要求男低音音色低沉、浑厚、老成、持重,还需要演员表现出巴西里奥咄咄逼人、狡猾诡秘的性格。此时弦乐组以极轻的力度奏出渐强节奏,扮演者宗师在演唱时,以快节奏、机械化的状态说着台词,他有着圆润的音色和清晰且自然连贯的发音,声音与气息的搭配连贯。从近乎耳语的极轻音,到狂怒和仇恨的火山般的爆发,在逐渐加大音域和增强演唱力度中,他用人声和和声织体共同铸就“罗西尼渐强”。

此次上海音乐学院和意大利科莫歌剧院联袂制作的《塞维利亚理发师》是成功的。罗西尼把形象的现实性与音乐语言的民族性和古典主义的明朗完美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的完美实践,而导演则在庞大的喜剧建制背后,以讽刺与挖苦的阐释为观众展示了作品的深刻性,展现出博马舍喜剧里的现实主义,值得我们致敬。
(单金龙,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