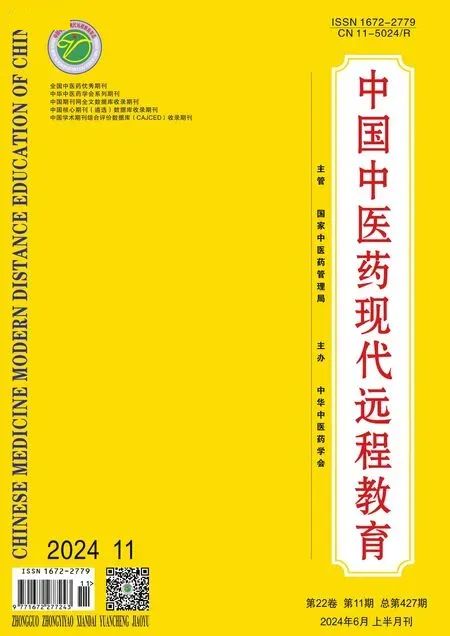《黄帝内经》主明则下安理论探析
胡依凡 田相同
(1.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临沂市中心医院院长办公室,山东 临沂 276401)
“主明则下安”出自《素问·灵兰秘典论》,原文为“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1],突出了君主之官“心”对脏腑的统治及影响作用。中医之“心”不仅仅指现代医学解剖层面的概念。在古代哲学的影响下,通过对天地、自然及社会制度的取象比类,采用仿象推测的思辨方法,并结合生活观察,同时在不断探析、总结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理性地思考和分析,逐渐使“心”的概念脱离实体,演变为了功能化之“心”,形成了中医关于心的藏象理论。“主明而下安”的论点,对认识人体生理病理、防病保健,以至于临床实践都具有指导意义。
1 主明
1.1 君主之官早在中医学理论建立之前,先秦诸家之论中就提出不把心看作一个解剖实体,而是一个哲学概念,认为“心”代表了人体的感知觉、思维、意志、情感等活动[2]。古代哲学对《黄帝内经》中“君主之官”等观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荀子·天论》云:“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管子·心术上》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管子·内业》又云:“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认为心居人体中虚而为君,有制五官、管九窍、实四肢的作用。古代学者将人体藏器功能与国家官员职能做比类、参照,由此加深对藏器功能的认识。他们以人体和国家在诸多功能结构上的相类为依据,由国家之各部门的“不得相失”,推出人体各组织系统也必须信息畅通、动作协调,生命才能正常运行;由国家命脉系于君主是否明智,推出维系生命的关键在于心之神明是否健全[3]。
《灵枢·本神》云:“心藏脉,脉舍神”。心主神明和心主血脉是心的两个基本生理功能,二者相互影响。《素问·八正神明论》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水谷精微化生之营气运行于血脉之中,濡养滋润全身脏腑组织,是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灵枢·平人绝谷》云:“血脉和利,精神乃居”,《灵枢·营卫生会》又云:“血者,神气也”,提示心主血脉的功能正常,心神得到血液的滋养,则心神清明;心神清明,则能调控心血的运行,使血脉功能正常。故“血脉”和“神明”是“主明”的基础。
1.2 心主神明心主神明的观念并非中医学独创,早在先秦诸家之论中就已广泛存在[4],如《荀子·解蔽》中“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鬼谷子·捭阖》中“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孟子·尽心上》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神既有“生命活动的主宰及其总体的外在表现”之广义,又有“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等”之狭义[5]。作为广义之意,其功能由最高统帅担任,正如《素问·六节藏象论》云:“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张介宾《类经·脏象类》云:“心为一身之君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以应万几,脏腑百骸,惟所是命,聪明智能,莫不由之,故曰神明出焉”,都指出心是广义之神之所处,对生命客观的存在以及生理活动均是主宰。作为狭义之意,其功能为统领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等,如《灵枢·本神》云:“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任,使也,即处置事物者为心。《灵枢·口问》云:“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张介宾亦在《类经·疾病类》中指出:“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兼该志意。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惟心所使也”,又云:“情志之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求其所由,则无不从心而发”,可见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情绪,虽分属于五脏,仍总归于心主神明的功能、统领,其实质就是心接受外界事物并做出反应,五脏在“心神”的主导下协作完成一系列复杂的精神活动[6]。
基于西方医学的发展及对脑解剖、生理认识的不断加深,“脑主神明”论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心主神明”受到了质疑与挑战。《黄帝内经》中并未明确提出“脑主神明”,《本草纲目·辛夷》在继承了《难经》三焦命门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脑为元神之府”一说,将元神的概念引入中医学领域,后世多以此为依据提出“脑主神明论”。然纵观《本草纲目》,其并未把神志活动归属于大脑,而是归属于心,在理、法、方、药等方面回归“心主神明”说[7]。徐雅等[8]认为“心主神明”与“脑为元神之府”二者实质上是统一的,“心主神明”是指神志活动依存的本源,“脑为元神之府”是神志活动的功能体现,这恰恰说明了心作为“君主之官”的统治作用。
1.3 心主血脉《素问·痿论》云:“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罗桂青等[9]认为,中医对人体的认识带有“形而上”的思辨性质,对于“心”和“心主血脉”等概念,应该从人体生命现象的宏观角度去理解,而不能只是在没有生命气息的人体解剖结构上寻找证据。心主血脉理论是古人在解剖学认识到心与血脉密切相关的基础上,通过医学实践中的观察和取象比类,由五行学说推演而来的[10]。心为阳中之阳,像太阳一样,照亮并孕育万物。《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素问·五脏生成》云:“诸血者,皆属于心”,《淮南子·原道训》载:“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肢,流行血气”,均体现了心具有生血、储血和行血的功能。
赵坤以知识考古学为方法,探讨了“心”和“脉”的关系,总结出以下结论:秦汉时期,“心”与“脉”之间逐渐产生相关性;自战国开始,“脉”由血脉变成经脉,主行血气,心与脉的关系为“心-神-血气(脉)”,即心藏神并支配脉中血气的运行[11],故《黄帝内经》中脉的概念不仅仅是基于解剖学发现的行血之“脉管”。《素问·五脏生成》云:“诸血者,皆属于心”,《素问·脉要精微论》云:“脉者,血之府也”。《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云:“脉经云脉为血府,即此之谓也……其应心而动为无疑矣,故云心之合脉也”。血、脉属心,血居心、脉,血、脉、心联系密切,三者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
2 下安
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并通过“神明”和“血脉”主宰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素问·汤液醪醴论》指出:“精神不进,则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主不明”,则影响其他藏神之脏腑功能的恢复,导致病不得愈。《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主明”,则在心的统领影响下,各个脏腑生理功能正常且协调,人体才能抵御疾病,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不可否认,人体的各个部分都很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文主要阐述体现“心”作为“主”的重要性和对“下”的影响。
2.1 经脉是纽带经脉最初是在对人体体表观察的基础上,形成的与“天五地六”相配的十一经脉,后转变为《黄帝内经》时期与脏腑相联系属络的十二经脉[12]。《灵枢·经脉》在论述手少阴经循行时指出:“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以“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指出心经与肺和小肠的联系;论述脾经时说“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指出脾经支脉交于心;论述肾经时说“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指出肾经有一支脉络心。《灵枢·经别》记载:“足太阳之正……循膂,当心入散”“足少阳之正……循胸里属胆,散之上肝,贯心”“足阳明之正……散之脾,上通于心”“手太阳之正……入腋走心”“手少阴之正……属于心”,指出足三阳经及手太阳经、手少阴经的经别与心相联系[13]。《灵枢·经脉》云:“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心借助于经络的沟通、联络及经别的离合出入,与人体各个部位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通过经络系统的濡养、联系、感应等作用,支配和调节人体的生理活动。
2.2 心与五脏
2.2.1 心与脾心属火,脾属土,心与脾按照五行生克,为火生土的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南方生热……心生血,血生脾”,指出二者生理相关性;《素问·阴阳别论》之“二阳之病,发心脾”,指出二者病理联系性[14]。《千金方》云:“心劳病者补脾气以益之,脾旺则感于心矣”,《保婴撮要》记载:“盖心为脾母,脾为心子,然心既病则脾土益虚矣”,《质疑录》载:“少阴心火,正补太阴脾土,此虚则补母之义”[15],均指出心为母、脾为子,提示母病及子和虚则补母在心与脾病理联系中的重要性。
2.2.2 心与肺心为君主血,肺为相主气。《景岳全书·杂证谟》云:“忧生于心,肺必应之”,《素问·标本病传论》云:“夫病传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咳”,均指出心病不已,则传之于肺。《类经》记载:“心为脏腑之主,故五脏之系皆入于心,心之总系复上贯于肺,通于喉,而息由以出”,指出气血相随不可分离,心肺息息相关,故《仁斋直指方论·血营气卫论》云:“人之一身,所以得全其性命者,气与血也”。
2.2.3 心与肝心属火,肝属木,肝与心在五行中属母子,功能上相互既济。《难经·七十五难》中记载:“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如《备急千金要方》指出,当肝脏患病时,可以通过补子益母的原则,补益心气,心旺则母脏肝不病[16]。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从肝虚则补心、心实则泻肝两方面论述了心肝母子相感的联系。《读医随笔》记载:“肝气舒,心气畅,血流通,筋条达,而正气不结,邪无所容矣”,指出心肝气血调畅,则邪无居处。
2.2.4 心与肾心属火居上,肾属水居下。《内经知要》有云:“肾者水也,水中生气,即真火也。心者火也,火中生液,即真水也。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水火互藏,阴阳交体”,即真火根生于肾中阴水,为阳生于阴;真水根生于心中阳火,为阴生于阳[17]。《傅青主男科·虚劳门》中强调,一般认为肾虚导致的男子精滑梦遗之症,其实“不独肾病也,心病也,宜心肾兼治”,治疗应“欲补肾火,乃必须补心火,则水火相济也”,指出心肾病理上的相互影响。
2.3 心与六腑《灵枢·经脉》云:“主心所生病者,目黄,胁痛”,《推拿抉微》云:“胆病战栗颠狂,宜补心”,指出心病会引起目精黄染及胁肋部位疼痛等胆病症状,胆病也可辨证由心论治。《诸病源候论》中记载:“心主于血,与小肠合。若心家有热,结于小肠,故小便血也”,《医宗金鉴》中亦提到:“心与小肠为表里也。然所见口糜舌疮,小便赤黄,茎中作痛,热淋不利等证,皆心移热于小肠之证”,指出心与小肠相表里,心热可移于小肠。《医贯》中云:“若夫土者,随火寄生,即当随火而补,然有至妙之理。阳明胃土,随少阴心火而生,故补胃土者,补心火”,提出心火生胃土,补胃需补心的理论。《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候》中记载:“心劳者,忽忽喜忘,大便苦难,或时鸭溏,口内生疮”,指出劳心可致便秘或便溏。《丹溪心法·淋》云:“执剂之法,并用流行滞气,疏利小便,清解邪热。其于调平心火,又三者之纲领焉。心清则小便自利,心平则血不妄行”,指出心火亢盛,热移下焦,可导致膀胱气化失司,水道不利。《黄帝内经太素·经脉之一》曰:“心外有脂,包裹其心,名曰心包”。心包为心外薄膜,能够代心受邪。“心包代君行事,在三焦之中”,提示心包与三焦相表里,可以协助心来发挥调理三焦的功能。而作为运行元气、水谷和水液的通道,三焦通畅不瘀阻,才可使心神清明、血脉通畅。
3 小结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中所阐述的“君主之官”为藏象之心,是在解剖意义的基础上演化而成的功能之心,其主神明和主血脉的两个基本功能,决定了其对人体的统治支配作用。“心为君火,清宁则统周身之气,散乱则气消矣”“心乱则百病生,心静则万病息”“主明则下安”的论点,提醒临床上应用中医思维应注重对“君主之心”的把控,为临床及养生开拓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