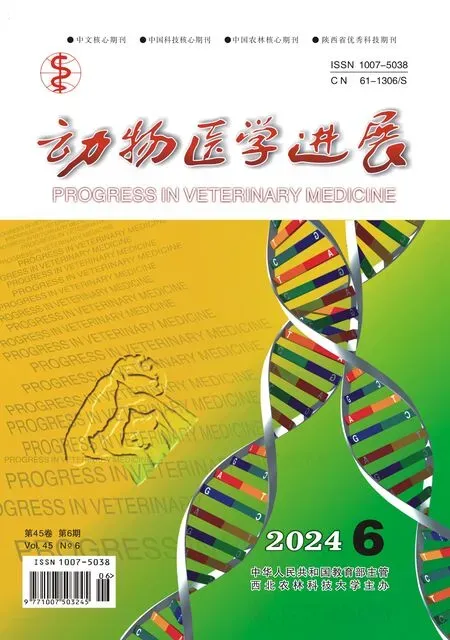抗菌药物影响禽肠道菌群及免疫应答研究进展
陈胜宏,闻晓波,冉旭华
(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人和动物的消化道内含有大量的微生物,其中细菌占绝对数量。肠道菌群不但有助于食物的消化、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而且在肠道发育、维持肠道上皮细胞屏障完整性、免疫系统发育以及抗感染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千百万年来,肠道内微生物与人、动物共同进化,构成了必不可少的内部生态系统或者称之为“超级有机体”。正常情况下,动物肠道解剖学位置、遗传背景(品系)、饲料、养殖模式、日龄、气候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导致动物肠道内细菌种类和丰度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可以保持特定生长阶段的稳态,维护机体健康和内环境的稳定。肠道微生物群落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宿主的物质代谢与吸收、生长发育、免疫调节及病原抵抗等功能[1]。然而,当这种稳态紊乱后,则会对机体健康产生深远且复杂的影响,例如抗菌药物的不规范使用会改变禽类菌群结构,降低肠道菌群的稳定性、多样性及丰度,进而导致肠道菌群屏障功能减弱、宿主肠道免疫系统受损,影响机体生长发育、物质代谢与营养吸收。为此本文对家禽肠道菌群的组成、肠道菌群与肠道免疫的关系、抗菌药物对肠道菌群及免疫影响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阐述。
1 禽肠道菌群概述
禽消化道内包含了大量的、动态变化的肠道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古细菌、原生动物、病毒,其中以细菌为主[2],且盲肠内的细菌数量最多[3]。在门分类水平上,主要为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及放线菌门成员[4],占总数的90%以上[2],且在消化道的不同部位,肠道菌群的组成和丰度均存在一定差异[5]。禽嗉囊内容物的细菌密度约为每克内容物108~109菌落形成单位(colony-forming units,CFU),主要为厚壁菌门(主要为乳酸球菌属)、放线菌门(双歧杆菌属)和变形菌门(肠杆菌属);禽肌胃内容物细菌密度约为107~108CFU/g,其组成基本与嗉囊内一致;小肠内菌群主要为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盲肠内细菌密度最高,约为1010~1011CFU/g,菌群的多样性也最高,预测约含有2 200分类操作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OTUs)和3 500个基因型[6]。综合不同的研究数据,厚壁菌门细菌占肠道菌群总数44%~56%,拟杆菌门细菌占23%~46%,变形菌门占1%~16%[5]。
动物日龄、品系、性别、饲料以及抗菌药物使用都是影响肠道菌群组成的因素,导致肠道菌群组成和丰度出现较大差异。如7~42日龄白羽肉鸡粪便菌群多样性差异不显著,但在7日龄前存在显著差异[7];鸡和火鸡的肠道菌群在种水平上的相似性仅16%[2]。有研究表明,公鸡十二指肠、回肠和盲肠内容物菌群多样性高于母鸡,但空肠内容物中菌群多样性低于母鸡;公鸡十二指肠和空肠内容物菌群丰度低于母鸡,但回肠和盲肠内容物中的菌群丰度高于母鸡[8]。与普通饲料相比,发酵饲料能够增加鸡肠道中厚壁菌门的相对丰度,增加瘤胃菌科和毛螺菌科等有益菌群比例,并且降低大肠埃希氏菌等有害菌所占的比例[9];通过饮水给予雏鸡4种常用抗菌药物——黏菌素、利高霉素、阿莫西林和恩诺沙星,发现使用抗菌药物会破坏雏鸡肠道菌群的动态平衡,导致菌群失衡,其中利高霉素给药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最为显著[10]。
2 肠道菌群与免疫系统的关系
肠道菌群在维持人和动物的生长发育、免疫系统的成熟以及机体健康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1]。例如,与正常鸡相比,无菌鸡盲肠扁桃体明显萎缩,并完全缺失淋巴滤泡[12];无菌鸡的杯状细胞发育不成熟,导致肠腔内黏蛋白缺失,进而造成肠道黏液屏障受损[13-14]。给肉用公雏鸡饲喂发酵乳杆菌和啤酒酵母,提高了公雏鸡的Toll样受体2(toll like receptor 2,TLR2)和TLR4的表达,同时提高了公雏鸡结肠组织内CD3+、CD4+和CD8+T细胞的数量[15]。张小龙等研究表明,低体重鸡血清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LPS)水平显著高于高体重鸡,TLR4、髓样分化因子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MyD88)和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及相关炎性细胞因子在低体重鸡空肠组织中的表达显著上调,导致肠道屏障完整性受损[16]。
基于肠道菌群的重要性,近年来,菌群移植技术已经广泛用于试验和临床研究,尤其是在肠道疾病治疗方面效果显著。例如,给患有肠炎的低体重鸡移植粪菌后,血清LPS浓度显著降低,空肠及其肠绒毛的长度均有显著增加,TLR4、MyD88和NF-κB等分子的相对mRNA表达量显著降低,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 1β,IL-1β)、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等促炎细胞因子的相对mRNA表达量显著降低, IL-4、IL-10等抗炎细胞因子显著升高,空肠炎症得到缓解,生长性能得以恢复[16]。同样,SPF鸡在接受健康鸡的粪菌移植后,体重显著升高,肠绒毛长度显著增加,血液中IL-1β、IL-18含量显著升高,同时对沙门氏菌的抗感染能力也有所增强[17]。以上试验均证实肠道菌群对免疫系统的成熟具有重要的作用。
肠道菌群与肠道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调控网络[18]。肠道黏膜表面存在大量分泌免疫球蛋白A(immunoglobulin A,IgA)的B细胞、上皮淋巴细胞、γδ T细胞、Th17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这些淋巴细胞的分布和功能是由肠道菌群调节的,以此对抗病原体感染,维持内环境的稳定[11,19-20],同时阻止病原微生物侵入肠道黏膜下层,对肠道单层上皮及肠道紧密连接起到第一道防火墙的作用[21]。反之,免疫系统也可调控肠道共生菌群的稳定性,肠道黏膜除了为肠道菌群提供定居点和营养外,黏膜层内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及树突状细胞对侵入的病原菌做出适当的免疫应答,既要控制和消灭病原微生物,同时避免产生过度的免疫应答,维持肠道共生菌群的生长和菌群稳定[12,22]。然而,肠道菌群与肠道免疫系统之间的复杂且精细的相互作用易受到外来多种因素的干扰和破坏,例如抗菌药物添加和微生物感染[18],造成营养物质吸收、代谢、抗感染免疫的缺陷。
3 抗菌药物对禽肠道菌群稳态的影响
抗菌药物的副作用更多的是造成肠道菌群紊乱,而不是药物的直接副作用。抗菌药物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导致禽肠道菌群失调,影响机体免疫力。尽管适当使用抗菌药物对禽的健康不会造成明显的副作用,但是抗菌药物添加是导致肠道菌群失调的最主要因素[23],对禽的免疫调控或健康造成一定危害。在动物试验中发现,混合抗菌药物(氨苄西林、硫酸新霉素、甲硝唑和万古霉素)投喂肉鸡后,肉鸡肠道菌群丰度及多样性显著降低,鸡肠道菌群失调,导致肉鸡的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M-CSF)、IL-17和TLR2显著降低,进而显著降低鸡肺部抗败血症支原体感染的能力[24]。另外,混合抗菌药物(万古霉素、新霉素、甲硝唑和两性霉素B)饲喂2周后再经LPS攻毒的蛋鸡,其IgM和IgY的总含量均显著降低,肠道中放线菌门、变型菌门显著升高,厚壁菌门显著降低[25]。Videnska P[26]等经16S rRNA测序发现,给母鸡饲喂四环素或链霉素后,其粪便中双歧杆菌、拟杆菌、梭菌、脱硫弧菌、伯克氏菌和弯曲菌的数量降低,而肠杆菌和乳杆菌的数量有所上升,相应的肠道微生物代谢物含量可能存在极大差异。
4 抗菌药物影响机体免疫的机制
为了证实抗菌药物对肠道菌群、机体免疫器官成熟及免疫相关指标的影响,通常采用给人口服广谱抗菌药物或给动物(小鼠或禽)投喂某类抗菌药物[27],通过16S rRNA或宏基因组测序,分析肠道或粪便中菌群组成及丰度变化,结合组织病理切片、免疫学、人工病原微生物感染等手段分析抗菌药物的影响,以此评估特定菌群变化对禽肠道健康及免疫指标水平的影响[17,24],并由此证实肠道菌群在调控禽类免疫应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5]。有研究数据和结果显示,抗菌药物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对机体免疫造成影响。
4.1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杀灭作用破坏肠道菌群稳态
肠道菌群的不同亚群之间普遍存在共生和相互依赖关系。某一类细菌的代谢产物是某些肠道微生物生长所必需的。例如,肠道中的许多细菌可以产生乙酸盐[28],而在无乙酸盐的情况下,粪杆菌不会在纯培养物中生长[29];青春双歧杆菌在低聚果糖(fructooligosaccharides,FOS)纯培养物上生长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乳酸,而在与哈氏真杆菌共培养时乳酸的可检测量明显降低[30];肠道罗氏菌与长双歧杆菌在FOS纯培养物中共培养时,肠道罗氏菌起初的生长被抑制,随着长双歧杆菌产生足够多的醋酸盐,肠道罗氏菌的生长逐渐恢复正常[31]。
但在消灭病原菌的过程中,由于抗菌药物的广谱杀菌活性,肠道共生菌群被抗菌药物无差别的杀灭或抑制。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抗菌药物或者联合用药,具有不同的抗菌谱,导致肠道菌群的变化也有差异。正常情况下,禽类肠道内的细菌通过发酵,产生短链脂肪酸及合成某些维生素,提高饲料转化率和生产性能。研究发现,禽类盲肠内微杆菌和鞘氨醇单胞菌的丰度与脂肪代谢呈正相关,可以促进禽类的生产性能;而放线菌科中的史雷克菌(Slackia)与脂肪代谢却呈负相关[32]。
4.2 抗菌药物破坏肠道免疫反应
肠道菌群时刻通过Toll样受体(TLRs)和NOD样受体(NOD-like receptors,NLRs)等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与宿主进行信号转导[33-34],参与宿主生长发育[34]、炎症反应[35-36]等过程。在抗菌药物的作用下,禽类肠道中某些有益菌丰度显著降低,而携带大量抗菌药物耐药基因的蓝藻菌丰度显著升高,回肠中黏蛋白2(Mucin-2)、TLR4、MyD88和NF-κB、IL-1β和IFN-γ等基因的mRNA水平均显著下降,导致免疫应答相关信号转导受阻,肠道调节炎症的能力减弱[37]。鸡TLRs在天然免疫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病原体多种成分可以同时激活几种TLRs,产生免疫反应[38]。肉鸡肠道组织和免疫器官的TLRs表达显著高于其他组织[39],鸡TLR2可识别细菌并引起免疫应答,鸡TLR4可特异性识别LPS,进而诱导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产生[40],但抗菌药物处理后肠组织中TLR2、TLR4的mRNA含量显著降低[41],导致肠道非特异性免疫降低。肠道共生菌可通过影响免疫细胞或者上皮细胞的活性进而调节肠道黏膜稳态。研究发现,非致病性沙门氏菌抑制人肠道上皮细胞炎症因子的合成,这可能是由于沙门氏菌阻止IκB-α的降解,抑制NF-κB的激活,下调依赖NF-κB的细胞因子表达[42];多形拟杆菌(Bacteroidesthetaiotaomicron)通过加快肠道上皮细胞系中转录因子核输出,进而抑制NF-κB的活性[43],而抗菌药物的滥用,必然会打破肠道共生菌调节的肠道黏膜稳态。
4.3 抗菌药物影响宿主免疫应答及免疫细胞发育
肠道黏膜固有层内的3型天然淋巴细胞(group 3 innate lymphoid cells,ILC3s)可以通过IL-22依赖的途径限制肠腔内微生物的转位。然而,抗菌药物对ILC3s的招募和成熟具有较大的影响,导致IL-22的表达下降,便于病原微生物的侵入[44]。同时,抗菌药物也可以破坏肠道内辅助性T细胞1(T helper cell 1,Th1)与Th2的比例,导致肠道内T细胞比例失调,降低Th17细胞的丰度,使肠道防御病原微生物感染的能力下降。
大肠内的细菌通过发酵纤维素产生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CFAs),SCFAs在维持上皮细胞的完整性、Treg细胞的分化和聚集以及调控炎症和免疫应答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抗菌药物可以影响肠道SCFAs的产量,从而影响Th17及Treg细胞的丰度,加重病原菌感染后的炎症反应[44-45]。通过给鸡饲喂混合抗菌药物(氨苄西林、硫酸新霉素、甲硝唑和万古霉素),发现鸡肺部抗败血症支原体感染能力显著减弱[24],其原因在于抗菌药物破坏肠道菌群稳态,导致乙酸、丙酸、丁酸及维生素A的生物活性分子(视黄醇、视黄烯)显著降低,其中丁酸盐可以诱导具有强抗菌活性的巨噬细胞分化[46],而维生素缺乏则与严重的支原体感染相关联[47]。
5 展望
抗菌药物在家禽生产中主要用于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但抗菌类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可潜在破坏家禽肠道菌群组成结构及定植屏障,间接导致宿主肠道免疫系统发育不良、免疫应答受阻等状况,从而为外源性病原菌在肠道内定植并最终引起肠道感染提供了机会。随着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及代谢组学的发展与应用,有助于研究者对禽类肠道菌群及其与机体免疫系统关系的进一步了解,并结合肠道菌群结构特征开发针对性的配方饲料、药物研发及疾病防治等的研究,通过调控特定肠道菌群的组成与丰度,达到调节禽类免疫系统发育、生长代谢、疾病防控等效果,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