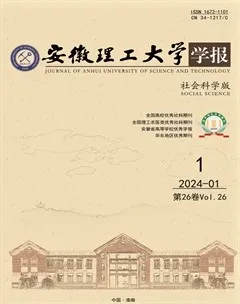无声胜有声
孙伟 于元元
摘要:文章基于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分析波特《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瘟疫叙述技巧。《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关于大流感的直接叙述寥寥无几,表面上大流感的叙事声音近乎为零,但波特通过对叙事视角、顺序和时距的巧妙运用使文本处处潜藏着对大流感的讲述。这种“无声胜有声”的瘟疫叙事技巧不仅能够彰显波特叙事手法精湛,真实展现大流感给人民带来的生理、心理双重痛苦打击,而且也能够给予后疫情时代下的当代读者启示。
关键词:《灰色马,灰色的骑手》;凯瑟琳·安妮·波特;瘟疫;叙事技巧;热奈特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24)01005206
收稿日期:2021-11-20
基金项目: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霍米·巴巴近20年(“9·11”之后)伦理学转向研究(20YJA752017);安徽理工大学青年基金项目(QNYB2021-11)
*通信作者:于元元(1972-),女,安徽淮北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作者简介:孙伟(1996-),男,安徽安庆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凯瑟琳·安妮·波特 (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 以写作手法精巧和叙事技巧独特著称,一生创作不懈,可惜却遗弃了大量作品。其作品存世虽不多可皆为精品,对后世美国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美国小说创作树立了一座标杆。1939年,波特基于个人经历创作并发表了小说《灰色马,灰色的骑手》(Pale Horse,Pale Rider)。这部作品的背景设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下的美国,讲述了一位女记者和中尉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自20世纪80年代起,《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便在学术界掀起一股研究热潮。整体来看,国内外关于《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医学、创伤叙事、宗教和心理分析等方面。如,简·德莫(Jane DeMouy)认为“小说女主人公米兰达是一个拥有双重身份的矛盾女性”[1];骆谋贝认为小说中一战的遮蔽与疾病表征的困难造成了文化缺场状态,并考察了疾病的污名化这一社会建构本质[2];李健健从宗教原型入手,认为“小说男主人公亚当体现了波特矛盾的政治观和破灭的宗教观”[3];王亭亭认为《灰色马,灰色的骑手》是一部创伤小说,是对个人和集体创伤的修复[4];沃尔什(Walsh)从心理学角度解析了米兰达的梦境[5]。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作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可挖掘主题众多,但整理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少有研究关注其“瘟疫”与“叙事”主题,更别说把二者相结合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欲着眼于《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瘟疫”与“叙事”,运用热奈特(Genette)的叙事学理论分析小说的瘟疫叙述技巧,并指出瘟疫叙事技巧蕴含的文本与现实意义,为《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研究提供新视角。
《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之所以能够成为波特的经典作品之一,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部小说是最能体现其精湛叙事手法的作品之一,小说中波特对瘟疫(大流感)的精彩叙述便是最好的例证。小说情节表面上似乎主要是在讲述战争和爱情,对瘟疫的叙述寥寥无几,但如细究便会发现处处潜藏着对瘟疫的叙述。这种看似“悄然无声”实则“掷地有声”的叙事主要归功于波特在叙事视角、顺序和时距上的巧妙运用。
一、固定内聚焦下的瘟疫
法国文学评论家热奈特在《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以下简称为《叙事话语》)一书中把叙事视角分为三类:零聚焦、内聚集和外聚焦。零聚焦表示叙述者采取一种上帝似的视角,对事件进行全知全能式的叙述,即叙述者所知>故事中人物所知;内聚焦是指叙述者从故事中某个特定人物角度叙事,叙述者只知晓故事中特定人物所知,即故事叙述者所知=故事中特定人物所知;外聚焦则表示叙述者知道的内容少于故事中的人物,即故事叙述者所知<故事中人物所知[6]120。在《灰色馬,灰色的骑手》中,波特不仅运用内聚焦叙述视角,而且只叙述女主人公米兰达的见闻与内心活动,叙事者等同于米兰达,即固定内聚焦。通过这一巧妙的叙事视角,波特一方面在故事情节上为读者设置了悬念,另一方面也真实展现了潜伏在战争后的隐形杀手——大流感。
瘟疫在小说中起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设置悬念的作用,而达到这一效果的主要手段就是从内聚焦视角——借助患上流感的女主人公米兰达来讲述故事。“在睡眠中,她知道自己睡在床上,不过不是她几个钟头以前躺下去的床,房间也不是原来那一间,而是她在什么地方见过的一个房间。她的心成了一块石头,在她的身体外面,压在她的胸脯上;她的脉搏迟缓而间接;她知道快要出什么奇怪的事情了……”[7]1。波特在小说伊始就通过这段关于米兰达梦境中怪异内心活动的文字叙述为读者设置了一个悬念,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此后,米兰达令人疑惑的行为举止一次又一次被提及,“她的思想迷迷糊糊地活动,不断地努力把她日常生活中各种叫人烦心的冲突汇合和牢固地结合起来……”[7]10,“她的头火辣辣地、隐隐约约地发痛,现在她注意到了,记得自己一醒过来就头痛,事实上昨天黄昏就开始痛了。她一边试着追溯她那不知不觉越来越厉害的头痛病……”[7]15。种种怪异的思想活动和行为举止,无不在提示着读者米兰达的身体出现了状况。然而,内聚焦叙述视角只能够让读者“看到”米兰达这些看似怪异的思想活动和行为举止,叙述者无只言半语提及其原因,因为米兰达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对于流感也一无所知。因此,读者迫切想知道在米兰达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阅读兴趣由此被进一步激发。
为推进故事情节发展,波特通过米兰达与亚当约会时的一段对话,借米兰达之口在小说中第一次提及了“瘟疫”一词,适机为读者留下了流感这个解惑的线索。这是典型的内聚焦叙述视角。
“我闹不清楚,”米兰达说,“你怎么设法延长假期的?”
“是他们给我的,”亚当说,“没有什么理由,反正那儿人像苍蝇似的死去。这种古怪的新疾病。就是要你的命。”
“看起来是一场瘟疫,”米兰达说,“中世纪的產物。你看过这么多葬礼吗,看到过吗?”[7]23
就在以上对话发生时,米兰达看到一支送葬的队伍经过,随后她之前令人疑惑的状况再次发生,“她有点头晕,脑子里像有‘金鱼在慢慢腾腾地打转”[7]29。米兰达此时断定自己的身体已经坏得不可救药了,随后的一句话更是给读者留下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不舒服极了,我觉得不太行了。不可能光是天气和战争的原因”[7]30。既然不只是天气和战争的原因,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米兰达的身体出现如此糟糕的状况?读者的好奇心此时被激发到了顶点。除了米兰达和亚当的对话,米兰达同事汤尼和查克的对话也再次向读者提供了关于流感的线索,“他们说事实上这是一艘德国船带到波士顿来的细菌造成的……他们认为细菌是喷射在城市上空的,有人说看到一团奇怪的、黑压压、阴沉沉的云从波士顿港浮起来,慢慢铺开到城市的这一头”[7]42。至此,细心的读者估计已经产生“米兰达糟糕的身体状况是否同他们所说的瘟疫和细菌有关”的猜测。但受内聚焦叙述视角所限,读者目前只能是有所猜疑,仍不能从小说中知晓明确的答案。直到小说后半部分,米兰达因病情愈发严重而晕倒,通过她醒来后与霍布小姐的对话,读者才最终意识到米兰达患上了流感。
“我亲爱的孩子,”她对米兰达的衣服瞟了一眼,尖声说,“怎么啦?”
米兰达把电话听筒凑在耳旁说:“我猜是流行性感冒。”[7]65
故事情节即将进入尾声时小说才第一次直接提及流感,至此谜底终于解开。流感的出现解释了读者之前对米兰达糟糕状态的各种疑惑,以及葬礼不断增多的原因和“细菌”传言的由来,读者在豁然开朗之际也不得不惊叹波特在叙事视角上的巧妙选用。波特巧妙地选用了固定内聚焦视角进行叙事,在这种视角下叙事者便等同于米兰达,“他”没有零聚焦的全知全能,但也不受限于外聚焦的条条框框,同时也比多重内聚焦多了份神秘,这种恰到好处的选择使大流感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要素。小说中,多次关于大流感“欲罢还休”的叙述为小说设置了悬念,大大提高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与此同时,固定内聚焦视角的选择也真实地展现出当时潜伏在战争背后的隐形杀手——大流感的破坏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整个美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备战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流感的潜入与爆发。根据后来的科学溯源,“大流感于1918年2月起源于美国哈斯克尔县,随后迅速传播到当地军营,在4月份时全国的军营都相继爆发了流感,然而军队医疗队没有太在意,美国人民也毫不知情,最终这场大流感席卷整个美国直至全球,造成了美国近70万人和全球超过5000万人死亡。”[8]波特使用内聚焦视角,通过米兰达的言谈举止向读者真实地描绘出了流感的“狡猾”和大流感期间人们的茫然与无助。
二、瘟疫患者的非线性叙事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根据时间顺序将叙事分为预叙与倒叙两大类。预叙指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即从前往后叙述;倒叙指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追叙,即从后往前叙述。但在实际写作中,许多作家并不只是简简单单地从前往后或者从后往前直线性叙述,倒叙中插入预叙或预叙中插入倒叙也颇为常见,热奈特把这种叙事顺序称为叙事的无时性,即非线性叙事。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非线性叙事多处可见,这种叙事以米兰达的意识任意跳动、毫无逻辑为特征。
小说开头就使用了典型的非线性叙事手法。“我该骑哪匹马呢?游荡儿、小灰还是长鼻子,眼光邪恶的露西小姐?我多么喜欢这座曙光中的房子啊,这时候,我们大家还没有完全醒来,像扔乱了的钩丝那样纠缠在一起。”[7]1开头第二段,米兰达脑海中首先出现了几匹马,然后意识迅速转向一座房子,以及房间里的人。米兰达此时的意识还停留在现在,但在紧接着的第三段中便突然转向过去,转而提及她曾经见过的陌生人、她的亲人与宠物。“那个陌生人呢?我记得那个瘦长、泛绿的陌生人老在这一带徘徊,受到我祖父、我姑婆、我的远亲、我衰老的猎狗和我银白的小猫欢迎,他在哪呢?他们为什么喜欢他,我真不明白?再说,他们眼下在哪儿呢?”[7]3随后,她的意识又漂流到了现在,继续谈到之前的马;再随后,她的意识又瞬移到即将到来的清晨。“嘿,为了我这一回打算去的旅行,我该借哪一匹马呢,小灰,还是露西小姐,还是能够在黑暗中跨越沟渠和懂得怎样摆脱控制的游荡儿呢?清晨对于我来说是最好的时刻”[7]3。不难看出,小说伊始米兰达的自我叙述便呈现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无序性,这种非线性叙事手法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迷惑不已。
小说伊始米兰达的非线性叙事虽然无序,但尚在读者的接受范围内,因为此时米兰达所讲述的场景和人物都是她可触及且熟悉的。然而,随着故事情节发展,米兰达在病床上的一段自我叙述则大大超出了读者的可接受范围,整个叙事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中。在病床上,病重的米兰达思维完全混乱,她的思绪首先从房间飘到绵延的落基山脉,“我巴不得在寒冷的山上雪地里,这是我喜欢的”[7]52。前一秒正在叙述那里庄严的白雪和蓝天、凛冽的寒风,后一秒话锋却很突兀地从寒冷的落基山脉急转至另一个地方漫游起来,“啊,不行,我需要温暖……什么棕榈树和杉树啦、黑魆魆的影子啦、温暖而不刺眼的天空,就像这个奇怪的天空刺眼而不使他温暖一样”[7]33。就当读者也随着米兰达的思绪漫步于阳光明媚、景色宜人的环境中时,米兰达下一句所讲述的场景却又开始发生变化,“灰色的苔藓在颤悠悠、慢腾腾地摇摆;辽阔的天空中有秃鹰在翱翔;岸边,踩烂的水生植物散发着气味”[7]33、“一个危机四伏、神秘莫测、充满死亡的场所,暗藏着盘缠的花斑毒蛇、眼光毒恶的彩虹色的鸟、脸上流露出人的智慧的豹和鬣毛格外浓密的狮子;尖叫的长臂猴在宽阔的肉质叶中间翻筋斗,树叶闪耀着硫黄色的光,流出致人死亡的腐液;叫不出名字的腐烂的树干倒在缓缓流动的沼泽地里”[7]33。米兰达随后所叙述的场景,更是让读者产生置身于黑暗与死寂之中感觉。米兰达这段病房自叙,场景完全超出了她当时所处的病房,总是出其不意地迅速变换,从寒冷高耸的冰山到温暖辽阔的平原再到死气沉沉的丛林;叙述时间也完全混乱,在回忆和现实中反复横跳。这段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的无序性叙事彻底让读者陷入困惑。
以上两处主人公自述是小说故事情节非线性叙事的典型缩影。米兰达的叙述像水中的浮萍,毫无头绪、飘摆不定,常常让读者望文生疑。波特如此安排叙事,正是她作为一名叙事大師细腻又精妙叙事手法的绝妙体现,并非故弄玄虚、故意刁难读者。根据医学临床研究,“流感患者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热,而发热会导致患者意识混乱,模糊不清,当病情严重时患者体内的毒素会诱发寒战和发热症状,从而出现忽冷忽热的现象甚至幻觉”[9]。了解流感患者的临床表现后再读小说,关于米兰达的所有疑惑和不解便会烟消云散。流感患者出现发热症状时很难保持意识清醒,所以自述经常毫无逻辑、无序。小说开头,米兰达时而谈论眼下的房间,时而回忆往昔的人与物,时而提到即将来临的清晨,便是因为她已经出现发热症状。随着病情加重,流感患者身上会发生寒战和发热症状交替出现现象,意识越发混乱,有时甚至会出现幻觉。米兰达在病房时而感觉置身于寒冷的落基山脉,时而感觉徜徉在温暖的平原,又时而感觉身陷死亡般的丛林,这正表明她的病情已经到了完全丧失意识、失去时间和空间概念地步,忽冷忽热的症状使她出现幻觉。
波特使用非线性叙事手法真实再现了流感患者的意识状态,通过患者意识的无序性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性,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了大流感的威力。如果说波特采用内聚焦视角让读者见识到了大流感对患者外在躯体的打击,那么此处的非线性叙事手法则让读者感受到了大流感对患者内在意识的冲击,大流感威力可见一斑。
三、时距背后的创伤叙事
时距是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故事时间(故事实际延续的时间)和叙事时间(叙述故事所用的时间)之间的对比关系。作品中故事的实际延续时间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叙述它的时间可以发生变化,因此便有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长短的比较。热奈特把时距分为四种类型:停顿、省略、概要和场景,并用公式形象地解释了它们的含义。停顿指“故事时间≈0,叙事时间=N”;与停顿相反,省略指“故事时间=N,叙事时间≈0”;概要指“故事时间>叙事时间”;场景指“故事时间=叙事时间”[6]145。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波特讲述不同事件采用不同的时距,使小说的叙事节奏变化多样,但详窥小说,这种叙事技巧也道出了波特本人的心理创伤。
场景类型意味着故事时间等于叙事时间,一般以对话的形式出现。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战争的讲述主要是通过场景的方式展现的,如小说开始部分人物之间的对话都是围绕购买“战争自由公债”展开。“我们在打仗,有些人在买自由公债,而其他一些人似乎对这事一点也不热心,这就是我们要指出的。”[7]5“咱们的美国小伙子在贝洛森林作战和牺牲,任何人都能攒五十块钱来打败德国佬助一把力。”[7]14随后的对话也是在去军营看望士兵的背景下进行的。米兰达与亚当的对话也大量涉及战争:“啊,不会再有战争啦,难道你看报吗?我们这一会要把战争彻底消灭,而战争是早晚会被消灭的。”[7]8
停顿类型指故事时间很短,对应的文本叙事时间无限长。停顿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对亚当的描述和对米兰达在病床上的思想意识的讲述上。小说中,每当米兰达与亚当同场出现时,叙事节奏便会突然变慢。如,米兰达在与亚当第一次相遇时,她脑中一瞬间对亚当形成的印象在文本中却有接近500字的描述,“看到一个年轻人躺着,右腿上着石膏,装着轮滑,眼睛里流露出不友好的、恶狠狠的光芒……这个有血有肉的人体现了我对整个事件的看法”[7]55。此处便是典型的停顿,故事时间接近零,而叙事时间趋于无限。之后米兰达每次与亚当约会时都会伴随着对亚当详尽的描述,叙事时距无限拉长。“他们溜达着,步调一致,他那双结实的、擦得亮晃晃的高级皮靴,在她的薄底黑山羊皮鞋旁,坚决地迈着步子”[7]59、“他的眼睛是淡褐色的,眼睛里有橙色的小斑点,他头发像干草堆”[7]61。除了描述亚当外,小说对米兰达在病重时思想意识的描述也运用了停顿。如,当米兰达第一次得知自己身患流感时,躺在病床上的她一瞬间便开始了想象,而小说中却整整用了一页纸来描述她的意识动态,叙事时间在此处似乎趋于永恒。“她躺在床上,心里想,她看到过的人当中,只有比尔激动到一定程度……后来那许多声音变得只剩两个词儿,一起一伏,在她的耳旁叫嚷。”[7]75随后两处关于米兰达病重时思想意识动态的叙事,不但笔墨浓厚,甚至还使用了省略号来代替那无限长的叙事时间。“事先几乎一点也没有察觉,她飘进了黑暗,握着他的手,进入的不是睡乡,而是梦境[7]78”、“米兰达一边用她的脑子在回忆中摸索她从前学过的、用来称呼她没看到过和不认识的东西那些词儿,一边在想,遗忘是一个永远在原处旋转的灰色的漩涡”[7]81。
省略类型与停顿相反,是指故事时间无限长,而对应的文本叙事时间却很短。省略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对大流感的讲述上。小说中提到的大流感在现实中从1918年爆发至1920年结束,持续了2年,而大流感所对应的文本叙述在小说中却屈指可数。纵观整篇小说,瘟疫与流感字眼仅仅出现了7次。大流感何时爆发波特没有交代,读者直到小说后半部分才意识到流感在蔓延;对于大流感的蔓延情况,波特就仅有一句话,“他们派不出救护车,也没有床位,又找不到医生和护士,他们都忙得很,情况到处都是这样”[7]81。至于大流感何时结束,波特在小说结尾一笔带过,“不再有战争,不再有瘟疫了”[7]101。在现实中持续2年之久的大流感在文本中却像流星般短暂划过,其叙事时距之短甚至让读者忽略了瘟疫其实也是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
如果说内聚焦叙事视角和非线性叙事顺序的运用是波特作为一名叙事大师的有意安排,那么多种叙事时距的综合选择则是波特曾作为一名流感患者的本能所为。波特1918年不幸感染流感,曾连续9天高烧40度并一度病危,医生认为她很难活下来,家人甚至为她准备好了葬礼,但波特最终死里逃生,幸运地活了下来。然而在经历流感的折磨后,尚在康复阶段的波特却得知她的爱人——一名美国陆军中尉因感染流感而离世,这一噩耗让本就脆弱的波特陷入绝望,作为幸存者的她感觉不到一丝生的喜悦,世界犹如一片死灰。
根据波特的传记作家琼·吉文纳(Joan Givner)记载:“虽然波特从流感中康复,但这次经历对她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以至于她后来都不愿意回忆,直到18年后波特在瑞士的巴塞尔地区,阿尔卑斯山脉让她联想到丹佛的落基山脉和她的流感经历才让她以小说的形式讲述了那段她曾不为人知的经历。”[10]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认为:“讲述对于创伤患者是一种治疗行为,创伤痊愈的标志之一是患者能够讲述他们的故事。”[11]18年后,波特终于鼓足勇气希望借助讲述大流感来治愈自己的心理创伤。然而,从面对不同的事件采用不同的叙事时距可以看出,波特的这次心理创伤治愈过程并不顺利,在面对曾带给自己无尽痛苦的大流感时,她仍然无法释怀,内心充满挣扎,所以在文本中不愿过多提及大流感,以至于本该贯穿整个故事的大流感被一笔带过。她对过去仍然无法释怀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是,她的回忆更多地停留在大流感之外的事物,尤其那段她与陆军中尉美好的爱情往事,对应在文本中便是米兰达和亚当约会时的叙事时距被无限拉长,二人恋爱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波特刻画得无比清晰。连续9天的发烧经历也注定是波特无法摆脱的痛苦回忆,对应在文本中便是她对米兰达病重时思想意识动态的详细描述。因此,相比生理创伤,大流感给波特带来的心理创伤更持久且难以治愈。而波特的心理历程也是当时多数大流感亲历者的真实写照,大流感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创伤远甚于生理伤害。
四、结束语
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评论《灰色马,灰色的骑手》时曾说道:“波特在小说中极少提供可以为读者把握的外在现象,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她苦心经营,巧妙地把素材、主题、结构和风格融为一体的展现。”[12]小说对瘟疫的叙述完美佐证了这一评论。波特虽在文中极少提及瘟疫这一外在现象,但表层之下处处潜藏着对瘟疫的叙述,这种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的叙述便源于波特对叙事技巧的精心设计。固定内聚焦视角在为读者设置悬念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大流感的“狡猾”及其对患者躯体外在的打击;非线性叙事在增强文本真实性的同时,也让读者体会到了大流感对患者意识内在的冲击;而叙事時距间接呈现了大流感给患者造成的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因此,波特的瘟疫叙事技巧,在文本意义上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和可信性,在现实意义上则真实展现了瘟疫的可怕及其对美国人民甚至是世界人民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双重打击。总之,这种对瘟疫的“无声”叙述,无论是文本还是现实层面,都比直接的“有声”叙述更具威力。细读《灰色马,灰色的骑手》这部经典文学作品,波特在小说中对于瘟疫的“无声”叙述,无疑能够给后疫情时代的当代读者带来启示,具有浓厚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DEMOUY JANE.Elegy for Katherine Anne Porter[J].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1999(75): 504-510.
[2]骆谋贝.医学人文视角下《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疾病叙事[J].外国文学研究,2021(2):153-164.
[3]李健健.《灰色马,灰色骑手》中亚当的替罪羊形象之政治、宗教意义解读[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4]王亭亭.大流感、战争与创伤记忆:《灰色马,灰色的骑手》中的创伤叙事[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1):112-115.
[5]WALSH THOMAS F.The Dream Self in Pale Horse,Pale Rider[J].Wascana Review of Contemporary Poetry and Short Fiction,1979(2):61-79.
[6]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300.
[7]凯瑟琳·安妮·波特.灰色马,灰色骑手[M].鹿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8]PHILLIPS HOWARD,KILLINGRAY DAVID.The Spanish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21[M].New York: Routledge,2001:58.
[9]ALFRED BOLLET J.Plague & Poxes:The Impact of Human History on Epidemic Disease[M].New York: Demos Medical,2004:123.
[10]GIVNER JOAN.Katherine Anne Porter Conversation[M].Jackson: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1987:172.
[11]CARUTH CATHY.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 and History[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1996:4.
[12]GERNES SONIA.Life after Life:Katherine Anne Porters Version[J].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1981(4):669-675.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