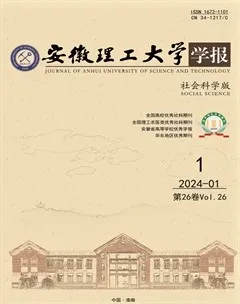技术义肢·知觉后勤·速度中心:维利里奥电影技术观
摘要:维利里奥常从技术维度思考电影的美学内涵,并关注到电影技术与人的关系,即电影如何综合运用技术询唤人的情感。维利里奥笔下的电影不仅融汇了各种技术,而且还作为人体感官的延伸,为人体源源不断地施以知觉力量。在此基础上,维利里奥进一步论述了电影的核心问题——速度,并将“速度”置于现象学维度上加以探讨。
关键词:维利里奥;电影;技术义肢;知觉后勤;速度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24)01004705
收稿日期:2022-05-12
作者简介:邓婷婷(1996-),女,重庆人,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外文学关系。
①1895年12月28日,《火车进站》的放映标志电影的诞生。
保罗·维利里奥 (Paul Virilio,1932—2018)是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媒介理论家,他思考电影的角度十分新奇且具有启示意义。
自1895年电影诞生①以来,关于电影本体的探讨便层出不穷:杜拉克认为电影是一门“视觉艺术”,德吕克认为电影的本质是“上镜头性”,巴拉兹认为“电影是一种文化”,巴赞认为电影是“再现完整的幻想”,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爱森斯坦认为“电影是一种语言”[1]。这些早期电影理论探索者将电影看作一个整体,关注电影的本体,却忽略了其他维度。尽管后期电影研究逐步涉及声画、剪辑、叙事等角度,但关注电影技术维度的理论家依旧屈指可数。让-路易·博德里首先关注到了电影的技术问题,并在《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一文中揭示了电影通过摄影机、放映机、银幕等基本电影机器产生的意识形态效果。丹尼尔·达扬在《经典电影的指导符码》一文中也将电影的剪辑技术放诸关键位置加以论述。然而,他们对电影技术的思考仅停留于技术作为电影的一部分如何影响人的情感,未将技术放置在电影的核心位置加以探讨。
保罗·维利里奥突破了上述研究局限,他将电影技术置于战场之上,使其在战场中展现出了独有的功能、性质。立足于此,维利里奥将电影技术从战场延伸至社会,将综合运用各种技术的电影称为人的“技术义肢”技术义肢是替代或补充正常身体机能的人造装置。(technical prostheses),并把电影技术与人体知觉相联系,体现出电影的“知觉后勤”特征。此外,维利里奥不仅聚焦于电影的技术层面,还探究了其本质问题,即“速度”。
一、作为“技术义肢”的电影
与以往研究电影的范式不同,维利里奥对电影的思考始终立足“战争”这一话题。1990年他出版了《战争与电影》(War and Cinema)一书,详尽地叙述了电影与战争的关系,尤其在视觉方面,力图展现出电影技术对战争视野的无限延伸。维利里奥从战争中看到电影技术对肢体的替代,并以“技术义肢”为其命名。
维利里奥描绘了电影技术在战场上综合运用的现实图景。首先,战场上影像技术是对“眼睛”这一感官的补充。利用热气球、风筝、鸽子、小型侦察机等工具连续拍攝影像捕捉敌方行踪、再现敌方远程场景的空中侦察技术,即是战争与影像技术的初期结合形式,它对人体器官“看”功能的延伸力度令人极为惊叹。同时,影像技术与武器的结合也能够极大地拓宽武器的辐射范围与精确度。“装载在飞机上的照相摄影机的窥视孔,作为一种间接瞄准的仪器,形成了对大火力武器瞄准镜的补充 。”[2]序20世纪以来,随着武器技术和信息科技不断地推陈出新,战争越来越讲求出奇制胜,在作战双方行迹更加难以捉摸形势下,战争便更需要影像来延长视线,将再现目标提升为瞬时呈现目标。其次,战场上影像技术也是对“耳朵”这一感官的补充。除了“看”,“听”也是战场上需要抢占的先机。在战争中声音技术能够促进信息交互,如录音技术的发展使情报的收集更为便利。交互系统中的“声音形成的综合性密码文件,发往欧陆各处,作为编成密码的情报……”[2]57,提供给战争中的情报部门。声音技术不仅能够促进信息交互,也能够缩短信息交互时间,便于决策者及时调整军事计划。20世纪初,法国古斯塔夫·费里耶法国科学家和军官,对法国无线电通信的发展作出了贡献。(Gustave-Auguste Ferrié)中校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上安装了远程无线电报天线,以保证军事单位与指挥中心无线电联系通畅,这极大地缩短了信息交互时间,抢占了战事先机。后来,他甚至把无线电系统放置于飞机上,实现了对空中炮火的即时性远程指导。
维利里奥关注到电影技术在战场上对人体感官的延伸,但他没有止步于电影与战争的历史性关系探索,而是用类比的方法将电影技术延伸至当今社会,更深入地探寻其运用形式。在维利里奥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结束”[3],而是以一种更隐蔽、更纯粹的方式伪装成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即“军事-工业集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4]。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披着“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外衣,将军事领域与工业领域融为一体的现代社会运行模式,这一模式已然成为当今世界的常规状态,电影技术也在“军事-工业集合体”中发展成为一系列“技术义肢”。
第一,影像技术延伸了视线,成为视觉的义肢。眼睛这一感官的“技术义肢”有不同的类型:眼镜、望远镜、电影、电视、手机等,这些各异的“技术义肢”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对视线有矫正或延长的作用。维利里奥在《视觉机器》(The Vision Machine)中对这类技术义肢有专门的论述,“视觉机器”[5](thevision machines)就是“技术义肢”在视觉维度的代名词,“它使得我们能够去修改或拓展我们看到的方式”[6]76。维利里奥指出,诸现象和可感诸相在光的照耀下显相,需要中介才能为视线所达及。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电子窗口成为人们观看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维利里奥精准地预测到当今社会人们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一块块屏幕,其中,影像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观看范围,提高了认知清晰度,是延长视觉的主要方式。但影像技术也有弊端,弊端之一是观看者也同周遭事物一同暴露在光线下,在“看”的同时也成为“被看”的对象。弊端之二是人们的“看”并不是自由的,而是被局限于机器中,因为这些视觉机器的目标是“把所有可能存在的矛盾逻辑都变得视觉化和技术化,并构建起一个空间,让计算机化的记录与图像的想法能够不断地升级和延伸。”[7]这一升级和延伸将使远程在场遍布现实世界,长期如此,人的视觉将被机器替代。
第二,声音技术可以成为听觉的义肢。广播、收音机、录音笔、电话等都可以作为听觉的延伸,它们通过技术方式使声音强度增大、辐射范围变广,以打破人体发音或听力极限。如,收音机可以拓宽受众范围,使远程到达成为可能;电话这一“技术义肢”的发明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它通过声音的瞬时传达,跨越空间的鸿沟,快速有效地传递信息。这些听觉的“技术义肢”消解了距离,其对“存在”的颠覆使哲学意义上的“人”也随之被消解。
战时电影技术的系统运用发展到今天,已然成为形态各异的技术形式,成为身体器官的诸多延伸,全方位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然而,维利里奥并不囿于研究电影技术对人体器官的延伸,他还进一步探究了综合运用各种技术的电影所产生的知觉力量。
二、作为“知觉后勤”的电影
电影技术不仅作为“技术义肢”外在于人,还作为“知觉后勤”向内影响着人的感官,为人体源源不断地传输知觉力量。电影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打破传统时空观,在视听维度建构电影内部时空以控制人的感知。
维利里奥用“知觉后勤学”[8]206(logistics of perception)一词概括电影技术对人知觉的影响,并认为它是人们依赖“技术义肢”的重要原因。他提出这一概念并将其放置于战争中加以论述,故本文也基于战争论述“知觉后勤学”一词的内涵。在军事领域中,“后勤”是指战争中的组织者运用各种手段调动武器、物资和人员,以维持前线战事需要的一种组织方式。同理,“知觉后勤”就是为感官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觉力量。从“知觉后勤”角度来看,电影技术不仅作为“技术义肢”外在于人,还逐渐成为人体器官的延伸,甚至是心灵的一部分。维利里奥认为电影是战争的“知觉后勤”,即电影能在知觉方面为战争提供持久作用于感官的“后勤”保障,为战争的胜利保驾护航。
首先,在战争中电影技术可以传递感知。在影像方面,电影技术可以是张贴在军营里的明星画报:玛丽莲·梦露是军人宿舍墙上贴得最多的“招贴女郎”,她的身体被给予理想化的上镜[2]61,通过可达到的视线制造出精神上的抚慰,为士兵的心智注入战斗的力量。传递感知的电影技术也可以综合运用于一部影片中:1934年希特勒下令拍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企图通过这部影片向全世界散布纳粹神话,以期赢得精神上的胜利。在声音方面,声音技术的瞬时传达可以被用来安抚军心:“人们甚至设想了一种‘无线电对话系统,让女性发话者以一种悦耳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来领导飞行分队,既为他们导航,也在他们执行任务期间进行抚慰。”[2]58
其次,电影的运作机制影响知觉。电影是根据视觉暂留原理运用摄影和录音手段把外界事物的影像和声音摄录在胶片上(数字电影除外),通过放映以及还原技术,在银幕上形成能表达一定内容的活动影像和声音的一种技术。观看者必须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观看荧屏,否则就难以动用视、听感官在转瞬即逝的时空中抓捕光影,而这就使观众坠入了电影编织的意义网络中,电影也由此影响到人的知觉。这一影响路径可以用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的“镜子阶段”[9]来阐释。人们观看电影,犹如回到“镜子阶段”,即6—18个月的婴儿在镜子前第一次看到自己,第一次有“我”的意识出现的时候。如同婴儿在镜子前构造出一个想象中的“我”,观影主体也在银幕前幻想一个想象的“我”,此时,观众的心理与婴儿几近一致。和拉康镜像阶段之镜一样,“银幕当然并不真的映照我们的身影,却能够成功地制造一种混淆了自我与他人、真实与虚构的状态,充分地唤起一种心理认同机制。”[10]因而,电影通过声音、影像、观影环境、剪辑技术等作用于人的感官并使人们回到想象界。
最后,电影技术的综合运用建立了一个供观众沉浸的虚拟空间样态,全方位地为人们传递感知。“摄影机复制了习惯性视野的状态……让观众在一个连贯完整的时间体块中产生一种身临其境(proxémique)的错觉。”[2]23这一“时间体块”是电影建构的,电影利用摄影技术、剪辑技术等缝合一块块零碎的画面与时间。一方面,电影的景深镜头复制了纵深的空间样态,以一定的画幅比例把现实世界的样貌展现在银幕之上。时间虽已流逝,但在已然逝去的时间刻度下,消失的空间样貌可被再次呈现,甚至反复呈现于银幕之上。银幕之上的时空不再是我们正在经历着的时空,时间的复制使人们感受不到时间的长距离流动,在静止的时空段里,人们感受着空间的固定性。另一方面,正反打镜头同样切割现实世界,它所呈现出的两帧画面在剪辑技术下展现某种相关性。通过某种叙述逻辑,电影利用正反打镜头能够将两个毫不相关的画面整合并体现出关联性,如,利用剪辑技术将拍摄于不同时间的两组不同的人脸特写画面,在同一时空呈现出互相凝视的状态。以上是电影投射出的影像带给我们视觉上的错觉,声音方面亦是如此。电影中的背景音乐本不属于常规化的生活,但音乐的加入不会使观众感到突兀,相反,在音乐的渲染下观众更易沉浸其间,并与之产生共情。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技术的综合运用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观,它通过视听语言构造出全新的电影内部时空。电影可以穿越时间的束缚、空间的限制,在古代、现代与未来中穿梭,在想象中遨游,电影技术便以此影响人的知觉。
维利里奥告诉我们,电影对个体的侵袭不只局限于对其视、听感官的延长,还由外至内地影响着人的知觉。当人们通过电影进入到有别于现实的时空,即拉康笔下的想象界时,电影就作为“知觉后勤”为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觉力量。
三、以“速度”为核心的电影
维利里奥对电影的探究并未简单停留于技术以及技术与人的关系层面,而是更为深入地思考电影的核心问题。他认为“速度”是电影的核心,“速度”主要体现为电影马达的速度和电影带来的竞速观看。此外,他还进一步将“速度”放诸于现象学思维中寻找其本质。
维利里奥强调电影是速度的产物。其一,马达的速度造成电影的光影交替,这是“电影背后的支配性力量”[8]203。电影工业将电影帧率标准定为每秒24帧,即每秒钟放映24格胶片。静止的胶片在马达的加速中移动,与人眼的“视觉暂留”(Persistence of vision)和“似动现象”(phi phenomenon)原理一同构造出连续的电影画面。“视觉暂留”指眼前的物体被移走后不会立刻在眼前消失,而要在视网膜上停留0.1到0.4秒。正是人眼的這一特性,使电影每一帧影像的间隔时间被眼睛忽略。似动现象诱使观众从心理上将本来逐个放映的静止画面,“视”为连续性运动,进而使静止的影像在一定速度上显现出动态的效果。因此,马达的速度是电影显相的关键。其二,电影带来一种“竞速观看”(Dromoscopy)。眼睛为了适应马达的速度,随之产生一种视觉上的速度,即竞速观看。速度决定事物向我们显现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它决定了事物的形态,因而“竞速观看”之物以一种“认识形体”出现[6]39。维利里奥认为:“伴随着加速度,旅行就如同是拍摄影片。”[11]我们观赏汽车或火车车窗外的风景,如同观众凝视电影银幕,也就是说,人们在速度提升下的所见之景与电影影像传输给我们的景是一样的,即电影在高速中源源不断地传送并引起视觉奇观。此外,维利里奥还认为竞速复制下的事物只能短暂地显现出奇特的状态,他用“伪像”(simulacra)[12]来描述这一状态下诸事物在视觉上的短暂显相。这里的“伪像”与原件相比,是一种虚拟影像。电影影像便是一种伪像,即真实世界在竞速状态中所呈现的虚拟幻像,是光作用于人眼之像,是一种假象。当机械化速度消失后,即马达不再加速后,电影的光影将不再变幻,呈现出静止状态。
维利里奥将“速度”概念放置于现象学领域,着重思考“速度”与人类感知的变化、肉身所处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速度”与人类感知密切相关,“速度”提升后,事物状态的变化首先展现在视觉体验上,继而再作用于其他感官。身体所感知到的空间严格局限于可感显相的世界,因此速度在这个可感空间中表现为加速或者减速。伊恩·詹姆斯在《导读维利里奥》中认为,速度-空间(speed-space)不是由密度、重力、体积等维度构成,而是以“速度”为尺度建构的空间样式。在这个空间样式之中,所有呈现之事物都是竞速复制下的假象,是经过速度这一中介存在于视域中的显相元素。维利里奥强调,虽然“速度”立足现象学,但其本身不是一种现象,而是诸现象之间的关联,一种连接主体与诸显相之间的桥梁[6]42。在传统认知中,速度是空间内物体的移动速率。但这个认知有个前提,空间概念是物理学或化学领域中的范畴,具有物质性和广延性,非维利里奥笔下的速度-空间。速度不只让人们更快速地移动,“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能够去看到、听到、知觉到,从而更密集地(more intensively)构想当下世界”[13]。竞速可以带来事物在视域中存在样式的改变,同样也可以带来人感知世界方式的改变。在这个竞速世界,事物在不同的速度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为处在静态下的感官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维利里奥借电影告诉我们:“技术,不过是速度的表象,速度,才是技术的本质。”[14]现代世界看似以技术为主导,但其核心是“速度”。甚至现代社会的一切学科,诸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归根到底就是“竞速学”,是关于“速度”的竞争。
四、结束语
在维利里奥看来,电影从身、心两个维度作为人的延伸,无论是直接经验世界,即作为“技术义肢”的电影,还是间接感受世界,即作为“知觉后勤”的电影,都需要技术作为人与世界的媒介。此外,技术控制下的电影,无论是竞速复制的假象,还是感知的求新,都使我们开始用“速度”维度去衡量它。
参考文献:
[1]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9.
[2]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M].孟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PAUL VIRILIO.Bunker Archeology[M].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1994:58.
[4]郑兴.不合时宜的军事空间[J].读书,2018(3):167.
[5]保罗·维利里奥.视觉机器[M].张新木,魏舒,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5.
[6]伊恩·詹姆斯.導读维利里奥[M].清宁,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
[7]约翰·阿米蒂奇.维利里奥论媒介[M].刘子旭,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78.
[8]郑兴.“速度义肢”“消失的美学”和“知觉后勤学”:保罗·维利里奥的电影论述[J].文艺理论研究,2017(5):201-208.
[9]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4.
[10]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7.
[11]保罗·维利里奥.消失的美学[M].杨凯麟,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150.
[12]PAUL VIRILIO.Negative Horizon[M].London:Continuum,2005:115.
[13]PAUL VIRILIO.Open Sky[M].London:Verso,1997:12.
[14]PAUL VIRILIO.Speed and Politics[M].New York:Semiotext(e),1986:46.
[责任编辑:吴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