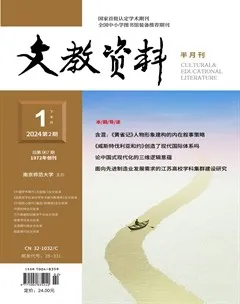“哀者歌其事”: 《诗经》中的农业劳动者形象建构
程雁
摘 要:《诗经》诞生于农耕文明时代,是农业劳动者艰难生活的烙印。它将民间的世俗风情和农民的劳动状态引入诗章,描绘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及其生活心态。换言之,《诗经》把农民生产劳作、日常生活与情感心理勾连起来,放置于乱世社会的诗性表达之中。《诗经》建构了贫苦而坚韧的农业劳动者形象。劳动者负担统治者暴敛的重负与繁重的徭役,面临灾荒与战争的威胁,谱写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哀歌。这彰显出《诗经》中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内蕴。
关键词:《诗经》;农业劳动者;现实主义;形象建构;诗性表达
学界公认《诗经》成书于农耕文明崛起的时代,其作品“在道德观念与审美情趣上打上了农业文明的烙印”[1]。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是农业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与农耕文化发展的推动者。他们在农耕经济缓慢发展的过程中,忍受着赋税徭役的压迫,时刻面临无妄之灾(包括天灾与人祸)的威胁,难以挣脱饥饿的枷锁,用坚忍与幽怨唱出了一曲曲哀而不伤的歌。本文基于《诗经》对农业劳动者形象的描述,辨识其形象的成因及社会文化意义,并探讨这一诗性所书写的现实主义精神内蕴。
一、《诗经》中农业劳动者命运的普遍性
“风”是当时对地方音乐的称呼;《国风》是从《诗经》时代各地诸侯国广泛搜索集成的,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唐代孔颖达在解释“风”的时候指出:“国风之音,各从水土之气,述其当国之歌而作之。”[2]朱熹亦言:“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3]《国风》浸染了民间世俗风情,再现了民众的悲欢离合与平凡曲折的生活。
《诗经》中能表现这一点的诗章如《曹风·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於我归处。”[4]蜉蝣是一种朝生暮死的昆虫,此处借蜉蝣悲叹生命之悲苦、渺小。再如《曹风·下泉》曰:“忾我寤叹,念彼京周……四国有王,郇伯劳之。”[5]伤感周王室之衰微,怀念往昔之盛世。又有《王风·兔爰》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6]感叹生活在这样动荡的年代里,不如长睡不醒。愤慨之情溢于言表。傅斯年先生解此诗曰:“遭时艰难,感觉到生不如死。此《诗三百》中最悲愤之歌。”[7]《诗经》时代,正值社会转型期,奴隶制逐渐走向崩溃,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饥馑、瘟疫、剥削和压迫使百姓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从心底生发出人生竟不如短命的蜉蝣的悲叹,可哀,可愤,可叹。这些诗在一定高度上,对底层农业劳动者的悲剧命运进行了宏观描述,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人文关怀与写实精神。
二、《诗经》中农业劳动者贫困的具体成因
(一)剥削者的横征暴敛
《诗经》时代,剥削者对劳动者残酷压榨。《魏风·硕鼠》以硕鼠比喻贪婪的剥削者,字字滴血,斥责了统治者竭力搜刮民脂民膏,丝毫不顾百姓死活的恶行,控诉不公平的社会,表达了百姓强烈的不满和怨恨。尤其是诗末尾两句“乐郊乐郊,谁之永号”[8],展露出现实的黑暗与生活的穷困。在此情形下,劳动者萌发出要离开剥削之地,找寻安居乐业的理想栖息地的美好企盼,让人悲愤又无奈。
《魏风·伐檀》也有同样的思想倾向。其中的“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9],生动地刻画出这样的一幕:汗流浃背的伐木者们在河边挥舞着工具伐木造车,面对水中轻缓的波浪即兴而歌。好一幅热烈、激扬的劳作画面!但伐木者们的心却是无助的、冷漠的。因为彼君子“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却能“取禾三百亿”,[10]庭有县貆、县特、县鹑,百姓怎能无怨?
被称赞为“《诗经》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的《豳风·七月》一诗,从春耕写到夏忙,从秋收写到凿冰,以时令为顺序,详细地描绘了先秦时代的农耕生活,朴实无华,深刻淳真。其中有因贫苦而产生的哀怨:十一月北风紧,十二月冷森森,“无衣无褐,何以卒歲”“穹窒熏鼠,塞向墐户”。[11]严冬时节堵好墙洞熏老鼠,关闭北窗封涂门户,以抵御寒风,居室何其陋也!更凄惨的是他们八月里摘葫芦,九月里收麻子,到头来却只能又采苦菜又砍柴,靠那些粗糙的野菜果腹。陈子展说此诗是“关于奴隶们一年四季怎样为奴隶主(公与公子)从事耕种生产而自己却过着挨饿受冻的生活的最古老最详细而又最真实可靠的韵文记录”[12]。诗中还有“我朱孔阳,为公子裳”[13],映射出一种无奈的哀怨。此外,诗歌还描写了秋收过后几次小规模打猎和大规模狩猎,但小规模打猎如“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是要“为公子裘”[14];大规模狩猎所获得的“言私其”要“献于公”[15]。这反映了劳动者与剥削者生活的悬殊,显示出剥削者对劳动者的盘剥,积郁着劳动者对剥削者不劳而获的不满。
(二)灾荒的无情冲击
《诗经》时代是“靠天吃饭”的时代,古人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远不及现在,天灾会使劳动者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从维护统治与自身形象出发,古代稍有“仁心”、稍微“圣明”的统治者都会关注灾民。《诗经》里有不少描写统治者救灾、祈雨的篇章。但需要指出的是:一场灾难若引起了统治者足够的重视,必然已经对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破坏。例如饥荒若受到统治者极大关注,必然已经使民众流离失所,饿殍遍野。
证之于《诗经》,则有《小雅·鸿雁》一诗。其诗第一节说:“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16]漫漫原野,矜寡孤独之人举目即是。再对比统治者救灾的行动,便可知灾民之浩荡、灾情之严重,不禁让人哀叹民生多艰!
战乱导致的灾荒是致使劳动者贫苦加剧的原因之一。《小雅·苕之华》第二节说:“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17]《毛诗序》认为这首诗的旨意为“大夫闵时也”,“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18]。战乱频繁,使人发出不如不降生的哀叹,足以见得民众食不果腹,困苦异常。
旱灾是古代农耕社会的重灾,可以对农作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使无数劳动者破产。就连不可一世的统治者逢天旱时也要跪天祈雨。《大雅·云汉》第三节言“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周余黎民,靡有孑遗”[19]。天降荒旱,灾满人间;万物焦枯,存者悲苦。第五节又说“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20],大地像被烈火焚烧,庄稼难以存活。剥削者尚有往年存粮,劳苦者何以为食?统治者怕饥民暴动,统治不固,便祈祷雨露。《毛诗序》言此诗乃“仍叔美宣王也。宣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似有理据,但说“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21],则有牵强附会之嫌。陈子展言“宣王元年以邵穆公为相。是时天大旱,王以不雨遇灾而惧,整身修行,欲以消去之。祈于群神,六月乃得大雨。大夫仍叔美而歌之,今《云汉》之诗是也”[22],强调了宣王欲复兴王化之状;然而全诗中赤日炎炎,哀鸿遍野,哪里得见“天下喜于王化复行”?大夫自然歌颂其王,而民众已遭旱灾,损失惨重,岂因一雨骤降而民众安乐乎?岂因一雨骤降而压迫不存乎?傅斯年认为此诗为“丧乱之音”,“恐亦是东迁后语,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故曰:‘天降丧乱,饥馑荐臻。”[23],甚为精当。
鼠灾也给劳动者埋下饥贫的种子。在《魏风·硕鼠》里,劳动者把剥削者比喻成贪得无厌的硕鼠。只有深切体会过硕鼠的危害才会有这样饱含愤怒的比喻。郭璞认为硕鼠“形大如鼠,头似兔,尾有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24],是破坏庄稼的“能手”,劳动者普遍深受其害。
此外虫灾亦频繁发生。《小雅·大田》第二节谈及劳动者在田间灭虫的辛苦形象:“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25]陆玑认为“螣”是蝗虫[26]。朱熹对此解释得更清楚:“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皆害苗之虫也。”[27]诗里还说“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这从侧面表现出劳动者对虫灾的愤恨与畏惧:害虫何其多也,须用烈火焚烧。由此可推测出当时劳动者所拥有的田地并不太好,杂草丛生,距河流也比较远。
根据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劳动者年谷不登,日常家庭生活难以维持,时常发生挨饿忍饥之事。忍饥不免困乏,困乏无力使家庭破产,于是劳动者沦为穷困者。这是普遍现象,也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个逻辑怪圈贯穿《诗经》时代始终,贯穿《诗经》中劳动者的一生。
(三)繁重徭役与残酷战争的破坏
《诗经》时代,夷狄交侵,国势动荡,征伐频仍;加之鲜有体恤民力的统治者,杂役、力役与军役异常繁重,而且没有固定期限,多为随意性征发,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王风·君子于役》通过思妇苦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28],表露出无休止的征役给百姓带来的痛苦。《秦风·小戎》也流露出“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29]的忧伤。《小雅·绵蛮》更是详述了劳动者服役的辛苦:“道之云远,我劳如何!”“岂敢惮行,畏不能极。”[30]情真意切,反映了某一时期统治者对普通劳动者役使之沉重,缺乏必要的关怀。《魏风·陟岵》也饱含对长久服役的怨恨之情与对还乡共享天伦的渴求。《毛诗序》言此诗乃“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国迫而数侵削,役乎大国,父母兄弟离散,而作是诗也”[31]。不义战争使民众超期服役,生死难料、疾痛惨怛之时,既呼桑梓,便欲还乡,然欲还却不可还,不能侍亲而终,不能守妇育子,何其悲哉!方玉润对此诗的评价更为详尽:“人子行役,登高思亲,人情之常。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纵千言万语,岂能道得意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32]无论是父母思子还是子念双亲,都是同一种情感。这样的美好思念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周南·汝坟》中思妇坦言“未见君子,惄如调饥”[33]。闻一多先生认为“调饥”谓性欲之饥,单称饥若食,乃“调饥”“朝食”之省。挖掘至人性深处,惊世骇俗。诗中“王室如。虽则如,父母孔迩”[34],以烈火喻王室苛政,生动贴切;因父母需要赡养,故强调丈夫不应离家。这昭示出王室劳役造成了劳动者家庭分散的不合理现状。《邶风·式微》描写被征发徭役的劳动者的怨忿达到了高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35]征役使民众厌恶,激起天怒人怨。《召南·草虫》《卫风·有狐》《卫风·伯兮》《邶风·雄雉》均是女子思念征夫的哀怨之曲;《邶风·击鼓》与《王风·扬之水》是征夫思家念妻的幽怨之歌;《周南·卷耳》一诗则把思妇的心与想象中征夫的行动融于一体,一唱一和,一吟一咏,一声爱一声怜,一声思一声念。“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36],思妇睹物思人,情寄丈夫;“陟彼高冈,我马玄黄”[37],征夫登高怀远,挂念妻子。乱离时代竟有此纯洁凄美的清音,真令人欣慰、喟叹——如此坚贞浪漫的爱情因征役被山水阻隔,从深厚之感情越发衬托出现实黑暗。
再者,战争对农家生活的破坏也是致命性的。《豳风·东山》借一个经历了东山战场而幸存的征卒之口,讲述了战后田园荒芜、家乡残破的景象,暗寓战争粉碎了安定的农家生活。《豳风·破斧》则既写出了繁重徭役的可憎,又写出了残酷战争的可恨,艺术感染力极强。前两句以“既破我斧,又缺我斨”[38]起始。斧、斨均为生产工具
却因为四国之君长年累月服役而残缺,家计亦处于困苦中。末四句言“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虽然周公征服了四国,但无数战士裹尸沙场,幸存者亦背井离乡,何其哀也!傅斯年先生在解释此诗时言:“周公东征,虽功烈甚大,而民亦劳苦。此实哀诗。”[39]即便英明如周公,即使是正义的平叛战争,也不可避免地对劳动者生活造成破坏,更别提其他君侯发起的非正义战争了。
总之,《诗经》中的劳动者常常被迫去服兵役与劳役,过度的徭役使家庭劳动力不足,耕作时间受限,进而影响收成与收入,使劳动者在贫困的边缘徘徊、挣扎。而苛重的剥削与天灾人祸更使他们难以招架,最终陷入贫苦的沼泽中难以自拔。《国风》中有劳动者拼命做工而衣食匮乏的记载,《小雅》中有劳动者饥不择食的悲愤倾诉,《大雅》中有民众受尽灾苦的哀号……这些诗歌反映出《诗经》中贫苦劳动者的普遍心声。
三、《诗经》中农业劳动者形象与现实主义意蕴
《诗经》竭力运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通过描绘贫苦劳动者的形象,再现劳动者的真实生活。可以说,这类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决定了其必须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来阐述生活,表达生活。这些诗篇多取材于劳动者生活与社会现实的密切结合处,是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高度统一的产物。
(一)主观与客观的完美统一
贫困劳动者的主观意识与思想感情乃为现实所激发,与客观历史背景相符合。这是该类诗比较显著的特点。如《王風·兔爰》,通过控诉自己悲惨的境遇,揭示了当时动荡的社会背景。陆侃如先生与冯沅君女士亦认为此诗为“伤乱之作”,并引崔述《读风偶识》的推测:“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家室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40]无论具体年代为何,此诗用意是泣诉乱世中“家室飘荡”,实是无疑了。生活不安定,便无固定耕作之地;既无生产资料,何以养家糊口?自给自足尚难,何以应对剥削?既难逃过苛政,生活如何不贫困?主观心理状态与客观社会背景达到了和谐统一。
(二)对贫苦劳动者生活的典型艺术概括
选择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如《豳风·七月》中那个辛苦的农夫自述的“凄惨动人”的生活感受,与千万个底层劳动者相同或相似。如《唐风·杜》里描写的流浪者哀呼“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41],悲叹自己孤苦伶仃,内心无比伤感。这种哀呼具有深远的现实内涵——此流浪者即彼流浪者,彼流浪者即一切流浪者,一切流浪者都是贫苦劳动者。
(三)颇具匠心的细节描写
现实是细节中的现实,细节是现实中的细节。捕捉最富于表现力的、最能够显示事物本质与人物心理的细节,是充分表达现实的一大技巧。这一点在这类作品中集中表现为思妇所流露出的个性化心理。如《周南·汝坟》与《王风·君子于役》,通过思妇的内心独白,充分表达了其对长期远役在外的丈夫的无限思念和对家庭团聚的期待之情,真实而又自然贴切。
(四)多采用起兴手法
起兴手法的运用能增加诗的真实感与亲切感,让人易于联想,入乎诗中,找到与心灵产生默契的结合点,从而达到心灵共鸣。如《桧风·隰有苌楚》一诗,以“隰有萇楚,猗傩其枝”起兴,羡慕“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42],感慨苌楚(阳桃)无牵无挂,无知无欲,对比自己经历的贫苦与承担的重负,沉痛至极。再如《小雅·苕之华》第一节以萎黄的凌霄花起兴,感伤生逢乱世;第二节以叶子青青的凌霄花起兴,对比自己贫窭的遭遇,悔恨“知我如此,不如无生”。又如《唐风·鸨羽》先是以性不树止的鸨鸟集于栩木起兴,比喻自己征役的悲愁;接着诉说自己为王事奔走不停,“不能蓺稷黍”,担忧“父母何怙”[43],加深了情感抒发的强度,悲婉愤激,催人肝肠。这些皆与社会现实相呼应,勇敢而全面地再现了贫苦大众的生活。
四、结语
《诗经》对贫苦劳动者形象的塑造,无论是在选材上还是在艺术创作手法上,都蕴含了广泛而深刻的现实主义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是贫苦劳动者铸就的,是在广袤的沃野与无限辛酸的生活中孕育的。它来自在陡峭的山岭中采药、在汹涌的江水中捕鱼的生活现实。它是干旱季节里那片剩余的绿叶,亦是洪涝时节里那棵永远挺拔的树。
《诗经》中描绘农业劳动者形象的作品,实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章。从人文现实意义上讲,它是深深根植于劳动者心中的悲苦所迸发出的火花。其作品大到阶级矛盾,小到家庭生活,展现出广阔的生活画面,有着极其厚实的生活基础。其所蕴含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激励着后世心怀“古仁人之心”的志士树立关注民众疾苦的崇高信念,以及对这一至高理想的不懈追求。
参考文献
[1]袁行霈,聂石樵,罗宗强,等.中国文学史:第1卷[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54.
[2][18][21][3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 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945,1192,367.
[3](宋)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
[4][5][6][8][9][10][11][13][14][15][16][17][19][20]
[25][28][29][30][33][34][35][36][37][38][41][42][43]褚斌杰.诗经全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67,170,84—85,128,127,127,172,172,172,172,223,327,401,401,295,81,144,324,12,12,43,5,6,181,135,164,137.
[7][23][39]傅斯年.傅斯年诗经讲义稿笺注[M].董希平,笺注.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157,88,203.
[12][22]陈子展.诗三百解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563,1052.
[24][26](清)徐鼎.毛诗名物图说[M].王承略,点校解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05,163.
[27]高明乾,佟玉华,刘坤.诗经动物释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5:37.
[32](清)方玉润.诗经原始[M].李先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46.
[40]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