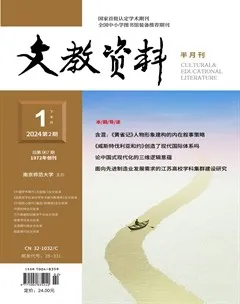《史记·商君列传》三家英译本对比分析
贾芹 吕鑫岚
摘 要:本文概述了《史记》的华兹生、倪豪士、杨宪益三家英译本的基本情况,以《史记·商君列传》为例,从古汉语的视角就其中的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出现的翻译问题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为中华典籍外译工作抛砖引玉。
关键词:华兹生;倪豪士;杨宪益;《史记·商君列传》;语言对比
中华典籍翻译始于公元5、6世纪,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典籍译者,特别是西方汉学家群体,为中国文化传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史记》作为集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为一体的伟大著作,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史记》的域外传播最初起于东亚,于 18 世纪传入
俄国,于 19 世纪中叶有了德文译本和法文译本。本文所研究的《史记》三家英译本分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
《史记》选译,八九十年代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翻译的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及其团队的《史记》译本,70年代杨宪益、戴乃迭所翻译的《史记选》。以下分别简称华译、倪译和杨译。
一、三译本基本情况
华译《史记》(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于 1961 年和 1969 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两度出版,
并于 1993 年修订完再次出版。在汉代的两卷中,华兹生打破了《史记》原著按体例排列的顺序,而是按照时间的顺序重新排列文章内容,使得人物出场顺序和事件发展相吻合,人物及叙事内容更加清晰,保证了译本所述内容自身的完整性,突出了《史记》文学方面的成就。而且华兹生尽量避免在正文后附加注释,将有些不得不向读者解释的内容融入正文中,在不打断读者阅读的同时增强文章的连贯性,这一点受到很多学者的赞扬。华译的目标读者定位是英语国家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而不是专业历史学者,所以华译《史记》具有非常强的可读性。
倪译《史记》(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1994年出版了第一卷,后来又出版了七卷,其团队的翻译工作如今还在继续着,尚未全部完成。倪译将精确性放在首要位置,而将可读性放在其后,因此其译本具有史學研究的严谨性。倪译有翔实的注释。注释内容主要包括文字的训诂,中国古代地名的考证,历史人物的介绍,中国古代礼仪、习俗、典章制度的文化知识背景说明,中国后世学者对《史记》的研究(如《史记索隐》《读书杂志》等历史研究以及近现代研究)。每篇文章的最后还附有“translators note(译者注)”,用于记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现存译本书目、中外研究成果、自己对于此历史事件的立场看法以及一些其他尚存的问题等。倪译团队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具备丰厚的学术基础。
杨译《史记》(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于1974年由香
港商务印书馆出版,选取了《史记》中31 篇较为著名的篇章。2001 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 Selections from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史记选》),内容为从 1974 年版本中选出的18 篇,译文简短朴素,几乎没有注释。华译和杨译都是选译,不是全本翻译。
二、《史记·商君列传》三译本对比
本节以《史记·商君列传》为例,从古汉语的视角就《商君列传》三家英译本:华兹生的The Biography of Lood Shang[1]、倪豪士的The Lord of Shang[2]和杨宪益的Lord Shang[3]中的词汇、语法等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对比分析,希望为中华传统典籍外译工作跨越学科界限、增加研究维度抛砖引玉。
(一)词汇
1. 人名、地名
对于汉语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不同译者采用了不同的记音符号系统。华译全部采用现
代汉语拼音,某些地方存在错误,如“杜挚Chi”“黾 Min 池”“商於 Yu”等。倪译则全部采用威妥玛拼音,如“秦 Chin”“孝 Hsiao”。威妥玛拼音是一套由英国人创造的用于拼写中文语音的记音符号,它的拼写方法接近英文,在不需要声调符号的情况下就能达到接近汉字读音的目的。而杨译则将威妥玛拼音和现代汉语拼音混用,如同时存在“秦 qin”和“戎狄 ti”,这样可能会给国内外读者带来一定的混淆。
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字——两个字只有读音相同,形体和意义完全不同,这对于只能记录语音的记音符号来说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卫” 和“魏”:华译和倪译使用“wey”“wei”两种注音方式加以区分,两者都给“wey”加了具体的注释,倪译不仅在“wey”和“wei”后面标注了汉字,而且对卫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做了简介;华译侧重点在于解释卫和魏的区别;但杨译均使用“wei”,且没有相关注释,难以区分,容易给外国读者造成困惑。这或许是中国学者进行外译时需要普遍注意的一点。
2. 官职、制度
原文中有大量官职名称,如“中庶子”“左庶长”“大良造”“五羖大夫”等。这类中国古代的专有名词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对应词汇,因此无法进行简明的解释,但至少在同一个版本中应保持翻译的一致,不至于使读者对同一个名词产生疑惑。华译将“左庶长”和“大良造”直译为“the rank of zuoshuzhang”和“the rank of daliangzao”,在后面的注释中对秦国的爵位等级制度进行解释,并说明该爵位所在的等级。倪译尽量在原文中进行简单的字面意思翻译,并在注释中标注威氏拼音和汉字原文。如倪译分别将“左庶长”和“大良造”译为“Left Chief of Staff”和“Grand Excellent Achieve”,同时在注释中标明“Tso Shu-chang 左庶长”“Ta Liang-tsao 大良造”。然而,在同一语境中,同一个官职“中庶子”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译法:“Counselor of the Palace” 和“Household Headmaster”,这样翻译就缺乏了一致性,会给读者带来疑惑。杨译试图将这类古代的专有名词转化为现存的对应或相近的英文名词,但并没有对此进行严密的解释,如其将“左庶长”译为“adjutant general”,事实上,这是一系列二十个贵族等级 (爵) 中的第十位,头衔是根据国家为其提供的服务而授予的,并不承担任何明确的官方职责,但同时杨译又把“大良造”译为“the
sixteenth rank”。
关于古代典章制度,也是翻译中一个绕不开的难点。如“相牧司连坐”,其中“牧司”为监督举发,“连坐”为一人犯法,有关的人连带治罪。华译“mutual surveillance and mutually responsible before the law” 和倪 译 “each member of the group guiding and watching the others and responsible for others crime”,虽然有所解释,但“连坐”作为法制史上的一个特定词汇 并没有被准确地表达出来。而杨译直接用“mutually responsible for each other”来概括,似乎也缺失了一点内涵。
典章制度有时在正文中很难解释清楚。“为田开阡陌封疆”意为废除井田制,重新划分田塍的疆界。华 译 “the ridges that marked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elds under cultivation were opened up”,没有具体解释清楚“井田制”的概念。倪译 “ [wey yang] marked out fields,removed the raised paths and boundaries balks in the fields”,他对于此类情况会给一个注释,注释中说明了“阡”“陌”为田间小路,“阡陌” 合在一起作为一个词语,指的是“田界”。杨宪益掌握了一定的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知识,所以此处表达相对准确:“the old boundaries between the fields were abolished”,但相较于倪译的注释,还是不够全面。
3. 数词、量词
古代汉语的数词在大部分情况下和现代汉语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时候一些整数并非代表实际数目,而是泛指数量多。俗语“三过其门而不入”是指路过家门的次数多,而非恰好路過三次 。“八戎来服”的“八”也是泛指边疆地区各个少数部族及其他小国家,并非具体指八个民族。华译“eight tribes of rong”(即“八个戎族部落”),和倪译“eight Jung”都错误地理解了“八”;只有杨译“even barbarians submitted to his rule”最接近原文意思,符合古代汉语中用特定数词表示概数的用法。
相较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量词是不发达的,
但并不代表没有量词。“十金”到底是多少金子,就表达得比较模糊,那么就要根据当时国家统一的度量衡单位进行判断。在汉代以黄金一斤为一金,那么“十金”就是“十斤黄金”。华译译为“ten pieces of gold”(十块金子),倪译“ten chin”将“金” 作为一种货币单位,杨译则译为“ten gold pieces”(十枚金币)。这都是由于缺乏古代历史文化背景而造成的错误译法。
4. 古今异义词
古今异义词也是翻译的一个难点,如果不具备相关知识,很容易以今义当古义。“去之魏”其实是三个词,“去”在古代汉语中是动词“离开”,并非现代汉语的“到……去”,“之”是动词“到”。华译“he left Qin and went to Wei”,准确翻译出了两个动词的意思,并且把省略的宾语“秦国”补充完整。倪译“he left for Wei”和杨译“he went to Wei”都只说了商鞅动身前往魏国,就忽略了“去”的含义,混淆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去”的意思。
古代汉语中,“山”“河”有时是具体特指某一座山、某一条河,发展到现代后,词义才有所扩大,泛指山岭和河流。例如,“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中的“河”特指“黄河”,“山”特指“崤山”。华译“the Yellow River marks the border between it and Qin,but it alone is able to enjoy the advantages of the area east of the mountains”,只注意到了“黄河” 而忽略了对“山”的特指。倪译“it borders Chin along the Ho[River],but it monopolized the profits from the East of the Mount”,将这两个词语的首字母大写,显然译者知道“河”和“山”都是特指,但是他并没译出具体的指代内容。而杨宪益作为中国学者,其译文“For they lie west of the mountains with their capital at Anyi,separated from us by the Yellow River but possessing all the advantages of the east”,也只翻译出了“黄河”而没有指出“崤山”,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
5. 敬辞、谦辞
古代汉语中,称呼常可以不用人称代词而使用敬辞、谦辞,如称自己为“寡人”“不谷”“小人”,称别人为“君”“子”“陛下”等。因此,在赵良的话中,“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意思是“我要是接受了您的情谊,恐怕那就是我既贪位又贪名了”。华译 “If I were to heed your suggestion” 和 杨 译 “Were I do as you ask,sir”,用 I 和 you 对译“ 仆” 和“ 君”,都不如倪译“If your servant were to heed your lordship” 中 用 “your servant”和“your lordship” 翻译“仆”和“君”更能体现出谦卑和尊敬的意味。
(二)语法
1. 语态、时态
英语中有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汉语的被动句分为有标志的被动句和无标志的意念被动句。被动
句标志包括“于”“见”等。文中出现的被动句如“汝可疾去矣,且见禽”“见非于世”“见敖于民”等都是典型的有标志的被动句,翻译为英文应该用相对应的被动语态表示。这三句对应三位译者的译文分别为:华译“you had better hurry on your way before you are arrested”“except the censure of the age”“he is bound to rouse the animosity of the world”,倪 译“You can fly quickly,or you will soon be taken” “are naturally abused by their age”“are sure to be despised by the common folk”,杨 译 “You must leave without delay”“or you will be caught”“are condemned by the world、are mocked by the mob”。可见,华译只有部分内容翻译出了这种语法形态,在翻译“见非于世”“见敖于民”时,他将被动语态转换成了意思相近的主动语态,忽视了语法上的对应。倪译和杨译对语法形态的把握和翻译都是相对准确的。
无标志的意念被动句如“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从主语和谓语的关系来看,应该理解为“被限制、被局限”。华译“stupid men are constrained by them...unworthy men merely cling to them”,依然存在上述问题。倪译“...he simple are bound by them...the inferior restrained by them”相对准确。而杨译“...the foolish keep them...the foolish are bound by them”显然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意念被动句,只有后半句是按照被动语态翻译的。
语法范畴中的“时”表示动作行为和时间的状态,汉语借助虚词来表示,例如“且见禽”的“且” 表示将要,对应英文的将来时。华译“you had better hurry on your way before you are arrested”忽略了时态的对应。倪译和杨译都用了“will”,是相对准确的译法。
2. 词类活用
古代汉语中有大量的词类活用现象。名词放在动词的前面,它不是动作行为的实施者,而是对动作行为起着直接的修饰限制作用,从而担负起形容词、副词的语法功能,充当了修饰谓语动词的状语,即名词作状语。“日以削”是时间名词作状语,意思是“一天天地”。华译和倪译使用了相应的副词“daily”或短语“from day to day”,而杨译则译为“his territory was dwindling away”。“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中的“西”和“东”都是方位名词作状语。华译和杨译将“西侵秦”译为“marches west to invade”,状语和谓语形成状中关系;而将“东收地”
译为“...the lands to the east”,即“收回东边的土地”,这就构成了动宾短语,与原文的语法结构不对应,另外,原文是相同的句式,而译文则用了不同的句式。倪译“invade Chin in the west”“guard its land in the east”,将两处都译为动宾短语,也都未遵循原文的语法结构。
形容词的意动用法不是说使得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具有这个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或状态,而是主观上认为他具有这种性质或状态。“民怪之”中的“怪”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意为“人们对这件事感到奇怪”。华译“The people were suspicious”和杨译“The people were sceptical”,都是用一个系表结构来代替动词;倪译则直接选用相应的动词来表示“The commoners wondered at it”,虽然这两种方式意义相差不大,但從语法角度讲倪译更加贴合原文。
“宠秦国之教”意为“以独揽秦国的政教为荣宠”,“宠”为意动用法。华译译为“exploiting your favoured position to dictate the ways of Qin”,倪译译为“plays along with the state of Chins policies”,杨译译为“monopolize state power”,三者都没有翻译出“以……为荣宠”的含义,只体现出“掌握秦国政教”,这样实际内涵就产生了偏差。
使动用法就是主语所代表的人物并不施行这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而是使宾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施行这个动作。使动用法和普通动词的用法虽然都是动宾结构,但在语义和表达效果上,使动增添了“迫使”的意思。如“齐败魏兵于马陵”中,“败” 在古代汉语中是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后加宾语则为使动用法,即“使魏兵战败”。华译译为“The following year Qi defeated the Wei forces”,倪译译为“Chi defeated Weis troops at Ma-ling”,杨译译为 “The following year Qi defeated the army of Wei at Maling”,三者都只是用了普通动词加宾语的形式,没有体现“迫使”的意思。另一处“将兵围魏安邑,降之”中,“降”本身是及物动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不多见,它和普通动词很相近,只在意义上有所区别,增加了“迫使”的意味。华译“forced it to surrender”和倪译“caused it to surrender”都突出了使动的用法;杨译“subjugated the city”则没有。
3.句类
汉语中四大句类之一的感叹句是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一类句子,可以表示快乐、惊喜、悲伤、恐
惧等感情。例如:“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华译译为“I made the law—and this is what I get”,倪译 译 为 “Alas,that the disadvantages of making laws should come to this”,杨 译 译 为 “So I am suffering from my own laws”。华译和杨译都没有将表示感叹的 “嗟乎”翻译出,但是二者都将引申的意思“立法的弊端涉及到了自身”表达了出来;倪译将“嗟乎” 译为“Alas”是十分准确的,因为“Alas”在英文中是表示悲伤、遗憾的叹词,一般译为“唉”,但后面的句子倪译仍然是直译,其中的引申含义则需要读者自己理解、联想。
(三)修辞
原文中有许多比喻修辞的运用,利用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用具体的、浅显的、熟知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深奥的、陌生的事物,使句子更加生动形象。例如:“君之危若朝露”“亡可翘足而待”,华译译为“your existence is as precarious as the morning dew”“your demise would be speedy”,倪译译为“my lord is as insecure as the morning dew”“one can await your fall standing on one foot”,杨译译为“you are as vulnerable as the morning dew”“your end will come as swift as a kick”。同样是对比喻句的翻译,华译和杨译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将本体和喻体间的相似点表达得十分清晰,将隐化为显,更有助于读者的理解。而倪译本着忠实原文的原则进行直译,没有添加自己的理解,译文仍是比喻句,需要读者自己理解体会。
三、结语
国外汉学界和中国翻译界的前辈和时贤对中华典籍外译工作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翻译界学者认识到:“对于《史记》而言,除了来自语言和文化层面的误译外,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困难——因为译者选择了不同的底本而造成理解差异,从而导致误译。而且这种误译对于译者来说是很难察觉的。如果不对相关平行文本作深入细致的筛查式研究和专业化、学术性求证或论证,要意识到此类误译几乎毫无机会。而这样的研究、求证工程浩大,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耗时耗力,开展起来谈何容易。”[4]倪豪士在談及他的翻译过程时曾提及:“《史记》内涵丰富,而我们的翻译又是为了学者的精确翻译,所以我觉得合作模式更为合适。美国没有多少学者懂《史记》……我们没有和中国大陆的学者进行翻译合作,因为他们通常英语不够好,大多数中国的
《史记》研究专家与学者都不甚懂英语。”[5]华兹生、倪豪士和杨宪益的《史记》译本都是极为优秀的英
文译本,具有重要地位。三译本虽各有千秋,但对古汉语的词汇、语法以及修辞、文化等知识也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熟悉和误解,导致三家译本的翻译都出现了这些方面的纰漏。由此,笔者对于中华典籍翻译工作的难度、价值和意义也有了新的认识:第一,中华典籍的翻译,应该注重对底本和注本的研究。第二,多视角、多维度、跨学科研究会促进对原作的研究和中华典籍翻译的发展。第三,中华典籍翻译中有很多共同的语言点和文化点,对这些的整理研究有助于实现翻译的一致性。总之,用我们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并与国外汉学家沟通合作,更有效地进行中国历史文化的国际传播,这是我们古典文献学、训诂学、古代文学和翻译界所共同面临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Watson B.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Qin Dynasty) [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89-100.
[2]Nienhauser W. H.Jr.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Volume VII[M].
Bloomington Ind: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87-96.
[3](汉)司马迁.史记选[M].杨宪益,戴乃迭,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162-181.
[4]高风平.从传播到传真的接力与博弈:《史记》外文译本述评[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18):58-66.
[5]魏泓.历史的机缘与承诺——美国著名汉学家倪豪士《史记》翻译专访[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8(3):8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