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古诗十九首中的爱情诗论略
戴建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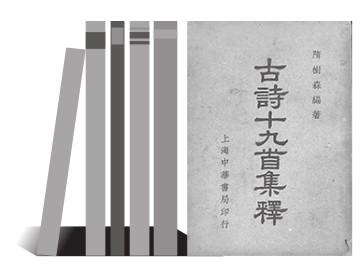
爱欲是人类最强烈的生命冲动之一。
因此,古今中外文学的主题类型中,要数爱欲主题最受作者青睐,也要数爱欲主题最让人神魂颠倒,因而也最为历久弥新。
讲六朝诗歌,我们得从《古诗十九首》讲起,因为它们是魏晋诗歌的滥觞;而讲《古诗十九首》,我们首讲其中的爱情诗歌,因为这些情诗最能拨动我们的心弦。
《古诗十九首》中有很多作品表现爱欲主题,那一首首炽热的情诗,或是对爱欲的大胆肯定,或者对爱的强烈渴求,或是对爱的热情呼唤——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此前,谁敢放肆地高喊“荡涤放情志”?谁敢坦承自己“空床难独守”?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它们读来照样“惊心动魄”!
爱的渴求
在聊《古诗十九首》的情诗之前,先和大家侃侃《古诗十九首》。
说起《古诗十九首》,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
它作于何时?起于何事?因何而作?何人所作?
这一连串的问题,也许鬼知道,反正我不知道。要是听到你问这些鬼问题,九泉之下的屈原肯定会马上坐起,奋笔疾书他的《天问》续篇。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它的喜爱,更没有影响大家对它的赞誉。
人世现有的最好形容词,差不多都堆到了《古诗十九首》身上。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你们听懂了没有?这意思是说,《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的珠穆朗玛峰。顺便交代一下,刘勰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最宏伟最系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他的话古今都极有分量,他对很多作者和作品的评价可谓一锤定音。
南朝梁代另一位著名诗论家锺嵘,对《古诗十九首》同样是击节称赞,并把它列入《诗品》中的上品:“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不过就是十九首诗歌,竟然让他“惊心动魄”,而且首首诗都“一字千金”! 我的个天!
更为推崇的是明代胡应麟,可能觉得“惊心动魄”还赞得不到位,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诗薮》)
对《古诗十九首》研究的历史,俨然就是赞美大比赛的历史,评价一个比一个高,调门一个比一个响。王世贞说《古诗十九首》“是千古五言之祖”(《弇州山人四部稿》),话音刚落,陆时雍马上接过话头说,它们“谓之风余,谓之诗母”(《古诗镜》)。
看了陆时雍的评论才知道,五言古诗原来都是《古诗十九首》生出来的!
作于何时
既然知道《古诗十九首》是五言古诗的“诗母”,那谁又是《古诗十九首》的“诗母”呢?《古诗十九首》让人心醉,人们自然会固执地问:它作于何时?又作于何人?为此争吵了一千多年,可能还要一直吵下去,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确切答案。
《古诗十九首》产生的年代及其作者,在南朝时就是一本糊涂账。徐陵编《玉台新咏》时将其中九首算在枚乘名下,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说:“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锺嵘在《诗品》中却说“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枚乘活跃于西汉早期,傅毅属东汉初期,曹植和王粲又属曹魏。徐陵、刘勰和锺嵘同为梁人,对作者归属和作品年代,三人虽然没有同台吵架,但完全是各说各话,而且他们也是道听途说,“或”“旧疑”云云,显然他们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后来七嘴八舌就更多了,有的说是张衡,有的说是蔡邕。其实,西晉陆机就不知道这些诗的作者,把自己的仿作称为“拟古”,梁昭明太子编《昭明文选》,在诗题下注得明明白白:“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
《古诗十九首》诗题纯属偶然,刚好这些诗歌都没有标题,刚好是前代传下来的“古诗”,又刚好收录在《文选》中的只十九首,所以人们就随意把它们称为“古诗十九首”,久而久之这叫法就成了标题。往雅处说,就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或柴可夫斯基第七号交响乐,往俗处说,就像农村叫大郎八郎三妹一样,有多少个就叫多少,数字完全是凑巧。
既然“不知作者”,为什么冒出来那么多说法呢?越是人人都没有证据,越是人人都有胆量,反正每种说法都死无对证,因而每种说法都无对错之分,即使胡说也不会使自己名誉受损,更不会引起任何纠纷,于是,人手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不过,虽然不能指定它们作于何人,也不能考出它们成于何年,但我们可以根据诗歌内容、风格和情调,大致推断它们产生于哪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说,依据诗里诗外的“蛛丝马迹”,来复原或接近事情的真相。一直觉得自己有点福尔摩斯的本事,今天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我正好来小试牛刀——
由于西汉避讳极严,不避君讳属于重罪,东汉则不必讳西汉皇帝。西汉第二位皇帝刘盈,《古诗十九首》中有“盈盈楼上女”“馨香盈怀袖”,可见,这些诗歌大部分或全部不是西汉的作品。
《古诗十九首》第一首说道: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
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
西汉建都于长安,洛阳不可能如此壮丽繁华,董卓之乱后“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那时洛阳已没有“双阙百余尺”的巍峨宫殿,显然《古诗十九首》不会写于建安时期,更不会在建安之后。
东汉前期班固《咏史》诗质木僵硬,中期以后五言诗才渐趋成熟,从诗风诗艺的角度看,《古诗十九首》这种“动天地,泣鬼神”的杰作,到东汉后期才可能出现。
《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对死的恐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那对生的依恋,“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那对功名的舍弃,“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那对爱情的珍视,“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那对爱欲的肯定,还有“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那及时行乐,在在都指向了人的自觉。《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二者在时间上先后相接,在价值取向与情感体验上又一脉相承,前者比后者可能早几十年或十几年,绝大多数诗歌作于汉灵帝与汉献帝之间。
它们并非写于一人,也非写于一地,又非写于一时。
《古诗十九首》作于哪个时期,我觉得基本可以结案了 。
作于何人
《古诗十九首》是何人所作?
即使福尔摩斯再世,他也不敢来接这个案子。就算“上穷碧落下黄泉”,也不可能找出半点线索。其实,最正确的提问应该是: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名垂千古的经典,作者为什么不留下自己的大名呢?难道东汉后期的诗人不希望名垂千古吗?
真是咄咄怪事!
一点也不奇怪。
敦煌词大多不也都是无名氏的作品吗?
古代把人分为贵贱,也把文体分为雅俗。
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我来给挚虞做一次翻译吧:古诗都应该以四言为正宗。四言诗才算是雅音之韵。其他的各种体式的诗歌,比如说五言诗,虽然可以写得委婉曲折,看起来明艳照人,听起来悦耳动听,但那都是一些不入流的诗体,这就像歌妓生得再娇艳,打扮得再时髦,也仍然是一名歌妓,也还是登不了大雅之堂。
一直到刘勰还认为“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文心雕龙·明诗》)。刘勰的意思与挚虞大同小异,作为诗歌正体的四言诗,诗风应以典雅温润为本,而世俗流行的五言诗,只有清新华丽才能招人喜欢。
刘勰还从语言学的角度,阐述了为什么四言高于五言,听听《文心雕龙·章句》是怎么说的:“四字密而不促……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四字就是四言,四言诗就是四字诗。他觉得四字句紧凑但不局促,那些庄重宏大的诗体和颂体,用五言就未免过于轻佻,用四言则十分得体。他还说写五言诗,不过是偶尔的权宜应变之方。写四言诗可以堂堂正正,而写五言好像偷鸡摸狗。
五言诗在六朝人心中的地位,现在大家看明白了吗?四言才算“正体”,而五言只是“流调”。所谓“正体”是说四言是诗的正宗,“流调”是指五言诗不过是上不了台面的流行曲调。挚虞在《文章流别论》说得很明白,五言诗“俳谐倡乐多用之”,唱五言诗的都是一些娼妓舞女。挚虞和刘勰对四言与五言的评价标准一样,四言诗既然是诗歌“正体”,那写四言诗才是走正道,写五言诗即使不是邪门也是旁门。
于是,汉代“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文心雕龙·明诗》)。那时的诗人即使写了五言诗,谁还敢署上自己的大名呀?倒不是他们感觉写得太差,而是觉得五言诗的体式太卑。
因此,在当时一个有头有脸的文人,可能出于好奇偶尔写写五言诗,但爱面子又不敢署名,于是就出现了《古诗十九首》这种佚名的名诗。更准确地说,《古诗十九首》不是佚名,而是匿名。
词也有类似的情况,开始只是民间创作,敦煌词的作者全属佚名,开始也只在民间流传,晚唐五代也只在青楼传唱,填词就是为了给“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中唐以后才有诗人拟作,如白居易和刘禹锡等人,开始都是写一些短小的小令:“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晚唐少数失意的诗人才大量填词,如科场失意的温庭筠大写艳词,无非就是破罐子破摔。
当然,东汉后期那些诗人也不可能长后眼睛,当时根本预料不到越是往后,五言诗越是行情看涨,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笔下的五言诗,是流芳百世的不朽经典,致使自己也错失了流芳百世的良机,可惜!
正因为《古诗十九首》是匿名之作,反正谁也不知道是谁写的,诗人们用不着端着装着,敢在诗中毫无保留地敞露真情,所以这些诗歌“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宋陈绎《诗谱》)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古诗十九首》中有些情感内容,“可为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诗人匿名使得诗歌垂名,真可谓诗人不幸诗歌幸,可喜!
不知道杰作的作者,我们当然非常遗憾;但要是没有了杰作,那可就是文学史上的灾难。可以不知道世有此人,但绝不可以世无此诗。
“空床难独守”
言归正传,我们接着聊《古诗十九首》中的情诗。
就像进入酒店或商场,开门迎宾的都是清一色的美女一样,一翻开《诗经》,最先迎接我们的就是爱情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淳朴的小伙子在求爱。
汉乐府中的《陌上桑》家喻户晓,“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这是心生邪念的使君在求偶。
從《诗经》到汉乐府,爱情都属于永恒的主题。诗人一写情诗就来神,大众一见情诗就来劲。
情诗在哪个时代都十分常见,《古诗十九首》中这首情诗又有什么新鲜之处呢?
上文谈到,《古诗十九首》大多写于汉灵帝和汉献帝之间,也就是建安前十几年或者几十年,时间上是和建安诗紧紧相接。东汉后期,不断的社会动荡,加速了王权的崩溃;而随着王权的迅速崩溃,儒家的价值大厦也随之瓦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礼崩乐坏”。原先人们遵循的行为规范,转眼便成了束缚人们的锁链;原先大家崇拜的精神偶像,转眼就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批判名教成了一种炫酷,反叛孔丘当然更显派头。
你们看看阮籍如何挖苦儒生:“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在外装得冠冕堂皇,一回家便肮脏不堪。刚一露嘴说了几句心里话,赶紧又满嘴仁义道德。整天忙于周旋应对逢迎拍马,那副卑微伪善的丑态叫人发愁。
人们突然发现什么礼义,什么节操,什么勋业,什么盛名,不是欺世盗名,就是转瞬即逝,只有“年命如朝露”是真的,“轗轲长苦辛”是真的,“与君生别离”是真的,“思君令人老”是真的……
既然这样,“虚名复何益”?“高节”又有何用?何苦还要“守穷贱”?何苦还要“守空床”?
于是,就有了我们正要讲的《古诗十九首》之二《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清初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说:“其兴趣全在起首‘青青二句,振起一篇精神。”为什么说“振起一篇精神”呢?
还得从头道来。
首二句中的“青青”“郁郁”,都是形容植物葱翠茂盛的样子,“青青”侧重于色调,形容“河畔草”青翠欲滴,“郁郁”则偏重于意态,形容“园中柳”茂密笼烟。这两句写景由远而近,眼光从远处的“河畔”移到眼前的“园中”。草只有绵绵不尽,才有一眼望不到头的“青青”之色,柳只有笼烟飘絮,才会呈现出“郁郁”之态,大家平日不妨仔细观察一下,几把草不可能一望“青青”,几株柳也不会满眼“郁郁”。
在《古诗十九首释文》中,朱自清先生认为这两句“是那荡子妇楼上所见。荡子妇楼上开窗远望,望的是远人,是那‘行不归的‘荡子。她却只见远处一片青草,近处一片柳”。从第三句“盈盈楼上女”可知,不仅“河畔草”“园中柳”是从诗人眼中看到,连“楼上女”也是从诗人视角写出,她是诗人要表现的对象。这正是此诗高妙的地方,“分明是从作者眼中拈出,却从似于女中眼中拈出;分明是从作者眼中虚拟女之意中,却又似女之意中眼中之感,恰符于作者眼中意中,真有草蛇灰线之妙”(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诗人“设身处地”的本领真是到家了,以致骗过了朱自清先生。
我左袒吴淇的说法,“青青”两句的景象,“分明是从作者眼中拈出”。这首诗并不是代言体,不必假托笔下的“楼上女”之口,诗人直接站在前台抒情写意。代言体诗如李白的《长干行》,一起笔就说“妾发初覆额,摘花门前剧”,这样诗中所写的一切,都是“妾”耳中所闻,眼中所见。
从写作手法上看,这两句既是赋——直描春景,也是兴——引起下文。大家看,河畔春草一片翠绿,园中垂柳丝丝飘拂,春归大地,春意盎然,春色撩人。此时万物萌发勃勃生机,春日里的少妇同样也春心萌动,所以说首二句“振起一篇精神”,你们听懂了没有?
这样,自然就过渡到了——“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盈盈”指女子仪态的优雅倩丽,“皎皎”指女子美艳得光彩照人。“窗牖”这里泛指窗户,在上古,开在墙上的窗叫“牖”,开在屋顶上的窗才叫“窗”,后世因很少把窗户开在房顶,慢慢这两个字便都指窗户了。“盈盈”二句的意思是说,楼上那个美女美得让人窒息,站在窗户前明艳动人,谁见了都会神魂颠倒。
诗人进一步描绘“楼上女”:“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娥娥”形容女子姿容姣美,“红粉妆”是说她浓妆艳抹,“纤纤”当然是指她的纤纤玉指,是形容她双手修长圆润,“素手”指女子双手洁白柔嫩,“出”在这儿是指把手伸向窗外。
“盈盈楼上女”这样的俏丽佳人,所有男人都梦寐以求,光彩照人更让男人魂不守舍,春日里“当窗牖”也情有可原,今天的女孩子不是同样喜欢春游吗?女子姿容娇美是上天恩赐,哪个女孩不希望像“楼上女”那样“娥娥”娇艳?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不过,“纤纤出素手”可就有点出格了,“素手”当然十分迷人,“出素手”却格外惊心,说轻点她是在搔首弄姿,说重点是在招蜂惹蝶。“纤纤出素手”的“另类”举止,让我们自然想到了潘金莲。楼上女为什么会这样呢?且看下文:“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倡家女”古代指歌舞伎,大多是卖艺而非卖身。“荡子”,相当于今天的游子,指长期出外闯荡不归的男性,不是风流浪荡的花花公子。“荡”在这里指游荡或闯荡。
要是回家了还算“荡子”吗?“守空床”不是“荡子妇”的宿命吗?
麻烦的是,今天的“荡子妇”,偏又是昔日的“倡家女”,让“倡家女”守“空床”还能不“难”吗?
读到最后,大家才恍然大悟,呵,难怪她要“当窗牖”,难怪她喜欢“红粉妆”,难怪她“出素手”!不正是由于难守空床吗?这首诗前后相互照应,读到后面便明白了前面,回顾前面更理解后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首诗的新意在哪里?
大家还记得“楼上女”“娥娥红粉妆”的打扮,记得她“纤纤出素手”的招摇吧?中国古代强调“女为悦己者容”,《诗经》中《伯兮》说:“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大意是说,打从丈夫东行之后,我的头发蓬乱得像草窝,倒不是没有发油梳妆修饰,可心上人不在自己身边,打扮得花枝招展给谁看呢?杜甫《新婚别》中,新娘子也对即将从军的丈夫说:“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丈夫还没离开便马上“洗红妆”,以此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专一。南宋诗人徐照《自君之出矣》比喻更新奇:“自君之出矣,懒妆眉黛浓。愁心如屋漏,点点不移踪。”自从夫君离家以后,娘子就懒得施粉画眉,她的思念忧伤就像那屋漏,一点一滴都在同一个地方。而“楼上女”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自己的那位“蕩子行不归”,她的妆饰才那么起劲,她的妆容才那么浓艳,她的行为才那样招摇。
古代大量的思妇诗,或抒发对丈夫真挚的思念,如曹丕的《燕歌行》:“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或表现对外地丈夫牵肠挂肚的担忧,如唐代陈玉兰的《寄夫》:“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或表现对久别重逢的期盼,如李白的《长干行》:“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但这首诗中的“楼上女”,她关切的重心不是自己“不归”的丈夫——“荡子”,而是她自己的烦躁,所以她要浓妆艳抹地装扮,要急不可耐地“出素手”招惹人,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她都守不住“空床”。
“空床难独守”是突出的重点,也是让人刺眼的焦点,更是全诗与众不同的要点。
清张玉谷《古诗赏析》认为,“此见妖冶而儆荡游之诗”,他说“既娶倡女”,就不应“舍之远行”,否则必定家门不幸。这种解释当然十分可笑,诗歌不能等同于告示,再说太太如果真的“妖冶”成性,荡子寸步不离也照样红杏出墙。不过,张玉谷看出了此女的“妖冶”,她自己不能安分,丈夫又怎能放心?
这首诗真正的与众不同,不只是写出了少妇“空床难独守”,写出了她不安于室的烦躁,写出了她“红粉妆”的娇艳,写出了她“出素手”的惹人,更在于诗人对这一切不仅没有道德的谴责,而且在对她生理渴求的描写中,表现出对这种渴求的理解和宽容,诗人似乎朦胧地懂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人们对爱情诗的态度,通常判定雅俗的标准是,言情则为雅调,涉性者为俗词。即使今天谈婚论嫁,公开场合,谁都只说是爱情的美好,谁会承认是性的需要?
可是,渴望性的满足是真切的人性,对“空床难独守”的宽容,就是对人性的尊重,而尊重人性就是人的觉醒。
过了几十年以后,三国嵇康才从理论上阐释,“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嵇康《难自然好学论》)。
正是在這一点上,这首诗引领了时代风潮,是魏晋人觉醒的先声。
此诗在艺术上的特征十分明显——
如前面六句连续用六个叠字:“青青”“郁郁”“盈盈”“皎皎”“娥娥”“纤纤”,但丝毫没有重复单调的感受,读起来反而一气呵成。
又如全诗句句宛转相生,河畔园中草青柳绿,真个是“春色满园关不住”,自然引得“楼上女”春心荡漾,一春心荡漾就会驱使她浓妆艳抹,也会引得她“出素手”勾人。勾人而身边又无人,自然会想起自家男人——荡子,既为“荡子”自然就“行不归”,“归”家就不算“荡子”;既为“荡子妇”自然只一人在家,因而也就只有“空床”相伴;既为“倡家女”自然习惯了灯红酒绿,一个人肯定“空床”难守。大家细心体会,就明白什么叫“环环相扣”。
风流梦
对生的依恋,对死的恐惧,是汉魏人觉醒的突出主题。
当突然意识到生命短暂的时候,你会用此后的余生干点什么呢?
饥饿者可能希望大吃一顿,失恋者可能希望大爱一场,有志者可能希望再拼一把,有德者可能希望造福一方……
面临死亡边缘时,《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抉择可谓五花八门:既然“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后悔“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应赶快建一番丰功伟业;既然知道“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那最好的选择“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酒要饮美酒,衣要穿名牌,让人生“潇洒走一回”;既然看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那“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让自己非富即贵,不枉一生……
而下面这一首诗中的主人公,当他发觉转瞬白头的时候,他的人生选择尤其不走寻常路——做了一场风流梦: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
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东城高且长”,首句是说洛阳东面的城墙又高又长。古代的城墙分为里城和外城,此处的“东城”是指里城。里城外面的一道墙叫“郭”,后世常以“城郭”泛指城市。古代常称东郭先生,南郭先生,现在的城市既没有里城,也没有外郭,今天只有东城大爷,西城女孩。“逶迤自相属”是说城墙绵延不断,沿着里城绕了一圈,首尾又连在了一起。“逶迤”形容蜿蜒辽远的样子,“相属”就是回环相连形状。
为什么一起笔就说“东城”呢?洛阳东面城墙有三个门,偏北的叫“上东门”,此诗下一首开关就说“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郭北墓”指洛阳北邙山墓群。可见,从东门北向远眺,可以望见成片的墓地,为下文人生苦短埋下伏笔。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回风”就是旋风,北方的秋天本来就很干燥,自下而上旋转的秋风,卷起地上的沙土和草叶,满天沙尘扑面,到处黄叶乱飞。“萋已绿”是“绿已萋”的倒装,“萋”通“凄”,形容绿草在秋天里变得萧瑟枯萎。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意思是一年四季不断地更替变化,一入秋天就一年将尽。中国人俗话说,年怕中秋月怕半,过了月半似乎过了一月,过了中秋就像过了一年。这句是感叹时光飞逝。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并不是早晨的风,而是一种鹞鹰类的猛禽。蟋蟀俗称促织、蝈蝈等。《诗经》中有《晨风》《蟋蟀》篇。连晨风这样凶猛的飞禽,也对时光流逝十分痛苦,连蟋蟀一入秋天也声声哀鸣,悲叹生命的短促。面对时光流逝,无知的虫鸟都知道悲伤,更何况多愁善感的诗人呢?
不过,人到底是万物的灵长,面对生命的无常与短促,虫鸟只是徒劳地“伤局促”,而人却懂得如何去放纵:“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荡涤就是冲洗、清除、洗涤,“放情志”就是开阔心胸,放纵情感,“结束”就是拘束、束缚。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不打破人为的禁忌,不冲决精神的囚牢,不放飞自己的情志?为什么要自己捆住自己,自己禁闭自己呢?
这是诗的前半部分,我们来回顾一下诗情的发展脉络:诗人来到洛阳东面,眼见又高又长的城墙,蜿蜒延伸回环不断,一阵旋风卷起枯枝败叶,夏日的满眼翠绿,转眼变成一片枯黄萧瑟。四季转换好像飞轮,眨眨眼就从年初到了年尾。秋天的晨风鸟也一脸苦相,蟋蟀更是彻夜忧伤。物尚如此,人何以堪?这就引出了“荡涤放情志”的念头。
这就是常说的“因景生情”,诗人把“放情志”的情怀,写得入情入理,应验了“人禀七情,应物斯感”的名言(《文心雕龙·明诗》)。
人生既然如此匆匆,不如放飞自我,怎么开心就怎么干,怎么快活就怎么活!
“荡涤放情志”五字之中,“放”和“荡”既是句中的关键,也是全诗的中心。
诗的前半部分写何以要“放”“荡”,后半部分写如何去“放”“荡”。
那么怎样才算最好的“放情志”呢?
于是就转入了诗的下半部分。
马斯洛说,爱情是人的高峰体验。清人吴淇认为,对于男性而言,“盖人世一切,如宫室之美,车服之丽,珠宝之玩”,都抵不上佳人“切身受用”。另一个清人张庚也说,能让自己“放情志”,能让自己不“自结束”的,“莫若艳色新声”。
“何为自结束”的顾虑一打消,声色之欲就像被压抑的火山喷发而出。要“放情志”就得找佳人,要找佳人就得去燕赵。
大家知道,战国时期,燕的都城在蓟,靠近今天的北京市。赵的都城在今天的邯郸,在河北的南部。古人认为燕赵多美女,此时的诗人正在洛阳东城,到哪里去找燕赵佳人呢?
白日的风流梦里。
你们看,在他的风流梦里,想什么姑娘就來什么姑娘:“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燕赵佳人像玉一样洁白,像玉一样温润。我的个天!
让人神魂颠倒的是,她的穿着是那样入时,那样得体,“被服罗裳衣”飘然而至,简直像天上的仙女下凡。“罗”泛指绫罗绸缎,古时“衣”是指上衣,“裳”是指下衣,美人从上到下的行头都雍容华贵。这是典型的“白富美”。
他的梦中情人还并不是头脑空空的绣花枕头,而是来到他窗前“低眉信手续续弹”,演奏的“清曲”是那样悦耳动听。她的审美趣味多么高雅,她的才艺又多么精湛!
他听得如醉如痴:“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或许是弦柱调得过紧的缘故,琴声越来越高亢激越,这种急管繁弦让人悲凉。汉魏人对悲音有一种偏好,他们觉得欢乐之音难工,而愁苦之音易好,奏乐以悲音为荣,听乐以悲音为雅。
再说,演奏时的“弦急”“柱促”,也表明佳人当时十分激动,不然,就不会有下两句——“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驰情”其实就是感情撒野,或是想入非非。诗人在梦中与情人亲密接触,佳人也不由得双颊飞红,不禁下意识地“整巾带”,一边起身徘徊,一边陷入沉吟。
正如吴淇所说的那样:“曰‘美者,分明有个人选他(他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个人听他;曰‘整巾带,分明有个人看他;曰‘聊踯躅,分明有个人促他。”吴淇还说掉了一点,佳人知道身边分明有个人爱她。
这就更容易理解了,她与他早已“心有灵犀一点通”,“弦急”表明她的激动,“整巾带”说明她的矜持,“踯躅”表明她心如小鹿,“沉吟”更表明她在做决断——“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佳人此刻已经芳心暗许,希望与他永结夫妻,两人从此终生成双成对。
在古代诗歌中,“双飞燕”是夫妇和爱情的代名词。这个比喻的后半部分太妙了,“衔泥巢君屋”不仅形象表现了“成双入对”的恩爱,还表现了他们一起共筑爱巢的甜蜜。一位“美者颜如玉”的佳人,还没等小伙子主动求爱,便迫不及待地要和他白头偕老,真是天下掉下来大馅饼!
清代朱筠对这首诗的结尾赞不绝口:
结得又超脱、又缥缈,把一万世才子佳人勾当,俱被他说尽。(《古诗十九首说》)
我真不忍心煞风景,可又不得不告诉大家,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大馅饼,其实就是诗人的一场风流梦,从“燕赵多佳人”到“衔泥巢君屋”,全是诗人“荡涤放情志”的梦境,是他最希望“放荡”的对象,“美者颜如玉”的燕赵佳人,其实就是他的梦中情人。从“何为自结束”的诗句看,诗人平时为人拘束内向。只有一辈子与风流韵事无缘的人,才会把风流韵事想得这般美好。
后来的李白也常常梦游,如名诗《梦游天姥吟留别》,但到最后梦都醒了,“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而此诗中的诗人一直还沉浸在风流梦中,还在和燕赵佳人一道“衔泥巢屋”,因为只要美梦一醒,自己仍然孑然一身,眼前还是家徒四壁,社会依旧烽火连天,百姓照样流离失所……
只在风流梦中才能“放荡”,只在温柔乡中才像个男人。
这首诗中情感的发展脉络,上下两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还有诗中比喻的妙处,我都和大家随文细读了一遍。“青青河畔草”的美像倡家女明艳照人,“东城高且长”的美似大家闺秀深藏不露,只要反复比较、咀嚼和品味,艺术鉴赏能力定会日益提高,审美感受定会不断细腻。
不论是“青青河畔草”,还是“东城高且长”,它们既是汉魏人的觉醒的产物,同时又是汉魏人的觉醒的表现。
只有在人的觉醒的时代,人们才能直面自己心理和生理的渴求,男人才敢公开叫嚷“荡涤放情志”,女人才敢公开坦承“空床难独守”。
这两首诗之所以成为传世经典,就在于它们写出了人人心中之所有,而人人口中却不敢言的那种渴望。
它们的诗情都大胆得叫人惊心,它们的诗艺都高超得让人惊艳。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文学研究所所长,2023年3月入选“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