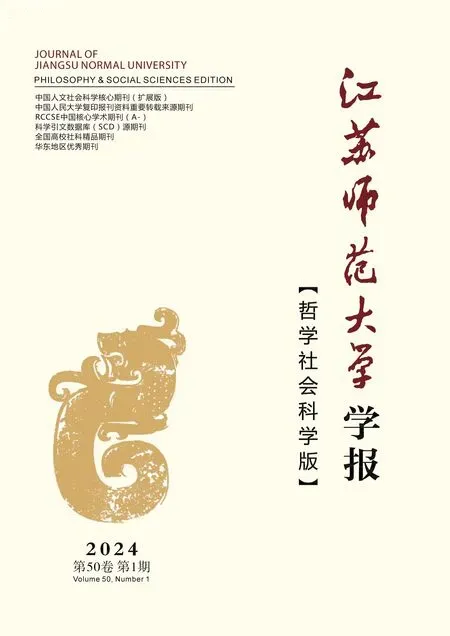以“人”为视角:先秦天人范畴的形成
王振红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天人范畴,是先秦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至关重要的核心范畴。先秦时期,天是指上帝、自然、天命、鬼神等外在于人类但又能影响甚至主导人类的存在,而人们对天的认识即天的观念则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同样,先秦时期的人也在不断地发展当中,人对自我的认识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天人关系之中,不论是宗教之天还是自然之天,抑或是道德之天,对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制约、规范乃至决定作用;然而,天不能自我言说,它只能通过人的认识与阐释而得以呈现。由此而言,人类的发展比如从原始部落到国家社会,从蒙昧迷信到自我觉醒,从神道设教到礼乐制度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对天的认识即天的观念的形成与演变。质言之,在天人之间天是被动的,人是主动的,天的观念既是人建构出来的,又被运用于人类自身的不断生成与发展之中;所以,立足鲜活的“人类世界”,通过人类自身的发展历程不仅可以梳理先秦时期人之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而且能深入阐明天之范畴的发生与演变。
一、原始社会:人神杂糅、天人未分
人类产生之初,人的生产能力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都非常低下。在此情形下,人类只能依附于自然界,从自然界索取天然的生活必需品以维持生存;不仅如此,人类还没有认识到自身与动物乃至于植物的区别,可以说,此时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人对于外在的自然界与内在的精神世界及人类社会远没有清晰的认识。然而,自然世界的地震、风雨、雷电、山火、海啸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不同部落之间的残酷争斗等无时无刻不威胁、困扰着人类;正是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促使人类在冥冥之中意识到有一种外在的无比强大的力量时刻左右着人类。这种外在于人类却时刻左右着人类的力量,就是原始社会时期人心目中的天。这一时期的天,一般被统称为神灵。
据考古发掘,我国很多地区的史前墓葬之中的骸骨上往往撒有赤矿粉,考古学家认为这是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证明。实际上,原始人认为不仅人类有灵,而且万物亦皆有灵,而人类的灵魂与万物的灵魂还可以相互沟通;重要的是,原始人还认为灵魂具有超越人类、超越自然的力量。因此,当史前人类陷入天灾、战争、疾疫等困境之时,力量弱小、意识蒙昧的原始人既无法阻止这些灾祸的发生,更认识不清它们发生的原因,在极端恐惧与无助之下他们开始以自我虔诚的灵魂沟通、祈求拥有超越力量的神灵,以求得它们的护佑。相信万物有灵,并通过祈祷、祭祀等方式去沟通神灵,从而趋吉避凶,这即是史前人类的精神世界的主要构成。
在原始人看来,既然万物有灵,那就崇拜万物。于是乎,原始人的精神世界中便产生了众多的神灵,这从原始宗教的诸多形态便可见一斑:天体崇拜,崇拜日、月、星辰诸天体以及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动物崇拜,敬畏与自我联系比较紧密的各种动物;植物崇拜,赋予花、草、树、木等以神秘的灵性与力量;生殖崇拜,则是对人类生殖现象、生殖器官、性行为的敬畏与膜拜;祖先崇拜,相信祖先有灵,且祖先之灵能保护他的子孙后代;图腾崇拜,则是把某种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动物、植物甚至是非生物视为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相信它们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并以此力量来保护自己及自己所在的部落。凡此种种神灵,都是原始人不自觉的精神建构,即他们以自己尚在蒙昧状态之下的精神意识,创造出一个众神杂处的世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发的精神建构虽然蒙昧,但着实难能可贵,因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正由此而发端。
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尤其是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随之增强。人类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人类实践能力的增强,比如基于生产生活的协同、分工、分配实践,为了群体生存延续的婚姻生活、族群管理实践等,都不断丰富着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经验;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类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即人类对个体自我及社会结构有了初步的认识,对自然世界及其基本构成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可以说,人类在惊恐未定的同时,已经对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差异及其基本构成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其实,人类崇拜万物之神灵,以越来越繁复的仪轨祭祀神灵,在此过程中人类最初的自我意识开始萌发,而且已经不自觉地将万物对象化了,同时也将神灵进行了初步的人格化。当然,此时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并不清晰,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所以,这一时期人类与万物、神灵之间依然没有清晰的分野。
正是因为人与万物尚未分野,人的神灵与万物的神灵、人力与神力的沟通转化才成为可能:一者,原始人以虔诚的祭祀祈求神灵的护佑,此时人与神虽然能沟通,但人是卑微的祈求者,神是高高在上的保护者,人力与神力的地位相差悬殊;二者,伴随着祭祀手段、仪轨的完善,祭祀者尤其是巫师们通神能力的增强,他们甚至以巫术等手段将神灵的力量化为己有。《山海经·中山经》载曰:“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1)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报,第124页。晁福林认为此“传说的主体是人化为草,草即是人。这里的人很有神性。巫师很可能指瑶草为神,神之灵魂已附于其上,所以瑶草就有了神性”(2)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 6页。。此外,晁福林还指出,河南濮阳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的第45号墓墓主尸体两侧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像,以及遗址中蚌壳摆塑的人骑龙图像,说明墓主具有“降龙伏虎的神威”,他“亦神亦人,神人不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天神或鬼神。化神力为己力,表面上是神力在起作用,但却往往增长的是人的力量”(3)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人力的增强并不意味着神力的减弱,人类吸收、消化神力以增强己力,反过来,神力只有融入人力才发挥作用,人力与神力相互为用,在一定程度上两者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力与神力此消彼长的情况显然不同。
要而言之,原始社会早期在人类意识中人与天地自然浑然一体,人类尚未意识到自己与动物、植物乃至于非生物的区分,与此同时人类又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在此情形下,人类与万物、人类的灵魂与万物的神灵之间的关系具有如下三个特点:其一,既然人类与万物一体,所以,人类的灵魂与万物的神灵可以沟通,且人人都可以沟通神灵,正如《国语》所言:“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4)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14-515页。。其二,人混同于自然之中,同时震慑于大自然之种种神秘的威力,原始人于是“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依于神”(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故此,此时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就无法真正确立。比如,图腾就是建立在“群体主体不分化以及人和动物生命一体化的基础之上”,图腾意识表现出原始人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同一性(6)李景源:《认识论发生的哲学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其三,人类与自然没有分野,人类就不可能对自身及社会结构,以及万物的分类构成有清晰的认识,即内在的社会秩序与外在的自然秩序都没有形成;同样,在万物有灵观念下形成的众神也是杂乱无序的,即众神的世界也没有形成一定的秩序。可以说,“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的确是这一时代特征的准确概括。
二、传说时代及夏朝:敬神识天、天人初分
在没有文字的传说时代,口耳相传形成了诸多传说,诸如盘古开天地、神农尝百草、伏羲建八卦、燧人氏钻木取火、黄帝战蚩尤、唐尧禅让、大禹治水等。这些传说,虽然在文字产生后经过后人屡次的编纂与改造,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人类认识、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有了显著的增强,以及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初步形成。这一时期,人类一方面还保留着对各种神祇的崇拜,即此前较为原始的“天”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对茫茫苍天尤其是对自然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自然之天的观念获得了巨大进展。所以,这一时期天兼具鬼神与自然两方面的特征。
就鬼神之天而言,上述诸传说中的主人公往往亦人亦神、亦人亦兽,无不具有神力。如盘古“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7)《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见《广博物志》,(明)董斯张撰,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85页。;又如伏羲人首蛇身,仰观俯察,以天地阴阳变化而作八卦;再如黄帝大战蚩尤,请雷神与旱魃施展神力,终于擒杀蚩尤。这些传说无不渲染了神力在史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这些传说更包含着人类对天地自然的认识与改造。比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反映了人类对自然万物创生的猜想,所谓“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8)董斯张:《广博物志》,岳麓书社,1991年版,第185页。在古人看来,天地阴阳孕育人类,而盘古首生,其死后身体各部位化为风、云、雷霆、日、月、星、辰、五岳、江河、地里、田土、草木、金石云云。可见,在古人的观念里盘古亦人亦神,是开天辟地的神灵,其化身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类对天地万物初步分类与认识的过程。
而《易经·系辞下》有言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9)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6页。包牺氏即伏羲氏,虽然八卦创始者未必就是伏羲氏,但《系辞》通过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法,对自然、社会进行分类与认识,并总结、抽绎出其中的法则,从而向上贯通神明的德性,向下分析归类万物的情状。此后,《史记》对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记载,一方面阐述他们在宗教、政治、社会层面的制度创设,如黄帝之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1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页。;颛顼帝“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1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页。;帝喾则“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1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页。;虞舜“乃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祡,望秩于山川”(1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页。。上述引文中的“鬼神”“封禅”“迎日推策”“治民”“抚教万民”“类于上帝”云云,无不体现了五帝时期不仅在神道设教、制度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获得了巨大进展;更重要的是,当此之时鬼神、历法、政教等是融为一体的,如果用西周之后的思想文化来概括,那就是鬼神之道、自然之道、政道及人道在此时尚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
另一方面,《五帝本纪》则重点记载了五帝时期人们在深入认识大自然的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改进历法等实践活动,诸如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1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页。;尤其是唐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1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17页。。此段文字源自《尚书·尧典》,据刘起釪先生的研究,这段文字反映了唐尧任命官员、制定历法、指导民事等活动,其史料的来源非常复杂,是把远古关于太阳女神的神话和它经过转化后的传说、远古关于太阳出入和居住地的神话和它转化为地名的传说、古代对太阳的宗教祭祀有关材料、古代对四方方位神和四方风神的宗教祭祀有关材料等组织在一起编纂而成的,保存了极为珍贵的远古传说及天文历法的材料(16)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63-64页。。由此可见,原始社会末期人们通过对自然之天的深入认识而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但他们对自然之天的认识与对太阳神及诸自然神祇的崇拜并非泾渭分明,也没有因为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进一步认识而否定自然神祇的存在。
同样,夏人也非常注重祭祀鬼神,并以各种手段与上天相沟通。关于夏人沟通上天,《左传》《竹书纪年》等文献都有相关记载。在《左传·宣公三年》中,楚子问鼎中原,王孙满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17)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68页。。张光直认为,“鼎”就是通天的神器,“象物”就是鼎上的动物纹样,而“以动物纹样为主的艺术实在是通天阶级的一个必要的政治手段”,而“古代王朝之占有九鼎便是通天手段独占的象征”(18)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62-63页。。不仅如此,夏人还以歌舞沟通上天,《山海经》就有夏后开舞《九招》的记载:“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19)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14页。无独有偶,《竹书纪年》亦有“夏后开舞九招”的记载。夏后开即夏启,方诗铭等注曰:“《帝王世纪》:‘启升后十年,舞九韶。’《山海经·大荒西经》:‘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又《海外西经》:‘夏后启于此舞九代。’《楚辞·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下〕康娱以自纵。’又《天问》:‘启棘宾(商)〔帝〕,九辩九歌。’‘九招’‘九韶’‘九歌’‘九辩’,当为一事。”(20)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对此,桓占伟指出:“禹、启可以通过神秘的巫术和仪式性舞蹈,与天地万物建立系统关联,成为能通天地的先知先觉者。”(21)桓占伟:《“夏道尊命”:儒学视野中的夏代宗教政治认同》,《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5期。由此可见,夏人以各种手段沟通天地,“事鬼敬神”的观念与行为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依然居于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夏人对自然之天的认识更为深入,尤其是历法的制定(夏历)及因治水而积累的丰富的地理知识最具代表性。相传大禹“颁夏时于邦国”(22)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証》,收入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其实,在大禹之前唐尧即已“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2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17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禹颁布“夏时”自有其渊源。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笺曰:“得夏时,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24)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5-586页。司马迁亦于《史记·夏本纪》记载道:“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2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页。一般认为,《夏小正》虽然成书时间不早于战国时期,但其中有关星象、物候、农事等方面的记载当有更早的来源。许尧汉等就通过比较《夏小正》与彝族十月太阳历,认为两者同源于远古羌历(26)许尧汉、陈久金、卢央:《彝夏太阳历五千年——从彝族十月太阳历看〈夏小正〉原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这说明《夏小正》成之者非一人,著之者非一世。夏人除了在观象授时、制定历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外,大禹治水更凸显了中国人在远古时期既已拥有疏通、改造山河大地的能力,同时展现出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史记·夏本纪》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溼。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2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页。;在治水成功之后,大禹更是“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28)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0页。。很显然,大禹治水的成功,不仅疏通了中原地区及其周围的河道,使得农业生产获得巨大进展;更为重要的是,以大禹为代表的夏人通过治水建构出一定的自然秩序与政治社会秩序。艾兰就曾指出,大禹治水其实意味着给世界制定一种物质上的次序,而定九州、铸九鼎则意味着制定一种政治上的次序(29)艾兰:《鬼之迷——上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0页。。这确是符合实际情形的洞见。
《礼记·表记》记载了孔子对“夏道”的论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30)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09页。对于“尊命”一词,孙希旦释曰:“尊命,尊上之政教也。远之,谓不以鬼神之道示人也。改夏承重黎绝地天通之后,惩神人杂糅之敝,故事鬼敬神而远之,而专以人道为教。”(31)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09-1310页。孙氏把“命”解释为“上之政教”,而且特别强调夏人“不以鬼神之道示人”,而“专以人道为教”。事实上,从原始社会刚刚进入文明社会的夏人依然“事鬼敬神”,他们不可能“专以人道为教”,孙氏的观点显然有些绝对化。桓占伟曾指出“命”作为夏代的共识性核心观念,具有“时令”与“王命”两大内涵。重要的是,夏代统治精英靠着通天地之能获取了王权,而王权也因有通天地之能而蒙上了神圣色彩。故时令和王命构成的夏代之“命”,能对天下万方形成无形的威慑,具有不容置疑的神圣性。时令的实用性,王命的权威性,再加上二者本具的神圣背景,共同促成了“命”在夏代的核心观念地位,形成了夏代的宗教政治认同(32)桓占伟:《“夏道尊命”:儒学视野中的夏代宗教政治认同》,《世界宗教研究》,2021年第3期。。需要指出的是,夏人依然“事鬼敬神”,夏代之“命”还具有不容置疑的神圣性,与此同时夏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业已初步形成:从“时令”的角度而言,夏人将天象、物象、星象及山川河流作为对象加以认识、利用甚至改造,在此基础上夏代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发展;从“王命”的视域而言,大禹治水、后稷耕稼、行政机构的建立、政令的颁布,则说明夏人对社会人群的组织结构、运行管理亦有相当深入的认识,自觉的制度建设实践与社会治理意识已获得一定进展。要之,到了夏代鬼神之天虽然高高在上,但它隐藏在“时令”与“王命”的背后,而此两者构成的“夏道”充分说明了大禹治水之后人力的显著增强,以及夏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初步确立;也正因为如此,夏人从而建构出前所未有的自然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
三、殷商时期:率民事神、天人相与
《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33)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10页。殷人尊神,这在甲骨卜辞、考古发掘以及传世文献中都有充分的反映。殷人所尊之神,主要指祖先神、天神与自然神。相较于夏朝及传说时代的神灵崇拜,殷人一方面认为“上帝有很大的权威,是管理自然与下国的主宰”(3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0页。,而山川风雨诸神(自然神)亦对人类的生存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逐渐地把祖先神作为祭祀、祈祷的主要对象,即祖先崇拜在殷人的神权世界中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35)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7页。。从注重上帝、天神及自然神祇到以祖先作为主要崇拜对象,这应与五帝时期、夏朝及殷商时期人们的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增强,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密不可分。
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可知,殷人遇事必卜,“以祭祀、求告、崇拜的方式来求助于祖先、神明”(3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61页。。殷人之所以求助祖先、神明,是因为他们认为上帝、祖先、山、川、日、月、风、雨、土地诸神祇具有令风、令雨、降祸、将食、降若、受年等方面的能力;尤其是,“殷人的上帝或帝,是掌管自然天象的主宰,有一个以日月风雨为其臣工使者的帝廷。上帝之令风雨、降祸福是以天象示其恩威,而天象中风雨之调顺实为农业生产的条件,所以殷人的上帝虽也保佑战争,而其主要的实质是农业生产的神。”(3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0页。炎黄部落、夏朝及商朝都地处黄河流域,农业逐渐成为他们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卜辞中很多有关令风、令雨、受年之类的记载,正说明了殷人对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视。然而,农业生产一方面深受必然性的自然节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也深受大自然偶然性的风雨雷电的影响。五帝时期及夏朝已经制定了历法,商人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阴阳历,也就是说,商人已经掌握了一些必然性的自然节律,能够根据一定的节气时令耕种收割庄稼;然而,偶然性的风雨雷电等却不容易为人所把握,所以,殷人只能通过卜问神灵的方式求得启示或预测,从而趋吉避凶。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殷人是在掌握了一定的必然性的自然节律的基础上,又试图去探索、了解大自然的偶然性与不规律性。晁福林先生就曾指出:“殷人对自然的认识充满着盲从与迷信,但是殷人的自然崇拜里毕竟包含了不少对奥妙的、变化无常的自然现象的积极探索。”(38)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可以说,殷人对自然之天的探索是在对上帝崇拜、自然神与天神崇拜的氛围下进行的,即理性与非理性在互相渗透中向前发展着。
在殷人祭祀、崇拜诸神灵的过程中,祖先神逐渐成为主要的崇拜对象。据晁福林先生统计,祖先祭祀方面的辞例多达15000多条,超过其他任何一类辞例的数量,这是殷人重视祖先崇拜的有力证据(39)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殷人极为重视祖先崇拜,有着多方面的历史渊源:其一,人类产生之初,血缘关系是维系人类社会运转的重要纽带,到了父系氏族阶段,伴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剩余产品的出现,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而这又导致了人们的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尤其是到了夏启“家天下”之后,祖先的身份、财产、权势、地位对于他的后代而言变得至关重要。可见,血缘不仅成为维系氏族、部落内部关系的关键要素,而且关系到人们的身份、地位、财产、权力的继承。在此情形下,祖先与其子孙的关系日益加强,祖先崇拜也就顺理成章了。其二,在人类社会早期的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之中,年长且具有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的部落成员自然而然地成为首领,他们带领、指导部落成员打猎、耕种、治水、打仗等,在部落及部落联盟的生存发展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等都是如此。这些首领不仅生前具有极高的威望,而且在死后也为部落成员所祭祀、崇拜,甚至被神化成各种神灵。如大禹死后化为社神(40)《淮南子·汜论训》云:“禹劳力于天下,死而为社。”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85页。,继续护佑大地生灵。其三,正如上文所说,早期人类不仅相信万物有灵,而且以各种方式沟通神灵;在颛顼“绝地天通”之后,沟通上天神灵的权力集中到专门的巫觋阶层手中,而部落、部落联盟以及方国的首领既是行政事务的主导者也可能是众巫的首领。到了商朝,商王不仅是众巫之首,而且死后甚至可以“宾帝”,即上升到上帝左右,护佑子孙后代。当然,重视祖先崇拜并非殷人所独有,但殷人的祖先崇拜却有其自身的特点,那就是“殷人不仅把远古先祖、女性先祖,一些异姓部族的祖先等都和列祖列宗一起网罗祀典,尽量扩大祖先崇拜的范围,而且还有完整而周密的祭祀制度”(41)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5页。。
关于天神上帝、自然神、祖先神三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郭沫若明确指出“帝”或“上帝”是殷人的至上神,认为上帝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它有好恶、能够命令,一切天上的风雨晦暝、人事上的吉凶祸福都由它主宰,而且这个至上神就是殷民族自己的祖先;此外,殷王以“帝”称号如“帝甲”“帝乙”“帝辛”等,这表明“帝的称号在殷代末年已由天帝兼摄到了人王上来了”(42)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对此,胡厚宣有更为详细的阐释,他说殷人的至上神——上帝“主宰着大自然的风云雷雨,水涝干旱,决定着禾苗的生长,农产的收成。他处在天上,能降入城邑,作为灾害,因而辟建城邑,必先祈求上帝的许可。邻族来侵,殷人以为是帝令所为。出师征伐,必先卜帝是否授佑。帝虽在天上,但能降人间以福祥灾疾,能直接护佑或作孽于殷王。帝甚至可以降下命令,指挥人间的一切。殷王举凡祀典政令,必须揣测着帝的意志而为之”(43)胡厚宣:《殷墟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下),《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不仅如此,帝拥有极大的权力,有日、月、风、雨诸神等供帝驱使,称之帝使;五方之神亦听命于帝,称为“帝五臣”(《合集》30391)。殷人以为帝是全能的神灵,拥有无上尊严,在人间也只有人王与之相侔,故商之高祖太乙、太宗太甲、中宗祖乙死后升天配帝,而从武丁到帝乙则对死去的生父以“帝”称之(44)胡厚宣:《殷墟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下),《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王晖不仅认为上帝是殷人的至上神,而且指出上帝与祖先神、自然神之间具有一定的上下关系;上帝像人王一样有一个供他役使的官僚系统,如“帝正”(《合集》36171)“帝史”(《合集》35931)“帝五臣正”(《合集》30391)等皆是上帝的臣属(45)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7页。。很显然,学者们之所以认为上帝是殷人至上神,以及至上神有其相应的官僚系统,这是因为人间世界已有人王及国家官僚体系的出现。在现实世界中,殷王作为天下共主,业已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神灵世界,作为至上神的上帝已与殷人的祖先神合二为一,殷王至高无上的权力从而有了神圣的依据。
与郭沫若、胡厚宣、王晖等人的观点不同,晁福林认为在殷人的神灵世界之中祖先神、天神、自然神三足鼎立,互不统辖,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各自干预着同一个人世间的风雨阴晴和吉凶祸福。其中,占有最重要的主导地位的是祖先神,而商王朝的祖先神既是商王朝的保护神,也是诸方国、诸部族的保护神。居于殷代神权崇拜显赫地位的是殷人的祖先神,而帝小心翼翼地偏坐于神灵殿堂的一隅。殷代的帝和土(社)、岳、河等神灵一样,既具有自然品格,又具有某种人格。帝不是万能之神,也不是最高主宰;帝只是众神之一,而不是众神之宗。殷代尚未出现一个统一的、至高无上的神灵。这是因为,殷代政治结构是王权、方国联盟势力、族权等的联合体,与之相适应的神灵世界理所当然地呈现着多元化的状态(46)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8页。。但是,伴随着王权的增强,以及王权对神权斗争的胜利,殷代后期的帝“逐渐转化为人世间祸福的主宰,成为具有某种人格神的至上神。殷代最后的两个王称帝乙、帝辛,就标志着这个转化的完成,也说明了王权已经和神权相结合”(47)晁福林:《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73页。。可见,晁福林并不否认殷代至上神的存在,他认为到了殷代后期伴随着商王权力的加强,上帝才逐渐发展为至上神。总体而言,晁福林认为祖先神在殷代的神灵世界中拥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以往学者们抬高了上帝的地位及功能,把殷人的上帝看作统一的至上神与殷代王权、方国联盟势力、族权构成的联合体政治结构是相违背的。
要而言之,殷人的神灵世界主要由祖先神、自然神、天神三部分构成。殷人所崇拜的祖先神既有遥远的先祖神灵,又有近世的祖先神,既祭祀男性祖先神,又崇拜女性祖先神;同时,殷人的祖先神既保佑殷人,也护佑与殷人关系亲近的其他方国、部族。殷人的自然神则包括了日、月、风、雨、雷、电、山、川、土地诸神灵,殷人在崇拜、祭祀自然神的同时又积极地探索自然的奥秘,一方面在认识大自然的必然性上有了显著进展,如历法、纪年、纪日方面的进步;另一方面,殷人对大自然的偶然性试图进行探索。殷人的天神有帝、上帝与天三种称谓,从卜辞所载内容来看,上帝主要功能是支配各种气象,可见它是负责农业生产的神;此外,上帝高高在上,既有帝廷又有供其驱使的臣僚,殷王死后则“宾于帝”;凡此种种,都说明上帝与自然神、祖先神颇有不同,诸多学者也正以此为据把上帝看作至上神。无论是认为天神、自然神、祖先神三足鼎立,还是把上帝作为至上神,统领自然神与祖先神,这都说明殷人的神灵世界业已形成了一定的秩序,而此秩序总是随着殷人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变化而变化。此外,殷人把祖先神、自然神与天神作为崇拜、祭祀的对象,并使用各种手段、祭品与法器去沟通神灵,以求神灵给予启示或护佑,在此过程中殷人虽然会把自己投靠于神灵,但其虔诚的心理依然体现出积极的主动性。可见,殷人的“尊神”并非今人所谓迷信,其间活跃着积极的自我意识与明确的对象意识。
四、殷周之际与西周时期:敬天保民与天人内涵的定型
殷周之际是一个剧变的时代,殷周鼎革不仅标志着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也意味着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在此剧变之中,天人观念的变化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政权鼎革的主要内容又是思想文化变迁的主要表现。从上文所述可知,殷人对于祖先神、自然神与天神的崇拜、祭祀,主要是在生产生活的具体事项中祈求神灵的护佑与启示,这与殷人的政治统治及其合法性并没有建立直接的关系。到了殷末,王权与神权开始融合一体,殷王死后亦以“帝”称之,这既说明了王权的增强,也表明上帝与政治权力相融合。其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殷纣王“我生不有命在天”(4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52页。之言,明确地指出了殷人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神上帝。殷人的这种观念,为周人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武王伐纣,“小邦周”取代了“大邦殷”,这对周人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周人为了解释殷周鼎革的必然性,创造出迥异于殷人的天人观念:一方面借助天的观念建构政治伦理,神化其政权合法性;另一方面将德融入天的内涵之中,从而将宗教意义上的天神观念与世俗意义上的政治、伦理观念融为一体。
首先,周人认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但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它随着道德的有无而转移。周人往往将其获得天命的源头追溯至文王,如《尚书·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49)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99-1300页。。可见,周人认为上帝之所以“大命文王”,其原因就在于文王崇尚德教,慎用刑罚,关心民众,勤于政事。而与之相反,殷人之所以丧失天命,正是因为殷纣王“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50)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07-1408页。。殷纣王嗜酒淫乐,凶残百姓,他酗酒的腥气与百姓的怨气升闻于上帝,上帝于是降灾祸于殷人。在周公等人看来,天命可以转移,否则,周人就无法获得上帝早已授予殷人的天命;但天命的转移是有条件的,它随着道德的有无而转移,文王明德慎罚、勤于政事,纣王嗜酒放逸、残暴荒淫,故天命转移到周人的手中。显然,周公等人反复宣扬的文王受命,以及天命随着道德的有无而转移之观念,解决了殷周鼎革的合理性与周王朝政权合法性的问题。
其次,“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人虽然认为周王朝的政权源于上天所命,但是天命的获得则根源于周人之“德”。因此,周人极为重视“德”,想方设法一直拥有“德”,进而永保天命。同样,周人之“德”主要来源于文王。《诗经·维天之命》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51)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83页。这就是说,文王拥有无比纯正的道德,从而获得庄严肃穆的天命。需要指出的是,文王之“德”之所以能够获得天命,其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文王有勤政爱民之“德”,还因为“德”本身就源于“天”,具有神性。《何尊》有言:“唯王恭德谷天,训我不敏。”唐兰先生释“谷”为“裕”,训为“顺”(52)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马承源先生释“德”为“德性”(53)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何尊》此句意谓周王以恭敬的德性顺承上天。巴新生先生则进一步指出,“恭德”与“顺天”为互言,敬德的本质就是顺天(54)巴新生:《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流变》,《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可见,敬德之所以能够顺天,就是因为“德”本身就源于“天”,与“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显然,文王之“德”同样具有上天所赋予的神性,敬德亦即顺天。
不仅如此,正是因为文王之“德”既有神性的神秘亦有人性的光辉,故能成为此后历代周王之典范。《诗经·周颂·我将》曰:“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55)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88页。《左传》昭公六年引此诗则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56)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44页。《大盂鼎》亦有言曰:“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57)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卷5第02514,第443页。《番生簋》:“番生不敢弗帅型皇祖考……元德。”(58)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卷10第05383,第170页。斯维至先生认为“型禀”与“刑型”就是《诗经》之“仪式”,而文王之德即文王之典,德也就是法典的意思,即道德本身即具有法典之意(59)斯维至:《说德》,《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需要指出的是,“文王之德并非后世的道德伦理,文王之典亦非后世的法典,而是文王以恭敬的心理与行为扬弃部落习惯法、原始禁忌,进而形成的敬天保民的‘德型’,所谓‘仪刑文王’云云就是视文王为范型(‘德’的化身)而加以效法”(60)关于“德”的演变,巴新生认为,作为氏族图腾之“德”最初为同氏族全体成员所共有,此后随着权力的集中以及图腾的父系化、个人化,“德”逐渐为部落首领所独享;当中国进入文明之初,“德”则由氏族部落首领演化而来的人王所独享。《尚书》中所见的“桀德”“受德”“文王德”就是例证。(巴新生:《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流变》,《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无独有偶,赵法生通过分析文王的所作所为,认为文王之“德”包括如下五项内容:恭敬天命、昭事上帝;惠保庶民,不侮鳏寡;勤勉政事,不遑暇食;明德慎罚,怀远柔近;礼贤下士,贤能归附(61)赵法生:《殷周之际的宗教革命与人文精神》,《文史哲》,2020年第3期。。此五项内容之中,第一项就是宗教方面的内容,其余四项皆为人事。可见,文王之德主要体现在天命与人事两个方面,文王一生兢兢业业,营造出一种迥异于殷人的新的精神面貌,堪称典范。此后,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继承并发扬了文王之德,将天命与人事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对此,傅斯年曾言:“一切固保天命之方案,皆明言在人事之中。……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为‘惟德之用’,如是之天道即人道论,其周公所创耶?”(62)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赵法生认为,傅斯年以“天道即人道论”解说周公之天人论,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实,周公的天人论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人道即天道论”。在周公那里,这两方面是相互为用、密不可分的。周公不仅“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他也“无一事舍天而言人事”(63)赵法生:《殷周之际的宗教革命与人文精神》,《文史哲》,2020年第3期。。这一观点确有洞见。自文王至周公,周人之德与周人之天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包含、相辅相成。只是随着社会的日益世俗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皇天上帝遥远而神秘,道德、人事则因人而成;故此,周人越来越重视道德与人事,对天则敬而远之。
最后,周人的天命观与西周初年的宗法制、分封制相结合,从而实现了超越性的天及天命与现实世界的血缘、地域的有机统一,构建出天子居中、诸侯拱卫中央的局面。《尚书·召诰》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64)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34页。元子即长子,也就是上天的大儿子。为了证实周人上承天命,周人甚至将其始祖后稷视为天帝之子(65)《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周人始祖后稷乃姜嫄踩到天地的脚趾而生,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再生载育,时维后稷。”,而且认为周之先王皆可“配天”(6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581页。罗新慧认为,西周时期的“配天”观念,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周王配天。强调周王之行合于上天,王是合格的天命接受者。二,天作配。意谓天选立周王为其下地之佐,强调天对尘世最高权力的决定作用,也显示王具有神性。(见氏著《周代的信仰:天、帝、祖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63页。)。在文王受命之后,历代周王代表上天治理天下,王权被赋予了皇天上帝的神性。同时,根据周初的宗法制度,历代周王都是周族之大宗的嫡长子,居于天下之中央;相对于周王,其他庶子都是小宗,他们按照远近亲疏、山川形势被分封到周王室的周围,在享有相应的爵位、封地、民众、赋税等权力的同时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周人的分封以宗法血缘为原则,所谓“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周人往往将同姓之国分封在宗周附近物产丰富、形势险要之地,而异姓侯国则被分封在较远的周边。要之,周人的天命观与宗法、分封相结合,使得周天子既是皇天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也是天下的大宗、天下的共主;周天子享有祭祀天地的特权,代表皇天上帝治理天下,成为天下的中心;周边的同姓、异姓诸侯从宗教、血缘、政治、文化等领域认同周天子的中心地位。可以说,西周初年的天命观与宗法制、分封制有机结合,将宗教、血缘、地缘融为一体,共同确立了中国大一统的基本格局。
要而言之,殷周之际殷人对于天命的认识尚处于矛盾之中,殷纣王认为天命不会转移,而祖伊认为纣王荒淫残暴,天命将抛弃殷人;与此同时,周人则认为天命会随着道德的有无而转移,正是由于文王拥有非常纯正的道德才得以受命。由此可见,殷周之际开明的殷人祖伊与周文王等人都认为天命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源,而道德在天命转移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从文王受命到周公制礼作乐,周人始终在围绕着如何永葆道德而孜孜努力,将礼乐制度贯彻到周人政治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周人(尤其是周天子及其他统治阶层)时刻崇尚道德。正如王国维所言:“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67)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7页。在周人看来,“德”可以向上承接天命,向下通过礼乐制度建构人间秩序;与之相应,拥有纯正道德的周天子即是“德”的化身,同样向上承接天命,向下通过宗法分封建构政治伦理(68)余英时指出:“周公‘制礼作乐’是礼乐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变动。概括地说,周初以下礼乐已从宗教-政治扩展到伦理-社会的领域。‘天道’向‘人道’方面移动,跡象昭然。……周礼是以‘德’为核心而建构的整体人间秩序,也可以称之为‘礼’的秩序。”(见氏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联经出版社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1-32页。)。可以说,西周时期的皇天上帝(天命)、周天子、道德、礼乐构成了互含相摄、相互为用的关系,具体表现就是:其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随道德而转移;其二,“文王之德之纯”,于是得天受命;周天子“仪刑文王”之德即可上承天命;其三,礼乐为道德之器械,有礼即有德。要而言之,在周人之天命思想与道德礼乐的背景下,敬德与顺天为互言,敬天保民与明德慎罚相辅相成,道德与礼乐互含互摄。因此,天命与人事具有了统一性,所以“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亦“无一事舍天而言人事”。
五、结 语
纵观原始社会到西周时期天人观念的演变,可以看出它们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人类从蒙昧无知、人物不分、民神杂糅的状态逐步走向觉醒与独立,人类社会的秩序亦逐渐形成与完善;与之相应,在此过程中天之观念的神秘性日益减少,理性因素逐渐增多。原始社会早期,在人类意识中人与自然界尚未分离,当面临着各种威胁与困境的时候,人们便幻想出各种各样的神灵并加以崇拜,所以,这一时期天的观念主要表现为神灵之天,而人则匍匐于各种神灵之下。原始社会末期以至夏朝,人类对自身与大自然有了一定的认识,人类社会的组织也从部落、部落联盟发展为国家;与之相应,这一时期天的观念一方面表现为鬼神之天在生产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人们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对自然之天的认识有了较大进展。殷商时期,殷人征服自然、治理社会及控御四方的能力有所增强,然而,殷人却极为崇拜神灵、遇事必卜;殷人的神灵世界主要由天神上帝、祖先神、自然神构成,殷人祭祀神灵的虔诚心理并非全是迷信,其间活跃着积极的自我意识与明确的对象意识。西周时期,周人制礼作乐,将道德礼乐、人文精神融入宗法制、分封制与井田制等制度之中,建构起较为和谐的人间秩序;与之相应,周人在继承殷人之上帝观念的同时又发展了天及天命的观念,重要的是,周人将天及天命与政权的合法性相联系,而且与道德礼乐融为一体,形成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天人观念。至此,天与人的内涵及基本特性的定型,以及天命通过道德礼乐与人事融为一体,天人范畴由此形成。这对中国古代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与发展方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