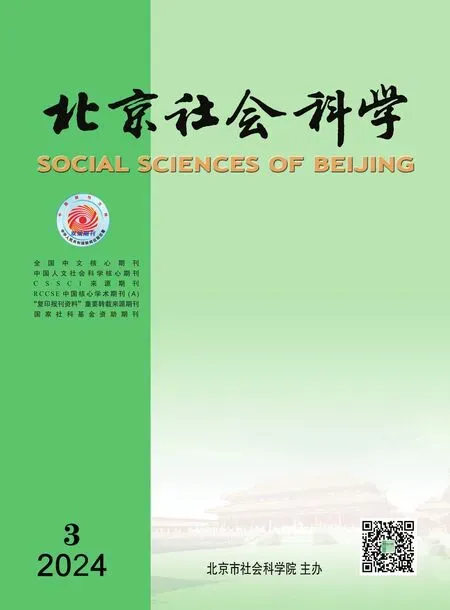图像、接受与生命
——兴象的现代诗学意义阐微
王明辉
一、引言
在中国古代诗学话语中,兴象是一个非常重要但被学界相对忽视的范畴。兴是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之一,代表了中国传统诗学对诗的一种根本性理解。象本是一个易学范畴,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的一种重要理解。至少在魏晋六朝时期,象就延展为古代诗学中的核心范畴。到了唐代,兴与象结合成为一个诗学范畴。这二者的结合,不仅仅是两个核心范畴在意义上的简单叠加,更是中国诗歌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后在理论层面的体现。兴象范畴在明清诗论中得到广泛应用,在理论内涵、使用范围等方面均有新的开拓,直到民国时期,还有学者运用兴象讨论问题。经过历代论家的使用与阐发,兴象已成为古代批评家把握和提炼古典诗歌艺术特征的重要理论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象范畴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兴象的理论内涵得到进一步发掘、阐释和拓展,极大丰富和加深了学界对此范畴的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学者们对兴象范畴的重视不断提升,却几乎没有人将其提到中国诗学核心范畴的高度。本文认为,兴象范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广阔的阐释空间,经过当代学者的阐释,兴象完全有理由成为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并为中国诗学落实“三大体系”建设提供理论资源。故不揣粗陋,略陈浅见,尚祈方家赐正。
二、图像诗学
在诗学领域,我们一般把外界的事物称为物象①,把诗歌中对这些物象的书写也称为物象。诗中的物象,主要是指物的名称,在古代文论中被称为物、景、物象或景物等。此时,这些词作为一个名词概念,尚不涉及情感和艺术表现等问题,然一旦物与情产生关联,则物象就可能转化为意象(或兴象)。意象问题暂且不论,我们先讨论兴象。何良俊曰:“袁海叟尤长于七言律,其《咏白燕》诗,世尤传诵之。而空同以为《白燕诗》最下最传,盖以其咏物太工,乏兴象耳。”[1]袁凯认为时太初《白燕诗》“尚未尽体物之妙”[2],故作《咏白燕》,那么他应该自信这是“尽得体物之妙”的作品。但李梦阳(号空同子)却批评这首诗“咏物太工,乏兴象”,可见兴象的审美重心已经不在体物、咏物上。这种超越体物的追求与兴象在中国文论中的出现时代有关。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诗人十分强调体物,“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3]。到了唐代,诗人们有了新的艺术追求,开始强调风骨和兴寄,进而有了对兴象的追求。殷璠在《河岳英灵集》②中首次以兴象论诗,正是对唐诗新艺术风格的敏锐体察。兴象不再强调对物象的精细刻画,也不仅是追求物与情的紧密结合,而是指向了更高层面的审美境界。对此,学界已经有很多重要阐释,但其重心多强调兴在象外,而对兴中之象却重视不够,兴象范畴中图像诗学的意义尚未得到充分阐发。
图像性是兴象的重要特征,但兴象所蕴含的图像性不在于语词层面对物象的描摹,它更强调超越语词符号、回归整体视觉审美经验。中国传统诗文具有音、形、义的多层审美追求,分别对应耳、目、心等感官,是听觉审美、视觉审美与思维审美的多重结合。兴象可以体现此三者的交集,起于视听审美,终于思维审美,是一种由耳目及心的高层次审美。兴象由视听审美发端,但又不同于直接的视听审美。比如偏重文辞者追求的“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4],这种审美主要是对文章中语词的发音、字形及表层意义的欣赏,偏重视听层面的形式美。兴象的审美追求与此不同,就文本而言(暂不涉及听觉),它更重视进一步发掘语词深层的审美意义,注重语词及其组合所呈现并引发的整体性审美体验,属于一种思维层面的审美。但兴象又不同于纯粹的思维审美,它仍属于感性领域,必须以象的方式加以把握和观照。兴象是“看”的结果,但却不缘于单纯的视觉的看,而是缘于一种超越感官视觉但进入思维层面后又保有图像性的内在观照,也就是所谓的“内视”[5]。因而,兴象是一种内视图像。
古代文论中常用“如在目前”来指称作品带来的画面感。一般来说,读者阅读文本后产生的画面感,并不仅指某个事物的图像,而是一种整体性图像,古人往往用“宛然”来加以形容。颜之推曰:“兰陵萧悫……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6]胡应麟曰:“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穷路’‘城阙辅三秦’等作,终篇不着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7]颜之推的“宛然在目”,也就是胡应麟的“兴象宛然”。前者“宛然在目”的不仅是芙蓉、露、杨柳、月,后者的“兴象宛然”也不仅是指城阙、三秦、风烟、五津、歧路、儿女、巾等任何一种物象,宛然指向的不是这些物象叠加形成的图景,而是由这些物象及其他语词共同构成的一种整体性的结构性图像。这一图像是可视的,但又不是直接出现在眼前的。兴象中包含着一种尚未完成构形的想象式图像,它具有图像的基本特征,但又有未完成的特点,是处于变化中的、充满创造可能性的开敞性图像。虽然语词决定了视觉想象的本质特征,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内视图像的所有细节,而这恰恰是欣赏者可以用想象和联想自我补充和完善的。或者说,兴象中包含一种前图像结构,从色彩来说,尚未着色;从结构来说,是框架、骨干,其作用是规定了内视图像的本质特征。不同的欣赏者可以为之丰富色彩、增添细节,甚至调节形状、比例,但基本框架必须与其本质特征保持一致。从此意义来说,兴象与英加登所说的“观相”有相通之处,兴象中包含“图式观相”的成分,又更接近于“具体观相”[8]。但兴象与这二者又都有不同,主要体现在,欣赏者头脑中最终完成的兴象是一种“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9]的内视图像。
内视图像可以分为多种情况,单个语词引发的内视图像、一句话引发的内视图像、整部作品引发的内视图像等,但目前并没有相应范畴对此进行区别。蒋寅先生曾撰文探讨意象等范畴[10],涉及了这个问题。蒋文以“两个黄鹂鸣翠柳”为例,认为“黄鹂”“翠柳”不算意象,只是物象,也是语象,只有“两个黄鹂鸣翠柳”这个完整的画面才是意象。我们借此作为思考起点,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选择用翠柳而不用垂柳、高柳、烟柳,当然有作者的斟酌考量,单纯将之看作物象或语象似乎并不妥当,为什么不能算作意象?第二,如果将“两个黄鹂鸣翠柳”视为一个意象,那么全诗四句又该如何界定?四个意象吗?依蒋文之意,全诗四句大概就指向意境了。古代诗学中“境”的概念应该具有空间感及身心参与感,故意境也不能单纯视为多个意象的叠加,因而以意境来指称四句诗呈现出的整体图像未必合适。审美体验中单个意象形成的内在视像与整体的内在视像有必要区分开来,兴象正可起到这种区分作用。
从图像诗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把意象看作文本中饱含情感的物象或物象组合,其根本特点在于,意象构成的图像必须基于物象,不存在没有物象的意象。兴象则是指,作品全部文本呈现出的一种整体性视觉图像,其根本特点在于,兴象虽然仍是图像,但已经超越了具体物象及其叠加,进入了新的审美层次。如潘知常先生认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鸡声、茅店、早月、人迹、板桥、晨霜,六个意象被组合到一起,并不是轮流用一个意象取代另一个,而是将它们叠印、融合到一起,改变各自的力度、方向、作用点,造成一种既不同于鸡声、茅店或早月,又不同于人迹、板桥或晨霜的全新的美学功能,这一美学功能不但不同于六个意象中的任何一个,而且也不同于六者相加之和,最终造成一种匆忙赶路的焦急气氛,取得极感人的艺术效果。”进而他指出:“抒情诗的意象结构确实蕴含着诗歌美学意蕴的全部秘密。”[11]这里对“意象结构”的阐释已经非常接近兴象。但兴象与意象结构仍有不同之处,兴象是全局性整体性的审美视像,存在着根本就无须具体物象的情况,读者在欣赏和把握兴象时也根本不在意其中是否包含物象,而意象结构则必须建立在物象组合的基础上。兴象可以不基于物象,存在没有物象的兴象。正如胡应麟所言:“终篇不着景物,而兴象宛然。”[7]文本中没有具体景物描写,但却可以在读者心中呈现出一幅视觉画面。陈伯海先生对《登幽州台歌》的阐释更可以说明这一点:“陈子昂的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正是从通篇直抒胸臆之中,烘托出诗人独立苍茫、俯视今古、长歌当哭、涕泪纵横的动人姿容。有人以为这首诗没有塑造形象,其实正是融景入情(把人物形象放在心态形象的背后)的好例子。”[12]
兴象不是简单的物象叠加,而是在作品文本的基础上,借助欣赏者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形成一种基于内在视域的视觉建构,追求一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视觉美感。在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这主要代表了唐诗的创作成就。虽然诗论领域内的兴象一词出现于唐代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但当时的兴象作为理论范畴尚属于一种模糊的直觉的把握状态。宋人虽然对此有所认识,但并未使用兴象一词。真正对兴象范畴进行深入阐发和运用的,是元明清的诗论家。尽管这些诗论家并没有对兴象的意蕴进行清晰定义,但在他们运用兴象进行批评的实例中可见其对兴象的基本理解。元明清诗论家创造的兴象浑沦、兴象玲珑、兴象宛然、兴象深微等美学命题,在理论上都突破了对诗歌表层视觉呈现的把握,转为探寻诗歌在整体情境下的内在视觉审美及在此基础上更深远的审美意蕴。当下,图像论与诗学的结合日益紧密,传统的兴象范畴在图像论视域中当有更广阔的阐发空间。
三、接受诗学
在古代诗学实践中,兴象范畴主要面对的是接受问题,诸如兴象有余、兴象标拔、兴象玲珑、兴象高远、兴象浑沦、兴象宛然、兴象萧疎、兴象深微等,多是从接受者角度对作品进行的审美评价,兴象范畴在此方面的理论内涵值得发掘。
(一)兴象接受的多重向度:生成、共生、生发
兴象具有生成性,是作品文本与读者体察到的审美意蕴之间的审美中介,是一种不可目视只能内视、不可言说只能直观的心理图像。或者可以说,兴象是在读者头脑中复现的作品,它当然不是作品本身,但包含了作品的本质特征及读者的主观理解,因而在不同程度上会对作品有补充、删减、变形和完善。兴象既充满不确定性,又因此包含多重可能性。这里的不确定包括象的位置、轮廓、形态、色彩、质地,也包括象与象之间的远近、高下、大小、多少等关系,甚至也包括观照与体验象的角度、姿态、心理等。兴象是一种未完成态的象的结构性呈现,指向丰富深远的审美意蕴,其结构关系的定型、内含意蕴的落实,都涉及接受的问题,与读者密切相关。
兴象具有共生性,可以看作作者和读者以文本为链接、以兴为契机、以象为媒介展开的审美经验的传递、激发、共振、交流与互动。按照兴“触物以起情”[13]的含义,读者阅读作品也是一种“触物以起情”,也是一种兴,其通过作品所把握到的内在视像当然就是兴象。这时的兴象中就包含了双重的兴。既有作者之兴,由作品传递出来的不在场的兴,也有读者之兴,在阅读作品时产生的即时的在场的兴。以读者在场的兴去呼唤、去抵达作者不在场的兴,正契合中国诗学传统中“以意逆志”的阐释观念。
再进一层,兴象具有生发性。读者面对作品,在审美体验中产生兴象,这其中的联想与想象都属于创造性的生发,这又是一种兴。正如顾随先生所说:“吾人读诗只解字面固然不可,而要千载之下的人能体会千载上之人的诗心。然而这也还不够,必须要从此中有所生发。……前说‘因缘’二字,种子是因,借扶助而生发,这就是生发,就是兴。……可以说吾人的心帮助古人的作品有所生发,也可以说古人的作品帮助吾人的心有所生发。”[14]算上这一层的兴,那么兴象中就至少包含三重兴的涵义:作品中包含的作者不在场的兴;读者面对作品时在场的兴,读者因作品而生发的兴。同时,也出现了三种象的涵义,作者之象、作品之象、读者之象③。如此,兴象沟通了创作与接受两端,可以开掘出更深广的理论内涵,也为接受者进入更高一层的审美体验——意境——铺平了道路。
(二)兴象接受的制约因素:语境、情境
接受者对兴象的把握受到语境和情境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语境是把握兴象的基础。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语词上。虽然我们认为兴象超越了语词符号,但同时兴象也不能完全脱离语词符号。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内视图像,兴象中包含着很大程度的视觉想象成分,而这种想象必须基于语词及其构成的文本结构。欣赏者首先要认可和尊重语词的规定性,不能抛开语词随意联想和想象。比如读到“悠然见南山”这句诗,我们当然可以根据个人理解进行不同的阐释,悠然的姿态如何?见的姿态如何?南山的状貌如何?这些都可以有言人人殊的个性化解读,但却不能背离基本的语词意义,比如将悠然误解为怅然、凄然,将南山误认为北山。这句诗当然是非常简单易懂的,但也有很多文本不那么易懂。葛晓音先生认为:“读懂文本为一切学问之关键。”[15]其实,不仅是做学问,即便是欣赏作品,也必须以读懂文本为前提。兴象基于对文本的理解,文本理解基于对语词的认知,因而,把握兴象必须尊重语词。其次,认知心理学认为,视觉系统会利用图像中的背景线索为物体赋予意义,而背景线索则会影响前景物体在人们视野中的呈现,感知颜色与感知距离都取决于背景环境。感知艺术形象也存在着类似的心理机制。在把握兴象的审美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语境的影响。这里的语境是指整个文本构成的相对封闭的语言结构(而非语用学中的语言应用场景)。同样的语词(或语词组合),在不同的语境下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兴象。从接受角度来看,语境既是一个文本场,也是一个心理场,不同的文本场会影响接受者的心理场。同样以南山为例,《国风·齐风·南山》中有“南山崔崔,雄狐绥绥”[16]。这一文本结构中的南山,其意义与“悠然见南山”中的南山大相径庭,两首诗令人感受到的兴象自然也大有不同。因而,读懂文本、明晓语境是把握兴象的第一步,也是兴象审美的基础。表层的读懂文本容易理解,也相对容易做到,而深层的读懂文本更难,需要涉及明晓语境、知人论世等。兴象审美看似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实际上却必须受文本和语境的制约,否则就可能流于妄想臆解。
另一方面,情境也对兴象有着重要影响。这里的情境包含着两种意义。首先是作者创作的情境。从创作角度来看,情境必然涉及创作者的性情、生平、遭际等。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17]尽管诗歌创作不等同于著书立说,但其背后的道理是相通的。“诗歌的背后是人,是无数活生生的个体,在诗歌中固然可以提炼出很多共同经验和共通情感,但更多的是不同个体的私人体验与私人情感,而这些是需要通过具体的、私人的、场景化的还原才可能把握的。”[18]把握兴象也需要紧密结合作者当时的境遇,深入体会其可能产生的心境,才能对作品的兴象有更准确更深刻地体察。其次是读者欣赏的情境。兴象必然受到读者欣赏时的情境影响。兴象更强调基于当下的在场的审美体验,这是一种互相生发、互相感动、彼此交融的对话式审美体验,而不是将作品视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把握,这也正是兴的关键所在。在兴象的生成和体验过程中,欣赏者参与其中、融于其中,欣赏者本身的情感体验和兴发想象,都是兴象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哈姆雷特作为人物只有一个,但作为人物形象,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可能有一万个甚至更多个哈姆雷特。这是由于,在不同的情境下,同一个读者可能对同一个作品、同一个形象产生不同的审美理解,构建不同的兴象。再如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给处于不同情境的读者带来的审美兴象也大有不同。对于一般的阅读情境而言,这句诗带来的兴象可能不过是明月与雄关而已。但倘若是一位有历史感的读者正在感慨历代边疆战事,他由这句诗中体会到的兴象则应是历尽沧桑而不变的明月与不知经过多少次战火冲击、经历无数次重修而面目全非的雄关,而这还不是全部的画面,其背后还有千年的战与和、绵延不断的血与火、无数战士的豪情与幽怨。此时,明月、边关、锋镝、铁马、朝堂、闺怨等无限意象、无穷思绪纷至沓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此时审美活动进入一种高峰体验,仅靠视觉画面似乎已经无法承载读者心中激荡的感悟和体验,审美活动将自然趋向于身临其境的想象,意境就很自然地成为兴象之后的审美阶段。
(三)审美接受的逻辑次序:物象、意象、兴象、意境
循此思路,我们认为,在审美接受过程中,兴象是抵达意境的必由之路,而且是最后一站。很多学者已经关注到“象外之象”与诗境、意境的关系,但并未从此角度得出结论。司空图《与极浦书》曰:“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9]“目击可图”代表的是视觉之像,以逼真和再现为旨归,指向的是物象,也就是“象外之象”中的第一个象。“诗家之景”中充溢着作者的情思意兴和艺术创造,代表的是“象外之象”中的第二个象,其特点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这正是对内视的最好解说。古代诗学中的意象与兴象都具有“象外之象”的特点,为区别二者,上文从视像方面提出一种新观点,即意象更偏重具体,需要基于物象或物象组合,偏实;兴象更偏重整体,不一定需要基于具体物象,故偏虚。意象距离物象更近,兴象距离意境更近。如此,我们就可以排列出一个审美接受的逻辑次序:物象、意象、兴象、意境。
有学者不同意意象(兴象)与意境之间存在层级关系,因为二者之间未必有艺术的提升。[19]这种质疑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试从接受诗学的角度尝试给出一个解释。就接受者而言,面对一个艺术作品,大概可以经历“目、心、身”三个审美阶段。目,代表外在的看,这是一种视觉动作,眼睛所看到的只是纯形式的存在(此中存在辨识的成分)。此时的艺术作品尚未能成为审美对象,比如心不在焉的游客在美术馆参观或毫无兴趣的学生在语文课上读诗。这也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看,其结果很可能是视而不见。心,代表内在的观。一方面,接受者用心去体察,开始将注意力真正集中在艺术作品上,这时他所面对的就不再是与己无关的他物,而是审美对象。另一方面,接受者在观赏的同时,会产生内在视像,即经过自身情感经验加工过的审美形象。意象、兴象,都属于这个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阶段,虽然可以内视但尚未身临,接受者还处于一种旁观的立场,没有真正沉浸其中。此时的接受者仍是欣赏者而非体验者,其审美活动属于欣赏而非体验。身,代表着亲临其境的体验,接受者不再持旁观视角,而是融入其中,成为境中的一部分,这就进入了不知庄生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生的物化境界。
王幸福是以一个老光棍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屋子里的。你不同他说话的时候,你会以为他是哑巴。必须要说话的时候,他也是木讷的。他的目光不正视人。他会躲到门外的楼道里抽烟,但常常被李大头叫回来。李大头似乎是怕他跑了。乔三喜做饭的时候,他会去帮他,李大头会把他推开,说,你到外屋待着。李大头说他脏,公开表示对他的嫌恶。李大头的态度感染着我们,我们也都对王幸福表示出嫌恶。但王幸福似乎感觉不到这些,他慢慢地吃饭,早早地睡觉,很早地起来去室外寻公厕。
将“物象、意象、兴象、意境”作为审美接受的次序,这种提法未必成熟,但却可以为同仁从接受层面研讨审美活动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此思路中,兴象代表着图像性审美、观赏性审美的最高阶段,但兴象不是审美过程的终点,结合生命体验的意境才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最高审美理想。
四、生命诗学
尽管兴象作为一个诗学范畴,与作品形式和审美活动密切相关,但从本质而言,兴象不是形式诗学,而是生命诗学。生命诗学的提法与西方的生命哲学密切相关,但我们不同意某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诗学“没有切入到人的生命的核心”[20]的说法。虽然中国传统中没有生命诗学的提法,但对生命诗学的追求却一直都在。我们在此不讨论生命诗学在哲学层面的意义,也不辨析其在西方美学领域内的复杂内涵,而是从广义的角度来发掘兴象中蕴含的生命诗学。
(一)生命感发的审美表达
兴象来自中国传统诗学,兴是感发生命,象是审美观照,二者结合正体现了中国诗学的生命审美特质。心物交集产生审美早已为中国文论家所揭示,《诗品序》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1]《文心雕龙·明诗》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2]叶嘉莹先生认为,这种人心与外物的感应,其基本原因在于生命的共感。她说:“在宇宙间,冥冥中常似有一‘大生命’之存在。此‘大生命’之起结终始,及其价值与意义之所在,虽然不可尽知,但是它的存在,它的运行不息与生生不已的力量,却是每个人都可以体认得到的事实。……‘我’之中有此生命之存在,‘物’之中亦有此生命之存在。因此我们常可自此纷纭歧异的‘物’之中,获致一种生命的共感。”[23]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万物背后存在着一个共通的生命,人是万物之一,诗也是万物之一,因而他们都是有生命的。钱钟书指出,中国文评的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24]。蒲震元提出:“中国传统艺术批评中重艺术生命整体特征(或曰重艺术生命整体美)批评的另一种常见形态,是以天地万物所表现的生命有机整体性特征来观察艺术作品,这里姑称之为‘泛宇宙生命化’批评。”[25]这些观点都可与叶嘉莹先生所说的“大生命”互相印证,其背后是“气化流行”“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中国传统的生命观,也是中国诗学的生命观。
中国诗学本身就包孕着生命诗学。从创作发端来看,先是世间万象的生命活动触发了作者的生命感动,作者因而情感活跃,灵感勃发,无论是欢喜怡悦,还是愁苦忧郁,亦或愤怒悲慨,这些情感波动都是生命的表现形式。苏珊·朗格认为:“情感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中、强化了的生命,是生命湍流中最突出的浪峰。”[26]《毛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27]韩愈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28]对于创作者而言,情感波动自然会产生创作冲动,因而其作品中势必带有强烈的情感特征,也就是生命特征。当艺术作品完成以后,欣赏者面对作品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共鸣,进入一种如痴如醉的欣赏状态,这又是一种生命感动。在创造和欣赏的全部过程中,象与兴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所谓“兴必取象”[29]。中国诗学追求的审美理想就是兴起之情与表达之景融为一体、“互藏其宅”[30]。
(二)生命经验的审美应答
兴象作为接受者审美体验中的重要环节,正是将作者传递的生命图景与读者既有的生命图景结合的关键节点,其中充溢着生命经验的流通往复,也可看作“情往似赠,兴来如答”[31]在内视层面的实现。我以我手写我口,是一种生命诗学。我以我眼看我心,也是一种生命诗学。从作品中发现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体察与构建自己独特的审美兴象,以生命呼应生命,当然更是生命诗学。虽然兴象要以作品文本为基点,但它已经超越了作品的形式层,近乎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形象层[32]。我们强调的是,兴象中必然包含着真实的生命体验,这是语言符号甚至其他艺术符号很难直接表现的。当我们读到“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诗句,所引发的兴象中不仅会呈现出包含了风雨、落花等的内视图像,还会包含着字面无法表现出的内容,比如风的温度、雨的湿润与花的芳香,这些都超越了视觉感官,其实已经溢出了视觉器官所能感知图像的界限。在兴象中,欣赏者所有的生命体验,感官的、心理的、意识的、潜意识的,都可能会借此得以呈现。此时,兴象也可以看作欣赏者自我的生命经验及生命图式通过艺术品得到的感性印证与审美应答。进而,如果把世界看作一种作品,那么作为世界的观赏者和接受者,我们也会产生对世界的兴象。对此兴象的直观、体验与领悟是我们生命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内容。因为我们在意的其实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我们眼中的世界,或者说是世界在我们心中的兴象。
正如叶嘉莹先生指出的:“中华民族是有灵感的,重直觉的,常常有归纳性地写出一个很珍重的很宝贵的概念……我们的缺点就是缺少那逻辑性的理论性的规范化的那种说明和分析……我们如果看一看,再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的传统诗论,就可以用他们的一些个逻辑性的理论,来对我们的一些概念加以说明。”[33]兴象就是这样一个“很珍重的很宝贵的概念”。中国古代诗论家们很少对兴象这样的范畴进行细密分析,而是采用一种用法即意义的思路,在具体批评情境中以此范畴来表达自身对某种艺术境界的深刻把握。在中国古代诗学的很多审美实践中,范畴是起点,也是终点。范畴背后所指向的审美境界,需要读者以自身的“学养、灵感、慧心”去补充、体察与感悟。中国诗学的核心在于体验而不在于分析,兴象所代表的生命诗学的终极追求即在于此。
(三)警惕脱离生命体验的话语生产
我们对兴象的分析与阐发,目的是发掘这一范畴可能蕴含的深刻理论内涵,但实际上这种操作恰非兴象所指涉的真正意义。兴象作为一个中国传统诗学范畴,正与诸多同类范畴一样,指向的是一种事实存在但随时而动、难以言表的审美经验。这种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此类范畴正是源自生命体验的审美观照,生命是跃动的,审美是跃动的,范畴也是跃动的。所有的知识话语都是指向月亮的手指,诗学的终极目的不是范畴不是理论,而是指向洋溢着活力的审美体验,指向生命本身。重提、激活一个范畴的最好办法其实不是理论阐发,而是在审美体验和批评实践中多加利用。期待更多的传统审美范畴可以真正进入我们的批评实践甚至日常审美,那才是传统文化真正意义的复兴。
五、结语
当下的中国诗学研究是在与西方文论的对话中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一些原属于中国古代诗学的范畴由于和西方话语具有一定的共通性而被继承发扬开来,如意象、格调等,它们顺利进入了现当代诗学领域。但也有一些古代诗学范畴与西方话语共通性较少,因而无法在以西方话语为主要言说方式的现当代诗学研究中获得立足之地,只能成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内部话语。除了相关领域的学者之外,这些范畴受到的关注和研究非常有限,如兴象、文脉、势、态等。然而,这些范畴对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不同于异质文化的经验和表述,正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和建构自身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基石。学界已有很多成果正在揭示和阐发这些范畴的意义,兴象受到的关注也日益增多。在中国古代诗学领域,多数学者使用兴象都会与唐诗联系起来,但也有人如胡应麟、方东树等力图将兴象范畴扩大到整个古代诗歌范围。在古体诗与近体诗、唐诗与宋诗对举的情况下,兴象的意义更偏向近体诗和唐诗。而当下我们面对的文学局面是古诗与白话诗对举,中国诗与外国诗对举。在此形势下,兴象完全有可能也有理由成为古诗乃至中国诗的代表性特征之一。与意象和意境相比,兴象是受到忽视但又不应被忽视的一环。兴象比意象更偏重整体,比意境更偏重视觉形式,在逻辑上正可视作意象到意境的中间环节。在继承前辈学人的基础上,如何将兴象进一步阐释为中国诗学的核心审美范畴,构建意象—兴象—意境的审美次序链条,进而整合其他具有民族性的批评范畴,构建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体系,开展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新时代文艺批评实践,正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
注释:
① 此处的物象仅指具体人物或事物,不包含抽象名词。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对于文本中的抽象名词及其他非物名词如何界定一直没有形成共识。有学者以语象来加以指称,但语象来自西方文论,是对不同外文词语的翻译,本身所指并不明确,国内学界对其具体内涵的理解亦大有分歧,故暂不提及。参见赵毅衡、陈晓明、蒋寅、孙春旻、黎志敏等学者的论文。
② 《河岳英灵集》是唐代殷璠编选的专收盛唐诗的诗歌选本,提出了兴象说、音律说,鲜明地反映了盛唐时代诗歌高峰期的创作特色和理论特色。
③ 三重兴与三种象并非一一对应,但均从不同层面呈现了兴象的丰富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