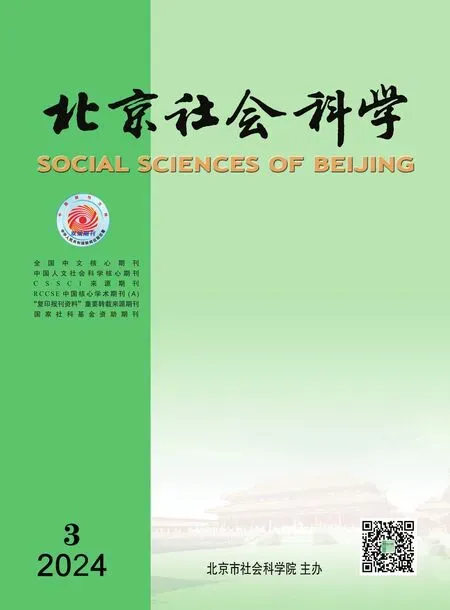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美学意蕴及当代启示
孙琳琼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深刻指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系。虽然不同群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美好生活应然包含“美”和“好”两个基本向度,其中,好生活是美生活的现实基础,美生活则是好生活的理想升华[2]。在政治哲学视阈中,“美好生活”一般内蕴正义、平等、自由、解放等价值尺度,抑或说,是否具有这些“内涵”可以作为审视一种生活是否“美好”的原则和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美好生活”不仅表征基于需求的个体生活状态,更表征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政治规范性要求。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美好”从来不是抽象的理念预设,也不是与现实相适应的理想状态,而是深嵌于无产阶级的现实生产劳动之中,与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关。无论是在早期还是成熟时期的作品中,马克思都将艺术活动作为真正自由的劳动的典范来看待[3]。在现实生活中,“美好”的向往既需要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更需要能够塑造审美主体的政治经济客观条件。马克思就是坚持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理想生活的建构,不仅确证了“美好生活”的未来景象,还指明了通达“美好生活”的现实之途。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美学维度,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为人民立足现实创造美好生活提供启示。
二、基于审美视阈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的自由活动之间的对抗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一般作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美学思想的重要参考文本。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意义上阐释了人的本质与美的规律之间的关系。在恩格斯早期研究的启发下,马克思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尝试解决困扰他的“苦恼的问题”。马克思从摘录他人观点的《巴黎笔记》开始,逐步过渡到《手稿》的写作,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他持续近40年的研究主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及诸多政治经济学手稿中均提到美的问题,显然不是随意提及,也不是为了创造出一套美学理论,而是为了更好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自在自为的审美之境是人生存的理想之境,体现了人的有限性和超越性的内在统一,在现实社会中,审美活动的实现通常需要主客观方面的条件,即具有审美能力的现实的个人和审美对象。马克思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损坏了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现实生活已然成为人民从事自由自觉审美活动的桎梏。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审美活动丧失主体条件
审美活动的主体条件是具有健康身心的人。当人经常处于疾苦中或人的精神境界未达到一定水平时,审美活动就不会发生。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展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无产阶级身心造成的损害。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损害无产阶级的身体健康。资本只以增加利润为目的,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4],否则资本家对工人健康问题是毫不关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身体损害的最高程度也是首要表现,就是使工人失去生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当时医生的话描述了“累死”现象,这一现象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生意兴隆的地方。马克思深刻指出,与从事过度劳动的人的死亡速度相似,死者的空位马上有人补充上,似乎对生产运转毫无影响。
即使工人没有因为劳动直接失去生命,但他也会因超强度的劳动缩短寿命。马克思引用1864年的公共卫生报告指出,职业造成无止境的肉体折磨致使成千上万男女工人缩短甚至丢失了生命。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本唯一关心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资本家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把工人看作与生产资料一样的消耗品,不断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无论工人健康与否。马克思引用北明翰市长在卫生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当时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而在利物浦,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
在工人短暂的生命中,他们的健康状况是非常恶劣的。1852年至1861年间,在从事花边生产的女工中,患肺病的比率持续上升。陶工“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型的”[5],患瘰疬病的陶工占三分之二以上。从事火柴制造业的工人,“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他们患上一种被称作“牙关闭锁症”的职业病。马克思引用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痛斥道,资本“依靠工人的劳动和技巧,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但伴随而来的是工人身体退化”[6]。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工人的畸形为条件的,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之前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工人身体上的畸形化就已经形成了。而工场手工业阶段工人畸形化程度的加重则形成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当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之后,工人身体的畸形化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此,马克思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而一切所谓“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这些做法的结果就是使工人“被贬低为深受劳动折磨的机器的附属品”[7],成为局部的人、片面的人,工人的生活丧失丰富性,最终沦为一种谋生行为,畸形发展。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害工人的精神世界。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8]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在较差的社会风气中成长,未能养成合格的道德感。工人难以得到像样的教育,无法获得合格的知识。由于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平的低下,工人获得艺术修养几乎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工人道德的败坏。马克思引用1866-1867年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儿童在道德方面产生的极端负面影响,即儿童在社会氛围的影响下如何逐步走向堕落,在这种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少男少女往往“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9]。而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经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的做法,也使得很多人相信,在这种条件下,道德的败坏已然成为必然的选择和结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在恶劣的工作、生活和居住环境下成长,未能形成良好道德修养。
除了限制工人道德水平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蚕食了工人的受教育权,使工人在知识水平上也得不到提升。英国法律规定,儿童每天要受到一定的义务教育。资本主义学者则声称,儿童时代到10岁就结束了,并成功迫使政府将儿童的界限从13岁下调为12岁。政府要求儿童每天最多只能劳动10小时,以保证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工厂主则借口细巧的织物需要灵巧的手指,而这只有年幼儿童才具有,因而反对政府对儿童的保护。事实上,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当时社会能够提供给儿童的教育资源是非常差的,不少学校的教师是否具有教学资格、是否识字是受到质疑的,“儿童只得到上学证明书而受不到教育”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比比皆是。
由于没有养成较好的道德情感,也没有得到足够的知识文化,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几乎不可能具备审美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劳动时间尽可能地被延长,以至于就连儿童都不得不面对不牺牲些睡眠时间,就没有时间游戏的生活状态。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夺去了儿童的游戏时间,还夺去了家庭范围内满足某种需要的自由劳动时间。由于没有游戏和从事自由劳动的时间,工人就不可能形成审美能力,也不可能从事需要较高修养的审美活动。工人只能在酒精的麻醉中逃避现实的残酷,他们“染上了各种恶习;酗酒、赌钱等等,完全堕落了”[10]。儿童和青少年在街上“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11]。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审美活动丧失客体条件
资本主义不仅摧毁了审美主体,而且摧毁了作为审美客体的精神劳动产品。资本主义摧毁了原有的艺术形式,且不能产生出新的富有灵韵的艺术,使审美活动丧失了客观条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同以艺术和诗歌为代表的“某些精神生产部门”之间的敌对关系。
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原有的艺术形式消亡了。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受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制约,但同时,物质生产的发展也同艺术生产存在着不平衡的关系,艺术的繁荣并不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铁道、机车、电报、避雷针、动产信用公司、印刷厂等这些资本主义时代新出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与自然原有的关系。自然不再是人所敬畏的领域。特别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自然逐渐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得希腊神话不再成为人们的信仰,也使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希腊式的艺术“停产”。古希腊艺术因此成为再也回不去的绝唱。在资本主义时代写作史诗,似乎已经不合时宜。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不可能产生新的具有灵韵的艺术作品。资本造成审美观的扭曲,使艺术品的创作更多关注商业价值而不是精神价值。资本主义审美观的扭曲最集中地体现在对金银美的理解上。金银,原本是因为它独特的光泽和灵活多变的形式而被赞美,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们对金银美学价值的看法。金银之所以被当作美的,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强大的“魔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的描述,生动地展示出在资本主义对金银的崇拜中,财富的创造和占有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并不可阻挡地向艺术领域扩张,审美的内核自此被消解。金银作为货币,是财富的直接体现,它能使一切美化,因而是最美的东西。美不再属于艺术,而是属于金钱,艺术的灵韵变成了金钱的万能,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审美观的扭曲。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一切劳动必须换算为物质劳动才得到存在的合理性,即便是“最高的精神生产”,如果期待得到承认,也只能因为“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12],从事写作、绘画、作曲、雕塑的人作为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人,即非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服务”只有被加入生产,才能被看作“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这样的劳动才能得到社会认可。于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艺术创作成了和商品生产一样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角斗场。马克思以编书为例,他指出,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生产的人,工匠或行家,都是在“为书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13]。资本家不关注艺术创作的质量,只看重艺术生产是否给他带来利润。利益原则代替了审美原则,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衡量艺术的标准。在利益标准的指引下,所生产出来的艺术唯利是图,而非注重精神价值的凝聚,艺术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了仅仅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没有灵韵的工具。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破坏了原有古典艺术,也不能产生出新的具有灵韵的艺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自觉的审美活动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缺席。基于此,马克思对如何恢复审美活动在人的活动中应有的地位,打破限制人的自由活动的藩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三、基于政治经济学视阈看审美活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及其限度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系统揭示了资本的逻辑并走向人的逻辑。马克思认为,仅仅依靠审美活动是无法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的,需要进一步追问审美活动得以存在的基础。
(一)审美活动自身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及限度
马克思发现,审美艺术活动自身具有一定的突破资本原则的可能性。一方面,在艺术鉴赏上,资本主义的价值原则不能完全应用于艺术品的价值上,艺术品价值具有不受资本主义定价原则限制的可能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援引富兰克林的观点指出,鞋匠的劳动、矿工的劳动、纺织工的劳动,尽管是可以和画匠的劳动交换的,但用鞋、矿产品、纱来衡量画的价值却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的定价原则,即将一物的价值看作与它交换的物的价值,二者的价值皆可以抽象为一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于是万物都有了可以量化的价值。资本主义的定价方式只涉及量,而不涉及质。资本主义是靠一个外在于艺术品的、与之相交换的他物来给艺术品定价的。但艺术品的定价方式决不能是量的,不能是外在的。于是,艺术品自身的价值就与资本主义的定价原则相抵触,艺术品自身体现出不受资本主义价值原则支配的可能性,即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艺术创作具有不受资本主义生产控制的一面。艺术创作既有为资本增殖服务的一面,同时还有与资本增殖无关的一面。艺术创作作为一种劳动,具有不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的一面。对此,马克思将创作《失乐园》的约翰·弥尔顿与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创作的作家相比较,认为密尔顿的创作源于天性的能动表现,虽然《失乐园》的出售使他获得5英镑,但他依然是非生产劳动者,而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同样是艺术的创作,既可以落入资本主义的工厂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也可以不落入资本主义工厂,成为非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即自由活动。马克思还以歌女的例子来说明艺术生产不受资本主义控制的可能性。自行卖唱的歌女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她没有参与资本的生成过程;但被剧院老板雇佣去唱歌的歌女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当唱歌是为了赚钱时,她就已然参与了资本的生成进程中,是否参与资本的生成过程也是我们评价艺术活动本身性质的尺度。
艺术能否作为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抗衡的独立领域,如“审美乌托邦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成为战胜资本主义的基础呢?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艺术生产对资本主义超越的限度进行了讨论,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马克思认为,这里的大多数情况,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书画和表演等艺术形式,都还只是“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形式”[14],艺术创作大规模地步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总体而言,艺术创作正在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言,今天,西方消费文化的兴起,艺术商品化、商品艺术化,文化已成为文化产业,无论是艺术产品还是表演艺术,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中。艺术活动不仅没有保持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立性,而且完全被资本化。
通过充分发挥艺术活动相对独立性,冲破资本主义统治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了,这就有必要继续追问艺术活动的存在基础,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谈论恢复人自由活动的方式。
(二)审美维度的恢复表现为自由时间的恢复
什么是社会存在的艺术活动得以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必须先满足吃、喝、穿、住等一系列基本的生存需要,然后才能从事政治、文化、艺术等活动。当人的生产有了剩余之后,才可以从事艺术活动,人的审美—自由活动才会得以展开。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古代人“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资本”,“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艺术品,用于宗教的和公共的建筑”[15]。古希腊辉煌的雕刻、神话史诗和建筑艺术,正是发生在物质生产的剩余上。审美意识出现的基础是剩余产品的出现。
剩余产品本质上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财富,剩余产品也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它是由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而劳动,是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的运用。因此,劳动可以归结为时间,剩余劳动在同等意义上,就可以被归结为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指超出工人再生产自身的那部分劳动能力,这部分对于工人而言,是超出他们必要劳动而进行的那部分劳动时间,是工作存在的需要。人的生命活动表现为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活动。劳动即是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所进行的活动。在自然状态下,当劳动足以满足人的需要时,满足需要的劳动就将停止,这是必要劳动时间的截止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工人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限制,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仍要从事劳动时,即剩余劳动时,他的劳动就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满足了其他人,即满足了剥削阶级的需要。因此,剩余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表现为被剥削的时间。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即一部分人的自由以另一部分人的被奴役为条件。在对立的阶级之间,“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16]。这意味着,一方生产的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另一方的自由时间。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是自由时间,正如剩余劳动产品、剩余价值从它真正的主人即工人手中转移到了剥削阶级手中,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自由时间也转移到了剥削阶级手中,但这并不改变自由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于是,我们看到,社会存在的审美维度赖以繁荣的基础——剩余产品,本质上是自由时间。
什么是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和社会存在的审美维度有何联系?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是真正的财富,是人全面发展的空间,是人的审美自由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础。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17]对此,马克思进一步解释道,“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被理解为“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18]。《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再次体现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即“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19]。马克思反复强调,自由时间即是财富。而“财富”(Vermögen)一词在德文也有“能力”的意思。说自由时间是财富,也意味着自由时间是人的能力发展的基础。自由时间是人的能力获得全面发展的基础,人的全面发展自然也包括了人在审美领域的发展,故自由时间是人进行自由活动的基础,社会存在审美维度的恢复也建立在自由时间的基础上,因此,对社会存在审美维度的恢复就成了对自由时间的恢复。
(三)实现自由时间恢复的两个条件
马克思认为,恢复自由时间有两个条件,一是在生产关系上取消剥削,二是在生产力上节约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这两个条件给出了说明:“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20]这段话表明,马克思、恩格斯视阈中理想社会具有两个标志:剥削将不复存在;一般物质劳动花费的时间显著缩短。
自由时间的恢复,首先需要改变现有剥削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痛斥道:“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21]资产阶级剥夺了属于工人的自由时间,使社会中占大多数的劳动者丧失了自由时间。要恢复大多数劳动群众丧失的自由时间,就必须调整生产关系,消灭剥削制度。马克思看到,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都是一方能力的发展以另一方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社会中存在着一些不劳动的人,这些不劳动的人,不仅从劳动者那里获得了生活的物质条件,而且还获得了他们的自由时间。必须改变使剥削者不劳而获的生产关系,即取消资本主义私有制,取而代之以公有制,使工人的剩余价值不归资本所有,而是归社会所有,而工人又通过联合起来,共同占有剩余劳动,从而占有自由时间。
自由时间的恢复,根本要靠生产力的发展和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为了使个体性得到发展,必须“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这样才能“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使个人“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2]。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将劳动时间缩减到足够小的范围内,人才有充足的自由时间从事艺术活动。但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并不意味着降低需求,而是相反,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要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已经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经济—节约,就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即将生产费用降低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同于在发展生产力,因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23]。发展生产力就成为恢复人的自由时间,进而恢复人从事审美的自由活动的根本条件。
当工人拥有了自由时间,就意味着过量劳动伤害人身体的情况就能得到遏止,也意味着工人拥有提高精神生产的可能空间。工人恢复了从事审美活动的身心条件,在自由时间里发挥自己的才能,将自己的精神世界作为被改造的对象,由此恢复工人自身活动和劳动产品的审美维度,使自由自觉的活动成为可能。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工人重新占有自由时间,是人的自由活动得以恢复的根本途径。
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美学意蕴的当代启示
我们从审美活动这一自由自觉的典范活动出发来审视理想生活可以看到,马克思在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及其深层次原因时,没有以纯粹的“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展开,也抛弃了从抽象国家理性出发的“权力批判”道路,而是以现实人的生存状态为实际考察对象,在自由理想与现实生存的辩证张力之中,深入现实并寻求现实通达自由理想之途。正确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审美维度,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顽疾,突破“物的关系”的局限性,更好地通达生活之美好。
(一)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
近年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潮流中,倡导“回到马克思”,尤其是“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呼声越来越高,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哲学语境、历史语境与国际语境等,也成为一种研究趋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突出的特点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这里所说的哲学,不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也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即从人的生存论意义上考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不是从个人主体的预设出发,也不是从个人行为的视角出发,而是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考察现代经济过程。从哲学美学视阈出发,能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在哲学视阈中,我们可以看到审美活动与人的本质以及人的自由之间相关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阈中,我们不仅看到审美活动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更看到审美活动与政治经济活动以及精神生产等多方面的关系。立足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美学意蕴的思考,我们看到马克思如何将理想社会的生成扎根现实政治经济批判,以理想的生存状态照亮现实生活。马克思强调人但没有深陷人本主义泥潭,强调现实也没有走入经济决定论的怪圈,就根本而言,就在于他很好地处理了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对自由理想的展望更多地体现在实现自由理想的现实道路的思考和规划中。对马克思来说,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不是伦理的预设和逻辑的推论,而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统一的客观趋势和结果。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是作为严密思想体系的理论武器,而不是支离破碎的思想碎片。[24]只有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才能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洞见时代,以不断提升的体系化研究和学理化阐释水平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进程。
(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的理想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的定位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那里,“美”从来不是抽象的理念预设,也不仅仅是与现实相适应的理想状态,而是深嵌于无产阶级的现实生产劳动活动之中,与个体的自由自觉活动和自由全面发展相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开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具有指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深切的审美观照,当然,这里所说的审美不是理论形态的美学,而是内化于改造世界与创造历史的活动之中的价值追求,是现实的理想性之维。在把握美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的定位问题上,许多理论家是背离马克思初衷的,如以马尔库塞、阿多诺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关于人类解放的美学话语从对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中释放出来,使之获得独立意义。将审美局限于精神解放、个体解放的层面,导致审美活动失去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到这一问题,尝试以审美介入激活政治话语、塑造感性共同体等方式重建美学与现实的关联,如巴迪欧(Alain Badiou)以“非美学”概念呈现丰富的政治内涵;齐泽克(Slavoj Žižek)尝试融合美学政治批判和精神分析视阈;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运用美学视阈透视生命政治规范,使美学以非实在性的感知方式重返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借助交叠辩证法实现对真理的交往拯救,为审美寻求参与政治交往的现实之途;朗西埃(Jacuqes Rancière)以平等预设沟通政治和美学,重思艺术参与政治斗争的方式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阐释,但本质上依然是理论建构,并未真正将美好嵌入现实生活本身。
(三)有助于为人民立足现实创造美好生活提供理论启示
正是立足审美这一独特视阈,马克思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和局限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使人失去本质力量的同时,也使审美的艺术活动沾染上资产阶级美学的机械化、单质化等习性而走向衰落。为此,马克思提出,通过历史的解放进程将人从资本统治的片面性中解放出来,使人重获精神的富足与文化的繁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人民美好生活,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并以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评价标准,既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内容,又体现出审美理想之维,将人的有限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跃升为对自由理想与本真生存的更高层次的回归。这一点,无疑体现了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审美维度启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并不是以另一方的完成为逻辑前提。美好生活的追求绝不成为脱离生产领域自娱自乐的消遣,应当多方面和多层次地嵌入人们的实践活动总体,并与人的理想性追求保持关联。特别是在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冷静分析资本逻辑与审美价值的博弈,尝试解答如何在市场洪流中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个体的身心协调发展。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美学意蕴,有助于指导人们立足现实创造美好生活,把握美好生活追求的理想之维和现实之意,为新时代审美文化建设提供启示。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审美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展和开辟的重要维度。正是基于对审美维度的自觉关照,马克思逐步实现了对隐藏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整体生存结构的考察。这一考察,从更深层次来看,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的活动方式与存在方式的考察,是立足现代工业社会内在矛盾对未来社会的考察,是对人的自由解放的现实途径的考察。在上述意义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审美维度,为我们回答了人类存在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这对于理解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内涵及其内在标准,深入推进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