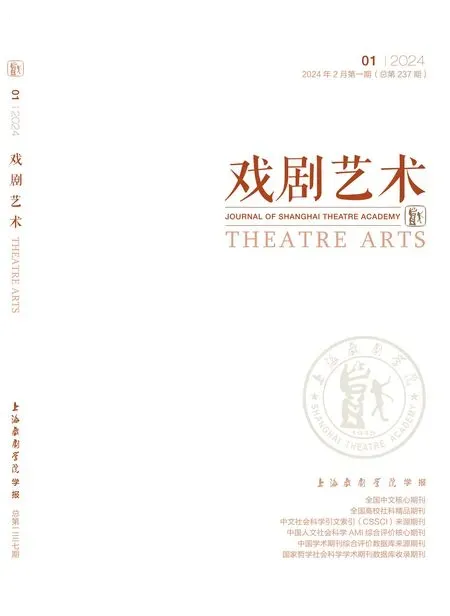论“行事”的叙事意义
——一个探索“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的叙事活动的特别视角
袁国兴
一、“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的影像表意特征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9页。“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在亚里士多德的话语体系中,可能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诗人用言语述说的方式把人物动作表述出来。比如他说,“假如用同样媒介摹仿同样对象,既可以像荷马那样,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或化身为人物),也可以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第9页。在史诗中,“叫人物出场”或“化身为人物”,只是说在表意形态上借用了人物的动作,至于怎样呈现和表达这些动作,却可能有不同的手段和方法。起码在荷马那里,这些都与诗人的言语述说行为有关。亚里士多德“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的另一种可能是用人物动作表达人物动作。悲剧与史诗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物的“出场”方式不同。因此亚里士多德才特别强调,悲剧诗人在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之外,“还可以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第9页。。“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当然就无须什么人再用言语述说的方式去表述人物的动作了。
在亚里士多德的话语体系中,动作不等同于行动。“‘动作’,指表演或身体的动作。身体的动作是用来表达行动、情感等的。”“亚里士多德把诗(主要指史诗、戏剧诗)里发生的主要事件称为praxis(普剌克西斯,源出动词prattein普剌屯,即行一件事的‘行’),意思是‘所行的事’。有人主张译为‘事件’,但事件有一些是被动的,不如译为‘行动’,例如反抗暴力的行动、因为丈夫另娶妻子而进行报复的行动。”(4)罗念生:《行动与动作释义》,《戏剧报》,1962年6月30日。行动、事件、所行的事,具有某种相同的意识指向,都是指用动作表达的具体对象。不管这些动作是用言语述说出来的,还是“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的,动作都与行动有所不同,通过动作表达人物行动是亚里士多德“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的基本命意所在。
在上述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是一个复杂的意识传通系统。以言语述说为主要叙事意图表达手段的史诗或小说等叙事作品,言语述说的叙事意图可以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用言语述说的方式直接表达叙事意图;一个层面是用言语述说的方式去描写影像(人物行动,或其他物象),然后再用影像去表达叙事意图。戏剧、影视作品与史诗、小说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戏剧、影视作品不再有什么人能直接述说自己的叙事意图,一切叙事意图都是“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的方式表达的。即使有时可以用言语述说的方式间接表达叙事意图,其言语述说也都出自作品人物之口,其述说行为也具有一定的“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的表意特征。这是小说话语中所谓描写与一般叙述的不同,也是戏剧、影视作品与小说叙事体式的不同。在这样的思考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定:不管是史诗、小说,还是戏剧、影视作品,也不管是描写的(在小说中),还是“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的(在戏剧中),凡是人物行动或客观物象,都具有一定的独立表意功能。直接述说叙事意图是一种表意方式,用人物“所行的事”去呈现叙事意图是另一种表意方式。就叙事意图表达的符号特性来说,前者的表意符号是语言词汇,后者的表意符号是行动或事件等具体影像。在史诗、小说等叙事作品中,影像符号经由了语言符号的再度重塑。在戏剧、影视等叙事作品中,影像符号则是“使摹仿者用动作”来直接摹仿的。影像符号的塑形方式与用影像符号去表达某种叙事意图,既有一定的连带关系,又不完全等同。电影符号学家所谓“去‘说’一种语言就是去使用它,但去‘说’电影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去发明它”,(5)[法]克里斯丁·麦茨等:《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3页。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在戏剧、影视叙事活动中,当人们“发明”某种影像时,已经把某种潜在的叙事意图存蓄在里面了。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影像表意与语言表意的并不完全相同。就影像表意来说,虽然有时因为“使用”的方式发生改变,“发明”的意向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这并不能改变“发明”是一种表意形式,“使用”是另一种表意形式的基本事实。戏剧、影视“语言”的双重表意机制,在史诗、小说的影像塑形中也同样存在,只不过在一般情形下,人们都用笼统的艺术表达意念来解说了。所谓描写或艺术形象塑造等用语,有一部分意涵就与“电影语言”的“发明”意向有关。由于戏剧、影视作品的影像,都是“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的,塑形这些影像的“发明”意向,与把这些影像当作叙事符号去“使用”的意向,相对而言更容易显露出它们的某些界隔。去“说一种语言”与去“说电影语言”的不同就体现在这里。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小说语言——以语言词汇为表意符号的真正的语言,与“电影语言”——以影像符号为主要表意特征的事件或人物行动,在叙事意图表达上都有一定的能指意义,但使用的条件和切实意义指涉却有所不同。当人们使用语言符号去表达某种叙事意图时,可以有限度地脱离开具体事件的展开情境,许多与事件展开情境有关的事,既可以被人叙述出来,也可以不叙述。就像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的那样,“史诗……能描述许多正发生的事,这些事只要联系得上”就可以叙述(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贺拉斯:《诗学·诗艺》,第86页。。而悲剧做不到这一点。不仅悲剧“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要受到具体事件展开情境的限制,就是小说或史诗的描写性话语,也与叙述人“用自己的口吻”来直接叙述有所不同。在史诗和小说的叙事行为中,那些与“正发生的事”有关、却不一定被人叙述的“事”,在戏剧、影视作品中,却不能不给予相应地关照,否则事件就无法“发生”,也不一定都“联系得上”。虽然在一般的戏剧、影视作品研究中,人们已经意识到,“影像只是由于上下文和它所要求的蕴涵关系才取得自己的符号价值。同一个影像(或更确切地说同一事物、同一实体和同一事件的再现)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有多少(或者可能有多少)可以引入这个影像的不同环境,就可以有多少不同的意义。除了影像所展示的内容之外(甚至包括它所展示的内容),一个影像从来只是表述人们有意让它表述的内容”(7)[法]让·米特里:《影像作为符号》,崔君衍译,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332页。。但如果仔细辨析的话,影像符号构成的“上下文”关系,与用影像符号去表达具体叙事意图的“上下文”关系,还不完全等同。一方面,任何影像的构成,不管是人物影像、还是器物影像,都不能由单一因素构成,构成一个影像的不同因素间构成了一定的“上下文”关系。另一方面,用不同影像的碰撞和对接方式去表达叙事意图,这些影像之间也构成了一定的“上下文”关系。与影像语言词汇性意义构成的“上下文”关系相比,影像“使用”中所发生的“上下文”似乎更有决定意义。在戏剧、影视叙事活动中,影像的确型依赖于某种“上下文”关系,影像的叙事意图表达也依赖于某种“上下文”关系。把一个影像构成中不同因素的“上下文”关系(即影像语言词汇性意义的生成)与影像链接关系中呈现的“上下文”关系(即“使用”影像去传通具体叙事意图)进行适当区隔,对于认识戏剧性叙事活动的展演形态具有特殊意义。
二、“所行的事”与叙事意图的表达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叙事有时也可被人称为“序事”,即对事件的有目的与合理性的安排和释读。(8)谭帆:《“叙事”语义源流考——兼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虽然这与从西方介绍进来的叙事意念不完全相同,但任何叙事活动都与“事”有关,叙事也是对事件关系的一种认知,这是不容否认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具体分析这一问题。《雷雨》中有一个情节:周冲从花园来到客厅,呼唤四凤未果,又从侧门走出了客厅,与此同时四凤从屏风后走出来。周冲寻找四凤,这是周冲的个人行为,它由一系列“所行的事”构成——周冲从花园走到客厅,一边走一边呼唤四凤的名字,并不时四处探望,如此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周冲在寻找四凤。可是,周冲寻找四凤找到没有呢?随着周冲走出客厅和四凤从屏风后走出来,说明四凤不想见他。周冲的行动与四凤的行动,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仅靠他们各自的独立行动还无法表达更完整的叙事意图。只有把周冲的行动与四凤的行动链接到一起,才能在这两种行动的对话关系中把最终的叙事意图完整地呈现出来——因为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的不一定是四凤,还可能是周萍或蘩漪等什么人,如果那样的话,叙事意图表达就将向另外的方向发展了,而与四凤不想见周冲没有什么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在戏剧性叙事活动中,事与事的链接关系是叙事意图表达的主要依托,这是“序事”与叙事在中国古代可以通用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人物行事活动两种叙事意图表达途径的探讨,不仅对认识戏剧、影视叙事形态有意义,对一般叙事形态研究也有意义。为什么有些叙事活动中的事件和人物可以以假乱真呢?事虚理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也并不都从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角度去评价和体认具体叙事活动。事件、人物以及一切以影像姿态显示的表意对象,它们的真实性对理解叙事意义的表达固然重要,但与此种真实性比起来,它们参与“所行之事”的合理性似乎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一般人们所谓的艺术真实都可以从两个层面去审视:一个层面是以事件、人物以及其他影像方式呈现的表意对象是否真实——陈白露是真实的,孙悟空是不真实的;一个层面是事件、人物以及其他影像的行事方式是否真实——即使是虚拟或虚构的事件和人物影像,其行事活动也不能逾越一般的生活逻辑。如果符合一般生活逻辑,我们就认为它是合理的,因而也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就是指行事逻辑的真实,不一定是指事件、人物以及影像本身是否真实。我们在上文中谈到,在戏剧性叙事活动中,影像具有表意符号的能指意义,能发挥出类似于语言词汇的表意价值。而我们知道,人们一般不会去追究语言词汇的“真实性”问题。如果我们认定“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的影像具有类似于语言词汇的表意价值,那么相对而言我们对其现身姿态的真实性,理解得也会更宽容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戏剧性叙事活动的事件、人物以及其他影像等常有虚拟或虚构的成分,而人们对它们又不会去过多计较的原因。影像符号的语言词汇性表意特征,不仅能解释戏剧性叙事影像的虚拟或虚构成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般性艺术作品的影像、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样态的并不完全相同。从这样的角度来讨论戏剧性叙事活动,很自然地就会意识到,一般的戏剧性故事展演都有两个有连带关系的体式特征:一个是,戏剧性故事不能完全按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展演,凡是“戏”都不能跟现实生活完全一样,因为它要用“发明”的影像词汇来传通特定的叙事意图,“发明”的就不一定是实有的;另一个是,戏剧性故事的展演有相当部分是在阐释人物行动或事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发明”影像的叙事意图与使用影像去表达某种叙事意图紧密联系在一起。《雷雨》的故事“太像戏”,因而有时作者也感到不满意。(9)“写完《雷雨》,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我用的过分。”曹禺:《日出·跋》,《曹禺文集》(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381页。然而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戏剧之所谓戏剧又必然会带来一些“像戏”的成分,否则也就无所谓“戏”了。“像戏”和怎样“阐释戏”是一体两面的事,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对戏剧性故事的展演似乎更为重要。《雷雨》的故事,有相当部分都与“阐释戏”有关。比如,三十年时间过去了,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周朴园怎么就能认出鲁妈是侍萍呢?三十年音讯皆无,这是“演戏”的前提,这一点不接受人们的质疑。但剧作要拿出让人信服的行动来诠释周朴园与侍萍相认的合理性,在这一点上必须符合人们的日常习见。如果人物行事关系合理,行事根据充分,不仅剧中人能够照章行事,观剧人也能接受其剧情演化逻辑。否则戏剧表演就失去了叙事或“序事”的价值。《雷雨》通过三十年不变老屋的布置,通过周朴园和侍萍都记忆犹新的、放在老箱子里的那件绣着梅花的旧衬衣,让尘封的记忆被唤醒。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三十年的音信皆无,侍萍不会“误入”周公馆,当然也没必要为二人相认去设置一些相关的戏剧情节。
戏剧性事件的设置与阐释都是“戏”的必要组成部分。从人物行事关系角度切入对戏剧、影视作品的叙事形态研究,剧作事息在剧中人之间、在剧中人与观众之间、在剧中人以及观众与故事的“序事”关系之间,有某种相对独立的传通渠道。它们都以行事的合理性为前提条件,但由于各自浸入戏剧活动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尽相同,因而也常常会有某种不同的对于行事合理性的理解。用行事活动来“阐释”戏剧性事件的展开,有某种不便,也有某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一般人们所说的戏剧性和剧场氛围,有相当部分就是从这种特定的事息传通渠道中显现出来的。
如前所述,戏剧性叙事中的每一人物的行事活动,都有促使其发生的目的性与合理性,与事件的设置与“阐释”有直接关系。为了让周朴园与侍萍相认,剧作才设置了三十年不变的老屋及其一系列与其有关的“事件”,否则作品不一定如此这般地展演。但戏剧展演的最终目的是向观众演绎故事,戏剧作品人物的行事活动是演绎故事的唯一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戏剧性叙事活动中的作品人物与观众应该具有大体一致的浸入故事展演的立场,可事实上却不一定如此。原因就在于,有些故事事息能够或便于用人物的行事活动来展演,有些则不能或不便于用人物的行事活动来展演。小说能把一部分不能或不便于通过描写的方式告诉读者的故事内容,用叙述人话语直接表述出来,戏剧性叙事活动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因而有时为了向观众传通某种事件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设置一些相应的情节,让作品人物以行事方式去阐释和“解说”故事的来龙去脉。(12)“有些故事里有解说者,他们或多或少地对故事情节进行介绍,并不时在故事中出现,解释发生的事或介绍故事中出现的新情况,但有些故事里却没有解说者。这些故事是完全由人物‘表演’出来的,其中一个人物一般充当解说者的角色,但本身并不是解说者。”[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如此一来,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人物行事流与观众感知故事流之间就会产生一些缝隙。比如在《原野》中,十多年前花金子的父亲就把花金子许配给了仇虎,剧中当事人都应该知道这件事,可是观众却不知道。而观众不知道,他们感知故事流就会受阻。因此,为了弥补观众感知故事流的欠缺,作品用常五与花金子唠闲嗑的方式,把相关故事背景告诉了观众。这样的表演活动对于表演行事流来说,虽然不排除有某种可能性,但多少都会让人感到有些冗余,花金子自己的事还需要别人告诉她吗?我们说过,戏剧性叙事以人物行事活动的合理性为依托,其所谓合理性有必然性合理与可能性合理两种选择,而可能性合理之所谓可能,就是因为它有多种选择余地,有相对宽松的行事合理性选择条件。这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可能的行事活动,人们对其可能性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因为观众与剧中人有时并不站在完全相同的立场去从事或体察故事的展演,因而对可能性的需求和理解就可能有所不同;反过来说,恰恰是因为有了观众与剧中人对可能性行事活动的不同理解,戏剧性叙事活动才有了可被选用的多种展演空间和展演条件。一般人们所说的戏剧性或剧场氛围,大多与这样的展演空间和展演条件的选择有一定关系。
如前所述,在亚里士多德的话语体系中,“所行的事”就是指人的行动,人的行动都与“事”有直接关系。为了方便探讨,我们以“行事”的意念来指称“所行的事”。电影符号学家所探讨的影像符号的叙事意义,主要着眼于影像符号的词汇性意义怎样构成,行事意念探讨的是怎样“使用”这些“词汇”去表达更确实的叙事意图。虽然它们都以影像的姿态呈现,但探索意向侧重点有所不同。就人物的行事活动关系而言,任何行事活动都要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目的性。不管是周冲的行动还是四凤的行动,它们都属于一个行动主体的有目的、合理的行动。而周冲行动与四凤行动的链接也是有目的、合理的。只不过前者受必然性支配——一个人的行动目的可以由多种行为来表达,但只要参与到这一行动目的表达中来,就要与这一行动目的相符,与该行动目的不符的其他行为不能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而后者受可能性支配——周冲的行动与四凤的行动链接是可能的,除此之外,周冲行动与其他什么人的行动链接也是可能的。一般的戏剧、影视作品的叙事意义,都可以从这两个层面着手进行分析,即人物本身的行动目的是什么,以及在不同人物行动关系中体现的叙事意图是什么。虽然它们都属于用行事的方式呈现叙事意图,但其叙事意图表达的路径并不完全相同。在这样的思考中我们看到:所谓必然性行事,大多是指每一个人为实现自身行动意图而展开的叙事行为;所谓可能性行事,大多是指为实现在不同人物行动链接中体现的叙事意图而展开的叙事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必然性行事主要是在为可能性行事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叙事意图主要是从可能性行事活动中被圈定、被最终确型的。
跟环境、健康联系紧密的还有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产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保护,推进秸秆、农膜资源化等任务,这些工作都有量化指标,也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三、事息传通与戏剧性
在小说类叙事作品中,人们已经意识到,“故事”与“本文”不完全相同。“故事(story)是以某种方式对于素材的描述。”“本文(text)指的是由言语符号组成的一个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在欧洲人人都熟悉‘拇指汤姆’的故事。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是从同一本文阅读这个故事的。”(10)[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页。在作品“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之外,还有一个“故事”的本体可以追寻。如果说在“故事”与“本文”的探讨中,小说等叙事活动存在着“不同的本文,其中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的现象(11)[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3页。,那么由于戏剧、影视活动也是叙事性活动,其“故事”与故事的表达也有一定的分离探索空间。在戏剧性叙事活动中,故事不表达当然也无所谓有,可一旦表达就等于承认它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被表达出来的故事,可以从怎样表达和表达了什么两个侧面去探讨。从事息传通的角度看,怎样表达更多体现为故事中人物之间的行事关系是怎样的;而表达了什么则更多体现为故事的“序事”关系是怎样的。如果说“本文”与“故事”可以分开来讨论,那么,观众是从“本文”中知晓故事的,而故事与“本文”又有所不同——这就等于告诉我们,观众对故事和“本文”都有一定的自主感知能力。他们一方面从作品人物的行事关系中去理解故事,一方面也从作品的“序事”关系中去理解故事。
任何戏剧性叙事活动的展演,都不可能不中断地一直展演下去。就剧中人的行事意向表达来说,他只能参与自己在场的事,不能参与自己不在场的事。而观众却与剧中人不同,所有剧中人参与的事,观众都在场。比如四凤与周萍私通这件事,观众都知道,侍萍却不知道。原因就在于观众对事息的感知渠道与侍萍对事息的体验渠道不在一个平面上。与剧中人知情、观众不知情的事息传通相比,有时还会出现观众知情而剧中人不知情的事。戏剧展演最终也要满足剧中人知情的需求,而一旦让剧中人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与观众的感知故事流达到同步的时候,往往都预示着某种重大事件的发生,戏剧展演活动也就可以结束了。许多耳熟能详的悲剧或喜剧故事,都与特定条件下观众知情而剧中人不知情的事息传通渠道有一定关系。比如《奥赛罗》《钦差大臣》等,观众都早于剧中人知道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剧场氛围和剧场事息的缔结,都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让剧中人知情为纽带,否则故事不一定以这种方式展演。而这种特定的让剧中人知情的方式,之所以被人称为是戏剧性表现,就是因为通过人物行事活动来展演故事,故事中人物的行事方式与观众感知故事的方式并不完全同步。如果把这样的叙事意图展演方式挪移到小说叙事活动中来(用言语述说方式去展现人物行动,即一般所谓的描写),有时也会产生某种戏剧性效果,从而与一般文本叙述产生某种区隔。
从传播学的视角审视,事息意念与信息意念有所不同。事息意念是说表意符号以事件、人物行动或具体影像方式体现,其表意倾向并不单一也并不纯粹。不管是影像的构成还是影像的使用,都与特定的“上下文”脱离不了干系,它们的确实叙事意图表达,往往需要表演者和观众去双向适应和共同凝聚。而一般意义上的言语表达,以语言为表意符号,语言表意更多与信息传通有关,说什么和不说什么都更为清晰明了。因为语言词汇意义是原有的、切实的,不管谁去说或谁去听,都不会有太大出入。在小说类叙事作品中,叙事意图主要以语言词汇的信息符号形式进行传通,而在戏剧性叙事活动中,叙事意图主要以事件、行动以及其他影像的事息符号形式进行传通。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我们看到:一般的戏剧性叙事活动,都存在着三种互有关联又互不相同的事息传通流:一种是作品人物之间的事息传通流,即作品人物之间的行事关系是怎样的;一种是故事本身的事息传通流,即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序事”关系是怎样的;一种是观众获取表演行事流和故事序事流的特定方式,即观众感知作品人物行事流和故事序事流的具体途径。这三种事息传通流,相近或相通,但并不完全等同。虽然说在小说等叙事作品中,也可能存在类似的事息传通流情况,但叙述人话语能够相对容易地把三种事息传通流的区隔和不一致的地方抹除或淡化,让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而一切都是“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的戏剧性叙事活动,没有这样的话语条件,三种事息传通流的区隔和不等同就从这当中凸显出来。它一方面增加了戏剧性叙事活动的困难,一方面也让戏剧性叙事活动躲避开了人们的过多指责——戏剧之所谓戏剧,必然会有一些与现实生活不一致的地方。
如果说在小说等用言语述说方式建构的叙事作品中,从人物行事关系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视角去探视人物行事活动的叙事意义,有时还显得没有那么必要。因为叙述人可以“用自己的口吻”把叙事意图直接表述出来,可以把一部分描写的“事件”用“说明”的话语去直接叙述,因而为不同人物行事活动提供链接条件的需求并不十分强烈。那么,在戏剧、影视作品中,由于没有叙述人用自己的口吻直接表达叙事意图的话语条件,一切都是“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的,此时,“事件”构成的单元及其与整体事件的关系,就被放大、凸显了出来。在戏剧性叙事活动中,有些人物行事活动仅从叙事主题、叙事的最终意义表达上审视,可能没有什么必要;但从链接故事情节、让许多事“联系得上”的角度审视却不可或缺。有时恰恰是在二者的分立和并不完全同一中,才让戏剧、影视活动充满了叙事的张力。
“冰说”以韩同林、郭克毅为代表,他们认为,冰臼主要是由冰川融水(包括冰川压融水)携带大量冰碎屑、岩屑及冰川粉物质,沿冰川裂隙自上向下以滴水石穿的方式形成滚流水钻,对下伏基岩进行强烈的冲蚀和研磨作用下形成的。
3.假设单件化妆品的不含税价为P,买家购买套装相对于分别购买套装内所含产品的可享优惠率为R,则套装化妆品的不含税价为2P(1-R)。令,P≤2000,2P(1-R)>2000。 根据自网易考拉中选取的100组不参与活动打折的单件和套装化妆品样本,以“优惠率=[单件价-(套装价/套装所含件数)]/单件价”计算得知,优惠率R大多集中在0.15%-1.75%。
表演行事流与观众感知流的分离与统一,不仅对故事的展演与故事的感知有影响,也对故事的“序事”关系有一定牵制作用。从人物行事活动角度审视,无论是剧中人的行为还是观众对戏剧情节的感知行为,都被限制在了特定的时域里。人物行事活动与特定场景、情境有关,离开展演条件,人物行事活动无法进行。观众感知对象也被限制在了特定时域里,离开作品人物的行事关系,观众也无法知晓故事的完整呈现过程。可是正因为如此,剧中人和观众都通过一定的行事活动去展演或理解故事,那么对故事本身来说,这也只是展演和理解“序事”的途径有所不同而已,故事本身并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雷雨》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周公馆,时间不超过一天一夜,这是作品人物行事流与观众感知故事流的具体时空条件。可是故事序事流却不能不从30年前侍萍被赶出周家大门的那个夜晚讲起,从而说明故事序事流有自己独立自存的一面,与表演行事流和观众感知故事流并不完全等同。
推移质起动流速的计算方法很多,这些方法计算得到的起动流速不仅差别很大,而且由于多数方法是在一定的粒径范围、水深范围、流速范围内推导而得的,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大局限性。在实际中,冰碛坝的物质组成级配很宽,引流渠水力条件变化迅速且范围大,因此选择一个使用范围较广,且具有一定精度的推移质起动流速计算方法是模拟人工引流渠冲刷发展的关键。
戏剧性叙事活动的三种事息传通流,既有分别,又有某种一致性。没有分别,在戏剧展演中做不到,只要用作品人物的行事活动来表达叙事意图,戏剧表演流、观众感知流以及故事序事流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戏剧性叙事之所谓叙事,又以这三种事息传通流的内在一致性为依据,否则故事到底是什么就无法让人理解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戏剧性叙事活动,都从设计这三种事息传通流的分离与不同一开始,最终又要让三种事息传通流殊途同归,把各自事息传通中必要的、又好像没有及时呈现的部分一一表达出来,形成一个在各方面看来都合理的事息传通网状结构。戏剧、影视作品与史诗和小说作品比,区别到底在哪里?怎样认识它们的不同?如果不用相对单一的行事活动来表达叙事意图,允许有叙述人直接阐释和“解说”故事的机会,小说与戏剧的体式分别就不会那么明显;而如果不是这样,三种事息传通流的不能完全同一就是一种必然现象。从这个角度切入对戏剧、影视作品的叙事意图表达研究中,不仅对认识戏剧性叙事活动的展演方式有意义,对探视小说的描写话语及一般叙述话语的不同也有一定启示——起码为小说的戏剧性表达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