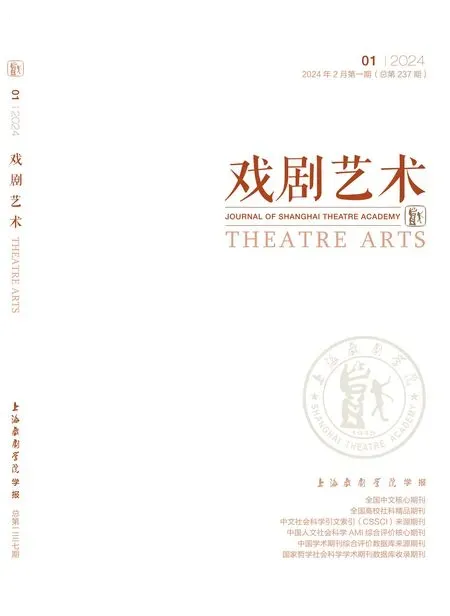全球迁徙者的登场:艾杜与丘吉尔剧作里跨越边界的女性形象①
颜海平 著 周佳 译 李德光 校译
“跨越边界”的意识(1)这里并不绕开现代语境英美词汇中“迁徙”涉及的法律机制及其运行的内涵,本文聚焦的是该词在现代意识中的塑形过程和在生活世界中的效能影响。,在过去数十年欧美文学和广义的人文学研究中延展并日益多样化。(2)自全球疫情以来不同国家与文明之间加剧的隔阂与对立,全球范围内边界林立、流动停滞的状况,是过去数十年经济全球化以来“边界穿越”作为变动中人文地理主导特征的深度和覆盖度的折射。自“喧嚣的1990年代”(3)该称呼源自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2004年出版的《喧嚣的九十年代》,参见Joseph Eugene Stiglitz,The Roaring Nineties: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 (New York:W.W.Norton &Company,2004)。以来,随着全球人文地理形态的加速转换,人文话语将艺术作品中各种“迁徙人”意象,作为“旅途中”“在路上”“灵活流动”“不受束缚”的“主体性”载体加以表述的论断亦新意层出。(4)相关著述参见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Routledge,1994); Aihwa Ong,Flexible Citizenship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 Rosi Braidotti,Nomadic Subject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本文将检视“迁徙人”意象在当代两位重要女性作家作品里的形塑过程,探讨她们“边界跨越”中的多重动能及其内在悖论。(5)批评性探讨参见Arif Dirlik,“The Postcolonial Aura,” in Dangerous Liaisons:Gender,Nation,&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eds.Anne McClintock et al.(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501-528。具体而言,本文剖析在1980和1990年代里欧美文学与女性研究领域中被基本忽视的加纳女作家爱玛·艾杜(Ama Ata Aidoo)和被高度关注的英国女作家卡尔·丘吉尔(Caryl Churchill)笔下的女性形象,并由此构成两者之间对话性相遇,以展开一种由并置而互鉴的探讨。就语言媒介和历史时间而言,两位作家都用英文书写,都是由英帝国瓦解而显形的战后世界时空巨变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杜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后不列颠”(post-British)时代撒哈拉以南非洲重构及其社会剧烈转型中的杰出黑人作家(6)二战后期出生在加纳(殖民史上被称为黄金海岸)的艾杜,是二战后非洲大陆最为重要的作家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推动者之一。她成长于反殖民统治和民族独立运动中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执政期间,后成为著名诗人、剧作家,与Wole Soyinka,Chinua Achebe,Ayikwei Armah 等比肩,在加纳第四共和国总统杰瑞·罗林斯执政期间,曾任教育部长。她的名言:“成为作家,你不是必须只用英文书写。”参见爱玛·艾杜在爱玛·艾杜创作中心成立大会上的演讲(Ama Aidoo,“A Speech at Launch of Ama Ata Aidoo Centre for Creative Writing,” March 2017,www.GhanaWeb TV.com)。该中心设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非洲传播学院(the Afric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in Accra,Ghana)。作家尼·阿伊克维·帕克斯(Nii Ayikwei Parkes)为首任主任。,丘吉尔则属于前欧洲宗主国动荡中社会场景再建和英国文坛重塑的代表人物之一(7)卡尔·丘吉尔于二战中出生在伦敦,10岁时随外交官父母居加拿大,1950年代返回英国,就读于牛津大学,毕业于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创作了戏剧、电视、广播及其他多种形式的作品,在英语世界影响广泛,被称为“莎士比亚以来英国最伟大的当代诗人和创新者之一”。。不同于一般分类将艾杜归为后殖民研究、将丘吉尔限于英美研究,本文悬置这样的认知划分,将她们笔下独特的女性意象跨界并置,聚焦于辨析这些意象如何以不同形式登场,在穿越地缘边界、社会区隔、意识鸿沟的大迁徙中,指向二战后氤氲上升的一种“交织性世界史”(8)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3.的全新视野,以及其中所蕴含、所唤起的迁徙中人们的差异性共振、可能生成的变革性相连。(9)贯穿于两者共鸣之中的差异性的内涵与属性,是女性主义跨国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参见Yan Haiping,“Transnationality and Its Critique,” in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Ama Ata Aidoo,eds.Ada Uzoamaka Azodo and Gay Wilentz (Trenton:African World Press,1999),93-126。
与普适化的现代性范畴所界定的人的流动性不同(10)对这种普世流动的批评著述参见 George Steiner,Extraterritorial (New York:Atheneum,1975); Janet Wolff,Resident Alie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艾杜作品审美感知核心的女性移动,是一种边界转换性生存(transboundary existence)的特殊模态,示意出迁徙者在全球性变迁中,寻觅着物质和意义世界中被重重遮蔽的生存路径,在地方的、民族国家的和全球的场景之间,某种身心浩渺居无定所的特质,呈现出一种本雅明所称的“常态化应急性”(11)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ed.Hannah Arendt (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9),257.的漫长旅途。卡尔·丘吉尔的戏剧时空里也出现了以不同方式形成的此类“迁徙者”形象,三棱镜般折射出现代资本逻辑和现代人类轨迹的相互缠结和张力,以及其中囊括裹挟或动态展开的广阔多样的女性人生。始创于1970年代而高频上演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她们的剧作里栖息着一种人性内涵的移置和深萦徘徊的脉动(12)“人性内涵的移置”主要指原先因循传承中对人的属性界定及其意义特质的既定理解,出现了充满不确定性的转换,其核心内涵“不可言喻”的状态。,这种移置中的脉动,在过去数十年间的全球各地被强化、深化和复杂化,对我们把握变动世界中多重的人文地图、历史语境,不同个体、群体乃至人类整体和生灵万物之间的关联状态,不啻为充满示意的认知路径。(13)参见弗·詹姆森“认知图绘”论。Fredric Jameson,“Cognitive Mapping,”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s.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347-360.
一、迁徙者:动能与悖论
对于1970年代如何构成战后世界全球性结构再重组的一个历史时刻,学界探讨已久。(14)关于战后主要工业国之间谈判设立的世界经济(商务与金融)秩序,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0年代的全面危机及其终结的主要著述,参见Fred L.Block,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Samir Amin et al.eds.,Dynamics of Global Crisis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2); Stephen E.Ambrose,Rise to Globalism (New York:Penguin Books,1971)。这一刻目睹了工业强国之间为修订新版“国际秩序”而展开的危机四伏的谈判(15)参见 Fred L.Block,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163; Stephen E.Ambrose,Rise to Globalism (Harmondsworth:Penguin,1971,1976),20-22。,也见证了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此新版秩序的构建中,面对如何处理新出现和脱胎于老欧洲的诸多困境难题。(16)Ngugi wa Thiong’o and Micere Mugo,The Trial of Dedan Kimathi (London,Nairobi and Ibada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1976),47.对于后独立年代的非洲大陆如何变革自身以穿越过去与航行未知的文化蕴意,艾杜有敏锐的意识。(17)Vincent O.Odamtten,The Art of Ama Ata Aidoo (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94),43-115.她于1970年发表的剧本《阿诺瓦》(Anowa)(18)Ama Aidoo,The Dilemma of a Ghost and Anowa (London:Longman,1985 &1996),61-124.本文中引用的《阿诺瓦》内容,出处相同,不再一一标出。取材于一个古老的非洲口述传说:“不听母亲言”的女儿为追求自由而越界远行,收获的是能量蓬勃的初期绽放,但最终死亡的历史人生。艾杜在剧本里将这个古老传说设置在19世纪中期欧洲扩张主义全面侵蚀的黄金海岸,批评家们认为其中的意识形态与经济统治模式指向古典殖民主义在非洲的独尊来临之际,同时隐含的是这一漫长的来临和独尊,在历经巨大变革后的独立非洲变奏重返所呈现出的时空张力。(19)Vincent O.Odamtten,The Art of Ama Ata Aidoo (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94),46.艾杜以将古老传说嵌入世界现代史的“口述”风格(20)Ibid.,13.,展现非洲与殖民主义遭遇之际孕育的一种穿越边界的人性构成;同时示意出这一人性构成在1970年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正被复杂转写。《阿诺瓦》的形式结构因此是一个双重时空的交叠并置和互为探究:对现在的叩问,唤起对古老传说的重访;而在重访中生成的,则是把握未知进路的史诗般驱动。
剧情开始时,穿越边界的脉动正在黄金海岸的主要区域方逖地区(Fanti)显现,这似乎为来自耶比村(Yebi)的少女阿诺瓦(Anowa)提供了非比寻常的许诺和期待。自幼就与其他耶比女孩不同,她是“融多重人世轮回于一身的灵童”,她只“倾听自己的故事,欣赏自己的笑话,遵从自己的主张”。阿诺瓦拒绝诸位求婚男子,不顾母亲巴杜亚(Badua)的反对,择了一位名叫科菲·阿寇(Kofi Ako)的年轻人作为丈夫,并决定离开耶比村落。对此巴杜亚曾极度苦恼地说:“让她走吧。但愿她能走得好。”阿诺瓦脱口而出的回答“妈妈,我一定会走得好,好得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仿佛预示着即将展开的命运。于是阿诺瓦和科菲开始了他们的旅程。剧本“第二阶段”舞台提示示意,这旅程是在具有明确现代特质的动态场域——“高架路”上展开。阿诺瓦以她的无限活力拥抱这个开放空间,与科菲一起为他们的贸易业不眠不息地工作,历经“寒冷的夜间、炎热的白天、风、雷、雨、闪电”。她对科菲说:“我喜欢工作,我喜欢在路上。”然而,随着财富的增长,科菲开始做这世上“每个人都做的事”——圈养家奴。黄金海岸方逖区域古老的家奴制度,在高架路的目的地出现了新版本。在该剧“第三阶段”,无论阿诺瓦如何反对,科菲兴建了傲谷庄园(THE BIG HOUSE AT OGUAA),成为一名新式领主。庄园正厅悬挂着“维多利亚女王像”,两侧是“科菲与阿诺瓦像”和“(他们的)恩梭纳(Nsona)部族的鸟图腾”,俯瞰着正中地面上放置的“镶金座”。置身于这新杂糅的三位一体及旧殖民式的显赫庄园,阿诺瓦日益沉默。当科菲的财富如洪水般上涨时,阿诺瓦徘徊自转着。昔日方逖大地上光彩照人和风雨雷电中活力无限的灵异女儿,逐渐成为“先前自己”的“无声影子”。
阿诺瓦在边界穿越的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她与自己失去的声音交战,庄园上下无人能懂其中的哑语,在他们眼中,阿诺瓦渐渐变成某种眼神奇怪的、低回萦绕的在场。科菲责难她偏执于生活中“一般的苦痛和普遍的错失”,脱离常态人间,成为人间异类。阿诺瓦对“高架路”时空的想象与热忱陷入困境,她的痛苦在于整座庄园是一个持续运转、不停获取的机器,运转的目的是E.M.福斯特语中“对大地和人类的(资源)世袭”(21)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对“the Great North Road”的叙述,参见 E.M.Foster,Howards End(New York:Vintage Books,1921),14-15。“高架路”作为现代性结构场域的形象,参见[美]弗·詹姆森:《现代主义和帝国主义》,桑石译,《外国文艺》,1993年第5期。。将“无限扩张”作为“高架路”固有属性并成为其化身的科菲变成一个膨胀的男人,他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生灵视为其膨胀扩张的原料和工具,拥有和掌控它们就能“像沼地里的牛蛙一般坐食而肥”。曾与科菲风雨雷电同行的阿诺瓦,发现自己将以新的功能置身于科菲庄园所拥有的众生灵之列。科菲对阿诺瓦似乎就事论事地说:“我应该是新的丈夫,你应该是新的妻子。”丈夫把她视作庄园世界的一个部件,理所当然地去除她“在路上”的幻想时空,从此留在家中,身穿工艺华贵的衣裳,戴着宝石,专门照看这座庄园。这个部件的功能属性,是基于科菲作为“庄园领主”的独尊性而为阿诺瓦指定的命运。科菲认为“天下无数女人宁愿赌注一生来换取这样一天的享受”。但对阿诺瓦而言,这享受过于高价和强人所难:这要求她磨灭自己的想象力、生命力和生产力,要听从科菲将“灵异”作为“怪异”进行否定,要清理由此而来的情感、举止与谈吐,简言之,要脱胎换骨、里里外外地重新改变自己,从而隶属于丈夫,举止“正常”地专注于“男性场域”及其秩序世界。阿诺瓦新版命运脚本里的这些构成性要素,要求废除她与科菲先前的关系属性,宣告她自身的消失,幸运地变成“一个精致的小陶罐/底色光鲜,/打磨顺滑,/放在高贵的角落里”。注视着这份脚本,阿诺瓦奇怪的眼神看到的不是天下人争抢不得的“幸运”,而是一种具有隐蔽性的掌控形式,使得她难以呼吸,“当我把目光投向未来,我看不到自己。我只是个无处可依的旅人,到哪里都一无所有”。
意识到自己在科菲庄园里被全部锚定而又无处立足的悖论处境,阿诺瓦回想穿越耶比村边界、“在路上”那如同隔世的当初。作为历史长途的热忱旅人,阿诺瓦逐渐悟出,布满她生命轨迹的旅途,示意着无限敞开的时空,同时也是各种势力扩张缠结的角斗场域,这场域的纵横交错可以物化生命、耗尽身心、溟灭想象、钳制命运。由于一时无法对她的发现进行命名乃至超越,到该剧“第三阶段”,阿诺瓦诉说的对象似乎只有墙壁、家具和日益加深的自身身影,成为“边界穿越”中某种现代人性困境的物质载体。“(高架路上)旅人就是过客。把某人称作旅人,就是用无痛的方式说她居无定所。她没有栖身之处,没有家园、村落,没有自己的凳子,没有斋日、庆典、节假……没有立锥之地。”没有历史中的意义时空,只有梦魇缠绕的牵制。旅人阿诺瓦挣扎寻觅着,茫然四顾中,她在傲谷庄园里、科菲的农场家奴中抓住了自己依稀可辨的形影,随后提出的认知性的叩问亦是终极意义上的揭示,“我和你的家奴又有什么分别?在这里的任何人都不属于这里”。穿过不可化约的重重差异,艾杜笔下“新妻子阿诺瓦”的人身依附属性与庄园家奴们的交遇重叠:事实上,庄园里有了第一个“精致陶罐”,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版本的“陶罐”到来,一如圈养家奴的逻辑。被定格为“陶罐”的阿诺瓦,与作为傲谷庄园建造原料的家奴们,在差异中无言以对,在无言中遥相注目。
由此,阿诺瓦作为一个科菲庄园里,在锚定中被无视、无视中在场的悖论灵影,成为艾杜史剧长卷深处的引力重心。这一迁移人的灵影脉动,既是这一片大地来自被暴力撕裂的过去的呼声,亦是其在内涵外延置换中现时的回音。剧中双人歌队里的老汉与老妇在序幕伊始,将这苦痛呼声溯源自遥远昔日的黄金海岸遭遇的一系列创伤性变迁,这些变迁始自1470年代,于1870年代达到顶点,在与英殖民雄心持续强化时期的交织中,构成整个区域具有依附性的复杂过程。具体而言,1844年的《不列颠-方逖协议》开发了方逖地区,并最终将整个地区及其文化包括古老的蓄奴惯习与“作为整体的非洲的贸易经济”一起,移向和纳入“正在出现的全球性跨洋商业网络”殖民资本的运作。阿诺瓦故事结束时的1870年代目睹了英国正式将这一地区圈定为(帝国)直属殖民地。序幕里歌队叙说的正是这一历史的转折点,“这是阿诺瓦,/还有科菲·阿寇。/大概是三十多年前/我们部落的首领/签了那张字据——/他们叫做《1844年约章》——/把我们全都签约给了/那些从天边来的苍白人”。序幕唤起的时刻使阿诺瓦和科菲两人的故事从一开始即与跨越洲际的历史动因交织铭写。在歌队叙述的历史语境化过程中,古老民间传说的再现,成为世界史本身充满张力的症候性轨迹。
在此历史化语境中,阿诺瓦的旅程遂成为构成“现代非洲”的大规模人文地理瓦解裂变之历史时空缘起和流变的内在部分。穿越边界、展望愿景的生命灵童,在世界历史“社会经济的汇合湍流”中成为居无定所的迁徙者,她的困境深处记录着在殖民机制的全球运转与方逖社会的复杂巨变中,充满想象活力的人性是如何被挟控、物化、改变直至被殖民。该剧“第三阶段”里,这一人性转变的最初景象出现在阿诺瓦的童年梦魇中。阿诺瓦幼年听祖母谈那些“从天边来的/男人,长得……像煮沸的/或是烤熟的龙虾”,深受触动,梦见自己变成一个“大女人”,身体里“不断涌出男人、女人和孩子”,这时炎热的海滩上闯进一群长着龙虾头和爪的男人,“他们冲到我坐的地方,将我一把推开,然后抓住男人、女人和孩子,把他们驱赶到平地上用脚猛踩”或“把他们赶到全是石头的山上”,而“人群中从来没有哭喊或者低语,只有阵阵无声的爆裂,就像熟透的马铃薯或是饱胀的豆荚”。科菲庄园中,不同于“膨胀扩张”的科菲,“长大成人”的阿诺瓦注视着自己循环自转的灵影,在跨界透视中直抵如同隔世的童年梦魇,成为一种现场性和历史性的双重实存,揭示着《1844年约章》的双重秘密。《不列颠-方逖协议》的起因是方逖长老为了对付北边同族更善于征战的强悍部落转向欧洲殖民者寻求保护,而这“保护”导致的不仅是方逖区域的“直属殖民”,还有“那些在宏大海洋前站立着的堡垒将提醒我们的孩子们……一个更大的罪行”(22)关于昔日被贩卖者关押处的遗迹,参见“Ghana Museums and Monuments,”May 7,2023,Slaveryandremembrance.org。。“大海将见证”方逖部落首领如何与不列颠商人共谋启动横跨海洋的奴隶贸易,使“被贸易”的人们在全球运营的网络中成为辗转的物品、默默“爆裂”的生灵。他们至今仍是独立后的加纳,乃至广义非洲隐秘讳言、不可言喻、未能救赎之痛,深萦徘徊在黄金海岸、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世界各地。对这一切,“所有善良的人都竭力忘却;/他们已经忘却!”(23)参见2014年8月13日艾杜在皇家非洲学会年度文学节的访谈(Ama Aidoo,“An Audience with Ama Ata Aidoo at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s Annual Literature Festival,”August 13,2014)。相关历史文献,参见David Kimble,A Political History of Ghana:1850-1928 (Oxford:Clarendon,1963); K.Y.Daaku,Trade and Politics on the Gold Coast (Oxford:Clarendon,1970)。。而在艾杜的戏剧时空里,这“已被忘却”的人们被曲折重访,在阿诺瓦灵影中被记忆、再现、反思,被沉默而强韧地叩问,穿过现代史的动荡场域,萦绕出没在1970年代以降加纳和世界各地的观众现场。
《阿诺瓦》在加纳问世时,恩克鲁玛领导的首届黑人独立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已有四年。昔日的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被迫流亡国外。这一不稳定的局面暂时掩盖了后不列颠时代的加纳在现代资本主导的全球运营和变动语境中一系列深层次的难题,同时加纳面对的是充满多面性、不确定性的世界秩序的再布局。(24)Vincent O.Odamtten,The Art of Ama Ata Aidoo (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94),78.后独立时期深刻嬗变中的加纳乃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社会,在经历长期未决的结构性危机的同时,亦见证着“新殖民势力”(25)Ngugi wa Thiong’o,Writing Against Neocolonialism (Wembley:Vita Books,1986),14.抬头的历史转折。迁徙人阿诺瓦的故事是剧作家艾杜对这些危机的敏锐记录,也是一种反思和喻示。黄金海岸在旧殖民机制下的苦痛,加纳在新压力下的辗转,由这具形喻象,获得多重洞明。此刻,在阿诺瓦的女性体貌里寄寓、交织、萦回的1870年代黄金海岸的生灵,构成1970年代动荡的加纳与前生的隔世对话。前者(1870年代)对后者(1970年代)的呼唤或警示,犹如后者对前者的告别或重写,经由两者之间断中有续、续中有变、变中有联的人性灵影,差异化地揭示出两者内涵复杂的交叠、交锋和求变驱动。移动在过去与现在的复杂交叉之中,这一空间意义上徘徊的旅人由此具有一种“双重时间概括性”,即“过去与现在重叠的时间性”。
当艾杜深入19世纪的非洲,将她那被锚定而无所归的迁徙人凝练成现代人性界定性喻象之一时,英国的卡尔·丘吉尔也在1970年代的书写中重访很久以前的事,以度量自身所处时间中的场域转换。她于1976年发表的历史剧《白金汉郡闪耀之光》(LightShininginBuckinghamshire)(26)该剧名与首次出版于1648年的掘土派(Diggers,又译“真正平等派”,主张平分土地,代表乡村农民和城市平民利益)的一宣传册题目相同,示意出剧作家由历史反思,转向追求智性启示。关于掘土派的历史研讨,参见 George Sabine,ed.,The Works of Gerrard Winstanley (New York:Russell and Russell,1965)。,重新上演了17世纪英国的动荡时刻及其蕴含的解放性驱动力,它裹挟三位女性,在移动中横跨正在经历结构性巨变的英伦大地。第一位是玛格丽特·布罗泽顿(Margaret Brotherton),她徒步从出生地朗伯克比(Long Buckby)离开,走过北安普敦(Northampton),走过亚斯顿科莱顿(Aston Cliton),直至走过我们见到她的无名之地,一路上寻找生计。她并没有出现在那些地方的计划,也没有留在或离开那些地方的选择。意味深长的是,玛格丽特在舞台上的出场正值她以“路过性身份”(无名身份)抵达“在此”(无名之地)并因此受审之际。两位地方治安法官进行审讯后,给予玛格丽特“温和宽大”的判决:
治安法官甲:你必须回到你的出生地。
治安法官乙:如果她父母不是从那里来的,他们不会接受她。
治安法官甲:那么她父亲的教区。
治安法官乙:她从未在那里居住过。
治安法官甲:她最近居住的教区。
治安法官乙:他们由于她行乞,把她赶了出来。
治安法官甲:完全准确,我们也这么做。
治安法官乙:你为什么不结婚?
布罗泽顿:……
治安法官乙:玛格丽特·布罗泽顿,我们发现你已触犯漫游流浪罪,现判处你受鞭笞直到本教区边界,然后逐出教区,遣返,直到、直到……
治安法官甲:她的出生地。
治安法官乙:直到你出生地所在教区。下一个。(27)Caryl Churchill,Plays:One (London:Methuen,1985),194.本文中引用的《白金汉郡闪耀之光》剧本内容,均出自该书,不再一一标出。
当然,她的出生地教区不会接受她,因为她父母来自他乡。这里,玛格丽特的生命被定格为一种无法在现代范畴构成的现代秩序中合适安置的人类现象,具有一种无法争辩的合理性,她代表因法典词汇缺失而违背法律条规的人的存在。当时,即现代资本发轫之际的整个英国,到处是这样的人。世人熟知的16世纪早期的圈地运动,见证着自耕农是如何被羊替代,以及约翰·贺尔斯(John Hales)于1549年描述的情形,“……原众户之里,现尽为一人与其牧童所独占……盖诸般乱象皆因羊而起,本国种植耕稼,亦受其倾挤而尽被驱逐,昔日丰产五谷之田,今唯见羊群、羊群、羊群遍地”(28)Robert L.Heilbroner,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8),28-29.。当时,人们相继成为四处漫游的无居存在,为资本持续扩展而又变动无常的需要让路。伊丽莎白女王在16世纪末的一次全国巡视后迷惑不解地抱怨:“怎么贫困的人在到处跑呢?”(29)Ibid.
“贫困的迁徙”由此成为从英伦到欧陆乃至全球性的某种场景,其中构成的“人性的匮缺”(human deficiency)或更准确地说“人性的贫困化”(impoverishing humanity)成为资本扩展的内在矛盾本身。在丘吉尔笔下,这些“贫困的迁徙”“人性的贫困”构成现代人文地理秩序安排的难题,因此需要加以调节性的管理或惩戒。作为现代性初始有组织的大混乱的症候,他们被要求成为见证自身抹除的一种存在;而如此要求的不可能性,则记录着其中现代性初始机制运作及其或隐或显的暴力。(30)Robert L.Heilbroner,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8),28-29.就历史而言,早在16世纪中叶英国就出现了带有内在矛盾的现代迁徙的骚乱,直到18世纪中叶结束,两个世纪的此起彼伏,考验着直至改写了现代资本的初始并获得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的“文明化”(31)参见聂锦芳:《完整准确地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光明日报》,2022年7月25日。。裹挟于1640年代的英格兰发轫的这种机制运行之中,丘吉尔笔下的玛格丽特,以她持续不停而不被认可、或者说不被认可而持续不停的迁徙性,意喻着当时英国社会的特殊状况与含有全球变奏态势的历史内涵。具体而言,玛格丽特在剧中作为“贫困的迁徙”“人性的贫困”的女性出场,记载着当时英国议会在危机之中的应急措施及其悖论。全国不断扩大漫延的迁徙人群使议会感到恐慌,于是尝试用“地方化”来解决问题,一方面以少量的救济金将人们限定在各自的教区里,一方面以刑法来处理无教区的“漫游人”。(32)Robert L.Heilbroner,The Worldly Philosopher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8),29.这一英国议会国家机器的运作,具有不合理性的自洽性、随意武断的系统性,同时显示出的则是一种现代秩序的普遍逻辑:迁徙的人群,由于资本逻辑运行而不断移动以寻求可能的生计之处;同时,其来自资本驱动的多变无常又不得不被政府以不同形式加以定格限制。(33)对“定格限制”作为欧洲起源的现代性特征的研讨,参见John Torpey,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简言之,因某种场域变动而迁徙的人们,同时被定格为某种固然/“始终已然”(always already)(34)Jacques Derrida,“Structure,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278-293.的因其不可辨而不合理的存在,具有内在的可疑性、权宜之计的非法性或需要预设的有罪性。作为迁徙不定的存在,作为现代生产和人的关系之历史语境形成期的游动因子,玛格丽特不得不上法庭,在那里被命名、被定格,尽管她的迁徙性本身来自这种生产。两个地方治安法官对她不合理而又“温和宽大”的处理,使得玛格丽特仿佛是现代性巨轮下间接、偶然而又必需的代价,意图展现的则是现代人性受双重驱动悖论限制的结构性:一种始终定格的永久迁徙;永久迁徙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始终定格作为必然所需的代价。
这种始终定格永久迁徙的悖论内涵,正如地方治安法官对玛格丽特质询审判的字里行间所见证的,是雏形阶段的现代人的流寓性,而这一现代属性的核心特征,在丘吉尔笔下是社会性别化的。玛格丽特无法声称自己拥有现代制造的生存场所、各类资源和建制机制的所有权;而父权制的家族和财产拥有是这一切的物质基础与象征意义。“你在这里有没有亲属?告诉我们可以雇你工作的你的第三个表兄的妻子的兄弟的情况。”没有进入婚姻机制的玛格丽特,即没有男权家族资产及其亲缘关系的能指,于是成了这片土地上无所居者的社会性别化缩影和身体表征。在这里,带有某种掠夺性的获取及其相应的技术手段正在发生,并被作为男性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属性和自然化的力量赋予必然性。这一“自然化、具必然性”的历史内容,是在帝制下构成并在内战后变化中延续的封建男权财产。克伦威尔革命的初始发生,曾经是建立在对帝制秩序深刻变革的承诺之上,即基于生而为人、生而为英国人的公民权益,将在新的代议制中被全面呈现的真切愿景。剧本上半部的结尾重头戏,是新军准备与查理一世进行谈判前,新军代表和新军主帅克伦威尔之间发生的关于新生英联邦如何实现这一承诺和愿景的论辩——史上著名的“普特尼辩论”。(35)参见 Geoffrey Robertson,The Levellers:The Putney Debates,ed.Philip Baker (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Books,2007)。在这一辩论中,这一承诺和愿景通过形式上的“理性对话”和程序处理(“另立委员会专议”)被置换、被取消,结论是参加代议制运行的人,须具有帝制时代构成并延续的恒产人身份。这意味着追随新军的人们失去在战场上以死相搏的根据,事实上成为“玛格丽特化”的“无可辨认性、无合法性身份”之人。
玛格丽特们因在这个大迁徙时代“没有土地、教区、国家”而受审,这个世界将她们变成帝制男权现代变奏的后效意象,同时又要求她们从其可见的场景中消隐——因为她们没有身份等级可归置。作为被社会性别化的迁徙者(无论其事实上的物理性别是男性或女性),玛格丽特们揭示了现代人性的流寓困境。(36)关于性别、身体和政体的关系问题,参见 Teresa de Lauretis,Technologies of Gender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5,12; Sue-Ellen Case,The Domain-Matrix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6),127-186。在英国内战中社会机制肌理既延续又转型的复杂语境下,丘吉尔式玛格丽特们,勾勒出充满人性解放驱动承诺的克伦威尔革命,是如何在裹挟了这样的迁徙者的同时,悬置、定格和消抹其迁徙人生,并指向了这一双重限制在与帝制场域的交叠中变动建构的现代话语机制。丘吉尔通过剧中第二位女性——与玛格丽特形态不同而又遥相呼应的霍斯金(Hoskins),或者说通过两者互为变体的场景,对这一历史繁复性及其矛盾张力,予以凝练的揭示。作为克伦威尔新军信仰教宗的热忱成员和新福音派(New Gospels)女性传人,霍斯金对新福音满怀激情,构成对掌控教宗及其承诺愿景的教会的某种威胁,因而被排除在外。穿越旧帝制来到新疆域,她发现自己仍被某种原点牵控。极具表达能力的霍斯金对新福音开始阐释,而她只说了半句话,就被捂住口,最终被新权威的手下人赶出圣公会,这匪夷所思地令人想起玛格丽特受审时的“几无声息”。两者作为无以言表的喻像,指向现代性在欧洲发轫期,人性在物质实存和意义界定层面上的双重危机。挨了打的霍斯金被交给一位农妇,剧中第三位女性来护理,由此完成了丘吉尔借助女性的社会性别属性而承载的现代流寓三重奏:农妇的孩子一个个夭折,丈夫已追随克伦威尔军队而去、并将转而向爱尔兰进军。她头上崩塌中的屋顶和脚下消失中的土地,凸显出“主妇”无以为继,“家庭”正在成为年轻废墟和年老绝望的双重遗址,其中的人性内容正在化为蒙太奇式的灵影组群。
丘吉尔对英国历史界定时刻显现的人性灵影的重访,唤起艾杜重述阿诺瓦传说的“双重时间概括”,即“过去与现在重叠的时间性”。该剧上演时,英国充满了后帝国综合征和不确定性,丘吉尔在遥远的17世纪那场“未曾发生的革命”中让女性灵影重聚,反思过去,以重新把握和想象被抽象既定时间规则分隔为前世和未来的今生。“虽然如今没有人会期待基督在地球上建造天堂,”丘吉尔为1970年代末的观众写道,“但他们的声音(中有一种脉动)不可思议地与我们如此接近。”(37)Caryl Churchill,Plays:One (London:Methuen,1985),183.在张力隐伏的欧洲(38)Perry Anderson,“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s.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317-338.,各种版本的撒切尔主义及其还有待数十年才能开始显性化的多重后果登场之际,如此重新想象构成了一个面对正在到来的又一轮全球巨变的预见性警醒:革命性解放性的人间潜力的释放,可能会因对历史机遇的某种错过和误解而流失。“耶稣基督确曾来临,但无人有慧眼注意到,”丘吉尔笔下的霍斯金回溯细想,“正逢其时,但我们不知怎么就错过了。”重访叩问、更新想象和告诫警醒三重交叠,丘吉尔演绎出的是一种独特的揭示启迪,(39)Elin Diamond,Unmaking Mimesis (London:Routledge,1997),54,142.对动荡的现在与萦回的过去在相互有别之中的同时包容和概括:它在过去中触动现在,通过现在透视过去,在指向其一维度的过程中唤起另一维度,由此活跃起批判性的反思和前瞻。17世纪的流寓人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的英国舞台与欧洲社会,所带来的是对双重限制、悖论命运裹挟下数世纪人性困境的把握与叩问,相关着过去,切合于现时。如果说1980年代以来马歇尔·伯曼等同具影响力的“双重时间概括”书写,关注19世纪对现代性“人性困境”的文化处理,并重点强调其主动变革的精神资源,(40)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Penguin Books,1988),15.与之相对的后结构主义等诸种批评则立足于对主动变革的根据即“主体”(前提是制造“他者”)合理性的质疑。丘吉尔自1970年代末起以源源不断、丰富复杂、深邃灵异的女性喻像,持续深入地展开她对困境的批评性追问,以及对批评本身的问题化探寻。1983年的《沼地》(Fen)是其中另一例证。该剧追踪一片古老的沼地是如何在一双双手中转换了几百年,而新近则由英国股票金融交易所(the City)及多国拥有的机构接手。在持续易主的土地上,女工代代定格,命运延续,在那里,她们“始终已然”是人性耗损的具象,“她们脸上挂着结成冰凌的汗水,只有永无终日的劳作、劳作、劳作”(41)Caryl Churchill,Plays:One (London:Methuen,1985),171.本文中引用的《沼地》剧本内容,均出自该书,不再一一标出。,几无声息,仿佛流寓灵影,跨越时空往复出现。当农场主特沃森先生完成与英国股票金融交易所的全球并购交易转身欲离开时,赫然被一个“光着脚,身上披了一片数百年前的粗布在田野里工作的女人”和她的眼神抓住,“她确定是来自过去”,但与当下活着的“其他女工一样真实”。心情被扰动的特沃森先生问道:“你愤怒是因为我卖掉了农庄吗?”她回答:“是否因为这一点,会有什么分别?”特沃森回答:“自然,不会的,因为卖不卖掉,结果并没有不同。”她说:“这是我愤怒的原因。”至此,丘吉尔笔下的流寓游魂与艾杜笔下的迁徙灵影,承载着自身同时被始终定格的悖论,跨过生死、世纪、洲际、话语机制、法典秩序的区隔边界,带着各自的所有差异而遥相呼应、无言汇合。她们是如此遥远独特而无法显而易见,她们又是如此充满生命律动而无法历史缺席。
二、不可见性:另一种视域
这些具有双重和复数时间性的流寓律动、灵影在场,标记出艾杜称为(现代的)“人类历史中一种最为矛盾的不可见性”(42)Ama Aidoo,An Angry Letter in January (Aarhus:Dangaroo Press,1992),67.,而这种不可见性及其女性具象,对过去数十年在世界范围高度可见的“自由流动人”“宇宙原子人”,乃至作为“地球是平的”这一宣称能指的“全球飞人”的话语景观而言,提供了令人冷静清醒的另一种视域和跨界性视野。(43)对全世界通行无阻“全球人”意象的多种批评,参见 Norma Alarcon,“Traddutora,Traditora,” in Dangerous Liaisons:Gender,Nation,&Postcolonial Perspectives,eds.Anne McClintock et al.(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294。她们萦绕不去的律动在场叩问着这个“无边”世界里倍增的奇观,成为衡量世纪之交“边界”与“跨界”书写的另一种尺度。她们使人们审慎自问,大迁徙中的人性时空在何种历史前提下是自由的天地?各种迁徙者、路上人的追寻脉动,在何种条件下、范畴内或程度上能获得现代意义上的解放性?而被解读化约为“全球自由人”的话语景观,在现代人文地理的剧烈变更中,是否构成对其中内含的矛盾、困境和生命实存的遮蔽?艾杜和丘吉尔舞台上的迁徙者或流寓人,作为通常不可见的现代人类某种“移动受惩”(mobile penalizations)悖论本身,在过去数十年间引发了纷繁多样的话语生产。她们并非只是“当下热点”“突发现象”,她们从数世纪前走来,在世界现代史的体内深处长期存在;同样长期存在的,是绘制、认知和把握她们生命特征和历史内容的人文需要、智性揭示和变革启迪,这特征内容关乎现代生产日益复杂的组织原则、机制结构、权力关系,及其带来生命活力也带来生命伤亡的模式与变迁。艾杜和丘吉尔对迁徙、流寓、灵影意象不约而同的探究和喻指并非偶然。1970年代末正值全球秩序重组加速,被称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新一轮浪潮正处在还未显形的构成之际,其中蕴含的人性移置、人性再造、人性可能,以及人性代价的程度、形态、范围、规模当时还难以度量认知。(44)参见Noam Chomsky,Year 501 (Boston:South End Press,1993),60-61。两位作家重返并深入现代资本与旧制度缠结中的发轫场景,探究其既具体特殊而又囊括世界的全球性驱动及多重差异,(45)关于以资本为主脉的现代史如何具有充满差别性和异质性(包括国家与区域的差别、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对峙等)的全球性驱动,以及现代知识生产不同专业区隔分类制在处理认知这驱动的复杂属性方面的局限,参见Jacqui Alexander &Chandra Mohanty,eds.,Feminist Genealogies,Colonial Legacies,Democratic Futures (New York:Routledge,1997)。由此将她们数世纪后所感知到的又一轮结构变迁人性移置交织其中,转换为舞台艺术的三棱镜,以叠缩透视(telescoping)那跨过漫长的数个世纪、痛楚而恢宏的缺席在场、迁徙流寓中的生命之魂。
这一叠缩透视的艺术审美与历史思辨,与欧美1990年代以来大幅增长的文化批评产生共鸣。亦是来自丘吉尔出生地的宗主国大都会的佩里·安德森在1980年代后期援引马歇尔·伯曼绘制出的现代人性在迁徙流寓中的灵影化,谈欧洲现代艺术揭示的“氛围症候”(atmospheric symptoms)。“焦灼躁动与湍流化的气氛、心智精神的晕眩与迷醉、经验性可能的巨大扩展、道德界限与个人之间相互关联的毁灭、自我的膨胀和错乱、街头上和灵魂中的憧憧幻影——所有这些都是现代感知模态赖以降生的氛围”,正是在这种感知模态的驱动下,他接着写道,1960年代后期欧洲社会被误解而自称的那一场革命,其实是全球资本结构重新布局所预示的“放纵消费主义时代的降临”,或是此后被称为“历史的终结”的起始。(46)Perry Anderson,“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s.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319-329.参见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no.16 (1989):3-18。而来自后殖民时空的恩古齐·瓦·提安哥等作家则将此类“终结”论之起始作为症候,解读为一种变奏中大变迁的历史要求,即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跨越边界的阿诺瓦们的轨迹、脉动、寓意、启迪的及时把握,来再一次感知、揭示缺席在场、流寓之魂,来再一次言说、转写这一或延续或裂变的现代母题及其更新可能,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47)Ngugi wa Thiong’o and Micere Mugo,The Trial of Dedan Kimathi(London:Heinemann,1976),17.参见Yan Haiping,“Transnationality and Its Critique,” in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Ama Ata Aidoo,eds.Ada Uzoamaka Azodo and Gay Wilentz (Trenton,NJ:African World Press,1999),93-126。
三、全球迁徙者的登场
在欧美历史性的语境中,这种不可见性(invisibility)与缺席性(absence)有着属性的不同(48)欧美语境批判哲学中对“absence”的批判思辨,锋芒所指主要是欧洲形而上学起源于“神”的属性及其对此属性的批判或者说解构。关于此命题的早期且具有持续影响的阐释,参见Dominick LaCapra,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43-85。,前者指向的是现场存在的生命,在人为建构、有可辨性和合理性的话语机制意义秩序的运作中,被悬置隐匿的状态,而被悬置隐匿的前提是她的现场存在。如何处理这一悖论状态,成为批判哲学中关于人类知识的技术生产和方法问题的争论之一。艾杜与丘吉尔在数十年前就开始追寻这一悖论的流动性存在,尝试去度量这一悖论的历史条件和思考对此条件的转写路径。换言之,两位剧作家在书写和上演“永久迁徙”“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ce)的过程中,生成了一种戏剧能和剧场性(49)关于戏剧能和剧场性,参见Tracy C.Davis and Thomas Postlewait,eds.,Theatrical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65-89;颜海平:《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戏剧中的剧场性》,吴冠达译,《戏剧艺术》,2022年第2期。,将度量中的历史条件转喻、上演为人性艺术的生成本身,唤起文化批评家贝尔·胡克斯所说的“家园之所”(50)Bell Hooks,Yearning (Boston:South End Press,1990),41.(homeplaces)——在那里,被引发、裹挟、牵制和悬置隐匿的实存获得见证的路径、延展的想象、变革再造的动能。此处的“家园之所”是“生活中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温暖的庇护、身体的饮食、灵魂的滋养”(51)参见Jill Dolan,“Performance,Utopia,and the Utopian Performative,” Theatre Journal,no.3 (2001):472。发生的地方。这是一种物质界和精神界相遇交融的动态现场,与双重限制及其话语机制的“各种示意”(52)Bell Hooks,Yearning (Boston:South End Press,1990),41.拉开距离,打开另一种人间视域、另一个时空场域、另一重审美界域。(53)参见佩里·安德森所说:“视域的封闭……是当代西方艺术典型处境的标识:重现无尽的现在,而没有恰当适宜的过去或富有想象的未来。”Perry Anderson,“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s.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329.与安德森们或恩古齐们相对应,1970年代末的丘吉尔探究的是如何感知迁徙性生命的律动,从而得以揭示遮蔽和抑制这律动的话语机制的运行。丘吉尔用某种可称为“跨界体现”(cross-boundary embodiment)的舞台手法,示意出现代迁徙是一种矛盾的驱动,内在蕴含着强大的变革性,洞察和展示形态不同而又互为见证的生命载体如何被分散、被区隔,唤起的是超越区隔联结律动的驱动。《白金汉郡闪耀之光》于1979年的首演,是著名例证之一。斯塔夫德-克拉克(Max Stafford-Clark)导演的、联合股份剧院(54)联合股份剧院(The Joint Stock Theatre Company)1974年创办于伦敦,参与人包括David Hare、Max Stafford-Clark、Paul Kember和David Aukin。推出的这部作品,凸显了诸多创新的舞台表现手法,包括用不同演员饰演不同场景里的同一个人物,同一个演员饰演各种场景中不同的人物。作为排演过程中的即兴发现或者说艺术发明,这项创新在那些作为流寓迁徙人的具象,即那些分散的个体之间,生成了一种充满差异、“交叠共有的历史”(a shared history)的多维动态感知。“观众不必担心如何去搞清楚他们正在观看的是哪个人物,”丘吉尔写道,“(这里)出现的是一个牵涉到众多人的重大事件,剧中的人物以某种方式互为共振;而如果他们被更为清晰地界定,这一共振将不会发生。”(55)Caryl Churchill,Plays:One (London:Methuen,1985),184-185.
《白金汉郡闪耀之光》首演时,许多批评家以强烈的热忱注目这一舞台创新及其效果。大卫·麦罗维茨(David Mairowitz)写道:“这部回肠荡气的作品有个激动人心的特点,即预先推设了某个特定的历史基础,随后的展开不再强调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剧中的历史根植于一种‘连接性’的意识,这是作品的现场主角。”(56)David Mairowitz,“Review,” in Caryl Churchill:A Casebook,ed.Phyllis R.Randall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Inc.,1988),42.这种“连接性”由不同的具体身体承载,而具体身体的差异使得“连接性”本身充满弹性的想象空间和意义的张力。剧中扮演玛格丽特的珍妮特·查佩尔(Janet Chappell)也演霍斯金,扮演霍斯金的琳达·戈达德(Linda Goddard)也演农民妻子,她们俩又都扮演另外两位农妇及来自大迁徙历史长卷中的各色人等,她们在交叠中互为印证,如此生成的连接性意识,成为摆脱悖论命运的具象组合、动能现场。换言之,如此“动能现场”在“跨界体现”(cross-embodiment)的动态中酝酿、呈现、延展,指向具象个体在跨越个体中的各种形象,同时揭示出她们在个体转换和相互出演中唤起、凸显的“连接性”。(57)关于“跨界体现”(cross-embodiment)形式即内容的部分阐释及其中国例证,参见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1—253页。玛格丽特、霍斯金、农民妻子、“普特尼论辩”中“缺席在场”的人们,在“连接性”的呈现中,成为摆脱自身悖论状态的现场可能,她们成为丘吉尔笔下向“民主迈出的步伐”的实存条件。发人深思的是,丘吉尔剧作1979年舞台版中生成的“连接性”在呈现中亦被悬置,而又因悬置而格外凸显。萦回的女性迁徙者在跨界体现、交叠交织的同时相互错过,而这错过亦因此是对连接性本身的呼唤。在最为直接的事实层面上,玛格丽特和霍斯金在穿越动荡的大地、不断迁徙的场景中,身体不断交叠,眼神却从未相遇,在相互“路过性在场”中,成为彼此“被定格缺席”的症候的证人。她们的“连接性”在不同的生命体相互交叠、转换出演中展开,同时“连接性”本身并不指向“连接性意识”的孕育及其变革的出现。(58)“意识”和“想象”的时空性、物质性本身,指向了福柯意义上的“治理性”。丘吉尔晚年的作品对此有更为深入的书写。参见莫詹坤:《卡瑞尔·丘吉尔近年剧作的去乌托邦表达》,《当代外国文学》,2020年第3期。正如那些“正在出现但还未发生”的历史事件(59)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Wiley-Blackwell,1991),224.,她们是连接中出现的转变性潜能律动,但其潜力在律动中流寓化、流产化的高频率常态性,由于她们跨界体现的现场连接性而显得含义格外深远。比如,当农民妻子把霍斯金托在左手臂上,用右手舀着温水轻洗她的伤口血迹,霍斯金看不见农民妻子呵护的手,而继续执着于为获得《圣经》表征系统中的女性符号及对符号能指的承认而耗尽激情。在近旁街头上徘徊的玛格丽特,对霍斯金为了“证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选民”,而与这一领地上的权威布道士就规定的术语,也就是“以典籍为根据”对“这本书”的话语使用的合法性(“要原典引文?这是原典引文,不是吗?”(60)对文本中心认知逻辑和策略的批评,参见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Wiley-Blackwell,1991),60。)进行的激烈争辩,一无所闻,如同身处遥远的异域。(61)Gayatri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271-316.换言之,对于带有绕过自身社会与历史的复杂中介及其属性问题的认知倾向,或者说无条件的“集体性”观念本身——这一观念是英国新左派的要义之一,丘吉尔保持着审慎清晰的距离。然而她对“连接性”的舞台书写,构成了战后变局中包括新左派等各种批评出现的广阔社会基础和复杂变革动因的内在部分。(62)丘吉尔1996年6月在大不列颠图书馆与笔者的谈话中,回忆了她参与初创新左派,后与之“保持距离”或者说“独立”的经过。前几个场景里,曾经扮演过玛格丽特、霍斯金和农民妻子的同一批演员又分别扮演剧中包括其他农妇农夫在内的各种人物时,不同的个体身体在相互交叠、相互转换、相互见证中,萌生出某种舞台能量,形成逸出文本“结构元素”的物理气场。(63)Sandra L.Richards,“Writing the Absent Potential,” in Performativity and Performance,eds.Andrew Parker and Eve Kosofsky Sedgwick (New York:Routledge,1995),77.在现代世界与帝制权威既交锋又缠结的历史语境中,从资本发轫的内部产生并同时被遮蔽的迁徙人流寓性,在此通过区隔性个体的相互转换交叠,即跨界体现而生成的互相折射,揭示出构成这一世界的核心矛盾、复杂构成和变革驱动。同时,丘吉尔蕴含高度变革性批评驱动的“跨界体现”没有亦无意提供无条件结论性的剧终:它指向现代迁徙者们跨越个体区隔而相遇的能力或潜力,在呈现出其充满张力的在场的同时,警示其被多重中介退场或匿迹的现实与可能。这退场或匿迹不同于缺席,而是有待认知的、极为多变的在场轨迹和形式。(64)参见前文关于戏剧能和剧场性的注释。由丘吉尔式“叠缩望远、透视汇聚”审美方式而会合的过去与现在,由“跨界体现、互为连接”舞台路径而呈现的律动生灵,作为人世间无所居之现代历史人性困境的坚韧见证,并不宣称新的社会政治蓝图解决方案。这些律动是萦回于现代世界内部的灵影在场,亦是对徘徊重现的现代困境的衡量。“她做了个噩梦。”《沼地》里的流寓之魂越过生死的区隔,注视着一位熟睡的妇女时这样说。那位妇女正在梦见自己四处奔跑,但又滞留在一处,“她做着噩梦跑下楼……她到了外面的路上但又跑不快,于是手脚并用,想跑得更快些……她知道怎样让自己醒过来,以前这么做过……但她错了,她没有醒来,而是陷入另一个梦”——定格又漂浮、变化且重复的梦。这是一种情感的结构,通过一种可被称为“不能自拔中的高度苏醒”(dead awake)而感知“某个地方某种苦痛”的人类意识(65)Caryl Churchill,Plays:One (London:Methuen,1985),188-189.;这是一种缺席的在场,坚持不懈地呈现出这种多变形态的人间之痛,指向使之变奏重现的机制运行,并在界定这一多变之痛的属性中,评判着既变革又延续的人类历史本身。
相对于丘吉尔式“连接性”在英伦历史中氤氲的变革可能,艾杜式穿越边界的迁徙者、路上人既是这可能性既遥远又切近的回音,亦是更富有开创性的全球登场。如果说丘吉尔将“流寓人性”绘制为由英伦大都市发端和欧陆延伸构成的现代性特征,那么艾杜突出的则是这一特征指向的全球范围内跨国界、跨语言和跨族裔的某种人性裂变和生成,这裂变和生成与欧洲式的现代秩序及随后的全球扩张相伴而生,如影随形,横跨塑形这一秩序的所有边界,尤其是宗主国大都市与其边缘区域之间最根深蒂固的区隔鸿沟。(66)关于“区隔”作为自19世纪以来的全球结构性组织范畴及其社会、经济、政治、认知、伦理和审美的效能属性,弗·詹姆森的一系列著述影响广泛,参见Fredric Jameson,“Modernism and Imperialism,” in Nationalism,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43-66; Fredric Jameson,“Cognitive Mapping,” 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s.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347-360。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奈格里包括《帝国》在内的一系列著述是对这种“区隔性”在过去数十年中形态变化的探讨和命题更新;参见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而托马斯·皮凯蒂所著《21世纪资本论》则将此命题推到了世界范围人文社科跨学科跨领域的认知生产前沿,参见 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rans.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具体而言,当丘吉尔追寻着她那英伦本土的流寓女性,呵护着她们遭受苦痛的生命内核,倾听她们无声的歌唱,展现她们相互的“跨界体现”,艾杜则关注着她那全球迁徙的候鸟灵影,凝视着她们贯穿并超越这生命内核,在苦痛中裂变生成的能量。艾杜为呈现这裂变中的生成、生成中的裂变所使用的舞台书写,共振着丘吉尔式的叠缩透视、跨界体现的时空创新,同时带着艾杜式的独特驱动。
《阿诺瓦》的结尾是这种艾杜式驱动的例证之一。通过一个逐渐悟出的过程,阿诺瓦发现了在科菲最后提出解除夫妻关系而又不提供理由的沉默中的真相(67)按方狄部落的传统规则,科菲必须提供这一要求的理由。,即他“人性的枯竭”,傲谷庄园是这一枯竭的物理表征。就事实层面而言,庄园圈养了家奴而没有孕育后人;就表意层面而言,庄园拥有“镶金座”却没有人性意义的绵延。“科菲,你是死了吗?”阿诺瓦一字字问得缓慢而精确,“圈养家奴和建造宫殿,是不是耗尽了你的男性之源?”科菲随后的自杀,似乎并不仅仅是被如此揭示之后的别无选择,而是他长久以来累积的一切的最终物理体现。而阿诺瓦的终曲也暗含死亡,却更为多维复杂。她的“最后退场”演出如下:
阿诺瓦:……报信的人很快就会回来了,/地毯、图片、你、椅子,还有你,女王,/如果他们问起我,/就告诉他们我走了。/告诉他们,智者是怎么说的无关紧要,/因为/如今我比他们更有智慧。
[她的目光停在镶金座上,然后突然地往前跳了一两步,一下子坐在宝座上,开始像个孩子似地晃起双腿,脸上露出欣悦的笑容。她爆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后台突然一声枪响,随后一片静止。在男女惊叫声构成的后台喧嚣混乱中,阿诺瓦再次开始咯咯笑起来。灯光在她身上聚焦,慢慢转暗。]
后台的枪声表明科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用人性祭奠的傲谷庄园。另一方面,阿诺瓦的结局包括从“镶金座”上传来的咯咯笑声、光脚赤足和孩童般的笑容,完成了对新殖民三位一体镶金交椅的越界、瓦解,以及对其至高无上神话的解除(demystifying)。随着“阿诺瓦身上的灯光慢慢熄灭”,她的“咯咯笑声”犹如内蕴在实存女性身体里的精灵,成为萦回的一种在场,穿越后台的喧嚣混乱和前台的一片漆黑,在剧场内外长久振动。该剧1992年在伦敦盖特剧院(Gate Theatre)等处的演出效果表明,内涵如此复杂的人间诀别不仅揭示出傲谷庄园的苦痛隐秘,而且重新界定了庄园的核心组织机制——那把全权神话的镶金座,及其运作与延续。(68)1995年夏季,艾杜在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与笔者交谈中介绍了1992年该剧在盖特剧院演出时观众诸多层面的理解。艾杜在《阿诺瓦》的演出提示里说,阿诺瓦用“这样的(跨界组合式)最后退场”来“结束全剧是相当可行的”,这提示值得认真对待。如此收尾既是一种舞台审美的结构性选择,也是人类历史的洞察想象,使如此终局的阿诺瓦,不仅作为“某个地方某种苦痛”的见证,还成为一种指向再生的路径本身,这是一种踏荆棘满地以碎其限制的挣脱,一种人性裂变中的生成。“光脚赤足的”阿诺瓦坐在巨大无比的宝座上,背对着俯瞰宝座的“维多利亚女王像”和刚刚进爵的新领主及其图腾。当科菲自杀的枪声响起时,她“笑容欣悦”“双腿晃动着”,发出有节奏的“咯咯笑声”。这一现代世界戏剧史上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阿诺瓦场景”,透露出一种无以言表而又给予强烈启示的在场感;其丰富性复杂性所蕴含的实质,是对镶金座及其永恒性本身的废黜。
在该剧本里,这一场景还不是结束。艾杜在排演说明中亦表示,演出也可以选择按照剧本所写结尾。根据剧本,灯光从舞台两侧打出,空荡荡的镶金座上已“无人占据”“穿着深红色丧服的人们迅速将其围绕,仿佛这是葬礼床”。哀悼场景引出歌队老妇与老汉的最后出场,他们的评述结束了全剧。通过老妇的叙述,人们得知科菲自杀后,阿诺瓦“自沉”了,与似乎“始终已然”将她牢牢定格、无从摆脱的庄园同归于尽。然而老妇又将叙述进一步问题化,开始对阿诺瓦评头论足。尽管她一直着迷于科菲庄园的显赫气派,但现在老妇的谈论方式显得阿诺瓦与其说是庄园里“掠过的灵影”,毋宁说是某种超强的力量。“他们说(阿诺瓦)总是不停地工作,就好像她能一口气吃掉一千头牛。求神宽恕我说逝者的坏话,但是阿诺瓦吞掉了科菲·阿寇!”一直质疑科菲领主地位的老汉,则以令人想起阿诺瓦“咯咯笑声”的“吃吃笑声”来回答老妇的话,并认为领主的人生方案就人性而言原是不可持续的,“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疯了,除非他打娘胎出来时脑子就有病”。当老妇说阿诺瓦不属于这个现实的生活世界时,老汉内心被搅动了。他“安静下来,没有去看老妇”,转而将“阿诺瓦是否可能生活得好”作为问题交给了1970年代末的观众。“如果我们并不是像一直以来的那样为人处世,谁又知道阿诺瓦会不会是个更好的女人,更好的人?”仿佛被某种力量推动着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老汉随之开始交代阿诺瓦故事的合适善后,接着宣称:“噢,如果死亡之后还有生命,阿诺瓦的精灵肯定会有重要的话要说!”,由此邀请观众对“重要的话”展开想象,尤其是各自身在其中的那一部分。于是,当过去的界定时刻和现在的转折之处如此叠缩透视、跨界交织,多种不同的“结局”成为切实的可能,在当下和未来的此刻,一如历史上所有的此刻和过去,正如艾杜在排演说明中对置于19世纪黄金海岸语境中的《阿诺瓦》结局的示意,“选择是开放的”。
与丘吉尔“跨界体现”相对应,艾杜对古老传说的复述的审美方式的结构性特征,在于组织贯穿全剧的老汉老妇歌队,其叙述评论功能,为全球性秩序安排及其动荡重构所铭刻,同时是对此动荡的回应、对重构的把握、对铭刻中不同力量的认知衡量和变革尝试、对世界性历史场域的复杂参与和变革性书写。序幕引出传说及将其历史语境化的方式,对1970年代的观众而言,充满隐喻并将他们卷涉其中。在介绍剧中故事设置在19世纪中期的过程中,歌队灵活交错地使用了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态,并以反思过去、观照现在和指向将来的评注结尾。“啊,我亲爱的,/如果有这个人或那个人/为过好日子而依附上/那苍白人,/我们实在不必为此感到惊讶,科菲过去是、现在是、将总是我们中的一员。”换言之,被科菲规定为“精致陶罐”的阿诺瓦,以其“奇异的眼神”和“萦绕的灵影”揭示了科菲对旧殖民逻辑的依附性,而这样的“依附性”并不止于科菲。当歌队的老妇从科菲转到阿诺瓦“(这)不知道哪儿不对劲的美丽女子”,费力地琢磨着“她就是那种让她非同寻常的美丽弄晕了她对世界的构想的女子”,而这实在是由于“她母亲丢脸的溺爱”时,舞台一侧的母亲巴杜亚“突然爆发了,她手指着老汉与老妇,对着自己说:‘可能这也是我的错,但是,当她的名字总是这样挂在每一张只知道吃胡椒和盐的嘴上,阿诺瓦怎么能有好结果!’”在此,如何摆脱依附性的问题,经由巴杜亚传递给了歌队、“我们”——包括观众在内的每一个人。(69)序幕中歌队老妇提示,在耶比村看来,阿诺瓦生来合适去当女祭司,是母亲巴杜亚对此坚持拒绝,把阿诺瓦留在了人间。灵活交错的时态同样运用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老汉与老妇的歌队叙述中,两人争论完科菲和阿诺瓦的经历后又分别予以评论,表达对昔日传说的不同看法,由此形成观众的反思性参与,这些相左评判及其历史内涵和当下效能,最终取决于每一位当下观众的思考、判断和选择。
老汉:我的乡亲们,人们说他(科菲)买起男人女人来,就好像他们每一个人只值岸边的一捧沙子……把别人变成家奴这件事一定有某种伤害身心的东西……每座吞入家奴之所,都是自行毁灭之地。
老妇:耶比村的人,欢呼雀跃吧,/科菲·阿寇已经成功发达/……阿诺瓦却日益消瘦/她就是那个我们不允许再踏进这里的人!
传说故事所处的“过去”与其再度登场时诉说的“现在”,以两人歌队相互冲突的表述在此交汇,观众需要选择的是他们与这种传说历史的关系和在当下变局中的自身定位。如何选择的问题,内在于艾杜自1970年代末以来贯穿1980年代、1990年代至今的书写中,以其在跨地缘、区域和全球范围的起伏延展,构成一种引人瞩目又难以用既定话语加以评说的独特性。其中,融散文诗歌和历史叙事为一体的作品《我们的扫兴姐妹》(OurSisterKilljoy)(70)Ama Ata Aidoo,Our Sister Killjoy (Edinburgh Gate,Harlow: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1977).Our Sister Killjoy一书1988年首次作为 Longman African Classic 系列出版,1994年首次作为Longman African Writers系列出版。本文中引用的《我们的扫兴姐妹》的内容,均出自1977年版本,不再一一标出。是又一个经典例证。作品中所展现的多重移动的迁徙者/路上人,跨越的已不仅是耶比村庄和海岸角(Oguaa)之间,或加纳乃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分野,更是现代版图上全球范围内被不断重绘的边界。在重重遮蔽中寻找支撑物质生命和实现意义生命的路径,她们跨越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不列颠岛、欧洲大陆、北美大陆、印度次大陆、加勒比地区等被称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大都会与其边缘外围”“南方和北方”(71)本文所用的“大都会及其边缘外围”的概念,指向的是一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的界定规定,以及介于或内含于被其称为“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民族、区域与国别之间的人文关系。参见Jacqui Alexander and Chandra Mohanty,eds.,Feminist Genealogies,Colonial Legacies,Democratic Futures (New York:Routledge,1997),5-8。之间的所有边界,始终以其充满张力的人性意涵,瞩目着、呵护着、珍惜着、警示着包括人类在内的不同物种中的同道生命。“(警醒呵)全世界迁徙的候鸟,/开始时就已稀少的羽毛,/在无休止的长途/跋涉中/还在不断地/飘落/飘落/飘落。”而被不断跨越的这些边界本身,亦由此被重新界定——“迁徙者/路上人”的巨大动能及其动能中的深刻悖论,不仅见证着“地球是平的”这一宣称的遮蔽性,而且由此打开多边多重充满凹凸的世界性视域,移动着、触摸着、感知着有待揭示的无垠天际和广袤人间。
简言之,“阿诺瓦精灵”以不同的形态、韵律、音调、运动,变革性地出现、生活在艾杜的作品中,展现了现代迁徙者在常规定格中的人性裂变和跨越定格的坚韧生成。《我们的扫兴姐妹》中名叫希西(Sissie)的加纳少女跨越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和西方大都会的边界,这些边界的限制是现代全球秩序运行的要义及其规训机制的重心。当希西出现在(当时的)西德——这是战后美国飙升的世界中“以德国为基点的欧洲重建”的布局重心(72)Fred L.Block,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88.,正漫步徜徉于其“溢彩流光”的通衢之时,一位擦肩而过的雅利安妇女指着希西,向手牵着的女儿说:“看,那是一个黑人女孩。”希西由此被边界常规限制并定格。定格中启动的是将多彩人类化约为旧殖民主义机制系统得以延续的规则符号,由此构成的“存在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将人类按“肤色”“种族”的范畴分成的人性等级,及其数百年的支配秩序。由于不接受作为这一等级秩序“活见证”或其等级效力承受人的定格,艾杜笔下的希西,成为使得其支配逻辑脱臼、“存在之链”失效的杠杆,而由此通向人性新生的一种路径。希西“在之后的所有时间里,她都会为自己开始注意到人类肤色差异的那一刻而感到悔恨”。同时,在显性的“纵横交错”(cross-traffic)时空里,洞识其中隐性的“交叉杀伤”(cross-fire),她从此成为现代性大迁徙高架路上的生命导航。“她觉得有某种内在的东西在牵引着她……不管她走到哪里,任何人说的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她知道(人类肤色上的这些差异)从来都不重要。但她也逐渐懂得,有些地方的有些人,永远会在任何差异中看到为他们某种意图所用的借口。”这里的“某种内在的东西”以及它所具有的牵引力量,使希西能够在跨界移动中踩过荆棘,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与地球上历经人性裂变之痛的其他人们得以互通的杠杆,而这杠杆则同时成为希西跨界人生的路径支撑,其跨洲的覆盖幅度和共鸣规模超出了现代散文的地缘边界和书写规则,孕育出诗意萦绕的诗歌的千回百转。如果说《阿诺瓦》的结构是以歌队表演者的争辩式叙述为依托,《我们的扫兴姐妹》里散文与诗歌相遇相融的双重性则成为组织贯穿整部作品的节律,将希西“牵引”为一种移动的人性聚焦,在那里她的迁徙之痛和“全球迁徙的候鸟们”的轨迹相交相叠,并由此揭示出永久迁徙者转而成为现代流变中始终的在场,既是矛盾轨迹,更是变革本身。
这种散文诗歌的双重登场及其互相转换的变革功能在希西与一位巴伐利亚人的相遇中表现得深刻动人。后者是一位当代家庭主妇和母亲,她存在的根据是丈夫和儿子,没有人在意她的名字玛丽雅,直到她遇见了国际非洲青年夏令营中来自加纳的希西。与丘吉尔笔下17世纪的霍斯金/农家主妇/玛格丽特有着某种遥远而又奇异的相似,希西和玛丽雅发现各自处在无言以对而又相互连接的动态定格中,她们的傍晚散步引来的是诧异而又复杂的目光。当最后希西即将离开巴伐利亚、德国,最终离开欧洲时,玛丽雅起得很早,赶到车站送别。当希西被催促着上车时,玛丽雅将手里抓着的一包自己栽种的李子塞到希西手里,这是希西最爱吃的。列车鸣笛了,玛丽雅就立在站台上,只见她“微笑微笑微笑,眼里淌下一颗硕大的泪珠”。希西手捧着李子进入车厢,坐到窗边,转而向站台上玛丽雅看去,感知着这李子和玛丽亚泪水一样的沉。这李子是希西在玛丽雅家作客时的发现,深色有光泽、鲜美且滋养,“不仅因为那美丽的巴伐利亚黑色的土地,而且因为希西自己在那一刻具有的品质:青春/精神的平静/感觉着自由/知晓自己是非凡的珍宝/被爱着”。当列车猛然启动,逐渐加速时,两位女性在移动拉开的距离中停留不动,“互相注视着对方,说不出一句话来”。在一般的故事层面上,这是一个分离的场景;然而就其融合诗歌性和散文性互为张力的意象结构而言,这是一幅跨界连接的动态具象,调动起近代以来曾经是严酷的地缘、语言、历史、族裔等一整个系统性的区隔鸿沟,和超越这一切秩序限制及其严酷边界的人类渴望,成为相互交织的全球史上,置身于深刻差异时空中的迁徙者们之间一次革命性的相遇。作为丘吉尔式“霍斯金/农民妻子”英伦场景的双影变奏,这一艾杜式的跨越洲际的意象时空,犹如一双温柔而坚定的双手,捧住了全球性迁徙者的人生律动与相接相连的渴望,并将这律动与渴望高高举起,成为一种持续展开的视野本身。其中氤氲生成着“牵引”她们穿越区隔的“某种东西”,照亮她们“家园场所”的差异想象空间,指向这想象的具象脉动,她们就是“家园场所”的跨界实存本身。在丘吉尔的场景里,这“某种东西”的脉动与其被“错过”交叠。在《沼地》的结尾,死去的维尔(Val)醒来告诉观众:“我母亲想做一名歌手。这就是为什么她从来不唱歌。”而她母亲梅(May)“实际上就在那边唱着歌”。梅没有看见维尔,维尔没有听见梅。然而,她们都存在着,她们在那里、在人间,她们在舞台现场跨界同在。犹如艾杜的“全球迁徙中的候鸟”,她们身处彼此的在场,她们是跨越彼此区隔的时空。而观众和读者们,是否能从各自所处的差异时空中,看到、认出、听见、遇到这一切呢?
这种跨越现代地缘区隔秩序而强劲相连的人性律动,栖息在20世纪大量被定格为“西方”和“非西方”的想象书写与人生践行中,从文本到舞台,从大街到灵魂,贯穿于被命名为“中心都会及其边缘外围”的各种区域,横跨这一命名构成的两分逻辑及其所有边界,深刻地悬置、改变乃至超越其中数个世纪重复书写的人性建构和秩序等级。本文将两位充满不可化约的历史差异的当代作家,从她们被分类划开的专业领域研讨中邀请出来,在对读中将她们转换为一种批评性的相遇、一组多重时空构成的星座,以求重新思考她们笔下跨越边界的女性形象所承载的连接性律动,探讨以跨界身体的相互萦绕而差异共振的女性在场,衡量运作其间的无言动能,揭示其生命脉动的物质力量及其孕育的人间想象。简言之,她们的运行轨迹不仅构成了长时段意义上的现代性历史特征,同时蕴含着还有待认知的当下变革和作为当下的未来可能。在此,这些穿越边界的女性形象呈现为多重融合的动态图绘,她们被特制的迁徙、全球幅度的流寓,在相互见证中显现、强化并获得回归的活力,指向现代人类对自身状态反复不断的人文叩问,对人性艺术不断叩问的诸般追索。当全球迁徙者面对悖论命运而跨越各自的定格和区隔,向相互之间无限多样的叩问和追索开放,这开放生成的是人世间创造性的源泉,帮助我们汲取、转换甚至超越包括“主体与客体”“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大都会与其边缘外围”“北方和南方”等在内的现代话语观念机制,乃至迄今为止对这一切的想象和想象的边界——关于作为社会性别的女性、关于迁徙、关于困境错综的现代性及其变革的历史驱动和意义形态、关于贯穿其中的人类对家园场所的久远渴望、关于人类的现代艺术和创造中的人性本身。(73)这里提出的“人类的现代艺术”,作为理念和践行交汇的跨界场域,既连接着又深刻地不同于因循的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界定及其自19世纪以来日益本质化自然化的支配逻辑,指向一个还有待认知开拓的跨文化跨文明的人类历史谱系及其想象之域。参见本雅明语:“人类作为物种,在千百万年以前已经抵达了发展的完成;而作为人的属性,还刚刚处于她的起始之端。”Walter Benjamin,“One-Way Street,” in Reflections (New York:Schocken Books,198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