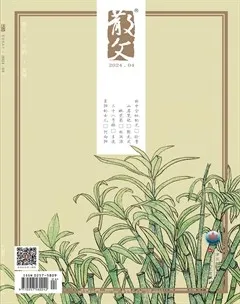老库民
周拥军
一
弥留之际是什么感觉?有说很愉悦的,也有说很痛苦的。老姑父赵忠良弥留时,我们既看不出他多么愉悦,也看不出他有多么痛苦。他神志清醒,一直念念叨叨,说:“如果不是老七,我走了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的日子,都是老七给的。”问他还有什么念想,他说:“只想跟老七再喝顿酒。”
老姑父和老七的感情不是喝酒喝出来的,而是修铁山水库修出来的。那年的一天清晨,广播响了。广播里的声音自称是指挥长,雄浑高亢,一听就知道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指挥长说,这里准备建一座大型水库,水库的名字也想好了,就叫铁山水库。指挥长说,水库一修,很多问题就解决了,灌溉没问题了,饮水没问题了,养殖没问题了,发电也没问题了,一个县的根基就立起来了。指挥长说的这些事很遥远,每一个人都觉得跟自己关系不大,广播里好多事都是说着说着就黄了。但接下来的事就大了,指挥长说,要修水库就得搬迁。水库建成后,得蓄水,一蓄水,村子就淹了,田地也淹了,人必须迁出去,重新安排地方居住、生产。山里人没经过大事,也没怎么出过门,听说要迁到上百公里外的地方去,大家都慌了神。指挥长的话音刚落,工作组就进了门。工作组太能做工作了,没几天,一大批人就一步一回头地搬走了,还有一部分没有动,他们跟工作组有约定,修好大坝再搬。老姑父和老七都在这一部分,算是滞留者。
老七和老姑父的祖上都没有修过水库,他们自己也没修过,他们只跟着指挥长干。指挥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开始指挥长安排他们清污,把一担担污泥从坝基下清出来,远远地运到山上去。这个活儿不难,只是费粮食。指挥长很大度,说,只要活儿干得好,粮食敞开吃。吃完一仓库粮食,污泥清完了。指挥长新的指令是炸石头。坝基的污泥清完了,那里空出来一个洞,得用山上炸好的石头填充。炸石头是个技术活儿,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开凿好炮眼,放好炸药、引线,指挥长下令点火。火点了,接下来是趴下,趴下后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那天的情况有点不对,人是全规规矩矩趴下了,但硬是没听到响。过了几个应该响的时间,老姑父趴不住了,爬起来就往山上跑。老七也跟着爬了起来。老七是猎手,懂火药,隐隐觉得那引线有问题。老姑父快到炮眼处时,老七一個前扑,把老姑父扑在地上,那一瞬间,炮响了。老姑父没事,老七的背上堆满了碎石,在医院整整住了一个月才下床。老七说他从没住过院,这次感谢老姑父,把一辈子的院都住完了。
二
为了迁走库区里的滞留者,指挥长想尽了办法,在遥远的中洲和君山各拦了一条长长的土堤,隔开湖,堤外是一片白茫茫的水,堤内成了一大片垸。垸内兴建了一排排房子。房子是一色的红砖红瓦,一家一通间,通间里又隔成小间。多的三隔,少的两隔。房子旁边就是大片的土地,是一看就知道种什么长什么的沃土。路不仅平,还直,从村里出发,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镇上,从镇上出发,用不了多久就能到达县城。房子建好、土地整好、灌溉排水系统修好,库区滞留者分批参观后,还是下不了决心。
但无论多么舍不得,他们还得迁。有人搬来了大道理,这里不迁,水库不能蓄水,上百万的农田只能望天收,还有几百万人的饮水将来肯定是大问题。还能说什么呢?山里的日子当然好,但这里几千人的日子要影响外面几百万人的日子,滞留者只能牺牲自己,选择外迁。迁并没有花多少时间,一辆辆汽车,拉着他们积攒了多年的那点行李,不费什么劲就到了新的定居地。指挥部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这边有锣有鼓有乐队有横幅,负责送行;那边也有锣有鼓有乐队有横幅,负责迎接。锣鼓声消失了,他们住进了小隔间里,成了新居地的新移民。老七迁到了君山。
太阳下山,垸里就安静了。刈草的、整地的、播种的拖着拽着累透了的身子回了家。家就在垸内的庄稼旁,跨过田垄,就是一排排的房子,一模一样的造型,从外形上看,分不清哪家是哪家。住在这里的居民也从不看房子,只看衣服。悬挂在屋檐下五颜六色的衣服,入眼就知道是谁的,没挂衣服也不要紧,那就一间间数,先数第几排,再数左边的第几间或是右边的第几间,也不难找。
老姑父迁到中洲垸,总搞不清家在第几间,数着数着就忘了,要重新来过,回家,对他来说就像面对一场没有预备的考试。
这里还不能算是一个村子,只是一个居民点。指挥长按先迁先入住的原则安排,后面迁来的,只能哪里有空房子住哪里。住进来,他们才发现,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口音不陌生,人一个都不熟悉,要扯上好一阵才能扯到相互熟悉的人身上去。
这里白天不难打发。白天大家都在忙,没人跟你扯,也听不到咳嗽声。扛一把锄头出门,不到饭点直不起腰,脑袋里除了眼前那块地想不起别的,也不允许想别的。到晚上就麻烦了,眼前看不到地了,也看不到庄稼了,脑海里就空了。脑海里一空,过去的人、过去的事,就约好了似的,拉着扯着挨挨挤挤地来了。老姑父的脑子里来得最多的是老七。梦到老七,必定是在跟老七喝酒。老姑父每年都要一个人背着一壶高粱烧,天黑从中洲出发,走三公里泥巴路,坐六十公里汽车,再走两公里土堤,到君山跟老七喝上一顿酒,第二天一早回来喝过酒后,老姑父和老七又开始重复同样的事。春天在垸子里播种,夏天一边忙垸里的事,一边上堤防汛。晚上没人通知出工也没人通知防汛了,他们就在梦里找熟悉的村庄,找记忆中的一草一木。
三
山上的溪流藏不住事,雨一来,它们总是第一时间发声,笑着叫着,急促地跑。从山脊跑到山腰,从山腰跑到山脚,到山脚时,它们的体量不断增大,大到实在跑不动,就在低洼处停下来稍作休憩。低洼处容量有限,没法为它们提供足够的空间,它们还没有休息够,后面的细流又在催着它们跑,一直跑到新墙河,踊身注入洞庭湖。几千年来,它们一直按照这个路线跑,无论多大的雨,用不了几天,就一泄而尽。但这一次,它们跑不动了。一道大坝拦住了它们的去路。水不管这些,还是按习惯一股劲地往前冲。新修的大坝禁不起这种冲击,没过多久就开裂,裂缝越来越大,水就从裂缝中冲过去,没多久,一座历尽千辛万苦修起来的大坝就垮了,一大截坝体跟着一股汹涌的水跑出去老远。
库区里,水淹过的地方成了滩。房子早就推倒了,没推倒的,房顶不见了,墙壁也不见了,只留下房子的四角,几只蟋蟀在那里忙忙碌碌。房子里的家什早就被搬空了,厨房里还有一些东西,几只残缺的碗里盛满了泥浆。老鼠们又回来了,这里是它们定居的地方,它们没有理由不回来。它们就在那里大大方方地进进出出,也不躲人。七斗丘、五斗丘都在,但田垄不见了,田里密布着沙石,农把式都清楚,这样的田,两三年内是种不出什么东西了。
老姑父得到口信时,库区里的水都退尽了。口信是老七捎来的。接到信,老姑父就动身了。信捎出去,老七也动身了。他们得去看他们的房子和田地。一到老宅基地,老姑父就迈不动步了。村庄已是一片废墟,但那里散发着熟悉的气息,什么都顺眼,包括那些大大方方进进出出的老鼠。这里听不到广播了,也听不到指挥长的声音了,上面离这里远得很,老姑父不想回去了,他准备留下来。老七也打算留下来。
留下来得有田地,得有房。田地好说,山边溪边东开一片西垦一片,夏天收一点秋天收一点,总能对付过去。房子是大问题。老姑父的房子是祖传下来的,到他这一代上百年了。老七的房子是他三十岁时做的,断断续续做了两年。开始是泥匠做,老七打下手,后来泥匠走了,老七接着做。奠基时,老七是地地道道的外行,竣工时,已成为一个中规中矩的泥匠了。多了一门手艺,做房就不在话下了。老七当大工,老姑父打下手,两幢泥砖房两个月就建成了。所有的材料都来自山上。从山上取来碎石,砌成屋基。门窗是现成的,当年拆房时拆下来的门窗还在水线上亲戚家收着。砖就是泥。田里的泥,灌水后,让牛踩成熟泥浆,加入稻草,做成砖坯,晾干后就是上好的砖。
乡亲们也陆陆续续回来了一些。做不起房,就搭一个简陋的帐篷。没有地,就在山上垦荒,红薯、南瓜、冬瓜,随便种点什么。熟悉的咳嗽声又回来了,他们打心眼里觉得还是这个乱糟糟的地方舒坦。他们睡在这片流过汗流过泪甚至流过血的土地上,才能让那些漂泊的梦安静下来。
四
广播里的声音又响了,迁回来的人多了之后,广播也回来了。这回还是修水库。这回说得很具体,修水库就是选两座相邻的、山体坚实的山,在两山间筑一道挡得住一库水的坝,把一些机器放进去,水库就建成了。广播里说,现在修坝的技术完全成熟了,再不会出任何问题了。广播里还说,返迁的还得迁走,但欢迎大家参与修坝。
这次跟上次一样,返迁的一部分迁了。老姑父和老七选择留了下来,他们要看一看,大坝到底要怎样修。他们被编入了扁担组,分配的活计是挑土。土在山上,有人专管取土,扁担组只管挑。从山上取土,把土挑到山下,扁担组有的是劲,这个活儿不难。山上有人喊口号,口号一起,兴奋劲儿就上来了,人人跟着喊起了号子。号子中,山一点点在消失,坝一点点延伸……一把把镐一把把锄生硬地挖下去,山上的碎石和竹筋一点点分开,被碎石和竹筋包裹的泥土分离出来,被一只只及时伸过来的箢箕接走。接走的泥被肩膀挑着,送到远处的坝上。坝上的人开着机器,一段段把土压实。
又出事了,事情出在取土组。取土组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一股劲往一处挖,把一面坡挖成了一张弓。等大家发现危险时,那张弓的上面那段掉了下来,正好压在小伙子的身上。老姑父和老七跑过去时,只见一双脚在动。老姑父和老七拼命刨,刨出上半身时,又一大坨土掉了下来。这回压的是老七。老七挖出来时,一只手已血肉模糊。工地条件差,指挥长找车送到市里的大医院时,那只手變了颜色。老七开始死活不同意截肢,指挥长拍了板,那只手就和老七分开了。老七提了个要求,在水库水线上的山脊建一座坟,把那只手埋在那里。
坝修成后,老姑父再次迁到了中洲,老七也再次迁到了君山。这回用不着工作组来做工作了,没人送,也没人迎,一担行李挑走了全部家当。房子再次交给水库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开垦的田地也交给水库了,水库很快就会蓄水,他们活动的痕迹马上就会被洪水清除。那里将是水的世界。
没了一只手,老七的身体很快就垮了。老七快不行时,他提出和老姑父去铁山看一看他的那只手。
公路旁,水很随意地平铺在公路两侧,很安静,没有奔流,没有汹涌,连涟漪都很少见,它就那样平静地躺在那里,沉默地看着公路上的人和车来来往往。
站在岸边,可以清晰地看见近处的湖床。湖床上有沙丘,沙丘上有一些不知名的水草,水草的叶片一片片尽情地舒展着,在这样安静的水域中,它们有足够的理由享受自由自在舒展四肢的权利。湖底有鱼,近岸的鱼个儿不大,但很活跃,它们三个五个聚在一起,鱼嘴不停地动,兴许是闲聊,话不投机尾巴一摆就散了。它们不知道,它们最平常不过的一举一动牵动了岸上的人久远的记忆,让他们心底波澜起伏。
看了水,在一处浅水边上岸,远远就看到山上的那座普通的坟。这座坟是老姑父参与建的,石碑上写着一行字:铁山水库伤残民工之手。老七仅有的愿望满足了,当晚就安静地走了,在另一个世界,,他终于可以白天安静地看水,晚上酣畅地睡觉,也再没有人来催促他搬家了。
老七不知道,他的名字和断手,都被收进了一本册子。我翻阅过一本铁山水库建设伤残民工名册,记录了谁来自哪里、哪里断了、哪里伤了、断在何时、伤在何地。尽管记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要素,但这本册子,仍再现了一个年代的火热。我们依稀可见成千上万的民工,把块石、泥土筑下去,把钢筋、水泥筑下去,把血汗和断肢筑下去……老姑父的名字在另一本名册里,他们统称为库区移民,记述更加简略,就是姓名、年龄、原住址、现住址、家庭成员。查看两本名册时,档案员在旁边守着。两本名册保存得不是太好,边卷了,页面发黄了,封面也破了,档案员重新包了封面,上面注明:永久。她说,这些册子是这里最重要的资料。
我看过一个同样重要的材料:2022年遭逢百年一遇的大旱,有的地方山上最耐旱的树都干死了,而铁山水库,不仅满足了近两百万人口的饮水需求,还满足了近百万亩农田的灌溉需求。这个四十多年前的工程展现的价值,应该能让那些指挥者和付出过沉重代价的伤残者、外迁者得到最大的安抚,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功臣。
可惜老姑父和老七都不在了。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