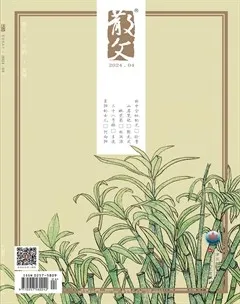稻城记
李春
我是2009年国庆去的稻城,和同事龚垠辉。
对普通游客来说,从迪庆进稻城只有这辆中巴车。需要提前一天买票,每天一趟,朝发夕至,六点出发,六点到达。客运站的售票处又小又旧,像个非法摊点,以至于买票的时候也像是秘密交易。
第二天一早,在黑暗中上了车。坐进去才发现,这辆中巴车像是一辆用废旧零件临时组装起来的车辆,从旧时代开过来,还没有迎来解放,感觉随时会熄火、散架,让人提心吊胆。唯一让人放心的是它的藏族驾驶员,卷毛、黝黑、瘦小,因黑而显得健康,因瘦而显得干练。六点钟,车子准时出发,没多久便出了城。道路越来越窄,整个高原像是只有这条路和这辆车,孤独、寂静。司机注视前方,目光坚定,双手在方向盘上熟练而快速地绕来绕去,像在扯拉面,仿佛双手的肌肉记忆已经代替了大脑反应,开车已经不需要脑袋,这双手已经熟悉了每一道弯或每一个坑。黎明前的高原,天色黑而浓,一种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的感觉,车灯在黑暗中永远是一副电力不足的样子,微弱而局促。道路坑坑洼洼,车子在路上跳来跳去,灯光完全失控,忽上忽下跳个不停,像是乱打的手电筒。车内一片漆黑,坐在车内也像坐在车外。乘客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像是一群偷渡客,在晨曦前的黑暗里,谁也不说话,我身边有人熟睡,像从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车子慢慢驶出云南的边界,虽然敦厚可靠的龚垠辉就在身边,但我还是忽然感到了不安,一种远离家乡的孤独感袭来,我的悔意越发加重:去那个叫作稻城的地方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返回或反悔均为时已晚,高原上除了这辆幽灵般的中巴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是动着的了。
我坐在引擎盖旁边,发动机散发出的热量让人昏昏欲睡。再醒来的时候,天终于亮开了,路上的霜花逐渐退去,阳光慢慢升高,一个从未见过的五彩斑斓的世界就在外面,美得让人疑心重重,恍若置身一个神话世界。车里面有其他人醒来,一声惊叫,继而引发了另外几声惊叫,最后变成满车惊叫,像是灾难来临。我保持着云南人对高原见惯不怪的淡然,但是内心还是被震撼了,这是早上的高原,干净得让人流泪,仿佛除了风从来没有人来过,一片创世之初的大地,从未被人类使用过的大地,像是一个还未被尘世污染的初生的婴儿。我第一次坚信这才是大地最初的样子,这才是大地最初的定义,这才应该是大地的起点或者终点。只有司机面无表情,像在转运一车精神病人。我们眼中的大地在他眼中不过是路途,此时我们眼中的大地是一片美不胜收的高原,而他眼中的大地只不过是一段车程。又走了一段,车外的景象忽然完全变了,光秃秃的树干兀立于山间,像是人工造就的信号塔,钢铁材质,整齐划一,仿佛经历过一次战役,或者是山火、雷击,原始、苍凉,使人不敢贸然迈进,像是停在了几千年前。
刚进稻城县城,正是中秋时节,已有阵阵寒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城边的青杨树,一片金黄,像是单调的高原上突兀出现的一道霞光,陡然闯进了车窗,心也随着一下子沉了下去,另外一个世界出现了。金秋的夕阳把叶子染得比其本身更黄,此刻,颜色就是温度,因为有了这样的颜色,感觉气温也好像升高了。河流干净清澈,像是刚刚诞生的样子,还未曾和人类产生联系,在明信片上,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界,没有一点社会属性。当我们走入其间,感觉整个人都化在了那片黄色里。举起相机,手也高原反应了似的,相机一直失焦,之前传闻的举手即得成为谎言。相机瞬间显得无能,怎么样取景都是片面,从哪里构图都是徒劳,相机在这样的自然面前瞬间沦为一块废铁,科技在这里显得笨拙、可笑、做作和多余,我索性把相机丢在一旁直接用眼睛看。这时,眼睛终于恢复了初始的功能,变成了比相机更值得信任的东西。我躺在厚厚的落叶上面,仰望蓝色的天空,黄色的树梢直插云端,干净得让人动容。我在云南其他的地方也曾见过这样的蓝和黄,但这样的蓝和黄走到一起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异样。
除了牦牛,狗是这个地方的另一个主角。在县城唯一的一条主街上,站满了狗,像是一次有组织的集会,它们还没有学会文明的规则,不避让人也不避让车,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反倒是人和车都要避让着它们。一些狗伏在斑马线上,根本不理会这些画在地上的规则,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规则制定者,这是它们的地盘,斑马线只是后来者无效的涂鸦。这些狗完全不像上海的狗、北京的狗、成都的狗、昆明的狗,那些狗早已变成了文明的附和者、人类的谄媚者,而这里的狗不一样,它们不是人的附庸和玩物,它们像狼,像一颗颗随时会出膛的炮弹,健硕、凶狠、充满杀气,不停地兜着圈子,高举着尾巴,审视每一个外来者。它们不像都市的狗来自软绵绵的交易市场,它们就来自身后的高原,原本应该是狼,被稍加改造之后勉强变成了狗。或许在它们眼里,我们才是狗。我不敢直视它们,生怕它们随时发难,扑了上来。
次日,在稻城近郊的一个村子,我们见到了一名依然沿用石器时代的狩猎方式放牧的少年,他为我们表演了一手绝活儿:用一条细细的皮绳卷起一枚石块,举过头顶甩了几圈,然后嗖地投出,石子在风中飞行,呜呜作响,像是把风打碎了,这是藏族少年的子弹。还有一位名叫卓玛的少女——在这里,叫卓玛的女孩很多——她和母亲背着背箩,从一条山脊上走下来,就像才从天空下来,走在回家的路上。卓玛十三四岁,个子不高。她的脸庞有点脏,像是几天没有洗,但是那双眼睛却干净清澈,像高原的雪水,使人不敢直视,像是从来没有看过东西一样。那是一双我从未见过的眼睛,虽然她家里一片漆黑,但是那双眼睛却在放着光芒,卓玛在哪里,光芒就在哪里。她的父亲则跟她完全不同,看上去年纪不大,却戴着瓶底一般厚的镜片,这在高原极为罕见。他盘腿坐在家门附近的一道围墙边,一锤一刀地刻着玛尼石。虽然已经高度近视,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把藏文的每一处尾巴都刻得纤毫毕现,仿佛他手中的不是刻刀,而是毛笔。我忽然明白他眼睛近视的原因了:他不是用手在刻,而是用眼睛在刻,眼睛甚至比手进入得更深更重。刻好的玛尼石依墙堆积,已经快成一座小山了。他盘腿坐着的姿势,不像是在镌刻,倒像是在祈祷,他一刀一刀地在制造自己的神灵,那些神灵出于他而高于他。他把我们引进家里,一座二层的石头房子。他饿了,将那双沾满灰尘的手,前一刻还与神交握的手,收回到了自己身上,一把一把地往嘴里送着糌粑。虽然胡子上挂满了白色的面粉,但他并不管它,就像他并不管他刻下来的灰尘一样。在红草滩,一位中年大爺坐在门口,说是门口,其实就是一个围墙的缺口,守着没有门的大门,按人收费,每人十元。他攥着薄薄的一沓钞票,靠在椅子上半梦半醒,满足而慵懒。手里的钞票被阳光晒得微微卷起,快要闻见焦煳的味道了。绕过红草滩,在旁边的村子里,一户人家正在给刚收割回来的青稞脱粒。场院中尘灰飞扬,藏族女子穿着筒裙在这场自制的风暴中穿来穿去,从风暴眼中把青稞分离了出来,这是这个家庭一年的口粮。
前天入城的柏油路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些交通提示牌立在公路两旁,成为这片黄昏的天空底下唯一的现代标志,对于进出的人员和车辆来说,这似乎显得十分多余。若不是这些提示牌提示我们,我几乎忘了脚下还有柏油路。柏油路是新修的,崭新而陌生,一看就没有多少车辆跑过。这是一条多么突兀的路啊,与两边的山脉格格不入,仿佛突然闯进来的冒失鬼。如果不是这样一条标志现代化的公路横亘在眼前,我几乎忘了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公路两边的山脉空旷磅礴,与天相接,让人震撼。我们骑着租来的自行车没走多久,就感觉呼吸急促,赶紧打道回府。
第三天,我們到了一座山脚下,跟随我们的向导说,山上有个寺庙,很少有人来,很清静,想必我们会喜欢。我们弃车登山,走进去的时候已是正午,一位年长的僧人正带着几个小僧人举行一场仪式。小僧侣将一碗一碗的五谷渐次往燃烧的经幡上面倾倒,火苗应声毕剥作响,他们口中念念有词,听上去十分悦耳。年长的僧人告诉我们,这是在祈祷风调雨顺。见我们没吃饭,一位小僧人赶紧拿来酥油茶和面点。他还没来得及洗手,拿给我们的碗上印上了他的指纹,但我并不觉得脏,因为那只手刚刚呼唤过风调雨顺,还留有五谷的信息,那是一枚信仰的印章,我毫不犹豫地端起碗,一饮而尽。走下山来,山脚的小河清澈湍急,干净得像是没有厚度,河水虽然很深,但河底一览无遗。
第四天,我们中午直达亚丁,目的地是神山仙乃日。考虑到徒步耗时过长,我们便计划骑马登顶。但由于马匹数量紧张,我们只得徒步而上。一路上尽是融化的雪水流成的小溪,伸手一摸,冰凉透心,头顶的阳光却晒得人头皮发麻。登上山顶冲古寺的时候,已是下午三四点钟,神山仙乃日就在眼前。我们席地而坐,感觉时间都停了下来,大地一片安静,仿佛这里从来没有过声音这种东西。蓝天底下,雪山白得让人心碎,骄阳和白雪如此神奇地共处一地,让人怀疑时空错位。神山峰尖的白雪融化成源源不断的白云,仿佛正在发功,把一缕缕白云向各个方向输送。我感觉在山的内部,一定有用不完的白云,我们沿途所见的白云,一定都是从这里出发的。这一刻,我开始相信神灵的存在。
为了一窥夜里的神山,我们在冲古寺的牛棚里订了两个床位。说是床位,其实是人位,牛棚里的大通铺,牦牛的邻居,一二十号男女和衣混睡。晚上八九点左右,月亮已经挂在雪山上空,天哪,霎时间,雪山仿佛全部换装,一个通体透明的银色世界忽然出现在了眼前。白天草木的绿色和山峦的青色全部褪去,眼下它们变成了雪山的暗部,我准备的所有形容词悉数失效,只知道这是一个可以消灭黑暗的世界。尽管牛粪气味扑鼻,但屋外干净圣洁,宛若一个水晶般的世界,高洁、柔软、清澈而微凉。我眼前的雪山,根本不是我在照片中看到的那种甜腻十足的风光摄影,那种把雄强、壮阔、神圣、原始、初生变成了甜美和腻味的摄影,那种抹杀和泯灭了山的性别和气味的摄影。现在的雪山和白天的雪山仿佛毫不相干,现在的雪山是另外一个,冰清玉洁,让人动容。白天的雪山是父性的,夜晚的雪山是母性的,白天的雪山是在你身边,你在它之外,而现在的雪山,是你在它之中,仿佛哪里都不可以动,一动你就会把它弄脏了,走在里面也必须轻手轻脚,不能影响它。它的静,是另外一种动,一种自我洁净。
没多久,我开始有了高原反应,头痛欲裂,龚老吓坏了,赶紧去找氧气,但是,这种地方哪里有什么氧气罐,氧气是自己的事。不只氧气罐,也没有任何像样的急救设备,龚老怕出意外,急忙带我下山,半路截到两匹下山的马,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一路骑到山下,放弃了这个银色天堂。说来奇怪,一到山下,高原反应自然消失了,刚刚发生的一切,恍若梦境。在住宿的藏民家里,几名东北口音气势豪横的中年男子,一边喝着茅台酒就着高压锅煮开的方便面,一边骂骂咧咧,直言这是什么破地方,来一次后悔一辈子,原来他们误把这里当成瑞士一样的度假胜地了。
我们返回的时候是10月3日,树叶明显地加速飘落,像是计算好了时间。看着一片片不断凋零的树叶,心也不断地一次次下沉,因为掉落的不是树叶,而是时间,还有温度。对比我们进来的时候,树枝已经光秃了许多,肉眼就能看到冬的气息,仿佛只等我们离开,高原的冬天就要迫不及待地来临。
后来,龚老把此行的许多见闻变成了绘画,这批画,即使有人出价不菲,他也一直舍不得出售。在一次画展上,我再次看到了其中的几幅,顿觉安心。看来只有来自原始大地和信仰的信息,才能够永存。
据说,现在的亚丁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修起了豪华的大门,卖起了门票,开通了电瓶车,设施齐全服务到位,它已不是先前的亚丁了,甚至不是我所进入过的那个亚丁了,它成了一个真正的景点,成了那几个东北男子想要的那种旅游目的地,舒适、便捷、现代,迎合了世俗的需求。听说山顶还修起了栈道,轮椅都可以轻松到达雪山跟前,像是逛一个公园。在雪山面前,人人可以举起相机手机对着它一阵猛拍,雪山,也因此不再威严,像被示众。
责任编辑:田静
——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