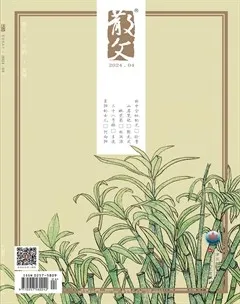三色何多苓
洁尘
2022年3月13日晚八点,何多苓个展“个人简史——学画记”在何多苓美术馆开幕。
这个展览持续两个月,展出何多苓1958年至今的珍贵手稿作品近二百幅,另外还展出有关创作的笔记本以及作曲的曲谱、建筑手稿等,所有内容均系首次面向观众开放。
我仔细地一幅一幅地看。那些从多年前延续至今的线条,那些神情动人的人物,蕴藏着艺术家不变的核心气质,灵气四溢,聚拢又飘散。参观到美术馆三楼自画像那一部分时,看到那些年轻的何多苓,瘦削,敏感,眼神孤独又安然,而何多苓也恰好站在这些画前。我对他说:看这些自画像,可以确定你确实不是一个自恋的人。何多苓笑:好像是,要不是那时找不到模特,我都不得画自己。
何多苓有本访谈录,书名是《天生是个审美的人》。有一次聊天,我们说,下一本书可以叫作《天生是个道家》。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变化,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何多苓一直待在他自己觉得舒服的地方,心无旁骛。
灰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文化史上,何多苓这个显赫的名字跟成都这个城市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何多苓,自然是成都的一张名片,但成都,对于何多苓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采访何多苓之前,我以为我会问他很多问题,关于他与成都,应该有很多问题可以问的。我问:成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说:咦?这个嘛,一下子说不清楚呢。我说:打个比方嘛。他想了想:避风港吧,就是避风港。
我突然发现自己没什么更多的问题可以问了。
我太明白“避风港”这个词对于一个成都人的意义了。可以说,这个词本身即包含了一切。
人生是需要被庇护的,艺术和灵魂是需要被庇护的。在这个朝阳且追求亮锋的时代,有的人不需要那么多的阳光,不需要那么多的注视,需要的是索居,甚至需要的是阴霾,需要一种远离喧嚣、远离喝彩的自在呼吸方式。何多苓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所有灵魂中对孤独、清冷有着需求的人,都会明白这种庇护的意义。
这就是所谓的“阴翳之美”。
2010年平安夜,在成都的高地艺术村落看画展,看到一幅名为《成都灰》的作品。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成都灰,优雅、轻盈、温暖且忧伤;这种灰色,往往是头天晚上的曲终人散和意兴阑珊之后,第二天拉开窗帘可以看到的;而头天晚上,聚之尽兴和散之落寞,那种滋味一路从酒杯洒向街头,然后带回家中,伴随着夜风,不冷,微凉,人生的幽微都在其中。
灰,不是黑和白的混合,而是一种独立的色彩。不是黑往后退一点,也不是白往前进一步。
灰,自成一格,自给自足。
灰是成都最常见的天色,也是成都这个城市的味道。在灰的味道中,人是不会胡乱飘起来的,总是背负着生命本身的重量,也带着日子里细微的点滴欢愉。在何多苓的画里,那种透明的轻盈的灰就是避风港。避的是怎样的风雨?这些风雨,是过分的欲望,是计较、争竞,是一颗胜负心。
我问何多苓,除了长时间居住的成都以外,他曾经居住过的纽约,对于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他说:纽约?纽约好啊。我问好在哪里。何多苓说:因为它很像成都,既然很像成都,所以我就离开它回到成都。
诗人杨子说他认为成都的文化是全中国唯一没有外省气息的文化,完全自成一体并有聚焦效果。我理解杨子所谓的“外省气息”,是某种欲与首都或中心比肩后产生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成都文化的确是自成一体,它是偏安的,同时又是傲然于偏安的。成都文化的根本是精致的颓废的个人主义,是享乐和冥想的混合,是大悲观和现世乐观的结合体;在此基础上,它会不可避免地回避凌空蹈虚和宏大叙事,回归到日常之中。所以,成都文化让人非常放松,放松到与本性一致的地步。这个城市仿佛从两千多年的道教传统中导出了一股活水,引导着滋养着居住其中的人不自觉地追求自在和放下的人生。
生长于斯扎根于斯,成都文化最优秀的一部分在何多苓身上体现得格外充分,那就是:源于充分自信地有意识地躲避潮流,与流行保持距离。用何多苓自己的话说,“本能使我对潮流和时尚有天生的免疫力”。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到現在,何多苓四十余年间的作品,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主体画面的孤独感一如既往。何多苓说:“我的作品表现个体而非群体的人……我的画上几乎不会出现(或保留住)一人以上的形体。”是的,他的画面中总是很少出现两个人以上,几乎总是独自一人,或在一个建筑空间里,或在某个自然场景里。人物的面部表情或者姿势总是忧伤的。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何多苓画过笑容。而且,他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女人,形单影只的女人,从婴儿(中性)到性别特征显著的成年女性,一概的神态寂寞,与这个世界有着强烈的疏离感。近年何多苓的作品中,让我相当感动的是画他母亲的一幅画。这幅画挂在他蓝顶艺术村的画室里。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忧伤且泰然地坐在椅子上,椅子前是一棵桃花。何多苓说,这是他在母亲去世前画的。从这幅画回溯,何多苓通过这么多关于女性的作品,完成了生命由始而终、由盛到衰的一种独特的叙事,其间的滋味,在我看来,是安静的、宿命的,也是自由的、神性的。
哀伤的,凝练的,敏感的,去时尚的,大宇宙观的,神性的,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在这些方面,何多苓跟安德鲁·怀斯如出一辙。这一点,也跟成都最精华的那一部分重叠。2008年,以《重返克里斯蒂娜的世界》这幅作品,何多苓向怀斯庄重地鞠了一躬。
世界与内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世界就是内心,内心就是世界。逐渐地,何多苓开始离开以高超技巧作底子的精细笔触,在依旧写实的基础上逐渐获得了自己写意的风格。近年,面对画室的花园,何多苓画了大量的“杂花”系列写生,笔墨灵动流淌,难以模仿也难以复制。但究其根底,他还是写实的,他绘写内心,绘写由自己的视线看到的世界,其他的东西,与他无关。
内行说,在中国当代,像何多苓这样有着高超技艺的画家很少了。我看过一个采访,记者问何多苓用不用枪手,他说:“我怎么会用枪手?画画最愉快就在于那一笔又一笔的过程,我怎么舍得让别人去享受这个过程!”
欧阳江河在他的文章里写道:
对何多苓来讲,技艺就是思想。他的创造力,他的自我挑战,他的刺激和快乐,全都来自他精湛的绘画技艺……当代艺术潮流断然认定,画得好本身就是问题之所在。所以全世界的画家们都忙着将自己的手艺抵押出去,免得它影响作品的当代性、观念性、大众性。所以,现在全世界数十万个在世艺术家中,真正称得上怀有一身技艺的画家已是屈指可数,我能数得出来的不超过二十人。活在这二十人当中,何多苓身怀幽灵般的绝技,像一个传说中的大师那样作画,愉快而镇定,言谈举止中带点老顽童的自嘲和忽悠,带点外星来客的超然,我想,他才不在乎我们是不是把他列入当代艺术的行列呢!
工匠式的执着精细,隐士般的冷静旁观,道家式的闲逸散淡。这段出自老友的文字,将何多苓描摹得很到位很传神。
白
2018年大年初一,一些老朋友在我家团年。酒足饭饱之后大家开始神说,我讲“拿手”的星座和血型,何多苓照例对我的“伪科学”报以温和的嗤之以鼻:“我金牛A型,上升……不,老子就到金牛,不上升。”
哄堂大笑。真是固执啊,固执到坚决不上升。
我跟别人说过何多苓是中国当代的达·芬奇,但没有对他本人说过,因为以他的低调和谦逊会立马反驳。他自然是中国技艺最好的油画家之一,所谓达·芬奇之喻,则是因为在本行的顶尖之外,何多苓还在各种领域里有着广博且深入的涉猎和钻研,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有很多“耍法”——他是科学爱好者,是兵器知识专家,是不光喜欢听大量听,还喜欢阅读总谱且会作曲的古典音乐发烧友,是作品数量不多但语感精妙的写作者,是资深诗歌爱好者,是喜欢高高跃起凌厉劈杀的羽毛球高手……他还有一个很来劲很认真的耍法——建筑设计。位于成都蓝顶艺术村的何多苓美术馆,一座通体雪白的建筑,就是他的设计代表作。
何多苓在建筑上的耍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知道他多年来精读各种建筑专著,对世界上诸多建筑大师的作品做过深入钻研。行迹所到之处,建筑是他最喜欢的风景,也是他反复观摩的对象。曾经有一年,他还和家人一起做了一趟“日本建筑之旅”,在日本全境追看安藤忠雄、妹岛和世、西泽立卫、隈研吾等建筑大师的作品。
凡事专注投入,必有恋慕之果跟随其后。何多苓热爱建筑,进而跃跃欲试着手创作,然后就有了以通体白色的何多苓美术馆为代表的一系列建筑设计作品。
紫
跟灰一样,紫也是独立的。在我的城市色谱里,成都灰和成都紫是并存的,前者是白天,后者是夜晚。关于成都紫,我曾经这样写过——
成都是什么颜色的?成都是蜀锦的故乡,所以有“锦城”“锦官城”的别称,如果抓住这个“锦”的概念来说,那就是繁复和艳丽的,但这种繁复和艳丽的色度并不高,它不是原色的呈现,而是一种间色,它混合了儒与道、暖与冷、明亮和暗淡、乐观和颓废、入世和出世、感性和智性。而且,它具有明显的阴柔气息。这种颜色,就说它是紫色吧。在光谱中,色相的排序是这样的:红、橙红、黄橙、黄、黄绿、绿、绿蓝、蓝绿、蓝、蓝紫、紫。从暖色入手,一点点掺,一点点兑,最后有了紫。这很像成都。
在画面上几乎从不表现笑容的何多苓,总是笑嘻嘻地跟朋友在一起。
认识何多苓三十年了。从最初有点怯怯地叫他“何老师”,到后来跟所有的朋友一样叫他“何多”。他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这话真没错。
关于跟“何多”的第一次见面,我一直记不清楚两个场景的前后次序。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情。后来我对“何多”说早年刚认识他的时候有点怕他,他问为什么。我说:感觉很严肃傲慢。他说:不是严肃傲慢,一是见生人有点不自然,二是那时可能有点刻(成都话,“装”的意思)。我说:那时,领子都是竖起来的。他说:啊?真的啊?那就刻翻山了哦。
其实,所谓领子竖起来,是我逗他的。这么多年来,“何多”顶着一头自然卷永远穿休闲装出入成都文化圈。2010年年底,首届新星星艺术节在成都举行,我作为主办方“艺术场”的朋友,专门提醒他们不要在颁奖晚宴的请柬上印上“请着正装出席”。在成都文化艺术圈,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哪个艺术家和诗人作家会专门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去参加一个活动。我倒不是认为这个习惯值得表扬,其实它甚至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被责备一下:实在是有点随意散漫了。但这在成都文化可能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在成都人看来,日常舒适的着装,就是最好的。
“何多”就是这样,一直保持着日常舒适的状态。泡吧时,给他点啤酒就行了,他爱喝;请他吃火锅的时候,记得多点黄喉就是了,其他菜都可以省略;周围写作的朋友都知道,新书出版了要送他一本,他喜欢看,而且一定是很认真地看;和他聊天,科学问题是他最喜欢讨论的,因为他爱好科学;和他聊交响乐一定要小心,因为他的音乐素养很高;他不用电脑,手机短信就是他的信箱,但他居然会用复杂的作曲软件;他在三圣乡画室里有一个“小型影院”,有很棒的设备,经常和朋友们在那里一起看电影……中年以后的“何多”随和好玩,早年那种带有欧洲贵族式的酷和清冷味道已经褪去,他放松、自在,将自己的本性和这个城市彻底地融合在一起。
“何多”在夏天的衣着最有意思。有不少他的学生送他T恤,那些年轻人自作的T恤,上面都有很有趣甚至很无厘头的图案,他喜滋滋地穿上,脚踏一双按他的话说“舒服惨了”的凉鞋,配上那头越来越卷的头发和哈哈大笑,喜感简直要爆棚。有一次夏天的画展,“何多”T恤加中裤来了,我问:你的裤脚咋个有两个蝴蝶结呢?女式的哇?“何多”一惊:不得哦,学生送的,整我的啊?转过身看后面的裤脚,果然。
我想来想去找不到更合适的人物,只能用一个过于滥俗的形象来比喻他了——就像老顽童周伯通,武功盖世,又始终拥有一颗赤子之心。
很多时候,我还是能够看到“何多”背后的那个何多苓。他依然潇洒清高,内心有一种固执的驕傲,永远散发着一种忧伤孤独的气息。这种气息,在白夜酒吧的深夜他举起酒杯跟朋友轻碰一下时会渗出来,在他独自一人出现在街角时可以领略,在他的作品里面也始终萦绕。有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一顿美味的晚饭后回他的画室看电影的路上,“何多”说,有一部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新片,他演一个无奈的老爸爸。这片子挺不错,他已经看过了,还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次。那晚的月亮很大很亮,天光和水光交错,荷花的香气若隐若现。那个时候,“何多”沉默地走在我的前面,不时地拂开路边垂到人眼前的柳枝。看着他的背影,我不知为何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大师!是一个注定留名青史、被一代又一代人仰慕的艺术大师!而现在,我们正和他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并和他共同热爱着这个城市,一起度过了那么多愉快的时光。
责任编辑:施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