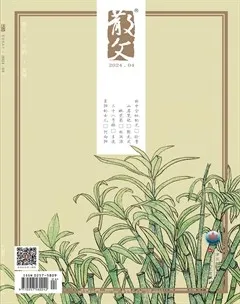我家江水初发源
向以鲜
我一直认为,长江固然伟大,但设若离开了三个蜀中诗人的歌唱,恐怕也将暗淡失色。这三个蜀人,是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东坡和明代的杨慎。虽然为黄河唱出过“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绝响,但最令李白动容和迷恋的还是长江。李白故乡四川江油的涪江,就是属于长江水系嘉陵江的支流。长江,无论是倒映着半轮“峨眉山月”的上游水系(平羌江水为岷江支流),还是“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中游,抑或是“孤帆远影碧空尽”的下游,都让李白为之倾注了全部的爱和赞美。如果说唐代的李白关注的是长江的速度之美,那么宋代苏东坡的长江,则呈现出一片时空交错的壮丽。李白提升了长江文化的流速,苏东坡则拓宽了长江历史的广度和深度。而以“滚滚长江东逝水”广为世人所知的明代的成都新都人杨慎,则在李白和苏东坡的长江之上,又写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长江,在速度与空间的背景中,织入了更多的尘世幻灭感。
从现代地理学意义上来看,长江并不直接发源于岷江,而是滥觞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峰西南侧。但在古代中国人的认知中,尤其是蜀人的地理坐标中,岷江就是长江的发源地。所以苏东坡才向世人宣称长江源头的岷江水是“我家”的江水,来源于“我家江水”的长江,天生就是我家的——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苏东坡在诗词中也多次写及岷江水,比如《南乡子·春情》:
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
春雨暗阳台,乱洒歌楼湿粉腮。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开。
按照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的解释,黄河之南的昆仑,自非岷山莫属。传说中的昆仑,就是中国西部的岷山山脉,并且主要展现于蜀地。所谓“昆仑”“祁连”,其实是“岷”的急读。有人认为“昆仑”语出古羌语,意即鸟屋,“昆”与大鸟之关系,在《庄子》“鲲鹏”一词中还能找到残存。古蜀人的先民主要由古羌人构成,如果说“昆仑”之称来自古羌语,那么为昆仑最先命名的,可能就是古蜀人。
苏东坡一生三次出蜀,最重要的两次均发生于青年时代。北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春天,二十一岁的青年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一起赴汴京赶考,走的是陆路,从眉山到成都然后北上,通过古老的金牛道和褒斜道进入关中,经过两个月跋涉,五月到达目的地东京汴梁。
嘉祐二年(1057)正月,初春的寒风中,礼部考试拉开了序幕。主考官为欧阳修,诗人梅尧臣(圣俞)担任详定官。古文大家欧阳修喜欢质朴的经世致用之论,坚决反对空谈、奢谈和妄谈,他开出的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南宋楊万里《诚斋诗话》记载:
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巩)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这个故事应该是可信的,非常符合欧阳修和苏东坡的风格。学生敢于杜撰典故,老师勇于认同,这对师生之遇,可谓旷世难逢。四月初八,苏东坡兄弟顺利通过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六天之后被钦点为当朝进士。
不久,苏东坡丁母程氏之忧,三苏一同返回眉山老家,从嘉祐二年六月一直待到嘉祐四年(1059)初冬的十月才算期满。朝廷的诏命早已多次下达,三人这次决定走水路回京——这是苏东坡人生的第二次出蜀——正是此次经历,让他初次亲近了真正的长江。虽然他就生活于岷江支流玻璃江边,但那毕竟不是真正的长江。
从苏洵的出蜀路线安排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父亲的深思:一次走陆路,历蜀道之古老与艰险;一次走水路,览长江沿途之雄奇与幽深。父子三人从眉山直奔嘉州(乐山),一直向东经泸州、渝州、涪州、忠州、夔州……完全就是当年李白和杜甫出蜀的线路。出三峡后,再坐船东行六七百里水路,至湖北荆州上岸,还要向北陆行一千多里,于嘉祐五年(1060)二月中旬抵达汴梁。算起来,此次出蜀,花在路上的时间差不多将近八个月(仅水上就漂泊了两个月)。八个月,对于一路游吟的父子三人来说,不是太漫长而是太短暂,有说不尽的欢乐和秘密,有望不尽的波浪和云涛,还有下不完的棋局。
上岸之后,苏轼将父子三人吟和诗作一百篇结集为《南行集》,又称《江行唱和集》,并在江陵(荆州)驿舍中写下《〈南行前集〉叙》。这是一篇研究青春时代苏东坡的重要文献,其中表达了苏轼对于诗歌写作最质朴的看法: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峦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
现今流传的《南行集》中,苏轼作品最多,达四十首。即便扣去疑为伪作的《咏怪石》和《送宋君用游辇下》,也仍然是三人中写得最多的。《南行集》中,苏轼初现诗歌锋芒,比如《新滩》,就写得非常传神:
扁舟转山曲,未至已先惊。
白浪横江起,槎牙似雪城。
番番従高来,一一投涧坑。
大鱼不能上,暴鬣滩下横。
小鱼散复合,瀺灂如遭烹。
鸬鹚不敢下,飞过两翅轻。
白鹭夸瘦捷,插脚还欹倾。
区区舟上人,薄技安敢呈。
只应滩头庙,赖此牛酒盈。
苏轼认为,诗歌写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人类的心灵吟出无数诗歌作品,有如山河大地涌现出云雾,百草万树结出花朵与果实,都是自然甚至是必然的过程,其原因在于:“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显然,父亲苏洵的深思之旅得到了两个儿子的热烈回应:“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苏轼的认识不仅来源于对长江之美的直接感受,也来自于父亲苏洵的教诲。苏洵曾为其二哥苏涣的名字写过一篇解析文章《仲兄字文甫说》,以一个雄辩家的口吻,惟妙惟肖地描绘和讨论风与水的各种形态与关联。也是苏洵以文字的方式,再一次向世人也向两个儿子呈现长江的变幻莫测——
亲爱的二哥,你可曾见过水与风相互作用的情形?水啊,它们自然而然地流淌着,只有停止才会显得深沉。有风浪平静的时候,有汪洋涨满河岸的时候,也有不断波动前行的时候。风激起了水,嗖嗖的风声来自虚空,并迅速吹遍天下四方。我们看不见风的形状,它们飘摇着由远而近。风离开我们时,没有人能找到它留下的痕迹,但是水能够显现风的存在。比如,风与水相遇于巨大的空间中,水浪曲折,水波蜿蜒,平静里相互推动包容,发怒时相互冲撞冒犯,舒缓如云朵,收敛似鱼鳞,急速如奔马,缓慢胜远方。风与水礼让着,旋转着,回避着,对视着,彼此间谁也不敢轻易行动。繁复如绉纱,凌乱如大雾,缤缤纷纷的样子,或停滞或波起,放眼望去百里如一。急风激流来到沧海,那又是另一种场面:壮阔的波澜澎湃汹涌,愤怒的吼叫,一声高过一声,纵横的水波相互交错,在苍穹之下恣肆,在无边的大海动荡、横流、回旋。时而像旋转的车轮,时而如环绕的绸带,时而似矗直的烽烟,时而就是奔流的火苗、飞动的白鹭、跳跃的鲤鱼。它们的形状怪异、姿态无方,展现出风和水最神奇的景象。所以,《易经》卦辞中说:“风行水上即为涣。”这也是天下最美妙的文章啊!
老苏为文果然老辣!从此,江水的形态被植入苏东坡的生命,风中的波涛纹理,成为苏东坡理想中的诗歌与文章的化身。所以,他才会在《文说》中颇有些自负地说: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长江带给苏轼无限的梦想和未来图景,也带给他无尽的失望、绝望甚至死亡。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湖州太守苏轼被来自御史台的皇甫遵等人押解至汴京,等待他的是沉冤和百尺深井般的牢狱。在扬州长江边的月夜中,望着滚滚波涛,苏轼觉得人生太虚无太渺小,不如纵身而去,图个痛快。但是,我们的苏东坡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垮的。在曹皇后和众人的努力下,历经一百三十天囚禁,苏轼走出乌台诗案的黑暗牢笼。
走出御史台大狱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独自一人,在差役的押送下,踏上贬往黄州的路途,家人则交给苏辙临时照管,随后再相机护送过去。走了一个月,东坡一行于二月一日到达位于汉口下游的偏僻小城黄州。
由于戴罪之身不允许住官舍,苏轼只能暂时借住在一处名叫定惠院的小庙,到了夏天,才在老友鄂州太守朱寿昌帮助下,住进条件相对好一点的临皋亭。四壁透风的临皋亭建在长江边上,是一座废弃的水边驿站。此时,弟弟也将苏轼一家老小二十几口人带到了黄州。不久,在黄州郡城东门外一里许的山坡上,苏轼找到一处废置的校场旧地,约有五十来亩,杂草丛生,蛇鼠出没,还有一口塌陷的暗井,隐隐可以听到流水声。苏轼称此地为“东坡”,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名号——从此,“东坡”成了中国文学史(包括文化史)上最璀璨的字眼之一。
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即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谪居黄州时的长江边。这是到达黄州的第三个年头,苏东坡四十五岁。这首词与熙宁九年(1076)中秋写于山东密州(现在的诸城)的那首《水调歌头》堪称苏词中的双璧:前者以俯瞰历史的角度,洞察古往今来;后者则仰望玉宇中的明月,与阴晴圆缺达成人生的和解。二者即使被放入整个词史中,也仍是难以匹敌的绝唱。苏东坡将人生之痛、时代之伤融进浩渺的历史时空,将英雄情结照进如梦的人生,苍凉之极亦悲壮之至——那卷起的千堆白雪中,除了拍岸的惊涛,还有诗人早生的无数华发。
黄州城西北的长江边上,耸立着一块巨大的火红石壁。远远望去,像一只巨人的红色鼻子正细嗅波涛的气味。当地人因形而名,叫它赤鼻矶,也叫赤壁。这个赤壁并不是真正的古战场赤壁,苏东坡自己在词中也并未一口咬定——“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然而纵然不是三国古战场,也一样可以借之抒写胸中块垒。赤壁也好,赤鼻也罢,只是引发诗人想象的诱因而已。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记述了一段苏轼的话,可与此词互读:
黄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败归,由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蒹葭,若使纵火,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来,因以小舟载酒,饮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我非常喜欢苏东坡在黄州时的另一首有关长江的词——《临江仙·夜归临皋》。与雪堂的朋友分别后,踏着月色照耀的黄泥板路,苏轼踉踉跄跄地赶往临皋亭。一路走走停停,来至家门时,已是三更时分。敲几下门,童仆早就睡得死一样沉,怕惊醒家人,苏东坡干脆就站在长江边,欣赏起夜色中的江景。浩荡的江水无止息地东流,几个渔蛮子打着明明灭灭的红灯笼还在捕鱼。如若此时漂来一叶扁舟,能够随之而逝,抛却人间一切恩怨与荣辱,去到无人知道也无人能够找得到的地方,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该有多好!这样想着,苏东坡不觉轻声对着波涛吟道——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作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徐太守耳边。人们竞相传说,钦犯苏轼在月夜中拿舟长啸而去。徐太守顿感此事非同小可,非得赶到临皋亭亲自看个究竟才能放心。当他终于赶到临皋亭时,一晚没有休息好的东坡终于回到家中,此刻鼾音如雷,睡得正香。
對他来说,睡在长江之上,比在任何地方都要安稳。
责任编辑:施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