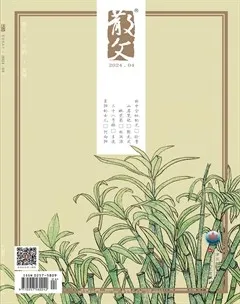山门·春分
琬琦
等待
如果需要等待,我们总愿意选择一个标志物。或者一只邮筒边上,或者一盏路灯底下,或者某个银行门口。那日,我在山门外等记者,选的就是一株木棉树下。不过,那一树在半空中燃烧的红花没有得到细致的欣赏,地上零星的落花也无人弯腰俯看。赏花这件事,需要闲适的心情,等待中的我显然并不具备。我只顾着翘首看一辆辆疾驰而来的小车,仔细辨认它们的颜色、车型和车牌号码,然后一次次失望。时间缓慢流过,一头名为“焦虑”的小兽似乎正在慢慢长大。
“唉!”几乎就在我叹息的同时,一朵花从空中跌落,嘭的一声重重地砸在地上。我被吓了一跳,忍不住靠前两步,蹲下身去,捡起那朵落花。这硕大的木棉花从那么高的地方坠下,竟然毫发无损。这是一朵简单的花,两指宽的红色花瓣,绿色花萼。几乎所有的落花都能唤起人们心里的叹惋和怜惜,但木棉花显然不是。我不止一次看到人们捡它,放在菜篮子里,红艳艳的一片。也有人用竹签子把它串起来,串满了,弯成一圈提在手里,好像提一串活蹦乱跳的鱼。人们说,这木棉花可以炒着吃、煲着吃,能祛除身体的湿气。在南方人眼里,“湿气”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概念,人的一生,就是与体内各种“湿气”斗争的一生。
又一朵花嘭地落下,溅起不小的回声。现在,我有两朵木棉花了。它们刚离开枝头,就像鱼刚离开水,新鲜得仍然可以听到浪花的奔流。我端详这两朵花,它们一模一样,一朵是另一朵的镜像,像是从同一个母体里同时出生的孪生子。它们虽然掉落,但体内依然有生命的力量,不会一下子就萎谢掉。我该拿它们怎么办呢?好像每一次鲜花在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在我心里萌发:该拿它们怎么办呢?不管如何小心妥善地呵护,还是阻止不了一朵花的衰败、枯萎。但我也不想纵容自己往这个方向继续想下去,那是林黛玉的方向,不是我的。
虚构的猴子
“禁止投喂、挑逗猴子,以防被抓伤。”
当记者把这句话一字一字地念出来时,我们都笑出了声。记者说:“这山上还有猴子吗?”领导说:“有,应该有好几只。”导游说:“可能只有一只了。”
为了一只猴子郑重其事地竖立一块警示牌,这件事显得有点好笑。当然,作为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我是见过这山里的猴群的。那应该是二十年前了,景区刚开发,引进了一群猴子。关在一个并不严密的大铁笼里,游人可以隔着笼子给它们投食。我曾经把花生放在手里,摊开手掌过去,猴子便伸出爪子取食,彼此间完成一次愉快的互动。但就有那种促狭的游人,手里攥着东西递过去,等猴子要取的时候,却又缩回来。如此三番,猴子便发怒了,瞅准时机,爪子闪电般出击,抓伤了游人。此类事件一多,猴子就成了顽劣的代名词,大家只是远远地看着,互相扮鬼脸、怪叫。后来不知是铁笼锈坏还是疏于管理,猴子走失了。偶尔会见到一只,端坐在高高的树上,警惕地辨认着树下的过客,像在寻人,又像在等待。
有好多年我没在此山中见过猴子了。这山脉据说方圆三十七平方公里,以丹霞地貌为主,赭红色的山峰有各种陡峭,亦有苍莽林木。几只猴子隐入山林,如同鱼被放归茫茫大海,要再寻找,恐怕是很困难的事情了。
如果猴子也像人一样会怀旧,也许会回到铁笼附近,缅怀从前的日子。依稀记得当年被我喂过的那只猴子,清亮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不安,抬眼看人时,额头上就浮现出几道抬头纹。那时我很年轻,未为人母,尤其爱看猴妈妈给小猴子捉虱子的样子。有时它赶着孩子在笼子里玩,有时让孩子吊在自己的脖子上,抓着笼子顶上的铁条荡来荡去。那小猴子又胆小又爱玩,常常被吓得吱吱地叫。导游提到的仅剩的那只猴子,是不是我喂过的那只?还是那只总是凶着一张脸的猴王?它有很强的攻击性,几乎把所有的男游客都视为潜在的敌人,看见谁都龇牙咧嘴的。据说也是它最先逃出笼子的。那其他的猴子都去哪儿了呢?是在山林里潇洒快活,还是被人捕捉去了?那也是一个小型的家国啊,也会有相亲相爱或者互相倾轧。如今,卻消失得干干净净。
二十年前的事情,想起来令人恍惚。每次跟人说喂猴子的经历,别人都不相信,以为是我编造出来的。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从警示牌下绕行,沿着人工步道往山上的寺庙走时,我对于猴子的存在,也产生了怀疑。也许我们经历过的一切,都是虚构的。那只虚构出来的猴子,如今正在我想象的树林里荡秋千。黑夜来临,它也将栖身于我想象中的山洞。想象,如同一束微弱的光,其所到处,即使是最黑暗的地方,也会被照亮。
瓦片
瓦片的形状如同有弧度的书页,总是以一种整齐排列的方式出现。小时候,我去看过一个制作瓦片的作坊,竹子加油毡布搭盖的简易棚子,里面垒着一墙墙的泥瓦。一个人将泥坯子灌到一个圆形模具里,然后用工具使之旋转起来,多余的泥便被甩出来。脱去模具后,地上就有了一个圆筒形的瓦坯。瓦坯晾干后,那人用一柄木槌轻轻地敲击它,圆筒就裂成四块泥坯了。这泥坯还得经过高温烧制,才能成为一片真正的瓦。
去所有的古镇旅游,黛瓦粉墙几乎都是不可缺少的元素。那些瓦片一页页排列成屋顶,屋顶便也成了一本向下摊开的书。每一本书,都记载着一幢房子的历史变迁,记载着房子里的悲欢离合。这样一想,瓦片作为记忆的鳞片,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对象。
瓦片可以算是最早进入我的视野的事物之一。当我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张开眼睛就能看见屋顶上的瓦片。当我尚未认识它的时候,就已经熟悉了它。它们通过巧妙的堆叠,起到了遮风挡雨的效果。那时我还看不清瓦的全貌,如今想来,在屋子里往上看,大梁和桁条构成了骨架,而瓦片则是一环环的肌肉——我们就像是在一条鲸鱼的内部生活着,点煤油灯,讲飘忽的故事。不过,直到现在,我也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鲸鱼,一切仍然只是基于想象。
瓦片作为书页的想象,似乎在山中的寺庙落到了实处。在一间耳房里,我看到了一垛黄色的瓦。那瓦片微微隆起的一面,用毛笔写着一些字。我弯下腰去读,佛光普照:某某某阖家,身体健康、学业有成、万事如意、大吉大利。再读几片,内容都差不多。字写得一般,墨水没有外溢,几乎都被瓦片妥善地吸收了。在这样的“书页”上,看不到属于毛笔书法的那种笔锋、枯笔之类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字就是字,简单、朴素,只为了表达字面意思。
我忍不住问住持:“这些瓦片是用来干吗的?”
“这是祈福瓦片,准备用来替换大殿上的旧瓦。”
“就这么直接换上吗?”
“不,外面还要封一层釉。”
我们一路走入寺庙,大殿、偏殿、回廊。这山有很多洞室,各种殿堂依洞室而建,可以节省很多砖瓦用料。抬眼看屋顶,那瓦片的排列跟我们家老屋的几乎一样。不同的是,老屋的瓦片是黑色的,这里的瓦片是金黄色的,与整个殿堂里的庄严、肃穆相适宜。
每一片瓦上,那层金黄色的釉质后面,就封著那些质朴的愿望。每日,殿堂里佛号声声,香烟缭绕。远道而来的香客在蒲团上跪下、合十,喃喃祝祷。在瓦片上写着的那些名字和愿望,就这样日日被这些虔诚和慈悲熏陶着。
写字
当住持写下“观自在”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笔在微微颤抖。他并不自在,我想。但我不知道,让他感觉不自在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是因为领导、记者,或者,我?我并不懂书法,但领导和记者都是书法爱好者,住持也是。三个人在寺庙的画室里讨论要写点什么。住持忙着把一些感觉可能碍事的东西从桌子上清理掉,从另一个房间取来两种不同质地的宣纸,在桌子上铺开,拧开墨水瓶,选择合适的毛笔。
第一个写字的人是记者。他显然对“现场挥毫”这件事了然于胸,拿起一杆笔,那笔头如同木棉花一般大小。他看了看笔,又略微打量了一下纸张,便饱蘸了浓墨,在纸上果断又从容地写了一个“禅”字。嗯,在佛门之地,写这个字甚是相宜。大家都喝一声彩。
住持是第二个写的。我这个不懂书法的人都能看出,他写的字并不算好,起码与墙壁上挂着的、据说是他临摹的《兰亭序》相去甚远。也许他只是有点紧张。一个紧张的人,恐怕此刻是无法“观自在”的。不过,出家人不是应该很淡定的吗?在写字的过程中,他似乎总是心神不宁。也许是因为手机不停地振动,他写几笔,又把它摁掉。三个大字终于落到纸上,他脸上流露出一点赧然,试图用笔去做一些修补。这时,手机又振动,他拿起来说:“是谁一直在找我?”
他没有接听电话,但是看了几个信息。并且将一些语音信息外放出来。其中有一段是:你得派人来看看,这里倒了一棵树,把路拦住了。
我有点哑然失笑。看来,当了住持的出家人也不清闲呀。上面来了领导视察,他得接待;寺庙的瓦片坏了,他得安排更换;就连一棵树倒了,他也得处理。一棵在春天倒下的树,可比木棉花坠落的声势要大得多。那会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呢?也许是老朽了很久吧,也许它想着撑过去年冬天就好,却没有想到自己终究撑不过春天。昨天半夜,我曾被窗外的雷电和风雨惊醒,也许是一道闪电劈中了一棵风华正茂的树呢?
就在我走神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一支细笔,准备落款。那棵倒下的树似乎就横亘在纸上,他几经犹豫竟落不下笔。导游在旁边小声地提示:“今天是春分。”他转过脸,有点茫然地问:“哪个分?”
我忍不住在心里轻轻地笑了,看着他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落款:癸卯年春分。我认出了,他的字体与写在瓦片上的那些朴实的字体一模一样。我想,一个出家人是如何感悟春天的呢?当写下“春分”的时候,他的心里,会有繁花盛开吗?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