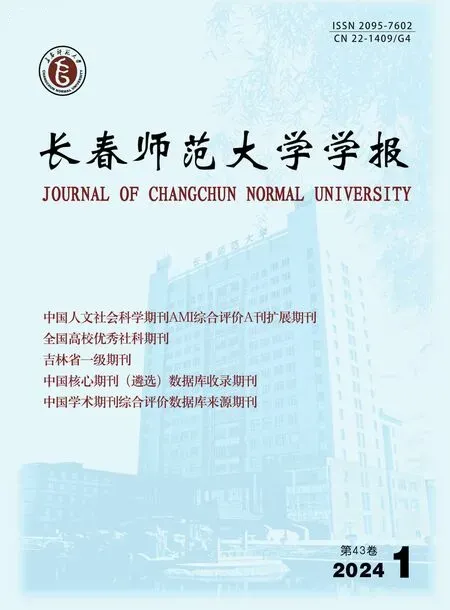宛敏灏词话观探赜
——以《词学概论》为中心
沈文凡,郭鹏飞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词话是词学批评理论的最典型载体。词话与诗话、曲话、文话、赋话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文献的主要形式。”[1]词话承载着宋代以来词鉴赏、词批评、词创作、词人研究等方面的众多成果,对现代词学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宛敏灏先生称其为“词学资料的渊薮”[2]285。
《词学概论》是体现宛敏灏先生词学思想的重要学术论著,是词学园圃中的扛鼎之作。在词话的源流和发展、词话内容的界定、词话资料的运用等三方面,该书阐述了独到观点和宏通见解,为现代词话研究开辟了行之有效的路径,体现出先生求真务实的著述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
一、阐述词话沿革
词话的产生如同词的产生一样,一直是词学界争论不定的重要话题。朱崇才认为,“词话史的理论研究应主要从理论的高度,深入了解剖析历代词论家的主要观点、主要理论成就及不足,探讨其理论的环境背景及意义。”[3]6早在《词学概论》中,宛敏灏先生就已经基于这种研究思路,深稽博考,阐明了词话的兴起和发展历程,深具学术洞察力。之后先生根据诗话源流考证所得,厘清了词话的重要特征和主要内容,并附以翔实的例证资料,令人信服。
(一)考证诗话与词话的起源
吴梅认为词话产生于南宋,其在《词话丛编序》中说道:“北宋诸贤,多精律吕,依声下字,井然有法。而词论之书,寂寞无闻,知者不言,盖有由焉……玉田词源,晦叔漫志,伯时指迷,一时并作,三者之外,犹罕专篇。元明以降,精言蔚起。”[4]这是现代词学中关于词话史的最早论述,但过于简要,难成系统。要论现代词话史研究较深较全者,宛敏灏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龙榆生在《词学十讲》中谈到词的起源问题,指出其是“由诗的‘附庸’而‘蔚为大国’”[5]211,词话的发展情况也大体如此。词话晚起于诗话,二者在文体性质和语言批评层面有一脉相承之处,探析诗话源流可以为考证词话之产生提供一些证据资料。宛敏灏先生另辟蹊径,从探析诗话起源入手,认为在词话专书产生之前已有单篇的文章或片段的议论。
郭绍虞在《宋诗话考》中指出诗话始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属于笔记体。“欧氏以前非无论诗之著,即其亦用笔记体者,如潘若同《郡阁雅言》作潘若仲《郡阁雅谈》之属,此后纂辑之诗话,每多称引其语,此类书虽在欧氏以前,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多及野逸贤哲异事佳言’,知非纯粹论诗之作,故《宋史·艺文志》以入小说类而不入文史类。是则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称《四库提要》)“诗文评类一”中也认为欧阳修、司马光、刘攽的诗话类著作是北宋最早的三家诗话,并指出刘攽《中山诗话》和欧阳修《六一诗话》“体兼说部”,位于《文心雕龙》《诗品》之后。可见,《宋诗话考》中关于诗话之体的论述大致和《四库提要》所称相类似。但宛先生并不拘泥于《宋诗话考》中“诗话始于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观点,他认为《文心雕龙》《诗品》中评论诗歌的相关篇章,以及《宋诗话考》中提及的《郡斋读书志》中的一些诗歌评论,同样是具有诗话性质的早期著述。也就是说,最早名为“诗话”者,未必就是同性质最早的著述。至于词话,《四库提要》“词曲类二”在“词话之属”一目首列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同理而言,《碧鸡漫志》应该不是最早的词话文献,在其前已有单篇的文章或片段的议论。
宛先生从诗话溯源过渡到词话溯源,论证了词话专书产生以前已有同性质的词话资料,展现出敏锐通脱的学术思维。先生根据诗话的起源情况推导词话的起源,在现代词学界极具创新意义。此举有利于还原词话发展的真实面貌,有效加深了读者对词话产生历程的理解,并启发了后学者在词话史研究方法上的开拓。孙克强延续此种研究思路,认为“词话之名借鉴于诗话”,并进一步指出:“最早以‘词话’作为书名的杨湜《古今词话》乃是记逸事、录本事为内容的,与《六一诗话》的性质相同。”[7]
(二)阐述由零散资料到系统专书的发展历程
由上文可知,词话专书和词话文献资料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词话文献资料必然早于词话专书,词话专书也必然由词话文献资料发展而来。二者的产生时间和关系,是宛敏灏先生词话史考证的重中之重。
最早的词话文献资料应当是伴随词的创作而来。宛先生强调:“如不以勒成一书者为限,则自有词以来,可能同时即有所谓词话存在。”[2]286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见解,其辩驳了民国以来学界对词话起源的通俗看法,其中的代表性观点是吴梅在《词话丛编序》中提出的“北宋无词论”。宛先生认为吴氏的主张并不符合事实,例如北宋晁补之和李清照各有论词篇章传世,且同见于《苕溪渔隐丛话》及《诗人玉屑》,不能因为其著述被搜罗在南宋的专书之中而忽略其著述创作于北宋的事实。另如唐宣宗时期的宰相令狐绹假借温庭筠新作《菩萨蛮》词密进,两人从此疏远。这一轶事在孙光宪《北梦琐言》、计有功《唐诗纪事》、王灼《碧鸡漫志》中均有记载,可见此事在唐代已经众口相传。晁补之、李清照的词评也应当是伴随原词创作而来,最初以口头相传,经过加工润色之后成为论词专篇。也就是说,在词话专书产生以前,已有文人开始采集、编著词话资料。词话资料亦是词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唐宋以来各类典籍的散见词话之中,虽然未达到词话专书的程度,但不能因此否认其存在和价值。吴熊和也认为,“宋人诗话多至一百四五十种,词话可考者,亦有其十之一二。”[8]368他在《唐宋词通论》中列举了多种成型于北宋的词话文献,有力支持了宛先生对吴梅词话史论点的更正意见。
词话专书起于晚宋,元、明踵事增华,至清始作者辈出,极一时之盛。宛先生认同吴梅将《词源》《碧鸡漫志》《乐府指迷》列为宋朝三部主要词话专著的做法。至于现存最早的词话专书,先生在《词学概论》中未作具体说明。后学者根据宛先生的词话史考述成果,继续深耕探微,大体得出北宋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乃是现存最早词话专书的结论。
为了完整地构建词话史框架,宛先生还详细介绍了《四库提要》和《词话丛编》的词话文献收录情况,并且着重分析了《碧鸡漫志》和《词源》这两部早期词话专书的内容,不仅展示了蔚为大观的古代词话成就,也体现出先生“授人以渔”的著述品格。
其一,关于《四库提要》和《词话丛编》的词话文献辑录情况。《四库提要》中著录词话凡五部十九卷:王灼《碧鸡漫志》一卷,沈义父《乐府指迷》一卷,陈霆《渚山堂词话》三卷,毛奇龄《词话》二卷(今称《西河词话》),徐轨《词苑丛谈》十二卷;存目词话凡五部十三卷:张炎《乐府指迷》一卷(此实系张炎《词源》下卷,以下皆称《词源》),陆辅之《词旨》一卷,沈雄《古今词话》六卷,王又华《古今词论》一卷,毛先舒《填词名解》四卷。《词话丛编》中辑录词话凡六十种,其中宋词话七种,包括王灼《碧鸡漫志》、吴曾《能改斋漫录》等;元词话二种,包括吴师道《吴礼部词话》、陆辅之《词旨》;明词话四种,包括陈霆《渚山堂词话》、王世贞《艺苑卮言》等;清词话四十一种,包括李渔《窥词管见》、毛奇龄《西河词话》等;民国以来词话六种,包括徐珂《近词丛话》、王国维《人间词话》等。
其二,关于《碧鸡漫志》和《词源》的介绍与分析。《碧鸡漫志》卷一详述曲调源流,卷二评论作家或纪事,卷三至卷五专论词调。宛敏灏先生经过分析,发现此书“惟对柳永及李清照特加指摘”[2]304。《碧鸡漫志》批评柳永《乐章集》“浅近卑俗”,“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9]84,贬斥李清照词“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9]88。《词源》上卷专论乐律,下卷泛论词的鉴赏和作法。宛先生首先分析了张炎的评词标准及其对清代浙西词派的重大影响,并通过考证张炎的家学及其先世和姜夔的交游情况,认为张炎词学承于家学,并且受到姜夔的很大影响。
宛敏灏先生以其宏通博大的词学知识体系和脚踏实地的文献分析功力,小心求证了词话的源头和脉络,确立了较为完善的词话史框架。
二、辨析词话内容
在《词学概论》中,宛敏灏先生犀利地捕捉到词话的性质和特征,细致地辨别了词话专书和理论词书的差异。此外,先生还根据历代的词话创作情况,潜心考辨,梳理出词话的主要内容,为后学者奠定了词话内容研究的重要基础。
词话以本事和评论为主要内容。对此,宛先生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一,词话的辨别标准是“其书内容是否为词话性质,而不计其是否以词话为书名”[2]291。例如唐圭璋所辑《词话丛编》中,词话书名不称“词话”者达半数以上,其中包括《碧鸡漫志》《乐府指迷》《花草蒙拾》等著名的词话书籍。第二,词话是“一种以谈词为内容的笔记,涉及范围广泛,是综合性的”[2]291。唐圭璋也持这种观点,指出:“前人论词,大都用词话形式,其中有记载词人轶事及研讨词作两类”[10]。倘专就某一方面问题集中探讨或系统地提出研究成果,则有别于一般词话而成为另一专门性著述,例如《四库提要》划归“词谱、词韵之属”的《钦定词谱》和《词律》便是两部有别于词话的专门性著述。这种严谨而实用的分类方法划定了词话的界限,前者属于一般的评论性词话,后者属于词韵、词谱、词乐等方面的理论专书。《词话丛编》的编纂体例再次佐证了宛先生的观点,其《例言》云:“所收范围,大抵以言本事、评艺文为主;若词律、词谱、词韵诸书以及研讨词乐之书,概不列入。”[11]6第三,词话的著述范围不宜限制过多。词话原是综合性笔记,只要与词学有关的问题均可记载或评论。
更重要的是,宛先生不遗余力地展示了词话内容辨析的具体方法,为词学爱好者发蒙启蔽。其一,多例互证。先生在辨析一个问题之后,经常给出多个文献资料进行佐证,以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在归纳词话专书和理论词书的区别之后,先生指出清代徐轨著的《词苑丛谈》是一部以本事和评论为主的专门性词话;清代沈雄编纂、江尚质增辑的《古今词话》是词话、词品、词辨、词评四种的汇编,虽名为词话,但并不全是词话之体;江顺诒纂辑、宗山参订的《词学集成》包括体制、音韵、流派、品藻等八个专题,是各类词学资料的汇编。宛先生举例的这三部词话在内容重点上各不相同,可以使读者增进对词学概念的理解。其二,显幽阐微。先生在举出词话例证的同时,还分析了各种词话的著作情况和优缺点,注重词话例证本身带给读者的资料性价值。例如,先生指出《词苑丛谈》后来被改写成《词苑萃编》,突出之处在于其注明了资料来源;清代《古今词话》明显袭用宋代杨湜《古今词话》的名称,但杨书已失传;《词学集成》论断较多,虽资料编次异于一般词话,但体例仍属词话性质。这些发现看似细枝末节,却有关宏旨,不仅全面展示了词话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普及了深微的词学知识。这种举一反三、循循善诱的著述风格体现出先生在教育事业上的大家风采。
“词话是记录词本事、评论词作、表达词学主张的专门著述,是词学批评理论的典型载体。”[12]在词话内容研究方面,宛敏灏先生开风气之先,不仅严格辨析了词话专书和理论词书的差异,总结了历代词话创作的主要内容,还在方法论层面为词学爱好者指点了迷津。
三、归纳词话利用方法
作为词学资料的渊薮,词话对今人研究古代词学功莫大焉。在《词学概论》中,宛敏灏先生不仅强调了词话资料利用的重要价值,更归纳出了词话资料利用的三大基本门径——整理、鉴别、选择,在方法论层面为后学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指导意见。
(一)“定人”“定题”的整理体系
词话资料浩如烟海,其发掘和整理十分重要。唐圭璋《词话丛编》是词话汇编的集大成之作,但未被收录于此的其他词话专书以及散见于各种著作的词话资料不知凡几。针对收录不全的词话整理现状,宛敏灏先生着重介绍了两种实用价值较高的词话整理方式,即定人辑录与定题辑录。这对今人编集新词话无疑具有启发性意义。
其一,定人辑录,即“作家本无词话专著而出于别人所辑录者。”[2]315宋代以来,大多数词话都是词人自己写作编次的,但仍有少数词话为他人所辑录,如《复堂词话》便是谭献的弟子徐珂集录的。推而广之,宛先生认为词家未作词话而其言论散见于本人各种著作的,皆可辑为某人词话。例如清代朱彝尊和张惠言没有词话专书传世,但辑录者仍可从他们的著述中广事搜罗,辑出相关词话内容,并附录晚出的相关评论资料,以此编成词话专卷。为了证实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宛先生还以朱彝尊为例,指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谈到的浙西词风之转变始于曹溶,《解佩令·自题此集》《词综·发凡》中的词评、词解,以及收录在其文集中的词序等,都可以作为朱彝尊词话专卷的内容进行整理和编次。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唐圭璋《词话丛编》中未见这种编次体例。朱崇才根据宛先生指出的这种编次方向,认为“《苏轼文集》中有四十馀条涉及词的话语,即可指称为‘苏轼词话’。”[3]1可见宛先生的这种辑录方法是很有学术前瞻性的。
其二,定题辑录,即“就某一专题采撷各家词话汇录成编者。”[2]315汇集各家词话关于某方面的论述,间附己意而分类编次成书。例如清代江顺诒编著的《词学集成》,全书分为词源、词体、词音、词韵、词派、词法、词境、词品等八门,即八个专题,是一部典型的分门别类的词话著作。但此书搜罗范围过于狭窄,类目编次较为粗糙,以致其内容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故此,宛先生秉持严肃治学之态度,提倡词话整理要广集各家意见,避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更进一步讲,“关于词韵、词的鉴赏、写作种种方面,都可就已有词话集为专卷。”[2]318
宛先生提出的定人辑录与定题辑录方法,不仅拓宽了词话整理的具体路径,也为后学者从事词话分类学研究提供了方法依据,惠泽词学之功不可谓不深远。
(二)端正严谨的鉴别意识
龙榆生在《词学十讲》中谈到晁补之、李清照的词论时说:“一个批评家的眼光,常是会被时代和环境所局限,从而‘以偏概全’,看不见事物的整体。”[5]212词话文献可资利用者不可胜数,其中是非曲直处需要词学研究者仔细鉴别。宛敏灏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了词话中的四点常见局限和错误。
其一,随意抄录,来源不清。这是针对某些注明体例不全的词话而言,例如清代田同之《西圃词说》在抄录王士祯《花草蒙拾》中“或问诗词词曲分界,予曰……”[13]一语时未注明出处,很容易让读者误以为是田氏的观点。其二,辗转互抄,字句大同小异。改其句而偷其意,是一些词话著作者的通病。《西圃词说》将邹祗谟《词衷》“咏物固不可不拟,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14]两句话语改为“咏物贵似,然不可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15]时却没有注明出处,可见田氏此书不严谨之甚。其三,说明出处,但粗心抄错。例如清代查礼《铜鼓书堂词话》中说:“《能改斋漫录》载陈济翁寄张于湖《蓦山溪》词云”[16],但《能改斋漫录》原作乃为“此陈济翁《蓦山溪》词也,舍人张孝祥知潭州,因宴客,妓有歌此”[17],并无“寄词”一说。可见查氏乃望文生义,乃致有此粗心之失。这一类错讹关乎到词作本事的考证乃至对词作原意的理解,后学者当加以重视。其四,引用错误,以讹传讹。引用出处标示错误的问题一般不容易被发现,但可能给读者带来严重的认知错误。例如1926年出版的胡云翼《宋词研究》,在“通论”部分引用清代宋翔凤《乐府馀论》“按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起宋仁宗朝……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18]这段话时,竟称其为吴曾《能改斋漫录》中的内容。这明显是引用错误,很可能使读者误认为此段话乃吴曾所言,若不加辨别辗转互引,难免导致重大的研究过失。
宛敏灏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二晏词时便开始展现。夏承焘在《二晏及其词序》中称赞宛先生“治学之劬勤若尔,宜其所积之厚也”[19],诚为持正之论。
(三)“视需”“去伪”的选择方法
词话资料深广博大、纷繁复杂,学者进行词学研究不可能也不需要广而罗之,这就涉及如何选择的问题。对此,宛敏灏先生提出了一个标准,即“视需要而定”,同时注重去伪存真。研究什么样的词学论题,就选择具有此类研究价值的词话资料,并慎重使用。
在选择词话资料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任何词话都有其论词主张,读时务须比较异同,辨其精粗得失。”[2]323这便是“视需”。宛先生指出,关于词作欣赏,可以参看特定词话中关于作品的评论,其中包括对名作的欣赏和对“恶词”的指摘,而以前者为多。例如张炎《词源》中的《意趣》篇认为苏轼《水调歌头》、王安石《桂枝香》、姜夔《暗香》《疏影》“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20]讲论作词之法,《词源》下卷及沈义父《乐府指迷》是较早的两部词话专著,其中涉及很多填词宜忌的词话内容;还有清代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在虚与实两种词体结构方式上有具体精微的阐述。
另外,词话中有些纪事失实,不宜轻信,引用尤须谨慎。这便是“去伪”。宛敏灏先生早在《二晏及其词》中便指出:“降及晚近,去宋日远,对于当时词家之认识遂愈不真。”[21]例如周邦彦作《少年游》是否出于其匿于床下偷听宋徽宗与李师师谑语一事,以及李清照晚年改嫁张汝舟之说,作为人物故事以资谈论尚可,但要作为史实引用则需要慎重考虑。唐圭璋编《词话丛编》时也在选择上精益求精,其《例言》有云:“词后附名流评语者,如孙默《十六家词》,气类标榜,率多逾量,兹并不录。”[11]7唐圭璋认为《十六家词》评语轻率失实,不足选录。两位词学大家在重点词学问题上体现出了颇为一致的学术见解。
宛敏灏先生基于其漫长而丰富的词学研究历程,秉持“授人以渔”的著述品格,提出了整理、鉴别、选择三大词话利用方法,为后学在词话研究上拨云见日,是名副其实的大师名家。
四、结语
宛敏灏先生致力于词学研究近七十年,对现代词学研究基本体系的构建贡献非凡。词话观是宛先生词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众多词话研究成果。他不仅阐明了词话沿革脉络,还梳理了词话的主要内容,并介绍了整理、鉴别、选择等三种词话资料利用方法。宛先生在词话研究的关键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创见和研究方法,其导夫先路之功令后学无限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