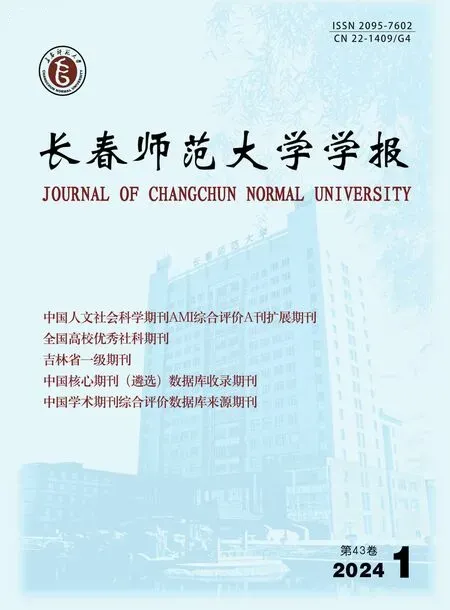南宋初太常寺音乐职能重建过程述论
唱明扬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7)
礼乐制度是帝制时代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宋代基本由太常寺掌管礼乐,其音乐职能为“掌乐律、乐舞、乐章以定宫架、特架之制,祭祀享则分乐而序之”。太常寺管理乐工、舞师等人员,在卤簿、警场、朝会、宴享等场合负责奏乐[1]3882-3886。其下属太乐局、鼓吹局、教坊等是宋代最主要的音乐机构,分别承担着雅乐、鼓吹乐与宴乐职能。
北宋后期,太常寺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动。一为崇宁四年(1105),太常所属音乐机构分割给大晟府,从此不具音乐职能。一为金人南侵的破坏。靖康二年(1127),汴京陷落,大量乐工和礼乐之器或被北掳,或散落乡野。至南宋,国势艰难,宋廷精简机构以节省开支,九寺五监或并或省。[2]474-475太常寺虽未废罢,但也变化明显。为应对军事压力,南宋政府长期保持缩减开支、收紧编制的状态;同时仍花费较大精力重制礼乐,尽力维持国家典礼的规格与排场。南宋太常寺及礼乐重建等问题仍是目前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之一①,本文试图从太常寺音乐机构的组织结构,乐工来源、数量及管理方式,南宋政治的影响等角度探讨南宋太常寺音乐职能的重建过程与变化情况。
一、太常寺对大晟府“遗产”的继承
徽宗朝礼乐制度的最大创举是成立大晟府与制作、颁行大晟乐[3]。崇宁四年,太常寺太乐局和鼓吹局转隶大晟府;元丰改制后,教坊隶于太常[4]4408,此时也转隶大晟。自此,礼、乐由太常、大晟二司分掌。宣和七年(1125),金人南侵,朝廷“诏革弊事”,罢大晟府[1]3027。但所属乐工去处缺乏记载,太常是否重设音乐机构也不得而知。靖康二年,汴京陷落,礼乐活动中断,音乐机构的废罢影响不大。
建炎初,高宗诏令不作乐[1]3029。绍兴十年(1140),礼臣奏请恢复用乐。至绍兴和议成,朝廷才诏告天下解除乐禁。[4]3994此处所禁为朝会、宴享之乐,郊庙所奏雅乐是“为上帝宗庙而设”[2]1894,不在禁止范围,所以太常最先恢复的是雅乐。在逐次典礼中,太常寺缓慢重建音乐职能,这一过程从接收大晟府“遗产”开始。
(一)搜罗、拘收大晟府旧乐工
南宋初,太常乐工多是寻访来的大晟旧乐工。绍兴元年明堂,太常卿苏迟言:“今亲祠登歌乐器尚阙,宣和添用籥色,未及颁降,州郡无从可以创制,宜权用望祭礼例,止设登歌,用乐工四十有七人。”乃访旧工,以备其数。[1]3029-3030
大晟府掌乐二十年,“旧工”大部分来自大晟府。为召集足够多的乐工,太常寺申请“重立告赏刑名”,加重处罚逃避征召的乐工。旧制,“诸大礼应奉人辄不赴者,杖一百;诸乐工避免不赴教习者,笞五十。”此时朝廷将其改为“诸大礼应奉人辄不赴者,杖一百。内乐工辄投他处者加一等,许人告;诸乐工避免不赴教习者,杖六十”,规定“赏钱一十贯”。可见寻访大晟旧工具有强制性,故称之为“拘收”[5]253。
除乐工外,中高层乐官也多为寻访的大晟旧人。绍兴十年,太常寺寻到“殿前司后军第一将下掌管医学任道,系前大晟府二舞色长”,申请殿前司“权行发遣,赴寺充舞色色长”,教习乐工舞象、舞仪。[5]254绍兴十三年(1143),太常申请将前大晟乐师陆诚拘收,充郊祀大礼分诣乐正。[5]51同年二月,王师心指出,此时缺乏老师教习乐工,而行在有很多大晟鼓吹旧工,要求将其聚集至太常,如有“已系有名目之人及见在官司人”,不得阻碍其发遣。朝廷同意了他的申请,可见政府对恢复礼乐工作的重视。[5]86-87
古代音乐传承实赖师徒间的口传身授,大晟府废罢及“靖康之难”使得乐工散落,南宋初险些出现音乐人才的断层。至太常重新搜罗大晟府旧乐工,才避免了这一情况的发生。
(二)搜罗各州军大晟府旧乐器
南宋初各典礼所用乐器基本来自大晟府。“靖康之难”,致金人掳走大量礼乐之器。[1]3027劫余之器在建炎二年(1128)发运至扬州,以供郊礼之用。[1]3029因渡江不便,这批乐器郊祀后未被带至江南。[4]3994中央乐器经历战火与南渡后损失殆尽,幸运的是部分州军尚留存大晟府颁降乐器。大观元年(1107),徽宗将大晟乐颁降天下,朝廷陆续将大晟乐器颁降各地。[3]106-111绍兴元年,为准备明堂礼,太常寺言:“所有将来大礼,欲乞依望祭礼例,止设登歌之乐,通作宫架之曲。仍令有司预先取会有颁降大乐州军,取见的实祗备将来供使。”[5]252此处“颁降大乐”便是颁降州军的大晟乐器。绍兴和议前,朝廷无暇制作新乐器,基本使用州军存留的大晟乐器。初仅备登歌大乐一料,宫架乐缺而不设。绍兴九年(1139),朝廷决定在次年明堂中恢复宫架乐,苏携请求于两浙等路州军搜调大晟乐器,朝廷下令“两浙、江东西、福建路、广南东路转运司依劄子内所乞事理施行”[5]253-254。绍兴十三年(1143)重启郊礼,相较于此前的明堂,需增设登歌大乐一料,置于望祭殿备用。[5]37景灵宫、太庙等处也要添置乐器。[5]52同年二月,太常提交了所缺乐器名目,朝廷决定继续起发两浙、江南等路州军的大晟乐器,部分乐器由军器所制造。[5]51绍兴十五年(1145),政府才命礼器局制作乐器。[5]55
南宋还据《大晟乐书》重作了景钟。景钟是徽宗时所创,用于皇帝亲郊。[1]3008绍兴十六年(1146),高宗令礼部、太常寺讨论景钟制度。[5]55段拂等据《大晟乐书》奏上景钟之制,最后朝廷令礼器局制造景钟。[5]56高宗与大臣于射殿观看新礼器,撞景钟,奏新乐,时人评价“文治自是彬彬矣”[2]2517。
《宋史》对南宋礼乐之制评价道:“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旧,未尝有所改作。”[1]2939“先朝之旧”即大晟乐。南宋初无暇制作礼乐之器,绍兴年间三次征调颁降的大晟乐器,为维持三年一次大礼提供了基本保障。
二、因陋就简——太常寺各音乐机构的重建与变化
南宋初并省冗职,太常寺也精简了人员编制,仅设“太常少卿一员兼宗正少卿,罢丞、簿,惟置博士一员。”[1]3884太常虽逐渐搜罗了一些乐工,但太乐局、鼓吹局事实上并未立刻重建。元丰改制后,教坊划归太常管理。[4]4408南宋教坊隶属关系不甚明确,本文姑且按元丰之制将其归为太常所属。此外还有钧容直、教乐所等其他音乐机构,下文将论及。
(一)雅乐的重建与太乐局的消失
太乐局是太常寺下属雅乐机构[4]1616,主要负责典礼所用宫架乐、登歌乐和二舞。北宋时“令、丞至守缺乐工凡三百四十一人。”[6]3632徽宗时太乐局属大晟府,宣和年间随其并罢。
南宋太常寺是否重建太乐局,缺少文献依据。《文献通考》叙述太乐局、鼓吹局之流变,仅至北宋末,对南宋情况只字未提。唯一记载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四《大乐局乐色名件》,记大乐局所用三十四种乐器。[7]576-577《宋史》载淳熙六年(1179)礼官编订南郊、明堂仪注事[1]3039-3040,最后载所用三十四种乐器,与《朝野杂记》基本相同,仅首尾不同[1]3042,可见二者有共同史源,可能抄自《会要》或《国史》。《宋史》仅言“大礼用乐”,《朝野杂记》中《大乐局乐色名件》标题与开头的“大乐局”等字可能是李心传所加,这条史料不能证明南宋存在大乐局。
《宋代官制辞典》“乐正”条云:“北宋太常寺太乐局置乐正,南宋不置太乐局,沿设乐正官”[8],但并无出处。《中兴礼书》明确提及鼓吹局存废情况(见后文),却无太乐局情形。此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书均不见南宋大乐局情况。据此推断,南宋应未设太乐局,仅剩乐正一职。
除精简官吏外,乐工人数也大大缩水。如表1所示,绍兴元年(1131)至十三年(1143)大礼实用乐工人数增长极大,实际并非如此。除搜罗的旧工,南宋乐工多是临时招募、雇佣的百姓,仅在大礼前教习数月,政府每日支付食钱四百文。典礼结束即放罢,等待下次招募。招募标准为“不曾犯徒刑剪刺,不系三路凶恶人”等,此外要求“曾经应奉”“稍谙乐艺”等,即有经验或稍具音乐基础。受募者多为“有产业铺户”,即商户。政府除支付食钱外,还免去本户行役。[5]57真正有编制、月俸的为技艺高超的旧工,如绍兴元年拘收旧工47人,按第三等供官待遇给予“每月料钱三贯文,米一石,每日食钱一百五十文。”[5]253绍兴十三年虽实用乐工452人,但此时太常“额管三十九人”[5]51,即编制乐工39人,其余413人为临时乐工。
绍兴十四年(1144),在大臣请求下,朝廷决定在所募人中选择173人为常备乐工,50人为守缺乐工。这些人仍不是编制乐工,只是名籍登记在太常,需要时据名单“先次籍定”,即优先雇佣熟练工。[5]53编制乐工和仅系籍在太常的和雇乐工有时都被称为系籍乐工。如绍兴十五年(1144)耕耤礼,礼臣言“太常寺见系籍乐工止管二百六十六人”[6]587,但隆兴二年(1164)洪适言“所有乐工凡二百六十人,太常有籍三十六人,有月给钱粮”[6]398,同年芮煇也提到“乐工除三十六人有钱粮外,其余并是无钱粮百姓”[5]61。可见,系籍乐工数量在扩大,编制乐工反而在减少。
总之,自绍兴十三年郊礼起,系籍乐工增至260人左右,实用人数稳定在450人左右,隆兴二年因战火重启有所减少。[5]60
南宋重建雅乐,未恢复太乐局建制。太乐局令、丞均不置,止设乐正一职,组织结构扁平化,层级空疏;乐工来源和待遇变化也很大。南宋编制乐工只有近40人,已大幅缩水。太常大规模和雇百姓,仅支付教习食钱,产生了系籍于寺的和雇乐工,减少了礼乐花费。绍兴十三年后,朝廷礼乐制度基本步入正轨。
(二)鼓吹乐的重建与鼓吹局的虚置
鼓吹局祠祭时设熊罴十二案[4]4429,也是卤簿仪仗的一部分[5]90,宿斋、行幸遇夜时负责警场奏严。[4]4429北宋鼓吹局“令、丞至守缺乐工凡百二十七人。”[6]3632太祖时鼓吹局便缺乏乐工[1]3302;真宗时“命籍兵二百馀工,使长隶太常以阅习焉”[4]4429;仁宗时设武严指挥,以充实鼓吹乐[6]2221;徽宗时鼓吹局隶大晟府,后随之并罢。
绍兴十三年前不置鼓吹局,大礼不设卤簿,只用常日仪卫[5]272;警场只用鼓、角各六十,金钲十二[5]119,“就用中军金鼓角匠充”[5]305。绍兴十三年,南郊开始使用卤簿仪仗和警场鼓吹。王师心提到此时“无鼓吹局”,无人教习乐艺等事,申请拘收大晟旧工三五人。[5]86-87同年七月十二日,礼部、太常寺收到“鼓吹局指教使臣”所上奏状;十七日,“鼓吹局申准已降指挥”[5]119。如此,王师心二月申请踏逐旧工,迟至七月已寻到人员充任指教使臣,鼓吹局在绍兴十三年完成了名义上的重建。
此次只恢复了两三个职位,未恢复乐工编制。绍兴三十二年(1162),太常寺讨论皇帝亲享太庙礼时言:“合用鼓吹二百三十六人,除太常寺见管令丞三人外,其余人乞下殿前、马、步三司差拨杂攒乐人。”[5]445八月,礼臣奏言中有相同记载。[5]604可见此时鼓吹局只有令、丞三人,所有乐工征调禁军充任,编制乐工阙而不置。此时令、丞地位也十分低微。礼臣劄子讨论令、丞仪仗中应穿服饰时提到,绍兴二十九年(1159),鼓吹令仅为从九品承节郎,丞为白身人;淳熙十四年(1187)则全为白身人,几与普通乐工无异。[9]
然而军乐与鼓吹乐区别较大。绍兴十九年(1149),大臣对警场鼓吹乐进言,指出军旅、祭祀事异而乐声清浊也应当不同,请求制鼓吹乐器取代军中所用锣鼓,并招募鼓吹乐工。[5]121据比对,鼓吹局合用乐器与士兵实用乐器区别很大。高宗令军器局新制乐器[5]121-122,此后鼓吹乐虽全由士兵充任,但多用新作乐器。
南宋鼓吹局虽名义上重建,实际只恢复了令、丞职位,原一百多名编制乐工阙而不置,所谓鼓吹局只是有名无实。得益于北宋以来长期抽调禁军充任乐工的制度基础与善乐士兵人数之庞大,南宋鼓吹局乐工均由禁军充任。南宋政府在长期军事压力下还能维持较大规模的卤簿、警场鼓吹,这种组织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宴乐的重建与教坊的兴衰
宋代教坊承袭前代之制,宋初隶属于宣徽院[1]3358,负责宴享之乐,“国朝凡大宴、曲宴,应奉车驾游幸,则皆引从。及赐大臣宗室筵设,并用之。”[6]3628元丰改制后隶太常[4]4408,崇宁四年教坊转隶大晟府。[6]3627北宋末诏罢大晟府,教坊乐工被金人大量掳掠[10],此后教坊名存实亡。
南宋初不置教坊。绍兴十四年,高宗令钤辖钧容直所“条具祖宗以来置教坊典故”,按旧制重设教坊;绍兴三十一年,宋金开战在即,六月高宗诏罢教坊。[6]3629教坊省罢后,技艺高超者留充德寿宫使臣,他们多为高宗御前祗应;其余多隶临安府衙前乐。[11]30-31衙前乐是地方音乐机构,各州均有设置。[12]此后教坊虽不复置,但名号犹存,被修内司教乐所取代。[7]577
《武林旧事》记载,乾道、淳熙年间,教乐所点集的乐工有五类来源:德寿宫、衙前、前教坊、前钧容直、和雇。[13]《宋史》将上述乐工称为“杂攒”[1]3345,前文所述鼓吹局抽调禁军充任的乐工也被称为“三司杂攒乐人”。教乐所提前点集乐工教习两旬,以教坊名号进行表演,结束后放罢,其组织形式与鼓吹局相同,均不设编制乐工,省去月俸钱,得以俭省开支。
教坊废罢后,教乐所承担宴乐职能,临时募集杂攒乐工,充任教坊名号。这种组织形式既满足了政府对宴乐的需求,又在长期面临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俭省了开支。
三、取具临时——南宋太常寺的乐工调遣制度
《宋史》将教乐所之制总结为“间用杂攒以充教坊之号,取具临时”[1]3345,实际上“取具临时”和“间用杂攒”是南宋音乐机构的共有特点。此外,“番衮祗应”是礼乐实践中常用的乐工安排手段。三者是南宋太常寺乐工调遣制度的主要方式。
(一)“取具临时”“间用杂攒”与“番衮祗应”
通过梳理太乐局、鼓吹局、教坊(教乐所)的重建过程及结构变化,可以发现三者组织形式极其相似。在乐工管理方面,保留少数编制乐工,其他乐工临时召集,事毕放罢,可称为“取具临时”;在乐工属性方面,均为拼凑混杂而来,是为“杂攒”。这种混杂的情况在礼乐实践的整体层面也很明显,在雅乐中最突出。郊庙本该由太乐局负责雅乐,但由于乐工不足,此时多抽调教坊、钧容直充任,再不足则抽调衙前乐或招募百姓。[6]587此外钧容直会充当教坊乐工进行表演。[14]综合来看,南宋在使用乐工时存在如下的机构差调链:太乐局(乐正)、鼓吹局——教坊、钧容直、三衙——衙前乐营——市人。各机构无从属关系,上层级机构常抽调下层级机构乐工,这使得北宋时职能划分较为清晰的雅乐、鼓吹乐、宴乐三类机构愈发混乱。
为缩减乐工人数,典礼中常有“番衮祗应”的情况。如绍兴十三年南郊,别庙、太社、太稷均需乐工。为减少人数,只设别庙乐正、乐工38人,演奏完毕再番衮前往太社、太稷奏乐;二舞只设64人,典礼中先后充任文武二舞郎。[5]51南宋大礼太社、太稷与二舞基本为番衮祗应,宫架、登歌二乐也多在圆坛、景灵宫等处番衮使用。[5]52此外,行事执事官等也会通衮祗应,解决助祭人员不足问题[5]98-105;朝会礼仪中,南宋射殿也被番衮使用了。[1]3381通过改换名号,射殿除充当崇政殿、紫宸殿、文德殿外,还在朝会中充当大庆殿。[6]644通过番衮祗应,人员、器物缺乏的南宋勉强在名义上维持了北宋之制。
(二)乐工调遣制度的缺点
上述三种乐工调遣方式,是各音乐机构的共通之处,实质是保留少量技艺精熟的编制乐工,通过他们提前教习临时乐工,完成乐工再生产。在这种背景下,教习的质量显得至关重要。但为了节省开支,隆兴二年洪适上奏,将大礼乐工教习时间从98天缩减至30天[5]60,乐工技艺更难保障,常有大臣批评其技艺粗疏。绍熙二年(1191)郊祀,耿秉批评太常乐工技艺不精。[1]3048嘉定二年有臣僚上奏:
郊祀登歌列于坛上,簉于上龛,盖在天地祖宗之侧也。宫架列于午阶下,则百神所同听也。夫乐音莫尚于和,今丝、竹、管、弦类有阙断,拊搏、佾舞,贱工、窭人往往垢翫獶杂,宜申严以肃祀事。[1]3049
祠祭典礼中,乐工水平低劣会被视为侍奉祖宗神灵不够虔诚。理宗时,姜夔进《大乐议》,将“人事不和、天时多忒”归为乐工技艺粗疏所致,请求品择、淘汰乐工[1]3051,可见乐工技艺之差。此外,也有大臣批评教乐所临时乐工水平低下。[11]31隆兴二年,洪适对抽调士兵组成的鼓吹乐表示质疑,将这些乐工贬低为“游手之人”[5]60,可见其身份低微、技艺不精。
虽有上述缺点,但这三种人事调遣方式满足了政府的需求,缩减了乐工编制,俭省了大量开支,成为南宋音乐机构重建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畸形的产物,源于长期军事压力下南宋政府使礼乐制度在名义上符合北宋旧制的需要。
四、结语:南宋政治与礼乐实践
通过梳理南宋礼乐制度重建过程可以发现,和、战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绍兴和议后,雅乐系籍乐工增至260人左右,大礼实用乐工稳定在450人左右;鼓吹局复置,重启卤簿仪仗与警场奏严;教坊按北宋旧制重建。海陵南侵后,隆兴二年首次南郊,雅乐与鼓吹乐实用人数缩减,教习时间也由三个月减为一个月;教坊直接废罢,教乐所接管宴乐职能。可见绍兴和议与海陵南侵是重建的关键节点。战争爆发后,国家财政压力增大,进而削减礼乐开支;和平之时,政府不论是为了强化政权合法性,还是为了粉饰太平、夸饰威仪,会增加礼乐支出。
和、战与政治关系紧密,影响了时人对南宋礼乐实践的认识。《中兴两朝圣政》将“肄习大乐”“复置教坊”“撞景钟奏新乐”等列入“圣政”,可见其评价颇高,而书中转引的《大事记》则将这些举动视为秦桧粉饰中兴的手段。[15]在主战派人士眼中,此时制礼作乐不合时宜,类似的看法不在少数。绍兴三年,江端友请于行在建太庙,吏部侍郎陈与义等人反对:
国家自渡江以来,讲武修备,期于恢复。盖恐不常厥居,故因府治残破之馀而居之。而宗庙神主,则往温州奉安,意可见矣。不知端友之意,谓今日定都于临安乎?将俟天下平定,而别议定都所在乎?[2]1190-1191
绍兴九年,胡寅给张浚的信中反对兴建宫室:“今乃于临安增修母后、渊圣宫殿,是不为北迁之计也。”[2]2042绍兴十三年,洪皓与秦桧说:“钱塘暂居,而景灵宫、太庙皆极土木之华,岂非示无中原意?”[2]2404淳熙末年,张枃请建青城斋宫,宇文价仍反对:“陛下方经略河南,今筑青城,是无中原意也”,孝宗即命罢建。[7]75对修建太庙、景灵宫等事,反对者都从“无中原意”出发提出批评,希望国家将精力与财赋用于收复中原,而不是营建宫室、制礼作乐,自然认为制礼作乐不合时宜,甚至将其视为秦桧粉饰太平的手段。
南宋初“十余年间,凡有诏令,必以恢复中原为言,所以系百姓心也。”[2]2042可见心念故国、不忘中原为当时的“政治正确”。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南宋宫室名物、典章制度等力求遵守北宋之制,实际却多无法实现,产生了虚名与实情的分离。如名义上首都是汴京,实际是临安;名义上有崇政殿、紫宸殿等宫室,实际是射殿改换名号;孝宗朝后名义上的教坊,实际是教乐所点集杂攒乐人充任。南宋之所以执迷于所谓的虚名,就是为了强化政权合法性,在恢复礼乐时以北宋为范本,力求恢复旧制。但经过一百多年的完善,礼乐制度至徽宗朝达到顶峰,这成为南宋无法摆脱的包袱。偏安后,统治者无意制作,礼乐制度得不到发展完善,停留在因陋就简的状态。在音乐机构上,就是太常寺一方面压缩组织层级,削减编制以俭省费用;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如“取具临时”“间用杂攒”“番衮祗应”等满足典礼需求。南宋太常寺音乐机构名义上完成了重建,实践中勉强维持表面的规格与排场,但各机构人员凋敝,乐工技艺粗疏,多为滥竽充数者,与北宋已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