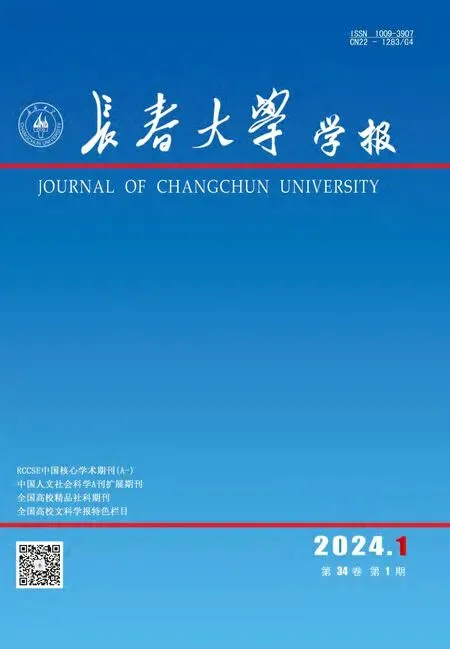莫言对卡夫卡式黑色幽默的借鉴与创新
——《酒国》与《审判》之比较
郝 燕
(蚌埠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黑色幽默,又被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大难临头的幽默”、“病态幽默”,是指一种以痛苦的娱乐方式对待死亡、疾病、战争等令人不安的或邪恶主题的幽默[1]。莫言与卡夫卡都是运用黑色幽默文学手法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文学作品都呈现出滑稽与恐怖交织的艺术特点,以表达世界的荒谬、冷漠、悖论和残酷。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指出:“比起众多追随拉伯雷和斯威夫特的作家——在我们的时代,追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家,莫言的世界更加趣味横生,也更为惊骇人心。”莫言追求不受理性制约的自由书写,并最终在黑色幽默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理想方法。他对黑色幽默情有独钟,这一点在《酒国》的开篇就已显露端倪。在描写卡车女司机时,莫言写道:“听到司机骂道路,骂人;粗俗的语言出自一个比较秀丽的少妇之口,产生黑色的幽默。”[2]3在一定程度上,莫言的创作风格受到卡夫卡的影响(目前已有不少学者撰文分析,如曾艳兵[3]、李运抟[4]等),对此,莫言本人也毫不避讳,他将卡夫卡的一篇小说列入影响他的10篇短篇小说中[5]。本文以《酒国》与《审判》为例,对莫言与卡夫卡的黑色幽默文学风格进行比较研究,其意义在于:一方面,以中国当代文学为参照物,可以深挖卡夫卡文学的中国元素,使卡夫卡研究更具中国本土的特色;另一方面,通过分析两者黑色幽默风格的共性和差异,揭示莫言对卡夫卡式黑色幽默的借鉴与创新,从而为更多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提供可供参考的范例。
一、共同的黑色幽默技巧:“反英雄”人物与对文本意义的消解
在小说中,莫言与卡夫卡都采用了共同的黑色幽默技巧:“反英雄”人物的塑造以及对文本意义的消解,向我们昭示出现代社会人孤独、焦虑和幻灭的心理现实,以及在非理性世界中的生存困境。
(一)“反英雄”人物
“黑色幽默”派作家往往塑造一些乖僻的“反英雄”人物,借他们的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的言行影射社会现实。《审判》与《酒国》都塑造了与传统英雄形象大相径庭的“反英雄”人物。他们怀揣匡扶正义的理想,秉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信念,想单枪匹马地铲除这个世界上的邪恶与不公,但最终却事与愿违,他们陷入无法理喻、无从逃避的罪恶漩涡,一步步走向毁灭。
《审判》的主人公K是一个无具体姓名、无出身背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他却胸怀大志,忧国忧民。被捕后,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代表着像施加给许多人一样的诉讼。我现在在这儿是替那些人来受审的,而不是为我自己。”[6]237在初审现场,他不畏强权,慷慨陈词,谴责司法系统的腐败与法律制度的不公。他开诚布公地指出:法院“滥捕无辜”,其意义在于对民众“施加荒唐的和大多数情况下不了了之的诉讼”[6]239-240。整个审讯过程,K都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强有力地控制了会场,自认为台下的观众都已经被说服,他甚至告诉自己他实际上是在“玩弄”法庭官员。但事实呢?在发表完高谈阔论后,K惊讶地发现,台下在座的观众正是他抨击的贪官污吏。他们的衣领上别着同样的徽章,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当听众和密探。他们表面上分成左右两派,一派沉默不语,另一派为他鼓掌喝彩——“好极了!说得太棒啦!好极了!接着说下去吧!”[6]237他们用这样的伎俩企图摸清K的底细,但实际上是一丘之貉,在“演练怎样去玩弄无辜人上当的鬼把戏”[6]241。K俨然成了一个滑稽的丑角,被法庭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种讥讽、落差的故事情节显现出黑色幽默的特点,在K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影子,既可爱、可敬,又可悲、可叹。
K是一个在逆境中求生存,且为伸张正义顽强拼搏的“英雄”。然而,他生不逢时,在这个善恶不分、黑白颠倒的异化世界里,无论他如何抗争,都无法摆脱被毁灭的命运。K垂死时的表现同样缺乏悲剧英雄的气概。当两个刽子手互相递着屠刀时,K清楚地知道他的职责是“一把夺过刀来,往自己的胸膛里一戳”[6]359。K知道古典悲剧的惯例,高贵的英雄拥抱自己的死亡,但最终他没有这样做。在死亡来临之时,求生的欲望让他想到了宗教。在幻觉中,他“看到灯光一闪亮,那儿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一个人突然从窗户里探出身子,两只手臂伸得老远”,但奈何“他离得那么远,又那么高,看上去又模糊又瘦削。”[6]359K企盼的救赎如同最高法院一样,可望不可即。在卡夫卡这里,人成为被世界、被生活、被上帝所抛弃的绝望的个体。K最终被处以死刑,“一个人的两手已经扼住K的喉头,另一个则把刀深深地戳进了他的心脏里,而且转了两转。K瞪着白眼,又看看近在面前的这两个人彼此脸颊贴着脸颊,紧紧地靠拢在一起,注视着这最后的判决。”[6]360也许,此时的K正体会着卡夫卡曾感受到的欢乐,因为在构思《审判》时,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许久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想象一把刀在我心中转动的欢乐”[7]。这种悖谬的感受是美国学者马修·温斯顿(Matthew Winston)所总结的黑色幽默用以迷惑我们的主要手段之一——在阴郁与幽默、威吓与娱乐、恐怖与滑稽之间迅速切换,让我们无法只对其中的一种情形作出反应。温斯顿认为另外两种主要手段是:呈现似乎是不可能的东西,并保证我们所见到的是事实;不断地改变我们与人物的距离[8]。这些特征在《审判》中均有体现。卡夫卡采用近距离的内部观察法,用冷峻、理智的叙述语调对“行刑”这种反常的、非理性的、梦魇般的场面进行显微式的细致描写。叙述者一本正经地在那里叙述荒诞不经和难以置信的事件,使我们感觉自己处于一个秩序井然、司空见惯的世界。这种近乎超然的叙述态度和白描的手法,外冷内热、悲喜交加的叙事风格,正是利用黑色幽默表现社会残酷与麻木不仁的一种方式。而当人们嘲讽故事中的人物后,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处于与之相同的境遇中,因此,人们是在嘲讽自己。《审判》揭露的正是现代人共同的生存困境。
《酒国》的主人公丁钩儿同《审判》中的K一样,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作者为人物所起的姓名上。莫言赋予他笔下的人物一个看似合理的姓氏“丁”,但与名字组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与“K”一样荒谬滑稽的符号——扑克牌里的“J”。因此,丁钩儿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在非理性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符号性的象征。如同小说中同样荒谬的其他人物的姓名一样,如酒国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刚钻、矮人酒店的掌柜余一尺、酿造学院勾兑专业博士研究生李一斗,卖“肉孩”的父亲金元宝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英雄人物形象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传奇式的理想化人物,他们身强力壮,智勇双全;另一种是侠肝义胆,建立丰功伟业的乱世英豪。丁钩儿显然不具备这些特征。从样貌上看,他长相平平,甚至有些怪异,“体瘦,皮肤黑,眼睛有点抠。……牙齿不整齐”[2]15,长着一颗“硕大的头颅”[2]4。丁钩儿还是一个优柔寡断、亦正亦邪的矛盾体:他与妻子的关系不好不坏,他想和情妇好下去又不想好下去,他对生活既热爱又厌烦,就连他的枪法也不稳定——情绪好时弹无虚发,情绪坏时百发不中。
丁钩儿是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查员,侦查破案是他乐此不倦的唯一一件事。接到上级任务后,他像孤身奋战的英雄一样赶往酒国市调查以金刚钻为首的领导干部“食婴”事件。然而,丁钩儿贪恋美色的本性,让他在侦查案件的道路上遭遇了一道又一道的屏障。不过,他思维的悖论习惯总能让他心安理得地沉迷其中。他坚信自己能将“女人与重任”双肩挑,甚至自欺欺人地认为:“和女孩子鬼混不妨碍履行神圣职责……因为与女孩子鬼混会使头脑清醒。”[2]44面对女性的诱惑,他一边“克制着自己想摸摸她的头发的欲望”,一边“进行着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开脱”[2]45。在赤身裸体的女司机用枪口瞄准他、对他施以性诱惑时,他自诩为“壮烈的英雄”[2]172。除美色外,酒是另一个让丁钩儿迷失自我的因素,酒也是小说《酒国》的一个核心意象。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酒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且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载体。在文化领域,酒更是超越了自身的价值,成为塑造英雄形象必备的媒介之一。这样的例子在描写传统英雄人物的扛鼎之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俯拾皆是,如“关公温酒斩华雄”“武行者醉打孔亮”等。莫言在几年前创作的《红高粱家族》中对酒文化也是大加赞赏,酒是高密人民昂扬的斗争精神与狂放的民族气节的象征。然而,在《酒国》中,酒成了万恶之源,助长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导致故事中的人物精神颓废,道德泯灭、良知与理性丧失,而酒场则成为罪恶与腐败的交易场所。在酒精的麻痹作用下,丁钩儿丑态百出,“像只怯水的小狗一样趴在桦木堆上”[2]22,“脖子像根晒蔫了的蒜薹一样软绵绵的……头颅挂在胸前悠来荡去”[2]91。丁钩儿富有人道主义精神,追求正义与真理,“让一切不正义的,不人道地在我的枪声中颤抖”[2]85是他的座右铭。但是,酗酒让他精神错乱,是非不分,作为社会正义象征的枪,却成了他屡屡犯下罪行的凶器。
在小说中,丁钩儿一共开过四次枪,第一次开枪是为了恐吓迟迟不开大门的矿场守门人,以达到炫耀自己高级侦查员身份的目的;第二次开枪本意是想惩治以金刚钻为首的吃婴恶魔,却阴差阳错地击落了红烧男婴的头颅,最后还一起享用这道被誉为“麒麟送子”的美食;第三次开枪杀死了自己的情妇与情敌,以泄私愤;最后一次开枪本意是为了驱赶啃食老革命尸体的老鼠,却“把老革命的脸打得千疮百孔,像筛子底儿一样”[2]326,这也让他糊里糊涂地成了杀害老革命的嫌疑犯。在面临死亡威胁时,丁钩儿同《审判》中的K一样,想得到神灵的庇佑,他躲入娘娘庙。但在这里,他又一次因为自己的“英雄”行为——教训一个戏弄女香客的小和尚,被人误解为调戏小尼姑的流氓,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最后,丁钩儿在逃亡的过程中,竟莫名其妙地落入茅坑溺亡。侦查员丁钩儿从起初的斗志昂扬的正义英雄一步步沦为杀人嫌疑犯,最终走向死亡。这是一个英雄逐渐消逝的过程,是黑色幽默小说中惯用的“反英雄”人物模式。
(二)对文本意义的消解
在黑色幽默文学中,意义是无意义的。黑色幽默作品呈现的世界本质是荒谬的,其思想基础是非理性的,因而作品中人物采取的行动是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说,其自身的存在就是一种错误。
《审判》中的银行襄理K,工作认真,待人和善,未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却在30岁生日当天突遭逮捕。他不知道自己被何人所控告,也不知道自己所涉罪名是什么。但为了自救,也为了寻找真相,他不得不四处奔走,八方求助。在卡夫卡的笔下,逻辑被完全颠倒了,不是错误受到惩罚,而是惩罚后寻找错误,“受罚者不知道惩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性难以忍受,致使被告者为了获得安宁,总想给自己的痛苦找到一个说明。”[9]100由于K是无辜的(虽然有学者从道德、人性、宗教等角度阐释了K的罪行[10-12],但从法律上看,他是无罪的),因此,尝试寻找罪过、洗脱罪名的努力都是无意义的。
在《审判》中,法院机构的存在本身也是无意义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法院的设置场所荒谬离奇。法院不是一幢能体现法律权威的庄严神圣的建筑,而是像迷宫一样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有的坐落于市郊的贫民窟里,有的则穿插在居民楼的阁楼上。法院内部空气污浊,嘈杂不堪,这样的法院连正常的工作职能都履行不了,更别提维护公平正义了。第二,法院的运行规则不可理喻。正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言:“在卡夫卡那里,机关是一个服从它自己的法则的机械装置,那些法则不知是由什么人什么时候制定,它们与人的利益毫无关系,因而让人无法理解。”[9]98-99从表面上看,法院的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但实则是“有组织的混乱”。每一级法官都被限制在自己的工作环节上,他们互不通气,不知道案件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案件下一步该呈交何处,他们对整体的“法”一无所知。第三,法院的裁决书不对外公开,就连被告也无从获悉。K最后被两个黑衣人带到市郊的采石场秘密处决,他至死也没弄明白自己所犯的罪行。更离奇的是,法院的最终裁决权只由最高法院掌握,而最高法院是任何人都无法接近的。K至死仍未弄明白,他从未谋面的法官在哪里?他从未踏入的高级法院又在哪里?显然,这是一种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悖论逻辑,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正因如此,昆德拉认为,处境的陷阱吸走了K的“全部思想和全部感情”,使K失去了灵魂,“只能去想自己的审判”[9]7。同“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最高法院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圈套,象征的是无所不在而又统治世界的神秘力量。它不制定法律条文,但它却无所不包。最高法院的缺席使世界显现出一种可怕的模糊,原有的价值体系分崩离析,从此世界陷入“制度化了的疯狂”之中,人类只能束手就擒,时刻准备接受被毁灭的命运。因此,昆德拉说,卡夫卡在这种“无法生存的状况”中发现了一种“奇异的黑色的美”[9]118,他的作品“粗暴地将一切的无意义揭示给我们”[9]121。
从故事情节看,《酒国》本应归为侦探小说,而莫言完全颠覆了侦探小说的严谨性,其叙述逻辑混乱,语言含糊,而且不断设置疑云迷雾,事件的真相并未随着情节的推进层层剥开,而是愈加复杂,最终也没有出现传统侦探小说“水落石出”的大结局。小说里描述的“食婴”事件扑朔迷离,亦真亦幻。莫言采用模棱两可的语调描写“麒麟送子”这道名菜。当大盘里的男孩被枪打掉了脑袋后,“像西瓜皮一样的脑壳或者像脑壳一样的西瓜皮架在一盘扒海参和一盆红烧虾之间,汁液滴滴答答,流着血一样的西瓜汁或者是西瓜汁一样的血……”[2]86。菜肴制作得栩栩如生,真假难辨。“食婴”事件是真是假?莫言自始至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作者有时认定烹食的就是婴孩——“我听到儿童们在蒸笼里啼哭,在油锅里啼哭。”[2]84——但有时又推翻自己之前的判定——“这是男孩的腿,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火腿肠。男孩的身躯,是在一只烤乳猪的基础上特别加工而成……”[2]88。莫言描写的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语言被彻底瓦解,成为被剔除了意义的空壳,因此,真与假、是与非、现实与非现实已无从分辨,由此导致“有罪”与“无罪”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不清。整部小说的主线是侦查员丁钩儿奉命调查酒国市领导“食婴”事件,但既然“食婴”事件无法得到证实,酒国市领导“食婴”的罪名也就无法成立,丁钩儿所有的侦查行为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虽然丁钩儿对“食婴”事件深信不疑,并锲而不舍地查找证据,想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然而,从前文分析可知,丁钩儿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完美的英雄人物,他立场不坚定,人品难以让人信服,且沉迷酒色这一嗜好让他频频产生幻觉。小说中有多处描写他嗜酒后肉体与灵魂分离的现象,因此,他的所见所闻令人生疑,失去了可信度。丁钩儿最后落入茅坑溺亡的悲惨结局,是小说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黑色幽默。丁钩儿认为自己具有的“理想、正义、尊严、荣誉、爱情等等诸多神圣的东西”[2]329瞬间化为乌有,案件调查也戛然而止,真相再也无从查清,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可以说,整个调查事件就是一场无厘头的闹剧,调查的结果也是无据可依的谬论,甚至连丁钩儿的存在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丁钩儿与K的故事一样,以悖谬的方式瓦解了社会正义的意义,凸显出某种无法理解的异化力量对人类命运的控制。面对没有出路、没有选择的绝对荒诞,人类只有借助幽默使绝望和痛苦得以宣泄。然而,在阴森的笑容背后,人类感受到的是愈发强烈的沉重与苦闷。
二、不同的黑色幽默书写方式:“出世”与“入世”
虽然莫言与卡夫卡的小说在技巧层面上都凸显了黑色幽默的特点,但两者却有着质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两者不同的书写方式上。
(一)《审判》——道家思想影响下的“出世”之作
卡夫卡对世俗之事漠不关心,而是沉醉于自己构建的文学殿堂中。他所幻想的世界似乎没有受到风云变幻的近代历史的触动。发生于20世纪初、决定欧洲命运的诸多重大事件在卡夫卡看来微不足道,他的书信和日记均未对它们给予足够的重视。面对“一战”全面爆发这样的大事件,他仅在1914年8月2日的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德国已经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学校。”[13]而1918年10月28日导致捷克共和国诞生的奥匈帝国的崩溃他却只字未提。卡夫卡这种“出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卡夫卡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尤其被老庄思想所陶醉。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常年摆放着老子的《道德经》与庄子的《南华经》,他反复研读这些书籍,并视其为“一笔巨大的财富”与“真理”[14]。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道”是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又是人们的行为准则,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5]45-46。老庄的哲学思想体现为“无为、好静、无事、无欲”[15]106,与世无争,顺其自然。“出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对现实、对政治的无声反抗。
卡夫卡对道家思想了然于心,他知道:要深入这个世界,必先走出这个世界。《审判》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超现实的、梦魇般的世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正常的,虽然从形式上看,卡夫卡构筑的法院体系貌似合理:有被告、律师、法官、案卷、庭审、判决等等,但这一切都夸张得变了形,与现实相去甚远。有学者用“梦境现实主义”[16]444一词来评价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小说中的法院机构笼罩在一股如梦如幻的神秘氛围中,其运行遵循的也是“梦境逻辑”[16]444,所有事情都缺乏动机与解释,人类的困境也因此变得迂回曲折,不可名状。卡夫卡所提出的这种控制人类命运的神秘力量,与道家思想的核心“道”是密切相关的。虽然两者都是虚构的概念,却真实地描绘出人类的生存境遇。这种神秘力量与“道”无处不在,是神秘的权威,是控制人类命运的各种无形的规则。梦幻世界的构筑体现出卡夫卡的黑色幽默观是一种从安全距离外投射的观点,他站在尘世之外,以局外人的身份去审视他所讥笑的不可救药的世界。“出世”是卡夫卡的处世原则,是他超越世俗的情怀与独立自由精神的体现。
(二)《酒国》——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入世”之作
莫言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怀有更多的积极的“入世”情结。如有学者指出,莫言的创作“生发于乡村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观念”[17]。莫言也曾在《我的父亲》一文中,将自己取得的成绩归功于“父亲的威严震撼”,他指出,“父亲的威严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的”[18]。不同于卡夫卡对于世事冷酷无情的态度,莫言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且情感很易触动,一如《论语》中的孔子,“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19]。萌芽于战乱的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肩负着拯救国家与人民的使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表达出儒家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与责任担当。正是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莫言怀有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怀。尤其作为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作家代表,莫言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的探讨中,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勇于干预现实的“问题小说”家。莫言的作品中有种“忧郁的调子”,究其根源,他认为是自己“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忧虑”,例如“高道德标准沦落问题”。
《酒国》颠覆了传统侦探小说的英雄神话,侦查员丁钩儿在酒色的诱惑下一步步地堕落为食婴的同谋,杀人嫌疑犯,这体现的是物欲横流、恶势力泛滥的社会对人性的摧残。除丁钩儿这个小人物外,小说中有权有势的贪官污吏们同样是被扭曲的酒文化毒害的牺牲品。因此,莫言认为,他的同情“不仅仅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而更多的是对所谓的强势群体的同情”[20]。他在《酒国》后记中,亦对小说中的几位小官吏表示了理解与宽容。他写道:“假若把我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会跟他们一样。”[2]366《酒国》出版于1993年,此时正值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但随之而来也有各种社会问题,官场腐败、权钱交易、奢靡成风。同年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将“惩治腐败和勤政廉政建设”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莫言通过“对酒文化的反讽和批判”[21],引导国民抵制腐败,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当然,《酒国》的批判精神不止如此,如有学者指出,《酒国》“直接指向数千年来国民性的愚昧与麻木”[22],另有学者认为,“莫言超前地看到了一个经济主义时代来临的巨大隐患,即放纵物欲追逐带来的社会全面腐败”[23]。可见,《酒国》是一部关乎人类历史、现在与未来的作品。莫言讲述的是中国本土的故事,但他揭示的是人类生活的真相和规律,他“站在人类的高度”[24],抒发的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切,以及拯救苍生的济世之志。
三、结语
虽然在技巧层面上,莫言与卡夫卡的黑色幽默风格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如“反英雄”人物的塑造、对文本意义的消解等。但从书写方式上看,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也体现出作家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追求。卡夫卡特立独行的个性,让他更倾向于“形而上的书写”,他向世人展示的是虚幻空灵的“出世”之作;而莫言侧重于“历史的书写”,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如“酒文化”“食文化”,以及特定历史背景下被摧残的人性,从而展示乡土中国的历史和命运。《酒国》与《审判》是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渗透、转换、变形的模板,莫言立足本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在民族风格和西方文学风格之间寻找契合点,从而让中国的声音进入西方读者的内心,让其文学得到世界的接受与认可,为中国文学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取得了更大的话语权,进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