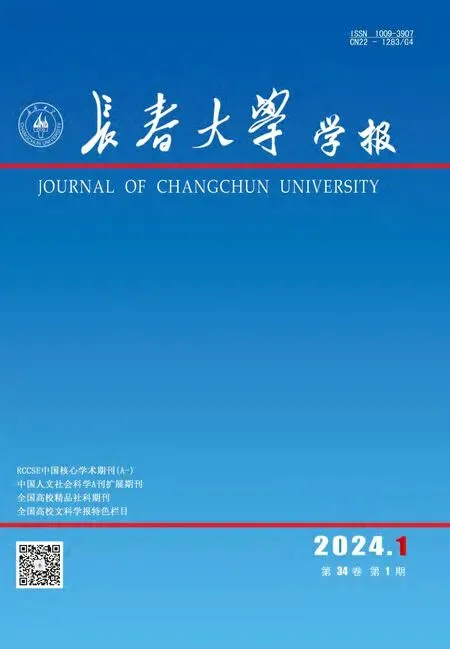《西厢记》唱词的文学性英译研究
余静良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武汉430074)
《西厢记》为元代戏曲作家王实甫创作的杂剧。该剧一经问世,便吸引了无数读者,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我国著名作家郭沫若盛赞此剧为“有永恒而且普遍生命力的伟大艺术品”。
《西厢记》文采璀璨,语言艳丽典雅,音韵谐婉动听,颇具诗剧风格,极富文学性、诗学价值与艺术价值。该剧语言的华丽秀美主要体现在其唱词语言上。我国著名剧作家、翻译家熊式一认为,“《西厢记》中的唱词具有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1]。英国学者G. Bottomley在《西厢记》译本序言中指出,《西厢记》中出现的大篇幅的唱词在英国可能被认为是“文学的”“非戏剧的”[2]。《西厢记》唱词饱含中国古典诗词的经典语句,或为对古诗词的恰切改写,或为对典故的熟练运用与深刻阐释。王实甫通过唱词的人物对话,运用和谐对称的韵律,使用丰富的修辞手法,展现出原剧的诗歌韵律节奏,建构出崔莺莺、张生、红娘及老夫人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凸显了各人物丰赡的思想情感,揭示了反对封建礼教和追求自由爱情的主题,进而彰显出戏剧的主题张力。
从现有成果来看,《西厢记》英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译本的比读分析、英译策略与方法的探讨等,研究视角大多聚焦于翻译美学等领域,而针对其自身的文学性开展相关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西厢记》文学魅力的真实呈现。鉴于此,本研究将立足西方诗学理论,从《西厢记》唱词的情感再现、形象建构与主题张力三大层面出发,详细探究许渊冲译本、奚如谷和伊维德译本及熊式一译本唱词的文学性,细致梳理三大译本在唱词文学性英译上的优劣,并尝试给出个人新译,以期在译本中再现唱词的文学性,凸显《西厢记》的文学魅力和诗学价值,丰富《西厢记》英译的研究成果,为其英译乃至中国古典戏剧英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野,从而不断促进中国古典戏剧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一、文学性内涵阐释
文学性是现代西方诗学理论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由布拉格学派创始人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于1921年在《俄国新诗歌》中首次提出。雅各布森认为,“文学研究的主题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3]。
纵观历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为作为独立学科的诗学确立了名称与方法,并认为,文学性可被视为“unfamiliar words(不常见的词)所呈现出的诗学效果”[4]。进入20世纪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及文学结构主义方兴未艾。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y)提出了陌生化(又译为“反常化”)技法,即“使事物变得‘不熟悉’,使形式变得困难,加大感知的难度和长度”[5]。其认为,作品通过陌生化技法产生的陌生化效果是文学性的基础。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穆卡洛夫斯基(Mukarovsky)提出“前景化”的理论,并指出,“前景化是自动化的对立……是对程序的违背,强调文学作品中变异的一面”[6]。“不常见”“前景化”“去自动化”等术语皆为穆卡洛夫斯基对文学性的形象概括。20世纪初,英美新批评异军突起。其中,领军人物艾伦·退特(Allen Tate)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张力”。他认为,“一首诗的突出的性质就是诗的整体效果,而这整体就是意义构造的产物”[7]。实际上,此处的整体意义构造就是文学性,即“张力”。在托多罗夫看来,结构主义诗学关注的是一种抽象的特征,其研究对象为文学性[8]。同时,英国文体学家利奇(Geoffrey Leech)提出了“变异”的概念,并将其分为主变异、次变异与第三变异[9],这对深入挖掘文学性的内涵做出了新的贡献。
以上种种阐释皆丰富了文学性的底蕴。然而,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绝非囿于以上几种形式,例如韵律、情感、形象和张力等都是作品文学性的彰显。简言之,文学性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是作家通过陌生化技法展现出的陌生化效果。而这种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文学性。可见,陌生化是文学性的基础和必然要求。而探索作品陌生化与文学性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艺术张力与感染力,使得读者获得审美上的持续愉悦。因此,作为审美的主体,译者应当具备高度的敏感力和敏锐的洞察力,熟练运用陌生化技法,深入挖掘原作的陌生化效果,竭力感知作品的审美特质,于译作中凸显其审美意趣与审美价值,从而彰显出原作的文学性与艺术价值。
本文将基于西方诗学理论,从《西厢记》唱词的情感再现、形象建构与主题张力三大层面出发,详细梳理《西厢记》三大译本唱词的文学性,细致探究各译本在唱词文学性英译上的优劣,并给出个人新译,旨在于译本中再现唱词的文学性,凸显《西厢记》的诗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二、《西厢记》唱词的文学性英译探微
(一)情感再现
文学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环,是推进中国文化以平等姿态同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文学翻译的核心标志便是“情”。情乃文学作品的灵魂,是其所具有的独特艺术价值。情感再现可谓文学翻译的首要任务。作为坐拥“元曲压卷之作”等美誉的《西厢记》,其辞藻华丽,诗意盎然;人物形象跃然纸上,饱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因此,如何于译文中再现原剧各人物丰赡的思想情感便成为了评判译本质量高低的关键因素。兹举如下一例,对各家译本的情感再现进行探讨:
原文:碧云天,
黄花地,
西风紧,
北雁南飞。
晓来谁染霜林醉?
总是离人泪![10]123
许译本:With clouds the sky turns grey
O’er yellow-bloom-paved way.
How bitter blows the western breeze!
From north to south fly the wild geese.
Why like wine-flushed face is frosted forest red?
It’s dyed in tears the parting lovers shed.[11]351
奚和伊译本:A sky azure and clouded,
An earth flowered yellow;
The western wind is stiff,northern geese fly southward.
At dawn what dyes the frosted woods the flush of drunkenness?
It will ever be the tears of separated lovers.[12]239
熊译本:Grey are the clouds in the sky and faded are the leaves on the ground,
Bitter is the west wind as the wild geese fly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How is it that in the morning the white-frosted trees are dyed as red as a wine-flushed face?
It must have been caused by the tears of those who are about to be separated.[13]191
原文唱词共分为六句。前两句是化用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诗词“碧云天,黄叶地”,最后一句同样是借鉴北宋词人曹祖的词句“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总是离人泪”。作者通过借用宋词,采用“碧云”、“黄花”、“西风”及“北雁南飞”等萧瑟的意象,传递出莺莺和张生的离愁别恨。此外,原文极为讲究工整对仗,如“碧”与“黄”、“云”与“花”、“天”与“地”、“北”与“南”。可见,该唱词通过化用中国古典诗词,采用诗歌常用的对仗和押韵手法,增强了原文的诗意,呈现出原剧的诗学效果,表达出莺莺十里长亭送别的悲伤与不舍之情。
对比分析许译本、奚和伊译本及熊译本发现:首先,许译本用词短促,铿锵有力,使用With clouds...,O’er...等短语,和原文“碧云天”、“黄花地”等三字格形成呼应。许译本不仅再现了原剧中莺莺和张生离别时的伤感、惆怅与不舍之情,且通过使用grey,way、breeze,geese及red,shed等排韵的形式,与原文中的“飞”、“醉”、“泪”排韵形成互文。反观奚和伊译本,其仅有clouded与southward、drunkenness与lovers两处使用了尾句押韵;同时,熊译本也仅有两处运用了押尾韵,分别为ground与separated、south与face。可见,许译本对于原剧唱词韵律的再现程度明显高于奚和伊译本与熊译本。其次,许译本的“妙译”之处还体现在对于原文唱词工整对仗的还原。例如,原文中“碧”与“黄”、“云”与“花”、“天”与“地”等形成对仗,“飞”、“醉”与“泪”互为押韵。许译本注意到了原剧唱词“工整对仗”的特点,采用bitter、 blows、 breeze,from、 fly,why、 wine-,-flush、 face、 frosted、 forest等押头韵与原文中的“碧”与“黄”等对仗形成互文。而奚和伊译本虽有western、 wind,stiff、 southward,dawn、 dyes和frosted、 flush四处使用了押头韵的手法,但连续押头韵词数明显低于许译本,且中间常有其他词阻隔。上述押头韵词汇中出现的阻碍不仅会使唱词节奏有所放缓,甚至会破坏、消解原剧唱词整体节奏的艺术表现力和美学效果,从而无法完整再现莺莺与张生离别时的苦楚与不舍之情。同时,熊译本也仅有west、 wind、 wild,fly、 from与-flushed、 face三处押头韵,且连续押头韵词数不及许译本。
综上,在整体节奏上,许译本更加符合原剧唱词简洁、短促的特点;在韵律层面上,许译本更加倾向使用排韵对应原文中的尾句押韵;在工整对仗方面,许译本则别出心裁地运用押头韵对应原文唱词的对仗和押韵。相较于奚和伊译本、熊译本使用长句、少韵的特点,许译本短促有力,对仗工整,“韵”味十足,深刻阐明和再现了莺莺与张生离别时的不舍、悲伤和苦楚,彰显出原剧唱词的文学性与诗学效果,堪称妙译。
(二)形象建构
《西厢记》唱词语言华丽典雅,顿挫抑扬。作者凭借其华美的语言,于剧中建构出不少鲜活的人物形象,如痴情的张生、聪明美丽的崔莺莺及勇敢机智的红娘。这些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跃然纸上。
其中,红娘的形象尤为突出,惹人喜爱。为了全面塑造立体与生动的红娘形象,王实甫于《西厢记》第四本专门设立第二折《拷艳》。该折名“拷艳”使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既有拷问红娘之意,又含“考验”红娘智慧及莺莺、张生之间爱情之旨。正因得益于作者的精心铺陈和细致叙述,红娘的形象才能显得如此逼真,从而赋予《西厢记》更多的文学性、诗学特征与艺术价值。然而,由于译者文化背景、语言风格迥异,其所秉持的翻译思想有所不同,采用的翻译策略也不尽相同。因此,各译本对红娘形象的建构与再现程度各不相同,对唱词文学性的传递亦有所差别。且看下例各译本:
原文:他们不识忧,
不识愁,
一双心意两相投。
夫人你得好休,
便好休,
其间何必苦追求?
常言道:“女大不中留。”[10]119
许译本:They know neither grief nor sorrow;
They know today but not tomorrow.
They love each other soul and heart;
They cannot bear to be torn apart.
My Mistress,overlook the matter if you can.
This is not an affair for you to probe or scan.[11]335
奚和伊译本:They don’t recognize grief,don’t recognize sorrow;
Their paired hearts are a perfect fit.
Madam,you’d better stop when it’s right to stop.
Why must you suffer now to trace down every clue?
The proverb says,“A girl grown up should not be kept.”[12]87
熊译本:They both know not grief nor sorrow,
Being devoted to each other in heart and soul!
My Mistress,do overlook the matter if you can!
Why should you probe into it too deeply?[13]182-183
从上述红娘唱词可知,作者通过使用排比与对仗的修辞手法,利用句句押尾韵的韵律节奏,引用民间俗语,辅以反问句的语气,于字里行间塑造出了聪明伶俐、机智勇敢、富有同情心的红娘形象。
三大译本中,许译本和熊译本均以清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批本《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为底本翻译而成,而奚和伊译本则参照明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金台岳家书坊所刊刻的《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诠释西厢记》翻译成书。事实上,金圣叹在其批本中对原剧的唱词作了大量删改,而唯有明弘治本才是最早、最完整的版本。虽金批本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最受欢迎,但从忠实于原剧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明弘治本更胜一筹。
仔细分析发现,首先,许译本和熊译本均出现了漏译现象,遗漏了金批本删减的唱词“常言道:‘女大不中留’”,译文的完整性大打折扣,对红娘形象的建构亦有所消解。而由于奚和伊译本参照的是明弘治本,因此,奚如谷和伊维德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对该句唱词进行了翻译,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完善了红娘的形象。其次,由于许渊冲秉持“三美论”的翻译理论和“充分发挥译语优势”的翻译观,欲于译文中延续原文唱词的“柏梁体”,深度还原原文句句尾句押韵的诗学特征,因而在译文第一句较为完整传递原文“不识忧愁”内涵的前提下,无故增添第二句译文,只为让第二句末尾的tomorrow与第一句结尾的sorrow互为押韵。然而,这却使得该译文过于冗长,故而产生了过度增译、因韵害意的问题。同理,第三句译文最后的soul and heart亦为对英语中固定表达heart and soul的错误改写,仅旨在与第四句译文末尾的apart一词形成押韵,因而也出现了因韵害意的现象。同时,第四句译文也是因译者无故增译而产生,故亦属于过度增译、因韵害意。在文学翻译过程中,适当押韵无伤大雅,但倘若为了趁韵而过度增译或减译,最终导致原文文学性和审美特质有所损失,便是得不偿失且不可取的。正如汉学家、翻译家伊维德先生所言:“我不反对译文中偶尔出现押韵,但是如果刻意通篇押韵的话,最后的翻译只能变成一种释意或者改写。”[14]最后,虽然奚和伊译本是依据明弘治本翻译而成,译文问题明显少于许译本和熊译本,但仍存在过于直译、译文表达非译入语地道表达等问题。例如,奚如谷和伊维德直接将该段第一句和第二句唱词“他们不识忧,不识愁”直译为They don’t recognize grief,don’t recognize sorrow,遵循了奚如谷和伊维德两位汉学家“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思想。但很明显,该句译文过于繁杂和冗长,并不符合英语地道的表达法。鉴于此,可以尝试用neither...nor...的固定搭配,将此译文改译为They know neither grief nor sorrow。
基于上述例析,不难发现,三家译本在陌生化再现、文学性传递及形象建构层面皆有尚待提升的空间。因此,笔者尝试将该段唱词改译如下:
They know neither grief nor sorrow;
Their paired hearts are well prepared for tomorrow.
Madam,overlook the matter if you can.
Why must you trace down every clue now?
As the proverb goes,“A girl grown up should not be kept home like a fowl.”
与旧译本相比,改译后的新译本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表达更为地道。新译第一句通过运用归化的翻译策略,采用neither...nor...的地道、简洁表达,避免了译文的冗长和臃肿,使得译文更为流畅,更加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表达习惯。第二,韵律更为和谐。改译后的新译本在避免出现“过度增译、因韵害意”现象的前提下,保留许译本中sorrow与tomorrow的尾韵,于最后两句译文增添了now和fowl,形成尾句押韵,使得新译本既恪守了“忠实于原文”的原则,又保留了原文唱词劝说的语气与和谐的韵律。第三,陌生化程度更高。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认为,译文应该保留源语文本的陌生化表现手法[15]。新译本一改旧译本归化的风格,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最大程度还原原文唱词的陌生化和文学性。例如,新译本运用As the proverb goes等表达,外加比喻的修辞手法,将原文中的俗语直译为“A girl grown up should not be kept home like a fowl”,产生了一种基于西方文化、英语读者及其话语语境陌生的表达,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原文唱词的陌生化,使读者不由自主地思考此处比喻修辞的用意,延长了其审美阅读时间,进而散发出唱词所独有的文学与诗学魅力。第四,文学性更足。陌生化作为翻译的重要审美特质,是文学性获得连绵不绝的生命活力之源泉,也是审美者获得新奇美感享受的动力。新译在采上述三家译本之长的基础上,运用直译的翻译方法,使得新译对于读者来说更为陌生化和前景化。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新译再现了原文的陌生化,揭示了译文自身的美学特质,从而不断赋予译文更为丰厚的文学性与艺术价值。可见,新译对唱词文学性的再现有利于原作文学魅力与艺术价值的彰显,进而让译入语读者感知《西厢记》文本的异域性和新奇性,体验来自中国文化的“异国情调”。第五,形象更丰满。纵观上述三大译本,许译本最后一句的弦外之音为“张生与莺莺的事不关你的事”,显然不符合老夫人在丈夫崔相国离世后身为一家之主、封建家长的身份,更有违老夫人和红娘间的主仆关系。同时,熊译本于第二、第三句末尾使用了感叹号,在最后一句结尾处使用了问号,仿佛昭示着红娘在命令和质疑老夫人。这很明显也与老夫人、红娘的身份地位不相符。此外,奚和伊译本第三句中的you’d better为劝说型口吻,与红娘勇敢和大胆的形象亦背道而驰。鉴于此,新译分别在第三句和第四句运用了祈使句和疑问句,不仅保留了原文唱词的句型,还较好还原了大胆、机智与富有同情心的红娘形象,从而传达了原文的文学性,赋予了新译更多的文学魅力和诗学价值。
(三)主题张力
张力(tension)是现代诗歌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起源于英美新批评学派,最早由美国学者艾伦·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提出。退特认为,诗的张力即为“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换言之,张力就是诗歌或文学作品的整体意义与艺术效果,是其精神内容、审美特征和想象空间的有机融合。一首诗或一部文学作品若缺乏张力,必然会影响其审美意义的阐发和诗学价值的再现。因此,基于《西厢记》唱词的整体意义、审美特征与诗学效果,兹举如下一例,对《西厢记》唱词的主题张力所蕴含的文学性及其英译进行探究。
原文: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10]165
许译本:May lovers’ neath the skies
Be united for ever and ever![11]485
奚和伊译本:May lovers of the whole world all be thus united in wedlock![12]285
熊译本:And we hope that all lovers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happily married.[13]269
该句唱词虽短小精悍,字数不多,但却有力地道出了当时青年男女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心声,表达了他们对自由恋爱和婚姻的憧憬。作者以此句唱词作为全剧的结尾,不仅印证了中国古典戏剧大多数以“大团圆”作为结局,且呼应了本剧的主题,即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婚姻制度,追求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并倡导男女婚姻应以琴瑟和鸣、两情相悦为基础。无怪乎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对此句唱词点评道:“结句实乃妙妙!”[16]
纵观三家译本,均凸显了原剧的主题,但在张力和文学性再现层面上却各有差异。许译本、奚和伊译本均选择用May作为祝福语句的开头,但许译本将原文译为两句唱词,并于第二句ever and ever处使用重复的修辞手法,增强了唱词语气,强调全天下有情人都应当永远在一起,强化了原剧主题,凸显出唱词的艺术张力与诗学特征,从而彰显出原剧唱词的文学性和诗学价值。然而,遗憾的是,许渊冲误将“眷属”一词译为be united for ever and ever,并未意识到“眷属”一词意为“家眷、亲属或夫妻”,而be united for ever and ever回应译文应为“永不分离”,二者不能完全画等号。相比之下,奚和伊译本则更为精准。奚如谷和伊维德将“眷属”译为较为准确的be thus united in wedlock,突出了原文唱词“结为连理”的内涵。但奚和伊译本在呈现原剧主题张力和文学性层面稍逊色于许译本,尚待提升。同时,由于译者熊式一“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思想,因此,其选择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毫无保留地翻译原文唱词,进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原剧的主题张力和文学性。
三、结语
《西厢记》叙事宏大,文笔不凡,意境优美,极富诗情画意。其主题明确,情节此起彼伏,人物栩栩如生,“蕴藏着深厚的文学性与诗学功能”[17],颇具诗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因此,《西厢记》素有“天下夺魁”等美称,被誉为中国古典戏剧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金圣叹曾给予该剧高度评价,认为其一经问世,便成为“世间妙文,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并将其誉为“第六才子书”。
《西厢记》唱词语言凝练优美、晓畅自然;辞藻艳丽、雅俗共赏;韵律和谐、诗意盎然;饱含着深厚的文学性与诗学魅力,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本研究基于西方诗学理论,从《西厢记》唱词的情感再现、形象建构与主题张力三大层面出发,详细探究了许渊冲译本、奚如谷和伊维德译本及熊式一译本唱词的文学性,初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情感再现上,与奚和伊译本、熊译本相比,许译本深度还原了原文唱词的秀美辞藻和句式的工整对仗。其运用排韵、押头韵和尾句押韵等手法,再现了原文唱词的和谐与富有诗意的韵律节奏,进而传递出莺莺与张生离别时的不舍、悲伤之情。其次,在形象建构上,许译本和熊译本均出现了漏译现象,许译本还存在过度增译、因韵害意的问题;奚和伊译本虽不存在上述错误,但仍出现了过于直译、表达不够地道等问题。鉴于此,笔者提出了个人新译。新译凭借表达更为地道、韵律更为和谐、陌生化程度更高、文学性更足与形象更丰满的特点,重构了红娘大胆、机智及富有同情心的形象,从而传递出原文唱词的文学性和诗学价值。最后,在主题张力上,三大译本均凸显了原剧的主题。但在文学性和艺术张力层面,许译本的再现程度要明显高于奚和伊译本及熊译本。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经典对外译介与传播的浪潮中,中国典籍的文学魅力和艺术价值能否得以彰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学性是否得到忠实再现与传达。换言之,“译文学,就得关注文学性”[18],因为“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学性的翻译”[19]。因此,译者应当充分发挥主体性与译语优势,增强自我陌生化手法辨识能力和文学性表达能力。在尊重原作与避免出现“因韵害意”问题的基础上,恰当运用“韵律式”写作手法,辅以修辞、用典;或夯实自身诗学识别和表达能力,时刻关注陌生化的文学性语言特质,以反常对反常,从而不断再现原作的诗学意蕴,提高读者的审美愉悦;或利用互文性理论,与原作形成互文参照,进而传递出其所蕴含的文学性、诗学魅力和艺术价值。这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学以更‘文学’的姿态同世界展开对话”[20],对提升中国古典戏剧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度和认可度、真正为中国典籍文化“走出去”提供恰切的路径和方法亦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