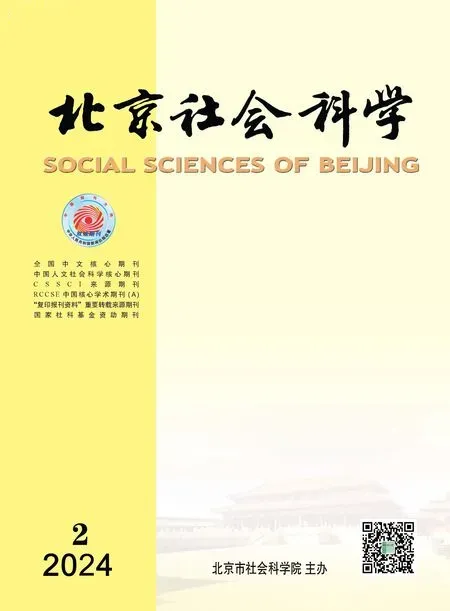“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
——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连 凡
一、引言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胡适是目前已知最早使用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英文最早出现在19世纪)概念的中国学者。胡适的学生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也使用了这一概念,并在回国后将其翻译成中文“新儒家(学)”。后来,卜德(Derk Bodde)翻译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时又使用了“Neo-Confucian(ism)”概念,从而促进了这一概念的传播。以上是从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到中文“新儒家(学)”概念的流传过程的大致描述。但对在此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冯友兰,学界往往只注意到其最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等著作及其翻译,而忽视了冯友兰早年留学期间及回国后头几年的学术经历及论著。刘述先与蔡仲德等人虽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但还不够全面细致,遗漏了很多细节,也没有结合时代思潮背景及冯友兰的学术历程深入挖掘其原因,这也导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冯友兰与“Neo-Confucian(ism)”概念的关系以及这一概念在现代学术界的流传与阐发过程。[1-5]
本文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线索,首先考察冯氏早年对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使用与阐发,进而探讨冯氏首创的中文“新儒家(学)”概念的流传及其阐发,在此基础上探讨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用“道学”概念取代“新儒学”概念的过程及其原因,并阐明“Neo-Confucian(ism)”及“新儒家(学)”概念在当时学术界的通行。
二、冯友兰留学期间对“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使用与阐发
冯友兰1919年底抵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不久在1920年1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在图书馆看到《一元论者》(TheMonist)杂志上刊载的一篇题为“《科学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Science)的论文,并想要将其翻译出来。[6-7]这反映了冯友兰在胡适的影响下,重视西方科学逻辑方法的学习,并试图在此基础上研究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8]同时,这也与1915年至1927年国内兴起的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密切相关。当时,文化保守主义者大体上延续了清末“中体西用”及复归原始儒家(孔教)的思路,认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华文明没有像西方文明那样发展出科学(物质文明)。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反传统主义者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及“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主张在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领域清算传统和学习西方。冯友兰虽然在1918年就已经从北大毕业回到河南开封,但在1919年与友人一起创办了《心声》杂志以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冯友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试图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从哲学内在发展脉络中找到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根源。这便是冯友兰自述其哲学研究生涯的起点。[7]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冯友兰在1920冬天写成题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的论文。[9]随后1921年秋天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讨论会上宣读了该论文。该文于1922年4月发表在《国际伦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JournalofEthics)32卷3号上。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在该文中共六次使用“Neo-Confucianism”概念,用来指称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宋明新儒家。冯友兰指出:“(《大学》)寥寥数语,将儒家的生活目的和方法,论列无遗,令人赞叹。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下同)的哲学家选出这些章节,在理解时不自觉地羼入了佛老思想。他们不同于原来的儒家,就在于提出了他们所谓的‘天理’,以反对‘人欲’,这些概念实际上是受了佛家的‘法’和‘无明’等观念的启示,在此之前一直无人多加谈论。真正的儒家,如前面所说,是认为人性虽善,其善则不过是个萌芽,或用孟子的话说,是个‘端’,还要大力培养、发展、完成它。可是按新儒家所说,天理早已是、永远是完全的,虽为人欲所蔽,只要清除了这些人欲,真正的心灵就会如钻石一般自放光芒。这很像老子所说的‘损’。不过新儒家还是与佛老根本不同,而且掊击佛老,极其激烈。它认为,为了‘损’去人欲,恢复天理,人并不需要保持一种完全否定生活的状态。他所需要的是按照天理来生活,而且只有在生活中天理才能够充分实现。”[10]在这段文字之前,冯友兰引用了《大学》原文,接着就指出宋代新儒家在诠释《大学》时不自觉地掺入了佛老思想。朱熹在解释《大学》“明明德”时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11]冯友兰指出,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变化气质以复归天理)的主张一方面受到佛教“法”(对应“天理”)与“无明”(对应“人欲”)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老子“为道日损”工夫的影响。性善在孟子那里只是萌芽(四端),需要后天的培养才能实现(四德),而朱熹则将善性(四德)直接提升为天理,认为天理(本性)原本就是圆满无缺地具备于心中,只是为人欲所遮蔽,所以要用“损”的工夫灭人欲存天理。冯友兰吸收西方的“Neo-Confucianism”概念,认为宋明“新儒家”之所以“新”(区别于先秦的“旧”儒家),在于受佛老的影响构建了本体工夫论(存理灭欲)的思想体系,但其追求的人生目标则与佛老根本不同,所以“新儒家”仍然是“儒家”。或者说,宋明新儒家既吸收了佛老本体层面的超越性,又没有放弃儒家人伦日用的现实立场,从而统一了超越的本体与现实的生活。冯友兰接着指出:“于是这些哲学家着手进行前面引文中的‘格物’,立即碰到一个问题:什么是‘物’?由此产生两个类型的新儒家。一个说,‘物’是一切外界的物和事。可是人要一下子格尽一切物,绝不可能,也没有人将这种解释付诸实践,就连作这种解释的朱熹本人也没有这样做。另一个说,‘物’是指我们心中的现象。这种解释,实行起来比较成功。双方都有许多精妙而服人的辩论,都对于人生的理论和方法作出了一些大贡献。”[12]冯友兰认为,朱子学与阳明学两派的工夫论各有长短,殊途而同归,都对中国传统人生理论及修养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该文的内容主旨及思想渊源来看,冯友兰认为中国思想原有三大学派:道家、墨家和儒家,其中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后来墨家失败,人为路线消亡,从此民族思想重视人伦日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而不是寻求客观真理,这就是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思想根源。冯友兰对宋明新儒家修养论及其导致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后果的论述,与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对以朱熹、王守仁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家格物方法论的论述大体相近。但与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立场不同,冯友兰以“能而未为”的理论来为中国文化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作辩护,强调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并以各有长短为理由,为中国文化争取平等地位。这一立场与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关于中西印文化的不同走向及中国文化价值的论述一脉相承。事实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绪论”部分在1920年10月已经刊登于《北京大学日刊》,冯友兰第一时间就在美国看到了。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出版不久,冯友兰即在美国发表英文书评,其中已经表现出为中国传统文化争取平等地位的现代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立场。[13]
1923年暑期,冯友兰在导师杜威的指导下完成其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The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 interpret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并通过答辩。在这篇博士论文(192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冯友兰直接使用“Neo-Confucianism”作为第十二章的标题,在正文中也反复使用了“Neo-Confucianist”和“Neo-Confucianism”概念。冯友兰从中西比较的视域出发,肯定了中西方主要哲学体系都兼有理想(本体)与现实(作用)两个层面,并且各自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达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因而可以相互补充。冯友兰具体探讨了宋明新儒学调和“有”(事物)与“无”(本体)的哲学体系,并将其与孔子调和自然状态与艺术状态、亚里士多德调和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黑格尔调和“我”与“非我”的人生理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使道家的本质与艺术更加和谐的一种尝试,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使柏拉图的理想国与现实世界更加和谐,宋明新儒学使虚无主义更有人情味,黑格尔的观点使进步主义更加神圣。[14]这里,冯友兰对宋明新儒学的评价及其思想立场与前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脉相承。
以上是冯友兰自述其哲学研究生涯的第一阶段,即其早年留学美国期间(1920-1923年)。[15]这一时期,冯友兰主要致力于从中西哲学的比较视域出发,阐明中西文化的不同性质和特征,从而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此过程中,冯友兰吸收了西方“Neo-Confucianism”概念,并对宋明新儒学的特征、分派、哲学体系及历史贡献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阐发。
三、冯友兰与中文“新儒家(学)”概念的阐发及流行
冯友兰于1923年回国后,先任河南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前身)哲学系教授,当年冬天到山东第六中学讲学两周,根据此讲演写成《一种人生观》,并于次年10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冯友兰对1923至1924年间在国内兴起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又称科玄论战)的正面回应,延续了之前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思想立场,力图调和科学“理性”(自由意志)与玄学“直觉”(神秘主义的精神境界)。[15]随后,冯友兰于1924年冬天将其英语博士论文改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AComparativeStudyofLifeIdeals)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以此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冯友兰进而将AComparativeStudyofLifeIdeals的中文翻译稿(1924年完成)与《一种人生观》修订整合成《人生哲学》,并于1926年9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共十三章,其中第一章至十一章是由《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修订而成,第十二、十三章是由《一种人生观》修订而成。以上是冯友兰自述其哲学研究生涯的第二阶段(1923-1926年)。这一时期,冯友兰主要是在比较哲学的视域下探讨了中西人生观的差异。[15]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生哲学》一书中,冯友兰直接将其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章节标题及正文中的“Neo-Confucianism”一词翻译成“新儒家”或“新儒学”。这是目前已知中文“新儒家”“新儒学”名称的最早用例。在《人生哲学》第十章“新儒家”中,冯友兰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宋元明时代所流行之哲学,普通所称为‘道学’或‘宋学’者,实可名曰新儒学。盖此新儒家虽自命为儒家,而其哲学实已暗受佛学之影响,其‘条目工夫’,与古儒家之哲学,已不尽同。惟此派哲学之根本观念,即此派哲学家对于宇宙及人生之根本见解,则仍沿古儒家之旧,未大改变:所以此新儒家仍自命为儒家,而实亦可谓为儒家。惟其如此,所以此新儒家虽受所谓‘二氏’之影响,而仍力驳‘二氏’,盖‘二氏’对于宇宙及人生之根本见解,实与儒家大异也。普通分新儒家为陆王、程朱二派,亦可谓为左右二派。陆王为左派,尤为‘近禅’。然正以其‘近禅’,故在其中新儒学之特点,即其所以异于旧儒学者,尤为显著。”[16]冯友兰给宋明“新儒家”下了定义,论述了“新儒家”的名义、特征及派别,并将其等同于中国传统的“道学”或“宋学”概念。可知这里的“新儒家(学)”概念已经成为指称宋明新儒学(宋学、道学)的专有名词。冯友兰认为,宋明新儒家之所以不同于先秦儒家,在于宋明新儒家受佛道二教的影响,虽然其本体工夫论与先秦儒家不同,但其宇宙人生观(天人关系)则与先秦儒家一脉相承,所以仍然是儒家。在对宋明新儒家内部两大学派的评价上,冯友兰指出,陆王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心性之学,直接以本心为天理,因此被程朱学派视为“明心见性”的禅学,但其实正是陆王心学超越而内在的直觉体验、本体与工夫合一的思想体系和人生境界、使儒学向普通庶民普及的理论与实践,集中体现了新儒学作为天道与性命相贯通(天人合一)的道德践履之学的根本特征。
从思想脉络来看,刚回国后的1923年至1926年之间,冯友兰大体上延续了留学时期的思想、方法及用语:即,在思想上受实用主义与新实在论(理性主义)的影响,在方法上主要通过西方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西方哲学观念,在用语上往往将“Neo-Confucian(ism)”翻译成“新儒家(学)”这样直接使用来自西方的概念。[17]从内容主旨及思想立场来看,冯友兰在《人生哲学》中强调中西文化的共性,其所罗列的损道、益道和中道三大派中,每派都是由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流派共同组成的。冯友兰虽然在表面上承认每一派都各有长短,但却将以先秦儒家与宋明新儒家为代表的中道派的层次和价值置于损道派和益道派之上,并且断定中道派是“其蔽似较少”的“较对之人生论”。[18]因此,如果说在上述英文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中冯友兰只是罗列叙述各派哲学而不作优劣之分,那么到了改写后的中文著作《人生哲学》中,冯友兰已经完全肯定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更加高明,因为中国文化的中道精神调和了科学与宗教,避免了走入极端。[15]由此可见,冯友兰已经完全摆脱了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反传统主义阵营,而正式加入新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的行列当中。[19]
比冯友兰的《人生哲学》稍晚一点,1926年10月李石岑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人生哲学》。冯李两书同名且都以中西人生哲学为关注对象,但其谋篇布局和旨趣目的不同。如果说冯著注重从科学(理性)与宗教(直觉)的比较视野出发,阐明他对中西方人生观的评价及其折中科学与宗教的思想立场,那么李著则注重顺着历史发展脉络建构全面系统的学说体系。因此,冯著名为中学教科书而实为个人思想专著,李著则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来看都是典型的教科书。李石岑在《人生哲学》第三章论述宋明哲学家的人生观时,作了一张“道家儒家释家及新儒家之心性理气比较表”,并在该表中使用了中文“新儒家”概念。李石岑指出:“旧儒家与新儒家的最大不同点,便是旧儒家不杂有禅道的思想,而新儒家则满参禅道的气味。至论到人生哲学,似乎新儒家所包孕的人生思想比旧儒家更丰富。宋明哲学所以有研究的价值,并不在于他们的本体论的思想,而在于各人所发现的一套生活法。”[20]李石岑在正文中引用了冯友兰的《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英文版,并在书末参考文献中予以说明。[21]而且李石岑也认为,宋明新儒家与先秦儒家的不同在于新儒家吸收了佛道二教思想,且新儒家的人生哲学较之先秦哲学更为丰富。这些论述都与前述冯友兰的观点基本一致。可知,李石岑是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和阐发宋明“新儒家”的,但只是偶尔使用了几次,全书中基本上还是使用“理学”(即宋明理学)这一传统宋明儒学概念。与之相反,冯友兰在其《人生哲学》中基本只使用宋明“新儒学”而不使用“宋学”“道学”“理学”等传统宋明儒学概念。1934年,李石岑出版了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下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中国哲学十讲》,并在第二讲“儒家的伦理观”中论述了以朱熹、王守仁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家的伦理观。[22]李石岑指出,宋明新儒家倡导的天理人欲、道心人心对立之说(存理去欲),使天道(天理)与心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宋明新儒家的唯心论从宋代朱熹发展到明代王守仁,将儒家的心性之学推到了极致,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并成为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23]值得注意的是,与1926年出版的《人生哲学》相比,《中国哲学十讲》是李石岑在他的思想立场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写作的,在政治层面上批评了宋明新儒家的消极影响,同时也肯定了新儒家在哲学理论层面上的重要贡献。
在冯友兰、李石岑二人之后,谢扶雅在其著作《人格教育论》及《中国伦理思想述要》(均出版于1928年)中专门论述了新儒家的人生观。谢扶雅在《人格教育论》卷上“人格之理想”第二章“东西史上之人格观”第一节“中国方面”的小节“(五)新儒家”的开头即指出:“如李翱者名虽为儒而血肉灵魂皆构自道佛,此实为人生哲学界辟一新格者也。宋以后闻风蔚起,思想之士,莫不取道家或佛家之观点,重新解释儒经,使彼宗之质,厘然一变。史家因立‘新儒家’之名以概之,以别于汉唐以前之原始儒家焉。”[24]这段论述与前述冯友兰的观点大旨相同。其所谓“史家”,当指冯友兰而言。谢扶雅具体论述了宋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邵雍与周敦颐的圣人论、张载的天人合一说、二程的理气说、朱熹的穷理说、陆九渊的唯心论、杨简的全我说、王守仁的大人说、刘宗周的人极说,最后总评宋明新儒家的人格观。谢扶雅又在《中国伦理思想述要》第三章“中国伦理底最高理想”第一节“个人的理想”之小节“三、新儒家(受道家佛家影响后之儒家一派)”中论述了新儒家(指先秦思孟学派至宋明陆王心学一系)天人合一思想的优缺点,指出:“这派之代表人物,为古代之子思孟子,中古之扬雄董仲舒等,近代之陆王学派。他们的特色,在修正旧儒家而采取道家之长,同时避去其短;其根本思想为天人合一,照上图所示,即从儒家扩大了‘人’底地位,从道家保留着‘人’底价值。道家主张人应浸没于自然之中,在那里逍遥,不再出来。新儒家似乎说:‘人既可浸没于人之中,则天亦无不可浸没于人之中。天如合入我中,我的人格不是博大高明到极处吗?’……入近代因受佛教底暗助,而此派之势益振,如陆象山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文集》)王阳明之‘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传习录》)一类话,不胜枚举。”[25]这段文字后来又被收入谢扶雅1929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伦理思想ABC》中。[26]谢扶雅认为,宋明新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代表为陆王学派,其优点在于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价值,使人乐观鼓舞,其理论依据在于性善本体论及存理去欲的工夫论,而其缺点在于人欲不容易去除,所以易流于颓放。这段论述可与冯友兰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及《人生哲学》中的论述相互发明,它们都认为陆王学派因其“近禅”而最能代表新儒家的精神特质。
由上述可知,冯友兰虽然不是最早使用英文“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中国学者,但却是最早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并进行系统阐发的第一人。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来看,中文“新儒家(学)”概念最早就是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背景下,由冯友兰、李石岑、谢扶雅这些熟悉西方学术界且有着中西比较视野的学者,在探讨中国传统人生观时自觉吸收西方学术概念并加以使用的。他们的思想立场虽不尽相同,但都积极挖掘中国古代思想尤其宋明新儒家人生观的价值。由此可见,中文“新儒家(学)”概念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已经在学术界流行开来。
四、冯友兰中文论著用语的转变及其翻译
目前,仍然有学者认为“Neo-Confucian(ism)”是卜德在翻译冯友兰的著作时首次使用的。要澄清这一误解,就必须系统考察冯友兰自述其哲学研究的第三阶段——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阶段(1927-1937年),代表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与第四阶段——“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建构阶段(1938-1945年),代表作为《贞元六书》[11],以及赴美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时期(1946-1948年),代表作为《中国哲学简史》(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此外,还必须考察同一时期冯友兰在海内外发表的中英文文章。
首先,冯友兰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中论述荀子思想时指出:“战国时儒家中有孟荀二学派之争,亦犹宋明时代新儒家中有程朱、陆王二学派之争也。”[27]其后,1932年5月7日冯友兰在《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合刊本上发表的《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中15次使用“宋明新儒家”而未使用“理学”或“道学”概念。[28]该文是目前已知最早使用中文“新儒家(学)”概念的期刊论文,在用语习惯上与冯友兰1926年出版的《人生哲学》完全一致。但随后,1932年6月冯友兰在《清华学报》第7卷第2期发表的论文《朱熹哲学》中仅有1次使用“新儒家”,而3次使用“理学家”,包括“程朱一派之理学家”与“陆王一派之理学家”。[29]到1932年12月,冯友兰在《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发表的论文《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中只使用“道学”及其所包含的“理学”(程朱)和“心学”(陆王)概念,而不再使用“新儒家(学)”概念。[30]从上述1932年发表的三篇研究宋明道学的文章用语来看,冯友兰从完全使用源自西方的“新儒家(学)”概念,再到“新儒家(学)”与中国传统的“理学”(包括程朱与陆王两派)概念并用,最后使用宋明儒学史上比“理学”出现更早的“道学”概念(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而不再使用“新儒家(学)”概念。
这一趋势延续到了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下)》中,冯友兰在该书章节标题及正文中都使用“道学”概念来指称以韩愈、李翱为先驱的宋明新儒学。而上述1932年他发表的三篇研究宋明道学的文章经修改后均被收入《中国哲学史(下)》中。其中,《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一文被扩充后收入《中国哲学史(下)》第十章论韩愈、李翱的部分中,但原文中的“新儒家”一词已经全部被改为“道学家”或“道学”。[31]《朱熹哲学》一文被采入《中国哲学史(下)》第十三章论朱子的部分中,原文中的“新儒家”及“理学家”的提法也全部被改为“道学家”。[32]《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一文被采入《中国哲学史(下)》第十四章论朱陆异同的部分中,原文中的“道学”(包括“理学”“心学”)概念都没有更改。[33]整部《中国哲学史(下)》中,“道学”概念出现了154次,而“新儒家(学)”概念仅出现了4次,并且有两次还是作为“道学”的同位概念被顺带提到的。即冯友兰在该书第十章“道学之初兴及道学中‘二氏’之成分”开头指出:“唐代佛学称盛,而宋明道学家,即近所谓新儒家之学,亦即萌芽于此时。”[34]这里所谓的“近所谓新儒家之学”表明“新儒家”概念在此之前已经出现。由前述可知,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李石岑、谢扶雅已经先后使用中文“新儒家”概念。英文“Neo-Confucianism”概念则在胡适191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1922年出版)及冯友兰1922年发表的文章和192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已经使用。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下)》第十章又指出:“韩愈提出‘道’字,又为道统之说。此说孟子本已略言之,经韩愈提倡,宋明道学家皆持之,而道学亦遂为宋明新儒学之新名。”[35]这里指出,韩愈提倡道统说而开宋明道学思潮之先声,后来“道学”成为专门指称宋明新儒学的名称。这也是冯友兰使用“道学”来替代“宋明新儒学”概念的历史依据。同章又指出:“及乎北宋,此种融合儒释之新儒学,又有道教中一部分之思想加入。此为构成新儒学之一新成分。”[36]冯友兰指出,唐代韩愈、李翱等人融合儒释而开新儒学之先声,而北宋新儒学的开创者周敦颐、邵雍等人又吸收宋初道教陈抟象数易学的宇宙本体论思想来建构其思想体系,由此可知,宋明新儒学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产物。陈寅恪在为《中国哲学史(下)》写的《审查报告三》中指出:“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然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36]同时,使用“新儒学”及“新儒家”来指称宋明新儒家(学),并指出其产生深受佛道二教的影响。陈寅恪的这段论述影响很大,尤其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中很少使用“新儒家(学)”而基本只使用“道学”概念的情况下,通常被视为早期中文“新儒家(学)”概念的典型用例。[37]
总之,1932年12月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文论著中使用传统“道学”概念取代了源自西方的“新儒家(学)”概念。其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前,冯友兰再也没有使用过“新儒家(学)”概念。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冯友兰在作为晚年定论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只使用“道学”而不使用“新儒家(学)”概念(除了作为西方学术界的称呼附带提到一次)。[38]冯友兰署名独著的英文论文除了前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之外,基本都是论述现代儒学的,也没有使用“Neo-Confucianism”概念。但由卜德等人翻译或润色的冯友兰英文论著中都使用了“Neo-Confucianism”或“Neo-Confucianists”概念[39-41],卜德在翻译《中国哲学史(上)》(1937年在北平首次出版,1952年在美国再版)时将“新儒家”翻译为“Neo-Confucianists”[42]。卜德在翻译《中国哲学史(下)》(1953年在美国出版)时又直接将“道学”翻译为“Neo-Confucianism”,并且置于章节标题的醒目位置。[43]1947年休斯(E.R.Hughes)翻译出版的《中国哲学的精神》(TheSpiritofChinesePhilosophy,系冯友兰《新原道》的英译本)中也将“道学”翻译为“Neo-Confucianism”。1948年卜德润色的《中国哲学简史》中也使用“Neo-Confucianism”来指称道学,并且置于章节标题的醒目位置。[44]虽然“Neo-Confucian(ism)”概念在西方学术界早已出现,而且冯友兰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论著中就已经使用,但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中使用并不普遍,其广泛流行要等到上述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等人翻译的《中国哲学史》(A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中国哲学简史》(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中国哲学的精神》(TheSpiritofChinesePhilosophy)等著作出版之后。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冯友兰首创并在1932年底之前频繁使用的“新儒家(学)”概念后来让位给了“道学”概念呢?这种用语上的转变与冯友兰对宋明儒学史的研究及其思想体系的构建直接相关。1927年至1937年期间,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学任务为契机,冯友兰开始深入钻研中国哲学史,并在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之后进入《中国哲学史(下)》的写作,开始系统研究宋明儒学。在此过程中,冯友兰逐渐意识到,使用一个意义不确定的西方概念来指称中国固有学派并不合适。因为“新儒学”同时对应于“宋学”“道学”“理学”等不同层级的概念,并且每一时代的儒学相较于前一时代都可称为“新儒学”。[45]因此,以1932年底为界限,冯友兰在其中文论著中基本不再使用“新儒家(学)”概念,而是使用中国固有的“道学”概念作为宋明新儒学的学派名称,并以“道学”来统摄“理学”(程朱)与“心学”(陆王),从而建构起宋明儒学的学派概念体系。之后1937年至1946年,冯友兰完成其“新理学”哲学体系建构的代表作《贞元六书》,从而由“照着讲”(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进入“接着讲”(“新理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的阶段,在吸收融合中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以宋明道学为根基建构其自身的哲学体系。这也体现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精神、范畴及概念体系的自觉建构。但为什么冯友兰要用“道学”而不是学术界更为流行的“理学”概念来指称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宋明新儒学呢?因为在冯友兰看来:宋代儒学中的“道学”名称在北宋时已经出现,较之南宋时才出现的“理学”名称更早;同时,“理学”名称既可指宋明理学,又可指程朱理学,存在歧义,而宋明儒学中的“道学”一般指程朱和陆王两派,较少歧义。[46]但由当代学者对“道学”“理学”概念意义的考辨可知,历史上儒释道中都使用过的“道学”概念,其复杂性和歧义性实际上远超“理学”概念。[47]因此,有学者质疑冯友兰的观点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不符。[48]撇开这些复杂的历史背景不谈,仅从冯友兰建构的宋明道学概念体系自身来看,他无疑是可以自圆其说的。这也是冯友兰的观点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除中国学者外,海外知名学者如日本的土田健次郎、美国的田浩等)支持的主要原因。
冯友兰在海内外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著作如《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等,基本都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思想、方法趋于成熟,用语由“新儒家(学)”转向“道学”之后完成出版的,加上卜德的翻译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流传过程中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掩盖了西方之前的“Neo-Confucian(ism)”用例,这才造成学者往往误认为“Neo-Confucian(ism)”是卜德在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首次使用,而后再转成中文“新儒家(学)”概念,或者认为中文“新儒家(学)”名称是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中国哲学史》时才开始使用。这些都是没有全面考察冯友兰在20世纪20年代的早期学术活动及其在30年代、40年代的用语转变所导致的误解。同时,刘述先认为“新儒家(学)”概念在当时并未流行成为学术界专有名词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释。[49]因为他只注意到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以后很少用“新儒家(学)”概念而基本只使用“道学”概念,却没有考察当时学术界的整体情况。事实上,在当时的中文学术界,除了前述李石岑、谢扶雅、陈寅恪受冯友兰的影响使用并阐发了“新儒家(学)”概念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在其论著中使用并阐发了宋明“新儒家(学)”,进而随着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学术界已经出现使用“新儒家(学)”指称现代新儒家(学)乃至战国秦汉等其他时代“新儒家(学)”的论著,可见“新儒家(学)”概念在当时的中文学术界已经通行起来。①
五、余论
需要指出的是,宋明新儒学思想的研究及其概念的阐发与在其基础上构建思想体系、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并倡导返本开新的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宋明新儒学的研究及中文“新儒家(学)”概念的使用肇始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冯友兰(同时也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冯友兰的著作经过卜德的翻译在西方流行后,在美国兴起了以宋明新儒学的研究为中心的“哥伦比亚学派”。该学派的领袖、美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狄百瑞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宋明新儒学现代意义的阐发上起到关键作用,并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宋明新儒学研究。事实上,20世纪以来海内外现当代新儒家学者在研究和阐发宋明“新儒家(学)”方面贡献巨大,包括第一代的冯友兰、张君劢、贺麟、方东美,第二代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的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此外还有陈荣捷、狄百瑞等人。他们都对宋明“新儒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阐发其现代价值并建构自身的思想体系。这也体现了现当代新儒家学者对宋明“新儒家(学)”的继承创新(返本开新)以及融合古今中西文化的努力。
注释:
① 论文如:车铭深. 论新儒家的理和欲[J]. 东方杂志,1937(1):283-293;绥之. 新儒家与基督教文化之关系[J]. 文化导报,1943(4-5):22-34;叶秋原. 基督教与新儒家[J]. 东方杂志,1943(2):21-23;胡秋原. 新儒学之道路(学术论著)[J]. 新中国,1945(7):15-56.著作如:(日)武内义雄著,高明译. 儒教之精神[M]. 太平书局,1942:63-86.详见该书前篇第八节“新儒学 其一——朱子学”与第九节“新儒学 其二——阳明学”。此外,贺麟在1941年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使用的“新儒家思想”“新儒学运动”中的“新儒家(学)”是指当时兴起的现代新儒家(学),而非指宋明新儒家(学)。贺麟当时创立了“新心学”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同时仍然用“宋明道学家”来指称宋明新儒家。参见:贺麟.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J]. 思想与时代,1941(1):13-22.已知最早论述宋明及现代之外其他时代新儒家的文章见于《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5期上连载的以下四篇文章:缪钺《学术通讯(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与钱宾四书》、钱穆《学术通讯(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与缪彦威书》、缪钺《学术通讯(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再与钱宾四书》、钱穆《学术通讯(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再覆缪彦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