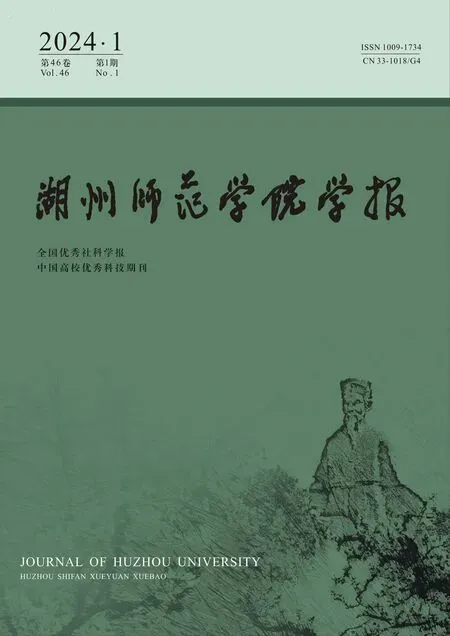唐大历江南诗文化圈及诗学景观*
——以浙东与浙西联唱为中心的考察
陈 超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7)
在唐初百余年历史中,京城一般既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京城不仅是唐初文士的人生舞台,也是初盛唐诗学发展的重要场域。但京城作为诗学中心的绝对地位,在安史之乱后被打破。在江南这个远离战乱的文化社群场域里,大批士人避难南方,江南俊彦翕集,诗人们雅集酬唱频繁,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诗学社交圈。至此,文学中心在唐代第一次打破了以京城为绝对中心的态势,文学能量进行了空间转移,江南地区逐渐崭露头角。
一、京城诗歌文化圈的他者:大历江南诗歌文化圈
唐初由于士族的中央化,众多文化士族纷纷迁徙至京。这些政治移民与文化移民齐集京师,奠定了京师政治、文化中心格局的基础。就政治中心的形成而言,毛汉光先生在《从士族籍贯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一文中指出了士族中央化的重要作用:“唐代官僚中的选制对地方人物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使郡姓大族疏离原籍、迁居两京,以便投身于官僚层;科举入仕者以适合官僚政治为主,地方代表性质较低,士族子弟将以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自求取晋身,大帝国由此获得人才以充实其官吏群。”[1]333在大批士人谋求仕宦,走向京师的同时,群英荟萃的京师也因此成了文化中心。
初盛唐的京城居于文化中心,因群贤毕集也成了诗坛中心,有着相对稳定的诗人群社交圈。这些社交圈以素喜奖掖文士的皇室或权贵为中心,其间荟萃了众多优秀的诗人,并常常举行游宴唱和活动。诗人们在得以进入这些社交圈的同时,不仅诗名渐扬,而且仕宦有望。京城在这些诗人群社交圈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权威的诗歌文化圈。(1)本文所提出的“京城诗歌文化圈”概念,主要是指京洛二都的京都文化对诗歌创作主体集群的吸引力。聚集京都的诗人们围绕在雅爱文章之士的皇亲或宰臣周围,通过游宴、文会等活动形成人际网络,借用这个网络的推奖揶扬提高自己的声名,从而最终实现自己的仕宦目的。而在形成这些重要的诗人群社交圈的过程中,这些社交圈本身就也拥有了臧否人物、甲乙诗歌的权威。京都诗歌文化圈正是在这些重要的诗人群社交圈臧否人物、甲乙诗歌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是这些诗人群社交圈能量的外化形式。在这个诗歌文化圈里,名家与权贵的品题或提携具有制造声名与获得身份认同的功用,因此诗人们扬名立万必以京师为起点。以小说家记载的陈子昂事迹为例,亦可清晰地看到京师诗歌文化圈对诗人声誉的推扬与身份认同的显著影响。
陈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师,不为人知。时东市有卖胡琴者,其价百万,日有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于众,谓左右:“可辇迁缗市之。”众咸惊,问曰:“何用之?”答曰:“余善此乐。”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闻乎!”答曰:“余居宣阳里。指其第处,并具有酒,明日专侯。不唯众君子荣顾,且各宜邀召闻名者齐赴,乃幸遇也。”来晨,集者凡百人,皆当时重誉之士。子昂大张宴席,具珍馐。食毕,起捧胡琴,当前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所知。此乐,贱工之役,岂愚留心哉!”遂举而弃之。舁文轴两案,遍赠会者。会既散,一日之内,声华溢都。”[2]436
陈子昂十年居京师而不为人知,以计策竟能“一日之内,声华溢都”。在“集者凡百人,皆当时重誉之士”的情况下,他呈文轴以期赏识,可见京城重誉之士的影响力。小说家所言之事未必可信,但作为“通性之真实”的时代背景不假。京城是初盛唐诗人社会交往与文学活动最重要的舞台。
安史之乱后,由于大批士人或避难或仕宦聚于江南,诗酒文会频频,使得江南成了京城之外又一重要的文学空间。在京都诗文化圈,这一时期活跃于诗坛的是新秀大历十才子,他们与这一时期的权相元载、王缙集团关系紧密,在频繁的游宴文会活动中开始于诗坛崭露头角。与此同时,大历江南地区两大诗会以及众多北人集聚江南被认为是南朝后南方文学的重新崛起。“这些诗会的兴起,加上这一时期虽未参加这两个集团,却基本活动于江南地区的刘长卿、李嘉祐、张继、戴叔伦、顾况、皇甫冉、秦系、朱放、灵一、灵澈等诗人,从而使得江南地区呈现出文学创作繁盛的局面,标志着南方文学的重新崛起。从此之后,文学中心又开始逐渐南移了。”[3]101“淼淼霅寺前,白苹多清风。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追吟当时说,来者实不穷。江调难再得,京尘徒满躬。”[4]84孟郊称赞其时湖州诗会繁盛,并将其江南风调概括为与“京尘”相对的“江调”,更是敏锐地揭示出江南诗歌文化圈的特色。
若在中国舆图上将大历时期诗人们频繁活动的范围作定点的点阵标示,则可以清晰地凸现一个以江南东道为主,旁及与其地缘关系密切的淮南道之扬州,江南西道之洪州、饶州、袁州等地区形成的诗文生态圈。这个诗文生态圈中以江南清丽泽国为地理空间,以地方官员和当地文士、诗僧为创作主体,以日常生活美学书写为焦点,呈现出与京城诗文化圈明显不同的特色。
首先,两者的形成机制不同。京城诗文化圈以皇室或权贵为核心人物,而江南诗文化圈以地方官员、当地文士和诗僧成为为主体,且三者之间频繁互动,《中兴间气集》卷下“道人灵一”条云:“自齐梁以来,道人工文多矣,罕有入其流者。一公乃能刻意精妙,与士大夫更唱迭和,不其伟欤?”[5]
安史之乱后避地江南的北方士人,大多通过故交与幕僚的社会关系托身此地,因而形成文人集群。颜真卿之于湖州,刘长卿之于睦州,独孤及之于常州,韦应物之于苏州等,都以地方官为诗人群主体,其与地方官僚佐及当地文士共同构成稳定的诗人集群。而在这个过程中,江南本土文士与诗僧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可著者如严维、皎然、灵一和神邕。可见除血缘和业缘外,地缘是安史之乱后江南文彦云集的又一重要因素。
大历时期的严维是越州地区文人活动的核心人物,安史之乱后避难越州的文士与其多有交往。严维是越州地区享有盛名的诗人。《刘禹锡集》卷一九《澈上人文集纪》云:“(澈)从越客严维学诗,遂籍籍有声。”[6]519除了与灵一、灵澈、清江、少微上人等颇有诗名的僧人交游密切,严维还与一些高僧大德多有来往,如其诗《赠别至弘上人》《酬普选二上人期相会见寄》《送桃岩成上人归本寺》等。严维外,灵一是越州地区诗名颇著的诗僧,与避难南来的文士亦有密切的交往。
皎然是大历时期湖州地区文人活动的核心人物,其与严维一样,是该地区社交网络的纽带。皎然一生,除年轻时曾北上谋宦外,大多居于湖州及周边地区。大历时期,“他与避地、游宦、出使、隐居江东吴越的几乎所有著名诗人交往唱酬,论诗讲艺,包括陆羽、李季兰、刘长卿、顾况、柳中庸、吴筠、颜真卿、皇甫曾、张志和、李华、张荐、耿湋、杨凭、杨凝、韦渠牟、李嘉祐、严维、朱放、灵澈、包佶、梁肃、秦系、李端、韦应物和权德舆等”[7]5。
其次,两者文化地理品格不同。水乡江南在安史之乱后由于经济重心转移和远离战乱,文化活动日益增多。“赏是文辞会,欢同癸丑年”(《经兰亭故池联句》),源出东晋的江南雅集传统,使得江南地理空间的闲逸特征被进一步放大。因此吏隐之地的江南文学活动与书写,作为安史之乱后士人身心安顿的一种方式,更关注其社交性与审美性的兼容。
湖州山水清远,可谓江南地理特征之显著者,历来得骚人墨客之心赏。唐李直方在《白蕉亭记》中云湖州:“吴江之南,震泽之阴曰湖州。幅员千里,棋布九邑。卞山屈盘而为之镇,五溪丛流以导其气。其土沃,其候清,其人寿,其风信实。”[8]6244江南山水佐旷达清机,士人与江南山水怡然契合,一歌一咏以抒情性。故明代陈以诚《吴兴艺文补序》云:“余独思颜鲁公在郡日……以余力缮成《韵海镜源》一书,至于遍招材彦参与,子侄、方外、白足皆得挥尘入席。唐季政衰,兵戈游起,乃有此一片洞天福地,任吏隐者逍遥如此。”[9]卷二六四如两浙联唱《云门寺小溪茶宴怀院中诸公》《竹山连句题潘氏书堂》《严氏园林》和《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等诗题可见,经盛唐衰败的中唐士人在水乡、佛寺、园林、茶道、诗僧等江南风物中悠然自放。他们的文学活动与文学书写在良辰嘉会和精舍寒泉之下乐群悟道,将文学审美生活化、日常化。
社交艺术性是大历江南诗文化圈的显著特质,宇文所安认为:“许多迹象表明诗人们正日益思考诗歌的艺术,这种思考与文学群体的社会背景不可分离,在东南圈子中,占上风的诗歌观念不是自我表现,不是道德标准的工具,不是脱离场合的纯艺术,甚至不是为获得社会地位而必须掌握的技巧,而是与南朝一样,将诗歌看成是一种为了社交而存在的社交艺术,一种本身就是社交事件的消遣。”[10]318以大历江南两次较大的文士集会——浙东和浙西集会来看,诗人们在诗歌、书法、绘画的艺术天地中激扬出的艺文才情,他们使得酬酢、宴饮和其他的艺文活动,能以一种更精粹而密集的方式纷然并陈,让诗酒与舞乐、书法和绘画都成了雅集中不可或缺的美感空间营造要素,使江南文会呈现出高雅的审美情趣。如浙西联唱中韦渠牟作《天竺寺十六韵》诗,颜真卿不仅为之作序、和诗,还使画工按其意境作画,所谓 “摘句配境,偕为胜绝”[11]卷四九○。
最后,江南佛教文化积淀使得诗僧肇自江南,盛于江南,僧诗和诗僧成为大历江南诗文化圈的最大特色和亮点,如浙西联唱的宴集诗、赠别诗、登游诗中便充满禅意。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称:“唐诗僧,自中叶以后,其名字斑斑为当时所称者甚多。”[12]425《唐才子传》直言诗僧的江南地域特征,称唐代诗僧最著者皎然、灵一、灵彻、清塞、贯休、虚中等八人,“皆东南产秀,共出一时”,后列诗僧四十五人,亦大多出自江南[13]44。胡应麟则特别指出:“唐诗僧越中独盛,辨才、灵一居会稽,灵澈、处默越州人,皎然吴兴,贯休濲水,皆其著者也;而寒山、拾得显化台州。”[14]179灵一、皎然、神邕等江南诗僧在两浙联唱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尤其灵一是江南诗僧中开风气之先者。他不仅把作诗看成明佛证禅的手段,而且重视诗歌艺术本身,实现了诗与禅的融合,对后世诗僧创作影响深远。
僧人作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东晋已出现,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的创作群体出现是在中唐。安史之乱后,佛教世俗化发展与社会政治状况等诸多原因造就了中唐江南诗僧大量出现。他们以诗传神写意,表现禅悟境界,对僧俗两界都产生了影响。诗僧以诗名世,他们将作诗当作自觉追求: “在中晚唐之前,僧侣固然也作诗,但大多把作诗看做明佛证禅的手段,并不把诗歌看成艺术,而比较起来,中晚唐诗僧往往有着迷恋艺术的创作动机。”[15]57他们在诗论和诗歌创作方面的开拓之功对后世诗僧起到了模范作用。(2)可参杨芬霞:《中唐诗僧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二、大历江南诗文化圈的诗学景观
作为京都诗文化圈的他者,大历江南诗文化圈不仅不同于京城的生成机制,同时也呈现出了自具特色的诗学景观。在这个诗学场域里,江南文士与诗僧、雅集与联句、江南书写是其中最突出的文学现象。
第一,京城的文学能量部分转移,江南地域诗学以领袖人物皎然为代表,形成的江南诗风从边缘跃升为主流,对京都诗文化圈产生了吸引力。皎然逐渐超出地域影响而成为全国知名诗人,他对孟郊、刘禹锡、白居易等中唐中坚诗人影响很大,又可见江南诗风对中唐诗风的影响力。
江南地区的文士凭借自己的地方诗名或声望进入诗学社交圈,与避地或仕宦江南的京城诗人酬唱,或参与地方郡守的文会活动,并在这些文学活动中逐渐扩大他们的声名,表现出与京都不同的艺术风貌。江南此时的创作环境使得他们不拘于京城的审美范式,努力发展自己的审美个性,熔铸江南文化的审美感发,如后期的吴中诗人朱放、秦系、张志和、皎然、顾况、灵辙等。皎然曾在《诗式》中云大历诗人多在江外,这无疑暗示在大历时期,江南诗风更具备时代特性。贞元八年(792)德宗令地方官于岫征集皎然文集入集贤书院收藏,可见皎然已获得全国性声名,以皎然为代表的江南诗风对京城产生了吸引力,甚至吸引了皇帝。
第二,大历江南地区诗酒文会频频,在这个文化圈中文人雅集具有常态特征。安史之乱后由盛世破灭滋长的恬退独善的社会心理,使诗歌容易被看成消遣娱乐的工具,游戏性是浙东与浙西联唱文人联句突出的特点。如浙东联唱《酒语联句,各分一字》《一字至九字诗联句》,浙西联唱《乐语》和《馋语联句》等。联句看似诗歌的游戏,在大历江南地区兴盛的联句现象却隐藏着人们对诗歌与游戏关系的别样解读。“游戏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它与平常生活的空间隔离。一个封闭的空间为它标示出来,物质上的或是观念上的,都从日常生活环境中圈划出来。在这个空间里,游戏举行,规则通行。”[16]22联句提供了一个不理眼前之事的非日常生活空间,少则两人多则数十人的共同文学创作组建了一个闲趣、公共与戏谑的空间,将真正的个人时空意识隔离在外,从而把江南打造成一个远离战乱、贮存诗意的文化记忆空间。
此外,有学者指出联句诗起源于齐梁时期,隋及初盛唐摒弃不用,大历江南地区联唱重新引起文士兴趣,有助于重新评价和复兴齐梁诗风[3]98。沿着这一思路,皎然联句创作潜蕴的诗学思想也得到抉发。
诗酒文会所作的联句也不乏佳作。如大历时期浙东联唱《入五云溪寄诸公联句从一字至九字》历来被视为思致与诗艺俱佳,如出一人之手:东,西。鲍防。步月,寻溪。严维。鸟已宿,猿又啼。郑槩。狂流碍石,迸笋穿溪。□成用。望望人烟远,行行萝径迷。吕渭。探题只应尽墨,持赠更欲封泥。陈允初。松下流时何岁月,云中幽处屡攀跻。张叔政。乘兴不知山路远近,缘情莫问日过高低。贾弇。静听林下潺足湍濑,厌闻城中喧喧多鼙鼓。周颂[11]卷七八九。
第三,安史之乱后的江南书写逐渐形成了与江南地域文化及风光相匹配的特色。无论是在写作理念还是写作内容方面,都深化了早期唐人对江南的概念化认知,进一步强化了文学创作中江南地域特征的闲、雅品格。
长安处庙堂之高,江南居江湖之远,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书写引发的情感在浙东联唱《状江南十二咏》与《忆长安十二咏》中有很好地呈现,这反映了大历时期人们心中的长安与江南的地理认知。如果说长安地理空间中更多具有帝都的政治文化中心色彩,因而显露出雍容、磅礴、繁华的空间属性,那么江南则蕴涵着清秀、雅致、娴静的空间属性。
安史之乱后文人对江南的书写方式,在继承闲、雅的地理文化特征描述同时,较之初盛唐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它改变了初盛唐时文人的江南书写范式。不同于《江南曲》《江南弄》和《采莲曲》等意象组合中的概念化江南,安史之乱后文人们由于亲历江南,因此对于江南的书写,便更多从一地一物着手,从而使得人们对于江南的感性认识也更加深入和细致。如浙东联唱中的诗歌创作,通过集会场所例如兰亭故池、松花坛、法华寺、云门寺等景致描绘,从微观角度强化了初盛唐时期的江南认知。浙西联唱中对集会场所、时令风物的描写同样如此。其次,中唐的江南书写深化了江南地域闲、雅的特质。由于安史之乱后大批士人会聚江南,诗酒文会成为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众人在欢宴唱和之际,笔下对于江南的书写方式自然多了一份逸乐与雅致,因此加深了人们对江南闲、雅的感观印象。独孤及在江南期间文宴酒会频频,其文集《毗陵集》所收相关诗文颇多,借此我们可窥见独孤及及其周围文士笔下的江南诗酒风流。如其文《建丑月十五日虎丘山夜宴序》云:“今兹虎丘之会……会之日,和气满谷,阳春逼人。岩烟扫除,肃若有待。余与夫不乱行于鸥鸟者,衔流霞之杯而群嬉乎其中。笑向碧潭,与松石道旧,兕觥既发,宾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吴趋数奏,云去日没。梵天月白,万里如练。松阴依依,状若留客。于斯时也,抚云山为我辈,视竹帛如草芥,颓然乐极,众虑皆遣。于是奋髯屡舞,而叹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罢皆赋,以为此山故事。”[17]131正是诗人们大量如上述笔调的江南集会书写,共同铸就了江南地域书写中的闲、雅特质。
三、渔隐意象与江南诗性审视
江南文化发韧于春秋吴越时期,其后历经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和宋室南迁等三次大规模文化南移,至明清最终形成我国文化地理上最为耀眼的江南文化。在江南文化臻于极致的发展进程中,文学书写和文学活动对其地域的文化特质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安史之乱后的江南虽然远不如北方战祸之惨烈,但也绝非文人笔下的洞天福地,如刘展之乱对湖州的破坏便在皎然诗集中有记录,其他诗人如刘长卿诗集中也不乏其他江南地区的战乱记载。但江南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地理概念,在安史之乱后的文学书写过程中,仍被视为远离战乱与仕宦的人生清静地。避地江南的文士雅集文会频频,“时俗以远而未扰,地也以偏而获宁”(吕温《裴氏海昏集序》)[18]卷三,他们徜徉在江南的山水之间以涤荡忧思,文学创作中的江南便化身为闲逸之地。而在这其中,由浙西联唱《渔歌》提炼的渔隐意象影响深远,其既体现了安史之乱后士人闲散旷达的心灵追求,同时又形塑了时人对江南的诗性审视方式。
渔父意象早在先秦便有庄子渔夫、楚人渔父,后汉有严子陵乐钓等故事,最终形成了既没有愤世也不为悟道的渔父意象。唐初诗歌中这类意象也屡见不鲜,以《渔父》为诗题的作品,大多在描述渔父形象的同时,寄寓作者所谓“非为徇形役,所乐在行休”(《全唐诗》卷一三六)的隐逸之念。安史之乱后有关江南文学书写中呈现出的闲逸、雅致特质,在张志和《渔歌》中塑造的渔父意象里得到了一次凝练和提升。据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其任翰林学士时,得知宪宗皇帝曾访张志和《渔歌》而不得,润州刺史任上访得五篇,立即写进。由此可见在张志和访颜真卿作出此词半个世纪后,该词仍主要流传于江南,但同时也已传播到东瀛,形成许多追和的作品[19]。渔父意象体现的去政治化的特征及闲逸悠乐的文人情趣,都与安史之乱的江南书写理念不谋而合。
《唐朝名画录》云:“张志和或号曰烟波子,常渔钓于洞庭湖。初颜鲁公典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为世之雅律,深得其态。”[20]35据《太平广记》卷二七所引南唐沈汾《续仙传》载:“鲁国公颜真卿与之友善,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曰:‘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天词,须臾五本。花木禽鸟,山水景像,奇绝踪迹,今古无伦,而真卿与诸客传玩,叹服不已。”[2]792张志和《渔歌》现仅存五首,兹录于下: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舴艋舟。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
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著荷衣不叹穷。
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干,醉宿渔舟不觉寒。
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
五首词概非一时一地之作,其中第一首流传最广。词中所涉地名有湖州的西塞山、霅溪,睦州的钓台,苏州的松江,以及湖南的青草湖和巴陵。《渔歌》中江南渔父的文学塑造,既有初盛唐人江南印象的积淀,又受安史之乱后文化地理环境的影响,从而提炼形成新的江南意象。唐朝的江南书写,由早期《江南曲》《采莲曲》和《江南弄》等乐府诗中的越女、吴姬等江南意象,转变为安史之乱后的江南渔父意象,这表明唐人对江南文化地理的闲、隐品格认知,无疑从皮相转入了风神。张志和《渔父词》影响甚大,不仅在当时有诸贤唱和,(3)陈振孙曾编集《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一卷,并云:“尝得其一时唱和诸贤之词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之所赋,通为若干章,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转引自贾晋华先生《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同时也成为后代文人词的远宗,尤其“词中所表现的‘真隐’观念,为其后的隐逸词所继承”[3]97。
由张志和在湖州创作的《渔歌》为生发点,经过本土与寓居其地的文士共同创造,“苕溪渔隐”文化意象在湖州蔚然大观,这正是文学在地化和文学层累的诗学景观。有学者称:“隐逸意象的建构是苕霅文化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和象征,是历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与寓居游历于此的文人的共同创作。至迟到宋代,苕霅文化意象已经具备约定俗成的内涵,其核心是隐逸脱俗的气度,风景如画的自然山水与人文关怀,以及远离政治或者政治核心的个性要求。”[21]87因此,大历期间浙西联唱中创作出的《渔歌》,不单契合此时期寓居江南的文士心理趋向与人生态度,同时也是唐代江南诗性审视建构的重要一环,并逐渐与唐代以后至明清最终形成的江南文化品格趋向一致。
翻检湖州地方诗文总集如《吴兴艺文补》,便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唐至明的文人在湖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渔父诗词,形成了一个渔父诗词写作的传统。如唐代杜牧任湖州刺史期间创作的《渔父》,宋代周紫芝、胡仔,元代赵孟頫与夫人管仲姬,明代刘麟等众多文人都创作了相关诗词。而“苕溪渔隐”意象的概括,最早应出自隐居湖州苕溪的胡仔,他作有《苕溪渔隐》诗,其后仍随之的有元代沈梦麟《苕溪渔隐》诗。二诗分别对苕溪渔隐的旨趣进行了诠释:
溪边短短长长柳,波上来来去去船。鸥鸟近人浑不识,一只飞下镜中天。[22]487
苕花白白覆渔罛,门外沧浪湛玉壶。西塞一蓑清入画,南溪百里直通湖。鲸鳌钓罢吾应老,鸥鹭同群尔不孤。留取残书归去读,水云乡里著《潜夫》。[22]606
又,清杨凤苞组诗《题归大鸾〈清苕渔隐图〉》:
斜日沙头荡桨归,柳阴闲卧绿蓑衣。何如禅舍传渔隐,画出杨花绕梦飞。(其一)
避地休嗟著处难,布帆无恙水云宽。江南苦被征轮尽,只有渔租不入官。(其二)
溪流如镜映朝霞,鸭嘴船轻故故斜。昨夜东风潮有信, 鮆鱼吹雪上蓂花。筍笠乌篷泛玉壶,舟仑翁风调世间无。却教山抹微云壻,分取渔歌入画图。(其三)
富贵神仙两不持,一竿浪迹欲何之。烟波莫道无人识,曾见璜书近钓丝。(其四)
他年豫想了经纶,满眼青山卜四邻。乞得头衔五亭长,算来原是卷中人。(其五)[23]卷十
此外,诗人们不仅将苕溪渔隐的意象频频诉诸诗歌,同时还形成了一个苕溪渔隐图画的传统,这种诗与画的艺文形式多方位地诠释了渔隐的内涵,可见文人们对渔隐意象蕴藏的文化品格的认同。渔隐意象所包含的远离政治的精神诉求,既成为构成湖州地域文化品格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江南文化闲、雅品格的呈现。这份由艺文形式构建的文学、文化遗产,不仅参与了对湖州地方的文化品格形塑,同时也深深地融为江南诗性精神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