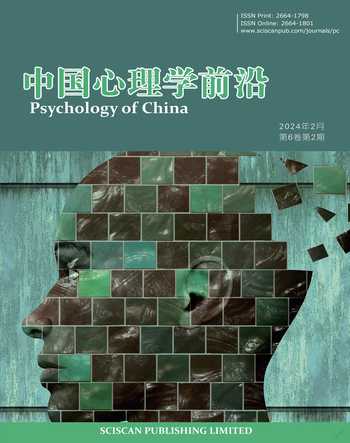跨民族友谊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杨秋杉
摘 要|跨民族友谊被视为一种积极的交流方式,其通过改善族群间的互动态度、增强族群间接触的积极性,以推动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从而实现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当前,跨民族友谊的研究尚处在起步的阶段。本论文在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从当前阶段跨民族友谊的概念定义出发,就其研究方向、研究视角,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以推动跨民族友谊研究向更深层次、更广泛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跨民族友谊;群际接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次出现在党代会工作报告,并写入新修订的《党章》,意味着民族工作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重大历史使命。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工作导向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和核心在于增强中华民族认同,而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是建立积极的群际关系、打破各民族心理界限(陈立鹏、段明钰,2020)。跨民族友谊被认为是心理学中改善民族间群际关系的最有效途径,它延伸自我认同,促进群际融合,培育共同体意识,强化一体性和共同使命感(管健,2020)。为了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让各民族同胞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愿景,跨民族友谊的相关研究已经受到广泛关注。
2 跨民族友谊概念的提出
目前,国内跨民族友谊的研究多受国外模式影响,其跨民族友谊的概念也主要借鉴于国外研究。管健(2020)在其研究中将跨民族友谊定义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民族群体建立起来的友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高质量的群际接触,具有共同目标、共同愿景、群际合作、地位平等、权威支持等特点和因素,以及高亲密度、相似兴趣、自愿接触等积极特性。该定义使用的“Cross-ethnic/inter-ethnic friendship”英文名词释义,以及对定义的修饰限定均参考自国外相关文献。这种定义方式也出现在国内其他研究中,比如赵佳妮(2019)将跨民族友谊定义为基于人际层面的不同民族成员之间交往互动建立起来的友谊;梁静和杨伊生(2021)将跨民族友谊定义为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体或群体在尊重对方民族习俗和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自我表露及文化交流等渠道建立的互惠亲密关系,具有跨文化交融性、跨群体转换性和高度普遍性等特点。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除了结合自身研究对象、研究立意、研究机制等不同,将国外研究中的“跨种族/跨族际/跨群际友谊”直接引申成“跨民族友谊”民族概念,也有直接延用“跨族际/跨群际友谊”的概念(赵福君 等,2015;刘峰、佐斌,2017)。
谢丹和常永才(2013)认为,我国只有民族之分,没有种族之别,所以跨种族友谊研究与国内跨民族研究的研究对象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不同民族或不同种族之间的友谊,且借鉴国外跨种族友谊研究成果并加以應用,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更有学者(梁静、杨伊生,2021)进一步提出,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由于受我国制度体制及社会氛围的影响,与国外跨种族友谊相比更加强调“群—我”关系在跨民族友谊中的作用,更加强调友谊双方的共同价值观念(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上位认同(国家认同)。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为,跨民族友谊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需要在更大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中解读,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注重探索不同民族逐步融合的社会变迁过程,考察历史和社会背景对跨民族友谊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更好地推动我国的民族关系研究和社会和谐研究的发展。
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起步较晚,仍需要对照国外研究中跨种族/跨族际/跨群际友谊的研究成果进行本土化改良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需要重视国外理论和国内实际条件的契合程度,尽可能减少操作性定义的不准确性。故本研究在讨论跨民族研究现状和展望过程中,引用国外文献时会慎重考虑其研究背景和对象,或延用原研究“跨种族/跨族际/跨群际友谊”进行介绍。
3 跨民族友谊的研究概述
现阶段,对跨民族友谊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研究取向:(1)将跨民族友谊作为一般性友谊进行研究;(2)将跨民族友谊作为特殊性友谊进行研究。
3.1 将跨民族友谊作为一般性友谊进行研究
该研究取向认为,跨民族友谊是一般性友谊的下位概念,只是体现在不同民族中,需要满足一般性友谊的基本特征并遵循其基本规律。所以一般性友谊的研究方法、产生条件、测量工具等对研究跨民族友谊也完全适用。
里斯和布雷克(Lease and Blake,2005)不仅利用一般性友谊的研究方法研究黑人/白人儿童跨种族友谊,更是在发现“跨种族友谊中的儿童一开始可能是通过交流想法和观点来认识对方的个人特质,并且在与朋友交往中,更加强调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而非基于种族差异造成的定型观念”时依据前人对一般性友谊的研究结果(Epstein,1989)进行解释,认为跨种族友谊的产生条件同一般性友谊一样,当个体或群体之间相似地方多过他们差异的地方,彼此之间就更有可能形成友谊。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提出“建立跨种族友谊可能有风险,尤其是当孩子必须违反同龄人群体的隐含规范才能建立这种友谊时需要承担更多风险”的观点,也参考了部分学校内同龄群体的特征如何影响其成员的教育愿望和成就的文献(Karweit,1979),这篇回顾性文献同样属于一般性友谊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谢丹(2013)在阐述研究要素时借鉴了不同学者对一般性友谊的概念界定,且遵循布科夫斯基和霍扎(Bukowski and Hoza,1989)的友谊研究层次模型从三个层次对多民族地区初中生族际友谊状况实施调研。
另外,目前国内外几乎没有专门评估跨民族友谊的测量工具,所以通常依据一般性友谊的行为与认知,采用一般性友谊数量质量量表、一般性友谊观的问卷施测,或者依据一般性友谊特质拟定的提纲进行访谈。
3.2 将跨民族友谊作为特殊友谊进行研究
格雷厄姆和科恩(Graham and Cohen,1997)通过研究种族和性别与儿童的同伴关系(社会计量评级和友谊)的关联,讨论了性别和种族作为同伴评估的考虑时有不同影响,从而侧面反映了跨种族友谊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性友谊。杨晓莉和赵佳妮(2018)在讨论跨民族友谊的影响因素时更多提及了民族文化、民族本质论等非跨民族友谊所不具备的特质。其他国内学者(赵旭峰、钟瑞华,2019;郝亚明,2019)也都提及民族文化隔阂、民族文化交融方式可能会对民族关系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国内研究多倾向将跨民族友谊作为特殊性友谊来理解,且主要关注群际接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个视角下的跨民族友谊。
3.2.1 跨民族友谊是一种积极接触方式
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认为,群际双方进行接触时能获得新信息和澄清错误信息的机会,从而改善群际态度。格律特等人(Grütter et al.,2017)在对有特殊教育需求和无特殊教育需求的青少年间友谊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相比对双方接触预期更乐观的青少年,预期双方接触后会出现负面情绪的青少年不太可能从群体接触中受益。该证据说明单纯的接触可能并不一定会对外群体成员产生更积极的态度、改善群际关系。所以在此基础上,奥尔波特(Allport,1945)专门区分了消极接触和积极接触,对积极接触提出四个最佳条件,包括平等的地位、共同的目标、群际合作、权威和法律的支持,且后续大量研究( Gaertner et al.,1999;Brewer and Kramer,1985;Chu and Griffey,1985)均支持了该条件在跨文化和跨群体中的一致性。雅库比克和费尼(Jakubiak and Feeney,2019)也证明积极性接触是改善关系、避免冲突的有效手段,且跨群际友谊恰好满足接触假说的关键条件,是一种极为理想的族际接触方式。
之后,接触假说进一步发展为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确证了跨群际友谊在减少群际焦虑、偏见等负面影响,以及促进自我表露、共情等积极影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佩蒂格鲁(Pettigrew,1998)声称为了实现健康的群际间接触,必须有友谊参与,以此强调了跨群际友谊在促进健康的群际间关系中的作用。
涉及接触假说和群际接触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减少偏见的作用机制。多维迪奥等人(Dovidio et al.,2003)对该作用机制总结出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认知因素、情绪因素在内的四个方面,跨群际友谊也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从依存关系上看,一方得益则意味着另一方遭损的零和竞争最容易引起对外群体的负性态度,而负性的态度又将导致一系列针对外群体的不友好行为。但是当与外群体并非是恶意竞争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关系时,盖特纳等人(Gaertner et al.,1999)提出,双方合作产生积极结果的获得是与外群体紧密相连的,因此有助于提升群体间的吸引力,产生跨群际友谊,发展为群体间相互依存关系,可以直接调节对外群体的态度,减少群际偏见。
从群际互动上看,跨群际友谊本身就是良好的群际互动方式,可以作为一种较好的偏见态度和行为矫正模式而存在(Pettigrew,1998)。
从认知因素上看,归因是人类的一种普遍需要,每个人都有一套从其自身经验归纳出来的行为原因与其行为之间的联系的看法和观念(Malle,2006)。波潘等人(Popan et al.,2009)发现,在以意识形态划分的群体关系中(比如保守党派和自由党派),合理归因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可以减少对外群体的偏见。而跨群际友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内、外群体界限分明的隔阂,改变划分内、外群体的维度,甚至将外群体纳入自我概念中,借此改变不合理归因倾向。
从情绪因素上看,佩蒂格鲁和特罗普(Pettigrew and Tropp,2013)在研究群体间冲突、偏见、刻板印象等一系列共同问题的应对方式时,提及情绪因素在减少群际偏见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情绪因素可以作为一种调节中介存在。跨群际友谊可以减少对外群体成员乃至整个外群体的负性情绪反应,或是增加对外群体的正性情绪体验(Pettigrew and Tropp,2006)。在群际接触中最为常见的负性情绪是因对接触感到不确定性、威胁性等唤起的焦虑。在一项对不同种族学生进行生理学指标和行为指标记录的研究报告中,与黑人接触较多的白人学生报告的群际焦虑显著低于先前没有与黑人接触过的白人学生(Mendes et al.,2002)。阿伦等人(Aron et al.,1997)通过测量结构化自我披露的被试身上皮质醇反应性,证明跨群体友谊显著降低了焦虑,并增加了跨群体互动的可能性。在群体间接触的初始阶段,减少焦虑可能最为重要,而随着持续接触和降低焦虑,增强同理心可能变得更加重要(Page Gould et al.,2008),在群际接触后期,跨群际友谊还会增强对外群体的共情能力(Pettigrew,2008)。总之,跨群际友谊减少群际接触中焦虑情绪,保障了群际间良性互动,增加了对外群体的理解和尊重,随之而来的即是偏见的减少。
3.2.2 跨民族友谊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跨群体友谊在情感和认知过程中同时起作用,尤其是在情感过程中起作用(Pettigrew,1997)。与一般常伴有群际焦虑与群际威胁等不适体验的群际接触不同,跨群体友谊是具有较强烈积极情感联系的互动关系,可跨时间、跨情境而稳定存在,甚至可以跨越現实世界而存在(管健,2020)。有研究(陈晓晨 等,2018)认为人们更容易基于亲身经历(即与外群体朋友友好愉快的交往经验)回答有关对于外群体情感的问题,即朋友间的积极情感联结更容易迁移到整个外群体。这意味着跨群体友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接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认知障碍,从而使积极接触效果得到更好的推广。因此,跨民族友谊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因其本身特性就具有极大的优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也要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赵野春 等,2022)。跨民族友谊从认知路径上可以通过获得和修正外群体信息,可以减少对外群体的偏见,改善对外群体成员的刻板印象;从情感路径上可以通过与外群体成员平等地接触,发展合作共赢的群际互动,促进彼此之间友善亲密地积极情感联系,并将对某个外群体成员的好感拓展到他所属的整个群体。因此,跨民族友谊可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可借助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包容性力量,建构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将共同体的边界泛化到整个社会或国家成为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即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管健、荣杨,202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通过各族群众的积极接触来打牢基础,家国同构的本质也就意味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集体认同(李修远,2022)。另外,跨民族友谊可以使内群体成员持更开放的思想、更稳定的情绪状态与外群体成员交往,并对外群体与本群体的差异更加包容(Korol,2017)。
4 总结
跨民族友谊本身作为一种积极接触方式,通过认知和情感两条路径使各民族同胞更愿意与其他民族成员进行深入的、高质量的接触。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刚刚起步,跨民族友谊有关的中介研究多使用以下思路:跨民族友谊可在本民族自我认同感的基础上,将其他民族纳入本民族自我概念中,从而改善民族间交往态度,其中包括减少对其他民族的偏见,或调整本民族规范性感知等,而对外民族和跨民族交往的积极态度又将增加各民族接触意愿,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
通过对跨民族友谊的文献整理发现,现阶段跨民族友谊研究仍存在不足,并提出以下展望:
从研究对象上看,如前文所述,多数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研究模仿国外对跨种族/跨族际/跨群际友谊的研究思路,缺乏跨民族友谊本土化研究范式。我国民族居住现状以“大杂居小聚居”为特点,五十六个民族分散在全国各省区市混合居住,在各省区市的少数民族又聚居在一乡、一县,且小聚居的少数民族区域内可能有汉族同胞同住,汉族区内也有少数民族聚居的情况。因此,各民族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和睦,大多数民族成员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基本相同,尤其是国家制度优势将民族独立和反政府活动等削弱民族关系的威胁降到最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的高度繁荣为民族交往交流提供足够物质和精神支持,导致我国跨民族友谊研究背景与国外跨种族/跨族际/跨群际友谊研究背景存在较大差异。未来跨民族友谊研究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研究模式,要深入考察我国不同民族成员间友谊实际发展情况及互动特征,结合当下民族工作政策和本土化社会语境,发展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能反映我国不同民族间友谊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研究范式,构建出反映中国特色民族实际的跨民族友谊研究理论,为我国的民族和谐和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从研究方法上看,虽然目前国内暂时多使用测量法对跨民族友谊进行量化研究,但近年来国内外开始出现实验法和干预法的研究尝试,更强调揭示跨民族友谊深层次机制以及为促进民族间的友谊关系提供实用性建议。比如研究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促进群际间产生跨群际友谊,并在三种干预模式下探讨跨群际友谊的产生(Vezzali et al.,2015)。阿伦等人(Aron et al.,1997)开发的亲密度构建任务程序涉及一系列逐步升级的相互自我披露和关系建设任务,已证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可以与陌生的外群体成员创建高水平的人际亲密度,这也暗示了自我披露和建立关系在跨民族友谊产生当中的重要作用。未来可以结合我国民族工作现状,包括充分考虑到我国独特的历史、民族分布、文化差异和社会情况,采用多元化和多维度的混合研究方法以获取更丰富、更深入的数据。同时,可加大与政策制定者和基础工作者的合作,参考其实践经验和意见,一方面可增加研究的实际价值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和政策提供实证依据,旨在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和睦和社会和谐的目标。
从研究工具上看,现阶段并没有公认的、统一的、仅针对跨民族友谊进行测量的评估手段,国内仅有的几篇对某地区跨民族友谊调查的研究工具都是在国外一般性友谊量表进行汉化的基础上修订而来,且国外跨种族/跨族际/跨群际友谊研究的测量指标多集中当下友谊状态,较少追溯过去的形成背景或考虑将来的延时效果,缺乏纵向研究和动态性研究,也限制了对跨民族友谊发展过程的研讨。所以,未来跨民族研究除了要编制适用于我国跨民族友谊调查的标准化量表,更要结合多种评估手段以弥补已有测量工具的不足。
参考文献
[1]陈立鹏,段明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几点思考——心理学的视角[J].中国民族教育,2020(1):17-20.
[2]陈晓晨,赵菲菲,张积家.跨民族友谊对民族态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J].民族教育研究,2018,29(6):96-103.
[3]管健.跨民族友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4):217-222.
[4]管健,荣杨.共同内群体认同:建构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认同[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7(1):39-49.
[5]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3):9-13.
[6]李修远.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中的集体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视角思考[J].西北民族大學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53-59.
[7]梁静,杨伊生.我国民族互嵌关系格局下跨民族友谊研究的本土化反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2(1):205-212.
[8]刘峰,佐斌.国外对大学生跨族群友谊的研究及对中国民族教育的启示[J].民族教育研究,2017,28(3):25-30.
[9]謝丹.多民族地区初中生族际友谊状况与教育对策(硕士学位论文)[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
[10]谢丹,常永才.族际友谊相关因素研究评述[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3,1(2):40-45.
[11]杨晓莉,赵佳妮.跨民族友谊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措施[J].甘肃高师学报,2018,23(6):99-101.
[12]赵福君,王党飞,张莉琴.新疆民汉合校中维汉学生族际友谊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5,25(3):11-14.
[13]赵佳妮.跨民族友谊对群际态度的影响:社会支持和亲密性的中介作用(硕士学位论文)[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9.
[14]赵旭峰,钟瑞华.红河南岸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5):8-13.
[15]赵野春,张立辉,滕承秀,等.渐进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然进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1):9-15.
[16]Allport G.The nature of prejudice[M].New Jersey:Addison-Wesley Pub,1954.
[17]Aron A,Melinat E,Aron E N,et al.The Experimental Generation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A Procedure and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7(23):363-377.
[18]Brewer M B,Kramer R M.The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Attitudes and Behavior[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85(36):219-243.
[19]Bukowski W M,Hoza B.Popularity and friendship:Issues in theory,measurement,and outcome[M]//In T J Berndt,G W Ladd.Peer relationships in child development.John Wiley & Sons,1989:15-45.
[20]Chu D B,Griffey D C.The Contact Theory of Racial Integration:The Case of Sport[J].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1985(2):323-333.
[21]Dovidio J F,Gaertner S L, Kawakami K.Intergroup Contact:The Past,Present,and the Future[J].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2003(6):21-25.
[22]Epstein J L.The selection of friends:Changes across the grades and in different school environments[M]//In T J,Berndt G W,Ladd.Peer relationships in child development.John Wiley & Sons,1989:158-187.
[23]Gaertner S L,Dovidio J F,Rust M C,et al.Reducing intergroup bias:elements of intergroup cooperation[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9,76(3):388-402.
[24]Graham J A,Cohen R.Race and sex as factors in childrens sociometric ratings and friendship choices[J].Social Development,1997(6):355-372.
[25]Granovetter M S.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J].Sociological Theory,1983(1):201-233.
[26]Grütter J,Gasser L, Malti T.The role of cross-group friendship and emotions in adolescents attitudes towards inclusion[J].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2017(62):137-147.
[27]Jakubiak B K,Feeney B C.Hand-in-Hand Combat:Affectionate Touch Promotes Relational Well-Being and Buffers Stress During Conflict[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19( 45):431-446.
[28]Karweit N S.The conditions for peer associations in schools[J].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enter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chools Report ,1979(282).
[29]Korol L.I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ulticultural Personality and Ethnic Tolerance Explained by Cross-Group Friendship? [J].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2017(144):264-282.
[30]Lease A M,Blake J J.A Comparison of Majority-race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a Minority-race Friend[J].Social Development,2005(14):20-41.
[31]Malle B F.How the mind explains behavior:Folk explanations,meaning,and social interaction[M].MIT press,2006.
[32]Mendes W B,Blascovich J,Lickel B,et al.Challenge and Threat During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White and Black Men[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02(28):939-952.
[33]Page Gould E,Mendoza-Denton R,Tropp L R.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cross-group friend:reducing anxiety in intergroup contexts through cross-group friendship[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8,95(5):1080-1094.
[34]Pettigrew T F.Generalized Intergroup Contact Effects on Prejudice[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7( 23):173-185.
[35]Pettigrew T F.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J].AnnualReview of Psychology,1998(49):65-85.
[36]Pettigrew T F.Future directions for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d resear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2008(32):187-199.
[37]Pettigrew T F,Tropp L R.Does intergroup contact reduce prejudice? Recent meta-analytic findings[M]//Reducing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Psychology Press,2013:93-114.
[38]Pettigrew T F,Tropp L R.A meta-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6,90(5):751-783.
[39]Popan J R,Kenworthy J B,Frame M C,et al.Political groups in contact:The role of attributions for outgroup attitudes in reducing antipathy[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9(40):86-104.
[40]Vezzali L,Stathi S,Giovannini D,et al.And the best essay is…:Extended contact and cross-group friendships at school[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15,54(4):601-615.
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Cross-ethnic Friendships
Yang Qiushan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Cross-ethnic friendship is regarded as a positive way of communication that promotes the identity of the ethnic community by improving the attitude of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and enhancing the positivity of inter-ethnic contact to realize the goal of enhanc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urrently, the study of cross-ethnic friendship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Based on a large amoun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ethnic friendship from the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trans-ethnic friendship at the current st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ethnic friendship research in a deeper and wider field.
Key words: Cross-ethnic friendships; Intergroup contact;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