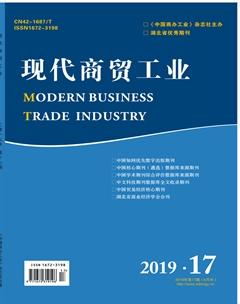精准扶贫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分析
秦龙金
摘 要:精准扶贫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一对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统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精准扶贫的工作提供必要性,反之,精准扶贫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从贫困与精准扶贫的认识出发,结合各组织各学者关于贫困的定义,对精准扶贫的概念进行思考;再回顾历史上致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并希望通过原因的回溯,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于精准扶贫的意义;进而分析精准扶贫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探讨这一对关系的内在联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必要性。
关键词:精准扶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7.064
“精准扶贫”自2013年被提出以来,席卷了中国大地的各个贫困地区,工作的参与涉及到政府、企业、学校、贫困地区等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的广大人民,简言之扶贫工作贯穿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扶贫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共同体意识需要精准扶贫来铸牢。关于扶贫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层次的关系,需要到历史中去找寻。
1 贫困与精准扶贫
扶贫,就世界范围而已,是一个很老旧的议程了。扶贫的首要问题是对贫困的认识,关于贫困,各个学者、各个国家、各个组织定义不一。十九世纪末,英国社会学研究者和社会改革者希伯姆·朗特里在对“国民效率”这一问题的反思中,提出贫困是导致国民体质衰退的重要原因,国民体质的衰退进而导致国民效率低下,在《贫困:城市生活研究》一书中,朗特里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是必需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即为贫困”;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认为,所谓贫困问题,是指没有足够收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家庭;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主张,“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朗特里、雷诺兹与森三位学者学术研究的侧重点主要经济领域,对贫困的认知更多是从物质层面展开。此外,从物质层面对贫困进行定义的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贫困,是指一定量的物质财产或收入的缺乏。贫困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要素的多层面的概念,绝对贫困、极度贫困或贫困指的是彻底缺乏满足基本个人必须的衣食和住所”。结合以上学者或机构对贫困的定义,笔者认为,这些定义是从一个广义的层面生发出来的,即贫困的普遍含义,具体而言是一种个人、家庭或群体对必备物质资料的缺乏;但就具体国家具体地区而言,除了最低限度的物质生存保障之外,贫困或许还应该与具体地区的文化有关,从外部看,这是一种脱贫精神的匮乏。
2 贫穷的原因
就西南山区这一范围而言,贫困既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又受社会因素决定。了解贫困的原因有助于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精准扶贫关系的理解,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于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2.1 自然因素
“任何生存者皆生存于生存环境之中,生存环境对生存者具有绝大的、不可超越的制约作用,人类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同样对人类具有天然的、绝大的、不可超越的、千百万年来如一的制约作用。”
“精准扶贫”自实施以来,其主要脱贫对象集中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以贵州、云南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又是整个“精准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是不争的事实。
农业社会以前,世界各地的狩猎采集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处于一种平均水平,不论在平原或是山地,游荡着的都是几十人一组的狩猎采集部落。偶然的能够被驯化动植物的獲得、信息传播便捷的交通、合适的气候,适宜的地形地貌成为了平原地区极具优势的先决条件,迅速地拉开了平原地区的人们同他们山地中的同胞的发展差距。早期的新月沃地、尼罗河谷底、恒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遂成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最早的城市与国家也先后出现于这些交通发达、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而此时此刻的安第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科迪勒拉山系还都处于狩猎采集的原始社会阶段,崇山峻岭中依然游荡着几十人一组的狩猎采集队伍。
踏入农业社会的平原地区,随着农业逐步发展,形成了一系列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这些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通过赋予更多人生命以意义,形成共同的认知,在共同的价值观下结成更大的合作之网,反过来推动农业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农业文化的出现是农业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农业文化反过来推动着农业社会向前发展,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凭借其不可抵挡的优势吞噬着一块又一块适合耕种的平原,结成更大的农业社会。在看到农业的发展催生出农业文化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农业文化对农业社会的发展所起到的反作用。 在山地社会中,由于农业的欠发展,在这一特殊的山地社会中形成的山地文化反过来对山地社会发展所需的物质生产产生的推动作用与其薄弱的生产能力一样微小。山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其薄弱的农业基础与弱势的农业文化相互影响之下,始终落后于平原地区。
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环境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子,并不是由于它对人性的影响,而是由于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但“地理环境对社会决定作用的形式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生着不同的结果,构成一个有规律的过程”。
2.2 社会因素
当人类进入到农业社会,告别萨林斯描述的“原始富裕社会”之时,不平等的萌芽开始出现。剩余财富的增多、私有制的产生、社会阶层的分化带来了导致贫富差距出现的财富分配制度,财富分配制度在阶级社会中不断得到固化,借助宗教与暴力机关的力量,形成阶级社会得以运行的一套逻辑。
当我们考虑到西南山地社会的贫困问题时,经济人类学关于财富分配的论述亦能为之提供一个清晰的观察窗口。首先,应当明晰的是,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思想是致贫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平等思想贯穿西南山地社会跨入农业社会后的大部分时期,马克思·韦伯将这种社会形态划分为专制社会,同时也是一种世袭社会。韦伯专制社会的定义是基于古代中国社会这样一个大的范围而言的,西南山地社会是其组成部分。在这样的社会中,只要世袭体制还完好无损,官员就会在个人层面上依赖统治者,政权的组织是由统治者血统直接的延伸。财富通常集中在少部分的群体手中,被统治阶级虽然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但在财富上的占比却少得可怜。
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产生了倾斜的财富分配制度,这种财富分配制度进而导致贫困。然而,平等的思潮在卡尔·马克思研究成果中被社会大众广为知晓,他原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资料占有的批判以及对工人阶级不公平境遇的同情却成为了党用以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有力武器。平等思潮不仅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以认识到并着手改善自身的贫困极不公平问题,同时对于彼时中国这样特殊的社会而言,实现公平、去除贫困从一开始便成为党引领国家前进的目标。
3 精准扶贫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简单概述西南地区历史上贫穷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之后,在21世纪的今天,在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号召下,这种贫困是可以被彻底消除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同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区互动交流有限,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常常令封建统治势力鞭长莫及。不少少数民族这种偏居一隅的状态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前还完整的保持着,一些民族甚至还停留在狩猎采集社会、母系氏族社会以及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阶段的例子是最好的证明。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清朝末年开始,多民族问题与国家发展的关系,逐渐被政治家、学者所重视,梁启超、杨度、章太炎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但彼时的“中华民族”实质上指的是汉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的意识逐渐发展,汉、满、蒙、回、藏五族概念被融入其中。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全面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概念进一步完善,将中华大地上识别认定的56个民族的囊括其中。在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贯彻下,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频度与深度达历史新高,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离不开的局面。中华民族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由于特殊的国情与历史的遗留因素,中国人民的贫困问题一直存续到现在。而今扶贫转入了精准阶段。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下,开展精准扶贫。从扶贫者的角度,精准扶贫在范围和深度上不同于传统的粗放式扶贫,扶贫范围上,它要求扶贫人员深入到一线贫困地区,细致了解这些地区的贫困状况;从深度来看,受扶对象以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为主,精准扶贫要求扶贫人员通过与贫困者长时间的直接接触,了解贫困者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摸清导致他们贫困的深刻原因,引导他们脱贫。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扶贫人员能以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扶贫工作的指导显得尤为关键。若缺乏对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识,扶贫人员就难以正确看待贫困地区同胞的贫困问题,不了解他们贫困的真正原因。扶贫工作的性质,有可能沦为一种扶贫者高姿态地对贫困者无偿的帮助,甚至伴随对贫困人员文化习俗肆意地破坏,极易对受扶者造成傷害。同时,这类的扶贫工作往往流于表面,脱贫无从实现。如果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增进各民族的社会边界的融合,那么精准扶贫便是在这融合了的社会边界之内重新分配各种社会资源。就像莫斯在《礼物》一书的末尾,表达出的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期许:共同劳动与个体劳动相交替的恰当节奏,在于财富集中后的分配,在于教育所倡导的人们彼此的尊重和互惠的慷慨,那时人们都围坐在共同财富的圆桌旁。
参考文献
[1]本杰明·希伯姆·朗特里.贫困:城市生活研究[M].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01.
[2]江姗.试析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国民效率思潮[D].南京:南京大学,2012.
[3]劳埃德·雷诺兹.微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宋正海.回归人类古老的生存信仰:地理环境决定论[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2):6-12.
[6]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8]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1.
[9]张坦.“宅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
[10]郑大华.中国年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J].民族研究,2013,(3):1-14.
[11]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западе Кита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