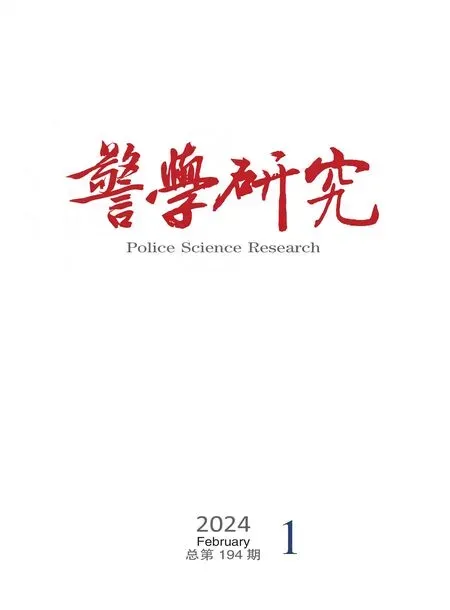袭警罪裁判规则实证分析与体系性重释
——基于609 份判决书的分析
陆 凌
(广西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4)
一、问题提出:袭警罪的理解分歧可能导致适用不统一
袭警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罪名,就罪状描述而言,该罪构成要件仍有较大解释空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77条第5款的规定,袭警罪的理解可能存在如下争议:何为暴力袭击,如何理解“人民警察”,该罪保护的法益是什么?理论上,对于“暴力”“袭击”、辅警是否适用袭警罪条款、法益等,确实存在很大争议。如何理解暴力,有最广义的暴力、广义的暴力和狭义的暴力之争。“暴力袭击”是否应具备相应特征,有以突然性等特征限制暴力和无须限制之争。关于暴力程度,有具体危险和抽象危险之争。辅警是否适用袭警罪条款,有肯定说、否定说、区分论之争。关于袭警罪的法益,主要有单一法益说和复合法益说之争。①各个争议的具体主张与理由详见于本文第四部分。
在立法解释空间与理论争议较大的情形下,司法认定可能不统一。当然,这有待检验。已有研究集中于条文的规范解读,为数不多的研究基于个案或者少数案例展开分析。有的研究虽称以上千份裁判文书为样本,但实际基于36份二审判决分析构成要件的认定。[1]有的研究虽基于较多判决书,但考察内容为行为手段、伤害程度。[2]据此,已有研究不能客观呈现袭警罪司法认定事实状态。
综上,本文拟基于609份判决书,运用统计方法,分析司法实践是否存在上述争议,若存在,司法如何认定,裁判规则是什么,进而分析司法认定的特征和存在问题,并针对实践诉求,体系性重释袭警罪的认定规则。
二、袭警罪司法认定实证分析
(一)样本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判决书来源于聚法案例网。2023年7月6日,笔者以“袭警罪”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选择文书性质之“判决书”,案由之“刑事”与“袭警罪”,得到1 224份判决书。随机抽取其中的50%,得到612份,删除无案件事实、未公开具体内容的3份,得到609份,作为本研究的样本。
(二)定罪实证考察
本部分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暴力袭击、辅警适用袭警罪条款、法益等袭警罪之核心争议的司法认定状况。
1.“暴力袭击”认定之统计分析。以下从行为方式、对象、结果、特征等方面统计分析“暴力袭击”的司法认定。
关于行为方式与结果。其一,行为方式方面。据表1,徒手袭击是袭警罪最主要的行为方式,此类行为共507例,占比83.25%。其具体形式包括手挠、手抓、手掐、抓掐、抓扯、掰扯手指、拍打、手击、肘击、拳击、捶打、击打、殴打、撞击、脚踢、脚踹、踢蹬、撕扯、拉拽、推搡、推怼、推倒、抱摔、掌掴、打耳光、牙咬、啃咬、撕咬、勒脖子、卡脖子、锁脖等。持械袭击侵害共68例,占比11.17%。所使用的器械包括菜刀、镰刀、匕首、刀片、剪刀、铁锹、铁棍、扳手、头盔、灭火器、燃烧的烟头、开水、金属簸箕、手锯、手铐、皮带、花盆、砖块、石块、石谷子、凳子、木棍、木棒、拐杖、木凳、杆将、树枝、拖布、瓶子、水瓶、水杯、执法记录仪、手机、小车钥匙、鞋、泥巴等。其中,采用一种方式袭击的共277例,占比45.48%,采用多种方式袭击的共230例,占比37.77%。驾驶车辆侵害的共28例,占比4.60%。具体包括驾驶轿车、摩托车、电动三轮车、电动车拖行,驾驶货车、小客车、面包车、越野车、吉普车、轿车、摩托车挤别、冲击、冲撞、顶行等,驾驶大型货车、轿车剐撞。6个判决没有说明具体行为方式,仅表述为“暴力袭击”。其二,暴力袭击对象方面。暴力针对人身共572例,占比93.92%,针对人身和物的共32例,占比5.25%,针对物的共4例,占比0.66%,未描述的1例。直接对物实施暴力的情形极少,直接对人民警察的人身实施暴力为绝大多数。其三,暴力袭击的程度、结果方面。在造成实害的案件中,轻伤的共11例,占比1.81%,轻微伤的共200例,占比32.84%,造成伤害但尚未构成轻微伤的共236例,占比38.75%,造成财产损失的共11例,占比1.81%。整体上,造成人身损害的共447例,占比73.3%,未造成实害结果的共151例,占比24.79%。对于未造成实害结果的案件,绝大多数判决仅描述暴力袭警事实,其中,多数判决使用“被告人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之表述,12个判决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如用木棍击打、砖块投掷等行为手段之表述,20个判决直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只有2个判决表明行为造成一定程度的危险,其表述为: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达到了危及人民警察人身安全的程度。①参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苏0602刑初381号,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案,〔2022〕辽0921刑初118号(判处三年有期)。另外,2个判决表明行为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②参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辽0204刑初435号,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辽0281刑初346号。据此,在未造成实害结果之案件的判决中,司法实践基本上采用了抽象危险的立场。

表1 行为方式、对象、结果与特征
关于是否以“袭击”限定“暴力”,从而使“暴力”满足突然性、积极性、意外性之特征。首先,没有判决使用突然性、突发性、瞬时性、意外性之表述。其次,42个判决在事实描述、事实认定中使用“突然”之表述。如张阅光在派出所办案区接受民警黄某询问时,突然冲到该民警面前用拳头朝民警左脸、左侧太阳穴的位置击打。③参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刑事案,〔2022〕辽0281刑初281号。10个判决在事实描述、事实认定中使用“趁民警、辅警不备”之表述。但是,对案件事实描述及其确认不等同于司法实践的主张、立场,这意味着不能将事实描述中的“突然”“趁民警、辅警不备”理解为法官要求“暴力袭击”具备“突然性”。而在52个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没有判决论及突然性、突发性。据此,至少在表述上,司法认定并没有以突然性、突发性、瞬时性、意外性等特征限定“暴力”。
2.辅警适用袭警罪条款和执法内容之统计分析。统计分析袭击对象的身份和辅警执法内容,以了解辅警适用袭警罪条款的情况。
据表2,袭击对象是人民警察的共392例,占比64.37%。袭击对象既有人民警察又有辅警的共136例,占比22.33%。袭击对象有人民警察、辅警和联防队员或者巡防队员的共2例,占比0.33%。袭击对象仅有辅警的共60例,占比9.9%。袭击对象有辅警、协警的3例。袭击对象既有人民警察又有协警、联防队员、社区保安队员、特保队员、巡防队员的共15例。整体上,暴力袭击对象为辅警或者包括辅警的共199例,占比32.68%。

表2 辅警适用袭警罪条款和执法内容
在袭击对象为辅警或者包括辅警的199个判决中,绝大多数判决未说明不具备人民警察身份的辅警何以适用袭警罪条款,仅有6个判决予以说明。在该6个判决中,有的认定辅警系在人民警察带领下执法,应视同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①参见弥渡县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云2925刑初288号,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浙0305刑初132号。,有的认定辅警执法权威一样受到保护②参见全椒县人民法院刑事案,〔2022〕皖1124刑初26号,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陕0802刑初1282号。,有的认定辅警系在民警指挥、指派下开展辅助性工作,符合法律规定。③参见永宁县人民法院刑事案,〔2022〕宁0121刑初50号,淇县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豫0622刑初264号。
关于辅警是否由人民警察带领或者与人民警察共同执行职务。112个判决表明人民警察“带领”辅警、协警等执行职务。在被袭击对象既有人民警察又有辅警的138个案件中,全部为人民警察和辅警一起执行职务。在袭击对象仅有辅警的60个案件中,绝大多数是人民警察和辅警一起执行职务,而在无公安机关或者人民警察带领下,执行任务的辅警的共4例,另外,出警人员为多人,但未说明出警者具体身份,辅警被袭击的共2例。
在袭击对象为辅警或者包括辅警的199个案件中,根据《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警务辅助人员意见》)第8条对于执法内容的划分④第8条:勤务辅警可以从事下列公安机关执法岗位的相关辅助工作:(一)协助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二)协助开展治安巡逻、治安检查和对人员聚集场所进行安全检查;(三)协助盘查、堵控、监控、看管违法犯罪嫌疑人;(四)协助维护案(事)件现场秩序,保护案(事)件现场,抢救受伤人员;(五)协助疏导交通,劝阻、纠正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采集交通违法信息;(六)协助开展戒毒人员日常管理、检查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公开查缉毒品;(七)协助开展公安监管场所的管理勤务;(八)协助开展出入境管理服务、边防检查;(九)参与灭火救援和协助开展消防监督管理;(十)协助开展社会治安防范、交通安全、禁毒等宣传教育;(十一)其他可以由勤务辅警协助开展的工作。,辅警执法内容“协助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的共162例,占袭击辅警案件81.4%,执法内容为“协助疏导交通,劝阻、纠正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采集交通违法信息”的共37例,占袭击辅警案件18.6%。说明在司法实践中,被袭击的辅警的执法均在辅警的职务权限之内。
3.法益认定统计分析。以下统计分析判决认定的袭警罪法益,以了解司法实践立场。
据表3,536个判决未说明袭警行为侵犯的法益,占比88.01%,73个判决说明了法益,占比11.99%。在该73个判决中,认定为单一法益的共45个,占比7.39%,其中社会管理秩序最多,共18个,认定为复数法益的共28个,占比4.6%,其中国家管理活动+人身权利的最多,共13个。

表3 法益类型
26个判决认定的法益为人身安全、人身权利或者包括人身安全、人身权利,占比4.27%,占说明法益的判决的35.61%。11个判决认定的法益为或者包括警察职务、执行职务、执法权威,占比1.8%,占说明法益的判决的15.07%。36个判决认定的法益为或者包括公务类(包括公务活动、国家管理活动、警察职务、警察执法权威),占比5.91%,占说明法益的判决的49.32%。
三、司法认定的特点、主要问题及其生成机制
(一)司法认定的特点
综合统计结果,发现袭警罪司法认定呈现出以下特点、倾向。第一,大多数行为方式(83.25%)为徒手袭击,而持械袭击、驾车侵害占比15.77%。第二,多数行为(63.35%)没有造成实害或者造成轻微伤以下(不包括轻微伤)人身伤害结果。结合第一个特征,说明绝大多数行为的暴力程度较低,造成的人身损害不严重。第三,没有判决论及暴力袭击应具备“突然性”等特征,说明司法实践不采用袭击限定暴力的立场。第四,绝大多数案件(99.18%)的暴力袭击针对人或者针对人和物,其中,93.92%案件暴力袭击针对人,而暴力袭击针对物占比仅0.66%,说明司法实践中直接对物实施暴力的情形极少,直接对人民警察人身实施暴力的居多。第五,多数袭击对象(64.37%)为人民警察,但袭击对象为辅警或者包括辅警占比33.05%,说明暴力袭击辅警在实践中也比较常见。第六,绝大多数判决(88.01%)没有说明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仅有11.99%的判决予以说明,说明在绝大多数判决中,行为是否侵犯袭警罪的法益并非定罪考量因素。
(二)司法认定的主要问题及其生成机制
综合统计结果,发现袭警罪司法认定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第一,法益考量严重缺失。绝大多数判决没有论及袭警罪的法益,行为是否侵犯了该法益不可得知,便存在行为未侵犯到袭警罪的法益而被认定为袭警罪的可能。另外,在说明法益的判决中,有警察职务、公务活动、人身安全、人身权利、公共秩序、社会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国家管理活动、执法权威等不同的表述,而有的为单一法益,有的为复数法益,说明司法实践对袭警罪法益的理解分歧较大,这可能导致定罪上的区别。第二,暴力的程度、是否侵犯到法益鲜少论及。由于绝大多数判决没有论及袭警罪的法益,暴力袭击在何种情形下侵犯到该法益,是否可罚,更鲜少被论及。如前所述,只有2个判决表明行为造成一定程度的危险,2个判决表明行为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在未造成实害结果之案件的判决中,97.35%判决仅描述暴力袭警的行为事实,便认定行为构成袭警罪,即只要行为人攻击了人民警察,就认定构成袭警罪。第三,暴力袭击针对物认定为袭警罪的理由不明。虽然绝大多数案件中的暴力袭击针对人,但仍有4个判决将暴力袭击针对物认定为袭警罪,这显然与条文表述的“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有出入。何种情形下暴力袭击针对物可认定为袭警罪,在解释上能否说得通,判决并未说明。第四,暴力袭击辅警认定为袭警罪的理由不明。虽然袭击的对象多为人民警察,但仍有9.9%的判决将仅袭击辅警的行为认定为袭警罪,22.33%的判决将袭击人民警察+辅警的行为认定为袭警罪,从身份上来说,辅警不属于人民警察,那么将袭击辅警行为认定袭警罪,理由何在?虽然也有几个判决认定辅警应视同民警、应同样受到保护,但其法律根据、理论支撑仍需进一步阐述。
综合司法认定的主要问题发现,第一,只要打执行职务的警察、辅警,极大概率被认定为袭警罪,即司法实践存在“唯攻击论”的倾向。第二,司法认定存在的主要问题关联密切,即若不考虑袭警罪的法益,自然不会考虑行为是否侵犯到该法益,也不会考虑袭击人或物、袭击辅警能否侵犯到该法益。
若要解决司法认定中关联密切的问题,须精准识别其生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体系性地重释认定规则。“唯攻击论”——只要打执行职务的警察、辅警即构成袭警罪,系“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直接照搬,但是,这一罪状并无行为程度、保护法益、行为如何侵犯到法益等构成要件的表述。这一罪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袭警从重”条款,并被《刑法修正案(十一)》设立袭警罪独立罪名后沿用。很显然,“唯攻击论”形成的规范原因是不考虑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关系、没有在《刑法》第277条体系框架下理解袭警罪的构成要件。要准确理解袭警罪,须基于袭警罪由妨害公务罪之从重条款演进而来的立法事实,厘清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关系。二者关系影响、决定着袭警罪构成要件的理解。
四、袭警罪认定规则之体系性重释:机理、路径与因素
针对“唯攻击论”的生成、传导机制——不考虑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关系→不考虑袭警罪的特殊性及其对构成要件理解的影响→不考虑袭警罪的法益→不考虑行为是否侵犯了该法益,下文对袭警罪认定规则体系性重释的安排为:首先厘清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关系,进而在二者关系框架下阐释袭警罪的法益,最后在二者关系框架下与袭警罪的法益指引下阐述“暴力袭击”的含义、辅警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形下受袭警罪条款保护。
(一)理解的前提与规定性:袭警罪之于妨害公务罪的特殊性
袭警罪的法定刑重于妨害公务罪的法定刑,即袭警罪设置了两个刑罚幅度,配置了“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更重的刑罚幅度,另外,没有配置罚金刑,根据何在?在条文表述上,《刑法》第277条第5款特别之处在于,第一,只能采用暴力手段,而不包括威胁,第二,暴力对象为人民警察。那么,哪些要素导致了袭警罪的法定刑更重?
首先,“人民警察”是否是袭警罪特殊于妨害公务罪的因素,从而导致袭警罪法定刑更重?理论界一种重要的思考方式即将特殊性集中于“暴力袭击”,而否定“人民警察”的特殊性。张明楷教授认为“人民警察”难以表明行为的不法增加,因为难以一概认为警察职务比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更为重要,另外,不能认为受到特殊训练的警察的身体反而更加需要刑法的保护;只有认为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构成标准高于第1款的暴力要求,因而对警察职务的阻碍程度更为严重时,才可以认为行为人的不法程度重于第1款。[3]但是,其一,由于我国警察职务的职责多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职责,其管理内容涉及违法犯罪、刑罚执行、社会治安、国(边)境治安、治安保卫、守卫重要场所、交通、消防、枪支弹药、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特种行业、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户籍、出入境,等等。,遭受侵害的可能性更广,且在处理防止违法犯罪活动、暴乱、群体事件以及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等问题时,遭受“暴力袭击”的风险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受害的概率、频率、程度来说,警察需要甚至更依赖于刑法保护。其二,也正是警察职业是和平时期风险极大的职业,最容易、频繁被攻击,一般预防的必要性更大,增设袭警罪宣示意义不言而喻。因此,“人民警察”是表明不法增加(更重),是袭警罪法定刑重于妨害公务罪法定刑的考量因素。需要说明的是,“人民警察”的特殊性指的是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特殊性,并不是“人民警察”身份的特殊性。另外,从立法历程、立法动机来看,警察职务的特殊性确实是增设袭警从重条款、袭警罪的首要考量因素。
其次,暴力袭击是否表明不法增加(更重),导致袭警罪法定刑更重的因素?从法条表述来看,除了袭警罪不可使用威胁方法,在暴力方面,“暴力袭击”与“暴力方法阻碍”有所区别。也正是承认这一特殊性,理论界才着力于暴力对象、暴力袭击的特征、暴力的程度以区分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本文同意暴力袭击是袭警罪特殊于妨害公务罪的因素。具体体现于哪些方面,下文将具体阐述。
综上,暴力袭击和“人民警察”对应的警察职务均是袭警罪特殊于妨害公务罪的要素。它们将影响甚至规定着袭警罪法益与其他构成要件的理解。
(二)目的法益:人民警察的职务行为
若在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关系框架下理解袭警罪的构成要件,法益应先被阐释,因为法益的理解会影响、指引着其他构成要件的理解。
袭警罪的法益主要存在复合法益与单一法益的分歧。部分学者认为袭警罪的法益是人民警察的公务活动和人身安全[4],包括国家正常管理秩序和人民警察的人身权益。[5]而部分学者认为袭警罪的法益是以警察公务活动为核心的社会公共秩序[6],人民警察的职务行为[7],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以维护公共秩序。[8]实际上,学者们都同意袭警罪的法益为或者包括警察职务,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包括警察的人身安全。
袭警罪的法益是否包括警察的人身安全?从立法表述、立法演进与动机来看,人身安全包含于袭警罪的法益。从条文表述上看,暴力袭击的对象是人民警察,袭警行为必然侵犯警察的人身安全,而且在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情形下,法定刑升格,说明袭警罪的法益包括警察的人身安全。从立法动机来看,袭警罪的法益包括警察的人身安全。但有学者指出,尽管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增设袭警罪多是出于对保护警察人身权和人身安全观念的支持,但是,立法者未必有这一想法。[9]从袭警罪的特殊要素来看,一方面,暴力袭击的对象是人民警察,似乎意味着袭警罪的法益包括人身安全。就对象与客体的关系而言,袭击人民警察,也就侵犯了人民警察的人身权利。但如前所述,袭警罪特殊于妨害公务罪的要素是警察职务,而不是人民警察这一特殊身份,因此,袭警罪的法益是警察的职务行为,而不是警察的人身安全。如此,从袭警罪特殊要素来看,结论并未唯一确定,即袭警罪的法益可解释包括人身安全,也可解释不包括人身安全。
本文认为,是否承认袭警罪的法益包括人身安全,并无太大意义。实际上,否定论者也承认袭击行为是通过侵害人身安全达到侵害警察职务的。设立袭警罪保护警察的人身安全只是手段,防止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才是设立该罪期望达到的目的。[10]将法益理解为人民警察的公务时,成立该罪也必须要求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暴力袭击行为。[11]因此,在判断暴力袭击是否侵犯警察职务这一目的法益上,无论是将法益理解为警察职务,还是人民警察人身安全+警察职务,二者的结论一致。概言之,暴力侵害正在依法履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人身安全是手段,妨害人民警察履行职务行为是目的。据此,袭警罪的法益可以表述为:通过侵害人身而侵害的警察职务。
法益的上述理解会影响袭警行为的可罚性。如果没有通过侵害警察人身安全而妨害警察职务,不能认定该行为构成袭警罪,如果侵犯了警察人身安全但并未妨害警察职务执行的,也不能认定该行为构成袭警罪。
(三)“暴力袭击”:针对人身、主动侵害性、达到阻碍公务程度
1.暴力应直接针对人身与不可避免危及人身的物。虽然理论上对暴力的对象,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暴力不仅包括对人身的强制力量,也包括对与国家机关人员等有关的物的强制力量。[12]有的认为不法有形力可以直接对人的身体行使,也可以针对物,但暴力应对人的身体有强烈的物理影响。[13]有的认为袭警罪中的“暴力”仅限于直接对警察的人身实施不法的有形力。[14]
在4个暴力针对物的案件中,有3起系被告人为逃避警察查酒驾、无证驾驶而逃逸并撞击运载警察的警车①参见通榆县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吉0822刑初354号;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辽0111刑初333号;攸县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湘0223刑初344号。,另1个系被告人猛踹派出所候问室的门导致正在锁门的民警倒地受伤。②参见榆中县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甘0123刑初110号。据此,司法实践将暴力袭击承载警察的物、与警察紧密结合的物的行为认定为袭警行为。整体而言,司法实践采取了暴力应针对人身的立场。这一立场是合理的,但应进一步说明理由。袭警罪中的暴力应针对人身,以人身为攻击目标,这可从袭警罪之于妨害公务罪的特殊性推导出来。从条文表述的语法结构上看暴力的对象,妨害公务罪之动宾结构为:阻碍+执行职务,袭警罪之动宾结构为:袭击+人民警察。据此,袭警罪之暴力对象应是警察人身,而妨害公务罪之暴力对象没有此限制,可理解为包括人身和物。然而,暴力应针对人身并非等同于暴力一律排除涉及物。当暴力直接针对承载警察、紧密结合警察的物,不可避免地危及警察人身时,应将暴力理解针对人身。有学者将此类暴力归入直接暴力,即直接对物使用暴力,间接打击警察人身,妨害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属于直接暴力,形式上看好像是间接暴力,但实质上同时针对警察人身,仍然是暴力袭警行为。[15]
综上,袭警罪的暴力可细化为两种类型,第一,暴力直接针对警察人身,第二,暴力直接针对承载警察、紧密结合警察的物,就效果而言,暴力作用于物即不可避免地危及警察人身。袭警罪中的暴力包括第二类型具有充分根据。其一,对居住人的房屋、承载人的交通工具实施放火、投放爆炸物等行为,确实会侵犯生命权、健康权。《刑法》分则第2章不少罪名(如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即是例证。其二,《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第1条第2款规定:“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实施下列行为的,属于《刑法》第277条第5款规定的“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实施打砸、毁坏、抢夺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据此,通过攻击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而攻击民警人身,属于“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在此,攻击警用装备是手段,攻击民警人身是目的,要达成该目的,必然要使用与目的紧密关联的手段。
本文属于狭义的暴力的立场,与广义的暴力说有所区别。后者认为暴力可针对对人的身体有强烈的物理影响的物,而本文认为暴力应直接针对承载警察、紧密结合警察的物,其效果与暴力和直接针对身体相当,而不仅是有强烈的物理影响。
2.暴力应具有主动侵害性。袭警罪的暴力是否要求突然性、积极性、意外性等特征?有的学者主张应用“袭击”限定“暴力”,从而有利于限制袭警罪的成立范围。[16]有的学者指出《刑法》第277条第5款并非单纯表述为“以暴力方法阻碍……”,而是使用了“暴力袭击”的表述。[17]有的学者主张以“袭击”的词典释义理解“暴力袭击”,根据《辞海》释义——袭击即乘敌人不在意或者不备突然实施攻击的作战行动,认为袭警罪的暴力应具有突发性、瞬时性和意外性。[18]根据通行的汉语词典的解释,袭击是指突然打击,不具有突然性的对人暴力不能评价为“暴力袭击”。[19]但是,《现代汉语词典》将“袭警”释义为用暴力手段攻击正在执行公务的警察。也就是说,《现代汉语词典》不要求袭警具备突然性。因此,根据词典释义不能得出袭警罪的暴力必然要求突然性等特征。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词典释义仅仅是划定一个进一步进行刑法解释的大致范围和基本界限。[20]而且,《刑法》中唯一使用“袭击”的条文即第451条,其规定:本章所称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时。该条文中使用“突然袭击”,说明“袭击”不需要突然性,否则就是语意重复。如果不要求突然性,也无需瞬时性和意外性。另外,如果要求突发性、瞬时性和意外性,唯恐司法实践中没有完全符合要求的案例,那么袭警罪条款可能被闲置。
“暴力袭击”要求何种特征?本文认为,“暴力袭击”应具备主动侵害性。当然,暴力的主动性并非袭警罪的特殊要求,而是妨害公务罪等犯罪对于暴力的一般性要求。强调暴力的主动侵害性,主要考虑袭警罪认定中的一个难点,即被告人摆脱、逃脱、反抗及其该过程中使用暴力的认定问题。暴力的主动侵害性,客观上要求具有侵害的行为,主观上要求具有主动侵害法益的意愿、故意。因此,单纯摆脱、逃脱等消极行为,而没有加害行为,不属于暴力袭击。但如果摆脱、逃脱过程中使用暴力,超出了被动,表现为主动加害,客观上有侵害行为,主观上有侵犯人民警察人身的故意,应认定为暴力袭击。实践中,针对出警行为的抵抗、反抗往往具有暴力性。在认定具有反抗情节的60个判决中,以暴力作为手段进行反抗的共57例。如在强制传唤过程中,朱重财暴力反抗,用牙齿咬伤王某右手上臂,用手指抓伤多名辅警,经鉴定,吴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民警王某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①参见信丰县人民法院刑事案,〔2022〕赣0722刑初167号。再如,民警依法对任恬右强制传唤,任恬右辱骂并暴力反抗民警,用手推打、撕扯民警栾某、刘某,辅警张某。②参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辽0624刑初196号。既然抵抗、反抗本身就是暴力行为,将其认定为暴力袭击也不成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摆脱、逃脱的动机与侵害故意并非对立,亦即被告人出于摆脱、逃脱的动机或目的,而故意采用侵害手段,仍属于暴力袭击行为。
3.暴力应达到阻碍公务的程度。关于暴力程度,有的学者认为必须达到阻碍公务执行的程度[21],有的学者认为具有妨害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抽象危险即可。[22]袭警罪作为妨害公务罪的特别条款,对暴力程度的要求至少应与妨害公务罪的一致。妨害公务罪是具体危险犯,妨害行为应对依法执行职务形成“阻碍”,从而使执行职务变得更加困难,才可能成立妨害公务罪。袭警罪作为妨害公务罪的特别条款,也应是具体危险犯。由于袭警罪的法益是人民警察的职务,暴力应对人民警察职务的正常执行造成紧迫的、现实的阻碍危险,达到阻碍警察职务的程度,才可能成立袭警罪。又由于阻碍警察职务的程度是通过暴力袭击人民警察达到的,因此,行为也应对人民警察人身安全具有紧迫的、现实的危险。
如何判断暴力达到阻碍公务的程度?首先,在判断逻辑、路径上,根据手段与目的法益的传导关系,即暴力袭击→人民警察遭受人身伤害或现实危险→阻碍公务,可将暴力达到阻碍公务程度的判断,转化为对影响警察职务正常执行的人身伤害或现实危险程度的判断。其次,在考量因素上,应综合考量持械情况、侵害部位、侵害次数、侵害时长、实际伤害及其程度,以及警察职务行为被耽误的时间、警察职务行为继续执行的可能性与难度(如是否需增援警力)、警察职务被耽误或被阻碍的后果,等等。根据上述判断逻辑、路径、因素,可得出以下几类结论:其一,一般情况下,暴力袭击造成轻微伤、轻伤等以上结果,导致人民警察无法继续履行职务、警察职务行为被明显耽误或造成严重后果,属于暴力达到阻碍公务程度。其二,暴力袭击造成人身伤害,但还不构成轻微伤,若导致警察职务行为被明显耽误或造成严重后果,也应认定为暴力达到阻碍公务程度。其三,对于没有造成实际伤害的暴力行为,如果行为本身危险性高,造成严重结果的可能性大,如利用杀伤性较强的工具侵害,或撕咬、踢踹要害部位,或长时间、持续侵害,对警察人身安全造成现实危险,也对警察职务正常执行造成现实危险的,也应认定为暴力达到阻碍公务程度。在151个未造成人身伤害的案件中,14个案件的行为人使用了菜刀、铁锹、砖头等袭击,6个案件的行为人驾车顶撞或拖带,2个案件的行为人用木棒向头部、脚踹肚子,这些行为对警察人身安全造成现实危险,应认定为暴力达到阻碍公务程度。总之,判断暴力是否达到阻碍公务的程度,实质即判断暴力袭击是否对警察人身造成伤害或产生现实危险,该人身伤害或现实危险是否影响警察职务正常执行。
而对于较轻微的暴力行为,但没有明显耽误警察职务执行、没有增大执行难度的,不宜认定为达到阻碍公务程度。在司法实践中,一次性扇耳光、拍打、推搡、推倒在地且未造成人身伤害的行为,一般不会耽误或阻碍警察职务执行,不宜认定为暴力达到阻碍公务程度。如在出警过程中,被告人杨超突然使用右手扇民警巫某某左脸耳光,随后被出警民警控制并带至什邡市公安局接受调查。①参见什邡市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川0682刑初86号。类似判决参见邵武市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闽0781刑初183号。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浙0203刑初971号。在此案中,被告人用手拍打民警非要害部位一次,没有也不太可能对人身产生伤害,且其随后被民警控制并被带回调查,说明警察职务行为没有被耽误,因此,被告人扇民警耳光的暴力程度没有达到阻碍公务程度。另如,被告人王富芹到北京市密云区政府门前要求解决其问题,并称15日民警王金福等人将其打伤,要求治疗,过程中,多次辱骂、推搡民警王金福。②参见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京0118刑初301号。类似行为见于阜新市太平区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辽0904刑初63号。再如,在民警依法传唤高某时,被告人陈丽丽为阻拦民警将其丈夫高某带走,突然上前将民警王某仰面推倒在地。③参见舒兰市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吉0283刑初137号。类似行为见于成县人民法院刑事案,〔2021〕甘1221刑初167号。上述用手拍打、推搡、推倒的行为,一般不会对人身产生伤害,且行为人随即被民警控制,警察职务行为也未被耽误,因此,不应认定暴力达到阻碍公务的程度。
(四)辅警受袭警罪条款保护:民警在场指挥、在辅警权限内执法、程序合法
关于辅警是否适用袭警罪条款,有肯定说、否定说、区分论之争。肯定论者将辅警视为警察,将辅警“扩张解释”为人民警察。[23]否定论者基于身份论,认为辅警不属于人民警察,自然不是袭警罪保护的对象。[24]区分论者认为当辅警与人民警察一起执法、辅警执法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时,可成为袭警罪保护的对象。[25]
本文认同区分论的做法。当暴力袭击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警务辅助工作的辅警时,可成立袭警罪,而当辅警单独执法时,不适用袭警罪条款。一方面,单独执法的辅警并非“依法执行职务”,自然也不适用袭警罪条款。《警务辅助人员意见》第9条规定了辅警不得从事的工作,其中第八项为“单独执法”。另一方面,对于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警务辅助工作的辅警,依法执行职务的,适用袭警罪条款。其根据在于,其一,《警务辅助人员意见》第4条规定,辅警应当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警务辅助工作;辅警协助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履行职责的行为后果由其所在公安机关承担。上述规定意味着,在协助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时,辅警与人民警察的行为后果一致。其二,对于该部分辅警以公务论,而非身份论,契合刑法的立场。《刑法》第93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其中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可见,“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实质根据。其三,从袭警罪之于妨害公务罪的特殊性与袭警罪的法益来看,区分论是恰当的。如前所述,“人民警察”特殊性是指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特殊性,并不是“人民警察”身份的特殊性。袭警罪保护的是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警务辅助工作的辅警,而不是全部的辅警。也正是由于袭警罪的法益是警察职务,只有暴力袭击侵犯了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辅警的警务辅助工作,才可能侵犯到袭警罪的法益。
如何理解“在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很多学者主张依法共同执行职务、一起执法并且辅警执法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即将“在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理解为人民警察物理在场的、共同履行职责之情形。指挥和监督的形式可多样,包括在场的和非在场的、当下的和非当下的、共同实施行为和非共同实施行为的,等等。很显然,上述见解是对“在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的限缩解释,即人民警察在场的、当下与辅警共同执行职务之情形。基于限制因将辅警解释为人民警察而扩大袭警罪适用的立场,这一限缩解释是可取的。
同时,辅警执行职务应合法。首先,执法应在辅警的职务权限之内,即属于《警务辅助人员意见》第7条、第8条规定的可以从事的公安机关相关辅助工作①第7条:文职辅警可以从事下列公安机关非执法岗位的相关辅助工作:(一)协助开展文书助理、档案管理、接线查询、窗口服务、证件办理、信息采集与录入等行政管理工作;(二)协助开展心理咨询、医疗、翻译、计算机网络维护、数据分析、软件研发、安全监测、通讯保障、资金分析、非涉密财务管理、实验室分析、现场勘查、检验鉴定等技术支持工作;(三)协助开展警用装备保管和维护保养、后勤服务等警务保障工作;(四)其他可以由文职辅警从事的工作。,超出辅警职务权限即不合法。其第9条规定了辅警不得从事的工作②第9条:辅警不得从事下列工作:(一)国内安全保卫、技术侦察、反邪教、反恐怖等工作;(二)办理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三)案件调查取证、出具鉴定报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四)执行刑事强制措施;(五)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六)审核案件;(七)保管武器、警械;(八)单独执法;(九)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辅警从事的其他工作。,若辅警实施该条款中的行为即违法。虽然,在司法实践中,袭击辅警的案件的执法内容为“协助预防、制止违法犯罪活动”和“协助疏导交通,劝阻、纠正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采集交通违法信息”,亦即辅警的执法均在辅警的职务权限之内,但审查辅警执法是否属于职务权限之内仍有必要。其次,辅警执行职务在程序上应合法。
综上,袭击辅警适用袭警罪条款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人民警察在场指挥和监督辅警,二者共同执行职务,第二,执法在辅警的职务权限之内,且程序合法。
——献给为战疫而奉献的人民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