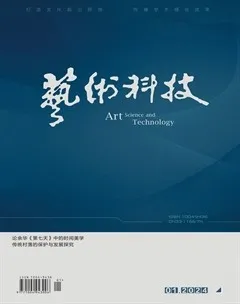论王小帅现代化主题影像空间建构
摘要:目的:作为“第六代导演”之一的王小帅,其电影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和空间意识。例如,很少采用三段体叙事、零散化叙事和主客观视点自由转换等叙事手法,从不让技巧脱离故事内容,形成喧宾夺主的场面,而是依托起伏较大的故事情节和意想不到的节奏切分来讲述故事。同时,他的电影热衷于表达个人和时代记忆。王小帅的电影叙事模式,着重通过人与人、人与城市之间的冲突来表现底层边缘群体与社会环境的格格不入,并由此揭示边缘人群与社会环境难以协调的深层原因。在他的《青红》《我11》和《闯入者》三部曲中,通过多重空间的叠加,表征了早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大、城市异化和城乡矛盾等问题。方法:文章通过分析记忆空间、社会空间和城乡空间,观照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发展历程。结果:通过分析王小帅电影所表征的社会问题,揭示现代化繁华背后的创痛和生活的残酷,将隐匿在主流意识形态背后的矛盾以原生态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结论:王小帅在电影里通过对记忆空间、社会空间和城乡空间的建构,书写了社会底层边缘群体孤独和迷茫的精神状态,表现了城市底层民众顽强的生命力,其影像空间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意蕴。
关键词:王小帅;电影;记忆空间;权力空间;城市空间;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1-0-03
伴随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电影创作者的内容创作和题材选择也受到影响。王小帅的电影坚持“以人民为创作导向”的理念,以人民为主体,观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1]。他的电影在书写人民性的同时,还注重建构影像空间。在其电影作品中,空间不仅是生产资料的对象和载体,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既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又是能够被感知的生活空间,具有人的属性,是蕴含精神属性的物质空间。
1 记忆空间: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消解
“集体记忆又称群体记忆”[2],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3]。王小帅的父母是“三线建设”的一员,他一出生就随父母来到贵州进行“三线建设”。作为“三线建设”群体成员的王小帅,对过去回忆的再现是对“三线”集体记忆的一种怀旧和建构。电影
《我11》中通过煤球炉子和炉上的铝制水壶、穿着中山装的男主人公和戴着碎花套袖的女主人公、凤凰牌自行车、台式收音机等,真切还原了过去家庭空间的生活场景。工厂墙面上的标语和广播、对人们行為的规训还原了以前工人工作的日常。王小帅立足当下,通过复刻过去工业厂区空间和再现工人日常家庭生活,还原了一段远去的集体记忆。老物件的出现营造了电影的真实感,也使电影故事叙事变得更加可靠。
工人的身份问题也在集体记忆的构建中被反复呈现,凸显了他们对身份的焦虑。在《青红》中,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工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发生变化,失去了往日的荣光。老吴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焦虑,他迫切地想要回到上海,哪怕是失去工厂的“铁饭碗”。《我11》里,当“三线建设”的荣光褪去后,谢觉强的父亲同样产生了想要调回上海的迫切渴望。产生身份焦虑的深层原因是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出现了问题,三线建设者一般来自经济较发达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初到建设地产生的心理落差,加上气候、语言和饮食等差异,造成了三线建设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区隔。在电影中,很少看到三线建设者与当地居民交往,他们基本都是和同群体展开交流。王小帅的电影主要表现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三线建设”不再受到大幅度的宣传和颂扬,大量三线工厂开始面临亏损甚至破产的命运,因此很多三线建设者纷纷想回归大城市。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和主观阶级认同,都是电影中三线建设者难以产生身份认同的原因。
王小帅的“三线”电影营造出种种近乎真实的历史幻象,重现了过去“三线建设”的历史给观众带来的怀旧体验。在怀旧中王小帅再现了曾经三线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和社会转型下个体产生的身份问题及其精神上的迷惘与痛苦,也让“三线”历史得以流传和被铭记。
2 社会空间:社会秩序的建构
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也是对个人进行规训的执行场所。规训是一种社会权力,在王小帅建构的社会权力空间中,充满了集体规训个人的符号。在
《我11》中,王憨一家因“三线建设”从上海来到西南山区,电影从王憨这个无忧无虑的11岁小孩的视角,讲述了一起“杀人事件”。电影开头的十字路口有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在王憨父亲送王憨上学途中经过的墙上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工厂大门上写着“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对联,这些符号都在暗示当时是红色革命年代。《地久天长》中,厂里的“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标语,“优生优育”的宣传告示,以及刘耀军和王丽云害怕怀二胎被发现的对话,都在告诉观众当时正处于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需要国家政策同意。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活动以工厂大院的集体为单位,个人的任何活动都要服从集体的安排,工厂大院规训着人们的行为和作息时间。在电影《青红》和《我11》中,工厂以广播为媒介,严格管控个体的工作和学习时间。时间的规划是对人们日常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规训,人们的任何行为都要服从工厂的军事化管理,个人的行为习惯和私人感情也要让位于工厂的生产目标。
工厂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紧张的国际局势,而且工业结构分布不均,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和华北一带,为了保障国防安全,国家开展了一场大规模推进西部工业化的运动,也就是“三线建设”运动。这场运动应用劳动密集型策略,动员许多工人参与建设。为了加强人员管理,按时完成生产任务,工厂会对工人进行任务划分、行为规训与监督和时间的管控。
集体对个人行为的规训,有利于整合分散的个人力量,提高群体的生产力,同时也有利于建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表示社会有序状态或动态平衡的社会学范畴”[4],“在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中,社会秩序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共同体是对社会秩序的经济、政治特性进行总体性和关联性的把握”[5]。在王小帅构建的权力空间中,社会秩序的建构不仅依靠集体规训,更重要的还在于个体自觉。三线建设者基于国家需要,自觉投身祖国建设事业,他们有共同的价值信仰规范,把集体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来自五湖四海的三线建设者成为一个共同体,其对共同体的认知增强了群体凝聚力,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权力可以通过一套精心设计的系统性空间知识形态(城市规划话语的形成、空间建筑范式的塑造、空间建筑元素的象征性与符号性表达)来创建自身的话语机制,从而完成将空间、人口、生命技术、组织制度融为一体的社会治理。”[6]王小帅建构的权力影像空间,呈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早期的工业化管理和监督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个人与集体的命运融为一体,集体对个人的权力规训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又是达到生产目标的要求。
3 城乡空间:现代化书写与社会互嵌
工业化的出现打破了封闭的农业社会组织,它要求人具有新的角色和功能。在变化和流动的工业社会中,个体不可能永远待在一个封闭、僵化的环境里,乡村中的家庭集体经济组织受到冲击,加上城市化发展对乡村土地的侵占以及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加速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王小帅的城市影像空间展示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城市遭受的种种不公待遇。例如影片《十七岁的单车》中的小贵,他从偏远贫穷的乡村来到城市务工,丢了公司配置的自行车,在寻找自行车的过程中遭受了来自城市的恶意和排挤。再如《扁担·姑娘》中的高平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被骗钱,最后丢了性命。乡村人员虽然进入了城市,但是很难真正融入城市,这是因为乡村与城市之间存在隔阂,其中最明显的便是身份隔阂。“1958年,我国新的户籍制度建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被严格限制,这种充满矛盾的、等级制的城乡户籍既分割了两种社会生产和生活,也分割了权利。”[7]户籍制度造成了资源向城市倾斜,城市居民拥有更多优于农村居民的权利,而这也造成了城市与乡村居民身份权利的不平等。
身份权利上的不平等导致进城务工人员产生身份焦虑,如《扁担·姑娘》中的高平来到城市打工,即使自己没有钱也给自己买了一套西装;《十七岁的单车》中周迅饰演的保姆,经常趁主人不在时偷穿主人的裙子和高跟鞋。对他们来说,亮丽的衣服是城市身份的象征,可以掩盖自己来自农村的身份,从而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王小帅电影中的人物在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往往是以他者为镜,而城市居民就是王小帅的城市影像空间中的“他者”。高平、阮红和小贵等进城务工人员以城市居民为镜,进行行为模仿和装扮,达到自我身份认同。在王小帅呈现的城市影像空间中,这种身份焦虑不仅存在于农村居民群体中,还存在于城市居民群体中。例如《十七岁的单车》中的小坚一直生活在城市,为了拥有其他伙伴也拥有的自行车,不惜偷钱买车。自行车在这里是家庭财富的象征,能遮掩小坚家庭并不富裕的现实,达到维护自我形象的目的。
工业主义催生的现代化大都市以货币经济为主导,这激发了都市人对货币的狂热追逐。王小帅建构的城市空间表征了金钱对人的异化。例如,《扁擔·姑娘》中,“扁担”们为了金钱而互相残杀;《十七岁的单车》中,小坚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偷钱买自行车。金钱对人的异化导致人们精神空间的疏离。“受货币经济工具理性的影响,现代主体的心灵也被物质文明所‘异化’。主体的生活内容由此发生改变,即排斥了非理性的、本能的特质和主观独断的冲动,也就排除了情绪化的体验。”[8]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观念,现代社会组织的内在脉络就是理性。理性强调效率,而效率是现代城市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在《十七岁的单车》中,小坚所工作的快递公司为员工配备新自行车,就是为了更快地将信件送到收信人手中;《扁担·姑娘》中的高平选择不正当的赚钱方式,也是因为这种方式来钱快。在快节奏生活的催压下,城市空间中的人际关系变得肤浅、短暂和淡薄。当朴实、善良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来到与乡村环境截然相反的城市时,很难在城市中得到他人的帮助,遑论融入其中。他们基本都是同乡间互帮互助,如《扁担·姑娘》中冬子带着一根扁担,只身来到武汉,投奔先来此地的同乡兼好友高平;《十七岁的单车》里,小贵与老乡一起住;等等。
城市林立的高楼大厦和鲜明的区域分割,使得城市物理空间变得狭小,无形之中拉开了主体间的精神距离。城市中的人在空间上的距离虽近,但在心理与精神方面却相隔甚远。城市主体间的精神疏离与传统乡村和谐的人际交往恰恰相反,这导致进入城市的农村居民很难适应这种人际交往方式。同时,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很难让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心声得到倾听。因此,在王小帅建构的城市空间中,农村外出务工人员通常是沉默不语的,就算被误会也不会开口解释,沉默的外来人员成了城市里的“异乡人”。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隔阂,主要源自现代和传统的对立矛盾。现代文明冲击着传统乡村文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更是加深了城乡隔阂。王小帅的城市空间电影表征了城市异化和城乡发展失衡的问题。面对城市异化问题,需要遵循城市主体性原则,城市发展需要与自然共存、与环境共存。针对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国家提出了多项问题解决对策,如实行免农业税、新农村建设等措施,以此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城市和乡村应是互相依存、和谐共生的关系,城乡应实现融合发展。
4 结语
王小帅建构的影像空间以现代化为主题,记录了早期中国工业化建设运动——“三线建设”,再现了三线建设者在特定年代的心路历程和面临的人生困境。同时,他也关注到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边缘群体和城市异乡人的境遇和感受。王小帅的影像空间聚焦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现代性感受,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对人精神空间的忽略。其现代化主题影像空间叙事,是认识现代化的一种方式,即通过对现代化背景下个体生命的书写,反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在电影中随着没有结尾的叙事而留置,促使人们去思考怎样更好地推进现代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索杰.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7.
[2] 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13.
[3]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9.
[4]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353.
[5] 磨胤伶,王坤.个人化社会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马克思共同体视阈下的社会秩序建构[J].广西社会科学,2020(8):86.
[6] 张羽佳.权力、空间知识型与乌托邦[J].探索与争鸣,2016(8):84.
[7] 姚尚建.城市身份的权利附加[J].行政论坛,2018,25(5):27.
[8] 邓志文.城市精神空间的生态反思及其重塑的实践路径[J].云南社会科学,2021(2):182.
作者简介:李婷婷(1998—),女,江西南昌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