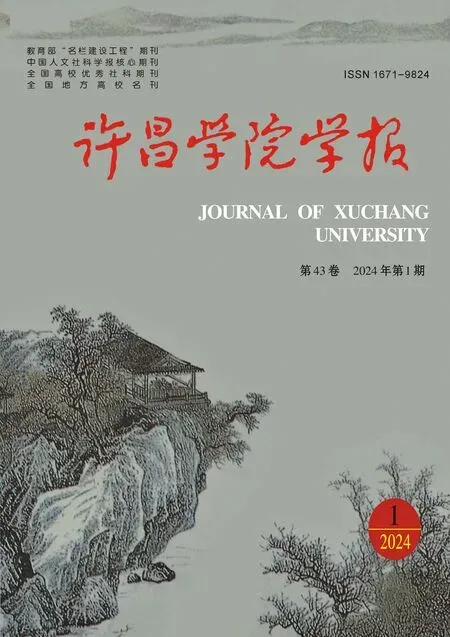孙吴“典军”小考
——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
崔 启 龙
(故宫博物院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北京 100009)
一、问题的提出
走马楼吴简州中仓出米简中常可见到临湘官仓供给“典军”及相关吏员廩奉的记录,这类记录的格式往往为“邸阁郎中被军粮都尉移右节度府某年某月某日书,给某人某年某月奉”。为方便讨论,现将这类文书集成、复原,胪列如下。


8.□/元年四月卅日付典军曹史许尚□(壹·1793)


12.禾二年七月,人月三斛,除小月,月人六日,其年二月十二日付典军曹史章松傍人吴衍、任奴(柒·2018)

14.出仓吏黄讳、潘虑所领嘉禾元年税吴平斛米十一斛三斗二升为稟斛米十一斛七斗九升+□邸阁右郎中李嵩被督军粮都尉移右节度府嘉禾二年八月六日癸+亥书给右田曹典事赵彻半年稟起嘉禾二年闰月讫十月月二斛除小(捌·2875+2928+2927)


17.典军户曹史章松、吴雒,集曹史赏立三人各一年奉,俱起嘉禾元年八月□□(陆·6042)
18.……曹典事□□□年一月起嘉禾二年七月讫□月……(陆·6065)

与一般州中仓出米文书不同,此类文书都是“右节度府”指示督军粮都尉、州中邸阁发放奉米的记录,发放对象包括“典军(某)曹史/典事”“某曹史/典事”“典军所主吏”。可以注意到,这些记录所载曹吏职衔颇不统一,有只称“典军曹史/典事”者(简1、6、8、9、11、12、13),有称“典军某曹史/典事”者(简4、5、7、10、17),这两类记录间亦有相重叠者,如第一类中的“典军曹史”许尚(简8、9)和章松(简12、13),在第二类中分别作“□□金曹史许尚”和“典军户曹史章松”,又如简10先后出现“典军主吏曹史徐檐”和“典军曹史章松”,这说明“典军曹史/典事”是“典军某曹史/典事”的简写。此外,简13中“典军所主吏缪雒”的奉米亦由“典军曹史章松傍人吴衍、任奴”一并代领,说明其身份应与典军曹史相类,均是典军之吏,只不过不具体署曹而已。除以上三种,还有径书“某曹史/典事”者(简2、3、14、15、16),虽未冠以“典军”,但其曹吏亦有称“典事”,考虑到此种官称较为特殊,不见于《吴书》以及吴简所示长沙临湘的郡县吏员系统中,加之其奉米供应亦需经由右节度府批准,我们怀疑这些曹吏也应是典军下的属吏。
需要补充的是,简3、15、16出现了“右(大)仓曹”,有学者结合出米简中“大仓丞”的记录,认为“右(大)仓曹”也是建业太仓辖下的职官(4)可参苏俊林:《孙吴基层社会身份秩序研究——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湖南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78页,后收入其著《身份与秩序——走马楼吴简中的孙吴基层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77-278页;徐雪:《〈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柒]〉职官称谓语研究》,西南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页。,值得商榷。首先,检诸汉唐史籍,未见有太仓管理机构分曹治事者(5)《续汉书·百官志》云:“太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国传漕谷。丞一人。”《宋书·百官志》:“太仓令,一人。丞一人。秦官也。晋江左以来,又有东仓、石头仓丞各一人。”均未言太仓下有分曹事。唐代的情况可参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第三章第四节“太仓的受粮和管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78页),其中征引唐代政书及含嘉仓砖铭,也均未见太仓下之曹。;其次,即便太仓令、丞下分设左右二曹,其曹名称当也不会与本署同名,称作“左大仓曹”“右大仓曹”。考虑到嘉禾年间长沙、武陵一带多有孙吴中军驻扎(详后),不排除“(大)仓曹”是典军下属负责处理与太仓往来文书、管理仓廪账簿的机构。
此外,简19中所见“中户曹尚书郎黄声”也颇值得瞩目,“中户曹尚书郎”乍看似是中央尚书之下的户曹郎,但细究之下却似是而非。汉晋以来,尚书机构下分“尚书曹”和“郎曹”,前者统率后者,每曹尚书一人,检诸史籍,其职官称呼一般是“某曹尚书”或“某部尚书”,后者为“一曹一郎”或“一曹多郎”,一般称“尚书某曹郎”“某曹郎”或统称“尚书郎”,但从未见有“某曹尚书郎”的称呼(6)《吴书·张温传》一篇就载有尚书吏的三种称呼,其曰“张温字惠恕,吴郡吴人也……拜议郎、选曹尚书”。暨艳“字子休,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又礼之还,当亲本职,而令守尚书户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结合以上所论,颇疑“中户曹”亦是典军下之曹署,“中”或非“中外”之中,而是“左中右”之中,户曹事繁,分为三曹应在情理之中。孙权之世,郎吏常作为朝廷使者频繁外任,故在中军远征之际,“尚书郎”被临时调任至“典军”属下处理文书事务也不无可能。

如上论不误,则典军之下有录事、主吏曹、户曹、田曹、仓曹、兵曹、金曹,俨然如同郡县行政组织。那么,“典军”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以往学界对此关注颇多,但焦点大都集中在“右节度”及其所反映的孙吴军粮调配体系上,相较之下,对于出米对象“典军(某)曹史/典事”的关注则明显不足。就笔者管见,目前仅有王素、谷口建速、苏俊林、徐雪、戴卫红等学者对此问题有所涉及。王素认为“典军曹史应是当时讨伐武陵蛮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2];谷口氏认为“典军”是孙吴负责军功查定和军队人事的官员[3]110;苏俊林[4]285、徐雪[5]58-60认为典军曹史是受中央管辖的军事系统的列曹官;戴卫红则认为“典军”或是“典军将军”之省,“典军曹史”即是“典军将军”下属诸曹的吏员[6]422-424。除此之外,唐长孺先生早在《吐鲁番文书中所见高昌郡县行政制度》中也论及“典军”,他认为汉晋史籍中“典军”基本均是中央官,“大致掌管功罪赏罚,行军布阵等军令之事”,但地方州郡僚属可能亦有以“典军”“典兵”为名目者,“只是于史无征而已”[7]363-364。综观以上成果,大都非专门之论,相关认识亦不乏抵牾之处,故关于此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二、汉晋史籍中的“典军”
“典军”之官,最早见于东汉灵帝“西园八校尉”。《后汉书·孝灵帝纪》载,中平五年“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李贤等注引《山阳公载记》详载八校尉姓名,其中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8]356,可见当时“典军”是为校尉名号。这一名号随后为曹操政权沿用,夏侯渊、丁斐先后担任。《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裴注引《魏书》:
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故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9]270
同书《曹爽传》裴注引《魏略》载:
(丁斐)为典军校尉,总摄内外……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为人所白,被收送狱……太祖笑,顾谓左右曰:“东曹毛掾数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9]289
彼时“西园八校尉”不复存在,《魏略》所载丁斐事迹中有“东曹毛掾数白此家”之语,所谓“东曹毛掾”是时任司空东曹掾的毛玠,由是可知典军校尉应是曹操霸府中之军职。但观之曹魏典军校尉的职事,却不尽一致,夏侯渊任职时正值袁绍新破,从本传所载行事看,其经常率军出征。而丁斐任职时则稍晚,可能在建安末年曹操征孙权前后,但此时其职任似已不再实际统军,而是“总摄内外”。从《魏略》记载丁斐“私易官牛”和曹操“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的评价来看,丁斐的实际职任很可能与管理后勤军需有关。这说明,曹魏的“典军校尉”可能只是军号,具体职事则随需而定。丁斐之后,“典军校尉”再不见于曹魏史籍。时至西晋,诸将军中有执掌宿卫的“典军大将军”,开府者可位比三公(7)可参张政烺:《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6页。。“典军”仍是军号,这与汉魏以来是一脉相承的。
蜀汉亦有“典军”,《三国志·蜀书·董和传》裴松之注云:
亮卒,(胡济)为中典军,统诸军,封成阳亭侯,迁中监军、前将军,督汉中。[9]980
同书《董允传》曰:
允尝与尚书令费祎、中典军胡济等共期游宴。[9]986
《王平传》载:
亮卒于武功……迁后典军、安汉将军,副车骑将军吴壹住汉中。[9]1050
此外,在《李严传》裴注引诸葛亮弹劾李严书中有联署者列衔名单,其中有“行中典军讨虏将军臣上官雝”。细观这份名单,可以发现其中对联署者官衔的记录颇有特点,试另举二例如下:
领长史绥军将军臣杨仪
行中护军偏将军臣费祎[9]1000
其中“绥军将军”“偏将军”等是将军号应无疑问,而其之前的称号,从“长史”为汉代以来将军府传统属僚这一线索来看,“中护军”等也应是诸葛亮军府中之军职,而军职前之“行”字,表示这些军职或是诸葛亮临时板授,并未经过朝廷正式任命(8)《宋书·百官志》载:“蜀丞相诸葛亮府有行参军,晋太傅司马越府又有行参军、兼行参军,后渐加长兼字,除拜则为参军事,府板则为行参军。”。“军职+军号”的署衔模式,在《蜀书》中俯仰可拾,《王平传》中“迁后典军、安汉将军”即是其例。这表明,蜀汉“典军”为军职,与魏晋之“典军”军号存在本质区别。但仅从上举诸条史料,也很难看出蜀汉“典军”的具体职事。总之,蜀汉之“典军”为军职而非军号,有中典军、后典军、行中典军,朝廷及重要军府均有设置,职事不定,但从其任者多加军号这一点看,典军的职事应与统军有关。
较之魏、蜀,《三国志·吴书》中孙吴“典军”的史料相对丰富,共检得七条,现不避烦琐,转引如下。《张昭附休传》:
及登卒后,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军事,为鲁王霸友党所谮,与顾(谭)承俱以芍陂论功事,休、承与典军陈恂通情,诈增其伐,并徙交州。[9]1225
同事又见《顾谭传》裴注引《吴录》:
全琮父子屡言芍陂之役为典军陈恂诈增张休、顾承之功,而休、承与恂通情。[9]1231
《朱据传》:
嘉禾中,始铸大钱,一当五百。后据部曲应受三万缗,工王遂诈而受之,典校吕壹疑据实取,考问主者,死于杖下,据哀其无辜,厚棺敛之。壹又表据吏为据隐,故厚其殡。权数责问据,据无以自明,藉草待罪。数月,典军吏刘助觉,言王遂所取,权大感寤,曰:“朱据见枉,况吏民乎?”乃穷治壹罪,赏助百万。[9]1340
《滕胤传》:


《濮阳兴传》:
左典军万彧素与乌程侯孙晧善,乃劝兴、布,于是兴、布废休適子而迎立晧。[9]1452
《贺邵传》:
出为吴郡太守,孙晧时,入为左典军,迁中书令,领太子太傅。[9]1456
孙吴“典军”在史籍中有称“左典军”者,亦有单称“典军”者,孙权至孙皓时皆有设置,可见非一时之制。从《滕胤传》《贺邵传》看,它不同于曹魏作为军号的典军,而更接近于蜀汉的典军,是一种军职。胡三省对典军有多种表述,他在“典军杨崇”条下注曰“杨崇盖(滕)胤帐下典军”,而在“典军施正”条下却注“吴制,中营置左右典军”,似乎认为孙吴中营和某些军府均置有典军[10]2434、2447。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据《张休传》“平三典军事”及“左典军”诸例,推测孙吴有左、中、右三典军[11]982下。
从上举史料看,无论是典军还是左典军、三典军,均与孙吴中军的关系极为密切(9)需要说明的是,孙吴“中军”的概念有时特指宫廷禁卫军,但有时又指除宿卫禁军外的京师诸军,此处“中军”取何兹全《魏晋之中军》一文中的概念,泛指卫戍京畿的部队,其中包括负责宫廷警卫的禁军。可参其著《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268页。。《张休传》《顾谭传》所载“典军论功案”是一组内容相对充实的史料,我们拟以此为例对这一问题做些说明。所谓“典军论功案”,实际上源于赤乌三年孙权命全琮发动的“芍陂之役”,《顾谭传》对该案始末有详载:
谭弟承与张休俱北征寿春,全琮时为大都督,与魏将王凌战于芍陂,军不利,魏兵乘胜陷没五营将秦晃军,休、承奋击之。遂驻魏师。时琮群子绪、端亦并为将,因敌既住,乃进击之,凌军用退。时论功行赏,以为驻敌之功大,退敌之功小,休、承并为杂号将军,绪、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构会谭。[9]1230
因为论功不平,全氏父子屡屡向孙权申告,指责张休、顾承暗通典军陈恂以“诈增其伐”。“伐,功劳也”,此处指代军功。秦汉时期申报、审核军功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包括申报、校验、登记等多个流程(10)相关成果可参朱绍侯:《西汉的功劳阀阅制度》,《史学月刊》1984年第3期;大庭修:《秦汉法制史研究》第四篇第六章“汉代的因功次晋升”,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457页;戴卫红:《伐阅之源流与演变:以出土资料为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31-241页等。。所谓“诈增其伐”落实在文书行政层面,是负责登记、审核军功的官吏通过在“伐阅簿”之类的籍簿中舞文弄墨的方式实现的。典军陈恂应当就是这类机构中的主事者。
从此案始末可见,典军负责登记、审核诸将功绩,全琮虽是卫将军、大都督,但对于典军的工作亦不能干涉,以至于全氏子弟屈居次功后,只能向孙权申告,这表明典军陈恂非是全琮军府之吏,很可能直接听命于孙权。从这次芍陂之役孙吴方面的军力构成来看,军将大都来自中军。《张休传》载传主“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军事,迁扬武将军”[9]1225,羽林自汉代即是禁军军号,羽林都督主宿卫应无疑问,张休兼平三典军事,暗示了典军与禁军间存在的关联。《顾承传》载“拜(承)昭义中郎将,入为侍中。芍陂之役,拜奋威将军”[9]1231,顾承以中郎将的身份入为侍中,职位或与张休相仿,亦主宿卫。全绪、全端二人当时的身份并不明确,《全琮传》只载“琮长子绪,幼知名,奉朝请,出授兵,稍迁扬武将军”[9]1383。不过,从张、顾子弟典掌禁军的情况来看,全氏子弟很可能亦是如此。此外,还有“五营将秦晃”,“五营”又见于《孙和传》,其载“权欲废和立亮,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9]1369,其中“无难”是孙吴宿卫营号[12]174-176,与之并列的“五营”,极可能亦是宿卫之营。综上,典军陈恂负责登记中军诸将战功,羽林都督张休又得以“平三典军事”,皆可说明典军与中军事务存在着密切联系。
至于《滕胤传》中的典军杨崇,胡三省言其是滕胤“帐下典军”,也可再商。本传言滕胤时任卫将军,孙欲迁任其为大司马,外驻武昌,滕胤不从,于是“勒兵自卫,召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以为乱”。滕胤在“勒兵自卫”之后,方才将孙反乱的消息告知二人,若二人是滕胤帐下将领,应当在其“勒兵自卫”时就已获知消息,不烦专门召见。况且当时“将军孙咨”也并非滕胤部将,《孙皎传》载“咨羽林督,仪无难督。咨为滕胤所杀”[9]1208。可见滕胤举兵时,孙咨是负责宿卫的羽林督。从最终“兵大会,遂杀胤及将士数十人”的结果看,滕胤当时掌握的兵力并不多,他联络孙咨,应当是谋求争取中军的支持以扩充实力,孙咨不从,于是被滕胤所杀。如此,则典军杨崇亦有可能与中军事务有关。
经过以上稍显迂曲的论证,我们已对孙吴典军的性质有初步了解:它并非军号,而是负责中军相关事务的军职。但这样的认识仍是雾里看花,史籍中关于典军具体职事的记载,除了《张休传》《顾谭传》中芍陂之役陈恂登记军功外,再无其他直接线索可循,只能另觅蹊径。史料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孙吴凡任典军者皆不加军号,这与中军诸营督将截然不同,与蜀汉的情况也不同。此外,孙吴历代名将无任此职者,唯一在《吴书》有传的贺邵,任典军前后分别是吴郡太守和中书令,与之相似,劝谏濮阳兴的左典军万彧,《孙皓传》称其“昔为乌程令,与皓相善”[9]1162,二人均在行政系统流转,亦无领兵事迹。这暗示典军的职事虽与军事有关,但很可能本身并不实际领兵。关于此点,《张休传》中“平三典军事”或可为一佐证。“平三典军事”于史籍中仅此一见,但类似的表述却有不少,如汉魏以来的“平尚书事”,除此之外,《吴书》中还有“平诸官事”“平九官事”“平西宫事”“平荆州事”,这些头衔应当都是从“平尚书事”衍生而来。“平尚书事”又称“录尚书事”“省尚书事”,原本是“皇帝派驻尚书机关的高级专员”[13]115,可代替皇帝平判尚书的文书。可知,两汉以来“平某事”的职衔大都与文书行政相关,其所“平事”的机构也往往与文书政务相关。孙吴有“平荆州事”之衔,又有潘濬“掌荆州事”,吕岱“代濬领荆州文书”,荆州是孙吴在长江中游的最高政务机关,“平/掌荆州事”就是指平判荆州文书事务。明乎此,我们就至少可以确定“平三典军事”的“典军”,其执掌也应与文书行政相关,它虽是在军中任职,平时也负责登记、评定军功,但其自身却并不领兵(11)依《吴书》行文惯例,一般会使用“督”来描述军事上的统属关系,如诸葛恪、孙峻“督中外诸军事”,又如张温率军赴豫章部伍出兵,孙权令其“董督三郡”,再如吕岱“督孙茂等十将从取长沙三郡”等,不胜枚举。张休当时是领有营兵的羽林都督,若典军亦是领有营兵的军职,行文中亦应用“督”而非“平”来描述前者对后者的统属关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典军的职官性质。。
除了登记军功,典军的职事还包括哪些内容?《朱据传》中“王遂诈领军费案”亦可提供一些线索。此案的相关记载一如上引,兹不赘。该案中朱据最终得以冤雪。此案的关键转折在于典军吏刘助,那么,刘助又是如何发觉实情的呢?我们试以文书行政的视角对此案再做剖析。朱然部曲应领三万缗新钱,但实际上却未曾领取,其营中“主者”自然不会将这笔款项入账,但由于王遂冒领,负责发放新钱的机构账簿上却实际存在一笔支出账,如此,负责典校文书的吕壹就发现了其中抵牾之处,此案由此爆发。由于这笔款项根本没有入账,营中“主者”和朱据陷入“无以自明”的尴尬境地。那么,谁最有可能发觉其中真相呢?我们推测是保留支出凭证的支出方。根据吴简中三州、州中仓出米简的基本格式可知,当时财务支出文书需要登载实际支出时间、领取人等详细信息,这些文书由仓吏定期整理呈交仓曹审核,成为日后审计、追查的关键依据。仓的管理模式如此,库应当去之不远(12)关于吴简中的库支出账,可参谷口建速:《走馬楼呉簡にみえる庫関係簿と財政系統》,收录于《社会·经济·观念史视野中的古代中国——国际青年学术会议暨第二届清华青年史学论坛论文集》下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2010年1月16日,第765-781页。。因此,“典军吏”刘助能够发觉真相,他本人很可能就负责相关文书事务。而朱据自黄龙元年“尚公主”后,作为驸马就再未驻屯外地,其部曲自然也就具备了“中军”的性质,这正是在典军的管辖范围内。综上,我们认为典军设置于中军,除了战时登记军功的职能外,平常可能还肩负有经办军需文书的任务,总之均与文书行政密切相关。
三、吴简中的“典军”
经过以上梳理,回过头来再看吴简中的“典军”,可以发现与传世文献存在契合之处。首先是职能方面,吴简中典军下有录事、主吏曹、户曹、田曹、仓曹、兵曹、金曹,与郡县行政组织几乎如出一辙,表明该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处理文书相关事务,这与《吴书》中典军的形象是相符的。但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既然典军是与中军有关的军职,那么,在军事组织中何以会出现诸如户曹、田曹、金曹等与民政相关的曹署(13)两汉军府组织架构中亦有诸曹吏,但较之郡县掾属似不发达,目前所见只有“兵曹掾史”和“稟假掾史”,可参《续汉书·百官志》。?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孙吴的兵户制度有关。关于魏晋时期的士家/兵户制度,学界不乏高论,有学者注意到孙吴兵户制与曹魏士家制存在差异:曹魏实行“错役法”,兵士家属作为人质要与服役的兵士分居两地,以防止士兵逃亡;但孙吴却只控制军将家属,所谓“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普通兵士家属则可随营居住[14]99-103。除了戍守地方的兵户,卫戍建业的中军亦是如此,《吴书·妃嫔传》载:
孙和何姬,丹杨句容人也。父遂,本骑士。孙权尝游幸诸营,而姬观于道中,权望见异之,命宦者召入,以赐子和。[9]1201
孙权所“游幸”的诸营,应当即是建业附近的中军军营,途中望见骑士何遂之女,这说明中营兵户也是合家居于营中的。这些随营兵户拥有专门的户籍,直接隶属于本营军将,不属郡县管理[15]。在承平时期,这些兵户的生活与普通郡县民差异并不大,他们同样需要耕种田亩、缴纳租税、承担徭役(14)唐长孺早已指出,孙吴的兵“决非是单管打仗的战士,他们同样要耕田”,详参《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收入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16页。,如孙权黄武五年,陆逊就曾建议“诸将增广农亩”[9]1132,此后孙休诏书中也称“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9]1158。直至吴末,贺邵还曾上书云“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宜特优育,以待有事,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慼”[9]1458。如此,兵户的日常生活除了与军事相关的事务外,自然也会衍生出一些如户籍管理、赋役征发、案狱诉讼等民政相关事务。因此,遍布孙吴境内的大小军营,名义上虽然不是郡县,但事实上却具备了郡县的行政管理内容。为管理兵户,孙权中军及各地军将幕府中,建立一套类似于郡县的行政系统势在必行。吴简中所见典军诸曹,正是这类机构。而典军的角色或类似于汉代将军府中“署诸曹事”的长史,总揽营中大小事务。孙吴在建业周边部署的中军数量众多,诸营林立,或需设置“三典军”以分部掌管相关文书事务(15)孙吴中军兵力史无明载,但有数据可供参考,《晋书·王浑传》载“吴丞相张悌、大将军孙震等率众数万指城阳,浑遣司马孙畴、扬州刺史周浚击破之”,同书《王濬传》称此事为“王浑久破皓中军,斩张悌等”,可见吴末孙皓之中军至少有数万人之多。。
《吴书》中所载基本均是中军之典军,但如上所述,各地军营亦有管理兵户的基本需求,想必地方诸军将幕府中亦应有类似机构,惜史书未载。吴简中之典军,应当为中军之典军。前揭成果多将典军与潘濬征讨武陵蛮的行动联系起来,可从。从《吴书》所载参与此次伐蛮行动的军将构成看,除了屯驻荆州的潘濬和吕岱外,还有不少来自建业者,如朱然之子朱绩:
绩字公绪,以父任为郎,后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绩领其兵,随太常潘濬讨五溪,以胆力称。迁偏将军营下督。[9]1308
吕范之子吕据:
据字世议,以父任为郎,后范寝疾,拜副军校尉,佐领军事。范卒,迁安军中郎将……随太常潘濬讨五谿,复有功。[9]1312
二人均是勋贵子弟,朱绩最初以父任为郎,此后继领叔父营兵,从此后“迁偏将军营下督”,及鲁王孙霸主动结交的记载看,他应当长期在京畿领兵。吕据年少亦以父任为郎,吕范病重时曾“佐领军事”。按,吕范晚年任丹阳太守、扬州牧,一直屯驻于建业。其后吕据升任安军中郎将,应当也是中军将领。此外,还有钟离牧,其本传所载仕宦履历只从“赤乌五年,从郎中补太子辅义都尉”起,不言从征武陵之事,但裴注引《会稽典录》载钟离牧自言:“大皇帝时,陆丞相讨鄱阳,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讨武陵,吾又有三千人。”[9]1395可知钟离牧应是以郎中的身份从征武陵,其所领之兵亦当来自中军。此外,从兵力上看亦是如此,史载潘濬初为将时(黄武元年)领兵不过五千人,吕岱在征讨交州时(黄武五年后)“督兵三千人”,至黄龙三年征讨武陵蛮时,考虑到兵士损耗及补充的情况,二人本营兵力之和至多不过万余,但据《吴主传》潘濬所督伐蛮诸军却有五万人,这多出的三万余人,恐怕多半皆是孙权调拨的中军(16)步骘曾向驻在武昌的太子孙登“条于时事业在荆州界者”,即孙吴在荆州部署的军将名单,有“诸葛瑾、陆逊、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卫旌、李肃、周条、石幹十一人”,检诸史料,除潘濬外,其余诸将均未参与征讨武陵蛮的行动。可知此次战役,荆州方面主要军将参与不多。。如此,在荆州出现管理中军事务的典军诸曹,似乎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
此外,典军诸曹的奉米支出需由右节度府经办,这有别于一般流程。在州中仓出米简中,仓米支取大都经由督军粮都尉和邸阁,本地军将支取奉廪即是如此,如:
20.出仓吏黄讳、潘虑所领嘉禾元年税吴平斛米卌九斛九斗二升为稟斛米五十二斛,邸+阁右郎中李嵩被督军粮都尉嘉禾二年五月十二日辛未书,给豫州+督军都尉朱节所主吏谢林、钟露二人稟,起嘉禾二年正月有闰月讫十二+月,人月二斛,其年五月十六日付吏吴杨。(捌·3050+3049+3048+3047)(17)此组简最早为邬文玲缀合,详参其文《〈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捌)〉所见州中仓出米簿的集成与复原尝试》,《出土文献研究》第16辑,第341-342页。
其中“豫州督军都尉”,应当是指时任豫州牧诸葛瑾军中的督军都尉(18)《诸葛瑾传》:“权称尊号,拜大将军、左都护,领豫州牧。及吕壹诛,权又有诏切磋瑾等,语在权传。”从行文来看,至少在孙权称帝至赤乌元年吕壹伏诛期间,诸葛瑾的职衔未曾发生过变动,故吴简所示嘉禾二年之时,其应带有豫州牧之衔。彼时吴与蜀拟分天下诸州,豫州在吴分,但并未实际控制,诸葛瑾驻屯公安,豫州牧只是虚衔而已,因此,“豫州督军都尉”还应视作诸葛瑾营中之军职,并非豫州州府之吏。,当时诸葛瑾屯驻荆州公安,军营距离长沙未远,其属吏从州中仓领受廪米,不见节度府干预。也有不经由督军粮都尉和邸阁,从州中仓直接支取奉米的情况,一般也均为太守、侯相、左右尉等长沙本地长吏(可参简柒·4194、4205、4212、4389)。而关于右节度府的性质,学界已多有探讨,指出其是孙吴统筹军粮调度的机构(19)可参罗新:《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侯旭东:《吴简所见“折咸米”补释——兼论仓米的转运与吏的职务行为过失补偿》,《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版,第176-191页;戴卫红:《长沙走马楼吴简中军粮调配问题初探》,《简帛研究》二〇〇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4-224页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担任节度官的皆是孙权的心腹要臣,如徐详、诸葛恪、顾谭等,从各自本传的记述看,节度应当就设置在建业附近,属于中央官。那么,远在荆州的典军诸吏需要经由中央节度官的特别许可,方才能从驻地粮仓中支取奉米。如此特殊的流程或可说明,典军与本地军将有所不同,原本也应是受中央直接支配的官吏。
至此,似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做出解释:孙吴兵户虽是随营居住,但实际作战时为轻装简行,一般只是征发兵士,家属则留于屯营(20)《蒋钦传》载:“初,钦屯宣城,尝讨豫章贼。芜湖令徐盛收钦屯吏,表斩之,权以钦在远不许。”可见蒋钦出征并非空营而出,屯营中应当留有军士家属及相关官吏。。此次伐蛮之役孙吴中军劳师远征,军中理论上只有兵士,为何又会出现典军田曹、户曹这类颇具民政色彩的曹署呢?是否有兵户家属也随军一同来到荆州呢?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潘濬此次伐蛮统军五万,从黄龙三年二月至嘉禾三年十一月,历时将近四年,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在孙吴军事史中都属罕见,表明这不同于一般的遭遇战,而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历时数年的屯戍,对于远征荆州的数万中军士卒而言意味着与家人长久分别,这在当时是有违人情的,不仅会导致兵士“怨旷积年”,士气低落,也不利于兵户的人口增殖(21)“怨旷积年”语出《魏书·蒋济传》。陈玉屏对曹魏“错役制”下兵士与家属长期两地分居的弊端有过探讨,指出不仅会造成士兵怨旷,还会影响士家人口的增殖,详参其著《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70-73页。孙吴统治者对此也十分重视,如骆统劝谏曰:“彊邻大敌非造次所灭,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史载孙权“深加意焉”。再如诸葛恪执政时曾言:“自古以来,务在产育,今者贼民岁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于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在曹魏“错役制”之下,一般采取定期轮戍的方式解决这种矛盾,而孙吴兵户随营集中居住,因此,在征讨武陵蛮时允许士卒家属随军屯戍应当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吴简三州仓出米简中,有向潘濬、吕岱所领营士及其家属支付廩粮的记录,表明参与征讨武陵蛮的屯戍军士中,确有与家属同居者(22)详参拙文《〈三国志·吴书〉“沤口”地望再探——兼论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待刊稿。。如:
21.嘉禾三年五月十一日甲午书,给大常刘阳侯所领留屯及从在武+昌吏士及妻二百一十八人,起其年四月讫五月,其八十六人留屯吏士,其廿一(玖·4214+4909)
只是这种临时性的迁移很可能并非举家前往。根据吴简中“师佐家属籍”的注记看,这些在官府/军队长期集中服役的师佐,有一些是将妻子、儿女乃至父母一同带往服役地点,也有相当部分的师佐家属并未随行,这可能是根据服役者个人家庭状况自行决定的,但家属无论随行与否,他们的行踪都在官府的掌控之下(23)关于吴简中“师佐籍”论者众多,此不备举。蒋非非曾对“师佐籍”中家属注记有专题研究,可参其文《走马楼吴简师佐及家属籍注记“见”考》,《吴简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9-122页;《走马楼吴简师佐及家属籍注记“屯将行”及“单身”与孙吴军法》,《简帛研究》二〇一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183页。。孙吴师佐及其家属虽非军户,但为军事化管理,故正式兵户的情况或许去之不远。但即便是只有部分家属随军,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类庶务也需要有官吏负责处理,典军户曹、田曹等民政类曹署正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吴简中的典军除出现在州中仓出米简外,还见于“举私学”相关文书。在《竹简〔伍〕》中,有一组序号相连、内容相关的“举私学”文书简:

26.列吏催促连岁不□□□□□令不□□又当勑诸□□(伍·3648)
这组竹简残泐较重,无法缀连,但内容相关。据行文语气看应是下行文书,内容大致是对举私学的一些具体要求。其中简25、27中,特别提到“其军吏应举者……”和“其诸将所举别列”,显示出军事系统举私学需要单独别列,与郡县系统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结合简22中“若知书,付典军、督军”的规定,似可认为军将及军吏所举之私学,如若符合“知书”的要求(24)“知书”可与吴简“举私学状”中“能书画”一类的记录对观(如《监长沙邸阁右郎中张俊移私学弟子区小文书木牍》,参张永强:《“能书画”的私学弟子》,《美术报》2019年6月8日第15版)。邢义田曾对居延汉简个人功劳档案中的“能书”记录做过探讨,他认为“能书”在字面意义上仅指能书写,“实际上可能还具有例如能史书或某种程度撰写公文的能力”,应可从,见《汉代边塞隧长的文书能力与教育》,收入其著《今尘集》,中西书局2019年版,第52-53页。,最终还是要交由“典军”和“督军”安排,而非同郡县吏所举私学那般发遣至“宫”。“典军”的身分如上所论,至于“督军”,一般认为是朝廷派驻诸郡监领郡兵的使者,但上引出米简有“豫州督军都尉所主吏”,可知各地军将营中亦置有此官,从“所主吏”的表述看,“督军”亦领有吏员。之所以如此安排,或与当时能够胜任文书行政的军吏短缺有关,简23“上大将军事□经□职使不供”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为了保证军队文吏的数量,必须保持军吏所举私学均是在系统内部流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再次印证了前文对于典军主管文书事务的判断。
四、余论
孙吴国祚短促,国家制度不及完备,但同时又杂有不少本朝创设的新制,加之《吴书》在此方面记载阔略,致使孙吴职官制度多有晦暗难明之处。“典军”就是其中一例。尽管我们根据残篇断简,努力拼凑出孙吴“典军”的形象,但距离历史实际恐怕还是有相当的距离。一些制度运行层面的细节,依据现有材料都暂时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只能俟诸来日新材料的发现。
但经过辨析材料,我们至少廓清一些基本事实:孙吴之典军并非军号,而是设置于中军的军职;它的功能兼及军政与民政:在军事上负责登记军功、调配军需,在民政层面负责兵户管理;其僚属组织形式一如郡县曹吏,而这又是孙吴兵户家庭成员随营居住的特点造成的。
军府兼理民政,令人不由联想到两晋南朝的州军府。关于此点,中外学者所论颇多(25)代表性研究有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三章“州府僚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210页;滨口重国:《所谓隋的废止乡官》,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5-333页;陶新华:《魏晋南朝中央对地方军政官的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他们指出两晋南朝时期州刺史例带将军号,致使一州之内出现将军府和州官两套行政系统。滨口重国指出,府官“有种种事务如筹措并出纳军费、管理并输送武器粮秣、征发动员兵士、任用府吏,以及屯田、军法等。为处理这些事务,必然要设置众多僚属。这些僚属与处理一般民政的州的机构密切相关,甚至有些官名如田曹、主簿等都与州官相同”[16]325。从结果上看,这与上文所论典军诸曹极为相似,二者均成为总揽军民事务的机构,不同的是,前者是一个军政侵夺民政的过程,形式上仍属地方行政机构的范畴;而后者则是军政体系对民政体系的模仿,但形式上则是与郡县分立的军营。这从北方十六国时期也能看到些许端倪。有学者注意到,十六国时期不少政权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军镇化”之势,相较东晋南朝而言,它的军事化程度更为彻底:干脆彻底弃用了郡县体制,以军镇代行地方行政管理职权(26)参牟发松:《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高敏:《十六国时期的军镇制度》,《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后收入其著《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273页。。一些军镇设有护军统辖军民事务,从前秦《广武将军□产碑》碑阴题名看,护军属吏有户曹、录事、主簿、功曹等,一如传统郡县僚属(27)高敏:《十六国时期前秦、后秦的“护军”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广武将军□产碑》拓片及录文可参(日)北朝石刻資料の研究班编著《北朝石刻資料選注(一)》,《東方學報》2011年第86册,第346-354页。,这与孙吴典军颇为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孙吴在军府机构趋于“郡县化”的同时,郡县行政“军事化”的趋向也很明显,首先,从吴简对长沙太守职衔的记录中,有“领长沙大守行立节校尉”的称谓(叁·3936、捌·4195),这说明当时长沙太守领有军号[17]340-346;其次,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值得关注:吴简中所见两件贪污案,即“许迪割米案”和“朱表割米案”中,两名当事人均是郡县系统吏员,但处罚时却都行用军法(28)有关两案的研究,可参徐畅:《新刊长沙走马楼吴简与许迪割米案司法程序的复原》,《文物》2015年第12期;陈荣杰:《走马楼吴简“朱表割米自首案”整理与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1期等。。行政长官而带军号、非军事场合行用军法,都曾被视作是南朝地方政权军事化的重要表征[18]。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又能从孙吴政权中依稀看到一些东晋南朝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