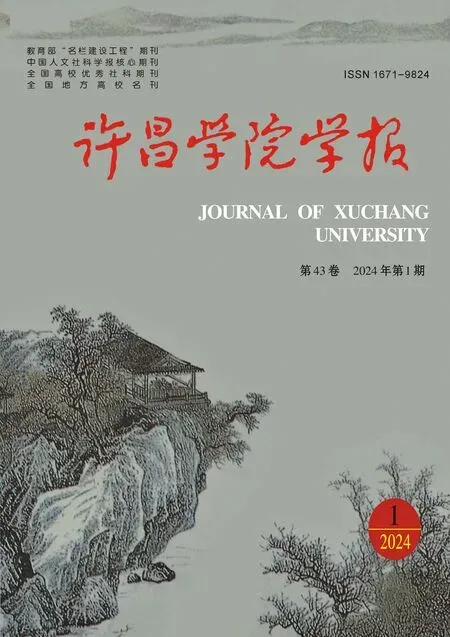语言、意义与人的生存:卢梭儿童语言教育与现象学回溯
杜战涛, 李佳琪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当代教育现象学家范梅南(Max van Manen)认为,教育现象学首先关心的并不是既成的知识,而是儿童的生活世界及其具体的学习体验,比如,关于阅读,“现象学所关心的是,儿童的阅读体验本身是什么”[1]50-51?在语言及其意义方面,范梅南说:“意义不是从日常生活的层层残骸与腐败中挖掘而出的。意义早已暗含于视觉、听觉、接触、被触摸,以及与世界的接触(being-in-touch)的前反思性的反思中。”[2]4-5“现象学……让我们和世界进行直接的接触。”[2]67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回溯,即回溯到与世界的接触上。当我们带着现象学视角阅读卢梭的《爱弥儿》时会发现,卢梭的语言教育也在使用现象学式的从语词回溯到其意义源泉的方法。接下来本文将首先对现象学的回溯方法略做讨论,然后具体展示卢梭的教育方法,最后对其价值加以简要评价。
一、从语言到其意义源泉的现象学方法回溯
回溯是现象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或方法之一,也就是说,从某一个事物回溯到其源泉或根源。接下来,我们对经典现象学家的回溯加以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胡塞尔。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谈到:“我们绝不会满足于‘单纯的语词’,即不会满足于‘对语词单纯的符号性理解’。”“那些产生于遥远、含糊和非本真直观的含义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回到‘事物本身’上去。我们要在充分发挥了的直观中获得明见性。”[3]168也就是说,单纯的语词本身,其含义是遥远而模糊的;本真的、真切的含义源于直观,即对事物的直接感知和把握,因而,为求得确定性的含义,我们要从语词本身回到其来源即直观。
其次,类似胡塞尔,海德格尔也强调要从没有根基的语词、概念,回到其来源。具体到海德格尔现象学来说,现象学的核心问题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存在问题,或者说,其现象学的目的在于获得存在之意义,并最终把存在之意义以明确的概念方式表述出来。然而,海德格尔谈到,对存在的几种现有理解,如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存在概念是不可定义的、存在是自明的概念等都是成见,是“无根基的”(bodenlos)或“浮漂的”(freischwebendem)[4]76,并使存在的真正意义被掩盖,这就需要重提并回答存在问题。
为了得到回答这一问题的正当起点,海德格尔回到了人或此在(Dasein)(78)“Dasein”一词主要指人的存在,它涉及的是人与存在的关联,因而并不等同于人,但根据本文的主题,本文对于此在和人不做严格区分。对存在的理解或领会(Verstehen)。这是因为,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而此在源始地包含有对一切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的领会,因而,唯有从此在的存在领会(Seinsverständnis)开始,才有可能进行有充分根据的讨论。
但海德格尔所回到的存在领会与胡塞尔的理论性直观不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理论性的直观并不是人与事物照面的最基本方式,最基本的方式是此在以“在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与其周围事物以工具的方式打交道,在这种方式的打交道中,此在会理解为作为工具的事物的存在意义。也就是说,此在(或简单地说,人)与事物的原初关系,首先和通常并不是中性的理论式观察,而是说,人与事物的关系首先和通常是工具式的,即把事物当作工具或用具,以有用性的方式来看待和对待事物。或者说,人总是先行以工具或有用性的视阈(Horizon)投射(Entwurf)到事物上去。
那么,此在之存在领会与事物之意义或事物之存在具体是什么关系呢?用海德格尔本人的话说,“对于小孩子对某个东西是什么(was ein bestimmtes Ding sei)的发问,人们可以通过指出这个东西用于什么(wozu es gebraucht wird)来予以回答,在此人们是通过用其所做的事情(was man damit macht)来规定所面对的东西的”[4]260-261。换句话说,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此在,以“为了做”(Um-zu)的方式,依照领会的“作为结构”(Als-Struktur),把物(Ding)领会为上手的工具或用具,比如,用来写字的笔或用来坐的椅子等等。在此,世内存在者便“具有意义”,而且,更严格地说,“我们领会到的不是意义,而是存在者和存在”[5]192。比如说,一个小孩子指着一个带长柄的网兜问我:“这东西是什么?”我回答说:“这是抄网。”小孩子听到这个回答以后,可能依然不明白这是什么。于是我继续解释说:“这是用来捞鱼的东西。”这个时候,小孩子便会明白它是什么了。
这便是人与事物最原初的关系,也是人理解事物的最原初方式。椅子是用来坐的,刀是用来切割的,雨伞是用来遮雨的,等等。我们本然地在某一处境中以有用性的视阈投射到事物上,以工具或用具的方式来使用事物,体验事物,并理解事物及其存在。籍此,事物及其意义便自身给予或呈现出来。
在对现象学的回溯略做讨论之后,我们接下来具体看卢梭的教育方法。
二、卢梭的语言教育方法
卢梭反对洛克式的停留在语言或符号本身的教育方法。卢梭倡导的方法是,从语言或符号本身回到语言或符号及其意义所产生的源泉上。
(一)卢梭对洛克式儿童语言教育方法的批评
在儿童语言教育上,卢梭反对洛克式的用字骰教孩子,甚至把整个屋子都变成印刷厂的方式[6]117。卢梭认为,通过这些方法,儿童只学到了语词(即符号),而没有获得符号所表达的观念,而“代表事物的符号如果不具有它们所代表的事物的观念,那便是毫无意义的”[6]109。例如,对于亚历山大的故事(79)这个故事说的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收到信报说他亲近的菲力浦医生已被敌方买通,准备毒害他。亚历山大一边把信给菲力浦医生看,一边吞下了菲力浦医生给的药,以此向菲力浦医生表明他对他的信任。,儿童在口头上知道了毒药、中毒、死亡、勇敢等词汇,但其实儿童对这些词汇的理解是:毒药就是旃那(一种治疗腹泻的植物),中毒和死亡只是一种不愉快的感受,亚历山大的勇敢在于他果断地、面无难色地吞下难吃的药。
卢梭认为这些教育方法是有害的,原因在于,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儿童通过这些方法没有真正理解这些语词的含义,而只是在口头上学会了这些语词,只是在头脑里记住了一些“不代表任何事物的符号”[6]111。其次,这些教育方法容易使儿童形成浮华、虚浮甚至虚伪的倾向。虽然儿童没有理解词语的含义,但他毕竟口头记住了一些名词,他会以此向他人炫耀,变得夸夸其谈。
在卢梭看来,这种教育方法的问题根本在于,它忽视了语言符号的来源。语言符号的意义来源于其所代表的事物,或者说,语词是衍生的(derived),事物是源生的(original)。进一步说,事物意义的源生之地又在于人的生存。这种对语言意义的追溯是卢梭儿童语言教育方法背后的核心理念。他认为,以洛克为代表的流行教育方法只关注语词符号教育,这无益于儿童真正理解语言的意义,因为“若没有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的观念,代表性的符号就什么也不是”[6]109,这是“没有根基”[6]126的教育方法。相应的,卢梭主张,儿童语言教育应进行回溯,从衍生的东西回到其根基或源泉,从而达到对语言的本真理解。
(二)从抽象符号回到事物本身
卢梭语言教育的第一步是回到事物本身。卢梭以反问的方式来表达这种顺序:“在学习事物的过程中,他们不就学会了符号吗?”[6]111这是自然的(natural)教育方法,即依照词语产生的自然顺序来开展语言教育,让学生首先接触事物,在接触事物的过程中学习语言。
在教育实践中,这一步骤表现为,能展示实际事物的,就不要展示文字、语词或符号,卢梭认为,“一般来说,在不可能把事物展示给他时,才能以符号来替代”[6]170,他主张,在教儿童识字时,不应该用语词卡片、地图或各种装置,而应尽可能地展示事物本身。卢梭说:“为什么这么多装置啊!为什么是所有这些代表实物的东西呢?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展示给他以物体本身,以便使他知道你跟他说的是什么东西呢?”[6]168
这种回到事物本身的自然方式区别于当时流行的人为的(artificial)教育方法,即只关注语词符号本身而剥离掉词语所代表的事物。我们或可以用图式来展示两种教育方法中的人、事物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在卢梭的自然方法中,三者的关系是:人—事物—符号,即学习者先接触事物本身,通过事物本身去理解代表事物的语言符号。在洛克式的人为教育方法中,三者的关系是:人—符号…事物,即学习者只接触语言符号,而不曾或较少接触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本身。
(三)回到对事物的亲身感知
回到对事物的亲身感知,强调的是人与事物的直接接触或体验性的关联。回到事物本身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亲身感知、体验事物是最能深化对事物的理解的一种。例如,讲解“太阳”一词时,有些教师会在教室中指着窗外天上的太阳给同学们看,有些教师则会引导学生在户外亲身感受太阳的光亮、热度等(当然要避免太阳直射眼睛)。后一种教育方式可以让儿童亲身感知太阳,形成对太阳的亲身认知。这种由亲身体验获得事物观念的方式显然是对太阳更本真的理解,因而也有助于形成对“太阳”一词更本真的理解。这也是卢梭主张“以地球为地球,以太阳为太阳”[6]170的用意所在。
在卢梭看来,这种通过亲身体验事物即感官接触、感知事物获得事物观念的方式符合人的理解机制。人的理解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感性理解,然后是理智理解。即,“由于进入人的理解的一切东西,都是经由感官进入的,因而,人最初的理解是感性理解(raison sensitive);感性理解是理智理解(raison intellectuelle)的基础”[6]125。具体来说,我们首先以各种感官比如手、眼睛等接触或感知事物,在这些接触或感知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感觉;接下来,“在对接续的或同时发生的几个感觉的比较中,以及对它们的判断中,产生了某种混合的或复合的感觉,我把这种感觉称为观念(idée)”[6]203。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感觉,我们的理智会对其进行比较、综合等,然后对事物形成总括的、抽象的观念,即达到了对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关系也包括人与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解。在对事物以及关系的理解之后,人们会用诸如“大、小、强、弱、快、慢、胆小和胆大等语词来表达”[7]162。
语言的起源也体现着人的这种理解机制。例如,我在荒野看到一种果实,它亮红油绿,显得很鲜亮,于是我用手触摸它,觉得很光滑,然后用鼻子嗅它,觉得它散发的气味很清新,还有些甜,也觉得较为安全,然后再用嘴轻轻品尝它,觉得它又酸又甜,味道很好,与我以前常吃的水果相比很相似。此外,我又看到,不远处的小鸟也在吃这种果实。于是我把以上这些感觉综合起来,形成它是可吃的、它对我的身体会是有益的等观念。这便是我对这个果实的感性理解和理智理解。在理解之后,倘若有记忆和交流的需要,我便将它命名为“A果”。
(四)回到现实利益和有用性
亲身体验事物比符号式教育更有助于儿童对语言意义的理解,但它并不是全部。因为如果儿童只是体验到事物的外表,那同样无法真正领会到事物及其语词符号的意义。例如,教师讲解“抄网”一词,告诉学生它是“打捞的工具”,并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抄网实物,让学生亲自看到、摸到这个带长柄的网兜。这的确会比单纯的正音、练字更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抄网”一词。但这还不够,因为课堂上的抄网是作为展览物品展示自身,而不是作为正在打捞东西的打捞工具展示自身。课堂上的抄网是教具,而不是上手的工具。抄网在课堂上没有展示出它原初的存在方式,因而也并没有展示出它自身之真正所是。儿童对“抄网”一词更深刻的理解应该来自于他在生活中对抄网作为打捞工具的使用,当他亲自用抄网在池塘捞起小鱼、小虾、水草时,他才会真正理解“抄网”一词的意义。再如,当教师讲解“蝴蝶”时,给儿童展示了蝴蝶标本,那么儿童的确亲自看到了蝴蝶实物,亲自摸到了它,感受到了它的质感。但儿童或许会认为,蝴蝶就是身体五颜六色的、一动不动、住在盒子里的物品。但事实上,死的标本不是蝴蝶的原初存在方式,蝴蝶是身体五颜六色的、常常飞来飞去的生物。因而,蝴蝶标本并没有体现出蝴蝶之真正所是,儿童通过蝴蝶标本并不能真正理解蝴蝶本身以及蝴蝶之语词的真正含义。
对儿童来说,抄网和蝴蝶都与他们的现实利益(interest)(80)需要说明的是,“interest”(法文为“intérêt”)一词,既有利益的含义,也有兴趣的含义。有关。抄网作为上手的工具,让儿童得以实现打捞水草的现实利益/目的,因而是有用的。而看着蝴蝶在花园中飞舞或追逐蝴蝶跑是好玩的,是一种游戏兴趣。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在前一种意义,即现实福祉的意义上讨论现实利益。
卢梭认为,要把“真正有用的东西”(objets d’utilité réelle)[6]177提供给儿童,因为儿童对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往往很有兴趣且理解得非常好。
这里首先需要对“有用性”做些说明。卢梭指出,“有用性”这个词具有“相对于他的年龄的意义,他清楚地看到它与他当下福祉的关系”[6]178-179。一个事物被认为是有用的,通常是指该事物对实现某个目标是有帮助的。和成人一样,儿童也有自己的目标或现实利益,他们知道生活中哪些事物于他们是有利的,哪些事物对实现这些现实利益是有用的。但和成人不同的是,儿童的现实利益就是指他们“眼前可以感觉得到的利益”[6]147。例如,大人们往往认为儿童的现实利益是儿童的长远发展、儿童在少年或成年时的幸福,但儿童的现实利益就是他们眼下、当下能够感受得到的利益。举例来说,“如果叫他答应他明天从窗口跳出去,就可以免掉他一顿鞭打或者给他一包糖果,他也会立刻答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不尊重小孩的约定的原因……小孩没有撒谎,只是他对他所许诺的事情没有什么了解”[6]13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儿童的想象力有限,他们根本“还想象不到他这个人在不同的时候的情景”,他们还没有发展出成熟的延展向遥远未来的时间观。因此,大人们认为的现实利益在儿童眼中是“同他们毫不相关的事物”[6]147“这些就是无(nuls)”,自然地,儿童也“不可能产生要做些相关于它们的事情的兴趣”。[6]173
其次,为什么要提供给儿童有用的东西呢?或者说,为什么儿童对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往往很有兴趣且理解得非常好呢?对此,我们可以举些日常例子。在上文论述中,我们对语言教育追溯到的终点是事物的原初存在方式,但对于不喜欢蝴蝶或对蝴蝶没有丝毫兴趣的儿童来说,蝴蝶即使按照其原初存在方式在花园里飞来飞去也不会引起他们更多的关注。因为儿童对那些他知道与他切身相关的事物往往有极大的兴趣且格外用心,而对于那些他觉得与他当下利益无关的事物是没有任何兴趣的或无动于衷的。卢梭说:“要使儿童习惯于把时间花在有用的事物上,但却是以他们的年龄可以感知到的以及在他们理解力范围内的有用的事物。”[6]178卢梭这是在说,虽然要使儿童去接触和认知有用的事物而非无用的事物,但这些有用的事物并不是成人所能理解的有用事物,而是儿童在其年龄阶段的理解力所能理解的有用事物。儿童无法理解成人世界的种种事物及其关系,他只能理解他自己所处的处境中的事物。如果教师认为有很多事物在儿童长大成人以后是非常有用的,于是便要儿童预先去理解成人世界中的各种有用事物,这是行不通的。对于那些不属于儿童世界而只属于成人世界的有用事物,“要提早学习是不可能的”,对于儿童所不能理解的成人状态应有的种种观念,就不能让儿童知道,这是《爱弥儿》“整本书要持续证明的教育原则”[6]178。
事实上,这种对有用性的追求并非儿童独有,有用性是人与事物的原初关系。在与世界照面时,我们已经预先把有用性视阈投射于事物之上,因而事物并不首先和完全是中性的(neutral),而是首先被把握为有益或有害的、有用或无用的。有用性是人与事物的原初关系,也是人理解事物的原初方式。
人最初关切并力图理解的,只是与他相关尤其是与他生存或生命保全相关的事物及其性质。而这一点,尤其体现为有用性。卢梭观察到,当一只猫第一次进入一个房间时,会东张西望,四处探测。类似的,在日常活动中,人的观察和研究也是“与他有关系的”,而非与他无关的,这种观察和研究是“与他自己的生存相关的实验物理学”[6]125。卢梭认为,儿童在理解与评估事物时,依照的是“事物对他的用处(utilité)、他的安全、他的生命保全以及他的福祉(bien-être)的显而易见的关系”[6]187。人类包括儿童在内,其最基本的考量是其安全、生命保全以及福祉,或者说,人最根本的、最内在的欲望是“追求他的福祉的欲望”,但又由于他“不能充分满足这种欲望”,因而,他会“不断寻找有助于满足这种欲望的新的手段”[6]167。这里既然是手段,而手段就必须体现为有用性,即,对于满足其欲望或目的是有用的,因而,有用性就是人考量其周围事物的基本视阈。
对此,我们也可举些荒野生存的例子。因为高度文明化的日常生活常常遮掩或弱化了我们对事物的基本理解方式,而荒野生存则展示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原初理解。首先看鲁滨逊的例子。鲁滨逊从海难中幸存后,回到船上搜寻可用的物品。在搜索中,他在一个抽屉中看到了钱币,鲁滨逊大笑,然后喊道:“垃圾……你们有什么用?对我而言,你们一文不值,不值得带到岸上去。你们这么一大堆,还比不上一把餐刀。”[8]73在荒岛这种极端的处境中,鲁滨逊是完全隔离于人类社会的,他会“按照自己的用途”“判断一切事物”,而且,鲁滨逊“希望认知一切有用的东西,并且他只想认知这些东西”[6]185。另外,在纪录片《荒野生存》(Marooned)中,求生专家埃德·斯塔福德(Ed Stafford)来到纳米比亚荒野,赤手空拳,没有任何食物和工具。他的重要行动之一便是环顾他周围,看他周围事物中有没有可以吃的。当他翻动水边的石块并抓到一条鳗鱼时,他便发出感叹:“多么好的一顿饭啊!”对他来说,鱼、鸟、树木,都不是用来观赏或进行理论研究的,而是用来吃的食物、用来防御猛兽伤害的庇护所。这就是人对事物的最基本的生存式或有用性的理解方式。
基于上述认知机制,教育者要把“真正有用的东西”(objets d’utilité réelle)[6]177提供给儿童。这一方面会激发儿童的主动性,使其主动探索、学习;另一方面,如果教师在有用性的前提下引导学生依照事物原初存在的方式体验事物,那么儿童也会形成对语言真正的理解。
(五)回到具体生存处境
在教学实践中,原则是教师要提供给学生有用的事物。但教师具体该以什么方式提供给儿童这些有用的事物呢?卢梭认为,教师要“创设一种处境(situation),在其中,人的一切自然需要(besoins naturels)都可以儿童心灵可以感知到的方式得以展示,并且在其中,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也会同样容易地得到开发”[6]184。为什么要创设一种处境呢?原因在于,在教育时,教师当然要激发学生对某些事物进行认知的兴趣,而认知的兴趣是与有用性有关的,而有用性则是与“他的现实福祉”[6]178相关的,而现实福祉则是在某种具体处境中的,那么,只要置身于某种处境,自然需要便自然地产生,而对相应手段的需要也会随之产生,并且基于本能,儿童也会自然地寻找甚至找到这些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对于有用性的理解也相应产生。
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卢梭关于请柬的例子[6]117。在教儿童学习语词时,我们可以创设一个关于请柬的处境。由于请柬上会写着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游泳、赴宴、划船、看电影等等,于是儿童急于认识这上面的文字。在这个处境中,没有老师的帮助,儿童也会自己想办法试着去认识这些文字。在这个例子中,儿童之所以急于认识那些语词,是因为那些语词对他是有用的,也就是说,他只要认识了这些语词,便可以知道明天要发生哪些对他有益的事件。由于明天的事件是与他切身相关的,于是请柬上的语词便是对他有用的,因而也是切身相关的。因而,对他来说,切身相关和有用性成为学习语词的根本动因。因而,卢梭说:“当下的利益(l’intérêt présent),是伟大的动因(mobile)。”[6]117而在某个切身处境中,当下的利益便作为动因而推动儿童对事物和语词的认知。
关于处境,卢梭谈到,如果爱弥儿像鲁滨逊那样孤身一人在荒岛上,那么,“爱弥儿想要学习的心,比老师想要教他的心更为热切”,他“希望认知一切有用的东西,并且他只想认知这些东西”,在这种处境下,老师甚至“无需指导他”[6]185。这是因为,爱弥儿的首要关切是他自己的生存,他必须认识他的周围环境,找到各种有用的东西,比如御寒衣物、刀斧等工具。在这种切身处境中,基于其本能,他能够认知并利用其周围事物,而且他对周围事物的认知也是最真实的、最真切的。
这种设置处境方式的优点在于,它让儿童亲自地、主动地去发现事物的有用性,而不是由教师告诉儿童。卢梭说,如果总是由他人把什么是有用的提供给儿童,那么,“儿童便无须自己去思考,也不知道有用性是什么了”[6]179。反过来,如果总是由儿童本人亲自接触事物、使用事物,那么,“由自己以这种方式来习得对于事物的观念,远比得自他人教导的观念要清晰且确定得多”[6]176,并且,这些观念才真正属于他自己:“在把事物放置在记忆之前,要使理解力已掌握了事物,那么,从记忆里取出的东西才属于他。”[6]207否则,如果只是记忆,而不是经由自己来理解,那么,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的。
语言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源于人与周围事物的直接接触、感知、体验和理解,其理解方式则是关系其生存与福祉的生存式理解。基于语言的这种发生机制,语言教育的真正方法也就自然呈现了。
(六)回到生命—世界的关联方式以及基本生存意向
回到实实在在的事物并最终回到具体生存处境,意义便可以自身呈现出来,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天性(nature)即人的自然倾向,或者说人的生命与世界的关联方式。
在卢梭看来,生命—世界的关联方式有三种:“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感觉时,我们便倾向于追求或躲避产生这些感觉的事物,这首先要看这些事物使我们愉悦还是不愉悦,其次要看它们对我们是否适宜,最后要看它们是否符合理性所给予我们的幸福或完满的观念。”[6]39也就是说,对于世界中的事物,人有两种基本倾向即追求或躲避,而追求与躲避则取决于事物相对于人的生命的价值,即,它们让我们愉悦还是不愉悦,它们适宜我们还是不适宜我们,它们是否符合我们的幸福或完满。而这三种关联方式,总体上说来,是从人这一侧出发所建立起来的生命—世界的关联。
生命—世界的这种关联方式的基础在于人的实际生存意向。首先,从形式上看,生存意味着,个体的基本意向(intention)在其世界中的现实化(以及落空)。个体的基本意向总是指向其世界中的某些事物,他要求实现他的意向,得到他所欲求的事物,从而维持自身、发展自身。其次,从具体内容上看,这种个体的生存意向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不是单纯的打交道或使用工具,不是剥离了目的(what for)的单纯如何(how),而是说,如何建立在目的之上。也就是说,个体总是处在某时空的具体处境中,基于其维持并发展自身的基本目的生发出特定的目的,并以其环境中的事物作为具体手段或资源来实现其特定目的。卢梭的这种回溯,并不只是停留于抽象的如何,而是把个体的生存或生命—世界的关联方式回溯到了目的与如何的基本关系上。其实,在操作上,我们当然可以把如何抽象出来并单独考察,但从根本上说,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或依赖于目的。
三、卢梭的语言教育与现象学回溯
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简略讨论了现象学的基本思维方式,然后具体讨论了卢梭的儿童语言教育方法。如果我们以“后视”的方式(从今天的视角看过去),从现象学的眼光看卢梭的儿童语言教育的话,我们会发现,它与现象学基本思维方式即回溯是一致的,但卢梭的回溯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为彻底。
首先,二者的一致性。回溯是现象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在语言上,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从语言符号回溯到其意义之根源或源泉上,比如直观(胡塞尔)或与用具打交道的在世方式上(海德格尔)。卢梭的教育方法也是类似的,它要求摒弃洛克式的单纯语词的教育,从语词回到语词所指涉的事物,回到有用性、个体的具体的生存处境,并最终回到个体的生命—世界的关联方式上。
其次,卢梭的方法最终回溯到了人的实际生存意向上。胡塞尔(《逻辑研究》时期)从语词回到了(理论性的)直观。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时期)则更彻底,从直观回溯到了更为基础的此在与世界的打交道之上或生存方式上。但是,海德格尔却主要把此在的生存(Existenz)限定在如何(how)上,而没有深入讨论此在的基本生存意向。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基本生存意向恰恰是最基本的或最为根本的。因而,在这个方面,海德格尔的回溯显得略为抽象,而卢梭的显得更为具体和根本,似乎更好地体现了现象学所要求的具体性和彻底性。
四、卢梭语言教育方法的价值
在今天看来,卢梭语言教育方法依然有重要价值,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它在现象学上的价值。正如上一部分所讨论的,卢梭的回溯方法最终回溯到了个体的实际生存意向,回溯到了目的,因而显得更为深入也更为具体。这对于要求具体性和彻底性的现象学来说,具有参考价值。
接下来是它在语言教育上的价值。卢梭反对洛克式的单纯停留在语词符号的层面的做法,而是倡导回到语词或符号的意义的根源或源泉。卢梭所反对的洛克式的做法,如果用后期胡塞尔的说法来表述的话,便是“意义抽空”(Sinnentleerung)[9]46-50的做法。也就是说,洛克式的方法只限于语言符号层面,而不关联到其意义的来源,这便抽空了意义。由于它使儿童脱离了语言或符号的意义源泉即个体的生命—世界的关联方式以及基本生存意向,因而儿童难以真正理解语言意义,从而会陷入空洞和肤浅,甚至会导致卢梭所说的只会背诵而不懂其意义的浮夸和虚伪。由于这种方法抽空了意义,脱离了与世界打交道,脱离了个体的基本生存意向,陷入纯粹的技术化,因而枯燥乏味且难于深入。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洛克式的方法的速度较快或者说效率较高,卢梭的方法速度较慢且较难全面实施。但卢梭的方法的优点在于,它有助于实现意义充实,有助于到达更为清晰、确定、稳固和深入的学习成效。因而,对于教育者来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回到语言的意义源泉即事物本身,回到对事物的亲身感知,回到实际切身处境,回到生命—世界的关联方式,并最终回到人的实际生存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