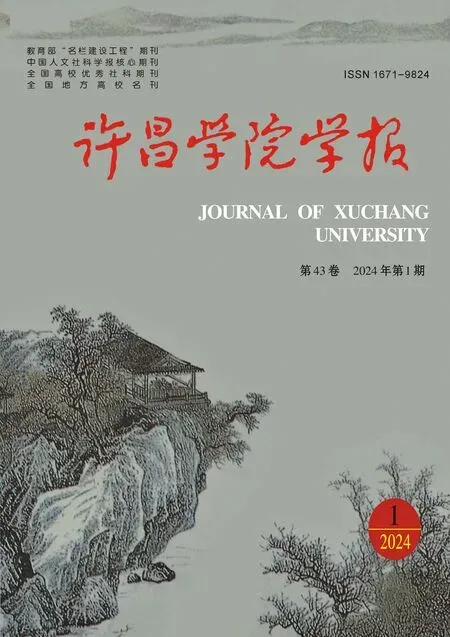《世说新语》“鬼子敢尔”论考
马 珏 丹
(清华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4)
《世说新语》一书是研究魏晋南朝的重要材料,其“方正”一门第18条载: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1]329-330
此条信息丰富:第一,卢志为北方士族代表,当时已沾玄风,陆机为入洛吴人代表,宿膺儒术,二者的争斗不仅是个人恩怨,也是北方士人与吴人及双方学问宗向冲突的表现;第二,“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安以此定之。”却未明言谁优谁劣,留下了争议,如叶梦得以为“云优机劣”,余嘉锡则认为“机优云劣”,反映出时代及评论者审美的变化;第三,现存材料中此事首见于郭澄之《郭子》一书,但《郭子》中并无“鬼子敢尔”一语,《世说新语》或有所改写或别有所本。后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取“卢充幽婚”的传闻以解释“鬼子”一语来源,“卢充幽婚”见于孔氏《志怪》和《搜神后记》,其中明言“子孙冠带,相承至今”,可知故事创作者并非用这则故事攻讦卢氏家族,而“鬼子敢尔”一语则带有明显贬义色彩,故“幽婚”传闻不足以释“鬼子”一语来历。《世说新语》作者在诸多说法中选取贬义更浓的“鬼子”一语自有主观原因。前人研究已对前两点有精彩论述,本文则主要对“鬼子”一语及其背后原因进行探究。
一
“鬼子”一词,因近代史的一些用法在中国文化语境内有了特殊的意义,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鬼子”一般指鬼所生之子或直接指鬼本身,如:
广语老鬼:“杀公者必是汝,可速还精神,我当放汝;汝若不还者,终不置也。”老鬼曰:“我儿等杀公。”比即唤鬼子:“可还之。”[2]266
这则故事中“比即唤鬼子”,便是指老鬼呼唤自己的儿子。因老翁为鬼,故对其子便径以“鬼子”称之。有时,“鬼子”也直接指称鬼,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
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怜之,鬼子乃敢尔!”即从生弟来。……[3]132
此处的“鬼子”即指女鬼,道士发怒,故以“鬼子”称呼女鬼,加重感情色彩。可见在志怪中,“鬼子”一词多表示与鬼相关的事物。
卢志之所以被称为“鬼子”,据刘孝标注,源于其先人与女鬼结合的传闻。这则故事亦见于《搜神后记》(54)“卢充”一条,旧本《搜神记》《搜神后记》皆辑入,现据李剑国考证,归入《搜神后记》。见陶潜撰,李剑国辑校:《搜神后记辑校》卷一○《卢充》,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582-584页。、孔氏《志怪》。现引《搜神后记》记载如下:
卢充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充以事对,此儿亦为悲咽。便赉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还。五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之貌。儿碗俱验。姨母曰:“此我外甥也。我甥三月末间产。父曰:‘春暖温也,愿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儿大,遂成令器,历数郡二千石,皆著绩。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子干,为汉尚书,子毓,为魏司空,有名天下。[4]582-584
“幽婚”指的是人与鬼相结合的婚姻。人和鬼的婚姻可分为“幽婚”和“冥婚”,魏晋时“冥婚”风俗颇为盛行,曹操便曾为自己的爱子举行冥婚,“冥婚”与“幽婚”间有细微差别(55)董舒心对前人关于“冥婚”的研究做了总结,指出:“‘冥婚’可以分为两类: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婚姻,按照性别不同又可以分为‘娶殇’(男性生者娶女性死者)和‘嫁殇’(女性生者嫁男性死者);死者与死者之间的婚姻,即将两个异性死者的尸骨合葬。……而我们所说的‘人鬼恋’故事则相当于冥婚中的第一类。”见董舒心:《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8年,第159-160页。。“卢充幽婚”故事即当时流行的“人鬼恋”传说,多见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者普遍认为“幽婚”传说的盛行与当时的女性生存状况和对鬼的新认识有关(56)如董舒心指出:“东汉以来人们开始将‘性情’与‘魂魄’联系起来为亡魂小说奠定了思想基础,宗法社会中男性中心家庭结构的确立使得‘女有所归’成为古代女性基本的生存法则,这势必导致未婚而夭的女性产生‘冥婚’需求。”见董舒心:《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第202-206页。李丰楙认为:“凡女子‘未字’‘未行’者就会面临卒后无所凭依的难题,为之立祠或采取冥婚即是一种补偿方式。”见李丰楙:《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9-10页。。就文本来看,“卢充幽婚”强调的是“幽婚”作为贤人(即卢植、卢毓)出现的先兆。《搜神后记》、孔氏《志怪》的记载并无贬低之意,其与当时志怪中“谈生”“辛道度”等故事颇为相似。谈生结局为:
呼其儿视,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谈生,而复赐之遗衣,遂以为女婿,表其儿为侍中。[5]389
辛道度结局如下:
秦妃始信之,叹曰:“我女大圣,死经二十三年,犹能与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为驸马都尉,赐金帛车马,令还本国。因此以来,后人名女婿为驸马。今之国婿,亦为驸马矣。[4]675(57)此条李剑国已指出非《搜神记》原书之条目,但据李剑国考证,仍为唐前小说,故风俗一也。见《搜神后记辑校》,第675-676页。
这些传说都强调女鬼与人相交不仅无害,还能带来好处,是家族兴旺的先肇。这类记载表现的是民间对世家大族发迹的想象和解释。但新起的传说无法在一时间攻下原有习俗的堡垒,志怪中也常见鬼怪害人的记载,如《风俗通义》载汝阳亭女鬼杀人、《陆氏异林》载钟繇与女鬼相接后数月性异常和《异苑》载秦树与女鬼相接后死亡等,可见在当时鬼与人相接有害于人的观点并未被摒弃。解释的差异性使得与鬼接触的传闻犹如幽明中的灰色地带,其含义的褒贬取决于阐释者的价值取向。
写作如做衣,开始便面临着选取与裁剪——哪怕因此不得不舍弃其他选择,因而成品便蕴含了极强的个人主观色彩。《世说新语》中“鬼子”一语,带有明显的鄙夷色彩。但在成书时间更早的《郭子》里,陆机对卢志的谩骂并未涉及“鬼子”一语:
卢志于众中问陆士衡:“陆抗是卿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于此!彼或有不知。”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识者?”疑两陆优劣,谢安以此定之。[6]1924
由此可知这一故事存在多种版本。《世说新语》选择“鬼子敢尔”进行记录,反映了作者对卢志的强烈否定。在《世说新语》中,与卢志有关的记载还有一条,“尤悔”第3条载: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1]987
从行文用字来看,对卢志污蔑陆机的行为颇为鄙夷,可见卢志其人在《世说新语》中的形象。
《世说新语》并非是对历史的严格记载,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世说新语》对前人材料的大量引用,尤其是对《语林》《郭子》二书的引用。但《世说新语》采用前人材料,并非完全袭用,常在细节处有变,从而突出所论人物与主题,试举一例: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1]808-809
同条,刘孝标注引《名士传》:
阮籍丧亲,不率常礼,裴楷往吊之,遇籍方醉,散发箕踞,旁若无人。楷哭泣尽哀而退,了无异色,其安同异如此。[1]808-809
《世说新语·文学》第94条载“袁彦伯作《名士传》成[1]299,则《名士传》先于《世说新语》。二书所记之事相同,但叙述重心有变化:《名士传》强调的是裴楷面对阮籍不合世俗礼法的行为能“了无异色,安同异如此”;《世说新语》的行文则使故事核心由称赞裴楷“安同异如此”一变为“两得其中”,笔墨重心已经偏向阮籍。为了实现这一变化,《世说新语》在行文中增添了对裴楷发问的第三者,第三者的引入是代读者发问,并由此引出裴楷对阮籍行为的解释,突出阮籍“方外之人”的形象。这种细微的改写虽未改变原事,但审美取向已然改变。
此类例子在当时小说中屡见不鲜,可见当时小说记载虽常有一事重出的现象,但部分重出之事作者已经进行改写,往往细微处有变,而行文的差别常取决于作者的审美。这类细微之处的改变无论是源于作者的有意改写还是作者对材料的选择,都反映出个人的倾向。以此观之,“鬼子”一语带有强烈的作者意识,《世说新语》的作者在众多故事版本中选择这一记载必有缘由。
二
《郭子》中“宁有不识者?”反映出的是陆机对祖、父功勋的自豪。《世说新语》中“鬼子敢尔”一语使士衡的形象更为刚烈,对卢志的贬斥也更明显。“鬼子”一语颇为突兀,刘孝标引孔氏《志怪》“卢充幽婚”之传闻以释“鬼子”一词。对此,余嘉锡先生笺疏:“余谓此乃齐东野人之语,非实录也。……干宝、孔约喜其新异,从而笔之于书。孝标因《世说》有‘鬼子敢尔’之句,遂引《志怪》之说以实之。不知《世说》此条,采自郭澄之所撰《郭子》。《御览》三百八十八引《郭子》并无‘鬼子敢尔’一句。唐修《晋书·陆机传》亦无此语,可以为证。此殆刘义庆著书时之所加。义庆尝作《宣验记》、《幽明录》,固笃信鬼神之事者。其于干宝辈之书,必读之甚熟,故于《世说》特著此语,以形容士衡之怒骂,而不悟其言之失实也。”[1]332此已指出“鬼子”一语乃《世说》所造,但仅将其原因归为刘义庆个人宗教信仰恐过于简单。刘义庆的宗教信仰使其对志怪故事颇为熟悉,但《世说新语》成于众手,作者对卢志的否定态度亦是其选用这一贬义色彩极浓词语的原因。
首先探讨“卢充幽婚”这一传闻产生的原因。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兴盛虽然有时代风气的因素,即佛、道、巫盛行,战乱频繁,六朝之人好言鬼神,但干宝等志怪作者以“实录”精神记载坊间传闻(58)干宝认为:“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见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搜神记·序》,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7页。,则时代风气之外,尚有触发因素导致具体鬼神事件的传播及其在传播中的进一步变形。张庆民在讨论钟繇与女鬼相合传闻产生的原因时曾指出触发这一故事传闻的现实因素(59)张庆民认为这则故事的产生“其旨意,乃是对钟繇修炼彭祖之术的嘲讽、讥刺,也是对当时名士风流的嘲讽、讥刺。”见张庆民:《陆氏〈异林〉之钟繇与女鬼相合事新论》,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第141页。。在今天看来颇为荒诞不经的传说,在当时往往有其根源。故而,在汉魏之际作为儒学世家而闻名的卢氏家族至东晋南朝时与“鬼”文化相结合,并被目为“鬼子”,当有现实因素。前辈学者对“卢充幽婚”这一故事产生的原因做了探讨,如张庆民认为“卢充幽婚”故事的本意是夸耀卢氏之富贵得由神助,是民间对卢氏一门“子孙冠盖,相承至今”的一种合理理解,并据此认为与鬼交往在当时是家族将兴旺发达之神异表现之一(与天神、地祇、动物显灵等故事相同)[7]。董舒心则认为这类“幽婚”故事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感生”类神话,“卢充幽婚”故事的出现可能与卢志向成都王颖建议收敛尸骨的善行有关,故民间故事中将其与“鬼女”相联系并将其作为美谈[8]170-171。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对此,本文认为可从卢氏与道教的关系进行补充,卢氏家族与“鬼女”传闻相联系,可能与卢志等人信奉道教有关。范阳卢氏兴起于儒学大师卢植,《后汉书·卢植传》载:
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9]2113
后曹操诏令称其:
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9]2119
据裴松之注《三国志》,汉末黄巾起义力量之一的五斗米教为张鲁所承,其信仰者曾自称为“鬼卒”。《后汉书》载:
鲁字公旗。……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9]2435-2436
对张鲁等势力的蔑称即为“鬼道”。卢植的兴起源于对儒学的精通与围剿黄巾军的功绩,则此时卢氏家族当与“鬼”文化相隔甚远。至卢植子卢毓则党司马氏,于《三国志·卢毓传》中察其行事,仍本儒家立身之道。卢毓之后传至卢珽、卢钦。《晋书》载卢钦:
后为侍御史,袭父爵大利亭侯,累迁琅邪太守。[10]1255
陈寅恪先生据此考证范阳卢氏在卢钦辈与天师道发生联系,并从卢氏与刘琨的姻亲关系论述其与赵王伦之关系进而证实卢氏对天师道的信仰[11]10。卢氏之与赵王伦发生关系,不特通过刘琨之姻亲关系,也有卢志这一层因素。卢珽之子卢志已和赵王伦关系亲密: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书郞,出为邺令。成都王颖之镇邺也,爱其才量,委以心膂,遂为谋主。[10]1256
赵王伦笃信天师道,陈寅恪先生已有论证,不烦赘述。卢志字子道,按陈寅恪先生观点,“道”在魏晋南北朝之际取作字多有宗教因素,此或可做一旁证。由此可推知,卢氏之与天师道发生关联,当在卢钦、卢珽一辈。
西晋时卢氏家族颇为显赫,卢毓为助晋篡魏之功臣。陆机出自吴国,三代为将,世膺儒术。其入洛之时,西晋学风已经转变,王弼等人的学说新起,由儒入玄已成新的风尚。故陆机与卢志的争端可从学术宗向、地域和政治思想的关系考察,但此时卢氏家族并未与“鬼文化”相联系。从现存文献看,将卢氏先人与女鬼联系在一起的传闻当流行于东晋后期,《搜神后记》、孔氏《志怪》均记载“卢充幽婚”一事,可见此事的盛传。但此时并未有贬义,而是将“幽婚”作为卢氏兴盛的先兆。这固然是因为六朝之人爱言鬼神,但卢氏家族对天师道的信仰应也是重要因素。
当时的道教修炼方式颇为杂乱,“房中术”盛行,女鬼与人交合之传闻很有可能源于道教的修炼方式。《抱朴子·内篇》曾指出当时房中之术的盛行:
虽曰房中,而房中之术,近有百余事焉。[12]348
葛洪长于西晋,又对道教行事颇为熟悉,由他的言论可知当时房中之术的兴盛。此时佛道两家常因传道思想而产生争论,佛教徒攻击道教徒的一大理论便是“不禁淫邪”,这也与道教广泛采用房中术有关。道教的房中术修炼及利用鬼神故事神化自己的方法强化了其神秘色彩,更容易吸引下层信众。然而故事一旦产生,其发展走向便不再由编造者控制,往往在传播中不断变形。正如张庆民对女鬼复生故事考察的结论:“由道教房中观念而引发的再生传闻,在其产生之初就发生着蜕变,并最终走向世俗化。”[13]74卢氏的兴起,加之其与天师道的联系,在世俗对“房中术”等修炼方式想象的催化下,产生“幽婚”传闻。
虽然研究者对“幽婚故事”背后的思想有不同的观点,但就文本来看,志怪小说对崔氏女与卢充的“幽婚”描写强调的是贤人(即卢植、卢毓)兴盛自有先兆,强调神异性,更多的是展现民间对世家发迹的想象和解释。彼时,卢谌虽没于北方,但其曾跟随刘琨辗转抗击外族,故在东晋王朝的评价并不低。在温峤等人的努力下,东晋王朝对刘琨进行了追赠:
太子中庶子温峤又上疏理之,……赠侍中、太尉,谥曰愍。[10]1690
因而纵使卢谌有出仕“伪朝”之举,亦未从根本上影响其家族地位及评价。故“幽婚”传闻为家族强盛之先兆,并不是对卢氏的攻讦,“鬼子”一词的贬义色彩也并不能代表“幽婚”传闻的感情色彩。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孔氏《志怪》,使人们将“鬼子”直接与卢氏“幽婚”的传闻关联起来,认为是卢氏“幽婚”的传闻导致此则记载。实则从“家族兴盛”之征兆到“鬼子”之语,其褒贬色彩差异颇大。
三
“幽婚”的传闻将卢氏与鬼神之说相联系,但不是卢志被蔑称为“鬼子”的唯一原因。署名刘义庆的《幽明录》亦记载女鬼与活人相恋终复生生子的故事(60)“广平太守冯孝将男马子,梦一女人,年十八九岁,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来四年,为鬼所枉杀;按生箓乃寿至八十余,今听我更生,还为君妻,能见聘否?’马子掘开棺视之,其女已活,遂为夫妇。”见鲁迅辑校:《古小说钩沉》之《幽明录》,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页。此外《幽明录》中还记载了如“崔茂伯之女”等人鬼相恋故事。,可见刘义庆并未对“人鬼相恋”特意贬低。从对范阳卢氏的发家史进行神化到明显的贬低,其间的差异,应考虑到卢氏家族在南朝地位的下降。
汉末至西晋,卢氏皆为显赫大族,卢植闻名天下,卢毓为司马氏一大功臣。但永嘉之乱,卢谌陷于北朝,终生不得南渡。
谌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值中原丧乱,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10]1259
南朝对晚渡之人颇为鄙夷,“晚渡伧人,其先人一般与胡族政权有染,他们要在东晋得到仕进机会,除了武功以外,只有靠特殊的际遇。即令得到入仕机会的人,想要预于江左的士流,那就更不可能。……卢氏子孙渡江,当在卢谌死、后赵亡、中原乱之时,其为晚渡伧人,更无可疑”[14]301-302。范阳卢氏虽然显赫,但“他们的先人与东海王越为仇,祖辈臣事胡族政权,自己过江又晚。凡此种种,都使他们无缘进仕建康”[14]303。卢氏子孙在南朝已经无力维持往日祖辈的荣光。卢氏族人卢悚已尝试利用道教起义,卢循更是与孙恩关系密切,希望凭借宗教的力量谋取政治地位。但二者都失败了,导致卢氏与宗教进一步捆绑,且社会评价更加恶化。孙恩、卢循的起义带有宗教狂热色彩,《晋书·孙恩传》载:
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吿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10]2633
恩穷戚,乃赴海自沈,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10]2634
这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行为方式是很难被整个士族社会接受的。孙恩败后,卢循复领其兵,他的对手主要为刘裕、刘毅。卢循虽然利用教徒的狂热对部队进行整合,但终败于宋武帝。这次失败给南渡的卢氏一支带来覆灭性的打击。
循势屈,知不免,先鸩妻子十余人,又召妓妾问曰:“我今将自杀,谁能同者?”……于是悉鸩诸辞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斩之,及其父嘏;同党尽获,传首京都。[10]2636
至此,卢氏家族在南朝彻底沦没,至梁时卢广自北来,南朝史传方又见关于卢谌后人的记载。
士族地位的保持需要强有力的现实基础,“冢中枯骨”并不能完全左右后世的评价。如陆玩面对王导联姻的请求答以“培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1]336。对此余嘉锡疏曰:“王、陆先世,各有名臣,而功名之盛,王不如陆。过江之初,王导勋名未著,南人方以北人为伧父,故玩托词以拒之。其言虽谦,而意实不屑也。”[1]337陆玩以祖宗之功名轻视王氏,而王氏终凭借王导功勋成为一流大族。当陆、王两家的地位发生变化后,这则事例在《晋书》的书写中情感色彩一变,成为陆玩对权势轻视的例证:“时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玩。玩对曰:‘培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其轻易权贵如此。”[10]2024可见现实地位起伏对后世评价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厮杀,以刘裕胜利而告终,曾与刘裕对抗且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卢循等人的形象被进一步妖魔化。刘宋立国,卢循等直接被定为“妖贼”(61)见《宋书》卷二十五天文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2页。《宋书》称“妖贼”凡一十五次,被其称为“妖贼”的人皆与宗教有关,涉及之人大致如下:孙恩、卢循、黄巾军、徐道覆、卢竦(按,即卢悚)。,以“妖”言之,足见其所具有的宗教属性。此时,“幽婚”的传闻已非家族兴盛的先兆,而成为卢氏近妖的佐证。家族的覆灭进一步影响了世人对卢氏家族的评价。作为刘宋宗室,刘义庆自然不会给予卢氏族人赞美。
由此观之,《世说新语》作者贬斥卢志为“鬼子”,并非仅因其家族先人有“幽婚”的传闻,也源于其后人卢循与天师道的捆绑及其争权失败后卢氏家族的现实处境。
四
以今日眼光看,《世说新语》当属于“志人小说”,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今天被称为小说的作品性质与现在有着极大差别。即使到了今天,研究者也没有否定《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但《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与正史依然存在区别,尽管此类书的作者都在标榜自己的“求真”意识,甚至《语林》因谢安讥其不实而遭摒弃,但作者个人的审美情趣或多或少渗透在写作中,这种主观性的渗入为小说的独立不断积累着因素。
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时,门阀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先辈的地位决定了后世子孙的地位,故有“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之语。但高门大族并非一成不变,王、谢、郗、桓、虞、萧等家族次第兴起,此消彼长。涉及现实评价时,不仅是先辈的荣光影响着后世的评价,子孙的现实地位也影响着前人的荣光。“卢充幽婚”的故事既可以作为“门第将兴”的征兆,也可以作为卢氏一族“近妖”的证据,其间的变化,不得不考虑卢氏的现实地位。或许可以这样说,卢志被称为“鬼子”,不仅源于其传闻中的先人卢充,更源于其利用天师道起义而失败的后人卢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