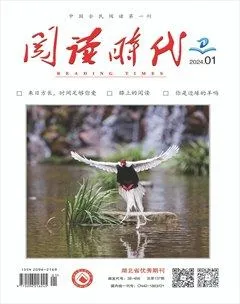童年里的《呼兰河传》
任永恒
距离哈尔滨三十公里处有座小城,叫呼兰,我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呼兰县靠着呼兰河,呼兰河是松花江的支流。在我看来:呼兰河是松花江的孩子,而呼兰县又是呼兰河的孩子。
那时候,大人是不准孩子们去河边玩的。但一到夏天,我们脑子里想的,全都是怎么到河边去痛痛快快玩一下午,回家还能不让大人发现。可我妈精着呢,我一进屋,她就一把把我拽过去,用手指在脖子上划一下,只要出现白道道,就二话不说,一大巴掌呼到我身上来。现在的孩子们估计想象不到,我们那会儿,可以说都是这样被大人打着长大的。
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是一次横渡呼兰河后。当我站在河的对岸,遥望家的方向时,就想:有一天,我会离开呼兰河,去很远的地方,也许还回来,也许不回来,就像萧红一样。
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县有个萧红,她是写《呼兰河传》的大作家。但直到我有了第一本《呼兰河传》,我才常常绕道从萧红故居门前走过,还常扒着门缝儿往里面瞅。但其实萧红的家人早已都不在那儿住了。
我坐在我家的楼顶上,开始读《呼兰河传》。坐在这里,抬眼能看见呼兰县的全貌。我向萧红故居的方向望去,萧红写的后花园,如今没有了,应该是现在的菜市场。萧红常去玩的公园还在,可是同现在我眼中的公园一样吗?十字街也在,街口有个叫“厚德福”的小饭馆,卖的锅包肉好吃极了,萧红吃过吗?
读着读着,我开始走进《呼兰河传》。我发现,萧红写的好多地方都已不在,比如我去那个叫“钓鱼台”的地方,呼兰河应该在那个石台子的下面,可现在站在台上看呼兰河属于遥望了。那么,萧红描写的看野戏的地方,就不是现在的河滩,究竟是哪里呢?
在工人文化宫楼前有一长溜的水泥台,每天早上我们上学的时候,总有一位年迈的老人,腰弯得与地面平行,破旧的帽檐上插着一块遮光的牛皮纸壳,一年四季的衣服永远是黑色的,夏天,后背常有一层层白色的汗渍,裤腿用一条带子缠着,好像脸上什么地方还贴着一块膏药……他放好小凳,倚着墙根坐下,高聲地喊着:“虱子药!耗子药!……”我莫名地觉得他就是“有二伯”,书中说,有二伯可能死了。书中的那个死去了,那么这个老人肯定是从《呼兰河传》中走出来的。
就这样,我拿着一本《呼兰河传》,沿着街道,沿着大河,沿着萧红的记忆,不停地走着。直到我能完全理解旧中国同新中国是不一样的时候,我,十四岁了。
那时候,若是大人问我,长大以后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定是:学文学,当作家。
(源自《阅读·中年级》,张甫卿荐稿,有删节)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