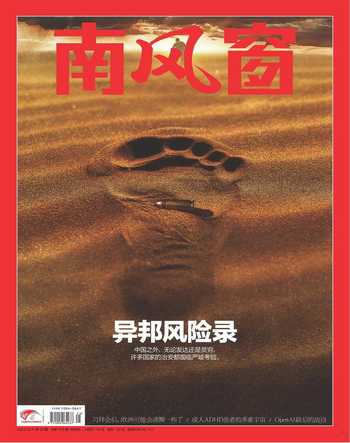“非升即走”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及反思
“非升即走”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及反思
沈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節选自《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1期
中国学术界引进“非升即走”的初衷,是为了优化学术资源配置,提升高校教师人事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西方,“非升即走”已经成为一项普遍实行并得到认可的学术制度安排,且形成了“以学术为中心”的学术生态,以此保障青年教师安心治学。尽管以“准聘—长聘”为特征的“非升即走”制度设计在中国学术界经常产生非议,但其专业性、科学性、有效性却是不容置疑和不可否认的。正因如此,这项制度却在争议中前行,成为当前“双一流”高校青年教师学术考核的基本制度安排。

进而言之,“非升即走”的制度设计,并非孤立和抽象的存在,相关的评审标准及程序依然受学术生态的制约,在操作过程中容易异化为“评审标准的易变性、评审程序的可操作性、评审目标的非学术性”。在缺少良性学术生态支持之下,“非升即走”的制度设计则可能异化成为小团体争夺利益资源的“合法工具”,因而广受诟病。起源于西方的“非升即走”制度设计,即使在某些西方极端案例中存在不足与缺陷,其也能够在原生学术文化背景中获得最大程度的调整。然而,当该制度落地中国高校后,与传统的人情、关系、面子、圈子的学术生态相结合,便会产生诸多摩擦与冲突,滋生“官气十足、门户林立、近亲繁殖、攀附结交、好高骛远、贪图虚名”等学术陋习。与其说社会舆论是在“炮轰”“非升即走”的制度设计,倒不如说是在指责“非升即走”背后的学术陋习,以及由此引发的“非升即走”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的“学术抗议”。
有研究表明,“高校频繁变动的考核制度、欠缺的保障条件和赋能不足的校园文化,使得高校青年教师劳动过程的焦虑感、被剥夺感、不安全感呈现逐渐增强态势”。高校青年教师不仅要经受竞争激烈的“非升即走”制度安排,而且还面临现实的生活难题,比如婚姻家庭、就业收入、住房改善、子女抚养等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挤占青年教师的学术时间,使本来就不宽裕的学术时间更加捉襟见肘。如果说顺应“非升即走”的制度设计是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的客观大环境,那么以“人情、关系、面子、圈子”为特征的学术生态,则是高校青年教师所必须应对的主观小气候。当客观大环境与主观小气候发生冲突且不可调和之时,可能爆发各种形式的“学术抗议”。落实到微观层面,轻则发生用脚投票的离职走人,中则产生矛盾纠纷的肢体冲突,重则发生伤人伤己的极端行为。
睿智与失智:现代国家的行政智慧问题
任剑涛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本文节选自《治理研究》2023年第5期
从主权视角看国家权力运作如何保有智慧,与经由行政执行权看国家权力的智慧问题,有很大不同。因为立法权的代议制、代表制是一种由讨论或辩论组成的权力形式,因此可以兜住国家权力失智的底。但在权力分立的体系中,行政执行权是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运作的,同时又是一种依照行政科层制度由上而下落实的权力形式。这就意味着,行政执行权被双重约束起来了:一是受立法权的法规约束,不需要行政执行者发挥太多创造性,其智力—智慧水平不是一个如何表现出来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克制的问题;二是受上下级关系的约束,“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有些过分其辞,但反映了行政科层制中服从上级指示的结构性事实。因此,行政执行者不能太过发挥主观想象与脑力智慧,否则行政执行就会在某个行政层级卡壳而无法执行下去。换言之,行政执行权中的智慧,不是首要问题,而是次级问题。

在这样的分权建制中,所谓行政睿智,是指行政执行权能够准确理解自己的权力定位,在行政执行中一抓就准,一抓即行,一抓见效。所谓行政失智,指的是行政执行权理解不了自己的权力定位,而且分不清行政问题的主次、轻重、先后、缓急,仅仅是机械执行上级行政组织和首长的指令,由此让行政绩效低下不说,还让人觉得未能保住起码的理智。
行政睿智与行政失智的分野,不仅在于国家基本结构是否供给了行政执行权以清晰明确的权源,而且在于行政建制自身是否设置合理,更加在于行政人员是否具有行政执行的理性认知、敏捷行动与致效追求。如果在三方面都具有肯定性资源供给,那么行政权就会在立法权抑制其太过主动的作为精神与积极判断的情况下,获得发扬其主动作为精神与敏锐判断力的契机,可以说,在现代国家的分权建制中,行政执行权并不是一种无需聪明睿智、埋首执行立法机构法规与决策的愚笨权力。相反,在权力定位、行权认知、分层分级、创意执行等因素推动下,行政执行权是有表现其智慧的广阔空间的。
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
汪德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比较》第105辑
现实中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可能更大,甚至可以说无法准确估算。一是2015年之前还有部分地方政府性债务未置换,遗留下来经转换形成当前的隐性债务。二是当前地方政府出于促发展等各种考虑,可以归类为隐性债务范围的资金,并非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也有部分用于招商引资或保运转、完成上级指派任务或达标考核等其他用途。这些债务资金因缺乏可供分析的准确信息,难以纳入估算范围。进一步说,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之所以“名目多、规模大、增长快”,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担负的职责范围缺乏清晰边界,其参与市场运作、或明或暗获取债务资金的手段多种多样,难以控制。从这个角度看,与地方政府有关联,但在法律意义上不能归为地方政府债务的资金,规模可能难以准确估算。
因此,任何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方案,都需要综合权衡其对这三个维度风险的影响。我们认为,应该继续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但要在不改变债务责任的前提下妥善处理存量隐性债务,避免利息成本过高、流动性受阻带来新的风险。从长期看,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改善政府投融资生态,降低无效低效投资,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同时要解决合理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
1994年我国实施了分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得以规范,但在财权和事权相匹配方面并没有得到有效完善。地方政府除了追求经济增长目标之外,往往还承担着上级政府摊派的“无资金”任务。因此,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方面,需要建立控制上级向下级政府随意下达“无资金”任务的机制,即要求上级政府在向下级政府摊派任务之前,必须综合评估地方政府的财力范围;另一方面,需要从法律层面解决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事权和支出责任不相适应的矛盾,分清基础设施建设事权和支出责任,禁止中央部门向地方政府随意下达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