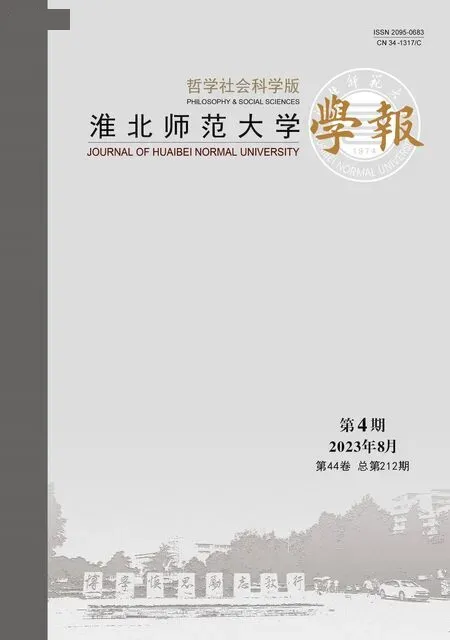论《寒夜》的战时经济叙事
陈广根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重庆 401331)
《寒夜》创作于1946 年,是继《家》之后巴金创作的又一高峰,是巴金“自己最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1],被视为“步入世界文学宝库而毫无愧色”的优秀作品[2]。新时期以来,《寒夜》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寒夜》是“继《家》之后另一部为接受者所广为聚焦的文本”[3]。研究者运用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症候批评等批评方法,对小说人物形象、主题意蕴等进行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本文尝试以经济叙事来对《寒夜》进行研究,发掘作家战时经济生活及经济观念等现实层面经济动因,分析小说主要人物的经济行为、经济心理、消费观等文本层面经济因素,通过战时经济叙事这一视角来探究小说文本丰富内涵。
一、经济功能与作家的战时经济生活
从社会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制于经济因素的制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毋庸讳言。对于个人而言,人们的吃穿住行等方方面面都折射出经济因素的强大影响。同样,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同程度上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也“形塑”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鲁迅曾经指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4]弗·杰姆逊曾经说过:“个人和社会经济的关系也许是现实主义的一个经典的模式。”[5]作为一门艺术形式,文学通过“艺术化”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也能反映社会经济的某些侧面,包括人们的经济生活。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6]。文学作品中,作家对现实生活经济因素的反映,可以称为“经济叙事”,这在现实主义小说中更为突出。
作为生命个体,作家本人的经济状况对其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包括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主题的确立等。巴金承认,《寒夜》“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7]257“要是我没有走上文学的道路(我由于偶然的机会成了作家),我很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样的结局。”[7]257,“小说里的描写并没有一点夸张”[7]257,因为“在战时的重庆和其他所谓‘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7]257-258直到1944年,40岁的巴金才与相恋8年的萧珊结婚,因为这样便“没有家庭的拖累”[7]259。“结婚时我们不曾请一桌客,买一件家具,婚后只好在朋友家借住,在出版社吃饭。”[7]259
抗战时期,窘迫的经济状况不只巴金一人,可以说是战时文人共同的遭遇。老舍在重庆“三年来,因营养不良,与打摆子,得了贫血病。病重的时候,多日不能起床;一动,就晕得上吐下泻。病稍好,也还不敢多作事,怕又忽然晕倒。”[8]。为了节约用度,老舍将烟酒茶等一并戒除,在贫病交加中创作《四世同堂》等文学作品。老舍主持的“文协”曾筹募基金,援助贫病作家,没想到自己也沦为需要救助的对象,令人唏嘘。张天翼无钱治病,《新华日报》1943 年4 月连续多日刊登《张天翼病剧》《伸出同情的手来,救助张天翼氏!》《从贫病魔掌中,援救张天翼先生!》等文章,呼吁救助张天翼。张天翼是幸运的,得到社会各界关注并及时获救,而有些作家则没有挺过来。1945年1月,缪崇群病逝于重庆,巴金痛惜之情溢于言表:“我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我的最好的一部分;我失去了一个爱我如手足的友人。那损失是永远不能补偿的了。”“听说你在病中说过,你不愿意死,不应该死。”[9]在此之前,陈范予、林憾庐、王鲁彦等巴金诸位好友亦先后离世。
作家们这种经济窘况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东部沿海、沿江工业地区和主要通商口岸相继沦陷,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关、盐、统三税收入锐减。在税源受损的同时,随着战事扩大,战时财政支出最主要项目军费支出急剧膨胀。1937年,军费支出达13.88亿元,在当年财政总支出中占比达66%;到1945 年时,军费支出在该年财政总支出中占比达87.3%。[10]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维护日益庞大的战时财政,国民政府唯一途径就是采取通货膨胀方式来实行无差别普遍征收。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通货膨胀总额已达5000 多亿元。[11]224在通货膨胀的刺激下,战时首都重庆,包括整个大后方地区,物价如脱缰野马,迅速上升。1945 年6 月底,国统区的物价是战前的1188.9 倍。[12]利用恶性通货膨胀,重庆国民政府当局把巨额财政赤字转嫁到广大人民身上,使重庆各阶层群众的生活状况不断恶化。在此情况下,重庆劳动者工资收入远远落后于物价的飞涨,陷于日益贫困中。根据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公布的资料统计,1943 年重庆工人实际工资只相当于69%的战前工资水平。[13]战时领薪阶层生活水平急剧下跌程度最大的是1944、1945 年。当时依赖工资收入生活的广大阶层,如公务员、教师等深受通货膨胀之害,难以维持温饱,处于苦难的边缘。
战前,重庆作为西南区域经济中心,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迅速变成全国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战时重庆经济的状况,对国民政府能否坚持抗日战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反过来看,抗日战争的军事形势,又直接影响战时重庆经济宏观决策和实际运行。战时重庆工业、商业、金融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得力于大量沿海工业、商业、金融业的内迁,也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成为全国文学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作家通过文学作品给我们呈现出丰富的战时经济叙事。巴金、茅盾、张恨水等小说将战时重庆苦难叙事延伸到市民经济生活领域,展现出战时首都普通市民的苦难生活,如巴金《寒夜》《还魂草》、茅盾《过年》、张恨水《傲霜花》等。在这些小说中,巴金《寒夜》将战时重庆市民苦难生活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表现最为突出,可以说是冰冷刺骨。
二、小说文本中的战时经济叙事
在经济叙事中,经济一般被视作为小说情节展开的重要因素,它有时会起到直接促进情节发展的作用,有时则会起到间接影响情节发展趋势的作用。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显性经济元素,如特定的经济事件——企业破产、银行倒闭等,也可以是特定的经济行为——收债、谋生等经济活动。同时,作为显性经济元素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数字往往以最直接、最具体可感的经济话语构成经济叙事的着力点,从而构成经济叙事中最富有经济色彩的表征。此外,常常影响人们行为的经济欲望,也可以看作是经济叙事显性元素。后者,我们可以称之为隐性经济元素。隐性经济元素通常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如对财富的看法,这往往使得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甚至爱情观等处理上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偏向,进而在行为反应上产生很大的反差,从而影响到故事的最终走向。《寒夜》文本有对经济事件的着力叙写,也有对人物的经济行为、经济心理的细致刻画,从而达到直面人物的生存本真状态,正是“现实主义”模式与风格的充分体现。《寒夜》触及到了社会经济的重要领域——城市市民经济问题。巴金看到了战时重庆统治阶级对人们的压迫,其小说中的经济话语反映了战时重庆底层民众的生存情状。对经济事件、经济数字、人们日常经济行为等相关经济细节的描写,使巴金笔下的人物真实、富有艺术感染力。
《寒夜》文本时间设置在1944 年秋至1945 年冬这段时间,主人公汪文宣在抗战爆发后一家四口逃难来到重庆。他与妻子曾树生是大学教育系毕业,曾经怀抱着强烈的教育救国思想,但社会现实将他们打回原形。在重庆,他失业长达三个月,依靠在银行当职员的妻子来维持全家生计。在一位同乡大力推荐下,他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领着极其微薄的工资。生活的重担将其压得喘不过气来,原本三十四岁的他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与同岁的妻子好像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14]65,他常常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无论是面临着婆媳不和,还是上级与同事的冷眼,乃至生活的苦难,但结局往往是事与愿违。
窘迫的经济状况使得汪文宣拥有极强的自卑心理,始终觉得让妻子承担家庭经济负担有种负罪感,但自己又不得不接受这种局面。在物价飞涨的年代,一支蜡烛也要三十块钱。1944年,洗衣大娘起初一个月要八百元,没过多久就变成一个月一千四百元,差不多上涨一倍,并且还在继续上涨。汪文宣一个月七千元薪水维持一家四口日常开支,可以说举步维艰。好几年,他连双袜子都没有买过,衣服破了一补再补。当准备给妻子买生日蛋糕时,他发现身上只有一千一百几十元,其中一千元是即将交出去的份子钱,而那个四磅的奶油蛋糕就要一千六百元,他连一磅都买不起。被公司解雇后,汪文宣几乎每天都在计算自己已经花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公司解雇的遣散费和曾树生留下的安家费,加上每个月的利息,还能维持多长时间。钱只有这点,可物价却一直在不停上涨,而钱又一天一天不停地流出去,自己却束手无策。他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但开支却又不断增加。他感到异常可怕:自己病重,又失业在家,坐吃山空,怎么办。一想到这事,他就发呆。
不合理的家庭支出加剧了汪文宣的自卑心理。小宣上学费用是整个家庭最大一笔开销,汪文宣无力承担,全部由曾树生设法解决。汪文宣病重前,小宣一学期花费两万多,而“这学期说不定要五万多”[14]196。当小宣来信说需要补缴三千二百元时,汪文宣焦头烂额。在汪文宣看来,儿子小宣学校补缴费用是天大的难题,自己无力解决,但在曾树生那里,却没有任何问题:“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我可以向行里借。我总比你有办法。”[14]70对此,汪母很有看法:“其实我倒想让他换个学校。我们穷家子弟何必读贵族学堂?进国立中学可以省许多钱。”[14]197但汪文宣即使自己再困难,也要坚持让儿子小宣继续读下去:“他上次考了个备取,他母亲费了大力辗转托人讲情,他才能够进去。”[14]197可以说,小宣入读贵族学校,是汪文宣夫妇二人共同的心愿,但更是这个家庭不合理的沉重支出负担。从这点来看,汪文宣与曾树生二人缺乏经济理性。曾树生坚持让孩子读贵族学校,更多的有自己坚强的经济后盾做支撑,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那么汪文宣如此坚持,也许更多的是出于对孩子和曾树生的爱。如此坚持,则更加剧了汪文宣经济上的自卑心理。
窘迫的经济状况、经济上的自卑心理,使得汪文宣无力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以致延误治疗,最终无药可治。当身体感觉不适时,他强忍着疼痛,舍不得花钱去医院看病,以致延误病情。可以说,汪文宣是因为延误治疗才导致最终无药可治。如果一开始,他积极配合治疗,去医院检查、透视,其病情还是有望能得到控制甚至好转。但在窘迫的经济状况面前,拥有自卑心理的汪文宣一开始心存侥幸,甚至讳疾忌医,没有认真对待病情,错误地以为吃上几副中药也许便好。汪文宣之所以愿意请中医,还是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一来,西医比中医要贵很多,诸如透视之类的检查费用更是昂贵;二来,中医张伯情是汪母的远亲,每次来家诊病只需给少许的车费就行,不收诊费,这样可以节省不少医疗费用支出。但中医的疗效并没有多大起色,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治疗,汪文宣病情日趋恶化。在曾树生和汪母的说服下,汪文宣来到宽仁医院。面对着昂贵的检查费及接下来更是天文数字的治疗费用,汪文宣更是绝望,只能在家选择中医进行“保守治疗”,但更多的意味着在“等死”。1945年9月3日,在抗战胜利日到来那天,他痛苦地离开人世。
可以说,在战时经济叙事中,汪文宣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其悲剧性角色更加突出。战时经济生活的挤压,使得汪文宣不堪重负,在理想与现实、家庭与工作、爱情与亲情等多重矛盾冲突中最终心力憔悴,成为战时重庆经济的牺牲者。
三、经济叙事的主题意蕴
自小说文本诞生以来,对《寒夜》主题意蕴解读呈现出“丰富性”,“寒夜”象征指涉亦没有形成共识。这些现象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脱离文本,过于追求理论深刻和观点独创。如果我们深入小说文本,则会看出,巴金将日本的侵略看作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一段漫长的寒夜,控诉日本侵略给中华民族和普通百姓所造成的沉重伤害。这一主题意蕴通过战时经济叙事充分呈现出来。
作为叙事的构成元素,人物与情节、背景等要素相互融合,共同构成叙事表达中无法替代的组成部分。“一旦人物被放回故事线索之中(而不是被从这里抽走),情节与人物的不可分割性就变得很清楚了。”[15]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不断展开的情节,人物不仅起到参与建构的作用,更是起着推动力的作用。《寒夜》小说文本中,有对人物的经济意识和经济行为的生动描写,也有对充满经济色彩的人物关系的多重建构,更有将这些人物置身于复杂而又现实、矛盾但又不可避免的经济环境之中,这些成为经济叙事中的又一重要表征。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迁渝,全国主要经济机构和众多工商企业纷纷入驻重庆。在战时经济政策刺激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重庆金融业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到抗战胜利前夕,除四行两局一会和四联总处等国家金融机构外,重庆还有4家小四行,26家省、市、县银行,57家商业银行,2家外商银行,24家银号、信托公司、钱庄等。[11]210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共有120余家行庄参加中央银行重庆分行票据交换。[16]随着经济的发展,一部分钱庄、银号改组为银行。战时银钱业,在商业投机和飞涨物价刺激影响下,获得较快发展,颇为发达,共有36家银号、钱庄在战时重庆新设。伴随新式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钱庄、银号也有较大发展,是战时重庆金融业发展中的一大特征。此外,战时还有花旗、汇丰、东方汇理、麦加利等外国银行在重庆等地设行货开办代表处。同时,重庆的保险等金融组织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11]211战时重庆经济的发展,培育出众多的资本家,他们依靠雄厚的资本运作在经济流通领域、金融领域赚取高额利润,迅速成长。在通货膨胀作用叠加下,金融资本、乃至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畸形繁荣,普通百姓则苦不堪言。
如果说汪文宣是战时重庆经济的牺牲者,某种程度上,曾树生则是战时重庆经济的“受益者”。她站在战时金融从业的风口,其薪资收入与隐形收入是普通工薪阶层无法比拟的。作为大川银行一名职员,曾树生实则为“花瓶”。在大川银行,曾树生游走于上司陈主任与客户之间,经常参加商业上的各种社交活动,以便获取利益。很长一段时间,她与陈主任在一起搭伙做囤积生意,经常出入胜利大厦、国际咖啡厅等高档场所,二人关系越显暧昧。在兰州,陈主任荣升为经理,如愿将曾树生调到自己身边,也最终导致曾树生与汪文宣离婚。战争的持续慢慢消解人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正如大多数人一样,汪文宣选择坚持、忍受,而曾树生则选择“活在当下”,先救出自己。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家庭经济收支中,曾树生与汪文宣事实上是实行经济“AA 制”。在这种“AA 制”中,随着曾树生收入的不断增加,其经济心理不平衡日趋明显。曾树生后悔当初的选择:“怪你有什么用?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14]77话刚说出口,曾树生要咽回去已来不及,但每个字像针似地刺进汪文宣的心里。事实上,在重庆,曾树生在陈主任的追求下已情感出轨,但她一直在汪文宣、陈主任之间徘徊。当曾树生下定决心离开重庆,远赴兰州,即便与丈夫汪文宣睡在一处,彼此的心却隔得很远,“她的心一天一天地移向更远的地方。”[14]167跟汪文宣分离,在曾树生那里“似乎并不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14]167
曾树生与汪文宣因恋爱而结婚,即便生活种种磕磕绊绊,多年的夫妻也是有感情的。离开重庆前夜,她还是恋恋不舍。“其实我也不一定想走。我心里毫无把握。你们要是把我拉住,我也许就不走了。”[14]176“你又一直在生病,妈却巴不得我早一天离开你。”[14]176“经济问题倒容易解决。你只管放心养病。我会按月寄钱给你。”[14]177飞离重庆后,最终曾树生还是向汪文宣正式摊牌:“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你的妻子,我不再是汪太太了。”[14]210可以说,窘迫的经济状况导致汪文宣、曾树生对待生活的态度出现严重分化,最终导致家庭的解体。曾树生是善良的,对于离婚,她一直心怀愧疚,按月给汪文宣汇款,叮嘱他治病注意身体。因两个月没有收到汪文宣的来信,曾树生急忙从兰州赶回重庆,结果物是人非,阴阳两隔。
曾树生与汪文宣离婚,除了曾树生不安于贫穷生活想救出自己外,婆媳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狭小的经济空间更是激化了这种婆媳矛盾,乃至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寒夜》小说文本中,婆媳矛盾贯穿小说始终,而汪文宣则处于婆媳矛盾漩涡之中。抗战的发生将汪母、曾树生捆绑在一起,长期生活在一个空间狭小的屋檐下,因价值观、消费观等众多观念的差异,乃至难以调和的分歧,最终将整个家庭给撕裂。在汪母眼里,曾树生只是她儿子的“姘头”,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结婚。汪文宣对曾树生越是好,汪母就越是恨曾树生,似乎将曾树生恨入骨髓。她们二人生活在一起,互相折磨,“彼此的互相伤害”[17],使得双方都异常痛苦。在曾树生眼里,汪母在一天,这个家就不会拥有幸福,二人必须分开;分开后,曾树生与汪文宣或许还可以做朋友,在一起终究会有一天变成路人。如果没有战争,这个家庭不会变得如此不可调和。抗战,使得汪文宣一家四口来到重庆,窘迫的经济状况使得汪文宣没有经济能力另外独立安置自己的母亲,而自己又不会处理好母亲与妻子之间的关系,“自我主体终是无以确立”[18]。在汪母那里,她也曾想到等抗战胜利就会回昆明老家生活,但曾树生等不到那一天,也看不到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客观地说,为了这个家,汪母也付出许多。在这个家里,年届五十的汪母承担了绝大多数家务,洗衣、做饭、买菜、清洁、卫生等,宛然成了一个二等老妈子。为了补贴家用,汪母将身边值钱的东西能变卖都已变卖,连汪父留下的戒指这最后一件首饰也都卖掉。即使这样,汪母也无法改变窘迫的家庭经济状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济状况一天一天恶化下去。汪文宣病逝后,怀着对曾树生的怨恨,汪母带走小宣,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去处。
《寒夜》战时经济叙事触及战时重庆城市经济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控诉日本侵略给普通百姓带来的苦难,抨击战时重庆政府当局经济政策的失败与经济领域的腐败。巴金清醒地看到,底层民众因经济上的穷困所带来的苦难,主要不是因为自身的懒惰,也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更多的是因统治阶级对底层民众的压榨和剥削,这才是底层民众苦难的根本原因。所以,当汪文宣来安慰时,唐柏青愤激地说:“你说我应该怎样办呢?是不是我再去结婚,再养孩子,再害死人?我不干这种事。我宁愿毁掉自己。”[14]38统治阶级对底层民众的压榨剥削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小说借唐柏青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种人的。我们奉公守法,别人升官发财……”[14]38。在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编辑部主任兼代经理周主任以“公家的事”为由“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一名员工提出加薪的要求,而周主任自己“年终一分红,就是二三十万”[14]24。而一旦统治阶级觉得没有利用价值,便毫不犹豫将其开除。汪文宣在公司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处处小心翼翼,尚在病中却被公司无情解雇,仅仅得到一个半月薪水的补偿。
结语
长达十四年的抗战最终迎来光明,但汪文宣死在抗战胜利日,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突然传来时,汪文宣一句“你完了,我也完了”[14]243更是对日本侵略无声的控诉。汪文宣一生的幸福就这样被日本的侵略给摧毁,虽然日本侵略者宣告投降,但他却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用颤抖的手捏着笔,吃力地在纸上写着:‘我可以瞑目死去。’”[14]243这是血泪的控诉,虽然这审判来得是那么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