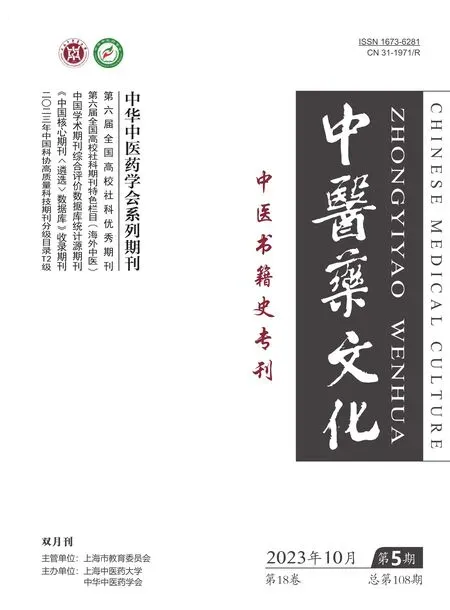正典与世俗之间:《串雅》医疗知识空间的构筑
刘雨茁,王育林
(1 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长春 130117;2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029)
《串雅》是清代士人赵学敏编纂的一部医方,往往被认为反映了清代江南地区走方医群体的医疗技术和经验。当代学者对此书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如赵东丽等从古籍版本的角度对《串雅内编》的袁氏刻本与榆园刻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从整理修改、语言风格等角度探讨两版本的异同[1-2];又有陈仁寿、吴小明等学者以《串雅》为史料基础,探讨清代浙江地区民间走方医的医疗特点[3-4];王静对清代走方医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部分涉及对赵学敏及《串雅》的探讨[5-6];黄玉燕等学者则主要从学术思想、临证经验方面对《串雅》进行了研究[7]。上述研究均认为《串雅》的文本呈现了清代走方医的医疗世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对《串雅》内、外编共8 卷的内容进行了逐条的史料溯源,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文本都直接转录自《本草纲目》,另有部分来自《石室秘录》与《万氏家抄济世良方》,与既往认知有较大出入,因而《串雅》的史料性质有必要被重新审视。那么,《串雅》的文本世界如何组成?其能否真实反映清代江南地区走方医的特点?赵学敏编纂《串雅》构筑了怎样的医疗知识空间?本文将试图解答这些疑问。
一、赵学敏与《串雅》的基本情况
赵学敏,字恕轩,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生卒年颇难确定,根据现有史料可推知赵氏大致生活于清雍正、乾隆年间,约嘉庆初辞世。赵学敏之父为杭州地区的官员,育有赵学敏、赵学楷兄弟二人,并希望“一子业儒,一子业医”,故而赵学楷幼年时即读医书,并最终以医为业,而业儒的赵学敏也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赵学敏早年“性好博览”,对星、历、医、卜等方技之学均有所涉猎,其中即包含了大量的医学典籍[8]460-461。《串雅》自序中详细胪列了赵学敏所读医书:“予幼嗜岐黄家言,读书自《灵》《素》《难经》而下,旁及《道藏》《石室》,考穴自《铜人内景图》而下,更及《太素》《奇经》。《伤寒》则仲景之外,遍及《金鞞》《木索》;本草则《纲目》之外,远及《海录》《丹房》。”[9]5-6可见赵学敏涉猎广泛,其中除《黄帝内经》《伤寒论》《难经》等医学经典之外,也旁及《石室秘录》《伤寒金鞞疏钞》等明清医著。赵氏有汇抄医书的习惯,读书每有所得便抄撮成帙,“久而所积溢簏外,束庋阁上,累累几千卷”[8],因而著成《利济十二种》,包括《医林集腋》《养素园传信方》《本草纲目拾遗》等12 部医方、本草、养生类著作,其中即囊括了《串雅》。
《串雅》约始著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其时赵学敏宗子赵柏云自中山航海归来。赵柏云为游历南北的走方医,二人论及医学,赵学敏认为“其道颇有奥理,不悖于古,而利于今,与寻常摇铃求售者迥异”,肯定了走方医诸技的效验,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即“旁涉玄禁,琐及游戏,不免夸新斗异”[9]6。因此将赵柏云所示走方医诸法重新修订,删去为国医所不道的部分,与自己纂辑、收藏的医书进行汇编,而著成《串雅》一书。赵学敏编纂《串雅》的主要目的在其自序中已有说明:“存其可济于世者……使后之习是术者,不致为庸俗所诋毁……谁谓小道不有可观者欤?”[9]6即希望能够将走方医医技中雅驯、价值高的部分留存,以便后人学习使用,避免误入歧途。《串雅》分为内编4 卷、外编4 卷,内编分为截药、顶药、串药、单方四部分,截药与单方下又有总治、内治、外治、杂治诸门;外编则包括禁药、字禁、术禁、起死、保生、奇药、针法、灸法、熏法、贴法、蒸法、洗法、熨法、吸法、杂法、伪品、法制、药品、食品、用品、杂品、医禽、医兽、鳞介、医虫、花木、取虫、药戏诸门,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禁方、外治、兽医、医花木、药品等诸多领域。那么这些内容的具体来源为何?它们是否能够真实反映清代民间走方医的医疗技术?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串雅》的文本世界。
二、《串雅》文本溯源考
《串雅》医药知识的来源在赵学敏的数篇序文中能够管窥一二,兹胪列于下。《串雅》自序中这样写道:“有宗子柏云者,挟是术遍游南北,远近震其名……因录其所授,重加芟订,存其可济于世者,部居别白,都成一编,名之曰《串雅》。”[9]6又《利济十二种总序》云:“柏云故虚怀士,颇以予言为然,慷慨出其历游方术顶串诸法,合予《养素园简验方本》汇编之,串而曰雅,知非江湖俗技之末也。”[8]而《串雅》凡例对这部书知识来源的描述最为详细:“是书采录得于柏云手抄者十之三,《百草镜》《救生海》者十之三,《养素园》及‘江闽方本’者十之三,其一则传于世医者,悉汇而成帙。盖筌蹄由始例得并志焉。”[9]8《救生海》即《救生苦海》,与《百草镜》同为赵学敏之弟赵学楷所撰医书。综观以上三种说法,其间互有出入,《串雅》自序仅提及赵柏云提供的医方术法;《利济十二种总序》在此之外,还指出赵学敏所纂《养素园简验方本》是《串雅》的另一知识来源;凡例则将《串雅》的知识来源分为四部分,即赵柏云抄录的医方、赵学楷的医著、赵学敏的藏书及著作、世医传习的验方。这些医书均已散佚,难以再窥知其貌,而《串雅》的文本中也未注明各条文的引用来源。因此,我们难以对《串雅》的知识来源形成较为具体、清晰的认识,也就难以评价其史料性质,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对《串雅》的文本进行逐条的溯源工作。
笔者利用“爱如生中医典海”“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数据库对《串雅》内、外编共八卷的文本进行逐条检索,并与可能作为来源的文本进行比对,最终发现《串雅》的文本来源主要集中于《本草纲目》《石室秘录》《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等几部医学典籍。具体条目的溯源情况详见表1。

表1 《串雅》各卷条目的溯源情况
由表1 可见,《串雅》文本的首要来源是《本草纲目》,共284 条,约占《串雅》全部条目的29%,这些条文多取自《纲目》的附方或时珍发明部分。其次是《石室秘录》与《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其中来源于《石室秘录》的条目为70 条,《万氏家抄济世良方》为52 条,约各占《串雅》全部条目的7.2%和5.3%。此外尚有龚廷贤编纂的数部方书,以及《卫生易简方》《遵生八笺》《集验良方》等,与《串雅》重合条文较多,亦是《串雅》可能的文本来源,由于文章篇幅限制,难以全部呈现。总体上看,《串雅》共有接近一半的条文能够找到明确来源,而《串雅》内编可溯源条文的比例又远高于外编,来自上述三部医籍者约占58.5%,而外编仅为28.2%。这些部分来源于既有的医学典籍,不能简单认为它们直接反映清代走方医的医疗经验与技术,而赵柏云游历得来的民间验方,很可能在未能找到来源的部分中。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为何判定这些条文是直接抄录自《本草纲目》等书,而不是转引自其他可能的中间文本,或是《肘后》《千金》等更早期的文本?理由有三:其一,赵学敏有阅读、抄录《本草纲目》《石室秘录》《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等书的先决条件。编纂《串雅》后不久,赵学敏便着手撰写《本草纲目拾遗》,因此赵氏对《本草纲目》应当已经十分熟稔;而前揭《串雅》自序中则提到赵学敏读书旁及《石室秘录》,其所撰《本草纲目拾遗》也多处明确引用了《石室秘录》以及《万氏家抄济世良方》[10],故而将相关条文抄入《串雅》亦在情理之中。其二,抄录条文数量庞大,已详于上文,且从体例编次上看,来源于同一部医籍的条文会更为集中,如内编卷四就存在连续20 条材料都来源于《石室秘录》的情况,很难说这是巧合。因此,通过他人医著作为中间文本转抄或抄录自早期文本的可能性较小,而直接从原书中抄录的可能性更大。其三,与《本草纲目》等书对勘,发现相关条文与《串雅》的文本相似度极高。大部分条文与《纲目》等书完全相同,或仅有个别字存在讹写等差异;小部分条文则经过改动,但多为语句的删减与拼接,仍可见明显的抄录痕迹。笔者进行溯源检索时,同一条文有时会存在多个可能的文本来源,将其进行比对后,则发现仍以《本草纲目》《石室秘录》《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等相似度最高,兹举一例如表2 所示。

表2 “摩腰丹”在不同医籍中的文本比对
因此,《本草纲目》《石室秘录》《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等书作为《串雅》的直接文本来源的可能性极高,而《串雅》凡例中提到的《养素园》与“江闽方本”的部分应当即对应这三部医籍。《石室秘录》《万氏家抄济世良方》二书,其编纂者陈士铎与万表、万邦孚等均为浙江人,其书刊刻后也主要在此区域传布。而《养素园简验方本》(又名《养素园传信方》)为赵学敏编纂,其选方也可能有来自《本草纲目》的部分。这些部分应当是赵学敏根据其知识兴趣选择并编入《串雅》,并对部分文本进行了一定改造,使其与走方医的知识体系更加符合。赵氏进行文本改造的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种:其一,简化、合并语言。赵学敏有时会将来源文本的语言简化,使其更为精炼。例如内编卷二“擦疮成水”条,其来源《石室秘录》在方前有“人有病手臂生疮,变成大块如拳头大者,必须用刀割去,人必晕绝,不可学也”[11]24一句,在《串雅》中则被赵学敏简化为“人有病手足生疮,变成大块,不必刀割”[9]74,而除此之外的部分文本均一致。其二,删减理论、医案故事的部分,使文本更趋于简易化、实用化。如内编卷一“起痿神方”条,即删去了其来源《石室秘录》中方药前后论述痿证病机的部分:“痿症久不效者,阳明火烧,尽肾水也。然能不死长存者何?盖肾水虽涸,而肺金终得胃气以生之,肺金有气,必下生肾水,肾虽干枯,终有露气,夜润肾经,常有生机,故存而不死也。”[11]244而仅摘录了其方药、剂量及服法。与之类似,同卷“安寐丹”条下也同样删去了方解的内容,仅保留了实用的部分。又如内编卷四“仙传膏”条,其来源《本草纲目》除主治、药量、制法、服法等之外还附有一段故事,强化了该方的神秘性:“有一贵妇病瘵,得此方,九日药成。前一夕,病者梦人戒令翌日勿乱服药。次日将服药,屋上土坠器中,不可用。再合成,将服,为猫覆器,又不得食。再合未就,而夫人卒矣。此药之异有如此,若小小血妄行,只一啜而愈也。”[12]1313而这部分也被赵学敏整段删去。其三,改换名目,赵学敏有时会将原书中的方药名称改换为更接近走方医习惯的名目,以达到将这些文本“嫁接”至走方医医学体系中的目的。如内编卷三中的部分顶药、串药都存在改换原书中方名的现象,如“四宝顶”原为“狗宝丸”,“砒霜顶”原为“紫金丹”,“牛郎串”原为“遇仙丹”,“双牛串”原为“济世散”等等,不胜枚举;又有部分方本无名,可能为赵学敏将其名称补入。但除名目改换外,这些条目的主治、方药部分都抄录无误,文本内容基本完全重合。其四,整合知识,赵学敏有时会将来源医籍中的不同条目进行整合,从而形成新的条目。如外编卷二“青布熏”条:“恶疮防水青布和蜡烧烟筒中熏之,入水不烂。疮伤风水,用青布烧烟于器中,以器口熏疮,得恶汁出则痛痒瘥。臁疮溃烂,陈艾五钱,雄黄二钱,青布作大炷点火熏之,热水流数次愈。”[9]191-192实际是由《本草纲目》中的三处用青布熏法的条文拼接而成,即“恶疮防水:青布和蜡烧烟筒中熏之,入水不烂。陈藏器本草”“疮伤风水:青布烧烟于器中,以器口熏疮,得恶汁出则痛痒瘥。陈藏器本草”“臁疮溃烂:陈艾五钱,雄黄二钱,青布卷作大炷点火熏之,热水流数次愈。邓笔峰杂兴方”[12]2183。内编卷三“青绿顶”条也是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将《本草纲目》附方中治疗顽痰不化与风痰卒中的二方整合,并对新条目进行命名。值得一提的是,赵学敏进行知识整合时也偶有讹误,与来源文本发生龃龉。如外编卷四“取疳眼虫”条,有“或用覆盆子嫩叶捣汁点目眦三四次,有虫随眵泪出成块也,无鲜叶以干者煎浓汁亦可”[9]259一句,在《本草纲目》中是“牙疼点眼”条的治疗方法,即通过将药汁点入眼中治疗牙痛,并非治疗疳眼有虫,由于《纲目》中此二条前后连续,因此赵学敏才误将其也作为取疳眼虫的治法。
三、“弃俗从雅”:《串雅》的医疗世界
经由上节的讨论,我们了解到《串雅》有约一半的文本有明确的来源,这些是经过赵学敏选择的知识,而并非清代走方医的实际经验;而未被溯源的文本或许有更复杂的流传过程,其中部分文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走方医的医疗实践。本节将试图分析赵学敏如何将既有文本“嫁接”至走方医学体系,以及为《串雅》构筑了怎样的医疗知识世界。
走方医掌握有区别于正统医学体系的独特医疗技术,如截、顶、串、禁、拔牙、捉虫、点痣等。《串雅》凡例中称“顶、串、截为走医三大法”,“顶”即涌汗、涌吐之法,“串”即攻下、泻下之法,而“截”则为禁绝之义,谓使其病截然而止。由于这些疗法往往取效极快,疗效显著,因而受到病者的青睐。除此之外,《串雅》中亦有载:“走医有四验,以坚信流俗:一取牙,二点痣,三去翳,四捉虫。四者皆凭药力。”[9]11截、顶、串诸法外,治疗牙病、眼疾、虫病以及点痣也是深受民众需要的医疗服务,尽管这些疾病不会危及生命,但却是对生存质量有较大影响的常见病,其中又以捉虫为要。《串雅》凡例称:“取虫为走医第一要法,而选元尤有起死回生之术。无此二门,则无由见神,故兼存不废。”[9]8可见取虫是走方医最重要的奇技之一,往往通过神奇的效验来获得病者的信任。另外尚有禁法、蒸法、针灸等,治疗内外科不同的疾病各有优势,“治外以针刺蒸灸胜,治内以顶串禁截胜”[9]10。除医治人类疾病外,走方医也治疗各种兽禽、花木奇疾,范围极广。走方医对于治疗方法与方药的分类方式也与正统医学不同,其他医籍往往按病证、脏腑分门别类,而《串雅》《串雅补》等书则主要依照截、顶、串、抵、色等走方医疗法进行分类,两类医籍的体例有较大差异。
尽管赵学敏依照走方医的医疗体系与分类习惯编纂《串雅》,但其中的内容却与走方医的实际应用情况相去甚远。清末医者鲁照在《串雅补》自序中提出:“恕轩所辑《串雅》,与方士所传不同。然观其门分截、禁,而法不外抵、色。”[13]可见鲁照熟悉清代走方医的医疗技术与习惯,并将其与《串雅》进行了对照,并指出了其中的差异。经笔者文本溯源,鲁照《串雅补》中的条文并未溯及早期文本,因而其内容应当更接近清代走方医的实际面貌,这也反证出《串雅》知识结构的复杂性。综观《串雅》全书,内编四卷主要包括截、顶、串诸法以及单方的内容,即内、外科的药物治疗,也是走方医最核心的治疗技术。然而内编中58.5%的条文可以溯源至前揭《本草纲目》等医籍,另外尚有部分条文存在可能的文本来源,因此赵柏云提供的走方医方术应当仅占二三成左右,甚至外编中被称为走方医第一要法的取虫门,40 条文本中竟有38 条来自《本草纲目》。可以推知,赵学敏删去了部分赵柏云提供的“夸新斗异”的医方,并选取《本草纲目》《石室秘录》等书中与截、顶、串诸法相对应的医方补入。这些经过筛选、来自《纲目》等书的医方相对详明,依托于既有医籍,并且具有较为清晰的文本流传谱系,更具经典性与权威性,因而赵学敏将其与部分真实的走方医医方混于一编,实际上是一种“弃俗从雅”的取向,即在保留了走方医学知识框架的前提下,对其中具体的医疗知识进行了优化与改造,意在“使后之习是术者,不致为庸俗所诋毁”,构筑了一个更为典雅的走方医学知识空间。
《串雅》外编四卷与内编有较大不同,涉及内容更为庞杂多样,前两卷多为除内服药物外的其他医疗技术,如禁术、急救、针灸、熏洗等较为简易甚至关涉玄怪的疗法。而这其中的针法门、灸法门、起死门、字禁门等部分,能够溯源的条文相对较少,可能更多来自于走方医的实践经验。卷三有关药品辨伪、食品、用品等部分,似乎是赵学敏为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而设,意在使《串雅》的读者能够识别伪药,免受走方医的欺骗,以及满足部分日常需求。走方医也是伪药的制造者与使用者,《串雅补》自序中提到“抵者,偏药抵金以欺人也”[13],有些走方医会通过制售劣质药物牟利,《串雅》外编卷三《伪品门》与《串雅补》卷三《抵方》都详细记录了走方医常用的伪药以及作伪的方法,因而这一部分内容的预期读者可能并非医者,而是缺乏医药知识的民众。卷四医兽禽虫、医花木的部分则几乎没有可以溯源的文本,其条文体例也与其他部分差异较大,很可能是来自于民间经验,可见赵学敏也为走方医的奇技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因此,《串雅》医疗知识的核心部分大多来源于既有医学文本,主要通过抄录以及进行知识改造的方式将其整合进入走方医的医学体系中。而少部分核心知识以及相对边缘的知识则主要来自于民间经验,很可能是经过反复的医疗实践后,在部分地域逐渐形成影响力,而被赵柏云、赵学敏吸纳,以“金疮铁扇散”一方为例,可以对这一过程管窥一二。“金疮铁扇散”见于《串雅》外编卷二《起死门》,主要用于刀石破伤的急救,由象皮、龙骨、老材香、寸柏香、松香、飞矾等药研末制成。此方创制与流行的大致经过,在《金疮铁扇散原序》中有载:
乾隆丙子岁十月几望,阳曲县民张成□刃伤李登云左耳根,深八分余,又伤项颈,横长三寸,血涌仆地气绝。邑令杨验毕将去,或曰:“胸微温。”令乃顾众曰:“谁能为予救治者?”时有韩士勇曰:“能,但治法与人异,敷药后必扇之。”邑令乃忆太谷县民有剚腹肠出数寸者,医士卢福尧治而愈,其法亦如之。乃问曰:“汝药得非卢医所传否?”士勇曰:“然。”遂令敷药扇之,须臾血止,俄而苏呻吟有声,越日痂结霍然愈……余膺简命,职在抚绥,凡可登民袵席者,敢弗仰体圣慈多方补救。今卢医方药起死回生,屡效于世,则流播岂容或缓。因招之……伊乃喜诺且曰:“雍正年间,得之塞外神僧,年来救治良多。”因令照方修制,遇伤辄试,皆效,爰厚赠卢医刊其方,以广救济云。时乾隆二十一年仲冬谷旦,山西巡抚兼管提督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明德识。[14]
由此序文可知,此方大约在雍正年间创制或传入,乾隆初曾在山西一带广为流行,并由山西巡抚明德刊刻传布。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余杭人沈大润行经山西而获此方,便将其带回浙江地区推广[14],并将相关的治验案例汇编为《金疮铁扇散医案》。《医案》共记录了11 位患者,除1 位山西僧人外,其余病患皆为浙江籍人士,其身份均为街边孩童、修屋者、孀妇、兵丁等普通民众。《医案》末称:“其余效验医案甚多,不能殚述,即此以例其余。”[14]可见“金疮铁扇散”在浙江一带应用较多,且在民间社会医疗中已具备一定影响力,同为浙江人士的赵柏云很可能在行医游历中闻知,将此方抄录下来,最终被赵学敏编入《串雅》。综上,《串雅》的知识来源、种类以及预期读者都是多元的,而并非是单一的走方医验方汇编。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赵学敏的社会身份上来。赵氏以儒为业,兼习方技之学,虽好阅读、收集医书但并非职业医者,没有直接参与到医疗实践中,其著书的动机或许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士人的知识兴趣,同时也试图为后来习医者以及需要医学知识的普通民众提供学习借鉴的范本。学者边和指出赵学敏医著中文献资料来源的多样性与大众性,与既往传统医籍形成鲜明张力,并将其作为18 世纪士人文化向大众文化下沉的代表人物[15]。然而从《串雅》中我们得见,在18 世纪亚文化兴起、社会下沉的背景之下,医药知识的世俗面向仍然无法完全摆脱早期医疗文本的影响。赵学敏的《串雅》是将民间走方医学体系与既有经典文本“嫁接”、对其中具体医疗知识进行优化与改造后的产物,依托于《本草纲目》《石室秘录》《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等既有文本,结合部分民间医疗经验以及与百姓日用相关的药物和边缘医疗知识,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医疗世界,我们得以藉此管窥士人主导下的医学知识的再生产。《串雅》所构筑的,正是一个介于正典与世俗之间,士人、医者与大众共享的医疗知识空间。在方书商品化、种类繁多、广泛流传于坊间的清代[16],《串雅》的“杂合性”也映射出赵学敏编纂医书一方面要适应大众应急性、碎片化阅读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既有医学文本确立一套规范化、程式化的“范本”,从而尽可能确保知识的可靠性与临床疗效,也对其他民间医疗技术构成一种规训力;同时兼顾内容的多样性与独特性,以满足文人学者“博物”“尚雅”的知识取向。《串雅》是清代中后期医学社会化日渐成熟的缩影,它的知识面向各阶层或群体,与医学精英或大众构建的医学体系均有不同,以期能够在书籍市场上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以走方医学的知识架构搭建书籍的内部空间,则隐含着对“民间医学”一定程度的认同,无意中起到了弥合精英医疗与大众医疗鸿沟的作用,对民众的医疗知识普及也有更强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