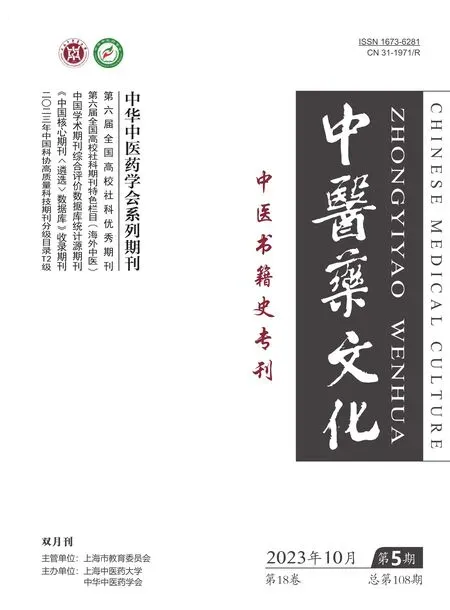清代综合本草编纂体例概说——“后《本草纲目》时代”的沿袭与突破
张苇航,韩 悦
(1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2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上海 200031)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成书15 年后,即他逝世的那一年终得在金陵刊刻完成①《本草纲目》的撰写“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即定稿于万历六年(1578)。万历八年(1580),李时珍赴太仓拜访王世贞,请求作序,但王仅题诗赠之。直至万历十八年(1590),王序始成;同年金陵书商胡承龙承接书稿,开始刊刻;万历二十四年(1596)刊印成书,并由李时珍次子李建元进献于朝。。由于该书“搜罗群籍,贯串百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子目十四·医家类二》),资料宏富且实用性强,很快就得到学界与医界的双重关注。自万历三十一年(1603)江西本刊行后,历代刻印传抄不绝。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存世的《本草纲目》明刻本即有8 种,清时传本约56 种,民国印本约11 种(其中各版又有多次翻印)[1]201-204,可见其广泛的影响力,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言“业医者无不家有一编”[2]。又据学者统计,在1593—1911 的300 多年间,现存的231 部本草著作中有90 部直接受到过《本草纲目》影响,仅明代就至少有18 种后续性著作[3]。《本草纲目》之名亦远播海外,成为被翻译和介绍次数最多的中医典籍。直至今日,对其进行阐释、研究和普及的书籍仍络绎不绝。
在这样一座医药学丰碑的映衬下,其后的传统本草著作在学术成就上显得有些暗淡无光,以至于其后的本草发展史可以用“后《本草纲目》时代”来概括。尤其是清代的本草书籍,在数量上虽占存世本草的近半,而被称道者寥寥可数。如尚志钧先生将明代本草归纳为“整理集成期”,而清代本草为“整理普及期”,水平出现整体下降,又缺乏划时代意义的杰出作品[4]。但作为运用传统方法编写本草的最后一个时期,清代的医药学家们仍在古代知识体系的背景下不断寻求从理论、方法至实践的充实与突破,并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与现代药物学的接续。本文基于本草书籍的断代史,尝试从编纂体例入手,对清代成书的综合性本草书籍概貌进行描摹,并从中反思传统医药学在近世发展的瓶颈和艰难转型。
一、本草书籍的分类
作为传统中医学的半壁江山,本草学的发展显示出更强的承续性,且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博物学特质,其源头可追溯至《诗经》《尔雅》所记的“鸟兽草木之学”②孔子认为,学《诗》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刘宝楠阐发:“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其性。《尔雅》于鸟、兽、草、木,皆专篇释之,而《神农本草》亦详言其性之所宜用,可知博物之学,儒者所甚重矣。”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869-890 页)。1977 年出土的阜阳汉简《万物》,即被认为是属于博物学的早期本草著述之例。。早期的本草学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本草”一词虽首见于《汉书》,但《艺文志·方技略》中并未见直接相关的书籍,在具体行文中又与“方术”“医经”等并列。如《汉书》卷十二《平帝纪》记载:“五年春正月……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5]207《汉书》卷九十二《游侠列传》又记载:“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5]3092至《隋书·经籍志》,本草书籍与其他医学书籍一起,明确被归入“医方”类,正式列入传统医学体系[6]。
在当代的书籍分类中,“本草”被归入“中药学”范畴。如《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将中药学分为本草、中药材、中药炮制制剂、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品、各科用药、中药药事组织,其中“本草”一项下再分为本草经、综合本草、地方本草、食物本草、本草各论[7]。对传统本草分类最为细致的当属尚志钧先生,他将本草相关书籍共分为本草经类(包括本草经注解本)、综合性本草类、药效类、地方性本草类、炮制制剂类、鉴别类、歌括类(包括歌诀及便读)、类书、图谱类、食物本草类(包括食养、食疗、烹制方法)、药用植物及驯养类、单味药类(包括单味药文献、单味药考证、生药学研究、药理研究、化学分析、临床应用)、杂著类(包括本草史料、用药理法、艺文、近代中药研究资料、辞典、药典及其他杂著)共13 大类[8]。中医文献的权威工具书《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本草”下列本草经、综合本草、歌括便读、食疗本草、单味药专类药研究、炮制、本草谱录、杂著8 大类[1]191-258,其中又分细目,具体如表1。

表1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本草”类书籍细目
其中,“本草经”类书籍的出现始于晚明而盛于清,与乾嘉考据学的兴盛直接相关,是经学与传统科技的渗透交汇,而数量众多的“歌括、便读”“食疗”及“杂著”类,体现了本草文化的民间性与实用性。
二、清代综合本草概况
虽然对于“综合本草”迄今为止仍无明确的概念定义,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内容上,这一大类都牢牢占据本草书籍的主流,是本草学术发展史的核心,也充分体现出本草知识的层累现象。一般认为,综合本草始于《本经》,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为其第二次总结,后循官方修订的《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品汇精要》为主要脉络发展,直至《本草纲目》这部集大成之著作,反映了综合本草具有内容的综合性、知识的全面性以及系统的传承性三大特点[9]。
清代的综合本草类书籍虽然在数量上占综合本草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但历来评价不高。尚志钧将清代本草特点归纳为“三少六多”,即大型综合性本草少,有新见的本草少,水平高的本草少;本草种类多,药物分类方法多,编写以节纂改编为多,食物本草相互抄袭的多,注释联系五行生克多,应用以临床和启蒙读物多[10]。陈仁寿从文献学角度分析了清代本草古籍的特点,同样指出清代缺少具有较高价值的划时代综合性本草文献[11]。对于这一时期本草文献的学术价值,重点集中于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和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而后者的主要成就在植物学方面,一般被归入“本草谱录”类。
清代的综合本草在《本草纲目》的强大影响力之下,出现大量摘录、改编《本草纲目》而编辑成书的现象,即使有部分个人经验和创见,也因《本草纲目》珠玉琳琅、成就过于凸显,而使其后出现的本草著作或多或少都被遮掩或忽视了。但从书籍发展史的整体来看,清代本草不仅在数量上占据存世本草书籍的近半数,内容亦极具特色,其编纂体例正是了解书籍总体状况的良好切入点。
三、清代综合本草编纂体例及特点
体例,原有规则、纲领之义,用于书籍的编纂方面,指著作的编写格式或文章的组织形式。如《宋书》卷五十五《傅隆传》载:“汉兴,始征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12]阅读古籍,明晰体例是前提。余嘉锡先生提到研治古书的“四误”中,“不明古书之体例,而律以后人之科条”便是“误三”[13]。对于条目众多、内容繁复的本草类书籍,把握编纂体例极为重要。同时,有计划、成系统编写的综合性本草书籍,往往已有比较完善的目录和凡例,便于读者在阅读前大致了解书籍的编纂原则和内容概况。
结合综合性本草书籍的特点,其编纂体例亦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来理解。狭义的编纂体例主要指每一味药物下的具体条目,主要涵盖名称、出处、产地、采收、炮制、归经、性味、功用、主治、宜忌、配伍、组方等内容;而广义的编纂体例首先应包括药物的分类方法。以《本草纲目》为例,其“凡例”首条即言明“通列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各以类从”;又明确其药品分类顺序及依据,“今各列为部,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再具体到每一药物,“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次以修治,谨炮炙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14]223。这样一纵一横、纲举目张,搭建起全书框架,能明确反映出该书的编纂思路和目的。因此,本文所指的编纂体例包括药物分类方法和药目编纂细则两个方面。
(一)清代综合本草分类方法
1.承袭《本草纲目》的自然属性分类法
一般认为,《尔雅》后7 篇将自然界事物分为草、木、虫、鱼、鸟、兽、畜,是自然属性分类法之滥觞。又据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所言“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桀错,草石不分,虫树(《证类》作兽)无辨”[15],推测早期的综合本草如《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等书,可能已在《神农本草经》三品分类的基础上,混合采用了自然属性分类法,但由于年代过早,不完善、不严谨之处难免较多,而自然属性分类法在历代综合本草中一直是分类学的主流,至《本草纲目》列16 部60 大类,便基本涵盖以往可见的传统知识。因此,后世综合本草,大都在其基础上再做减法,以突出实际应用的特色。清代采用自然属性分类法的代表性综合本草书籍情况大致如表2。

表2 清代代表性综合本草书籍情况
上述书籍皆是清代影响力较大的代表性本草著作。从药物分类可以明确看出它们基本没有脱出《本草纲目》的框架,但也或多或少做出了调整。尤其是《本草备要》,打破以“水”“火”开篇的具有哲学意味的分类惯例,以“草”“木”等临床常用药物居首,将药、证、因、机等联系起来,执简驭繁,切合实用,因而在刊刻次数上超越了《本草纲目》,成为历史上印行和传抄数量最多的本草著作。其后成书的综合本草在分类上亦多以此为据。
2.尊经复古的三品分类法
“三品分类法”源于《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分类法。具体原则为:“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20]三品分类法不仅与药效、毒性等实际体验相关,还受当时思想观念的重要影响,即符合“应天”“应地”“应人”的“三才之道”,但此分类法过于粗略,且不少内容已随着后世对药效与毒性的进一步认识而发生了变化,因此在后世本草书籍的编纂中,三品分类已经不再单独作为大纲使用,这一分类法往往只体现在对《本经》的辑复与注释中,甚至在《本草备要》中,《本经》的三品分类信息都不再单独出现。唯一明确采用三品分类法的仅为王子接的《绛雪园得宜本草》[21]。该书载药362 种,包括上品123 种、中品139 种、下品100 种,其中亦不再细分品类。因该书是《绛雪园古方选录》的附录,因此选药与论述皆着重于以《本经》记载阐发仲景经方用药配伍,虽简洁明了,但缺乏目录,查阅不便,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一部完善的综合本草。三品分类法在清代综合本草的编纂体例中逐渐淡出,反映出本草学的科技属性被广泛认知和加强,虽然此时仍推崇尊经复古之风潮,但一方面,经验丰富的医药学家们很清楚其适用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借复古来推新知的动机。
3.推崇实用的其他多种分类法
清代本草的一大特点即是分类方法众多。这既是本草编纂者们经验和个性的体现,也是在《本草纲目》这一集大成的巨著影响下,力求“切于实用,而堪羽翼古人”[22]的尝试。除自然属性分类法外,清代综合本草大致还采用了药性分类法、药效分类法、药物归经分类法、脏腑归属分类法、病证分类法等等。总体上强调药物的作用,推崇实用价值。
(1)药性分类法
药性理论体系始建于金元,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首次系统化地将药性理论引入本草,并创立药物归经说,著成《珍珠囊》一书。原书已佚,或被误认为李东垣之作,但元代杜思敬所编丛书《济生拔粹》收录该书,名《洁古老人珍珠囊》,李时珍《本草纲目》亦多引此书内容,并明确其为“金易州明医张元素所著……谓之东垣珍珠囊谬矣”[14]10。采用此种分类法的综合本草书籍较少,内容也相对简单,代表如明末蒋仪的《药镜》,正文录药348 种,按药性的温、热、平、寒分为4 部;明清之际的佚名抄本《药性主病便览》,载药160 种,分寒、凉、温、燥、热5 类;又有清代蒋介繁的《本草择要纲目》载药365 种,李文锦《思问集》载药220 种,何其伟《药性赋》载药350 种,皆以药性的寒、热、温、平进行分类。
(2)药效分类法
清代之前,药效分类多与三品分类或自然属性分类法混杂,起着进一步说明应用的辅助作用。清代中后期开始,为了便于对药物性能、主治、功用等进行分析和比较,尤其便于临床遣方用药时的查检选择,出现了多部以药效分类法为总纲的综合本草书籍,如黄宫绣的《本草求真》、沈金鳌的《要药分剂》、汪必昌的《医阶辨药》等。黄宫绣认为“本草一书,首宜分其形质气味,次宜辨其经络脏腑,终宜表其证治功能”“庶使毫厘千里,无有差谬”[23],故将药物统分为补、涩、散、泻、血、杂、食物7 大类,各类下再分若干子目,如卷一“补剂”下分温中、平补、补火、滋水、温肾;卷二“收涩”下分温涩、寒涩、收敛、镇虚;卷三“散剂”下分散寒、祛风、散湿、散热、吐散、温散、平散等等。论述时先对各子目进行概述,阐释分类概念、理论依据及此类药物的使用要点,以临床实用为要。
(3)药物归经分类法
将药物按经络归属进行分类的方法,亦源于张元素《珍珠囊》,以往多应用于本草歌括、便读中,可见该分类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简明切用。以此分类方法为编纂大纲的综合本草目前只见于清中期以后,如张节的《本草分经》[刊于嘉庆六年(1801)]、陈仲卿的《寿世医窍》[刊于道光十八年(1838)]、姚澜的《本草分经》[刊于道光二十年(1840)]等。姚澜的《本草分经》前由梅雨田所作的序言中称“经图及本草,其医之始事”,“原叙”中言“读者但识其性味主治,而于所入之经络,每多忽之”,故《本草分经》“原例”中明确“是编以经络为纲,药品为目”,又“分列补和攻散寒热六者”以为补充[24],反映出姚氏对药物归经的重视。
(4)脏腑归属分类法
脏腑归属分类法可以看作是药物归经分类法的延伸,但其正式作为药物分类大纲应用于综合本草的时期却早于药物归经分类法,大约在明代就已出现。首刊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由彭用光所编纂的丛书《体仁汇编》中,有《十二经络脏腑病情药性》一书。虽然书名中将“经络”放在“脏腑”之前,但在具体论述中,概念重点已由经络向其所隶属的脏腑转移,实际上已正式将药物依据脏腑归属进行分类。明末顾逢伯的《分部本草妙用》(1630)、清代吴古年的《本草分队》(1840)与凌奂的《本草害利》(1862)等综合本草均采用脏腑归属分类法。这样的转变可能与脏腑辨证在临床应用中逐渐受到重视有关。代表作如《本草害利》,便是凌奂继承其师吴古年“用药如用兵,盖脏腑即地理也,处方如布阵也,用药如用兵将也”的理念,在《本草分队》的基础上,“遂集各家本草,补入药之害于病者,逐一加注”[25]1-2,完善而成。凌氏根据五脏六腑将药物分为11 部药队,又根据各脏腑特点,列补泻凉温诸项,再根据药效强弱,分猛将与次将。如“心部药队”下,有补心猛将、补心次将、泻心猛将、泻心次将4项;“肝部药队”下,列补肝猛将、补肝次将、泻肝猛将、泻肝次将、凉肝猛将、凉肝次将、温肝猛将、温肝次将8 项;而“胆部药队”下,仅有补胆猛将、泻胆猛将、泻胆次将3 项。该体例主旨明确又新颖别致,但无论《本草分队》还是《本草害利》,民国前均未付梓,仅以抄本形式流传,亦为憾事。
(5)病证分类法
病证分类法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又案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亦有偏著”之观点[26]。该分类方法在历代本草中亦多作为辅助,如《本草纲目》卷三、卷四的“主治”部分即属此类。明末陈澈的《药症忌宜》、贾所学的《药品化义》、戚日旻的《药性便览》以及清代尤乘的《药品辨义》、修竹吾庐主人的《得宜本草分类》等皆以此法作为主要分类方法。其中,《药品化义》一书传本较多,包括原刊本(已佚)、李延昰补订本十三卷以及尤乘增辑本三卷(即《药品辨义》)。该书将药物分为气、血、肝、心、脾、肺、肾、痰、火、燥、风、湿、暑、寒14 类,同时结合了贾所学所创的“药母八法”理论,即在每类前加一小引以体、色、气、味、形、性、能、力来概述本类药物的大致情况[27]。这一体例虽有特色,但在书中与传统体例同时出现,二者又缺乏内在逻辑联系,使得此类编纂法未得到有效的发展与深入。
(6)其他
清光绪十九年(1893),一部以语录体编著的《本草问答》[28]问世,即中西医汇通派代表医家唐宗海与其门生张伯龙讨论药物理论与应用的记录。该书以问答形式编写,分上下两卷。上卷四十五问,涵盖药物治病原理、中西用药异同、药理药性、四气五味、药物产地、药效辨析等等;下卷三十问,除药物炮制、反畏宜忌、分经用药、临证用药、评价药书之外,还包括六经六气、脏腑气血、外感内伤等医学理论。从内容上看,此书虽未按常规形式记述单味药物,但重在对本草理论的阐释与发挥,因此亦被归入综合本草类,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此外,清代还有大量综合本草书籍缺少目录与凡例,在编纂时体例不清,分类较为随意。此类本草往往质量不高,缺乏独特见解与学术价值。
(二)清代综合本草药目细则
在对具体药物的阐释上,《本草纲目》已经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模板,即药物正名后,先注明最早出处,后依次为释名、集解、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诸条,根据具体情况又有精简,有些后面另有附录药物。清代综合本草多以此为据,尤其是近半数以自然属性分类法为主的书籍,但也有个别细目显示出特色。现将清代代表性综合本草中出现的药目细则总结如表3。

表3 清代代表性综合本草药目细则
将其上药目细则结合代表性书籍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窥见清代综合本草编纂体例的特点大致包括以下三点。
1.删繁就简,医道为先
就具体编纂条目而言,清代综合本草大多包括正名、性味、归经、功效、主治、宜忌等传统部分,部分书籍会扩展到药物的产地、采收、性状、修治、鉴别及配伍等内容。由于《本草纲目》对前代文献的收集较为全面,大多数撰著者亦缺乏李时珍那样数十年如一日的持续积累,因此多对具体细目进行大规模精简,其下亦不再采用堆叠文献的形式,而有意识地选择之前有代表性的医药学家的论述,如李东垣、朱丹溪、王好古、陈嘉谟、李时珍、缪希雍等。多数本草不设“释名”“集解”,不再引经据典地进行药名、辨疑等考证,而将论述重点集中在性味、功用、主治方面。其中大半书籍为行医多年、经验丰富的医者所撰,以指导临床为先。部分综合本草,如《得宜本草》《长沙药解》等更是为配合经方的应用而设,重在对配伍应用的阐释。同时,对药物采收、性状、产地、炮制等内容的记述相对减少,已有医药分家的趋势出现。
2.用药审慎,关注禁忌
与前代本草相比,清代综合本草审慎用药的思想更为突出,表现在多数代表性本草书籍注重说明药物毒性,或专设用药禁忌之项。如汪昂的《本草备要》、黄宫绣的《本草求真》等,都明确列出禁忌项,且加以详细说明。《本草害利》更是审慎用药的典范。吴古年认为用兵“苟调度不精,一或失机,一败涂地,即用药不审,草菅人命也”;而凌氏更是继承了此种观点,首先通过书名即强调“凡药有利必有害”[25]1-2,又从“害”“利”这种新颖的体例出发,将病证用药禁忌的讨论作为重点。这种重视用药安全的趋势可能与清代医家队伍的大量扩充以致良莠不齐的现象增多有关,另一方面似乎也反映出医药学知识的普及化,使得更多民众对医疗的安全度产生关注。
3.传承为主,各具特色
综合本草的传承历史源远流长,随着时代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其编纂体例不断丰富,内容系统渐趋全面,基本涵盖了传统知识对某一味药物的全面认识;同时具有强大的同化能力,特别在明末至清代,将大量地方性和外来药物顺利纳入传统本草体系,运用传统方法在性味、功效与使用上对其进行补充。代表者即《本草纲目拾遗》,该书载药921 种,其中有716 种补充《纲目》之未载,有161 种对《纲目》药物进行补订。另外,清代综合本草著作在编纂体例的框架中,也尽力凸显各自的特色,如《本草述》对炮制方法的重视,《本草害利》对药物毒性的强调,《药品辨义》对“药母”理论的发挥等等。虽然总体水平难以超越前代,但亦不乏有启发性的见解,值得进一步发掘研究。
四、后《本草纲目》时代综合本草编纂思路的探索
从本草学术的总体发展看,清代似乎是一个尴尬的时期。前有《本草纲目》这一里程碑式巨著,后有西学东渐带来传统知识体系的动摇。而本草学作为传统科技的代表学科,这一时期被我们称道更多的,反而是受过经学训练的学者们运用传统方法对《本经》开展辑佚、注疏的成就。对于立志编纂综合本草的医药学家们,如何在继承中实现突破,无疑是更加艰难的问题。赵学敏曾提到,友人闻其欲著《本草纲目拾遗》而劝其放弃,言道:“濒湖博极群书,囊括百代,征文考献,自子史迄稗乘,悉详采以成一家之言……亦何有遗之待拾欤?观子所为,不几指之骈疣之赘欤?”而赵氏反驳道:“物生既久,则种类愈繁。俗尚好奇,则珍尤毕集……禽虫大备于思邈,汤液复补于海藏。非有继者,谁能宏其用也?”[19]2其在努力数十年后,始成《本草纲目拾遗》这一清代综合本草的代表作。该书不仅纠正了不少《本草纲目》之讹误,且收载了大量地方性本草,还按自然属性分类,在各部类下列述了强水、倭硫黄、奇功石、西洋参、红毛参、阿勃参、帕拉聘、拔尔撒摩、金鸡勒、吕宋果、西国米、阿迷酒等外来药,反映出当时域外药物的输入情况,以及中药理论对外来药物的兼容与同化。然而此书在编纂体例上仍不脱《纲目》之架构,只是在时代发展的前提下,凭借更开阔的眼界并借力于物质资料的丰富而已。赵学敏所提到的“物生既久,则种类愈繁”,虽然从理念上已触及了生物进化的边缘,但仍缺乏科学方法的支撑,最终仅限于药物范围的扩充,而无法更进一步深入。传统本草发展的瓶颈,亦可从清末《本草问答》一书中反映出来。唐宗海弟子张伯龙提出“诸家本草扬厉铺张,几于一药能治百病,及遵用之,卒不能治一病者,注失之泛也。又或机意求精,失于穿凿,故托高远,难获实效”[28]1-2,迫切希望博通中西医的唐宗海能对本草阐述发明,拯救流弊,但唐宗海对此的回答也仅限于用取象比类的传统思维方式诠释药效、以气化诠释中药理论等,难以达到方法学上的突破。
形式是思想的反映。从清代综合本草书籍的编纂体例,可以大致看出在《本草纲目》所构建的相对完整的传统知识体系下,后世本草学家为推进发展、呈现特色所做的艰难努力。综合本草将何去何从?从书籍编纂思路的侧重点可以看出,从清代中后期开始,逐渐出现了三条分化的路径:一是传统路径,即延续《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着重于资料的补充,这实际上是本草的博物学回归。一是实用路径,即以实际效用为引领,从临床经验出发充实、发展本草理论,是本草的医学回归;这同时也是本草知识的下沉和普及路径,是传统本草得以在民间蓬勃发展的基础。最后一条是现代路径,是从19 世纪开始,逐渐融合生物学等现代学科发展而来的。相较于中医学的其他学科,本草学的现代转型似乎比较顺利,这可以从近代绝大多数本草书籍已改用“药物学”来命名中反映出来,其原因可能与东西方共具的博物学传统有着联系。对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利用,使得本草学成为中药学,使得这条现代路径越走越宽、越走越顺;但同时也因对实验技术的依赖,让中药学局限于生药学,有脱离中医特色而成为现代药学依附的危险。因此,现今我们有必要回到中药学正式形成之前的“后《本草纲目》时代”,审视传统博物学的尾音和现代药学的萌蘖,通过回顾来路而展望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