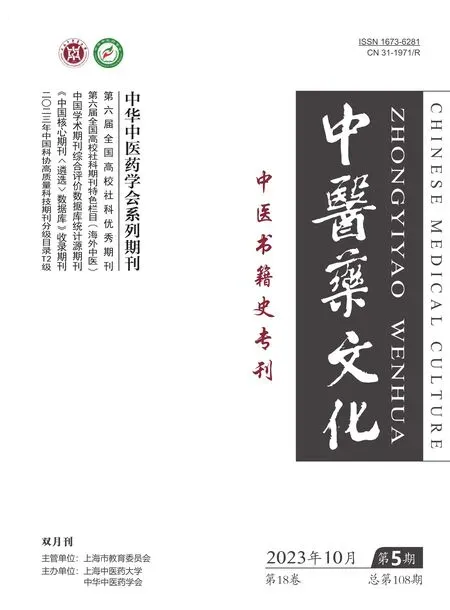《神农本草经》成书考
丁振国,张净秋
(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北京 100069)
古书的生成与写定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其牵扯问题较多,涉及各部古书情况又差异较大,加之早期文献不足征,即使是流传有序的先秦经部典籍,至今亦无一部成书脉络清晰明鉴,更何况早已散佚之医学类古书。近年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似乎相关问题可供探讨的余地逐渐拓宽,学界于此亦多有斩获。传统医学经典《神农本草经》一直为世人瞩目,研究者不乏其人①尚志钧先生早在20 世纪末即完成了《神农本草经》的校点,后几易其稿,最终于2008 年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代表性著作《神农本草经校注》。尚志钧先生之后又有:马继兴《神农本草经辑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 年);王家葵、张瑞贤《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年)等。。但或因时代较早,条件有限,或限于医部,未见通达,故其成书的相关研究仍有开掘之空间。本文即从古书通例视角出发,结合出土与传世文献,兼采历代目录著作、前贤成果,展开考辨。
一、书与“成书”
考辨《神农本草经》之成书,首先应对“书”“成书”的概念加以界定。一般学界认为,古代的书是以竹木简帛作为文字载体开始的②相关论述极多,如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载:“古代文字之刻于甲骨、金石及印于陶泥者,皆不能称之为‘书’。书的起源,当追溯至竹简和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版,第71 页)。。由于记载内容的差异,“书”的性质有所不同。李零先生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把“书”分为:作为档案的书,“文书”;作为典籍的书,“古书”③李零先生实际还提到书的另一含义,作为文字的书,“铭刻与书籍”。这实际与本文所言成书之“书”并非同一层次内容,故未提及。。这种分析对于探讨古书的形成,意义重大。“文书”是官方与私人日常性的书写,多为官方文件,日常行政事务记录,以及个人生活中的各类记录。“典籍”则是思想学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著述。虽然对文书与典籍做了这样的分割,但二者实际存在一定联系,特别是在早期古书典籍成书过程中。本文所探讨之“书”,当指古书典籍这一类。需要指出以避免产生混淆的是,今天一些档案文书的合集也被印制出版,称为“书”,这应该看作是“书”的内涵嬗变的结果[1]42-55。
再看“成书”。由于古书物质载体、古人撰著意识等因素的影响,古书成书概念与现代存在极大差异。文献学大家余嘉锡先生,当代著名学者李学勤、李零等诸多先生都有详细阐述[1-3]。简言之,古书成书特点为成书时间漫长、内容多经增广删改、所出绝非一人等。古人著述多不题撰者名姓,且因简牍沉重不易传播,多单篇流传,其结集成书多门人弟子或后世所为,所题书名亦多为后人所拟。“古代子书往往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其中不但有先生的著述、言论,也有门弟子或后学增益的‘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等内容。”(裘锡圭先生语)[4]一书即使出现相对固定的文本,也会在后世整理过程中出现增删、改动,因此所谓定本的最终确立实际经过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以儒家五经之一《尚书》为例,目前所知其成书过程可印证“书”与“成书”之概念内涵。作为一部历史文献集,《尚书》是夏商周三代最高统治者政治活动中诏令文件和谈话记录的汇编。中国古代史官传统悠久、制度发达,“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1715 页),有关内容古书记载颇有差异,如《礼记·玉藻》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礼记正义》(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1022 页)。,日常记录生成了大量文书、档案。这些原始材料经过整理——不同程度的删减、改写,连同一些仿写构拟的文献,成为具有“古书典籍”性质的篇章,再经编选形成《尚书》。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文献,学界称作“书”类文献②有关“书”类文献的范围,具体指涉,学界存在争议,本文非专论,故不做详细考辨与区分,如诰誓号令或档案文书、春秋战国普遍流传之“书”、传世之《书》等,宽泛地皆视为“书”类文献。三者实际存在一定历时层面的关联,且相当复杂,参看章宁《书类文献刍议》(《史学史研究》,2019 年第1 期,第93-101 页);程浩《古书成书研究再反思——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 年第4 期,第132-143 页)。,其数量可能多达数千篇[5]。至汉代,儒家理念成为统治思想,《尚书》推为经典。从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内容和命名来看,这些篇章都是政治生活中君臣特定行为所产生的文字记录,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可谓“因事立篇”[6],而实际上它经过了由“文书”到“典籍”的演变,漫长的产生、删改、构拟、选编过程之后方才成书。前文所言文书与典籍之间的联系由此足见一斑。基于对“书”与“成书”的理解,本文将对《神农本草经》的成书过程进行讨论,以期得到较为清晰的初步认识。
二、汉及汉前“本草”类文献的历史状貌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国内出土文献大量涌现,其中不乏医学类内容。这就使长期以来仅仅依赖传世文献的记载获知早期医药发展状况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的突破。
(一)出土秦汉医学文献中之“本草”考察
截至目前,汉及前代涉本草内容相关出土医药文献主要有以下十几宗:
(1)1907 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发掘汉代简牍,包含方技类内容;
(2)1972 年,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汉代医简;
(3)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五十二病方》;
(4)1977 年,安徽阜阳县双古堆出土汉简《万物》;
(5)1979 年,甘肃马泉湾发掘汉代简牍,涉及医药;
(6)1980 年,西安发掘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A 区遗址,出土“病历医方”木简;
(7)1987 年,湖南张家界古人堤出土汉代医方简牍;
(8)1993 年,湖北沙市周家台出土的关沮秦墓医方竹简;
(9)1999 年,额济纳旗出土汉代医方简牍;
(10)2002 年,湖南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出土秦简;
(11)2004 年,安徽天长市西汉墓出土医方木牍;
(12)2009 年,浙江湖州出土汉简,学界称“乌程汉简”,其中包含医药简;
(13)2009 年,北京大学收藏一批西汉竹简,包含医方;
(14)2010 年,北京大学又收藏一批秦代简牍,包含医方;
(15)2011 年,湖南长沙尚德街出土东汉医方木牍;
(16)2011—2015 年,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包含医方等;
(17)2012—2013 年,四川成都金牛区天回镇西汉墓出土医书;
(18)2018 年,在湖北荆州胡家草场大墓出土的简牍,包含医书。
其中(4)(11)(13)(16)(18)并未正式公布,但其中部分简牍释文已发表。秦代医简有三种,即(8)(10)(14),其余皆为汉代医简,秦以前医学文献未见出土。以下试举几例,以观医方体例及与本草之关系。
①取肥牛膽盛黑叔(菽)中,盛之而係(繫),縣(懸)陰所,乾。用之,取十餘叔(菽)置鬻(粥)中而 (飲)之,已腸辟。不已,復益 (飲)之。鬻(粥)足以入之腸。(关沮秦墓竹简《医方》)
取車前草實,以三指竄(撮),入酒若鬻(粥)中, (飲)之,下氣。(同上)[7]
②治赤散方:乾薑三分 术三分 烏头三分 付(附)子三分 白沙參三分 朱臾(茱萸)五分 桔梗三分 黄芩三分 細辛三分 人參三分 伏令(茯苓)三分 方(防)己三分 貸堵(代赭)七分 麻黄七分 桂三桂。凡十六物·六物當熬之令變色( 张家界古人堤医方)[8]
③毒菫,陰乾,取葉、實并冶,裹以韋臧(藏),用,取之。歲更取○毒菫。毒菫者【□□】菫葉異小,赤莖,葉從(縱)纗者,□葉,實味苦,前【日】至可六、七日琇(秀),產【□□□】澤旁。(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
①组所举关沮秦墓竹简医方,是目前所见秦汉医简所录内容最为普遍的一种体例形式,主要是以医方的组成、修合方法、服用事项为主①有关出土医方的体例,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如和中浚、李继明、赵怀舟,等《老官山汉墓〈六十病方〉与马王堆〈五十二病方〉比较研究》(《中医药文化》,2015 年第4 期,第22-34 页)。,一般不涉及本草药物本体的介绍。②组为张家界古人堤出土东汉木牍所载医方,其基本格式已与后世医方相近,载药物名及用量,并注熬煮要领。秦汉医方中对本草药物相关内容记录不多。③组所录为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中仅有的两段本草内容的细致记载,涉及本草的形态、滋味、花期、生境、名称等。与后世本草典籍对照,二者确有相似之处,这说明至迟在西汉早期对于本草的观察、思考和记载已经出现,但很明显这种记录还是一种对本草植物自然状况的描写,不是经常性的,具有某种随意性,未经归纳总结。
出土简帛文献所展现出的状貌,客观上说符合医学发展过程早期实用性为先的原则、理念。在医学仍处于经验积累阶段时,药物方剂的效验是第一位的,对于本草的深入理论化研究必然不会在此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这一时期的实践经验,对后世研究本草提供了一定的积累。胡平生先生所撰《从阜阳汉简〈万物〉看〈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10]对此有所探讨,可参看。
综上,截至目前未见有秦、西汉时期本草类典籍的著录及古书出土,可以初步判定西汉早期及前代,本草古书当未出现。
(二)“本草”一词的出现
本草典籍西汉早期并未出现,而“本草”一词在西汉已经问世,目前所知最早著录者,为《汉书》。共著录三则,具体如下。
①(汉成帝建始二年),又罢高祖所立梁、晋、秦、荆巫、九天、南山、莱中之属,及孝文渭阳、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黄帝、冥羊、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启母石、万里沙、八神、延年之属,及孝宣参山、蓬山、之罘、成山、莱山、四时、蚩尤、劳谷、五床、仙人、玉女、径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属,皆罢。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
唐颜师古注:“本草待诏,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11]1257-1258(《汉书·郊祀志下》)
②(汉平帝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11]359(《汉书·平帝纪》)
③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11]3706(《汉书·游侠传》)
三则材料记录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基本处于同一时代。汉成帝建始二年为公元前31 年,汉平帝元始五年为公元5 年。楼护生卒年不详,但其生活年代据《汉书》大致可知,当为汉成帝至王莽建新时期(公元前27—9)①《汉书·楼护传》言:“是时王氏方盛,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第3707 页)《汉书·成帝纪》载:(河平二年)“夏六月,封舅谭、商、立、根、逢时皆为列侯。”(第310 页)河平二年为公元前27 年,王莽建新朝则在公元9 年,故楼护活动之时代可知也。。可见,本草一词于西汉末期已出现。
材料①所示为成帝时期郊祀改革一具体举措,其实质是一场礼制复古运动,是儒生与方士两股势力的斗争,是前者对后者的打压。依据材料可以看出,当时所废除祠畤主要为高祖、文帝、武帝、宣帝时所立,且为方士所把持者,其中一些祠畤与皇帝个人运命、寿辰、福祉相关联[12-13]。文中载,遣返“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何谓“本草待诏”,颜师古注言,是凭借方药本草而“待诏”者,应劭云:“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诏。”[11]340现代学者对此多有探讨,认为具有某种才能而等待诏命之人,是待诏的一类②作为官职的“待诏”,涉及待诏的性质,研究者多有分歧,本文非专论,不做分析。,其所涉技能多种多样,如星象、龟卜、典禳、请雨、尚方等[14]371-373[15-16],显然本草待诏即包含其中,乃掌握方药本草者也,且其与方术有密切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本草的一方面属性。
材料②所论为汉平帝元始五年,征召天下通晓诸多技能与典籍者集于京师,其人数甚夥。其中本草与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并陈,从语义关系看,属并列关系。这里《史篇》一般认为是《史籀篇》的省称,其他很显然是类别名,指某一领域知识或技能。“本草”应与《史篇》同为典籍名,还是某一类别名,仅以此则尚难定论。
材料③出自《楼护传》,言及其家世背景与早年经历。楼护出身世医之家,这符合中国古代职业家族世袭的传统,他曾读“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这里“言”当释为“字”,显然此中本草与医经、方术属并列关系。医经当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之一类,方术也与“数术”有极大关联。医经、方术作为类名,是知识或技能的类别,本草当亦如此。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世医之家,医学相关技能与有关记录文书、典籍均为承继的重要内容,而此中本草所涉文字记载当数量不菲,其属文书记录,抑或古书典籍?如与材料②齐观,则二者所涉问题当一致。实际,《汉书·艺文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揭示这一问题的答案。
(三)《汉书·艺文志》未收“本草”辨
《汉书·艺文志》(后简称《汉志》)大致反映了西汉时期存世典籍的基本状貌,其文本基础源自刘向、刘歆父子图书整理的成果。据《汉书·成帝纪》载:“(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祕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11]310河平三年(公元前24 年),自此始至绥和元年(公元前8 年)刘向去世,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后向子歆“卒父业”,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 年)成《七略》[17]。《汉志》即在《七略》基础上“删其要”而成,故《汉志》反映的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所校中祕书之状貌。但实际涉猎图书范围不限于中祕,留存至今的诸书叙录可以明显看到,刘向校书实际囊括“中外”。中,即中祕之书;外,则为太史书、太常书,及长社尉臣参、臣向、大中大夫卜圭、臣富参、射声校尉立及民间书等[18]。有关《汉志》是否漏载当时存世典籍的问题,学界早有公论。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专设“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一节,有言:“《七略》及《汉志》,皆有不著录之书也。”并列举王应麟、章炳麟、顾实之考辨[2]190-193。刘向父子整理图书与上文“本草”一词见世,处同一时期,而查《汉志》方技略中未有“本草”类,那么是本草类古书尚未见于朝廷与民间,未问世,还是已问世却失载于《汉书》之中?
《汉志》未收载图书基于以下三种情况:一则“民间所有,祕府未收也”;二则“国家法则,专官典守,不入校雠也”;三则“前汉末年人著作,未入中祕者,《七略》不收,《汉书》亦遂不补也”[2]190-191。所谓“国家法则,专官典守”当指“礼仪律令”,显然作为医药类的《神农本草经》不属于第二种情况。以下就第一、第三两种情况略作考辨。
首先,民间藏本草书,未入祕府,可能性极小。
秦汉之际图书聚散兴废变迁甚剧,尤其秦之焚书影响颇大,但“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去[19],故医学几无波及。汉兴,惠帝四年(公元前191 年)除挟书律,至武帝时,“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祕室之府”[20]。又成帝时,令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此等规模之访书、求书运动,如真有本草之书,中祕岂能不藏,怎能无一丝线索,未见一处著录?此其一。
在西汉官职体系中太常与少府下均设“太医”,为属官。“太常之太医,主治百官之病,少府之太医,则主治宫廷之病。”[14]85-100,184-185居延汉简中存关于少府藏经验方并传布郡国之简:“永元四年闰月丙子朔乙酉,太医令遂、丞裦下少府中常方,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①参见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壹》。太医令“遂”字,从劳榦先生释文,见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9 年,第107 页)。足见医官衙署内存有一定数量的实用医学文献。又《汉志》提及,刘向校中祕书多人参与,其中“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侍医,颜师古注:“天子之医也。”[11]3074当为太医属员,则李柱国应知少府所藏医学文献,亦对当时医学书籍情况十分熟悉。若当时已有本草典籍,岂有不知之理,岂能不纳入整理之范围?此其二。
由于职业本身的特点以及对文化基础的要求,医学知识的生成与记录在秦汉及前代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知识的获取也只能依靠医学教育、实践和文本的交流得以实现。中国古代早期医学的传承有官方和民间两种途径。《周礼·天官·宰冢》下,述医师的职掌、分诊类别与考核评级,所言为官方医家执医制度[21]。《汉志》方技类小序中则言:“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11]1780这表明了医学在官方的地位。目前虽无早期官方医学教育可征考之文献,但按一般逻辑,其制度本身应包含教育的内容。民间医家的师徒传授记录相对易得,《史记》有扁鹊、仓公之事,虽扁鹊并非实有[22],但基于接受逻辑,师徒传承教育现实的真实性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前文载楼护世医之家事,其学医的民间家传也是确凿无疑的,而早期官方与民间医学的流动确实存在,既包括人员也包括相关文献与知识,传世文献与近年出土文献的研究足以证明。若当时民间藏有本草典籍,则应为医家所了解,尤其像与刘向、刘歆父子同时代的楼护,阅读过本草相关文献,亦在朝廷任过高官,不可能对当时国家图书整理工作中未收本草一事毫不理会。此其三。
综上,则“民间所有,祕府未收”的情况当不存在。
其次,西汉末年人所撰,未入中祕,此中所言无本草类书。
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于西汉后期,同时代所撰之书尚未入中祕,故未见于《七略》,未载于《汉志》。这类典籍既问世于后,当为西汉末及后世人所目见,为相关著作所著录、提及,如扬雄、王莽等之撰著。若本草类书有所出,当为世人所关注,其文本必有较广之传播,其体例、内容也当有相对较完整的呈现,异本较少,而据目前文献所显示,绝非如此。后世所见本草著作,不仅书名未定,作者未题,而且异本丛出,内容、体例千差万别。由此可知,所谓“前汉末年人著作,未入中祕者”,其中绝无本草典籍。
要之,《汉志》未载本草,非其存世而未收,而是当时本草类典籍尚未问世。虽然“本草”一名已经出现,且相关文献、记录已为楼护之徒所见,但其性质恐为长期医学实践所积累之日常文书、档案,绝非书籍,而真正意义上的本草典籍要到东汉方才问世。
三、汉末魏晋南北朝本草类图书的勃兴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
约于汉末三国,本草著作开始为世人所提及,由此至两晋南北朝,不仅所谓《本草》《神农本草》等书名频见于各类著作,而且有明确作者的本草著作和《本草》注本大量涌现。
(一)本草典籍的出现
学界一般认为现存最早记载《本草》,并加以引用、著录的文献有二。其一,东汉樊光《尔雅注》,存《毛诗正义》中,共二则。一则,《毛诗正义》曰:《释草》云“莞,苻蓠”;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蓠,楚谓之莞蒲’”。二则,《尔雅·释草》:“苕,陵苕。”《毛诗正义》:某氏曰“《本草》云:‘陵莳,一名陵苕’”[23]805,1107。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尔雅樊氏注》亦有考辨辑录[24]200。其二,《太平御览》卷八六五载:“《本草经》曰:‘卤盐,一名寒石,味苦。戎盐,主明目。大盐,一名胡盐。’”后小字注“《吕氏春秋》曰:《本草》云,戎盐,一名胡盐”[25]。
实际这三则材料的可靠性均待商榷。《毛诗正义》存“尔雅注”二则皆言“某氏曰”,马国翰据臧庸《拜经日记》“唐人义疏引某氏尔雅注,即樊光也”[24]196,认定樊光引《本草》注《尔雅》。但马国翰在《〈尔雅樊氏注〉序》中又言:“《释文》云:‘沈璇疑非光注。’然则称‘某氏’者,其缺疑之义乎?”[24]196足见“某氏”是否为樊光尚有争议。樊光,京兆人,后汉中散大夫[26]。如二则“尔雅注”为其所书,则东汉时《本草》一书即已出现。可备一说。
《太平御览》一则,注引《吕氏春秋》,后世一般以为乃高诱注文之佚文[27],若果如此,则高诱注《吕氏春秋》已参考《本草》,则《本草》典籍至迟于东汉末年已出现。今本《吕氏春秋》高诱注中未见此句,其是否为高诱注文无法确考,王利器先生认为,“盖‘《吴氏本草》’之误,‘吴氏’讹为‘吕氏’,转写者辄臆加‘春秋’二字耳。《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类》:‘梁有《吴普本草》六卷,亡。’今有清人辑本。”[28]查《太平御览》卷九七三“郁”、卷八二五“蚕”均载《吴氏本草》条目,然题为“吕氏本草”,恰可为王利器先生之说提供佐证,足见《太平御览》一则不足以说明东汉末已见《本草》。
比较确切的有关《本草》的记载始于三国。《毛诗正义》引三国孙炎《尔雅注》。《正义》曰:《释草》云“‘蘦,大苦。’孙炎曰:‘《本草》云: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叶似荷,青黄,其茎赤,有节,节有枝相当。或云蘦似地黄’”[23]195。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尔雅孙氏注》亦辑入。另外,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谷有蓷”条、“硕鼠”条亦引《本草》条目。
综上,宽泛而言,《本草》一书早则于东汉末年,至迟于三国时期就已出现。以此推断,《本草》书当初见于东汉。从传世文献记载来看,所谓《本草》一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为后世所称引,但称谓似不固定,相像或相关的名称有“本草”“神农本草”“本草经”“神农本草经”,参见表1。探其缘由,一方面恐源自古代书籍名称并不固定,称引也无一定之规,往往在约定俗成之下①所谓约定俗成,一方面指各种称谓具体所指书籍于当时人都明了,另一方面也指当时随意、无规则称引书籍名称的一种习惯。较为随意;另一方面,恐其所指书籍并不唯一,当存“同名异书”或“同书异本”的现象,后文还将提及。

表1 汉两晋南北朝与《神农本草经》相关著作题名及被引用情况
自东汉末年至北宋的700 余年,《神农本草经》的状貌如何,目前很难考辨。一则这一时期的本草书籍全部亡佚,部分存世残卷,无法窥其全豹;二则宋类书《太平御览》所收本草书籍佚文情况复杂,无法确证条文年代,佚文归属典籍及体例的真实情况等。千卷《太平御览》蔚为大观,大量引文直接源自前代类书《皇览》《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艺文类聚》等,其中存在以讹传讹的现象。编撰中引文又多有删减与改写,引用书名提法也不一[29]383-411,445-458;同时刊刻中亦存有讹误,虽其所收本草条文确有学术研究之价值,但对其考辨应持谨慎之态度,尽量避免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
学界一般认为,亡佚的《神农本草经》所存残文多保留在《太平御览》中。《太平御览》目前存世较早刊本有宋闽刻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蜀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及京都东福寺藏[29]111-122。详查该书,抛开明显有别的其他著作,与《神农本草经》相涉者有《本草》《神农本草》《本草经》《神农本草经》4 种①另有《神农经》一种,其内容与本草医药有关,但是否为《神农本草经》相关著作,不可知,存疑待考。,收药物条文共259 条②初步捜检259 条,其中《本草》20 条,《神农本草》9 条,《本草经》226 条,《神农本草经》3 条,《神农本草注》1 条。。依药物名称排比这些条文,其中重复著录者有13 种③其中卤盐、戎盐、大盐归为一种。,详见表2。重复著录条文文辞无完全相同者,因此存在条文来源不同的可能。但作为类书,《太平御览》著录的内容或为摘引,抑或“得意忘言”,即便出处、内容一致,用词存在差异也实属正常。不过,如果内容差异较大,甚至毫不关涉,则另当别论。

表2 《太平御览》收《本草》书异文条目与《新修本草》《大观本草》对照表
表2 将13 种药物重复条文与《新修本草》残卷、《大观本草》进行对照可看出以下一些差异。
(1)著录药名的调整。《太平御览》中称“枭桃”,《大观本草》称“桃枭”;《太平御览》中著录“陵苕”“紫威”,《大观本草》只取“紫葳”一名;《太平御览》中称“豕首”,《大观本草》称“蠡实”。
(2)著录药物的删除。《太平御览》载《本草经》中著录有“石决明”一味,至《大观本草》移出,归入《名医别录》。
(3)条文著录内容完全不同。《太平御览》中著录“陵苕”3 个条目,其中两条内容相近,言说其外部形态特征及洗头使发变黑的特性。而另一条则完全不同,主要强调其有助于治疗妇科疾病的性质。《大观本草》全取后者,未收前者。
(4)条文著录内容差异部分的脱落。在13 种药物中,“辛夷”“石流黄”“合欢”“海藻”“地榆”5 种药物不同程度存在这种情况。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条目著录的药物外部形态特征,至《新修本草》《大观本草》全部脱落。如:辛夷“其树似杜仲树,高一丈余,子似冬桃而小”;“石流黄,青白色”;合欢“其树似狗骨树”;海藻“茎似乱发”。
(5)疑似存在药物分合的情况。《太平御览》中著录“卤盐”“戎盐”“大盐”于一条目中,《大观本草》则分为3 种药,分条著录。可供对照的“麻蕡”“麻子”,情况相似,存在争议。不知《太平御览》著录体例上的具体差异,存疑待考。
以上内容虽是《神农本草经》一书极小部分的比照,但从中足以窥见《本草》自东汉出现至收录于唐《新修本草》、宋《大观本草》(或称《证类本草》系列著作),文本内容发生的巨大变化。其一,《神农本草经》的书名经历了由多个名称到定为一名的发展过程,其间“经”的出现与确立在本草书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其二,同一药味的若干条目,虽源自同名书籍,但内容却大相径庭,说明本草条文来源多样,即《本草经》存在同名异书或同书异本现象。同时,以“本草”为类名而并存众多典籍的现象是否存在也值得关注、思考;其三,《神农本草经》所纳药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间变化的烈度目前不甚明了,但从后世特别是陶弘景《本草集注序录》所言其见古本之状貌,足见当时的情状;其四,今所见宋本草书著录的《神农本草经》条文,是经过了一个内容筛选、删除过程而确定的,其中不仅涉及以往所言朱墨字、黑白字龃龉的问题,而且牵扯到正文内容的删减,且牵连本草植物形态书写等内容。其五,有关药物名称和药物独立、合并问题,也是《神农本草经》内容演变的重要方面。总之,从《太平御览》收《神农本草经》佚文来看,《神农本草经》的文本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本草知识的不断拓展、文字记录的日益丰富、各种典籍的不断出现,《神农本草经》才得以进一步嬗变。
(二)两晋南北朝时代本草著作的大量出现
本草著作的繁荣始自三国,至两晋南北朝无论在数量和类型方面都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这一状貌借助《隋书·经籍志》(后简称《隋志》)可得到充分认识。《隋志》收本草著作共计56 种,参见表3。

表3 《隋书·经籍志》收本草书分类
《隋志》是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录》而作。《正御书目录》载炀帝时西京之藏书,云:“唐初平……独得其目录,其后修《五代史》,因就加增损,以为《隋书·经籍志》”[2]120-121。《隋志》著录的本草典籍已经全部亡佚,但据书名还是可以看到当时本草蓬勃发展的状貌,其情状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特征。
第一,本草编纂者及书籍数量剧增。《隋志》载本草书名中常夹杂人名,一般认为乃是典籍作者。其性质可分为两类:其一,类似“神农本草”,基本为附会的上古神医或神医弟子,如“桐君药录”,《中经簿》载“子仪本草”①唐贾公彦疏《周礼》,引《中经簿》云:“《子义本草经》,一卷。”又曰:“仪与义,一人也。”见[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赵伯雄整理《周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133 页)。亦同此;其二,占大多数,多为现实中人,部分在史籍中有生平记载。作者数量的激增,反映出本草知识从数量的积累已经开始向质的方向转变,由知识的归纳、整理进入到学术化发展阶段,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与前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本草典籍著作的大量涌现。这是医学实践经验与本草知识积累以及医学自身发展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本草药物的系统性研究著作增多。随着本草典籍著作的增多,本草研究开始呈现出全方位、系统性特点,相关成果不仅包含实用性的经验积累,而且还明显带有理论化总结与探讨的意味和特点。如基于采药经验的方法总结著作、种植药物的技能典籍、专门种植特种药物的技术书籍、药材使用分类之作、著录药性及使用禁忌类书、用药方剂书、药物图录等。各种本草书籍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当时药物学发展的水平,同时也为后世本草知识谱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在医药经验不断丰富,理论积淀与总结不断强化的背景下,《神农本草经》的整理、注释与定本的确立也在同步进行。
第三,《神农本草经》在传播中异本频出,整理、研究趋于丰富。《隋志》著录《神农本草经》异本多出,不仅有三卷、八卷二种存世,还记有南朝梁时五卷本,惜已佚。这种情形实际一直存在,齐梁时陶弘景整理《神农本草经》,撰写的序录中就描述了他所见异本状貌。
此书应与《素问》同类,但后人多更修饰之耳……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生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树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多少,医家不能备见,则识致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卅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②[南朝梁]陶弘景《本草集注序录》(抄本残卷。甘肃:敦煌,718[唐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现藏日本龙谷大学,编号:龙530)。
陶氏称引“诸经”收药物数量多寡不一,这与《隋志》记载可相呼应。同时他也叙述并解释了《神农本草经》发展、传播的过程与异本重出的原因。抛开传抄过程中的讹误,该书异本并存主要源于“后人多更修饰”。其一,探讨内容的扩充,如药物产地为东汉时人所补;其二,研究领域的深化,如对药物植物形态、配伍作用的研究和专书的出现;其三,新发现药物数量的不断扩增,如吴普、李当之的损益等。内容的补充和研究深度、广度的拓展,实际也并非这一时期特有现象,本草典籍出现早期就有反映,上文所言《本草经》出现同名异书或同书异本即是。在本草典籍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伴随着研究的拓展与文本的整饬,这就势必导致文本的多样化。这一过程,一方面是本草知识与经验的不断积累,一方面是医家撰著的纷纷出炉,另一方面则是《神农本草经》在此基础上的不断发展与文本更新,三个方面相互促进,并行不悖。传世文献对吴普、李当之编撰本草著作的叙述也可印证这样的趋势,如:
普,广陵人也,华佗弟子,撰《本草》一卷……(李当之),华佗弟子,修《神农旧经》,而世少行用。(《梁陶隐居序》)[30]10a
昔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以救万民之疾苦,后世师祖由是,本草之学兴焉。汉魏以来,名医相继,传其书者,则有吴普、李当之《药录》,陶隐居、苏恭等注解。(《本草图经序》)[30]4a
魏广陵人吴普撰。普,华佗弟子,修《神农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种,《唐经籍志》尚存六卷。(《补注所引书传》之“吴氏本草”)[31]
以上三则材料均显示,吴普、李当之撰著本草书籍是在《神农本草》的基础上进一步修饬、补充而成。《太平御览》载《吴氏本草》佚文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吴氏本草》是在对前代医籍的总结和拓展基础上形成的。由此足见,当时本草著作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神农本草经》文本内容发展嬗变的背景与状貌。
本草的新发现、经验的整理和理论的发展促成了《神农本草经》的不断嬗变与异本的重出,该书越来越为世人所关注,成为“经典”。相关的整理和研究性成果也不断出炉,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成果类型大体包括集注体、音义体、实用性文本三种。集注体,有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雷公集注《神农本草》和无名氏《本草集录》。结合上文所引陶弘景作《序录》可知,陶氏撰“集注”多是对所见前代及当时《本草经》文献的综合整理和注释,完成类似工作者绝非陶氏一人,雷公集注亦为一种,其作者当为假托。而《本草集录》推测为《本草经》或同类内容著作的综合整理。音义体,是汉末魏晋南北朝兴起的一种随文注释之体,它不仅注解语词音义,而且阐释典章名物史事,疏通文义,还兼顾版本异同,是融合了音韵训诂与文献异本研究的一种新型注释体例①参见于亭《论“音义体”及其流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 年第3 期);万献初《〈汉〉音义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21 年,第1-3 页)。音义体后逐渐发展成摘字为释,别本单行的体制,陆德明《经典释文》成为代表性著作。。目前所知相关著作有姚最《本草音义》、甄立言《本草音义》。注释类典籍的出现,表明时人对于本草著作的重视和较为强烈地深入研究的主观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巩固了《本草经》经典地位与“经”的命名的实现。这一认识,下文还将详述。实用性文本,主要是指便于学习和利用《本草经》而撰写的著作,从遗留下的著作书名猜测,主要包括内容摘抄、分类使用等内容。有些书名较难理解,如《神农本草属物》《本草经轻行》等,似乎应属实用性文本,存疑待考。
在众多整理研究成果中,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是目前能见到的唯一孑遗残本。该书特点、价值和作者陶弘景的学术贡献,前人已有论述,本无须赘言。但相关内容与《神农本草经》成书有紧密关联,因此以下就应关注的要点略陈一二。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意义与价值应该辩证看待。伴随本草著作的大量涌现,《神农本草经》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富而多样起来,陶氏撰《本草经集注》也只是当时众多整理、集成成果之一。一方面,陶氏“苞综诸经”,发凡起例,集大成之意义不可小觑;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一时期并非仅他一人完成《本草经》集注整理,遗憾的是他人成就因文献不足征无法实考。即便如此,就算陶氏的整理确实堪称一流,拔得头筹,也要认识到后世对于《本草经集注》的关注、加持,乃至持续引用所带来的效应,对于《本草经集注》的意义,以及《神农本草经》“成书”的意义,当不容小觑。具体而言,在后世本草著作的演进过程中,《新修本草》以《本草经集注》为基础,“摭陶氏之乖违,辨俗用之纰紊”[31]29而成;后蜀编撰《蜀本草》,“以《唐本》《图经》参比为书”[31]25;至宋,《开宝本草》改正刊误《唐本草》而成,《嘉祐本草》则增补厘定《开宝本草》而成,至《证类本草》承继《嘉祐本草》的体例框架,引用各类文献撰写而成。在这样一种层层累积,不断发展过程中,不仅陶弘景之前及同时代其他本草著作由于不再被重视、提及,纷纷佚失,就连陶氏《本草经集注》也最终散佚。
虽然历代本草著作不断出现,内容、体例也有所变更,但其内核——《神农本草经》却居于尊位,始终未变。而历代所认为的《神农本草经》实质是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为蓝本,对于陶氏整理集注以前《本草经》的真实状貌,已无人问津。更准确地说,与其称历代药书以所谓《神农本草经》为基础累积而成,不如说是以陶氏《本草经集注》为基础逐步发展演进而成。真正后人意识中、目光里所认识的《神农本草经》,实际是经陶氏之手整理的《神农本草经》,换句话说,《神农本草经》的真正成书、定本,是陶弘景最终完成的①在后世本草著作发展演进过程中,由于传抄和历代本草作者个人学术观点的差异,《神农本草经》的文本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变动,但其内容的规模和体例并未触动陶弘景整理本的整体样貌和性质,亦未改变陶氏在《神农本草经》成书过程中的作用。因此,这里所作的论述是从宏观、整体而言,微观、个别的变动可以忽略。。
(三)作为“经”的《神农本草经》
在《神农本草经》成书的整个过程中,其以“经”的身份出现、被命名,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不仅标志着中药在传统医学中被给予价值肯定,而且为后世典籍成书与中药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今人探求技术类古书的经典化过程提供了样本。
古书经典化是近年备受学界关注的话题,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儒家经典,而相关出土文献的大规模发现为研究提供了更为鲜活的文献依据。随着研究的深入,探讨的兴致延伸至其他类典籍,也包括医书。这不仅大大丰富了研究内容,更拓展了结论覆盖的范围,打破了经典认知的局限性。正如来国龙先生所说:“‘经’不仅指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应该包括其他类的技术、知识的传统。因此,有必要拓宽传统的‘经’的定义,研究中国早期文本的固定与经典形成的整个过程。”[32]523
古代医学经典,《汉志》就已著录,方技略“医经”类中7 部医书,被认为是医学理论典籍。其经典化路径不可确知,但从后世研究和中国古代经典形成范式这一维度分析,其多半源自两方面因素:一则“圣人经典”的模式理念,二则内容的重大价值。本草在东汉以后出现繁荣,本质上是医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经典的出现是现实需要与学术成长的必然,而神农与本草的传说所营造出的相互关系,使“圣人经典”模式得以形成,进而催生出《神农本草经》的命名。古书一旦称为“经”,其意义与普通典籍便有了极大的区别,尤其在文本定型、接受、传播、研究方面。前文已述,《神农本草经》的成书过程不仅经过了异本共存、集成整合,而且后世又不断被接受,传播,逐步加以强化、固化。而“经”的确立与认同过程也历时并行,这无疑对文本的发展、定型及经典化道路本身产生重要影响。
从目前所知《神农本草经》称为“经”的记载情况看,经典化过程初期,称“经”似乎也曾出现反复。笔者所知传世文献著录《神农本草经》最早是西晋刘逵注《蜀都赋》,但其后的文献流传至今的版本文字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多数称引都不署“经”字(参看表1),只有《佛说柰女耆域因缘经》西晋译文中有《本草经》之称②原文为:“便取本草药方针脉诸经,具难问师……《本草经》说有药王树,从外照内见人腹脏。”参《佛说·女祇域因缘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四卷 经集部一[No.553],第897-898 页)很显然这里所说《本草经》并非中国古本草书,只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权宜之计,以《本草经》代指佛教故事中之药书。但从中亦可看出当时译者时代《本草经》称呼的普及程度和其“经”的地位。据方一新考辨,《大正藏》所收该经译文最早不会早于西晋,或为竺法护所译。参见方一新《〈佛说·女祇域因缘经〉翻译年代考辨》(《汉语史学报》第七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抛开传世文献流传过程中的转写变化,这似乎可以看出早期经典化道路上的不稳定性。经典化的完成,应在陶弘景时代之前,敦煌残卷“龙530”《本草集注序录》言:“故撰而论之,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③[南朝梁]陶弘景《本草集注序录》(抄本残卷。甘肃:敦煌,718[唐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释文参[日]上山大峻编《敦煌写本本草集注序录·比丘含注戒本》(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编《龙谷大学善本丛书》:16.京都:法藏馆,1997 年,第241 页)。足见《神农本草经》称呼之确定。不过有意思的是,卷末署题则为“本草集注第一序录 华阳陶隐居撰”,反而不称“经”,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书名中“经”字的书写也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也间接表现出方技类典籍的经典化程度较之六艺、诸子要弱。不过“经”的称谓最终被确定、习用后,其地位也就被确立了。
作为技术类古书,其经典化道路仍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注释、研究著作的出现对经典形成的意义;第二,“经”的泛化;第三,本草技术类书籍与以儒家为代表的经部、子部思想类书籍经典化道路的差异。
经典化的过程与注释、研究经典的过程往往相互交织,经典化的最初阶段文本的阅读与使用势必带动接受活动的繁盛与注释、研究著作的大量出现,而研究著作的不断出现反向又激发了世人对经典的关注与讨论,进一步抬高、巩固了经典的地位。从东汉《本草》典籍的出现到陶氏“集注”的完成,《神农本草经》实际走过的是一个成书兼及经典化的过程,而注释、研究著作的不断出现则是对其“经”的地位确立的再确认,再重申,再巩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前文所言经典化早期的不稳定性,形成呼应。
传世文献除著录《神农本草经》外,还能够看到很多被称为“经”的其他本草书,如《王季璞本草经》《李譡之本草经》《赵赞本草经》《蔡英本草经》《子仪本草经》《吴氏本草经》《神农采药经》。这种现象本身或许可被看作是流派传承中尊奉师承家法的体现,但同一类书出现如此多的经典,客观上也展现出了经典本草类书认定上的随意性。与后世本草类书很少再被确认为“经”的实际相较,早期情形可视作“经”的泛化的一种表现。这种情形是在早期医书中广泛存在,还是仅存于本草类书中的现象,恐怕还需进一步深入考察。
作为技术类经典,《神农本草经》与传统经部、子部思想类经典在经典化道路上也呈现出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思想性经典著作一经确定,定本往往不得更改,这主要源自思想的特质。一般而言,伟大的思想其内涵及阐述方式具有抽象性和高度的适用性,虽经时代变迁但仍具有指导意义。而技术类经典则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世界认知的拓展,科学技术会出现革新,知识领域不断扩充,技术类文本也必然随之而变动,企图如思想性经典一样变动不居,是绝对不可能的。从这一点出发,《神农本草经》的经典化过程也必然会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矛盾,即经典文本的固化与新知发现、技术革新的内在要求之间的矛盾。
南朝宋陈延之《小品方》残本中记载:“研寻治病,终归以药为方,本草药族,极有三百六十五种,其《本草》所不载者,而野间相传所用者,复可数十物。”[33]可见,当时《本草》记载之药确定为365种,但实际已有超出这一范围的数十种药物在民间广泛使用。其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更记载所见有395、431、319 种者,可以说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经典在定本与新变之间出现两难。即便如此,陶氏仍在整理《神农本草经》时以365 种定其所收药物数量,足见其思想还是受到“经”的地位及其固有药物数量的约束与限制。但陶氏也意识到大量新药的出现和其必须被增补入册的现实,因此在《本草经》外另造“名医副品”,仍遵循365 之数加以著录。这一过程所呈现出的“尴尬”局面,实际已经说明了本草知识的常态、现实性扩展、变动对本草经典地位及其固化状态的动摇。陶氏在接受、确认经典的同时,又不得不有所变通,最终只能采取折衷方式,即葆有作为核心理念和经典意味的《神农本草经》的形态,而扬弃其定本书之形态的外在边界。
综合上文,《神农本草经》的成书过程可通过图1 加以呈现。

图1 《神农本草经》生成示意图
大致而言,从本草药物的发现、知识的形成与积累、文字记载的出现到文书的诞生,这一过程可视为《神农本草经》成书的酝酿期。之后,从文书发展到《本草》古书问世,再到本草古书经典的确认,当为《神农本草经》成书的关键期。而随后经典的接受与强调,不断地复写和最终的固化,当为《神农本草经》成书的巩固期。三个阶段看似线性发展,实际其间的嬗变充分展现出古书形成的层累性特点。无论是早期文书积累聚集至数万言、数十万言,还是关键成熟期的同书异本或同名异书,乃至巩固期集注本、集成本的出现,以及不断接受过程中以《神农本草经》为核心的新本草的出现,实际内部都发生着复杂的聚合、选择、再写定的过程。从整个中国古代本草典籍成书的历史看,《神农本草经》的成书过程实际成为了一种范式,是中国古代本草书籍发展的一个缩影,主流综合本草的形成恰恰也展现出层累的特征,如图2 所示。

图2 主要本草系统表
《神农本草经》成书的层累性质,实际呈现出的是上古时代古书的一种共性,已有专家给予论述。裘锡圭先生就曾指出:“从简帛古籍可以看出,数术、方技方面的书,继承性特别强。流传下来的这类著作,往往是以较早的同类著作作为基础,逐渐修改增益而成定本的。”[34]在这样一个层累、继承的过程中,尤其是早期文本尚未定型,经典尚未确立的时期,文本往往分合不定、异本共存,很多今天所谓书名,恐怕当为“类名”,古书呈现出所谓“以类相存”的特点。李零先生也曾就此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好像气体,种类和篇卷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1]214从成书的历时角度看,很难说在成书初期同类文献中一定存在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文献,这样的文本恐怕只能是在文本逐渐发展的后期才形成。早期同类文献呈现出的应是一种无序性,在发展的某一阶段还可能呈现出文献发展层次的多元性、不均衡性,或对于最终定本的确立共同起到重要作用的多中心状态。在这样的进程下,“古书文本的演变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多条线索相互交错形成的复杂‘网络’。一种古书在同一时代存在多个版本系统乃是常态,其中只有少数版本得以流传至今或见于文献记载。更多的版本虽然早已湮没无闻,但其文本特征却可能通过‘隐伏’的形式传递下来,在时隔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浮出水面’,出现在较晚的版本中”[35]。
另外,同类文本在转写传抄过程中,合并分离极为常见,并没有固定的文本,且古人又多喜背诵、口述,转引、抄写变动字句、删减添加亦为常态,这就造成了文本的流动性[3]28-33[32]。从最初原始文本出现,到不断的增补、擅改和整理,期间即使出现暂时的写定文本,也会再次变动。所以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文本的面貌会相当复杂,仅从单一一个文本片段出发,其流传过程中丰富的变化,既可能是传播、整理过程中无意的增补、擅改,亦可能是主观上有意的改编。从知识体系扩容或者同类新增文本角度看,新文本的大量涌现还会影响旧有文本,其体例、内容会随着经验的积累呈现出单一或全方位的新变。这样的模式不断演进,势必造成文本或整个知识体系的多样、庞杂。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能较之以上所言更为繁复。
总之,《神农本草经》的成书过程极为复杂,目前由于早期文献尚不充分,很多问题还难于充分考辨,完全解决。但通过这一研究,还是能够充分体会到古代技术类典籍成书的复杂性,从而避免将发展的历时延展进程强行压缩,取消其时间空间上动态的演进嬗变过程,错误地将古书成书过程作简单化、静止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