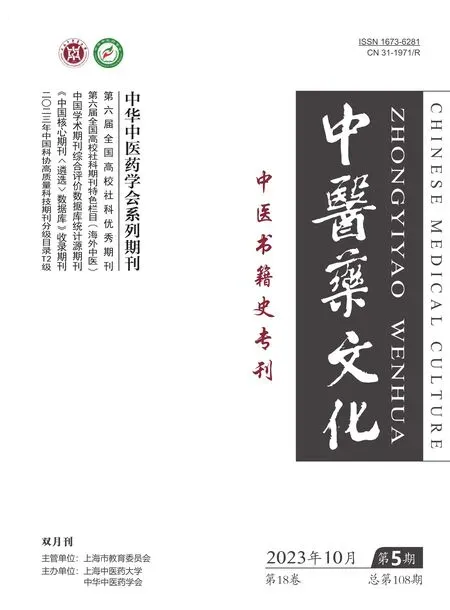宋代验方类医书的编印与流传
刘 辉
(大足石刻研究院,重庆 402360)
关于“验方”,现在多将其与民间医学联系在一起,如谢普《验方新编》即将其定义为“是以民间流传,经过临床反复验证,对某种疾病具有确切疗效,而药物组成又较为简单的药方”[1];舒鸿飞,段龙光则认为经方、时方和专方等临床验证有效者,均可称为验方,但同样强调其民间的性质[2]。一般来说,归入“验方”者多是个人行医治病经验的总结,组方简单、用药廉价、易得易用,针对特定疾病有良好的疗效。自南北朝开始即有医家将此类医方进行搜集编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验方类医书。
有关宋代医家方书的研究已有较多的成果,韩毅将宋代的方书分为官修方书和非官方的医家方书进行探讨,对医学方书的形成、知识来源与创新、传播应用等方面均进行了细致探讨,认为“宋代医学方书在中医基础理论、临床诊断方法、疾病症候和临床处方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和成就”[3]2;章健同样将宋代方书分为官刊方书和个人方书,认为两类方书各有所长,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宋代方书辉煌时期的风貌[4];薛芳芳等探讨了宋代文士编撰方书之风盛行的原因,并指出这些方书从实用性出发,删繁就简、重视效验、强调易用等特点[5]。对于验方类医书的研究则多以个案为主,如张雪丹、傅建忠等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考察了南宋官员陈晔及其所著《家藏经验方》刊印和流传等情况[6-7];又张雪丹等对宋刊本《备急总效方》的编印与流传进行了细致考述,对其医学和文献方面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8];钱超尘考证了《洪氏集验方》刊印版本与流传情况[9]等。以上均是对于某一验方医书的个案研究,关于验方类医书在特定时代的整体编印及流传阅读等情况还需做进一步探讨。另刘怀荣、石飞飞通过对唐代李绛《兵部手方集》中两则验方使用与传播的考察,揭示了唐代医疗发展史及与此相关的人物关系[10];刘希洋通过对清末以《验方新编》等方书传播情况的考察,分析了社会精英在医学知识传播上的努力和影响,揭示了民间验方知识的底蕴与生命力以及由此体现出的近代江南医疗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11]。以上研究虽并非都以宋代验方类医书为研究对象,但对笔者的研究也启发颇多。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不揣浅陋,对宋代验方类医书的编印及阅读流传情况进行初步考察,以求教于方家。不当之处,还请不吝赐教。
一、中国传统医书中的验方书
中国方药学自古以来多有以“验方”为名的医方书,范行准将其归入“传信方”一类,认为“医方传信之书,固创自不以医为业的知识分子,其后代有续作。以至渐又转至医家之手,而变其体例”[12]。范家伟也并未对二者进行严格区分,如其将刘禹锡《传信方》的编撰置于唐代医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观察,认为唐人编集方书“目的是将试而有验的药方加以整理及流传,绝非将医方隐秘不传”[13]。实际上,相较于更加注重医方来源之确切的“传信方”,“验方”的特点在于其更注重药方经过实践过程检验的有效性。沈括对于传世的著名医方持怀疑态度,“世之为方者,称其治效,尝喜过实。《千金》《肘后》之类,犹多溢言,使人不敢复信”。故而其在编撰《沈存中良方》时完全以其亲验结果为准,“予所谓良方者,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闻不预也”[14]。初虞世《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自序提道:“古人医经行于世者多矣。所以别著者,古方分剂与今铢两不侔,用者颇难。”[15]2187可见宋人在验方的编选中,即使医方有准确来源,但在对其疗效进行验证之前并非一概相信。即宋人所谓“验方”,当是经亲自检验确信其疗效的医方。
以“有效性”为基本原则,在南北朝时即有部分通医文人和医学人士将自己确认效验的医方进行编集,如历经南梁和周、隋三朝的姚僧垣,“尝婴疾历年,乃留心医药”“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前后效验,不可胜记”“乃搜采奇异,参校征效者,为《集验方》十二卷”[16];唐初名医甄权之弟甄立言,善治奇疾,可断生死,著有《古今录验方》五十卷[17]5090;陆贽被贬忠州时,“家居瘴乡,人多疠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17]3818,但此时相关著作数量还比较少,《旧唐书·经籍志》医术类中收录以“验方”为名的医书仅5 部,其中3 部为南北朝时期著作,《新唐书·艺文志》补为11 部,除3 部南北朝时期著作,2 部时代不明,也仅有6 部。
至宋代,文人士大夫编撰方书之风气盛行[5],验方类医书的编印数量大幅增加,其医方来源多为医家或士人多年经验所得,或博采众方,验证疗效择其精要而成。《洪氏集验方》后跋提到“上集验方五卷,皆予平生用之有着验,或虽未及用,而传闻之审者,刻之姑孰,与众共之”[18]。即其中一部分是其亲验有效,另一部分虽未亲自验证,但也是审慎确认治疗效果的医方。南宋朱景行说:“若夫医师之方集之者众,而未有灼然保其验者。吾宗君辅萃闻见,纪其效而录之,视疾痛疴痒之于身矣。”[19]正是强调对验方有效性的看重。而宋代验方类医书的作者更加注重的也是这一层面,如叶大廉在编撰《叶氏录验方》时选方极为审慎,其自序称“虽所积卷帙甚富,前此未见人用,或用而未见其效,与夫大廉疑之而未敢轻用者,皆不敢传之于人”[20]133;又如南宋医家李迅,自其父祖辈即开始搜集医方,“凡士大夫家传名方,每喜于更相传授,至于医生、术士,或有所长,赂以重贿,幸而得之,则必试而用之。心知其经验,有因病来叩,随证赠方,一无吝色”。即使确知医方来源,仍需逐方验证再次确认,可见其父祖务求其验的态度。李迅本人对医方治疗效果的追求更是犹有过之,据其称在撰《集验背疽方》之前“始则试之田夫野人,中则用之富家巨室,久而献之贵官、达官,有如印券契钥之验。屡欲编集,以贻后人,愧非专门而止”[21]3-4。最终成书时,又再次对已验证的医方仔细选择,“其间又有用药偏重,或太冷,或太热,或药性有毒者,今皆不录,独择尝用而经验者录之,庶几不至有误活人治病之意”[21]8。
除各种直接以验方为名的医方书外,还有很多虽不以“验方”为名,但其中所辑录的却多是各类“验方”的医书。中国传统医学本就重视医疗经验的积累,葛洪《肘后备急方》、孙思邈《千金方》等著名医籍多是医家自身行医治病经验的总结自不待言,刘禹锡《传信方》中所收录的药方也有不少曾亲加验证,所谓“于篋中得已试者五十余方”[22]即是如此。宋代此类方书更多,如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王氏博济方》一书始于王衮为治疗父母疾病搜集医方7 000 余首,“皆传之于家牒,得之于亲旧,故非耳剽口授,率经效用,因于其中择其精要者,理疗可凭,方书必验,得五百余首”[23]1;刘信甫编著的《活人事证方》前后集,书中医方皆是其行医过程中记录所得,“凡用药救人取效者,及秘传妙方,随手抄录……每方各有事件引证,皆可取信于人,并系已试经效之方,为诸方之祖”[24]3;许叔微撰《普济本事方》乃是“举生平救治诸方投而辄验者,集成一书”[25]。官方对验方的搜集编印也极为重视,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录事。每州(写)《本草》及《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26]。宋太宗重视医术,“暇日多留意医术,藏名方千余首,皆尝有验者。至是,诏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又万余首”[27]13507,后总编为《太平圣惠方》一书颁行天下。对后世医学发展影响甚大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其前身为元丰年间编著的三卷本《太医局方》,该书是神宗“诏天下高手医,各以得效秘方进,下太医局验试,依方制药鬻之”[28]729。可见其中医方虽来自民间,但都由官方亲验其效,也可算是验方一类。
二、宋代验方类医书的刊刻发行
(一)宋代验方类医方书统计
宋代皇室对医学极为留意,受此影响,宋代儒学士大夫习医知医风气大盛,不少士大夫都参与到了本草文献的整理工作当中,加之造纸术、印刷术等技术在医书刊刻中的应用,促使宋代本草的研究和编撰工作空前繁荣[29]。谢利恒论《宋明间医方》时提到:
中国经籍之传世者,至宋而始多,盖锓板之术盛于是时使然。然医家之书,经宋人蒐辑传世者,医经类甚少,同一经方也,本草类亦甚少,而方书独多。盖医理深邃,非尽人所能知,方药则事足便民,好蒐辑之者较众,而流传亦易,但格物之学不明,徒知蒐辑成方以治病,而不复能研究药性,所谓知有术而未足语于学也。[30]33
与普通医家有别,士大夫并不以医为业,或即使以医为业仍保留其儒家风气,称为“儒医”。其学医除为父母及自身疗疾外,更多的是为了从医学层面实现其济世救人的大道,虽难以进行更深层次的药性研究,但对于促进当时医学知识的传播进而改善社会医疗条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宋代编集刊印的验方类医书数量因年代久远及不少医学文本失传的缘故,现已难以进行精确地统计,但根据宋代的一些目录学著作,尤其是近人薛清录主编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冈西为人的《宋以前医籍考》、刘时觉编著的《中国医籍补考》和严世芸主编的《中国医籍通考》等书目,仍能对宋代刊刻出版的验方医书进行大致统计。由此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宋代验方医书的刊刻出版情况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了解,参见表1。同时,考察各医籍目录对验方类医书的收录情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当时社会对于验方类医书的重视和接受情况。

表1 宋代主要医籍目录收录验方统计
表1 中5 种宋代医籍目录共收录验方书籍80 部,除去重复书目共计43 部。另有一些如李日普《续附经验奇方》、叶大廉《叶氏录验方》、朱佐《类编朱氏集验医方》、孙矩卿《竹阁经验备急方》等虽同样是宋代坊印或私刻的验方类医书,却未被收入以上医籍目录当中。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笔者限于学力,难以进行更为完整的统计,只能留待以后再进一步研究。
另以上方书中,统计朝代可考者,北宋10 部,其中官方组织编印者4 部,私家著述6 部;南宋12部,均为私家著述。可见南宋验方类医书的刊印略多,且多是个人编集。韩毅指出,南宋医家编撰的方书种类繁多且出现了大量专科方书,中央和地方官吏撰写的医书也大量增加[3]518-528;靳国龙的研究显示南宋中央政府仅是重新校订刊印了几部北宋医书,少有创造,反而地方官员和民间多有医书刊印[31]。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或与南宋时的内外局势有关:一方面金兵攻破汴梁后北宋一代官方藏书多落入金人之手,南宋时可供编撰、校正之材料匮乏;另一方面南宋国势衰弱,勉强与金国对峙保住半壁江山已是不易,实无力再如北宋一样大规模编修医书[32]。
(二)宋代验方类医书编印缘由
宋代验方的编集者具有多样性,既有为官一方的地方官员,又有普通儒家士人,也有些是当时医学名家。与之相对应,宋代验方医书编印的缘由也有所不同,依笔者之考察,大致不外乎以下三种。
一是为方便他人治病而编印验方。当时医疗市场上医生水平参差不齐,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搜集效验医方进行刊印,可方便大众治病。南宋江畴在为张杲《医说》所作跋文中提到:“近世士夫所以每叹所在无良医,人之疾病,不得尽其理而死者亦众。然岂真无良医耶,不仁之心坏之也。”[33]士大夫已经属于当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尚且感叹难以寻找医德兼备的良医,普通百姓可想而知。刘昉“每患小儿疾苦,不惟世无良医,且无全书。孩抱中物,不幸而殒于庸人之手者,其可胜计!因取古圣贤方论,与夫近世闻人家传,下至医工、技士之禁方,闾巷小夫已试之秘诀,无不曲意寻访,兼收并录”[34];叶麟之为刘信甫《活人事证方》所作序中提到:“予尝怪世之庸医,未必得《周官》十全之术,设或遇人危笃之疾,反欲自珍其药,以为要利之媒,贪心未厌。”[24]5文天祥曾为儒医王朝弼所著《金匮歌》作序,其中提到“世无和、扁,寄命于尝试之医,斯人无辜,同于岩墙桎梏之归者,何可胜数”[35]。医疗资源的缺乏和质量低下短期内难以解决,编集刊印验而有效的医方就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如李朝正编印《备急总效方》还考虑到乡间僻远之处“医药难致,稔疾而横夭者,何可胜数?”对于百姓而言,普通医书又不便于检阅和配制,故多集已验单方,“命工刊之,以广其传。庶使遐陬僻邑,虽药物不备,随所有以用之,咸得蠲其疾苦,而无横夭之祸焉”[36]。又如文彦博曾患眩晕之症,久治不解,最终被国医龚世昌治好。“余嘉龚医之方,专用本草之意,因采仲景并《外台》、《千金》及诸家经验方,共若干,辄加注传于门内,以备处疗。”[37]文彦博编著此书主要流传于家族内,供族中子弟阅读治病使用。
二是为实现以医济世的理想而编集验方。自宋代以来,儒医阶层崛起,出于儒家“入世”的动机,宋代儒者对医学重要性的体认融合了儒家仁爱的精神,刊刻医书,也是为了使众人能够享有医学之利[38]。绍圣五年(1098),赵捐之为初虞世《古今录验养生必用方》作后序,其中提到:“仁者之事,利己则思利人,惠此则必惠彼。推狭以至广,由近以之远,欲斯人安于寿命,不至夭枉而后已。”[15]2189可谓儒者以医济世的内心写照。如南宋名医刘信甫本是儒学出身,后入医道,编著《活人事证方》是考虑到“囊有妙剂,仅可以济一隅,曷若鸠千金之秘方,足以惠天下之为博也”。故而“不私于己,以广其传,庶使此方以活天下也”[24]5。南宋方导编集《方氏编类家藏集要方》,自称是“以数十年家藏明方之得效者,与一二良医是正。分门编类以备检阅,或可疗人之疾,亦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焉”[39]。南宋魏岘编集《魏氏家藏方》主要来自于父祖收藏和自己亲试有效之方,“不敢自奇,用锓诸梓,以广其传。虽复所藏非富,未足以尽疗世人之疾。或者采而用之,有所全活,则庶几区区之心,不得于彼,而得于此耳”[40]。南宋医家严用和先后编印《济生方》和《济生后方》,乃是“采古人可用之方,裒所学已试之效,疏其论治,犁为条类”而成,书成后即锓木以广其传,以期“不惟可以备卫生家缓急之需,亦可示平日师传济生之实意云”[41]。温大明先后编印《海上仙方》前后两集,据其自序称晚年自恨无以惠人,“辄取五世家传名方,并生平行医应效圆散……的有起死还生之效,活人以代耕。设或藏私,则所济者狭矣。谨录施以传,非惟世人有疾者一展卷而识之,得此者亦可以自助”[42]。
三是为改变当时医家风气而编集验方。对于一些以医为业者,专门有效的技术是其赖以谋生的手段,自然会秘珍奇技,不肯轻易外传。这一风气虽不利于医学知识的传播与保存,但在尚未有专利保护制度的古代,却也有其合理性,这一点直到清代依然如此[43]。王衮《博济方自序》中提到,“今之人有得一妙方,获一奇术,乃缄而秘之,惕惕然唯恐人之知也。是欲独善其身,而非仁人泛爱之心也”[23]1。林灵素曾提到:“近世有人,或得一方,小小有效,则终莫得之,此亦为衣食故也。若夫腰金佩玉,出权贵之门,又安敢望其面目乎?”[14]苏轼好友巢谷有“圣散子方”,“惜此方不传其子,(苏轼)余苦求得之”,苏轼得到此方时,巢谷还担心其外传,与苏轼“约不传人,指江水为盟,余窃隘之”[44]。杨士瀛提到医学乃是“天将寓其济人利物之心,故资我以心通意晓之学”,但有些医者“隙光自耀,藏诸己而不溥诸人,政恐玉毁椟中,草木俱腐矣”,故撰《仁斋直指》一书,“庶几仁意同流,亹亹相续……并书此(序)为同志勉”[45]。南宋包惔为黎民寿作《简易方序》中提到,“或彼常人,或得一法一方,则私以自秘奇妙,唯恐人之知也。君则不以为私而为公,与人同之,唯恐人之不知也”[46]3。李健祥认为儒学逐渐介入医学,“儒而知医”者除将部分儒家伦理思想引为医患关系的准则,更重要的是对医学典籍的校注与整理[47]。在伦理方面,儒医将儒家修齐治平之术引入医学领域,继而提出医者仁恕博爱、聪明理达、廉洁淳良等基本素质的要求[48]。受此影响,“儒而知医”者更容易突破医学技术传播的障碍,将验而有效的医方刊印分享。当然,上文引述的那些化私为公、济世救人的说辞与做法固然有着自我肯定和为作者美言甚至营销的动机,但仍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传统医学在知识流布、专业伦常(不得自秘)及医学专业化之间的进退关系[49]。
除以上三类情况外也有特殊缘由者。如北宋郭思是出于对药圣孙思邈的敬仰之情,故而编选孙氏有效验方广为传播。其自序称“余亦概尝阅诸家方书,内唯《千金》一集,号为完书,有源有证,有说有方,有古有今,有取有舍,关百圣不惭,贯万精而不忒,以儒书拟之,其医师之集大成者与”。有感于“孙君(孙思邈)之仁术仁心,格而不行处有之,郁而不广处有之”,遂趁闲暇“取《千金方》中诸论,逐件列而出之以告人,使人知防止于未然之前;又将《千金方》中诸单方,逐件列而出之以示人,使人知治之已病之后。其思家与知识家经用神验者,亦附之其中,各别称说,买巨石刊之,以广其传。以救急者为先,稍可待者为次,以寻常大病为三,以寻常次病为四”[50]。又南宋时王硕编集《易简方》最初是受人所托,但编成后在仕林之间反应良好,就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编辑,“盖自大丞相葛公始辞国政,归休里第,命硕以尝所验治方,抄其剂量大概,以备缓急之需……已而士夫之间,颇亦知之,不以其肤浅,而访问者踵至,遂因已编类者,揭其纲目,更加辨析于其间,其略亦粗备亦”[51]5。而陆游编印《陆氏续集验方》则是仿其唐代先祖陆贽所著《陆氏集验方》,可见是出于追慕先祖之意[52]。
三、验方类医方书的传播与阅读
宋代验方类医书的大量编印出版,对当时社会医疗和医学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淑慧通过对宋代政府编刻医书的考察,大致将官刊医学书籍的受众分为专业医者、医学生,朝廷重要官员、士人和社会上的一般民众等层次[53],但就大多并不具备官方背景的验方类医书而言,则有些不同。通过对宋代验方类医书作者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作者以儒医为主,甚至有些人只是单纯的士人,仅略懂医学。书中内容并非针对深奥医学理论的探讨与阐述,而是各种简便实用的医方,所需药材简单易得却常有奇效,这种医方特点的形成无疑与编纂者的知识背景和出发点密切相关。即便如此,对于医学知识在普通百姓间的传播仍不宜做出过高估计。刘希洋指出,“医学知识在不同地域、阶层、群体中的传播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均质的,单从供给层面径直将简易通俗医书的大量出版和流通等同于医学知识日趋普及是一种片面的认识”[54]。两宋时在广大乡村普通民众多不识字,见识有限,“夫田野山谷之氓,止知蚕而衣,耕而食,生梗畏怯,有自少至老,足不履市门,目不识官府者……其于文字目不能识,手不能书”[55]。对于这些普通百姓而言,购买书籍本就是少有之事,要读懂这些方书并自行配制方剂,并不容易。故而实际上这些验方类医书的读者主要仍是士人和医家,他们既是各类方书的编撰与传播者,也是接受与应用者。
上文表1 中针对宋代医学书目的统计即可看出宋代验方类医书在士大夫间的流传情况,尤其是王硕《易简方》、洪遵《集验方》、官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书,在多部书目中均有收录,可见这些验方类医书或是在民间广泛流传,或是被其他医家引用收录,而这本身也是验方类医书被阅读并产生影响之一端。李瑞良指出,图书的买卖活动在宋元时期已成为图书流通的主要渠道[56]。据张秀民统计,宋代医书约400 余种,出版可考者近100 种,有的医书甚至可能出六七版[57]。上文验方类医书依其序跋所言基本都曾刊印出版,使其读者群体极其广泛。以下略举几部验方类医书的刊印流传情况,试做说明。
真宗咸平年间陈尧叟任广西路转运使,“岭南风俗,病者祷神不服药,尧叟有《集验方》,刻石桂州驿”[27]9584。该书除刻石于桂州驿站外,还抄录了一份送至宫廷,真宗天禧二年(1018)八月,“内出郑景岫《四时摄生论》、陈尧叟《集验方》一卷示辅臣。上作序记其事,命有司刊版赐广南官,仍分给天下”[58]。真宗亲为制序,又官方出面刊刻颁行,使其传播影响范围更大。
北宋郎简“尤好医术,人有疾,多自处方以疗之,有《集验方》数十行于世”[27]。郎简与王衮约处于同一时代,据其为《王氏博济方》所作《序》称:
今春,钱塘酒官王君,惠然见过,出方书三编示予,且曰:衮平素善医诊,所摭精要方若干首,不敢自爱,欲刊摹以周施四方,冀人人得遂其生。予乐听所云,顿起夙惜之愿,称叹者久之,雅闻其人好奇博涉摭士也。因自录素所奇异方有验于人者,得三十余通,请附于类例之内,以助成一家。[23]1-2
王衮所著《博济方》书稿完成后欲刊印出版,遂寻杭州显宦同时通晓医术的郎简求序,郎简对王衮济世救人之意可谓感同身受,感叹良久欣然作序,并于自己《集验方》中又选30 余方附于其内一同刊印。南宋时,刑部郎中、知温州莫伯虚“以其家藏《经验方》附于后”[59],于永嘉年再次重刻发行。该书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均有收录,各书所记卷数稍有不同,或在当时已有多种版本。晁公武引当时名医云“其方用之无不效,如草还丹治大风,太乙丹治鬼胎,尤奇验”[28]731。
又有南宋抗金名将杨存中子杨倓,其称“余家藏方甚多,皆先和武恭王及余经用,与耳目所闻尝验者也”[60]1。杨氏此书刊印于当涂,对江淮间的社会医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书后延玺跋称:
枢密洪、杨二公,给事胡公前后守当涂,各有方书锓木于郡中,亦遗爱之一端也,其名曰《洪氏集验方》《杨氏家藏方》《胡氏经效》。今江淮间士大夫与夫医家多用此三书约证,以治疾无不取效。闽中相去差远,犹未之有。今刊诸宪司将以惠众,抑亦副三公欲广其传之意云。[60]355
《洪氏集验》即洪遵《集验方》,初刊于乾道六年(1170)姑孰郡斋;《杨氏家藏方》据其自序是淳熙五年(1178)初刻于郡斋,亦为官刻;《胡氏经效》疑即《宋史·艺文志》中所录胡元质《总效方》,据《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胡元质为平江府长洲县人,历官“大学正秘书正字校书郎礼兵部郎官,迁左司郎官给事中出知和州、太平州……”[61],又康熙《当涂县志》载:“(乾道)八年,常平仓池中产双白莲,知州胡元质以闻,因建双莲楼。”[62]则胡元质任官太平州当是在乾道至淳熙初,《胡氏经效方》也应是初刻于此时。延玺于淳熙十一年(1184)再次以官方刊印三书,流传自然更为广泛。
南宋官员陈晔在任福建汀州守官时先是主持刊印了方导所著《方氏家藏集要方》,此后又搜集自家验方,编印《家藏经验方》。此书涉及病证广泛,药方简便,且详细收录药方治病的验案[6]。故而刊行后传播较广,南宋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已有收录,此后医书也多有引用[7]。又据《本草纲目》引陈氏《家藏经验方》称:“方夷吾所编《集要方》,予刻之临汀。后在鄂渚,得九江守王南强书云:老人久苦淋疾,百药不效。偶见临汀《集要方》中用牛膝者,服之立愈。”[63]可见至少在福建与江西等地,《方氏家藏集要方》刊印后有较为广泛的传播,一些士大夫不仅有所阅读,还以之治疗疾病,证明其中药方确有奇效。
叶大廉“尝见医家有能疗人之病,而少有授人以方者。每自思之,与其施药与人,岂若录已验之方,使其传之寖广”,故编著《叶氏录验方》,经当地医家审校后初刻于淳熙十三年(1186)龙舒郡斋,是书刊行后主要流传于江淮间,影响甚广。宁宗年间李景和经人相赠获得此书,后亲试其中治方,“皆有奇效”。又曾用书中医药在婺州治疗时疫,“两狱遇有病因,居民间值时气,辄施解肌汤为剂,动以数十斤计,服者无不立愈,得名神捷诚不忝,江淮间人多信用之。他所或未之见,予故刻之冬阳郡斋”[20]134。即为广其传,又于嘉泰四年(1204)再次官刻出版。
影响最大者无疑是南宋王硕的《易简方》。王硕于史无传,《直斋书录解题》称其为永嘉县人。又雍正《处州府志》卷十三载:“陈言,字无择,青田人……其徒王硕为《易简方》并《三论》行世。”[64]可知其师从于南宋名医陈无择,施发《续易简方论》中称“王德夫作《易简方》,大概多选于《三因》而附以他方增损之”[65]亦可为证。《易简方》一书编写之初是受原左丞相葛邲之托,“以常所验治方,抄其剂量大概,以备缓急之需”。书稿初成之后在士大夫之间反应良好,“遂因已编类者,揭其纲目,更加辨析于其间”而成。王硕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医疗条件,“若夫城郭县镇,烟火相望,众医所聚,百药所备,尚可访问。其或不然,道涂脩阻,宁无急难,仓皇斗捧,即可辨集。今取方三十首……凡仓卒之病,易疗之疾,靡不悉具”[51]5。其完成后广受欢迎,流传甚广,对当时的社会医疗及医学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斋书录解题》称“其书盛行于世”[60]396,南宋淳祐三年(1243)施发作《续易简方论》时序称“今世士夫孰不爱重,皆治病捷要,无逾此书”[65]。冯梦得开庆元年(1259)撰《黎居士简易方论序》提到,“第山行水省,仓促急难,仓、扁未易卒集。故近世《王氏易简方》,士大夫往往便之”[46]9。又南宋刘辰翁《济菴记》提到:
自《易简方》行,而四大方废,下至《三因》《百一》诸藏方废。亦犹《中庸》《大学》显而诸传义废,至《诗》《书》《易》《春秋》俱废。故《易简方》者,近世名医之薮也,四书者,吾儒之《易简方》也。[66]
另据《亡名氏校正注易简方论》题词,“此书乃亲传真本,复加校正,与市肆所买者,大相辽绝”[67]。可见是书出版后出现多种不同版本,已开始刊印宣称持其原稿进行校正的版本。虽然此处题词可能是书商借以宣传之语,但也说明王硕《易简方》在当时社会上较受读者欢迎。此后亦多有对此书进行校正、增修、续作者,如宋代孙志宁著《增修易简方论》,卢檀作《易简方纠谬》,施发撰《续易简方论》[68]等,足见其影响之广泛。约生活在南宋理宗年间的福建著名医家杨士瀛对王氏《易简方》颇为推崇,曾在其《仁斋直指》中对该书及其后续作品进行评论:
《易简方论》前后,活人不知其几,近世之士,类以《春秋》之法绳之,曰《易简绳愆》,曰《增广易简》,曰《续易简论》,借古人之盛名以自伸其臆说。吁!王氏何负于人哉?余谓《易简方论》,四时治要,议论似之自有人心权度存焉耳。况王氏晚年剂量更定者不一,日月薄蚀,何损于明,若夫索瘢洗垢,矫而过焉,或者公论之所不予也。[45]11
以上这些医方均明确表明作者对其疗效曾亲自验证,其中一些更是经过多次刊印,使其实际疗效更具可信性。验方医书在刊印后受到广泛欢迎,极大促进了这些医方在当时和后世的传播,也有利于其他病患和医家学习使用。官方对于各类医书的流传也是积极促进,南宋时“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搢绅家世所藏善本,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板,以为官书”[69],上引各地“郡斋”本方书,即地方官府刻印发行;又《乾道令》有云:“诸州县医药方书,州职医、县医生掌之,置印历,听借人传录。”[70]
另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医家,其对各验方的整理都是致力于药方的由博返约及其标准化和规范化。杨士瀛撰《仁斋直指》称:“明白易晓谓之‘直’,发踪以示之谓之‘指’。剖前哲未言之蕴,摘诸家已效之方,济以家传,参之肘后,使读者心目了然,对病识证,因证得药,犹绳墨诚陈之不可欺。”[45]各种验方的编印出版,就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一样是为百姓提供了治病用方的标准,使百姓可以直接按照验方抓药。这在短期内难以提高社会整体医疗水平和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大大降低百姓的医疗成本。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在重视医学的整体社会环境下,大量的验方类医书得以编印出版。其作者群以儒医为主,目的或是为他人治病提供方便,或是为实现济世救人的理想,或是为改变当时医家风气,都促使他们积极开展验方类医书的编印事务。这些方书的出版极大促进了医学知识的传播与保存,很多方书为一些不通医学的士人、百姓治疗疾病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诸多医家也对此极为重视,一方面按验方医书上的方式治病,另一方面又将自己行而有验的医方编印出版。在此背景下,两宋医学知识扩散的广度与深度可谓空前:“通过医学书籍特别是大量方书的编撰、刊刻、流通和阅读来进行的,这些方书成为医学知识的载体,成了医学知识扩散中最重要的媒介。”[71]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宋代验方编印的流行与儒医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以往验方类医书的研究中尚未进行探讨。一般而言儒医多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家庭条件相对较好,从个人倾向上讲,在孟子“仁术”学说的影响下他们希望通过医学来实现济世救民的理念[72];从经济基础上来讲,其经济压力相对较小,盈利方面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故而他们能够将一些经过验证确有奇效的医方编印出版,而非珍藏以谋利。官方与民间各类验方医书的刊印出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医学知识秘传的禁锢,各家医学学说经此汇集,派别之间的界限自然会渐趋消弭[73]。
最后,一般认为宋代之后的医家更重视对医学理论的阐发,如谢利恒言:“唐以前之医家,所重者术而已,虽亦言理,理实非其所重也。宋以后之医家,乃以术为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此自宋以后医家之长。然其所谓理者,则五运六气之空理而已,非能于事物之理有所真知灼见也。”[30]46此就中国医学发展之大的趋势而言,当为确论。但通过对宋代验方类医书的探讨,我们即可发现,仍有部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医家注意到了医学理论探讨与现实医学实践的不同,并努力弥补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如韩毅所指出的,“与前代方书相比,宋代医家方书在临症经验总结、医案病案记述和验方、效方、秘方收集等方面,表现出相当大的知识创新”[3]533。注重理论探讨,以寻求具有指导意义的总体理论与法则或许只是宋代以来中国传统医学发展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