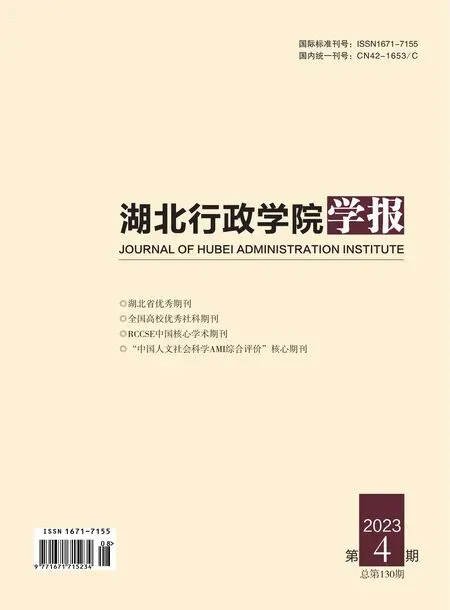生活化:群众主体性嵌入基层文化馆体系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梁来成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 武汉 43002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大众文化,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时代命题。公共文化服务只有向大众敞开,丰富群众生活,才能展现强大的创新创造活力,筑牢民族复兴的文化堡垒。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馆是中国特有文化部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职能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识字率较低,文化馆主要配合政府开展文字扫盲等教育普及工作。集体化时代,文化馆侧重配合各项政治宣传教育[1]。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馆职能演变表现为三个阶段。一是“以文养文”时期。在市场化浪潮中,文化馆普遍侧重文化产品经营。二是从2008年开始的“免费开放”时期。文化馆被设定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免费开放机构,其功能重新定位在进行公共文化普及和组织群众文化活动、开展艺术培训、引导民众休闲娱乐等方面,从而明确了其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其充分发挥了凝聚群众、引导群众、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布局优化和资源共享等作用。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经历了为期十年的大规模文化体制改革。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多元,政府对文化馆的保障不断完善,社会群众文化的热情不断高涨[2]。公共服务场馆免费开放政策实施后,关于文化馆的研究不断丰富,主要包括文化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功能与定位的阐释、问题与对策的分析等,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文化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文化馆功能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李国新指出,“我国文化馆(站)系统聚焦全民艺术普及核心功能推动服务转型升级,构建起了主要由知识普及、欣赏普及、技能普及和活动普及构成的全民艺术普及内容体系”[3]。巫志南指出,文化馆承担着“组织指导、传承创新、基层培训、创造指导、系统管理、综合平台”的六类基本职能[4]。在提升文化馆效能的问题上,于静等人认为应当以地方文化为本底打造文化品牌[5]。何义珠等人认为可以利用文化馆(站)等公共文化空间,开展民族文化活动,保护、传承、弘扬了优秀民族文化[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改善文化馆内部环境、提升文化馆内部人员素质、注重与政府与新闻媒体合作。
总体来看,一些学者聚焦在组织和技术层面如何提升文化馆服务效能的研究卓有成效,但是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当前的研究对于文化馆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独特地位论证尚不充分,没有厘清文化馆与图书馆、博物馆等其它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不同定位和差异化的职能分工,也没有清晰地指出文化馆区别于其它公共文化机构的关键之处。二是尽管一般研究者对于文化馆的群众属性高度认同,但是较少涉及对文化馆的群众主体性进行研究。由此可知,已有的文化馆理论研究与文化馆实践研究之间还存在着一些脱节和断裂。
二、主体性—生活化的分析框架
为了阐释清楚公共文化政策在文化馆体系中如何呼应群众,以及文化馆体系如何回应公共文化政策,我们调查了湖北省京山市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发现“群众主体性”是文化馆区别于其它文化场所的基本特征,“生活化”是文化馆贯彻公共文化政策、服务群众的“关键点”。依托生活化的理念和实践将群众主体性嵌入文化馆体系是提升其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可行路径。
社会实践的进步与主体性认识进步具有紧密联系。中国传统社会将民众置于被统治地位、模糊的集合体。“民贵君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无不体现作为对象化、客体化的主体性。英国近代政治哲学家斯宾诺莎表现出强烈的非主体性倾向,将笛卡尔等学者提出的人心所赋予的认知主体地位消除[7]。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8](P847)。由此而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众文化旗帜鲜明地将文化服务的主体和对象指向了民众特定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对象——“工农兵”。这一表述与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下处于被统治地位、模糊的集合体民众主体性有本质不同。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加快、社会分化程度加深,作为个体的民众,原子化特征愈发彰显,个体化倾向在群众主体性中更加突出。群众主体性的特征逐渐呈现出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双重维度。因此,新时期需要关注群众主体性二重性如何嵌入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优秀作品……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9](P314),对新时代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出新要求。公共文化服务蕴含的主体性既包含集体主义也包含个体主义。作为集体主义的主体性体现在关注民众一般性和普遍性的需求,致力于为民众文化生活提供公共性;作为个体主义的主体性体现在关注不同群体民众的不同层次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致力于为民众文化生活提供个体性。
在文化馆“免费开放”政策实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在文化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对群众主体性的二重性理解缺乏辩证性,文化馆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要么在“阳春白雪”的专业化路线上“曲高和寡”,要么在“下里巴人”的通俗化路线上“格调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果。简而言之,只有将群众主体性嵌入到文化馆的价值依归与日常实践之中实现群众主体性二重性的平衡,才能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需要。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0](P158)。这为理解两种主体性的融合提供了基础性的方向——从民众实际“生活”的角度。生活蕴含在特定的生活方式、特定的话语结构、特定的生产模式之中。社会生活的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是对民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存在方式的体认、再现和升华,推动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融合,构成社会总体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馆对于培养群众的文化自觉性,塑造群众文化身份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文化馆在关注群众主体性的时候,必须用生活化的方式进行呈现。首先,生活化意味着公共文化服务不是依赖纯粹想象建构,而是从民众生活实践的具体情境出发,凸显群众主体性,在生活化的理念、生活化的运作和组织架构中将群众主体性嵌入文化馆体系。其次,生活化包含着对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单元进行再思考,这意味着基本服务单元需要下移与下沉,重心逐渐转向城乡基层社区,推动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生产、供给和运作服从于群众生活实践需要。最后,生活化的文化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生产还需要吸纳群众自组织的文化团体及其文化产品。继而构建群众主体性嵌入到文化馆的机制,形成制度支持的生活化。生活化这一理念嵌入到文化馆的实践中,如同催化剂一样加速文化馆服务型转向,完成群众主体性的嵌入。
一是集体主体性与公共文化服务意义系统的互动[11](P20)。“意义系统”则是相对于由个人构成的社会整体而言的,意义系统以意义为基本要素,由个体多样性的意义选择及其在主体交往、互动中叠加、放大而形成的新成分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的意义系统。意义系统的持续性再生产在价值与实践的互动中方能实现[12]。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说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13](P139)个体的人只有社会性的交往中,才可以实现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塑造。人是“置身于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14](P96)的一种反映,但是这种意义之网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冲击,社会中的民众呈现原子化、个体化的结构,各类职业的“神圣光环”“温情面纱”,被市场交易行为所取代,社会意义系统缺乏有力的建构路径。文化馆价值与实践的生活化路径有助于民众意义系统的建构。群众性文化是社会生活方式的传承手段,包含着知识、娱乐、教育、美育等功能,生活化的互动,可以增强民众政治素养和知识素养,构成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面。促进群众公民意识、主人翁意识生成,推动民众思想文化与国家主流价值理念相一致,避免消极形式的意义系统的趁虚而入。比如,对冲和消解“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男女对立”等消极价值追求的扩张,抑制地下宗教在基层城乡社会的影响力。
二是个体主体性与公共文化服务实践的互动。遵循生活化的观念,确立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和途径。个体主体性与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互动的关键在于寻找群众艺术与群众文化的结合点。将文化馆的公共文化实践理解为生活化的互动,增强其对不同民众公共文化需要的嗅探能力,了解不同民众正在进行的文化活动是什么,迫切需求的公共文化有哪些。鼓励各类民众积极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培养民众良好的思想道德情操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促进群众性文化生活达成了娱乐性元素、休闲性元素与知识性元素融合构成了个体主体性与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互动的基本方式。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现阶段部分文化馆遵循生活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理念适应了群众需要,也符合于国家公共文化机构转型的需要。本文将以湖北省京山市文化馆为例,阐释其依托生活化将群众主体性嵌入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探索。2021年,京山市文化馆被评定为一级文化馆,其建筑面积有6000平方米,每年举办全市文艺骨干培训班、下乡辅导培训等活动80多次,服务基层群众超过2万人次,其中各类业务人员每年创作文化艺术作品100多件。因此,探索群众主体性嵌入基层文化馆体系的生活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生活化: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性的价值意蕴
1.生活化彰显普惠性价值
在群众主体性的价值层面,以民众文化生活的普遍需要为依归,为绝大多数民众文化生活服务。运用既有资源和阵地做好文化惠民活动,让广大群众充分享受文化成果。京山市文化馆主要从三个方面确保普惠性群众文化生活的政策落地。第一,强化阵地属性。将出租性活动室全部收回,设立为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场所。第二,优化服务质量。根据文化馆教师的专长,将各个免费开放项目细分为声乐、合唱、舞蹈、管乐、弦乐、美术、书法等方面,通过专业教师组织培训活动。第三,注重活动设计。一是关注群体需求,组织群众活动。比如,在健身舞热潮中,文化馆专门编排适合中老年人的健身舞,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选择。二是关注基层需求,定期委派专业教师到乡镇或村居甚至小区楼栋送公共文化服务。三是关注群体个性化需求,引入社会力量,邀请公共文化专家或社会组织来协助提供服务。
2.生活化突出地域性生活文化特色
生活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在地性群众生活实践的重要产物。基层民众长期以来的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为群众主体性嵌入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县域普遍存在特色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地方化戏曲、民乐传统元素、吸收独特民俗特色,原汁原味呈现乡音乡土之味,既可以较好链接所在地群众文化需求,又有助于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构建鲜明地方特色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立足本地特点,贴近群众需求,才能有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让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人。京山市文化馆立足地方优秀文化从地方生活中提取具有鲜明特色的要素,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依归。由京山市的本土原创曲目构成的文艺节目《家在京山》全部曲目皆取材于京山市民间传统文化故事,节目有表现京山市特有珍稀树种对节白蜡优美形态、呼唤生态文明的歌舞《千年之恋》,有表现京山市孙桥镇“女婚男嫁”的独特婚俗的《娶新郎》,有表现京山市民俗风情的《九佬十八匠》《一个人的皮影》《娶女婿》《像啷说》等。凝聚京山市本土地方化的特色民俗风情,将当地民众生活以文艺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京山市群众可以从中感受其县域的生活化韵味和民俗文化缩影。
3.生活化关注不同群体生活多层次文化需求
不同年龄层次、知识结构的群体有着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为了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精准递送,价值上要关注和回应不同群体层次性需求。比如,回应儿童暑期素质提升正在成为家庭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为放学后的孩子开办“四点半课堂”;回应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文化生活需要,开办老年艺术大学,组织老年人群体研讨传统文化、开展文体锻炼等实现着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回应年轻人上班族文化需要,在商务楼宇、产业园区等地点“见缝插针”,为年轻人提供符合快节奏文化生活需要的服务和产品。京山市文化馆积极聘请专业教师开展儿童书法培训、儿童演讲培训、儿童音乐培训、儿童舞蹈培训。与成年人的相关培训相比更加注重基础性与趣味性。京山市文化馆根据成年人群文化需求,尽可能多地准备相关培训课程,如民族舞培训、钢琴培训、合唱培训、美术培训、国标舞培训、民乐培训等。
四、生活化: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中群众主体性的实现路径
1.群众主体性嵌入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生活化素材
人民生产和生活是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丰富素材。京山市现有文化、艺术、体育等各类协会30多个,每年举办600场以上各类文体活动。社区文化节、春节民俗文化活动、广场舞比赛、各种文体比赛等活动品牌深入人心。“生态文化”“网球文化”等地域特色文化品牌初步显现,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源头活水”。
一是生活化的群众活动。群众健身运动以广场健身舞大赛较有人气基础。在全市范围内,乡村社会以镇为单位,组建一支或多支健身队参加;城区以社区为单位,组建一支或多支健身队报名参加;市文化馆负责展演活动的具体辅导、组织工作,并组织好基层文艺骨干广场舞的培训。
二是生活化的文化品牌。每年常态化、定时开展带有群众生活气息的文化活动,如“农家乐杯”文艺比赛、社区文化节、广场舞大赛、群众文艺展演、春节民俗文化表演、戏曲进校园、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等,培养群众主体参与意识。整合全市25个文学艺术专业协(学)会、257个业余演出团队,成立京山市文艺联盟,以此为基础组建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队在基层常年开展各类文体活动。这些活动体现出基层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15],彰显了群众主体性嵌入文化馆动态发展过程。经过历年沉淀,已经培育为被民众认可的县域公共文化服务品牌。
三是生活化的文艺精品。每年投入300多万元以奖代补,激发文化团体挖掘生活化素材的创作潜力,一批富有生活气息,反映生态发展、乡村振兴的文艺作品涌现出来。民俗歌舞诗《家在京山市》及歌曲《千年之恋》,分别获屈原文艺戏剧、歌曲大奖。广场舞《薅黄瓜》获“文化力量·民间精彩”湖北省群众广场舞展演一等奖。创作现代花鼓戏《渡口》列入文旅部戏曲剧本孵化计划,入选全国30强戏曲小戏孵化计划项目。京山市首部全国院线电影《云做的翅膀》荣获湖北省精品电影奖。音乐作品《春天的牵挂》《2020京山我爱你》在学习强国、央视新闻移动网、中央广播交通频道播出。一系列扎根群众文化深厚土壤的文化品牌从群众的广泛参与创作中脱颖而出。
2.群众主体性嵌入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生活化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公共文化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不仅受特定空间因素影响,而且受供给的友好程度影响。从消除空间性和友好性制约性因素出发,京山市探索“馆会合一,馆校合作”,创造生活化的条件,使得公共设施的开放有效融入民众生活之中,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
第一,建设公共文化平台。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其自身特点。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公共文化服务具有“生活”意蕴。公共文化服务从供给主导者主要是政府,但是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者的广大民众,又可以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直接生产者。京山市文峰公园定期开展“百姓舞台”文化演出活动,包含着音乐、舞蹈、器乐等各种艺术门类,群众性的自发的文化活动既满足了其自身需要,也促进了公共文化产品再生产。
第二,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一方面,通过系列惠民工程,推进公共文化资源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向基层弱势群体和普通市民倾斜,实施公共文化“进村入户”工程。开展送戏、送电影、送图书、送展览、送讲座、送文艺节目活动。文化下乡突出基层群众的主体地位,京山市加强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乡镇街道建成436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点、260个村级活动中心、421个农家书屋。
另一方面,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切实贴近百姓生活不仅包括内容产品的下乡,还包括内容生产供给“手段”下沉。镇村、社区、学校在公共文化上都有需求,依托网格化管理的手段,可以由文化馆内的老师划分片区进行辅导,由此建成一个以文化馆为“龙头”,以乡镇文化站为枢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培训供给网络。数字赋能公共文化资源。在信息社会中,民众网上获取公共文化成为人民新的文化生活方式。推进公共文化“数字服务”就具有了一定的必要性。京山市依托图书馆丰富的馆藏与网络资源、信息处理技术及专业图书情报人员队伍优势,建立数字资讯中心,为民众提供即时资讯、信息检索咨询、市民学习教育、资源整合推送等服务,推进市网上文化馆建设和开放,使民众快速便捷享受信息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同时,在生活化理念引领下,文化馆惠民服务采用对象化的办法。例如,文化阵地开放、群众文化活动组织、文艺联盟成立等,助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群众主体性彰显。312支民间文艺团队组成的京山市文艺联盟,常年活跃在基层;春节系列文化活动、群众广场舞比赛、社区文化节、京山市文艺联盟文艺展演等品牌文化活动深入人心。
3.群众主体性提升文化馆公共文化效能的生活化路径
其一,基层文化人才聚拢。依托文化志愿者和各类群众文艺团队,发挥其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用。鼓励群众自办文化团体,专业和业余文化队伍的互动相辅,汇聚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京山市孙桥镇以镇办刊物《桥乡风》为载体,聚拢了一批退休编辑、诗词学会会员、省作协会员。基层文化人才的文化作品成为弘扬乡土文化,满足群众公共文化需求的一扇窗。
其二,群众文化建设联动。畅通群众文化需求反馈通道,增进群众与文化馆互动。完善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反馈机制、公众满意度评估机制、重大文化项目服务考核绩效评估机制等,提升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让民众成为免费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京山市文化馆一方面设立馆长接待日,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倾听群众的呼声;另一方面也可以接受群众的评议与督促,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更加人性化。通过召开群众座谈会、设置意见箱,梳理群众反馈的意见及需求,吸纳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需求,探索让群众满意的免费开放制度,使免费开放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