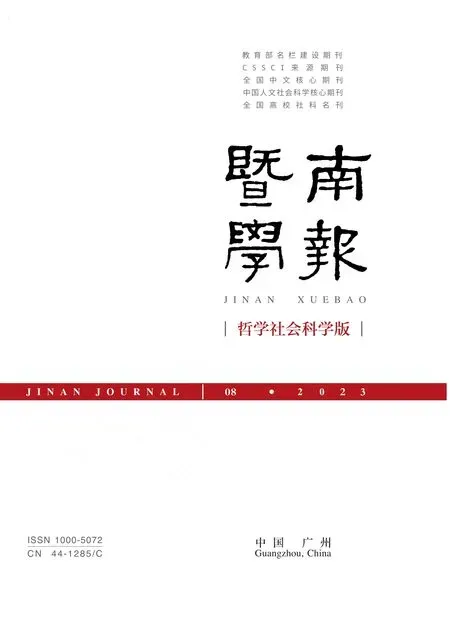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
邓 华
一、引言:遵循抑或背离罪刑法定原则
作为刑法基石性原则的罪刑法定原则(1)See Claus Kreß,“Nulla Poena Nullum Crimen Sine Lege”,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ttp:∥opil.ouplaw.com).滥觞于启蒙时代。它在预设了立法具有明确性、清晰性和完备性的基础上,规定了司法权对立法权不偏不倚的遵守,(2)参见高巍:《重构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同时具备规范立法和限制司法两个面向。(3)参见江溯:《罪刑法定原则的现代挑战及其应对》,《政法论丛》2021年第3期。它最早由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里亚(Beccaria)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系统提出,(4)参见[意]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1页。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演变成法律,并逐渐在资产阶级法律体系中得到了确认。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趋势,现今已成为世界各国刑法中最为普遍和重要的一项“帝王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意义重大,它既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也有利于保障人权。(5)参见贾宇主编:《刑法学》(上册·总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58—59页。
各国刑法实践中的这一基本原则亦适用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在国际刑法领域,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国际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外在表达。早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起草“国际人权宪章”(6)“国际人权宪章”指《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最初几稿时,其就已决定将禁止溯及既往规定为国际人权公约中一项普遍和不可克减的权利。(7)参见[奥]曼弗雷德·诺瓦克著,孙世彦、毕小青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修订第二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5页。在国际法层面,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演变来看,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从传统的视角来审视国际刑事实体法,即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要依据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则来认定国际罪行并处以相应的刑罚;广义则既包括对国际刑事实体法的审视,亦包含国际刑事诉讼法与国际人权法视域中的“法庭需要依法设立”原则,以“强调被告人的权利要受到依法和公正设立的司法机构的保障”(8)参见蒋娜:《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新进展——兼及对中国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王秀梅:《国际刑事审判案例与学理分析》,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ICTY,下文简称为“前南刑庭”)(9)前南刑庭是由联合国安理会于1993年5月25日通过第827(1993)号决议建立的特别法庭。参见刘大群:《联合国临时法庭对国际刑法发展的贡献》,柳华文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2018)》,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1页。的“切里比切(Celebici)”案中,前南刑庭对罪刑法定原则和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进行了解释,它指出,在世界主要刑事审判制度中,这些原则被公认为刑事犯罪的根本性原则。(10)See ICTY,The Prosecutor v. Delalic and others,Case No.IT-96-21-T,Judgment (Trial Chamber Ⅱ),16 November 1998,para.402.《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Statuteofthe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下文简称为“《罗马规约》”)则在第22条至24条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且非常详尽地诠释了这一原则的内涵和外延,(11)参见蒋娜:《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新进展——兼及对中国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包括“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以及“对人不溯及既往”。
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罪”与“罚”的规定要明确,“现代国际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是要尽可能清楚、明确地将预防、禁止和惩治国际犯罪的国际刑法规则加以编纂”(12)邵沙平:《现代国际刑法教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由于受到罪刑法定这一基本原则的约束,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不能对自己管辖范围之外的国际罪行进行审理。譬如,《罗马规约》规定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属事管辖权”仅包括战争罪(War Crimes)、灭绝种族罪(Crime of Genocide)、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和侵略罪(Crime of Aggression),其中并不包含“恐怖主义罪”,因此,“恐怖主义罪”就不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国际刑法尚未发展到足够成熟阶段,也没有一部统一的国际刑法典,(13)即使在具有统一刑法典的国内法体系中,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运行也同样会面临冲击,学界亦未曾停止对此进行反思,也有学者在国内法层面提出“重构”罪刑法定原则。参见高巍:《重构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因此,为了惩治国际犯罪和打击有罪不罚,一般国际法包括习惯国际法(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下文或简称为“习惯法”)的适用便在所难免。根据《国际法院规约》(StatuteoftheInternationalCourtofJustice)(14)1945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1 UNTS 993.第38条第1款(丑)项对习惯国际法的规定,即“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历来认为,习惯法由“国家实践(State practice)”和“法律确信(opiniojuris)”这两个要素构成,它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具有法律拘束力。(15)持续反对者(persistent objector)例外。此外,国际刑法要力求避免对同一国际罪行的法律适用存在双重标准,而条约的相对性特征使得犯有同一国际罪行的缔约国国民和非缔约国国民适用条约可能得到不同结果,因此,这也是习惯国际法在国际刑法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一个原因。譬如,在前南刑庭应当适用的法律这一问题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就强调,“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要求国际法庭应适用毫无疑问已成为习惯法一部分的国际人道法,因此,一些诸如并非所有国家遵守特定协定这样的问题便不会出现”。(16)Report of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pursuant to Paragraph 2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808 (1993),3 May 1993,UN Doc.S/25704,para.34.即法庭所适用的法律只能是已经属于习惯国际法的规则,如习惯国际人道法。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产生只有一些国家是而另一些国家不是公约缔约国的问题,是为了使国际刑事法庭的司法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具有合法性。但是,习惯国际法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它事实上始终处于一个演化发展的过程中,这可被视为它相较于成文法的“缺点”;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法规则本身具有确定性、清晰性和具体化等特点,因此,在追究国际刑事责任领域适用习惯国际法会否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又是一个值得探讨并加以澄清的问题。(17)参见朱文奇:《现代国际刑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47页。具体而言: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领域的标准和呈现与其在国内刑法中是否完全一致,抑或存在着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其正当性或合理性根基又在哪里?一般而言,国内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严禁适用事后法或溯及既往,(18)尽管一般认为,国内刑法严格适用罪刑法定原则,但也有学者指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犯罪现象也会层出不穷,而立法具有相对滞后性,如此便会导致立法对某些新的犯罪行为没有规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便不能论罪处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采用实质解释的方法,对刑法规定进行解释,由此扩张刑法规定的边界,借此容纳那些刑法没有规定的行为,以此作为入罪根据”,“对此是应当警惕的”。参见陈兴良:《罪刑法定的价值内容和司法适用》,《人民检察》2018年第21期。但国际刑法在这一点上是否就能做到完全禁止、毫无争议呢?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认定、解释、适用和发展,究竟是否遵循抑或背离了罪刑法定原则?为此,下文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下文简称为“二战”)之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Nuremberg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下文简称为“纽伦堡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下文简称为“远东军事法庭”)(19)“二战”结束后,同盟国在1945年和1946年分别通过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Nuremberg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the 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由此分别成立了纽伦堡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这两个国际刑事法庭是现代国际法意义上成立最早、对国际刑法最具影响力和冲击力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它们不仅进一步肯定了战争罪,而且使国际法新增了破坏和平罪以及危害人类罪。参见朱文奇:《现代国际刑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61—67页。对破坏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侵略罪”)的审判作为切入点,分别从实在法和自然法的角度进行分析,尝试对侵略罪的历史变迁展开实证考察,以期对前述问题作出一个初步的回答和阐释。
二、罪刑法定原则与“二战”后两大审判对破坏和平罪的认定
(一)破坏和平罪与罪刑法定原则:基于实在法的视角
早在纽伦堡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成立之时,它们在各自的《宪章》中便规定了对破坏和平罪的定罪处罚。但是,在两个法庭成立之前,国际法上是否就已经禁止侵略行为(act of aggression)呢?侵略行为是否会导致习惯国际法上的国际犯罪呢?进而言之,个人又是否需要为此负国际法上的责任?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审判过程中存在着争议。(20)事实上,历史记录表明,英、美、法、苏四国代表团在1945年7月就纽伦堡法庭的属事管辖权进行谈判时,发生了极大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美国代表团团长杰克逊(Robert H.Jackson)坚持主张在纽伦堡法庭《宪章》中纳入破坏和平罪,而法国代表则认为,破坏和平罪并非现行国际法规则,因此无法对这种行为进行个人国际刑事责任追责。在杰克逊的坚持下,纽伦堡法庭《宪章》最终涵盖了对破坏和平罪的管辖权。See Report of Robert H. Jackson,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ilitary Trials,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080,1949,pp.299-384.
事实上,在1974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侵略的定义》(DefinitionofAggression)(21)UN Doc.A/Res/3314 (XXIX),Definition of Aggression.之前,国际社会并没有就“侵略”的定义达成过一致,而且,从理论上来讲,作为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关于侵略的定义》在形式上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在这种情况下,距其近30年前建立的纽伦堡法庭已在其《宪章》第6条、远东军事法庭已在其《宪章》第5条中分别规定了“破坏和平罪”,即该罪行包括计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一场侵略战争或一场违反国际条约、协议或保证的战争,或为前述任何行为而参与共同计划或共谋的行为——即侵略是国际犯罪行为;那么,两个军事法庭关于破坏和平罪的实践是否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呢?而且,由于侵略行为的严重性,犯下破坏和平罪的人还被列入“甲级战犯”——“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分别指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22)参见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北京:法律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冷新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争罪的思路》,《国际法学刊》2021年第2期。的个人,因此,破坏和平罪不仅被认定为国际犯罪,还是一系列国际犯罪中最为严重的一项罪行。被告律师主张:侵略战争本身不是非法的,国际法并没有把战争当作犯罪,对破坏和平罪的指控是基于事后法(expostfactolaw),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因此是非法的;而且,战争是国家行为,个人在国际法上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纽伦堡法庭首先驳回了前述被告律师的主张,(23)远东军事法庭判决的宣布比纽伦堡法庭要晚两年,但它对纽伦堡法庭在“破坏和平罪”的认定方面,表示完全同意。参见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认为“诉诸侵略战争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犯罪行为(not merely illegal,but is criminal)”;指出破坏和平罪“是最大的国际罪行,与其他战争罪行的区别,只是它所包括的是全部祸害的总和”,因为从逻辑上讲,如果没有侵略行为就不会发生战争,如果没有战争就不会有杀伤、奸淫掳掠、虐待战俘等战争罪行,所以侵略战争是“全部祸害的总和”,也是“最大的国际罪行(Supreme International Crime)”。(24)See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Published at Nuremberg,Germany,1947,pp.186,222.
两个军事法庭认定侵略是一种国际法上的罪行,其主要依据是1928年订立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公约》(即通常所说的《巴黎非战公约》(PactofParis)或《白里安—凯洛格公约》(Kellogg-Briand Pact)),该公约彼时已有63个国家批准,包括德国和日本。(25)《国际条约集(1924—193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73页。虽然《巴黎非战公约》仅有1个序言和3个条文,但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禁止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之方法和推行国家政策之工具的多边公约,其中第1条明确规定:“缔约各方以它们各国人民的名义郑重声明,它们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合法工具。”第2条进一步规定:“缔约各国互允:各国间如有争端,不论如何性质,因何发端,只可用和平方法解决之。”亦即,诉诸战争不再是国家的合法权利。在“二战”开始前,德国和日本都已经加入该公约,因此两国都有遵守该公约的义务。纽伦堡法庭认为,自从《巴黎非战公约》订立后,侵略战争在国际法上已被视为违法,不仅违法,而且是犯罪,它在判决中明确指出:
《宪章》并非战胜国方面权力之武断的行使,而是《宪章》制定颁布时现行国际法的表达;在这种程度上,其本身即是对国际法的贡献。(26)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Published at Nuremberg,Germany,1947,p.218.
尽管《巴黎非战公约》中没有使用“犯罪”这一表述,但纽伦堡法庭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公约中认定的“国际法不法行为”,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其意义等同于“国际犯罪”。纽伦堡法庭还以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作为例证,指出该公约亦未曾使用过“犯罪”二字,但人们始终未质疑其中所禁止事项皆属犯罪行为,自公约生效后,已有许多犯下这些罪行的人被各国法庭逮捕,作为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和惩罚。因此,纽伦堡法庭强调,解释和适用法律不能拘泥于呆板的文字,而应重视“立法”精神和当时的环境,包括当时的公众意识、人类进步、社会舆论等。(27)See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Published at Nuremberg,Germany,1947,pp.220-221.不过,《巴黎非战公约》在有关侵略行为的非法性“如何确定”以及“由谁确定”等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也还没有制定出一套客观标准。(28)参见朱文奇:《东京审判与追究侵略之罪责》,《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除了《巴黎非战公约》,两个军事法庭还在判决中列举了其他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书和实践,以此佐证国际法在此前已把侵略行为视作犯罪,主要包括在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国际法公约和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署的《国际联盟盟约》等,(29)又如:1923年国际联盟所倡导的“互助公约”草案,其第1条便规定,“侵略战争是一种国际罪行”,“任何一缔约国不得犯此罪行”;1924年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议定书”在序言中也宣布,“侵略战争乃(国际社会成员间)团结之破坏,是一种国际性的犯罪”;1927年9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五国代表全体一致通过的一个决议案的序言中宣布,“侵略战争永不应被使用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故是一种国际犯罪”;1928年2月18日在第六次泛美大会中全体一致通过的一个决议案宣称,“侵略战争构成对人类的国际罪行”,等等。参见朱文奇:《现代国际刑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79—480页。还可参见薛茹:《论东京审判中的破坏和平罪》,《国际法研究》2016年第3期。其中都明显地限制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权。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TreatyofVersailles)第227条就已主张追究战争发动者的法律责任,协约国尝试以发动战争和危害人类和平罪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进行审判;尽管历史表明,当时“协约国内部并没有就侵略行为构成犯罪取得实在国际法意义上的一致意见”,第227条的本文被加入了威廉二世“不构成违反刑法的罪行”等措辞,审判依据代之以违反了“国际道义”和“条约的神圣性”……尽管这次审判尝试最终没有取得成功,(30)See Aron N.Trainin,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tlerites,Legal Publishing House NKU,1944,p.45.但其在国际法发展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巴黎和会被视为开启了认定侵略行为违反国际法的大门。(31)参见冷新宇:《国际法上个人刑事责任及模式的早期发展——兼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运用》,《国际法研究》2023年第2期。事实上,远东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把相关国际法律文书列举出来,以此加强论证,早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前,国际法上就已经确立:侵略战争在国际法上是犯罪行为。(32)参见朱文奇:《现代国际刑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82页。
至于能否在国际法上追究个人刑事责任问题,两个军事法庭一致认为: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是现代国际法的发展趋势,相关实践也相当丰富,包括对海盗罪和贩卖人口的惩罚等,前述对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进行审判的尝试也是一个例证;此外,人人有知晓和遵守一切现行法的义务,对法律的愚昧无知并不能作为免除个人罪责的辩护理由。(33)参见朱文奇:《现代国际刑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77—483页。从逻辑上来看,国际罪行在本质上并非由抽象的集体所为,而是由具体个人犯下的,只有定罪处罚犯下如此罪行的个人,才能真正地打击有罪不罚并使国际法规则得到有效实施。(34)参见李将:《国际法上个人责任的法理:制度渊源与价值关联》,《国际法研究》2021年第2期。
如此一来,两个军事法庭适用“破坏和平罪”便是基于现行法(lexlata),既没有适用事后法,也没有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进而,两个军事法庭在各自《宪章》中规定了“破坏和平罪”,便是对当时已经存在的习惯国际法进行“法典化”而已,至于《巴黎非战公约》以及其他国际法律文书中的相关实践,便构成了“破坏和平罪”这一习惯国际法规则存在的证据。(35)国际法委员会“识别习惯国际法”专题的结论第11条第1款归纳了条约对发展习惯国际法的意义。See UN Doc.A/CN.4/L.908 (17 May 2018).
简而言之,如果在两个军事法庭规定“破坏和平罪”并据此追究个人国际刑事责任之前,已经存在足够满足“广泛性、代表性、一贯性”要求(36)国际法委员会“识别习惯国际法”专题的结论第8条规定“惯例必须具备一般性”。See UN Doc.A/CN.4/L.908 (17 May 2018).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证据——即能够证成该项习惯国际法存在的话,那么,两个军事法庭追究“破坏和平罪”的个人刑事责任便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此特定历史背景之下,习惯国际法的存在和经“法典化”后适用恰恰是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前述两个军事法庭列举的证据是否满足了证明习惯国际法存在的标准?特别是在追究个人刑事责任方面。即使存在相关国家实践,那在具体规范层面又能否满足刑事司法所要求的明确性呢?如果从罪刑法定原则在国内刑法领域的具体实践来看,这显然是一个极其高的标准。我们无法忽略的一点是,国际法律体系较之国内法有其特殊性,相较于国内刑法典,习惯国际法始终处于一种演变发展的状态。为了惩治最严重的国际犯罪、打击有罪不罚,尤其在史无前例震撼人类良知的“二战”背景之下,我们无法亦无须完全以国内法的标准来框架国际法层面的罪刑法定原则——这显然具有历史正当性。因此,尽管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在国际法上是开创性的,但破坏和平罪在这两个军事法庭成立之前,在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之后已发展成国际罪行;(37)参见朱文奇:《东京审判与追究侵略之罪责》,《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两个军事法庭根据各自《宪章》的规定对“破坏和平罪”进行定罪处罚,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38)194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95(I)号决议,确认了两个军事法庭《宪章》中所包含的国际法原则。See “Affirm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Recognized by the Charter of the Nürnberg Tribunal”,UN Doc.A/RES/95(I)(11 December 1946).
(二)破坏和平罪与罪刑法定原则:基于自然法的视角
在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中,除了印度籍的帕尔(Radha Binod Pal)法官持不同意见外,(39)在11名法官中,帕尔法官是唯一主张全体被告人无罪的法官。参见中国法院网:《东京审判法官群像》,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09/id/1700403.shtml (2015年9月4日),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5月15日。其余10名法官都主张将侵略行为认定为国际法上的罪行,所有被告亦都负有个人刑事责任。其中,来自澳大利亚的庭长韦伯(Sir William Flood Webb)法官还认为:
国际法可以由正义规则和一般法律原则来补充,僵硬的实在法主义已不再符合国际法。国家之间的自然法与实在法或志愿法具有同等重要性。(40)United States et al. v. Araki Sadao et al.,The Tokyo Major War Crimes Trial:The Record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with an Authoritative and Comprehensive Guide (2002),卷2,“韦伯庭长的分述意见书”,第9页。转引自朱文奇:《现代国际刑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19页。
无独有偶,法国的贝尔纳(Henri Bernard)法官也从自然法的角度论证了侵略行为的非法性,他指出,侵略战争“在常理和普遍良知的眼中是(并且从来都是)一项罪行——常理和普遍良知表达了自然法,一个国际法庭可以而且必须依据这个自然法来判定提交给它的被告之行为”(41)[日]田中利幸、[澳]蒂姆·麦科马克、[英]格里·辛普森编,梅小侃译:《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
贝尔纳法官也认为侵略战争是国际犯罪,被告也犯下了侵略罪;但是,他这一结论是依据自然法得来,而非基于对实在国际法的适用。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韦伯法官和贝尔纳法官在援引自然法时便表明了他们的立场:退一步而言,即使在两个军事法庭设立之前不存在实在国际法可以规范侵略行为,但由于侵略行为显然已违反了“正义规则”“常理和普遍良知”,所以它也是违反自然国际法的行为,必然要被国际社会所惩罚。进而,这亦提醒我们,在考察两个军事法庭实践“破坏和平罪”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时,还有必要把目光流转至自然法这一领域。
我们知道,基于对“国际法效力根据”的不同回答——即国际法何以对国家以及其他国际法主体有拘束力,传统国际法理论有自然法学派(Natural Law School)和实在法学派(Positive Law School)之分。自然法学派盛行于17至18世纪,其主要观点认为国际法产生于人类理性(reason),不需要主权国家的同意,自然法是普遍永恒的;“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Grotius)被视作自然法学派的开山鼻祖,尽管他的学说亦体现出一种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的折中,但他仍是偏向于自然国际法而认为实在国际法是次要的。(42)参见邵津主编:《国际法》(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与自然法学派相对,实在法学派认为国际法的效力根源于国家的共同同意,条约和习惯国际法是国际法的主要形式,即条约是基于国家的共同同意,习惯法是基于国家的默示同意。奥本海(Oppenheim)即持实在法学派观点,他认为各国的共同同意是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国际法的正式渊源只有条约和习惯法。(43)参见[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Ⅴ、8页。李浩培法官也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国际法学家一般都认为国际法完全是任意法,因为国家既然有主权,两个国家就可以协定变更或不适用任何一般国际法规则。”(44)李浩培:《国际法的概念与渊源》,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尽管在20世纪以后又出现了许多其他学派,如新自然法学派、规范法学派、政策定向学派等,(45)参见邵津主编:《国际法》(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但总体而言,它们大多仍是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的变种和延续,传统国际法理论仍可统筹于这两大法学派之下。科斯肯涅米(Koskenniemi)曾指出,“每种学说都有其特定的哲学背景,这说明国际法能够反映出一些深刻的关于世界的规范性真理——或是‘国家主权’(意志说侧重于此),或是关于经济或技术进步、文明或人道动机的潜在趋势”。(46)[德]巴多·法斯本德、安妮·彼得斯主编,李明倩、刘俊、王伟臣译:《牛津国际法史手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956页。
“二战”之后,基于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出现了新自然法学派,其被称为自然法理论的“复活”或“复兴”。努斯鲍姆(Nussbaum)曾在其名著《简明国际法史》中阐述道:
重新乞灵于自然法只是表达了人们察觉到条约和习惯无法完整地描述国际法这一事实,并察觉对于争议问题的判决只能通过推理过程获得,而推理除了给定的实证材料外,还包括有限度地考虑正义和衡平……实证主义,像19世纪与之同源的科学唯物主义一样,曾经太过粗陋,太过强硬。这两者都引起了持续的进步,但是它们都要被修正。在这个时期实证主义仍然支配着国际法学,但它现在是一种“开明的”实证主义。(47)[美]阿瑟·努斯鲍姆著,张小平译:《简明国际法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页。
那么,“考虑正义和衡平”会跟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吗?一方面,追求法的安定性是文明、法治以及正义的前提,不管是判例法抑或成文法国家,也不管是国内法抑或国际法体系,都一致追求法的安定性。(48)参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另一方面,针对“二战”后对“纳粹法律之合法性的认定”这一问题,拉德布鲁赫(Radbruch)在其名篇《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中提出了著名的“拉德布鲁赫公式”:
首先,所有的实在法都应当体现法的安定性,不能够随意否定其效力;其次,除了法的安定性之外,实在法还应当体现合目的性和正义;再者,从正义的角度看,若实在法违反正义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它就失去了其之所以为法的“法性”,甚至可以看作是非法的法律。(49)[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著,舒国滢译:《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1946年)》,郑永流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443页。
客观而言,“拉德布鲁赫公式”不仅激起了自然法学的复兴,而且为“二战”后自然法和实在法的冲突和对抗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折中方案。可以说,这是非常务实的一种学术观点和做法。因此,当我们考察两个军事法庭实践“破坏和平罪”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关系时,如果从自然法的角度来看,“拉德布鲁赫公式”也可以为此提供一种论证思路。亦即是说,虽然我们在前文已从实在法角度论证了“两个军事法庭根据各自《宪章》的规定对‘破坏和平罪’进行定罪处罚,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但退一步而言,即使是实在法层面的论证也难以达到“零瑕疵”——甚至于最终指向“究竟是鸡生蛋抑或蛋生鸡”等哲学问题,(50)毕竟,如在关于习惯国际法的理论中,如何解释由“法律确信”导致的“时序悖论”,迄今在理论界仍然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参见邓华:《国际法院认定习惯国际法之实证考察——对“两要素”说的坚持抑或背离?》,《武大国际法评论》2020年第1期。那自然法仍可为此结论提供“补强证据”,进而形成逻辑闭环——而此时“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法”,自然还包括了“自然法”。
(三)纽伦堡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对破坏和平罪的认定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由此可见,纽伦堡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对“破坏和平罪”的实践不仅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同时这也是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其本身即是对国际法的贡献。在破坏和平罪被两个军事法庭“认定”之前,它事实上已经满足了习惯国际法的构成要素要求,但未曾被“认定”过习惯法的地位,其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争议”;而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认定”实践则终结了这种“地位未明”的状态。自从两个军事法庭作出历史性审判之后,国际罪行在实践中已明确无疑地适用于个人,追究个人国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亦明确无疑地适用于此后所有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个军事法庭不仅开创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实践,而且与此后的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一起,促成了传统国际法上关于国际罪行、个人刑事责任、特权豁免等理论的重大转变,从而对现代国际法、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1)参见朱文奇:《东京审判与追究侵略之罪责》,《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徐持:《重新发现东京审判》,《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2期。
因此,经考察后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严格按照国内刑法的标准来要求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适用,那么国际刑事司法机构适用习惯国际法规则来定罪量刑有可能会被质疑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尤其是涉及习惯法地位和内容尚存“争议”的那一部分规则。但是,如果我们综合考虑到国际刑法的特殊性,以及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区别,那罪刑法定原则跟习惯国际(刑)法的发展就并非不相容;相反,如前文所述,在特定情况下,罪刑法定原则还要求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所适用的法律只能是已经属于习惯国际法的规则。
三、罪刑法定原则与《罗马规约》对侵略罪的发展
(一)“二战”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遵循
一方面,如前文所证,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发展习惯国际法并不会必然导致其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另一方面,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遵循受到“约束”并存有“自觉”。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即《罗马规约》在第22条至24条中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52)参见蒋娜:《国际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新进展——兼及对中国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此外,在谈判《罗马规约》的过程中,各国也曾一致同意,《罗马规约》应反映习惯国际法,而非制定新法。(53)See Philippe Kirsch,“Forward”,in Knut Dormann ed.,Elements of War Crimes under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ources and Commenta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xiii.在司法实践当中,即使存在争议的情况,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也会尽量通过法理分析和逻辑推理来证成其认定、解释和适用习惯法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符合,通过形成逻辑闭环来“自圆其说”和“以理服人”。
譬如,当前南刑庭通过采用“同等严重性(ejusdemgeneris)”的标准来起诉战争罪中的性暴力犯罪时,被告人律师和一些大陆法系的学者对此提出了批判,认为通过该标准把性暴力犯罪行为纳入战争罪是严重违反了“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采用“同等严重性”标准事实上是在实践前南刑庭《规约》第3条:“国际法庭有权起诉违反战争法与惯例的人,违反行为应包括下列事项,但不以此为限……”(54)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Resolution 827 (1993)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3217th Meeting,UN Doc.S/RES/827 (1993),Annex.这一规定往往被视为兜底条款或“口袋条款”。(55)关于“口袋条款”的相关论述,详见前南刑庭在“塔迪奇(Tadi)”案中关于管辖权的中间上诉请求裁定:ICTY,The Prosecutor v.Dusko Tadi,Decision on Defence Motion for Interlocutory Appeal on Jurisdiction,Case No.IT-94-1-AR72,Decision (Appeals Chamber),2 October 1995,paras.86-137.针对这一争议,前南刑庭在司法实践中回应道:“审判庭认真研究了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安理会808号决议所附的报告,该报告认为,适用‘法无明文不为罪’这一原则要求国际法庭适用毫无疑问已成为习惯法一部分的国际人道法。”(56)ICTY,The Prosecutor v. Milomir Stakic,Case No.IT-97-24-T,Judgment (Trial Chamber),31 July 2003,para.411.即在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习惯国际法的做法并不违反“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据此,前南刑庭便得出结论,根据法庭的一贯做法,它并不是简单地依赖《规约》的规定来确定刑事责任的适用法律,而是要认定在罪行发生时有效的习惯法——因为性暴力犯罪作为战争罪中的一种罪行已经演变成习惯法,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本身亦不排斥适用习惯法,所以,前南刑庭可以对性暴力犯罪以战争罪来定罪处罚。(57)参见刘大群:《联合国临时法庭对国际刑法发展的贡献》,柳华文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2018)》,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1页。
又如,在塞拉利昂特别法庭“诺曼(Norman)”案中,当法庭被质疑《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第4条第3款规定的征募儿童罪(58)《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第4条第3款规定:“诱拐15周岁以下的儿童并强行征入武装部队或武装集团,目的是利用他们积极参与冲突。”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时,它的论理分两步走:首先证成禁止征募儿童行为在《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诞生之前已获得习惯国际法的地位;接着证明征募儿童行为应受到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定罪处罚。由此,法庭便通过对国家实践的考察、对相关国际法律文书和其他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案例的援引,明确地为自身“辩护”,即征募儿童罪是习惯国际法,因此法庭适用《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对该罪行的规定并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59)参见何田田:《征募儿童的战争罪:以“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案”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6—104页。
(二)《罗马规约》对侵略罪的发展挑战罪刑法定原则
关于侵略罪,我们知道,尽管它一开始被规定在《罗马规约》当中,(60)《罗马规约》第5条规定了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其中第1款规定:“本法院的管辖权限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本法院根据本规约,对下列犯罪具有管辖权:1.灭绝种族罪;2.危害人类罪;3.战争罪;4.侵略罪。”但《罗马规约》第5条第2款规定:“在依照第121条和第123条制定条款,界定侵略罪的定义,及规定本法院对这一犯罪行使管辖权的条件后,本法院即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这一条款应符合《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即只有在《罗马规约》生效7年后召开的审查会议上,通过侵略罪的定义和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条件后,国际刑事法院才能对侵略罪实际行使管辖权。2010年坎帕拉(Kampala)会议通过了《罗马规约》修正案,由此将侵略罪的定义以及法院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的条件正式纳入《罗马规约》。(61)参见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网站:https:∥www.icc-cpi.int/news/review-conference-rome-statute-concludes-kampala;《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侵略罪修正案》全文见:https:∥asp.icc-cpi.int/sites/asp/files/asp_docs/RC2010/AMENDMENTS/CN.651.2010-ENG-CoA.pdf;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5月5日。对此,有部分国家和学者认为这是国际刑法里程碑式的发展;(62)凌岩主编:《国际刑事法院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7页。但也有部分国家和学者担心,坎帕拉会议通过的侵略罪修正案定义内容存在模糊之处,这种不确定性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63)在1998年罗马召开的“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联合国外交大会”的最后时刻,各个国家仍就如何使侵略罪的定义能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纠缠不休,无法达成共识。See Michael O’ Donovan,“Criminalizing War:Toward a Justifiable Crime of Aggression”,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Vol.30,2007,pp.516-517.且修正案赋权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在联合国安理会没有认定侵略行为的情况下即可开展调查,这一做法也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64)参见《中国代表团在罗马规约审查会通过侵略罪条款的发言》,《中国国际法年刊(2010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页;杨力军:《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的侵略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6页。尽管如此,在坎帕拉修正案仅通过7年之后,即2017年12月14日,《罗马规约》缔约国在第16届缔约国大会上通过一项重要决议,决定国际刑事法院自2018年7月17日起“激活”其对侵略罪的管辖权。(65)See Resolution ICC-ASP/Res.5 on the Activation of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over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New York ASP Resolution),14 December 2017,adopted by consensus a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ssembly of States Parties.
根据坎帕拉修正案,《罗马规约》第8条之二对侵略罪的规定如下:
(一)为了本规约的目的,侵略罪是指能够有效控制或指挥一个国家的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人策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一项侵略行为的行为,此种侵略行为依其特点、严重程度和规模,须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明显违反。
(二)为了第(一)款的目的,侵略行为是指一国使用武力或以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任何其他方式侵犯另一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行为。根据1974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下列任何行为,无论是否宣战,均应视为侵略行为:……(66)参见《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审查会议RC/Res.6号决议,载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网站:https:∥asp.icc-cpi.int/sites/asp/files/asp_docs/RC2010/AMENDMENTS/CN.651.2010-ENG-CoA.pdf,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5月15日。
从《罗马规约》这一新增规定可以看出,侵略罪的定义反映了“二战”之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对国际刑法尤其是侵略罪(破坏和平罪)的重要贡献以及由此确立下来的原则,即在侵略问题上,通过追究个人刑事责任来强化侵略行为的国家责任;侵略行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破坏,它的实施主体只能是国家,但侵略罪只能由个人来实施——这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所确立下来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此外,我们也看到,《罗马规约》关于侵略罪的规定还植入了1974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附件第1条和第3条,这些条款亦反映了习惯国际法的内容。(67)See Roger S.Clark,“Negotiating Provisions Defining the Crime of Aggression,its Element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ICC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Over It”,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0,2009,p.1103.因此,从整体视角来考察,《罗马规约》修正案中对“侵略罪”的规定是重申乃至认定了“二战”以来的习惯国际法,并由此实现了对整体作为习惯国际法的“侵略罪”(“破坏和平罪”)的发展。
那么,国际刑事法院根据《罗马规约》修正案对“侵略罪”进行解释和适用时,能否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罗马规约》修正案中“侵略罪”的“明确性”作进一步分析。
对该条款持支持态度的意见认为:第一,该条款对“侵略行为”的规定兼具抽象定义和具体列举罪状,这种通过把抽象概念和具体罪状相结合的方法,可使法院(包括检察官)在具体罪状的基础上根据抽象概念来处理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侵略行为,因此,该条款既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又能适应情势发展的客观需求,最大程度地满足罪刑法定和惩治国际犯罪终结有罪不罚这两种价值追求之间的微妙平衡。第二,如前所述,该条款援引了1974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这是具有建设性模糊的表述,它使得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在遵循《罗马规约》有关条款的前提下,为判定侵略行为而援引联合国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附件有关侵略定义的除了第1条和第3条之外的其他条款。(68)参见凌岩主编:《国际刑事法院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0页。
而反对该条款的意见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批判:第一,质疑通过把抽象概念和具体罪状相结合的方法会带来法律逻辑上的问题,即,如果认为侵略罪定义对侵略行为的列举已经是穷尽的,那就没有必要再引用联合国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包括抽象的定义亦显得多此一举;如果认为抽象的定义已经清晰得足以适用且达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那对侵略行为进行具体列举便是画蛇添足。(69)See Devyani Kacker,“Coming Full Circle:The Rome Statute and the Crime of Aggression”,Suffolk Transnational Law Review,Vol.33,2010,pp.264-265.第二,如果认为联合国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是整一份被植入侵略罪的定义,那么根据决议第4条的规定,这份侵略行为的清单应该是开放式的,安理会可以决定侵略行为的其他模式,这便增加了侵略罪定义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使侵略罪定义难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不符合《罗马规约》第22条至第24条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安理会将来认定了新的侵略行为模式,但这种模式又未出现在《罗马规约》列举的清单里面,那么被告便可能据此提出抗辩,主张国际刑事法院对这种清单之外的行为模式行使管辖权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70)See Major Kari M.Fletcher,“Defining the Crime of Aggression:Is There an Answer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s Dilemma?”,Air Force Law Review,Vol.65,2010,p.260.第三,联合国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并非针对个人进行定罪量刑,因此在内容上难以满足刑法的特定性要求,也就无法满足罪刑法定原则。(71)参见凌岩主编:《国际刑事法院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0—81页。
那么,《罗马规约》修正案对侵略罪的抽象定义是否足够清晰呢?高度“概念化”本身能更好地界定对象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吗?抑或,“过度”的“概念化”不仅无法满足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反而会导致法律漏洞?还是相反?(72)关于《罗马规约》修正案中对侵略罪的定义(第8条之二)以及国际刑事法院启动对侵略罪管辖权的程序,在诸多细节规定上都存在着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争议和讨论,囿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一一展开。具体可参见凌岩主编:《国际刑事法院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6—99页。我们先假设“高度‘概念化’本身能更好地界定对象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是能够实现的,那目前《罗马规约》修正案对侵略罪的定义是否已经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再假设这一要求也已经达到,那么,进一步而言,如果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会否不利于打击国际犯罪——此处探讨的自然是侵略罪;因为,前文也曾指出,如果安理会将来认定了新的侵略行为模式,但这种模式不仅未出现在《罗马规约》列举的清单里面,亦无法被《罗马规约》的抽象定义所涵射,那么被告便可能以这种情形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来作为抗辩理由——那此时,是因“过度”的“概念化”导致法律漏洞从而不利于打击国际犯罪呢,抑或因“过于严格地”在国际刑事司法中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而导致可能出现国际犯罪的“漏网之鱼”?(73)国际刑事法院的前院长菲利普·基尔希(Philippe Kirsch)曾指出:“创立国际刑事法院,就是要打破这种犯罪、有罪不罚和冲突的恶性循环。” Philippe Kirsch,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1 November 2007.
这便又涉及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当然,在国际法领域,鉴于国际法律体系平行结构的特征,我们更多谈论的是“国际造法(International Lawmaking)”——那么,在目前人类理性范围之内,国际社会能否达成一份既能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措辞逻辑,同时亦能涵盖到所有侵略行为的条文?坦率地讲,要完美地兼顾罪刑法定原则和打击有罪不罚,即使在国内刑法领域,亦是难以百分之百实现的任务,毕竟,社会生活的形态千百万种,立法往往滞后于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成文的法律难以将所有的犯罪行为都事先加以规定。(74)参见陈兴良:《罪刑法定的价值内容和司法适用》,《人民检察》2018年第21期。而当我们在国际社会层面探讨“国际造法”时,其间更是充满了国家之间、国家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的博弈和妥协,乃至有意而为之的建设性模糊,这就使得一个“完美的”无漏洞的条文总是很难出现。(75)事实上,在《罗马规约》体系中,涉及是否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之争议的并不仅仅是侵略罪,而有可能是一个覆盖所有罪行的“全局性”问题,近年来的突出表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如何解释《罗马规约》第23条规定的“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涉及《罗马规约》第78条是否包含量刑基准的问题;其二,在非缔约国根据《罗马规约》第12条第3款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临时管辖的情势中,法院是否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其三,《罗马规约》第7条第1款第11项规定了危害人类罪中“其他性质相同的不人道行为”,这一规定事实上还是存在“口袋条款”问题,对该争议仍需作出解释和回应,等等。囿于主题和篇幅,本文对前述问题不再展开分析,但这些问题仍值得学界和实务部门做持续关注和研究。
进而,这又关涉如何平衡罪刑法定原则和打击国际犯罪这两者间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国际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其外在表达,其根本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打击国际犯罪、终结有罪不罚,这也反映了现代国际法的发展趋势,亦是国际法和国际社会追求的重要价值。一般而言,这两者应是可兼顾且能够共存的,因此,此处我们讨论的显然是“例外情形”。那么,在“例外情形”下,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在极端的例外情形下,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会否为了最终彰显打击国际犯罪的价值而在一定程度上“折中”罪刑法定原则?尤其当认定、解释和适用习惯国际法亦存在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之时。不同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不同的法官,也许会在个案中做出不同的考量,但根据我们在文中的初步考察,亦会发现,自“二战”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至今,罪刑法定原则仍是被普遍遵循的,即使在出现很大的争议时,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仍有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自觉”,并针对具体的“技术性”争议问题通过司法论证推理来“自圆其说”。尽管目前国际刑事法院仍未有调查起诉侵略罪的实例,但通过对照侵略罪的“前身”破坏和平罪以及纽伦堡法庭和远东军事法庭对破坏和平罪的认定、解释、适用和论证逻辑,当然还包括“二战”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传统”,我们可据此进一步预测,国际刑事法院在打击侵略罪这种人类社会最为严重的国际犯罪时,仍会把自身限定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范畴之内。
四、结 语
通过考察“二战”后侵略罪(破坏和平罪)的历史变迁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在发展习惯国际法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回应”并有遵循该原则的“自觉”。一方面,由于习惯国际法在效力范围层面能约束所有国家,所以在特定语境中,罪刑法定原则本身要求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只能适用习惯国际法或“重申了习惯国际法”的条约规则;另一方面,由于习惯国际法本身“不成文”“不稳定”的特性,它始终处于一种演变发展的状态之中,这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规则明确性在形式上存在着相悖之处,亦体现了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的差异性,所以,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通过认定、解释和适用习惯国际法规则来惩治国际犯罪之时,亦需证成该项规则存在的“解释或自由裁量空间”以及“涵摄范围”并不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规则明确性——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证明特定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明确性方面,其标准和要求显然是要高于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因为后者并不受限于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应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界,如果超出了这一界限,则有可能招致合法性质疑;罪刑法定原则亦由此贯穿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对习惯国际法的发展这一命题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