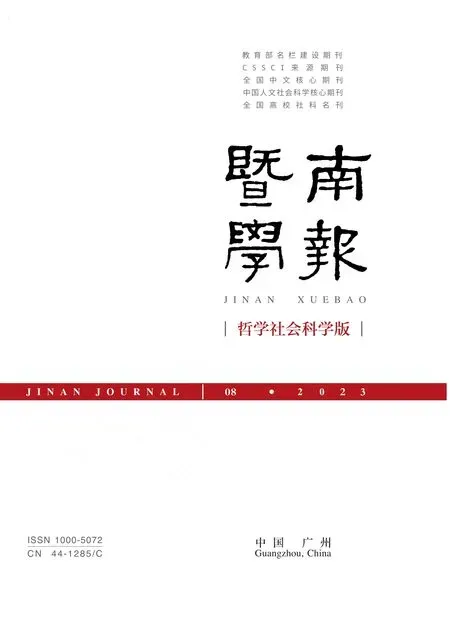论黄锦树“旧家”系列小说对鲁迅《故乡》的再生产
温明明
1997—1998年,马华文坛爆发了一场“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奶水关系”的论战,简称“断奶”论争,马华学者林建国、安焕然、黄锦树、黄俊麟、陈雪风、温任平等参与讨论。这场论争虽然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关系,但它提出来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奶水关系”“要不要断奶”诸如此类问题,对整个海外华文文学来说至关重要。林建国是这场论争中持“断奶”观点的主要发声者,他在《大中华我族中心的心理作祟》(1)《星洲日报》,1998年3月1日,“尊重民意”版。和《再见,中国——“断奶”的理由再议》(2)《星洲日报》,1998年5月24日,“自由论谈”版。两篇文章中反复申论:要解决“创作上困扰我们甚久的‘中国情结’”(3)林建国:《再见,中国——“断奶”的理由再议》,《星洲日报》,1998年5月24日,“自由论谈”版。。黄锦树虽然不是这场论争的主力,但他在论争后期也发表了《一般见识》(4)《南洋商报·南洋文艺》,1998年4月24日。,赞同林建国在《大中华我族中心的心理作祟》中倡导的“断奶”观点。其实在这场论争发生之前,黄锦树已经发表了系列文章(5)黄锦树的这些文章包括:1994年的硕士论文《章太炎语言文字之学的知识(精神)系谱》、1996年出版的专著《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1998年的博士论文《近代国学的起源》以及1998年出版的专著《马华文学与中国性》等。,全面检视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奶水关系,包括对“中国性”的梳理和批判。可以说,黄锦树才是马华文学“断奶”论的真正主力。他的硕士论文《章太炎语言文字之学的知识(精神)系谱》、博士论文《近代国学的起源》、专著《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和《马华文学与中国性》等,确实已经改变了传统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论述,尤其是对马华文学和文化中“中国性”的拆解,影响深远。但如果据此认为黄锦树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已经彻底地屏蔽了中国文学和文化,关在“自己的铁屋子”中埋头创作,显然也是误判,即便是他用力甚深的“中国性”批判,有论者已经指出其中既有失落也有认同:“从中我们窥见的还是大马华人政治/文化身份认同过程中的隐痛和失落,以及黄锦树潜意识中隐含着的作为华人的民族自豪感、优越感等‘中国性’认同。”(6)刘亚群:《经验的毁灭与爱的症候——黄锦树小说中的“中国性”认同透析》,《中国比较文学》2022年第3期。当然,这里无意全面辨析黄锦树的创作与“中国文学和文化”之间新的“奶水”关系,只想以黄锦树“旧家”系列小说与鲁迅《故乡》的关系作为一个个案来探讨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马华作家如何处理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复杂关系。
黄锦树在散文《我辈的青春》中曾饶有意味地说:“也许宿命的,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只能叫作《彷徨》。”(7)黄锦树:《我辈的青春》,黄锦树:《焚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这实际上揭示了他的小说与鲁迅之间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黄锦树十九岁时从马来西亚柔佛州赴中国台湾留学,此后一直工作生活于中国台湾,成为后离散华人,其出生地马来西亚居銮小镇也逐渐演变为“故乡”。黄氏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一开始写小说时以故乡的题材为主,到现在也还是这样”(8)黄锦树:《生命的剩余(自序)》,黄锦树:《焚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三十多年坚持以故乡为题材进行创作,成就了黄锦树在世界华语文坛短篇小说领域的重要影响,也使黄锦树成为“五四”以来现代故乡叙事传统的代表作家之一。
在黄锦树的故乡叙事中,有一个“旧家”系列是比较特别的,包括《乌暗暝》《落雨的小镇》《旧家的火》《槁》《火与土》《土与火》《火与雾》《归来》等小说,它们在叙事上都采用了“归乡/返乡”模式。以往对这批小说多从乡愁美学、身份认同等角度进行研究,但熟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及鲁迅创作的读者均不难发现,黄锦树的这些作品与鲁迅的《故乡》有着很明显的“相似性”。王德威在解读《旧家的火》《乌暗暝》等作品时,就曾指出黄锦树的这批小说在内里是一种鲁迅《故乡》式的写作:“黄锦树《旧家的火》则呼应《乌暗暝》式返乡小说的模式;父亲不在了,母亲株守旧家家园,难以割舍,但究竟时不我予。回乡的游子百感交集,又能如之何。鲁迅《故乡》式的情境,这回搬到马华胶林又演绎了一次。”(9)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黄锦树的马华论述与叙述》,《中山人文学报》2001年第12期。黄锦树在散文《火笑了》中也坦言:“这些小说和私人情感的关系密切,比较抒情,用的也比较接近散文的手法。虽直接来自经验,但它的文学原型也许是鲁迅的《故乡》。”(10)黄锦树:《火笑了》,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页。无论是王德威的“情境”说还是黄锦树的“原型”论,都说明黄锦树的“旧家”系列小说与鲁迅的《故乡》的确存在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用“叙事模式”(即离去——归来——再离去)的相似来概括,背后还有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例如作为东南亚离散华人的后代,黄锦树为什么要一再重写/复写鲁迅的《故乡》?这与他的华人身份和后离散经历是否有关?黄锦树又是如何在传承与变异中实现这种重写/复写的?这些问题既涉及美学,同时也攸关作家个人的伦理观念。
一、经验结构的相似:失乡与父亡
讨论黄锦树“旧家”系列小说与鲁迅《故乡》的关系,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黄锦树要以鲁迅《故乡》为“情境”和“原型”来创作“旧家”系列?相似的问题也可以是:为什么黄锦树和鲁迅在小说创作中都大量以故乡为题材?黄锦树曾夫子自道:“那并不是文学模仿,而是经验结构的相似。”(11)黄锦树:《火笑了》,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页。这揭示了黄锦树要重写鲁迅《故乡》的内在缘由,它甚至逼迫黄锦树不得不用文学的方式去回应由鲁迅《故乡》所建构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与“故乡”之间的复杂纠缠。对于黄锦树与鲁迅的故乡叙事而言,“经验结构的相似”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失乡与父亡。
鲁迅1898年离开家乡绍兴到南京求学,自此开始了“走异路,逃异地”(12)鲁迅:《〈呐喊〉自序》,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的人生之旅。“走异路”“逃异地”所开启的不仅是鲁迅寻求现代性的征程,也包含鲁迅与家乡的逐渐疏离。此后鲁迅赴日留学、辗转北京、南下厦门与广州,最终定居上海,虽在留日归国后的前三年返回杭州、绍兴任教,但家乡对鲁迅而言,已沦为了故乡,尤其是1919年卖掉祖屋举家迁居北京之后,鲁迅与家乡的“脐带”被切断,从而彻底变成了一个漂泊者和失乡者。
黄锦树196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高中快结束时,前途茫茫,更常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苦闷情境”(13)黄锦树:《非写不可的理由》,黄锦树:《乌暗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39页。,为了寻求一条生路,1986年被迫赴中国台湾留学,毕业后也选择就业定居安家于此。黄锦树是第三代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祖父母自中国大陆南来,父亲是土生土长的一代,而我则是国家独立后出生的一代,各自铭刻着不同的时间性”(14)黄锦树:《非写不可的理由》,黄锦树:《乌暗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37页。。黄锦树延续了其祖父母那一代的命运,成为一个新的离散者,当然他的“离散”与那些从中国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先辈有所不同,他是从先辈离散定居之地再度出走,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双重离散的历史记忆,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后离散者。这种后离散经验不仅使黄锦树与原乡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尤其他的后离散之地是中国台湾,某种意义上带有“归返”原乡的意味),也使他与马来西亚故乡逐渐疏离,变成一个类似鲁迅的漂泊者和失乡者。
与故乡的疏离,必然造成在情感和精神关系上与故乡的分裂,即使返乡也很难再融入,只能被迫成为故乡的“他者”或“异物”。鲁迅于1909年8月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后,曾返回杭州任教,后又在1910年7月回到绍兴,直至1912年4月才离开绍兴辗转至北京。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留日期间的“乡愁”在返乡后却变成了“乡痛”,以致在1912年3月7日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将故乡称为“不可居”的“棘地”(15)原文为:“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转引自何巧云:《鲁迅故乡情感之历时考察》,《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8期。,鲁迅与故乡之间的疏离分裂已经不言而喻。这一段重返故乡的经历对鲁迅具有重要意义,使他更清晰地看清了现代性情境下自我与“乡”之间的矛盾缠绕。作为类似鲁迅的失乡者,黄锦树也强烈地感受到了离乡之后与故乡的疏离分裂,这正是他在《落雨的小镇》中借助返乡的“我”所察觉到的:“我深深感觉到两种时间的差异,一旦曾经离乡,即使归来,内里滴滴答答响着的也是异时的时钟。”(16)黄锦树:《落雨的小镇》,黄锦树:《乌暗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1页。“两种时间的差异”和“异时的时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黄锦树:自己已不属于故乡。这一惨烈的事实背后是每一个失乡者都必须承受的精神之痛:与故乡的撕裂。黄锦树在散文《火笑了》中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痛苦:“对我(及弟弟妹妹)而言,离开意味着撕裂。那时我还很年轻,还不知道时间的力量这么可怕。”“二十多年过去后,我才渐渐知道,很多留台人离乡赴台的背后,都有一个撕裂的故事,尤其是家境不好的。”(17)黄锦树:《火笑了》,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页。
如何处理这“撕裂的故事”?“有的人借写作抒发,但更多人选择沉默,甚至原来有写作的也突然放弃了,以沉默的硬壳把伤口封起来。那沉默也是很悲伤的。”(18)黄锦树:《火笑了》,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页。鲁迅和黄锦树都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将失乡者“撕裂的故事”转化为文学,利用书写故乡来弥合失乡所带来的精神裂痕。“经验世界一直在发生激烈的变动,甚至变故,我找不到其他回应的方式——但遗忘是更多人会选择的方式。有些细节——甚至是无关痛痒的——我不想把它忘记,只好封存在小说里,在真幻之间”(19)黄锦树:《沉重的没有》,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87—188页。。鲁迅与黄锦树在创作中书写故乡,与他们的失乡体验有关,“那几乎已是写作的理由本身”(20)黄锦树:《生命的剩余(自序)》,黄锦树:《焚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除了失乡体验之外,父亡对鲁迅和黄锦树故乡叙事也产生重要影响,可把它视为黄锦树与鲁迅“经验结构相似”的另一项内容。《〈呐喊〉自序》历来被鲁迅研究界极为看重,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成为后人揭开鲁迅创作的一把钥匙。《〈呐喊〉自序》第一段讲的是年青时与故乡有关的梦,说明“故乡梦”在鲁迅创作中的重要意义;第二段则转向写父亲的病及其亡故,这同样说明“父亡”在鲁迅的写作生命中也具有重要价值。黄锦树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到了鲁迅创作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文学传统的独特内质:“鲁迅的文学也是写在父亲死亡之后(但我们其实开始得更早)。《〈呐喊〉自序》里鲁迅即沉痛地写到他父亲的病以致亡故,他的被迫离家、长兄为父地承担起一切。因此以鲁迅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文学,也可以说是父亲死亡之后的文学。”(21)黄锦树:《沉重的没有》,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页。
在黄锦树看来:“也许每个父亲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世界,端看我们是否有能力把它建构起来。父亲身世投影出来的深宅大院,有老树浓阴。那也是孩子虔心为他一砖一瓦搭建的墓穴,他未了的梦想。亡者的赠礼同时也是生者给逝者的爱的赠礼。若无力或无心建构就没有遗产可供继承,只剩下无端受之于父母的,易朽的身体发肤。”(22)黄锦树:《亡者的赠礼及其他》,黄锦树:《焚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那么,“父亡”给鲁迅的赠礼是什么?“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2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呐喊〉自序》第三段的这第一句话,或许就是鲁迅所承受的沉重的“赠礼”。父亲的早亡,不仅使鲁迅过早地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也使他的小说基本处于一种“无父”的状态,包括《故乡》。“无父”恐怕也是鲁迅《故乡》建立的现代故乡叙事传统的一个重要内核,其深层的隐喻和象征不容小觑。值得注意的是,黄锦树的“旧家”系列,几乎也是“无父”或“父正在死亡”的状态。
黄锦树的父亲英年早逝,对他而言,“父亡”直接的后果是加快了“旧家”的衰败:“父亲过世后不久,故家毁于火,像我一样深感失落的想必也大有人在。”“没料想旧家会毁,也没想到一家人会散得那么彻底。死者死矣,活着的也少相互闻问。”(24)黄锦树:《关于旧家的照片》,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页。在黄锦树的故乡叙事中,“另一个关键是父亲的死亡”(25)黄锦树:《沉重的没有》,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页。。父亡不仅使黄锦树从此必须面对父亲“缺席”的残酷现实,也迫使他去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的故乡叙事。“父亲”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生前没有积累下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父亡”后,除了“死亡”本身以及那随时都会变成废墟的“旧家”,“我”没有任何遗产可继承。
黄锦树将父亲的死亡作为一个象征来思考整体的马华文学,正如他用“父亡”来思考鲁迅及整个现代文学一样。他发现生命中的“父”与文学中的“父”几乎可以等而视之:“马华文学什么累积都没有,就只有冒着烟的废墟——我们必须继承那沉重的没有,那欠缺。”(26)黄锦树:《沉重的没有》,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页。面对这个“沉重的没有”,作为写作者的黄锦树只能纵火烧芭、替父写作,“在马华文学里,我必须成为自己的父亲,才能再度成为儿子”(27)黄锦树:《沉重的没有》,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页。。因而黄锦树曾将他的另一篇小说《如果父亲写作》视为“这故乡系列的终点之一”(28)黄锦树:《沉重的没有》,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页。,这个终点当然是美学或文学史意义上的,黄锦树试图为马华文学史重新确立一个故乡叙事的“起点”,这个“起点”无疑包含了他视之为“原型”的鲁迅的《故乡》。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回答:为什么黄锦树要在他的“旧家”系列中一再重写或复写《故乡》?因为他要“不断的回到开端,重新出发”(29)黄锦树:《沉重的没有》,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页。。当然,黄锦树对鲁迅《故乡》的不断重写或复写,对于《故乡》所确立的这条现代文学传统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不断地回到《故乡》和小说中的‘故乡’这一‘开端’,通过将各自的故乡置于自己人生和写作的‘开端’,《故乡》和‘故乡’的‘起源’意义,被不断再生产。”(30)卢建红:《作为“开端”和“起源”的〈故乡〉》,《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当然必须指出,黄锦树对鲁迅《故乡》的再生产是建立在两个不同时代(当代与现代)和身份(马来西亚华裔后离散作家和中国作家)的作家“经验结构的相似”的基础上,二者只是相似而并非相同。黄锦树与鲁迅的经验结构除了具有相似性,也还存在许多差异性,例如两人所面对的历史语境、时代命题、文化环境乃至抵抗对象等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导致黄锦树“旧家”系列对鲁迅《故乡》的重写,既有接受也有变异。
二、“反故乡”风格:哀怒与哀悼
黄锦树的“旧家”系列和鲁迅的《故乡》写的都是“失乡者”的返乡故事,黄锦树“旧家”系列的多篇小说,如《旧家的火》《火与土》《火与雾》等也都沿用了鲁迅《故乡》“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叙事模式,他们在小说中呈现的“故乡”也都是“反故乡”的:“《故乡》在中国文学中开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叙事风格与模式——即颠覆和瓦解游子归乡文学的温情美好、乡情眷恋的叙事传统和模式。……《故乡》所表达的‘反故乡’模式,是典型的现代性文本和叙事。”(31)逄增玉:《启蒙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诉求及其悖论——以鲁迅的〈故乡〉为中心》,《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
鲁迅《故乡》的开头,为我们描绘了一位离乡二十余年之人返乡后看到的故乡风景: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32)鲁迅:《故乡》,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页。
“返乡者”满怀期待重回故乡,但他看到的却是“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满心的期待变成失望,以致“心禁不住悲凉起来”。“萧索”“荒村”和“悲凉”,使我们看到了一幅有别于传统“归乡”文学中的故乡景观。
黄锦树“旧家”系列小说所呈现的返乡者看到的旧家景观,与鲁迅《故乡》极为相似。例如《火与土》中,念旧的“我”带着儿子重返自己的旧家,但触目所及却让“我”“大吃一惊”:
路到了尽头,眼前的景观却令人大吃一惊。
熄了火。在门的位置前停下,但大门早不见踪影。
“到了吗?这是什么地方啊?”
两间木屋都不见了,只见一片废墟。乱木横陈,有的是樑,有的是柱,有的是墙板。有的已成炭,有的半成炭。烧余的铁皮残片,生锈反卷。……
“爸爸,你的老家呢?”儿子问。
腾出来那么大的空间,令人错愕。以前被房子遮蔽的,一眼就看到了。譬如那些和家园一样老的杨桃树。那棵高大,吝于结果的红毛丹树。那棵正值盛年的山竹,层层浓阴,占了半边天空,俨然树王。
“这就是了。毁了。”
“为什么毁了?”
“有人放火。”(33)黄锦树:《火与土》,黄锦树:《土与火》,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我”带着儿子“披荆斩棘”回到儿时的“旧家”,但路到了尽头看到的却是一片“废墟”,“旧家”被“毁了”。《火与雾》中的返乡者回到“旧家”后,“有一种说不出的衰败的感觉。那胶园里的旧寮子还在,还是水泥的墙,陈旧如废墟。”(34)黄锦树:《火与雾》,黄锦树:《鱼》,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44页。《旧家的火》中的返乡者在暗夜回到“旧家”,“新月的微光中,仿佛经过一场灾劫,不可思议的荒凉。”(35)黄锦树:《旧家的火》,黄锦树:《由岛至岛》,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黄锦树在“旧家”系列呈现的“旧家”:衰败、荒芜、荒凉、陈旧如废墟,这是鲁迅《故乡》景观在南洋的另一个版本。
可以说,王德威所谓的“情境”和黄锦树指认的“原型”,其深刻内涵是指黄锦树“旧家”系列小说延续了鲁迅《故乡》的“反故乡”风格。黄锦树笔下的“旧家”和鲁迅笔下的“故乡”都呈现出“荒村”似的压抑、衰败与荒凉的色调,这是他们的共性,也是黄锦树“旧家”系列小说对鲁迅《故乡》传承和接受的突出表征。但是,在“反故乡”这一共性背后,两者也存在许多差异,这些差异正好反映了黄锦树“旧家”系列小说对鲁迅《故乡》的接受充满再生产性。
其一,阅读鲁迅的《故乡》,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两个故乡:过去的和现在的故乡,前者以少年闰土为中心,后者以中年闰土和杨二嫂为中心(36)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细读黄锦树的“旧家”系列小说,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两个故乡,但这两个故乡已不是《故乡》中时间范畴上的过去与现在,而是华人移民史意义上父辈的故乡和子辈的故乡。
黄锦树“旧家”系列中,父辈与“故乡”的关系更多体现为第一代移民与土地的关系,他们是“树的时代”,扎根土地是他们共同的信仰,那也是一个落地生根、建立家园并重新获得“故乡”的过程。《旧家的火》中,“父亲种植的观念十分原始,以为种子埋入土地,会发芽就表示它被土地接受,也接受了这异乡的土地”(37)黄锦树:《旧家的火》,黄锦树:《由岛至岛》,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种子被土地接受和接受土地的过程,是海外华人在东南亚落地生根建立新家园的过程,也是异乡变故乡的过程。因而,“父亲一直不愿意离开这里,这是他退无可退的最后立足之地”(38)黄锦树:《旧家的火》,黄锦树:《由岛至岛》,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晚年即使重病也不愿离开自己辛苦垦殖的土地,“这是他唯一的舞台,有着清楚的界域,明确的物质表征”(39)黄锦树:《旧家的火》,黄锦树:《由岛至岛》,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死也要死在芭里”(40)黄锦树:《旧家的火》,黄锦树:《由岛至岛》,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甚至在身体健康时已经在芭里为自己挖好了一个黄土坑,准备死后长眠于此,用来抵抗死亡所带来的“失去土地”/“失去故乡”的命运。但悲剧性的是,死后的“父亲”并没有被自己的子辈安葬在生前选好的地方,而是被葬在了一片新开发的坟地之中,对“父亲”而言,那是一个陌生的、非故乡的所在,最终,父亲仍然没有摆脱“失乡”的命运。子辈与“故乡”的关系,则更多体现为对“家”的记忆上,“树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今是鸟的时代”(41)黄锦树:《旧家的火》,黄锦树:《由岛至岛》,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离开父辈的土地飞向更广阔的的世界是他们的共同追求,“飞走”的那一刻意味着他们不断远离“故乡”的开始,并最终沦为“失去家园”和“失去故乡”的一代。
黄锦树笔下的“两个故乡”,其内涵与鲁迅《故乡》已有很大不同。同时,即使在黄锦树的笔下,父辈的故乡与子辈的故乡以及两代人与故乡的关系也存在本质性的差别,这揭示出鲁迅的《故乡》作为“起源”和“开端”,在离散南洋之后,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当然,黄锦树关于“两个故乡”的叙事也进一步丰富了鲁迅《故乡》的内涵及其文学传统。
其二,鲁迅笔下的“故乡”衰败与愚昧相连,叙述者充满悲凉与哀怒两种心绪;而黄锦树的“旧家”则是衰败与危险并存,叙述者兼具哀悼与恐惧两种情绪。
鲁迅《故乡》中,在表现故乡衰败的同时,也通过刻画闰土和杨二嫂尤其是中年闰土的“异化”,揭示了故乡的愚昧与落后,反映了鲁迅改造国民性和重建文化家园的启蒙诉求。鲁迅站在启蒙的立场上书写故乡,使他面对故乡的衰败时心生悲凉之情,看到故乡人的愚昧后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充满批判意味。反观黄锦树的“旧家”系列,黄锦树摒弃了鲁迅的启蒙视角,围绕“家”和“家人”展开叙事,写“旧家”的衰败和父辈对土地的感情,没有愚昧与落后,反而渲染了大量的“危险”,充满哀悼与恐惧之感。
鲁迅面对故乡的衰败和愚昧,既哀又怒,黄锦树面对“旧家”的衰败和亡者,则既哀又悼,两者似乎相似,但怒与悼的细微差别还是反映出了鲁迅和黄锦树对书写故乡的不同诉求。学界对鲁迅《故乡》中的“怒”已有许多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而将重点放在黄锦树的“悼”上。黄锦树在《由岛至岛》的“后记”《错位、错别、错体》中提出:“在我辈,所有已写下、将写下,未写下的,亦都可说是悼逝之书,悼其已将亡、悼其将亡、悼其未亡、悼其必亡。”(42)黄锦树:《错位、错别、错体》,黄锦树:《由岛至岛》,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黄锦树“旧家”系列也是一部“悼逝之书”,所谓“逝”即“逝去”或“失去”,他借助对“旧家”的书写来哀悼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逝”:“家乡”变成了“故乡”,“家园”沦为了“旧家”,“父”亡而“亲”不再,自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失家”者。“鲁迅的《故乡》是个句点,但我的《故乡》是连串的逗号。鲁迅的故乡只剩空屋,回去卖祖宅,但那房子基本上还在。但我见证的其实是一个世界的彻底消失,每个人都有的基本舞台,家的瓦解。如此彻底,最终房子烧掉了,成烬余的废墟。那是我当年离家时再也想不到的,有一天会‘无家可归’,满满童年记忆的地方云散烟消,树也砍掉了。”(43)黄锦树:《沉重的没有》,黄锦树:《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页。黄锦树的“悼”没有对故乡的批判,更多的是对失去家园的一种悲痛。
鲁迅对故乡的失望部分源于它的愚昧与落后,这对深化这部小说的启蒙主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黄锦树没有鲁迅那样的启蒙焦虑,但作为离散华人后裔,黄锦树也有自己的“忧患”,这使黄锦树的故乡书写充满“杀气”:“不论讽刺白描或乡愁小品,你都感觉字里行间溅着血光。大马华人的一页页历史,充满杀伐暴力,当然让年轻的作家轻松不起来。”(44)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黄锦树的马华论述与叙述》,《中山人文学报》2001年第12期。“血光”“杀伐”与“暴力”化为无形的危险和恐惧,弥漫在黄锦树的“旧家”系列中。
“旧家”中的危险和恐惧都不是凭空捏造,而直接来源于黄锦树的童年体验:“从有记忆开始,对夜里的胶园都会感到莫名的恐惧。我家没有邻居,最近的一户人家也隔了好几块胶园,望不见对方的灯火。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除流萤外,家是唯一的一盏灯。仿佛随时伺机而出的恐怖就潜伏在那难以穿透的黑暗之中,虽然老虎狗熊之类的猛兽已不大可能出现,眼镜蛇、蝎子、蜈蚣等已构不成威胁,最怕的其实是人,陌生人。基于安全的考量,养了许多狗。不管多早或多深的夜里,每当狗儿厉吠,全家人都会顿时神经紧张地站起,准备好手电筒,再严重些,则是拿起部落时代的武器,戒备着。所以,常在睡梦中莫名的惊醒,常为黑暗中突然出现的灯火而紧张,因为谁也看不见谁。总会有一些宵小、赌徒、吸毒者(‘白粉仔’)到处寻找下手的机会。家里也不乏女性,付不起疏忽的代价。”(45)黄锦树:《非写不可的理由》,黄锦树:《乌暗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38页。《乌暗暝》《非法移民》和小说集《雨》,记录的正是黄锦树童年时代“旧家”生活的危险和恐惧。
《乌暗暝》中,一面是慈祥的母亲在“火笑了”中不断召唤子女归家,一面是离乡的游子在暗夜中赶着返乡的路,在两个场景的穿插叙事中,一股浓浓的危险和恐惧氛围逐渐弥散开来,并控制着游子的心理活动,以致对家的期盼逐渐让位于对家人安全的担忧和焦虑,离家越近,这种紧张情绪就越强烈:“走过几户邻家之后,他心里突然有一股莫名的不安,狗的吠叫和灯火的紧张,无端地制造了恐怖气氛——仿佛什么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他突然疯狂地担心起家人,尤其当他走到应该可以看见家的灯火的地方竟然几乎无法确定家的位置。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逃出这一片黑暗,只有奋力朝家的方向狂奔而去。”(46)黄锦树:《乌暗暝》,黄锦树:《乌暗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399页。这篇小说为黄锦树的“旧家”系列染上了一层恐怖的色调,正如王德威所言:“‘近乡情怯’式的故事我们看多了,但少有作者能把游子心中的迷离恐惧写得如此寒意袭人。”(47)王德威:《坏孩子黄锦树:黄锦树的马华论述与叙述》,《中山人文学报》2001年第12期。
黄锦树“旧家”系列所描写的危险与恐惧,并非只是作者童年经验的复现,它在记录黄锦树“旧家”童年记忆的同时,充斥其间的暴力与灾难也将其故乡叙事由现实导向了历史:“伴随着连串的历史的灾难,现代问题却映照了人类历史的古老问题:恶的显现与暴力的反复重现,且在历史中展现出极大的力量。而它发生的现场或原址,总是被命名为故乡,或作为它的隐喻。使得作为欲望的能指的它深深的凹陷下去,把其他的一切牢牢的吸附进去,如同欲望的黑洞。”(48)黄锦树:《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台北:麦田出版社 2006年版,第322页。这个“黑洞”对黄锦树而言,即是马来西亚华人所遭遇的种族政治和族群伤痛,“从隐喻到直接去触及,从夜的恐惧到政治遭遇,不过是一步之遥”(49)黄锦树:《非写不可的理由》,黄锦树:《乌暗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41页。,“‘胶林深处’的生活,不正隐喻了大部分大马华人长期生活在敌意的环境下的无名恐惧?兢兢业业的过日子,任何时候,一瞬之间就可能让它化为乌有。”(50)黄锦树:《非写不可的理由》,黄锦树:《乌暗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40页。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回答:同样是“反故乡”风格的写作,为什么鲁迅的《故乡》只能作为“情境”和“原型”被黄锦树的“旧家”系列所接受?因为鲁迅和黄锦树的“反故乡”写作最终抵达了不同的象征领域:前者是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后者是离散华人的族裔伤痛。
三、“我们称之为路的,其实不过是彷徨”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51)鲁迅:《故乡》,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页。鲁迅在《故乡》结尾提出的“路”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反映了叙述者在返乡的绝望中“探索新路的勇气”(52)孙伟:《文化重建的起点——论鲁迅笔下的故乡》,《文艺研究》2018年第1期。。这使得此后在有关《故乡》的重写中,也不得不思考“路”的问题。黄锦树的“旧家”系列自然也传承了鲁迅《故乡》确立的这一叙事传统,《乌暗暝》《旧家的火》《火与土》《火与雾》等小说都花费了不少笔墨描绘和刻画通往“旧家”的“路”。但黄锦树也深知,作为后离散华人的自己所要面对和处理的“路”与鲁迅的“路”已有所不同:“自有中国(或中文)新文学以来,故乡很显然便呈现为尖锐的问题。鲁迅的《故乡》标明了此一精神史的起点,作为路标,恰如其分的结以‘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指出了整个问题其实关键在路,世间之路,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但鲁迅的精神漂游仍限于国土之内,几个急速现代化中的城市,还未及真正的边城——虽也曾留日,游香港——及经历更惨烈的失根失乡(‘文化大革命’)、被殖民及分裂国土(如台湾)中的暴力,及从华侨到华人的移民受虐的文化情境,都让整个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53)黄锦树:《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台北:麦田出版社 2006年版,第321页。可以说,黄锦树正是“从华侨到华人的移民受虐的文化情境”去重写鲁迅《故乡》的“路”。
黄锦树“旧家”系列对鲁迅《故乡》“路”的重写首先体现在改写“路”的现实处境。在黄锦树的“旧家”系列小说中,“路”的命运是逐渐隐没在草丛灌木中,并最终被自然所征服,直至消失。例如《火与土》,带着儿子重返“旧家”的我发现,由父亲开辟出来通往“家”的路已经隐没在高草灌木之中;《旧家的火》中,通往旧家的路被漆黑的夜和深浓的雾所遮蔽阻断,“深更的路和夜溶成一片,只有灯火可以将它勉强离析”,以致“回家的路”不再熟悉而变得极其陌生,“路像久别的故友,彼此在时间中都已变了很多,不再无话不谈”(54)黄锦树:《旧家的火》,黄锦树:《由岛至岛》,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这与鲁迅《故乡》中的“路”的命运是决然相反的,在《故乡》中,“路”原本并不存在,但“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而在黄锦树的相关小说中,“路”原本存在,旧家的荒芜,导致“走的人少了,自然就没有了路”。
鲁迅《故乡》中的“路”是与“希望”紧密相连的,“路”代表着“未来”。但黄锦树从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情境出发,却解构了“路”的象征内涵,“路”不再通向“希望”,反而直达危险和恐怖,例如《乌暗暝》中那位在暗夜中拼命赶路的返乡者,他每走一步路,就离危险和恐怖近了一步。“常常感伤的想,我们这一代只怕很快又老了,有形无形的阻碍那么多,究竟能不能杀出一条血路呢?还是最终不过像命案的现场,只留下一滩血而已?人走多了也不过是多些肮脏的脚印而已,并不一定就是路。”(55)黄锦树:《错位、错别、错体》,黄锦树:《由岛至岛》,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黄锦树的这段戏谑之语,表面上是对鲁迅《故乡》“路”的解构,但放在马来西亚华人受困的文化情境中来看,又何尝不是揭露了一个血淋淋的真相呢:“我们成长于(大马)历史终结之后:精钢铁笼已造好了,此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件,只有无力的挣扎与无用的感叹。呐喊过,彷徨过,接着以冷嘲。”(56)黄锦树:《生命的剩余(自序)》,黄锦树:《焚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黄锦树“旧家”系列中的“路”和鲁迅《故乡》中的“路”都带有隐喻性,但二者由“路”所引发的思考却并不相同。鲁迅《故乡》对“路”的言说,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探寻改变中国的可能性;黄锦树没有从启蒙的视角看待“路”,而是从离散华人的立场出发,视“路”为“一种潜在的历史叙述”(57)黄锦树:《光和影和一些残象》,黄锦树:《焚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即从“路”的历史来反观马来西亚华人的移民历史。黄锦树“旧家”系列中的“路”是祖父及父亲等早期华人移民在垦殖拓荒时披荆斩棘开辟出来的,它所抵达的“家”是这些华人移民在当地落地生根的见证。当然,“路”也是会变的,“多年以后当新路依着几何的原则和一些暧昧的政治隐喻不顾一切的笔直割进以后,原先的路像被斩成数截的蛇,某些段落迅速淹没在落叶和泥沙之中,草赶紧覆盖”(58)黄锦树:《光和影和一些残象》,黄锦树:《焚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裹挟着种族政治的“新路”横冲直撞,“原先的路”迅速消失,被还原成自然,以致后来者已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一条路。“新路”和“旧路”的对抗,是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华人命运的重要象征,“旧路”的消逝,不仅抹去了当年垦殖拓荒一代华人移民的足迹,也删除了几代华人共同的家园记忆,其背后还包括更为惨烈的华人族群历史的消逝。在黄锦树的“旧家”系列中,“路”不再象征希望和未来,恰恰相反,它是面向绝望和过去的,“路”的此消彼长,是马来西亚华人境遇最好的见证和象征。
黄锦树对鲁迅《故乡》“路”的重写、逆写和改写,最终也指向了自我,借此反思自己所处的这一代马来西亚华人的“出路”。“浓雾里摸着石头过河的我们,一步步涉水前行,隐隐有重山的阴影,根本就不确定路在何方。阳光偶尔穿过云间,照出诸物的实相。但一回头,那过去的、如今已是茶黄色旧照片里的世界,却随同我们的青春蓦然崩塌了,崩塌的现场如巨大的陨石坑。”“有时也不确定自己真正在做什么,毕竟走过的路很快又被顽强的野草埋没,前方又是一片阻断视野的荒莽。”(59)黄锦树:《我辈的青春》,黄锦树:《焚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找不到方向,看不到未来,又回不到过去,这注定是悲剧的“没有出路的一代”。黄锦树在小说《祝福》中,曾引用卡夫卡的一句话作为整个小说的题记:“我们称之为路的,其实不过是彷徨。”(60)黄锦树:《祝福》,黄锦树:《鱼》,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5页。“彷徨”也是黄锦树重写鲁迅《故乡》的“路”最终抵达的地方,它揭示出黄锦树在面对马来人强大的种族政治时的悲观无助,“也许宿命的,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只能叫作《彷徨》。”(61)黄锦树:《我辈的青春》,黄锦树:《焚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当然,虽然黄锦树清醒地意识到所有的路都不过是彷徨,每一部作品最后也都变成了《彷徨》,但他仍然坚持写作,仍然在写作中坚持回到“旧家”,他身上有类似鲁迅式的反抗绝望的精神气质,面对强大的马来国家机器,黄锦树选择不退步、不低头、不沉默,这样“彷徨”式的写作又何尝不是一种抵抗的姿态乃至策略呢。
结 语
黄锦树对鲁迅的重写,或者说对鲁迅遗产的吸收转化,不仅体现在他的“旧家”系列对鲁迅《故乡》的接受与变异这一个方面,还包括他的《伤逝》(1990)和《祝福》(2014)对鲁迅两部同名小说的“复写”,以及《他说他见过鲁迅》(2018)等对“南洋左翼鲁迅”形象的拆解,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黄锦树对鲁迅及其文学传统的再生产,限于篇幅关系,本文只讨论第一个方面。但我们从这一个方面仍然能够窥探出黄锦树对鲁迅及其文学传统的基本立场和再生产的方式。整体而言,黄锦树对鲁迅《故乡》及“鲁迅遗产”的再生产,经历了一个反思和去魅的过程,他摒弃了马华左翼现实主义文学把鲁迅建构成“政治鲁迅”和“革命鲁迅”的传统,试图回到一个真正的“文学鲁迅”,从诗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并再生产鲁迅。
黄锦树旧家系列小说对鲁迅《故乡》的再生产,并非只是为了还原或回到“文学鲁迅”,更不是为了在南洋为鲁迅树碑造像,黄锦树实际上是以“鲁迅”及其所象征的中国现代(故乡)文学传统为方法,“置入南方经验与视角、交织美学形式与伦理承担、汲取前作养分并化为己用”(62)张康文:《“诗性鲁迅”与“政治鲁迅”之间:论黄锦树的“南洋鲁迅”重构》,《台大中文学报》2022年第72期。,以此重新进入马来西亚华人史和华人族群所面对的诸多结构性困境,因而黄锦树宣告鲁迅等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实际上已经“死在南方”,“我们必须跨过当年南来文人的尸体往前走,批判地继承他们的遗产,故事必须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借用冯友兰关于思想史解释的有名切分),必须远远地超越他们的限制”(63)黄锦树:《跋:死在南方》,黄锦树:《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页。。这一点与黄锦树对郁达夫的重写极为相似,他也是以郁达夫为方法,来审视和处理马华文化和文学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在黄锦树看来,郁达夫在南洋的“失踪”,为这一区域“留下了一个象征性的技术难题”,成为一笔“更深刻更悲哀但也更难继承的遗产”(64)黄锦树:《跋:死在南方》,黄锦树:《死在南方》,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76页。。面对这笔“郁达夫遗产”,黄锦树从马华文学史起源的角度对它进行了转化吸收,他认为,“死在南方的郁达夫在星、马、印华文文学的始源处凿出一个极大的欲望之生产性空洞”(65)黄锦树:《另类租借,境外中文,现代性——论马华文学史之前的马华文学》,黄锦树:《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64页。,“经由他的献祭,或许我们也可以重新命名马华文学/史的起源”(66)黄锦树:《另类租借,境外中文,现代性——论马华文学史之前的马华文学》,黄锦树:《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台北:麦田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在《死在南方》《零余者的背影》《补遗》等“郁达夫书写”系列小说中,黄锦树用文学书写的方式承接了他对郁达夫与马华文学史起源的辩证理解,他在这些小说中反复操演郁达夫的失踪,就是为了通过这种“献祭”书写,完成他对马华文学史起源的重新问题化。而黄锦树“旧家”系列小说对鲁迅《故乡》的再生产,同样凸显了他对马来西亚现实的各种忧患和反省,无论是鲁迅还是郁达夫以及他们背后所象征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在黄锦树的小说中,都是作为观照马来西亚华人的“方法”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