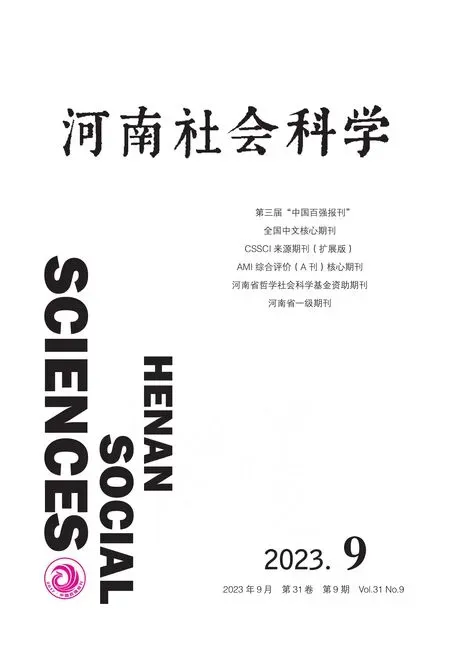唐钞本《文选集注》所见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
——兼论陆机的悲剧命运
冯 源
(河南工程学院 人文政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西晋太康十年(公元289)[1],吴人陆机携其弟陆云北赴京都洛阳求仕,至公元303 年陆机因兵败被谮而惨遭杀害,其间历时约15 年。在这段时期内,陆机在文学上与洛阳士人比肩诗衢,创作出大量广为传诵的诗篇,文名大盛,被钟嵘誉为“太康之英”[2]。对于这么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青年才俊的悲剧命运,学界历来广为关注,如史界名宿周一良先生指出:“综观陆士衡一生出处及其致祸之由,似不能不联系其出身吴人考察之也。”[3]77王永平先生认为,陆机“在北方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有力的援助,终于遭到杀身灭族之祸”[4]。还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①,均堪称洞见,然不同程度忽略了西晋时期文学作品中所承载的重要信息。千禧年之际,周勋初先生从日本将唐钞本《文选集注》较为完备之版本传回中国,这套珍贵文献中所载左思、陆机、潘岳的诗文及注解,为此论题提供了一个更加宏阔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的历史细节。今分别以唐钞本《文选集注》中所收录的《三都赋序》注、《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注、《答贾长渊一首》注等为视点,详加比勘、对照,厘清文学作品中呈现的西晋时期南北士人的文化冲突点,进而对陆机的悲剧命运有一更为全面、深刻的认知。
一、《三都赋序》注对“三国争统”②文化背景的揭示
公元280年,西晋平吴胜利,彻底瓦解三国鼎立之势,缔造出大一统之王朝。在政治、军事上取得霸主地位的西晋王朝,是否在文化上亦具备无可辩驳的优势?借助左思的《三都赋序》注,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唐钞文选集注·三都赋序》“左太冲”下有两条注解:
《钞》曰:“王隐《晋书》曰:左思少好经术……博览诸经,遍通子史。于时天下三分,各相夸竞,当思之时,吴国为晋所平,思乃赋此三都,以极眩曜。其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后乃成之。”[5]3-4
吕向曰:“三都者,刘备都益州,号蜀;孙权都建业,号吴;曹操都邺,号魏。思作赋时,吴蜀以平,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也。”[5]4
此两条注解信息量很大:第一条《钞》注引王隐《晋书》,指出左思创作《三都赋》的背景“于时天下三分,各相夸竞”,赋成于西晋平吴之后,左思作此赋的目的是“以极眩曜”;第二条吕向揭橥三都具体所指,亦强调《三都赋》成于平吴之后,并指出左思作此赋的初衷是“见前贤文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这里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三都赋》创作的文化背景:三国“各相夸竞”的是什么?“前贤文之是非”又是何指?
《唐钞文选集注》中《三都赋》集中记载了蜀国和吴国的“夸竞”言辞。《蜀都赋》中西蜀公子言于东吴王孙曰:“盖闻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跱。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5]14接之夸赞西蜀的地势、物产、风俗、文教之美,在篇中出语惊人:“焉独三川,为世朝市?”《唐钞文选集注》注云:“刘逵曰:张仪曰: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李善曰:……韦昭《汉书》注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吕延济曰:……三川,谓东京也。”[5]74三川,指周人旧居,地位正统,此处专指洛阳,即魏国都城。洛阳自古以来被视为“天下之中”,是最理想的建都之地,而西蜀公子的发问,摆明了对传统空间观念的挑战姿态。而在《吴都赋》中,东吴王孙则夸耀:“有吴之开国也,造于太伯,宣于延陵。盖端委之所彰,高节之所兴。建至德以创洪业,世无得而显称。由克让以立风俗,轻脱躧于千乘。若率土而论都,则非列国之所觖望也。”[5]98-101《唐钞文选集注》注云:“刘逵曰:《战国策》曰:黑齿、彫题,大吴之国也。昔周太伯三以天下让,延陵季子辞国而不处,遂化蛮荆之方,与华夏同风,二人之所兴。《左氏传》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去周国,适蛮荆,服玄冕而行周礼也……刘逵曰:孔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三以天下让人,无得称焉……《钞》曰:《孝经》云:有至德要道。郑玄云:至德者,孝悌也。太伯,周大王之太子。次曰仲雍,次叔,不见。次季历,贤,又生文王昌,有圣人之表。大王曰:兴周者,其昌乎?太伯知父欲立季历,因大王有疾,遂适吴越采药。太王没而不还,一让也。季历为丧主,赴之,不来奔丧,二让也。免丧之后,遂即断发,文身。三让也。其让隐,故时人无能知者,故孔子显焉。张铣曰:言我吴都建立太伯、延陵之至德,以创制大业,代无得而称美也……李周翰曰:言吴能建太伯、延陵之让节,以成风俗。盖谓让千乘之重,如脱履弃之躧履也……李善曰:《毛诗》曰:率土之滨。杜笃有《论都赋》。《左氏传》,叔孙婼曰: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汉书》曰:上欲王卢绾,为群臣觖望。臣瓒曰:觖,谓相叉觖而怨望也。《钞》曰:言中夏而比美,岂与列国同,每语优劣也。”[5]98-102针对东吴王孙的陈述,刘逵、《钞》、李善等注抉发吴国历史、阐发文句内涵,使读者明白东吴王孙所夸竞者乃在于东吴的道德优势。《唐钞文选集注》中的文本和注解,编就了一张意义之网,为我们理解“三国争统”的文化背景提供了一个视角。
传统文献《三国志》亦记载着蜀、吴君臣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激烈的“争统”言论和直接的“争统”行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蜀汉君臣闻风后立即回应:“太傅许靖、安将军糜竺、军事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权)黄柱、少府王谋等上言:‘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6]888刘备称帝发文称:“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帅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祚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6]889由《三国志》所载可以看出,在刘备及其大臣的视角里,曹丕称帝是篡逆,曹魏是窃据政权,而刘备才是绍继天命之人,蜀汉才是继承汉祚之国。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亮集》曰:是岁,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亮遂不报书,作《正议》曰:‘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戒在子孙。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亦将逼于元祸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于昆阳之郊。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于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继之以篡。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又《军诫》曰:‘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6]918-919。由此条文献可以看出,魏国华歆、王朗劝蜀国称藩的依据是“天命人事”,即曹魏既得天命且实力雄厚。诸葛亮《正议》由批驳项羽“起不由德”始,影射曹魏无德,必如项羽垂败;言项羽“虽处华夏”,却下场悲催,意在借项羽喻处华夏中国的曹魏;“昔世祖之创迹旧基”,表明蜀汉以东汉的继承者自居,有血统关系,强调蜀汉政权的正统性;“大人”谓有德之人,《易·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诸葛亮意在表明蜀汉是有德一方,有道德优势;文末“据正道”,这里的“正道”,当谓血统的正统、道德的制高点,在诸葛亮的意识里,蜀汉的政权才是正统。
吴国的“争统”言论和行为虽是待时而动,却也异常坚定。《三国志》载“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藩”[6]1121,即当曹丕称帝之时,孙权羽翼未丰,屈身事魏。而至黄龙元年(公元229 年)孙权称帝时,其告天文的措辞则陡然一变:“……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睿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6]1135此时,孙权公然标榜自己才是承天受命的真命天子,断然否认曹魏政权的正统性。
由以上考察可以看出,《三都赋》描述了三国鼎立时期“各相夸竞”的内容,与《三国志》所记载刘备、孙权、诸葛亮等人有关“争统”的言行相印证,可大略了解“前贤文之是非”的梗概。蜀、吴的“夸竞”与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争统”言行相辅相成。由此,可以明晰吴人陆机在出仕西晋之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心态之中,此为探讨西晋时期南北士人文化冲突的一个起点。
二、潘陆诗注记录西晋南北士人在融合中的文化冲突
西晋武力平吴之后,为巩固统治,晋武帝采取“笼络吴地统治阶级的绥靖政策”[7],其中一项举措是拔擢一大批吴地才俊,陆机、陆云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去吴赴洛。在南北融合的历史洪流中,不论中原士人如何看待吴士,亦不论吴士怀着怎样的心态入仕,南北士人注定要交织在一起。而在此过程中,西晋文学史上发生了一个看似平常实则大有深味的事件:中原士人潘岳代其宗主贾谧为吴士陆机写了一首赠诗——《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陆机也回复了一首——《答贾长渊一首》。这两首赠答诗看似普通,实则忠实记录着当时南北士人的文化认知。借助《唐钞文选集注》注解,在此一赠一答之间,可清晰把握西晋南北士人在融合中的文化冲突点。
诗题“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下方,《钞》注云:“谧字长渊,贾充所养子也。继充为鲁公,为散骑常侍。时陆机为太子洗马,谧以常侍侍东宫,首尾三年,与机同处。机后被出为吴王晏郎中,经二年,至元康六年,入为尚书郎,谧乃忆往与机同聚,又经离别迁转之度,故请潘安仁作此诗以赠之。”[5]309-310《钞》先叙贾谧生平、爵位,接以贾谧与陆机的交接概况,最后凸显述作之由:元康六年(公元296年),陆机由吴王郎中令入为尚书郎,与贾谧有重逢之喜,贾谧忆及昔日与陆机在东宫同处三年、继而离别、终又团聚,心有所感,故而请潘岳代笔,有此赠诗。由《钞》注,可知陆机在元康年间的仕履、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及缘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五臣之一吕向注曰:“大意述晋平吴,得陆生,与之同官,兼言别劝诫之事也。”[5]310吕向概述此诗题旨,有“言别”,兼以“劝诫”,使读者明晰此诗并非一首简单的言“情”之作,还隐含着政治意味。至此,我们可大致把握贾谧对陆机的基本态度:既念及昔日同僚之谊,极尽示好、拉拢之能事;又手执语言之棒,适时敲打,告诫对方在处事上务要注意分寸。
诗开篇两句“肇自初创,二仪烟煴”,发言玄远,上溯天地初开之时,按照陆善经的注解,其意“欲言晋之德,故历叙自古皇王也矣”[5]311;点出诗旨在于突出晋德,彰显西晋之君与开天辟地以来的君主乃一脉相承,突出西晋的正统地位。诗歌开篇即言此,表明在中原士人贾谧和潘岳的认知中,这是大前提,必须讲清楚,唯有在此基础之上,才得接叙人事。原诗接以列叙历代统绪中的帝王,突然笔锋一转曰“南吴伊何,僭号称王”,《钞》注云:“僭,滥也。言南吴是何主乎,乃滥潜称王,非正统也。为此语,叹机也。”[5]321-322《钞》注表明贾谧或潘岳对东吴孙权称帝极为不满,定义为“滥潜称王”,从根本上否定其承继正统,尤其“为此语,叹机也”,使读者明白潘岳这两句诗是专门针对陆机而发的。《钞》注明确揭示出这首诗歌鲜明的政治文化倾向。与此两句相对应的是“大晋统天,仁风遐扬”,《钞》注云“统天,言承天之统”,表明西晋乃承天之统而建,地位正宗,非南吴可以比拟,具有强烈的正统意识。寻绎潘岳原意,诗歌一开始即着眼统绪,当是为突出西晋的正统地位蓄势,《钞》注可谓切中肯綮。原诗步步紧逼:“伪孙衔璧,奉土归疆。”《唐钞文选集注》云:“李善曰:伪孙,谓皓也……《钞》曰:孙皓不承正统,故言伪也。”[5]323李善注和《钞》注均明确诗人命意所在乃是正统与否,显明其政治文化取向。
《为贾谧作赠陆机一首》开篇30句,主题是通过追溯历史,表达诗人对历史的认知和评价,看似风轻云淡,实则裹挟风雷,落脚点是标举大晋正统、东吴僭号。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朝代都会标举自己的正统地位,惯常地,我们会将之视为得胜的西晋王朝的一种历史文化姿态和自我宣扬。而此诗作于元康六年(公元296 年),此时距离西晋平吴已长达16 年之久,面对吴人,西晋文士仍然重申统绪问题,不能不启人深思其时仍然可能存在关于统绪的争论,或明或暗。由此,重申西晋王朝的正统地位,当视为贾谧对陆机进行劝诫的内容之一。
诗歌中间以34 句诗对陆机进行褒赞,接以16句表达二人的缱绻之情,最后以8 句对陆机个人的劝诫收结:“欲崇其高,必重其层。立德之柄,莫非安恒。在南称甘,度北则橙。崇子锋颖,不颓不崩。”《唐钞文选集注》此8 句亡佚,无缘得见《钞》注及陆善经注,不过,可借助六臣注版本中的李善注、五臣注来解读:吕向曰:“将崇高大之德,必须重其增益之事。言此以诫机也。”[8]459李善注云:“《周易》曰:谦,德之柄也。恒,德之固也……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变节,故谧引以戒之。”[8]459吕延济注云:“崇尔道德锋颖,勿使崩颓也。”[8]459李善征引《周易》原文,阐释贾谧以《易》理告诫陆机当谦虚守常,此为固德之本;且以“甘”因移植而易名,告诫陆机勿因由南入北而变节;吕延济直接诠释最后两句诗旨,是劝诫陆机保持道德锋颖。
全诗共88 句,整体来看,其内在的理路可分为三层:第一层历史叙事,于不动声色中确立西晋的正统地位,共30 句,占全诗的34.1%;第二层,对赠诗对象陆机进行褒赞并表达亲近之情,共50 句,占全诗的56.8%;第三层,对赠诗对象陆机进行直接劝诫和祝愿,共8 句,占全诗的9.1%。从各部分所占的比例看,这首赠诗的主体首先是言“情”,传达出中原士人贾谧对陆机的欣赏和团结之意;其次是对历史的评价和认知,但这似乎是大前提,坚定地传达着西晋王朝的政治文化取向;再次是篇幅很小的劝诫,核心是希望陆机能够谦虚守常,以便和中原士人同心和睦。
对于贾谧的赠诗,陆机以《答贾长渊一首》作答,亦载《唐钞文选集注》卷四八。陆机除礼节性地表达了与贾谧相似的缱绻之情外,主要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两个方面:其一为对王朝统绪的认识,诗句为“乃眷三哲,俾乂斯民……爰兹有魏,即宫天邑。吴实龙飞,刘亦岳立”。对此,《唐钞文选集注》注云:“李善曰:三哲,刘备、孙权、曹操也……《钞》曰:俾,使也。言天命使三人以治吴魏蜀也……刘良曰:吴,孙权也。龙飞,九五位也。刘,刘备也。岳立,言如四岳诸侯之立也。云吴实龙飞者,仕衡吴人,故有尊吴之意,不忘本也矣。”[5]246-248很明显,陆机在此将刘备、孙权、曹操并列,标举他们均为承统绪之人,迥异于贾谧赠诗中的“南吴伊何,僭号称王”。其二是对自己的认知和对贾谧的讥讽,诗句为“惟汉有木,曾不逾境。惟南有金,万邦作咏”。《唐钞文选集注》注云:“李善曰:木谓橙也。贾谧《赠诗》云:‘在南称甘,度北则橙。’故答以此言。言木度淮而变质,故不可以逾境,金百炼而不销,故万邦作咏。潘诫之木,而陆自勖以金……《钞》曰:汉有木者……言谧居京师邑,不越地境,在本乡。南金者……《尚书》云:元龟象齿,大辂南金。言当土所出为重,机言我亦当如南方之金,为万邦之咏,不学木之不逾境也。”[5]267-268在贾谧的赠诗中,曾以木相喻告诫陆机,而在陆机的答诗中,不仅言己不是木而是“南金”,并且讥讽贾谧为“不逾境”的木。
贾谧的赠诗和陆机的答诗曾在对方心里激起多大的波澜,我们无从考证,不过,从《晋书·陆机传》所载的一件事,可看出二人后来的关系已势同水火:“(陆机)豫诛贾谧功,赐爵关中侯。”[9]1473陆机本是贾谧“二十四友”中的成员,论名分,贾谧本是他的宗主,而在贾谧失势时,陆机非但不念主宾之情,反而踩着宗主的鲜血上位,可见二人心里的嫌隙甚深。事情发展至此,文化冲突最终酿成了生死较量。
三、陆机诗注中“时网”的诱惑与捆束
陆机《于承明作与士龙一首》中有“牵世婴时网,驾言远徂征”之语,《唐钞文选集注》注云:“李善曰:邹阳《上书》曰:岂拘于俗牵于世。曹子建《责躬诗》曰:举挂时网……《钞》曰:言为世事所牵引,故为时网所婴缠也……陆善经曰:言为世所牵羁,远征入洛也。”[5]273由李善及五臣注,此处“时网”喻俗世中的牵绊,而陆善经注则进一步坐实具体所指,明确“时网”喻陆机入洛。
那么,陆机此次入洛所为何事?据俞士玲先生考证,此诗作于元康二年(公元292 年)陆机赴洛任太子洗马一职的途中[10]。由此可知,陆机将入洛仕宦视为“时网”。此时的陆机,已有两次在洛阳生活和仕宦的经历,尤其是此前身为太傅杨骏祭酒的经历,使他对西晋官场有了切身的体会。在这次赴洛的途中,陆机还作了《又赴洛道中二首》其一,中有“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11]216,也用到了“世网”一词。可见,对于入洛仕宦,陆机已经有了惊惧的感受和认知。
既然陆机已清醒意识到入洛仕宦的危机所在,缘何还要执意前往?这自然有“时网”的诱惑所在。结合相关史料,我们或可勾勒一二,以便于对陆机的仕宦环境有一个较为切实的认知。首先,西晋的“绥靖”政策客观上为吴人仕晋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大环境。在洛阳,缘于统治的需要,西晋朝廷敞开怀抱,大力延揽南方才俊,尤以太康四年(公元283 年)晋武帝策问吴人华谭后为最③。太康九年(公元288 年),晋武帝又下诏“举清能,拔寒素”“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9]78。吴亡后闭门勤学“十一年”④的陆机,觉时机成熟,便毅然入洛。其次,陆机在西晋的仕途有贵人襄助。在洛阳,陆机、陆云得到了西晋重臣张华的赞誉:“伐吴之役,利获二俊。”[9]1472张华在西晋士林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对二陆青眼有加、广为延誉,并荐引二陆去拜会洛中名士如王济、刘沈等,为陆机在西晋官场的发展铺路搭桥。陆机初被太傅杨骏辟为祭酒,杨骏乃晋武帝皇后的父亲,既是外戚,又是权臣,算是有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此次陆机又被辟为太子洗马,这一职位对入选者的家世和才望要求殊高,且日后多能直通显贵,充分显示出西晋朝廷对陆机的重视。当然,除去这些有利的仕宦环境,陆机北赴洛阳的最大驱动力乃在于其自身。陆机出身吴郡四大家族之一,家世显赫,素有盛名,祖父陆逊曾与皇族孙氏联姻,是孙策的女婿,位至东吴宰相;父亲陆抗为东吴大司马,功勋卓著。东吴覆灭之时,陆机年龄尚轻,功业未著,对吴主孙皓投降深以为憾。而家族的光环、父辈的荣耀激励着他,所习得的儒家积极入世的理念牵引着他,所以,其奋不顾身勇闯“时网”,也就不难理解。
既是“时网”,不论外表多么光鲜、多具诱惑力,均不能掩盖其“捆束”的质性。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陆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终致覆顶之灾,足见其“捆束”功能的强大。聚焦陆机在洛阳的仕履,“时网”的“捆束”集中表现在陆机与中原士人文化观念的深度冲突上。入洛之前,陆机曾作《辩亡论》,将吴亡归咎于君主孙皓有“病”[11]716、所用非人,而并非吴士不如晋人。非但如此,出身吴国武力强宗的陆机,带着贵公子的傲气,“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士人”[9]1077,具体实例如下:
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三都赋》),闻(左)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9]2377
范阳卢志于众中问机曰:“陆逊、陆抗于君近远?”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珽。”志默然。[9]1473
尝诣侍中王济,济指羊酪谓机曰:“卿吴中何以敌此?”答云:“千里莼羹,未下盐豉。”[9]1472-1473
士衡在座,安仁来,陆便起去。潘曰:“清风至,尘飞扬。”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凤皇翔。”[12]
以上第一则事例中,陆机闻左思欲作《三都赋》,深不以为然,断定其作只趁“覆酒瓮”,骨子里透出不屑,并讥左思为“伧人”,此种称谓,是其时南人对北人的蔑称;第二则事例中,北人卢志可能有意摆个姿态,意欲陆机伏个低,而兀傲的陆机直接出语反击,把卢志顶得哑口无言;第三则事例中,晋文帝女婿王济着意夸赞北方羊酪,陆机当场回怼,大赞南方莼菜;第四则事例中,陆机在座,潘岳一到,陆机起身即走,丝毫不顾及对方的颜面。由这些事例可以看出,陆机对吴地的文化、物产颇为自负,且极力维护家族尊严,对不投机的北方士人在言行上坚决反击,逐渐和北方士人积累起嫌隙和怨恨。
而秉持“天下之中”为贵这一空间观念的北方士人,自《诗经》时代起已养成了优越的文化心理。西晋士人王济作有《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中有“蠢尔长蛇,荐食江汜。我皇神武,泛舟万里”之语,“蠢尔”出自《诗·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朱熹《诗集传》注:“蠢者,动而无知之貌。”[13]王济沿用《诗经》时代对南方轻视的语调,以晋武帝的神武反衬东吴的蠢动无知。左思在《魏都赋》中亦指出“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陲为襟也。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14],明确表达了北方士人以中夏为尊的空间观念及道德优势感。尤其在平吴之后,北方士人自信心高涨,如张载创作的《平吴赋》、挚虞创作的《太康颂》等,多歌颂晋德,而对东吴着意揶揄。前举潘岳的《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即毫不客气地指出“南吴伊何,僭号称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陆机和北方士人在文化认知和文化心态上的冲突殊为严重:孙氏称帝,在陆机看来是继承统绪,而在北方士人眼里则是“僭号”;北方士人盛赞西晋的道德、文化优势,而在陆机的认知里却以东吴为最。这些内在的冲突表现在言行中,就造成了陆机和一部分北方士人的凿枘不投。
从陆机在洛阳的仕履看,太傅祭酒、太子冼马、尚书中兵郎、殿中郎等职,皆为清选,表明西晋统治阶层颇为看重陆机的资质,着意培养,及至陆机后来卷入八王之乱,亦多被重用,并在乱局中节节高升。尤其是成都王颖在讨伐长沙王乂的战斗中,委陆机以“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的重任,着其全权统帅二十余万将士。南人陆机在军中骤然位居人上,极大刺激了素来轻视南人的北方士人,《晋书》云“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9]1479。在与北方士人重重的龃龉与纠葛中,陆机因统帅不力而惨遭大败,最终,因成都王颖听信了嬖宠孟玖“有异志”[9]1480之“谮”而被杀灭族。平心而论,成都王颖起初非常信任陆机,对其无丝毫地域之见,他之前营救陆机免死于齐王囧之手,继而委以重任并以功成后“爵为郡公,位以台司”[9]1479相勉励,足见对陆机的信任与看重。即使曾被陆机当众回怼的北方士人卢志在陆机出兵的关键时刻向司马颖进言,言陆机傲骄的态度不能济事,仍然未能动摇司马颖重用陆机的决心。《晋书》既明确指出为“谮”,说明“有异志”为不实之词,那么,对陆机始则信任有加且有自己判断力的司马颖,为何会信听谮言?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周一良先生以为,此“与机之身为南人,又出自孙吴之四姓高门有关”[3]77。若从当时南北士人的整体冲突看,此语有一定道理,但不免将“有异志”之理解导向出身东吴武力强宗的陆机怀有颠覆西晋之心的模糊境地,而若结合《资治通鉴》的谮语“机有二心于长沙”[15],则可进一步明晰所谓“有异志”是指陆机暗通款曲于被自己攻打的长沙王司马乂,所以才导致兵败。设若成都王司马颖事先不了解陆机的政治立场,他断然不会将二十余万将士的性命付与陆机之手,由此推断,司马颖在心底不见得信此谮语,而促使他不得不“信”的事实是,“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与牵秀等共证之”[9]1480。这样,俨然形成了一个军中南北士人对峙的格局,再加上之前素为司马颖倚重的文职士人卢志⑤的进言,待陆机兵败、被谮后与其他因素产生合力,陆机最终难逃悲剧命运。
注释:
①相关文章可参见翁频:《从二陆之死看西晋南北文化的冲突》,《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12—118页。
②王德华先生在其论文《左思〈三都赋〉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兼论“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中指出,“《三都赋》反映了三国鼎立、南北对峙情形下的正统之争,魏、蜀、吴三国所争并非建都问题,而是正统问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49页。
③《晋书·华谭传》(晋武帝)策曰:“吴蜀恃险,今既荡平。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雎,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静新附,何以为先?”(华谭)对曰:“……蜀染化日久,风教遂成;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蜀人敦悫而吴人易动也。然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参见《晋书》卷五十二《华谭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59页。
④《文选》载陆机《文赋》注引臧荣绪《晋书》曰:“(陆机)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页。
⑤臧荣绪:《晋书》卷十一:“颖形状美而神明少,乃不知书。然器性敦厚,委事卢志,故得成其美焉。”载〔清〕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