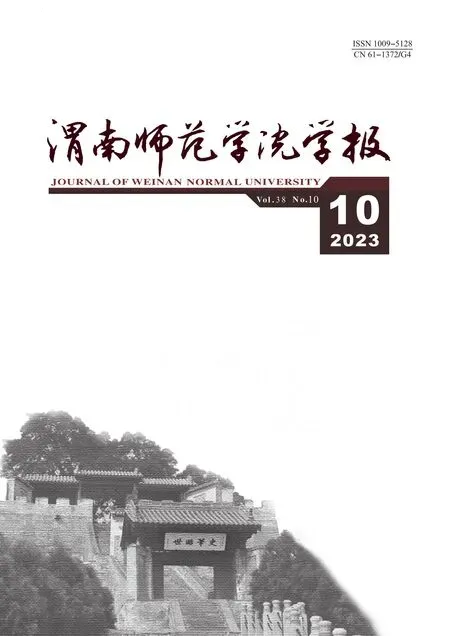董仲舒与司马迁学术传承关系考述
王文书
(衡水学院董仲舒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河北衡水 053000)
一、学术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董仲舒是西汉公羊学的代表人物。司马迁与董仲舒有过面对面的交谈,并且在《史记》中为董仲舒修撰了第一份传记,为后世的董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给司马迁在董学史上定位的话,称之为董仲舒和董学研究的“第一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由于时过境迁,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沧桑变迁,当时非常清楚的问题,或者说不成为问题的事情到当今也成为问题。目前,学界对于董仲舒与司马迁的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关于司马迁是否师承董仲舒的问题
南宋真德秀在《文章正宗》卷十二《董仲舒论春秋》按语中首次提及这一问题:“仲舒此论见于太史公自叙其学粹矣,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则迁与仲舒盖尝游从而讲论也。”后世学者多认可这一观点,例如,张大可在《司马迁创作系年》一文中将“司马迁受公羊学于董仲舒”系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认为司马迁壮游归来后曾于茂陵邑接受董仲舒教诲。[1]128-129但也有学者明确断定董仲舒并非司马迁的老师。杨燕起在《司马迁与董仲舒》一文中提出,司马迁明确反对天道观、因果报应说以及阴阳五行论,否定了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观点。[2]张韩荣发表《董仲舒、孔安国并非司马迁的老师》一文,题目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表达。该文以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为靶标,认为司马迁学术来自家学,司马谈不会让司马迁投到董仲舒门下,否认董仲舒是司马迁的老师。[3]陈桐生以为,从司马迁“闻董生”来源于古籍,不一定直接听闻董仲舒,《史记》《汉书》没有记载司马迁师承董仲舒,司马迁与董仲舒同居茂陵邑之说法不可靠,司马迁对董仲舒的评价远不如班固,司马迁对春秋史事评价兼采《春秋》三传,司马迁与董仲舒有相同的文化渊源才导致部分论点相同等九个方面,说明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不能成立。[4]
(二)司马迁与董仲舒是否同属于公羊学派
个别学者否定司马迁属于公羊学派。如赖长扬论断司马迁作《史记》是对春秋公羊学的批判。他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整个春秋公羊学之基础,“天人感应”是其主要内容,司马迁对阴阳五行说和《春秋》持批判态度,对朝代兴衰更替原因的阐释以及对于天道、天命等是否定和批判的。[5]杨向奎则直接论定司马迁为前期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6]两篇文章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成果,明显带有时代的印记,尚未脱去旧的影响,“文革”时期的影子仍在,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阶级划分方法依然支配学界。董仲舒与司马迁都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或支配,董仲舒虽作为公羊学大家,但也很明显地吸取了《谷梁传》和《左传》的内容,同样司马迁虽在春秋史上主要使用了《左传》的史料,但在义理上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绝对化地把司马迁归于或排除在公羊家之外都是不合适的。严格来讲,司马迁不是经学家,而是史学家。
(三)关于司马迁对董仲舒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
大部分学者以为司马迁史学思想方法承袭并在写作《史记》过程中贯彻了董仲舒的公羊学思想,在批判的基础上发展了董仲舒的学说,在某些方面又与董仲舒的观点存在差异。吴汝煜较早提出了司马迁对以董仲舒所代表的公羊学持批判与继承的态度,辩证分析了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关系。[7]汪高鑫认为公羊学对司马迁史学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主要还是董仲舒对《史记》写作影响最深,从天道观、古今观和大一统观等方面对司马迁史学观念产生重大影响。[8]学者沿着这一正确的方向对董仲舒与司马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不同学者的立足点会有不同,所强调的内容也会有所差异。但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方面共识:一方面,都承认包括董仲舒在内的公羊学派对司马迁创作《史记》有着深刻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同,司马迁学术深受董仲舒影响并服膺公羊学,并在《史记》的创作过程中大量采用了公羊学思想,在“大一统”“天人关系”“三统论”“别夷夏”“安民保民”等方面继承了董仲舒的衣钵,并体现在《史记》的历史叙述当中。另一方面,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司马迁在批判性继承董仲舒思想的前提下,又与董仲舒思想有不少差异,在某些方面发展了董仲舒的学说。边家珍认为,司马迁在董仲舒“王鲁说”基础上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据鲁说”。[9]陈璐认为,司马迁对董仲舒天人关系理论中“人”的含义作了界定,区别灾与异不同,有“灾后异先”说。[10]宋馥香、石晓明则强调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表述逻辑的不同,董仲舒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司马迁则是通过抽绎的方法来表述自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独到见解。[11]
综上可知,目前学界关注到的上述三个问题或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但是从时间维度,对于董仲舒和司马迁人生经历是否存在交往的可能性没有进行过考证,对于二人在学术探讨交往方面的具体内容也较少系统考察。本文意在考证司马迁和董仲舒人生经历交集以及二人交往内容的基础上,阐述司马迁在董仲舒研究史上的历史地位,进而比较系统地探讨司马迁在历史观上对董仲舒的继承,阶段性地解决司马迁和董仲舒关系问题。
二、有关司马迁和董仲舒人生经历交集的考证
(一)从董仲舒为孝景博士到建元元年之前不可能与司马迁有任何交集
《史记》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12]3127《汉书》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13]2495两者记载大同小异,《史记》《汉书》均认为董仲舒在汉景帝时期成为博士官。董仲舒所担任的博士官当为广川国博士,并非汉廷博士,时间在七国之乱前。《史记》载:“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12]2104可知,自汉高祖刘邦开始,各诸侯王国就有王国博士的设置。直到汉景帝七国之乱以后王国博士官才遭罢省。《汉书》载:“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13]395颜师古注云:“谓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损大夫、谒者诸官长丞员等也。”[13]396七国之乱后,董仲舒去博士官,在家乡下帷授徒。今衡水故城县有董学村,原名下帷村,相传为董仲舒下帷讲诵之地。
董仲舒教授弟子众多,其中不少成名成家,或以学问显达。《史记》载:“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12]3129从其弟子籍贯来看,均在广川或周边郡国,可以进一步推测董仲舒下帷之地就在其家乡附近,并未西去长安。直到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即位之初朝廷的举贤良方正的察举行动中参与对策才离开家乡,时年六十余岁。《汉书》记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13]2495
在《史记》中司马迁也没有言明自己是董仲舒的入室弟子。据张大可《司马迁创作系年》可知,汉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前145)司马迁生,生地为左冯翊夏阳县高门里,即今陕西省韩城西南9 公里之嵬东乡高门村。建元元年(前140),司马迁6 岁,迁父司马谈举贤良对策,出仕太史丞。司马迁随母居家乡,“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在建元元年之前董仲舒在家乡下帷讲诵,开馆授徒,司马迁尚在冲龄,随母于左冯翊夏阳县高门里家中,不可能与董仲舒有任何交集。
(二)董仲舒长时间留任江都
在建元元年对策完毕之后董仲舒被委派到江都国担任国相,到建元三年(前138)间董仲舒一直留任江都。其间不知什么原因,董仲舒被调回到长安任中大夫。“(汉武帝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13]159-160面对一系列的变故,董仲舒按照公羊学的灾异理论写就《灾异对》,被主父偃窃取,直接被诬告到汉武帝处,导致董仲舒遭遇人生一次大劫难——庙火之狱,最终在吕步舒的营救下才得以脱险,并在元光元年(前134)或二年(前133)又被派到江都国二次任江都国相,这就是所谓“再相江都”。也就是说从建元元年对策后被委派到江都任王国相,到元光元年或二年再相江都,中间回到长安约两三年在长安任中大夫之职。自元光元年或二年至元朔三年董仲舒一直在江都任上。元朔三年(前126),公孙弘任御史大夫,《史记》载:“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12]3128董仲舒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是在元朔三年(前126),同年辞职回长安。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按照张大可的考证,司马谈从建元元年(前140)到元封元年(前110)病死周南一直任太史丞或太史令。其间,从建元元年到元朔二年(前127)司马迁(约略六岁到十九岁)一直在家乡居家耕读。元朔二年(前127)夏天,汉武帝迁徙郡国豪杰及财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司马迁一家也迁至茂陵显武里,并目睹大侠郭解的状貌风采。从元朔三年(前126)到元朔五年(前124),司马迁壮游。《史记》载:“(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12]3293
所以,在元光元年(前134)到元朔三年(前124)期间,董仲舒二相江都或再相胶西,司马迁或在韩城耕读或刚刚迁居长安;从元朔三年(前124)董仲舒致仕归家长安到元朔五年(前124)期间,司马迁正在游历途中,与董仲舒发生交集的机会不会很大。
(三)司马迁曾与董仲舒有过交游
《史记》明确记载,司马迁与董仲舒有过交游,曾经从董仲舒处学习过《春秋》,了解过秦末汉初的史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回答壶遂所问孔子作《春秋》时说:“余闻董生(服虔注云:‘仲舒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董仲舒是当世著名的公羊学大家,是春秋学的领袖,“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12]3129。司马迁襄助其父司马谈修《太史公书》,在父亲的推荐下,到董仲舒居住的陋巷请教问题是完全有可能的。董仲舒出生在汉朝立国之初,与秦末历史亲历人物有交游,了解秦朝史实,也曾为司马迁提供了不少口述史的资料。荆轲刺秦是战国末的著名历史事件,董仲舒与亲历者秦医夏无且是朋友,为司马迁转述了夏无且的亲身见闻。《史记·刺客列传》载:“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12]2538
从时空角度考察,司马迁与董仲舒的交往主要集中在董仲舒致仕后深居长安陋巷著书立说的归隐时光。《汉书》载:“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13]2525在元光元年或二年以后,元朔三年以前,董仲舒一直在江都国和胶西国的任上,与壮游的司马迁会面的机会不大,也只有元朔三年致仕回到长安才有了闲暇时光接待各方拜访。董仲舒去世大约是在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到武帝元鼎三年(前114)之间。司马迁二十岁也就是元朔三年开始壮游,壮游结束在元朔五年,此后协助其父司马谈编修《太史公书》,有向董仲舒学习的时间和需求。二人又都居住在长安,从空间距离上讲也完全有可能,见面晤谈的主客观条件完全具备。所以,二人比较可能见面产生交集应该是在元朔五年(前124)至元狩三年(前120)之间,地点可能是在长安董仲舒家中。
综合以上考察可知,司马迁并不是董仲舒的入室弟子,其本人并未明确提及自己是董子的徒弟,但司马迁曾经向董仲舒请教过学问,董仲舒向司马迁提供过自己的见闻资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三、司马迁为董仲舒研究留下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司马迁是董仲舒研究的历史第一人。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写就了董仲舒第一份比较完整的传记,为后世的董仲舒研究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董仲舒研究有三大部分史料可以利用:一是《春秋繁露》及少量散见古籍中存世的董仲舒著作,并且这部分著作还被古往今来的部分学者质疑真伪;二是董仲舒的两部传记、少量历史文献中董仲舒生平的零星记载,以及有关董仲舒的大量诗文;三是现当代大量的董仲舒研究的专著和文章等。其中董仲舒两篇比较完整的传记:《史记》之《儒林列传》中有关董仲舒的部分,保存了443 字的董仲舒生平资料。《汉书》之《董仲舒传》,有8 841 字的材料,其中有关“天人三策”的内容8 009 字,余下的832 字才是董仲舒生平资料。相比之下,《汉书》的内容很多。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全文著录了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内容,其生平简史多抄录《史记》,内容大同小异,部分内容甚至是原文抄录。从这一角度来审视《史记》董仲舒传记内容,就弥足珍贵了。另外,在《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刺客列传》中有少量的有关董仲舒的内容,也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史记》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董仲舒的籍贯、事迹、贡献、学问传承等,为董仲舒研究奠定了基础。司马迁本人与董仲舒虽然相差50 多岁,但是两人曾经在同一块蓝天下生活过,对现代学者而言是同一个时代的古人,而且二人有过比较深入的交往,一起探讨过学问之道,董仲舒也为《史记》创作编纂提供过材料,也曾给司马迁提出过指导意见。如果没有司马迁撰写的董仲舒的传记,可能董仲舒的生平事迹就会完全湮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烟尘之中,后世研究董仲舒会更加困难。
《史记》之董仲舒传记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第一,籍贯、学源、仕宦等基本信息:“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董子故里问题历来争议不断,广川旧属赵地,因此,《史记》亦称,言《春秋》“于赵自董仲舒”,秦汉时期广川亦有郡、国、县的建制,即使景武时期郡国不时转换,但《史记》已经明确了董仲舒故里之所在,结合今天的口碑史料和地表遗存,董子故里无疑可以确定在今衡水市景县、枣强、故城三县交界的方圆5 公里的范围之内,相比较其他历史人物而言,已经是比较精确的了。董仲舒治《春秋》,精于《公羊传》,是公羊学传承的关键人物。第二,《史记》不仅比较清晰地胪列了公羊学的传承谱系,还重点介绍了《春秋》在西汉的传播,为儒学史、经学史、春秋学史提供珍贵的一手资料。“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12]3128-3129凡涉及经学史和春秋学史的研究无一例外都会参考以上两段史料。第三,司马迁用比较简洁的语言勾勒了董仲舒的人生历程,留下了下帏讲诵、长安对策、庙火之狱、两相江都、求雨止雨、再相胶西、悬车致仕、陋巷问策等董仲舒重要的人生节点,同时也是西汉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董仲舒的生平事迹,也丰富了西汉政治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史料来源。第四,司马迁记载董仲舒下帏讲诵,因钻研学问而“目不窥园”的故事,身居陋巷,“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的高洁品行,高度赞扬了董仲舒专注学问的好学精神与为人廉直的高尚品格,董仲舒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尊崇的先贤楷模。
因此,《史记》有关董仲舒的资料可以概括评价为研究董子学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是董仲舒研究必须关注不可能绕开的材料。对董学研究来说,如何高估这部分资料的价值都是不过分的。
四、司马迁对董仲舒三统说和孔子王鲁说的继承
(一)司马迁从史学编撰上实践了公羊学“孔子当新王”的理念
司马迁编撰《史记》完全接受了董仲舒对孔子作《春秋》的观点,他在《儒林列传》中提出:“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12]3115孔子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学说不见用,折返鲁国作《春秋》,建设素王之业,为后世垂立王法。司马迁的“孔子作《春秋》王鲁以当新王”的观点完全来自董仲舒。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回顾了一段与上大夫壶遂的对话内容,壶遂问司马迁:“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司马迁引述董仲舒的话来回答,云:“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12]3297在董仲舒看来,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春秋》王鲁说则突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手段。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13]2509董仲舒三代改制的历史叙事的归宿也在于此。“《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14]417
在义例上,司马迁将自己著述《史记》与孔子删订《春秋》作对比,以阐释董仲舒学说自命。司马迁发挥董仲舒的观点,洋洋洒洒,表达了史家著史的历史责任,强调“孔子王鲁当新王”之意义。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12]3297-3298
因此,司马迁在《儒林列传》赞扬董仲舒最明《春秋》之意指。“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12]3128
(二)司马迁接受了董仲舒的三统说
董仲舒的“孔子王鲁”的观点是放在更大的政治历史观下的。这个大的政治历史观就是三统说。“三统说”只能说是一个代表董仲舒历史观的名词而已,并不能完全概括董仲舒的历史观,三统只是董仲舒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全部。董仲舒对历史时代(不仅仅是朝代)更迭,提出两条大的原则性规律,一是“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二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在董仲舒看来,道具有稳定性和完美性,“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13]2518。“人道者,人之所由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14]1095可知,道即是古人定义的“规律”(包含自然规律——天道、社会规律——人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讲规律的稳定性和客观性。董仲舒所言“道”的另一个含义是社会实践或治理国家的方法。尧舜禹三代为治世,虽朝代发生更迭,但其所实行的治理国家的实践符合规律,没有必要调整变化;尧舜禹三代之后的夏商周三代,在每一朝代末期发生变乱,后继者要调整治理措施,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在以上两原则基础上,董仲舒回顾夏商周历史,提出三统说,他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往复的。每一位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正名号,改正朔,易服色,即“新王必改制”。董仲舒以为:“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它焉,不敢不顺天志也,而明自显也。”[14]29也就是说,新王之所以要“改正朔、易服色”,就是为了区别新王朝与旧王朝有所差异,从历法、服制上给出显著标识,显示新王朝的天命所系。
1.正名号
董仲舒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详细阐述了“正名号”的具体内容。“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14]448
司马迁在《史记》的历史叙事中落实了董仲舒正名号的规律总结。《史记》之《五帝本纪》称:“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12]44《夏本纪》称:“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12]88周武王灭商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12]108-109,“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12]127。司马迁证实了董仲舒先王之后在当世称客而朝,与当朝之统形成“三统”的事实。因此,汉武帝采纳了通三统的理论和“正名号封前朝”的建议。“汉兴九十有余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12]170
2.改正朔
通三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正朔。历法制度的变革是三通循环的重要表现,也是新王改制的重要内容。正朔是人承接天道的具体做法,内容很庞杂,不仅是历法的变革,包含在改正朔的基础上实行易服色、正祭祀、定官制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制度建设。余治平概括很是精当,他说:“按照董仲舒的理解,一年十二个月,有三个月可以被确定为岁之首,即所谓‘正月’,并以此月的颜色为本朝崇尚的主色彩。这三个月分别是寅月(农历正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子月(农历十一月)。‘统’字则蕴涵着开始、根本、纲领、纪要之意。根据寅、丑、子这三个月所建立起来的朔始律法、度制服色,就是董仲舒意义上的‘三统’。”[15]
司马迁完全接受了董仲舒改正朔的观点。司马迁曰:“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12]1256司马迁同样认为改正朔、易服色等手段是新兴王朝表示顺承天命而为的具体措施。司马迁强调了历法在政治制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12]1258夏、商、周三代分别属于黑、白、赤三统,三代所定正朔历法也各不相同,三统往复循环,其正朔也随之循环无穷。国家一统,诸侯行王之历法;国家分裂,诸侯各行自己历法。西周之后,礼崩乐坏,“正朔不行于诸侯”,始皇一统天下,代周而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汉初承袭秦制,使用古历颛顼历,司马迁以为“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应改正朔。司马迁在行动上,实践自己的学说,积极发起和参与制定了《太初历》的活动,《汉书》记载:“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13]974-975司马迁说:“余与壶遂定律历。”[12]2865
3.“忠敬文”
“忠敬文三道论”与“三统说”互为表里。根据董仲舒“三统说”,夏、商、周三王分别统属于黑、白、赤三统,其正朔、服色、官制以及治道的文化特质也有所变化。黑、白、赤三统的往复变迁不是与王朝兴替的简单对应比附,三统蕴含“忠、敬、文”三种不同文化风格、治理理念和治国手段,三者关系是相辅相成,不是毫无联系,前后有着深刻的呈递关系,是一种历史的螺旋上升。“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13]2518董仲舒承袭了孔子的损益观,而肯定夏、商、周的治道分别为忠、敬、文。董仲舒认为汉继周而建,当为黑统,主张汉朝“用夏之忠”。司马迁同样主张汉用夏之忠道:“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12]393与董仲舒的观点及使用概念均一般不二。从朱熹对董仲舒、司马迁的批评可见二者的一致性和承接关系。朱熹说:“夏火,殷藻,周龙章,皆重添去。若圣贤有作,必须简易疏通,使见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盖文、质相生,秦汉初已自趣于质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用夏之忠,不知其初盖已是质也。”[16]2179“太史公、董仲舒论汉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汉初承秦,扫去许多繁文,已是质了。”[16]3219朱熹认为,经历秦代的焚书坑儒等文化浩劫的涤荡,周文已经被彻底清扫,汉初文风和治道已经是质而非文了,董仲舒、司马迁的改文从质说,用承袭黑统用夏忠是不对的。可见在朱熹眼里董仲舒与司马迁的观点是一致的。
4.摒秦
为了理论的圆融和现实政治的需要,董仲舒和司马迁都排斥秦为一统。周汉之间的秦王朝国祚日短、使民暴虐、刑法苛苦,并且在服色制度上汉承秦制。为了与暴秦划清界限,并给汉朝上继周朝赤统而为黑统,以及说明孔子作《春秋》当新王为汉立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就把处于周、汉之间的秦王朝排除在三统之外。秦奉行五德终始说,为水德,“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历度闰余,未能睹其真也”[12]1259。秦朝在正朔服色上只作部分调整。汉代秦后,直到汉武帝,长时间未能实行改制。“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董仲舒为圆融三统说,遵奉《春秋》行夏之时,汉当为黑统,与秦制冲突。因此,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13]2504他认为秦仅是一个过渡,不算作一统,汉朝直接跨过秦,仍从周算起,汉继承周统,尚黑,为黑统。司马迁《高祖本纪》云:“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2]394秦无改旧的弊政,没有受到天命,未得真统,自周平王东迁一直到刘汉的建立,唯刘氏汉家得真“统”,司马迁也直接以汉继周,将秦从三统递嬗中剔除出去。
五、结语
综合考察司马迁和董仲舒的人生经历的交集来看,司马迁并非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但二人确有过交往,司马迁正值二十岁的青年时期,壮游归来后,向董仲舒请教《春秋》的学问,并为撰写《史记》向董仲舒询问一些口述材料。司马迁继承和传播了董仲舒的部分思想,并融入《史记》之中,主要有两点:一是认可孔子作《春秋》行素王之业为汉立法的思想;二是接受了董仲舒的三统理论。至于大一统、灾异论、夷夏论,二人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司马迁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公羊学派学者,只是继承吸收了董仲舒公羊学派的一些理论而已。但是,司马迁撰写了董仲舒的第一部传记,为董仲舒研究保留了珍贵的史料,不愧董仲舒研究第一人的称号,为董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