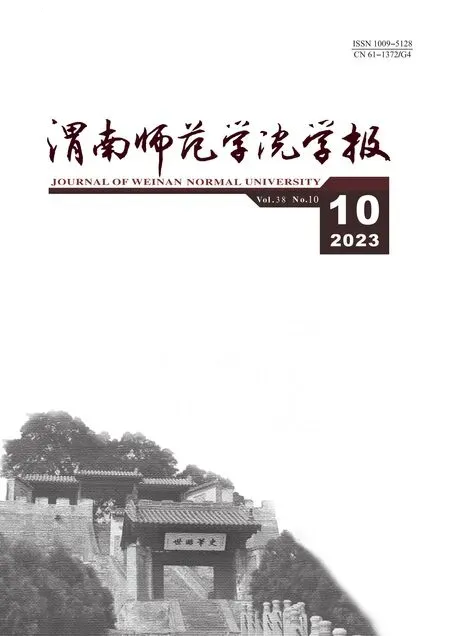从《晋书》看《史记》在两晋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师 帅
(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陕西渭南 714099)
《晋书》凡130 卷,包括帝纪10 卷、志20 卷、列传70 卷、载记30 卷,记载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讫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取代东晋的历史,并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兴衰。题为唐房玄龄等撰。作为二十四史之一,《晋书》反映了两晋十六国历史的全貌,是记述这段历史最为完整的唯一一部史著。本文以《晋书》为切入点,以《晋书》所载历史史实为依据,分析研究两晋时期《史记》传播与接受的历程,解读其传播与接受的特点,概据其成就,为史记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史记》在东汉时期,其地位在《汉书》之下。到了两晋时期,《史记》的史学地位明显得以提高。张新科认为:“汉魏六朝时期,是《史记》研究的开创阶段。”[1]4通过梳理《晋书》有关的历史记载,我们发现,和两汉时期相比,两晋时期随着史学脱离经学而逐渐走向独立,《史记》越来越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学习和评论司马迁与《史记》初步形成一种社会风尚。
一、对《史记》进行考证注释,是两晋学者孜孜以求的事业
两晋学者对《史记》文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史料的考证与注释上。这种研究方法,为人们阅读《史记》提供了便利。《史记索隐后序》记载,最早为《史记》作注的是东汉人延笃,著有《音义》一卷,但早亡佚。三国晋朝之际的儒学大师和史学家谯周,著有《古史考》25 篇,对《史记》进行考证、评述,揭开了我国古史考辨的序幕。《晋书·司马彪列传》云:“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2]2142谯周认为《史记》记载周秦以上历史,有很多内容采用民间传说和百家之言,因此与经典文献的出入较大,所以他依据旧典,撰成《古史考》,专门考证《史记》记载之误。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的历史考证著作,可惜散佚了,但《古史考》的许多成果被后来《史记》三家注所吸收利用。到了两晋时期,注释考证《史记》依然是学界的主流。其中徐广《史记音义》和司马彪《古史考》最有名。关于徐广著《史记音义》一事,《晋书》虽未记载,但通过裴骃《史记集解序》可知大概。《史记集解序》云:“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麤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汉书音义》称‘臣瓒’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瓒曰’。又都无姓名者,但云‘汉书音义’。时见徽意,有所裨补。譬嚖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以徐为本,号曰《集解》。”[3]4裴骃《史记集解》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基础,兼采经、传、诸史及孔安国、郑玄等人之说,增益而成。《史记集解》所引徐广所存佚文,皆以“徐广曰”形式注出。考查《史记集解》所存徐广佚文,可以发现徐广《史记音义》是一部考证性质的书籍,涉及注音、释义、释地理、补史实等许多方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注音、释义较多。涉及注音、释义的,如《史记·五帝本纪》“披山通道”,【集解】徐广曰:“披,他本亦作‘陂’。字盖当音詖,陂者旁其边之谓也。披语诚合今世,然古今不必同也。”[4]3-6《史记·五帝本纪》“舜让于德不怿”,【集解】徐广曰:“音亦。《今文尚书》作‘不怡’。怡,怿也。”[4]22-23涉及释地理的,如《史记·项羽本纪》“关中阻山河四塞”,【集解】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4]315对“四塞”的位置和名称作了解释。相比较而言,《史记音义》补史实较少,如《史记·吕不韦列传》“乃饮酖而死”,【集解】徐广曰:“十二年。”[4]2513对吕不韦“饮酖而死”的时间进行了补充说明。《史记·酷吏列传》“周阳侯始为诸卿时”,【集解】徐广曰:“田胜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为周阳侯。”[4]3138补充了周阳侯田胜的身世。通过《史记集解》,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徐广对《史记》研读的深入和精细。
西晋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彪,“专精学习,故得博览群籍”[2]2142,他汇集整理群书,著成《续汉书》80 卷。司马彪认为谯周所著《古史考》不够完善,摘出《古史考》中122 件史事,认为不妥,依据《汲冢纪年》中的说法,写成《古史考》一书。对此《晋书》云:“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2]2142司马彪的《古史考》也是一部专门的历史考证著作,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学术辩论。司马彪《古史考》,大约在《隋书·经籍志》以前,便散佚不存,因为《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司马彪《古史考》,但多为《史记》三家注所征引。据《史记》三家注所存司马彪佚文可知,司马彪对《史记》多篇进行了注音、释义、释地理。如《史记·苏秦列传》“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索隐】徐广曰:“庄子云南行至郢,北面而不见冥山。”骃按:司马彪曰“冥山在朔州北”[4]2251-2252。《史记·穰侯列传》“为华阳君”,【正义】马彪云:“华阳,亭名,在洛州密县。”[4]2323-2324都属于地理位置的阐释。《史记·滑稽列传》“汙邪满车”,【集解】司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4]3198《史记·高祖本纪》“日夜跂而望归”,【正义】司马彪云:“跂,望也。”[4]367-368此两例属于释义。其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三家注中所存司马彪佚文最多,据笔者粗略统计,约有20 余处,大多是注音、释义、释地理。
西晋史学家、训诂学家郭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2]1899。他曾经“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2]1910。郭璞学习研究《史记》,对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山海经序》云:“司马迁叙《大宛传》亦云: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书不潜出于千载,以作征于今日者,则山海之言,其几乎废矣。”[5]4对《史记·大宛列传》进行了评论。司马迁作《大宛列传》时,对《禹本纪》《山海经》所记载的奇异事情,采取存疑态度。对此郭璞感叹道,如果不是《竹书纪年》存在千载,为《山海经》作证,那么《山海经》所载奇异事情恐怕永远没人相信了。陈直先生认为:“郭璞此段,说司马迁不信《山海经》,因晋时所出《竹书》与《山海经》可以互证。然讥前人以未见之书,其评论亦未为允当。”[6]56陈先生的评价公允!郭璞对《史记》的学习与接受,主要是用《史记》中有关内容注解《方言》《尔雅》《山海经》等典籍。《山海经序》云:“案《汲郡竹书》及《穆天子传》,穆王西征,见西王母,执璧帛之好,献锦组之属。穆王享王母于瑶池之上,赋诗往来,辞义可观。……穆王驾八骏之乘,右服盗骊,左骖騄耳。造父为御,奔戎为右,万里长骛,以周历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济。东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庐,南轹鼋鼍之梁,北蹑积羽之衢。穷欢极娱,然后旋归。案《史记》:说穆王得盗骊、騄耳、骅骝之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亦与《竹书》同。”[5]4郭璞将《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与《史记》等历史著作进行内容比照,以此认证《山海经》所言的真实性。《山海经注》在注释《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时,其注语为“冀州,中土也;黄帝亦教虎、豹、熊、罴,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而灭之”,这条注语虽未交代出处,但对照《史记·五帝本纪》,“轩辕……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4]3,可知这条注语源自于《史记·五帝本纪》。郭璞对《史记》的熟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记》在晋代知识分子中流传的状况。
纵观两晋时期《史记》考证注释,虽然说大多局限在注音、释义等基础工作方面,但他们注释训解有见解,保存了丰富的音义训诂材料,多为后世注家所征引,在《史记》注释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二、研究探讨司马迁与《史记》,是两晋《史记》传播与接受的深入
两晋时期,出现了一些《史记》评论家,比较著名的有西晋张辅,东晋葛洪、袁宏、干宝等,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司马迁与《史记》进行了精彩评论。这些评论虽然比较零散、感性,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记》的传播与研读。其中比较重要的贡献是对“班马优劣”与“史公三失”等传统命题的探讨,提出了精彩评论,从而推动其向纵深发展。
对“班马优劣”传统命题的研究。从史学角度看,率先论述“班马优劣”的是东汉王充。王充《论衡·超奇篇》云:“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7]278认为从记事详略的角度分析,《汉书》优于《史记》。晋人张辅《班马优劣论》是较早论述“班马优劣”的著作。“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2]1640张辅以文字的多寡、叙事的详略来评价《史记》《汉书》的优劣。同时还从对事件的选择、对人物的褒贬以及体例的创新等方面,比较分析班马优劣,由衷称赞司马迁为“良史”,断言《史记》优于《汉书》。见解独特,富有启发性。由于张辅的比较缺少具体分析,仅仅流于形式上的比较,难以让人信服。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张辅的观点就提出了质疑。“或问:张辅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是固不如迁也。斯言为是乎?答曰:不然也。按《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惟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烦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班氏《汉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烦芜,不足编次故也。若使马迁易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耶?”[8]138刘知己从“烦省”角度对张辅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以繁简论优劣不可取。仅凭繁简定优劣的观点是片面的,刘知己的批驳是有道理的。
东晋文学家、史学家袁宏对“班马优劣”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后汉纪序》中云:“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以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9]1袁宏肯定司马迁《史记》不仅“非徒记事而已”,还有益于“扶明义教,网罗治体”。批评班固《汉书》是“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这是从创新与否评价班马的优劣,与张辅“迁既造创,固又因循”观点相同。正是在张辅、袁宏等人的推动下,宋代出现了倪思《班马异同》著作,明代许相卿在《班马异同》基础上,撰著《史汉方驾》,对《史记》《汉书》进行文字比较研究。在张辅等人的推动下,“班马优劣”逐渐成为《史记》研究的一个课题。
对“史公三失”传统命题的研究。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云: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史公三失”。班固的“史公三失”论断,后来成为《史记》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葛洪是魏晋时期较早研究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学者。《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葛洪摘抄《史记》,有《史记钞》14 卷。葛洪对“史公三失”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抱朴子·明本篇》云:“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中。”[10]184葛洪从取材、评论等角度高度评价司马迁与《史记》“实原本于自然”“皆准的乎至理”,批评班固对司马迁学术思想的错误认识,“固诚纯儒,不究道意”。在《西京杂记》中他热情赞扬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11]514可以看出,葛洪的评论与班固评论针锋相对。从此以后,“史公三失”问题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和议论。宋元明清学者在总结前人评价基础上,发表了许多富有见地的评论。所以说葛洪对“史公三失”问题的研究,具有上承两汉下启宋元明清研究的桥梁作用。
史学家干宝,则是从史书体裁上比较司马迁《史记》与左丘明《左传》的优劣。刘知几《史通·二体》云:“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8]8干宝认为纪传体《史记》记事分散,不如编年体《左传》简约集中。虽然其观点有些偏颇,但可谓一家之言。干宝也是按照这样的观点来撰述史书的,他的史传著作《晋纪》,是一部记载晋代历史的编年史,“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晋书》称赞:“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2]2150
三、学习研究《史记》人群的扩大,是两晋《史记》传播与接受的特色
和两汉相比,两晋时期传播与接受《史记》的人群明显增多,这些人主要有史学家,如干宝、司马彪、华峤、郭璞、陆机、王隐、虞预、孙盛、陈寿、袁宏、何嵩等;知名人士,如徐广、葛洪、张辅、张华、王戎、谢万、虞溥、曹毗等;帝王和大臣,帝王如前赵开国皇帝刘元海,前燕景昭帝慕容儁,大臣如戴邈、江逌、刘毅、桓玄、王濬、刘隗、刘胤、刘殷等,而普通老百姓则未涉猎。在这些人当中,既有汉人,也有匈奴和鲜卑人,如匈奴人刘元海,鲜卑人慕容廆等。《晋书》或直接记载他们学习《史记》的情况,或在本传中载录他们的奏章、书信,在他们的奏章、书信中,所引用《史记》人物典故很多。
《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记载了陈寿师从大学者谯周学习的情况:“(陈寿)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12]184史官何嵩,“博观坟籍,尤善《史》《汉》”[2]1000。东晋大臣戴邈,“少好学,尤精《史》《汉》”[2]1848。刘毅是东晋末年著名将领,在攻城略地之余,也是史书不离手。《晋书·刘毅传》云:“(刘毅)每览史籍,至蔺相如降屈于廉颇,辄绝叹以为不可能也。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2]2210道出了刘毅的凌云壮志。西晋名将王濬,在晋灭吴的战斗中起了重大作用,为西晋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晋书·王濬传》记载:“濬博涉坟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为乡曲所称。晚乃变节,疏通亮达,恢廊有大志。尝起宅,开门前路广数十步。人或谓之何太过,濬曰:‘吾欲使容长戟幡旗。’众咸笑之,濬曰:‘陈胜有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2]1207王濬修建宅第,在门前开数十步宽的道路,目的是要使路上能容纳长戟幡旗的仪仗。这种做法与气魄,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的气魄何其相似!王濬“陈胜有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感喟,使我们看到了王濬的鸿鹄之志,显示出王濬对《史记》人物典故的稔熟。王濬因灭吴功勋卓著,拜为辅国大将军、抚军大将军。后王濬遭人诬告,他在向晋武帝上书自辩的奏章里,多次引用《史记》人物或事件以自明。“虽燕主之信乐毅,汉祖之任萧何,无以加焉……昔乐毅伐齐,下城七十,而卒被谗间,脱身出奔。”[2]1212-1213引用乐毅故事,表白自己的忠贞。
关于当时人们学习谈论《史记》的情景,《晋书》中也有记载。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朝中重臣,长于清谈。《晋书·王戎传》云:“(王戎)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仪,善发谈端,赏其要会。朝贤尝上巳褉洛,或问王济曰:‘昨游有何言谈?’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2]1232在这次洛水游乐中,当时的政坛显要和以学术、诗文著称的名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谈吐风趣优雅、思维敏捷活跃。文学家张华,高论《史记》《汉书》的异同优劣,娓娓动听;哲学家裴頠,善谈名理之学,滔滔不绝;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评说张良、季札,高超而玄远。这段记载,既表现出魏晋风度的魅力与光彩,也表明了当时社会名流对《史记》《汉书》的热衷,对《史记》人物典故的娴熟。关于张华,《晋书·张华传》云:“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2]1068张华虽身为宰相,但他“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2]1074。东晋文学家曹毗,“少好文籍,善属词赋”[2]2386。他因做官名位不达,写成《对儒》一文。在文中多次引用《史记》人物典故,以抒发怀才不遇之情。“子不闻乎终军之颖,贾生之才,拔奇山东,玉映汉台,可谓响播六合,声骇婴孩,而见毁绛灌之口,身离狼狈之灾。”[2]2387妙用周勃、灌婴谗嫉贾谊典故,暗含自己不被重用的原因。此外还有文学家伏滔、书法家应詹、大将甘卓、大臣熊远、陈頵、蔡谟等也多次在诗文或奏章中引用《史记》人物典故。
在《晋书·志》总论中,有关于司马迁《史记》的评论。如《晋书·天文志》总论云:“及汉景武之际,司马谈父子继为史官,著《天官书》,以明天人之道……及班固叙汉史,马续述《天文》,而蔡邕、谯周各有撰录,司马彪采之,以继前志。”[2]277道出了司马迁首创《天官书》的意义价值。《晋书·律历志》总论云:“太史公《律书》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轨则,一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之本,其于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2]473-474引用司马迁的论断,说明乐律和历法的重要性。
通过《晋书》我们发现,对于司马迁的身世遭遇,当时文人士大夫不仅深深同情,而且还常常作为典故加以引用。东晋大臣刘隗,“雅习文史”[2]1835,颇有文才,为官刚正,不畏权贵,先后上书弹劾王籍之、梁龛、宋挺等人,在奏章中多次引用司马迁故事及《史记》人物典故作为论据,增强说服力。《晋书·刘隗传》记载,丞相行参军宋挺,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生。刘陶死后,他违背伦常,强娶其爱妾为小妻。又贪赃枉法,盗窃官布六百余匹,本应斩首弃市,但巧遇大赦而免予追究,后来,奋武将军阮抗欲任命宋挺为长史。刘隗得知后就上书弹劾宋挺,其中有:“昔郑人斲子家之棺,汉明追讨史迁,经传褒贬,皆追书先世数百年间,非徒区区欲厘当时,亦将作法垂于来世。”[2]1836汉明帝曾以官方立场,批评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13]682。刘隗引汉明帝诏书,批评司马迁的典故,虽然是作为反面教材告诫司马睿:宋挺虽遇赦免死,应予除名,禁锢终身。但说明作为大臣的刘隗,是熟知司马迁的身世遭遇的。杜弢是西晋末年荆、湘地区巴蜀流民起义军首领,“初以才学著称,州举秀才”[2]2621,后来晋元帝派王敦、陶侃等讨伐杜弢,杜弢兵败欲投降朝廷,朝廷不许。杜弢写信给昔日器重自己的南平太守应詹,回忆昔日友谊,并陈述曰:“昔虞卿不荣大国之相,与魏齐同其安危;司马迁明言于李陵,虽刑残而无慨。”[2]2622引用司马迁故事,说明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于是应詹把杜弢的书信,转呈给司马睿,并为杜弢和流民请愿说情,请求安抚接纳他们,丞相司马睿最终接受杜弢投降。这段记载说明司马迁的故事,不仅当时知识分子通晓,就连绿林好汉也知晓。
两晋时期文人学士在学习《史记》的过程中,还对《史记》人物进行评价。东晋将领、权臣桓玄,曾作《四皓论》一文,与善于清谈的大臣殷仲堪品评商山四皓的功过。《晋书·殷仲堪传》云:“桓玄在南郡,论四皓来仪汉庭,孝惠以立。而惠帝柔弱,吕后凶忌,此数公者,触彼埃尘,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党,夺彼与此,其讐必兴。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终吉,隐以保生者,其若是乎!以其文赠仲堪。”[2]2196桓玄认为商山四皓应该布衣素食,隐居山林以保养终生,不必参与到刘、吕二姓权力之争的斗争中。针对桓玄的观点,殷仲堪撰写了《答谢玄四皓论》一文予以批驳。“若夫四公者,养志岩阿,道高天下,秦网虽虐,游之而莫惧,汉祖虽雄,请之而弗顾,徒以一理有感,泛然而应,事同宾客之礼,言无是非之对,孝惠以之获安,莫由报其德,如意以之定籓,无所容其怨。且争夺滋生,主非一姓,则百姓生心,祚无常人,则人皆自贤。况夫汉以剑起,人未知义,式遏奸邪,特宜以正顺为宝。天下,大器也,苟乱亡见惧,则沧海横流。原夫若人之振策,岂为一人之废兴哉!苟可以畅其仁义,与夫伏节委质可荣可辱者,道迹悬殊,理势不同,君何疑之哉!”[2]2196殷仲堪认为商山四皓所以奋力救世,不是为一个人的兴废,是为了国家的安稳,使仁义畅行于世。可谓见识高远!在探讨与争鸣中,《史记》人物典故更加深入人心。
两晋时期,不仅汉族文人学士研读《史记》,匈奴和鲜卑的统治者也在研读。刘元海是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之后,十六国时期前赵政权的开国皇帝。《晋书·刘元海载记》云:“(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2]2645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品评《史记》人物,以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2]2645-2646刘元海感叹随何、陆贾无武功,不能建功封侯;周勃、灌婴无文采,不能开创教化的大业,以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
慕容氏是古代鲜卑族的一支,在南北朝战乱年代,慕容家族骁勇善战,在中国北方建立了燕国,成为当时十六国中的佼佼者。《晋书·载记》记载了慕容家族在历史上的辉煌。这是一个雅好文籍的家族,从慕容廆到儿子慕容皝,再到孙子慕容儁,都是饱学之人。慕容廆是一位武功高强、富有智慧谋略的杰出人物,为部落生存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晋书·慕容廆载记》云:“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长八尺,雄杰有大度。安北将军张华雅有知人之鉴,廆童冠时往谒之,华甚叹异,谓曰:‘君至长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2]2803-2804在晋成帝司马衍即位后,慕容廆为侍中,位特进。慕容廆与东晋太尉陶侃友善,曾写书信给陶侃,表示愿意为复兴东晋做出贡献。其在书信中云:“君侯植根江阳,发曜荆衡,杖叶公之权,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员殆得极其暴,窃为丘明耻之。区区楚国子重之徒,犹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厉已戒众,以服陈郑;越之种蠡尚能弼佐句践,取威黄池;况今吴土英贤比肩,而不辅翼圣主,陵江北伐。”[2]2809引包胥、伍员、文种、范蠡等典故,希望在北伐事业中建立功业。慕容皝是慕容廆第三子,十六国时期前燕的建立者,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能攻善战的军事家。《晋书·慕容皝载记》云:“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2]2826慕容儁是慕容皝第二子,前燕景昭帝,“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2]2842。慕容皝、慕容儁雅好文籍,《史记》《汉书》等成为他们必须阅读的史书。
四、鉴戒功用与史学地位的提高,是两晋《史记》身价提升的主要原因
两晋时期,学习研究司马迁与《史记》初步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史记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究其原因,除了“乱世多史”的传统之外,还与《史记》本身的鉴戒功用、魏晋时期史学地位的提高等密切相关。
从史学自身的特点看,《史记》本身所具有的鉴戒功用直接刺激了人们的传播与接受。我国是一个重视史学的国度,注重史学鉴戒功用,强调“以史为鉴”“以史资治”。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迭起、换代频繁。统治者和有志之士,迫切希望通过著史或前代史书总结经验教训,为当朝统治者提供治国安民的借鉴。“魏晋南北朝时期,尚有许多史家都是立足于史学的鉴戒功用而竞相编写史书。”[14]97史学家司马彪认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2]2141所以撰写《续汉书》。袁宏认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9]1说明史学具有“通古今”“笃名教”的作用,因此撰写《后汉纪》。《晋书·陈寿传》云:“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2]2138道出了陈寿《三国志》的宗旨。本着史书的鉴戒功用,当时史学家纷纷著史,出现了干宝《晋纪》、华峤《汉后书》、陆机《晋纪》、王隐《晋书》、虞预《晋书》等史书。
在编写史书的同时,人们也注意从前代史书中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良策。《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就成为人们必须阅读的史书。对于史书的鉴戒功用,司马迁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评价《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4]3297司马迁认为:“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4]3298道出了《春秋》的鉴戒功用。司马迁写作《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15]2735。他洞察古今三千年人事的盛衰、存亡、成败、得失,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政治家的卓识,在《史记》的写作中有意无意地为统治阶级提供一些治国的原则,希望对西汉王朝乃至以后的统治者有所帮助,有所借鉴,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终极目标。正因为《史记》本身所具有的鉴戒功用,直接刺激了人们对它的传播与研读。东晋大臣刘胤,“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结时豪”[2]2113,在八王之乱中,刘胤依附冀州刺史邵续。邵续由于势力薄弱,打算投靠石勒。刘胤劝邵续说:“夫田单、包胥,齐楚之小吏耳,犹能存已灭之邦,全丧败之国。今将军杖精锐之众,居全胜之城,如何坠将登之功于一蒉,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2]2113用田单保存灭亡国家、申包胥保全丧败国家的典故,批评邵续投靠石勒的行为。
西晋大臣江逌,不仅学习《史记》,还常常用《史记》中的典故规劝皇帝。“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书》洪祀之制,于太极前殿亲执虔肃,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逌上疏谏曰:‘臣寻《史》《汉》旧事,《艺文志》刘向《五行传》,洪祀出于其中。’”[2]2174在其奏章中,多次引用《史记》人物故事,规范人主。“穆帝将修后池,起阁道,逌上疏曰:‘汉高祖当营建之始,怒宫库之壮;孝文处既富之世,爱十家之产,亦以播惠当时,著称来叶。’”[2]2172-2173体现了《史记》的鉴戒作用。
魏晋时期史学地位的提高,是两晋《史记》传播与接受的学术背景。魏晋时期史学地位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史学的重视;二是史学脱离经学而逐渐走向独立。
政府对史学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对史官制度的完善和对史官选拔制度的制定上。在我国史学史上,设置专职史官,撰写史书,从曹魏开始。《晋书·职官志》云:“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2]735至两晋时期,由于史学的快速发展,史官的编制、选任、品秩、行政隶属关系及职责分工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西晋武帝时,开始设立专门的著作机构——著作局,隶属中书省。到晋惠帝时,著作局隶属秘书省。著作局最大的特点是官方设局,专修国史。著作局内设著作郎、佐著作郎、著作令史。他们的职责是“掌国史,集注起居”[16]490。撰修国史、集注起居是史官的主要职责。在选任史官上规定,“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2]735。对此,《晋令》有明确记载:“‘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8]178可见作为著作郎要有一定的史学功底,同时显示出当时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两晋时期的史官制度,使一些德才兼备的士人脱颖而出。何嵩“博观坟籍……领著作郎”[2]1000。干宝“少勤学……以才器召为著作郎”[2]2149。据笔者初步统计,《晋书》记载的著作官,大约有50 多位。诸如华峤、陈寿、司马彪、陆机、束皙、王隐、虞预、干宝、张载、孙楚、王涛、孙盛、孙绰、张亢、王沈、朱凤、谢沈、袁山松、徐广、习凿齿等,他们或少年出众,或精通经史子集,或孜孜不倦,均以才学任著作官。如孙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2]2148。徐广“性好读书,老犹不倦”[2]2158-2159。习凿齿“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2]2152。袁宏“文章绝美”[2]2391。束皙“博学多闻”[2]1427。张载“博学有文章”[2]1516。王隐“博学多闻”[2]2142。谢沈“博学多识”[2]2152。
动荡不安的魏晋时期,儒学失去了两汉时期独尊的地位,史学脱离经学而逐渐走向独立,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此《晋书》也作了记载。《晋书·石勒载记》记载,石勒于晋元帝太兴二年(319)自立为赵王后,即“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2]2735。石勒在建国初期,就设置了史学祭酒,这是史书最早关于“史学”一词的记载,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史学从此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在此背景下,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西晋目录学家荀勖,“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2]1154。荀勖以郑默《中经》为底本,写成《中经新簿》,把史学从经学中划分出来列为丙部。这不仅显示了当时史学蓬勃发展的状况,又说明史籍推动了目录学的创新。东晋著作佐郎李充,受命以荀勖所撰《中经新簿》为蓝本,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2]2391李充以五经为甲部,史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把史部提升到仅次于经学的地位,于是史学与经学同样成为教授与学习的对象。“经史”“文史”并称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郑冲“耽玩经史”[2]991,冯紞“少博涉经史”[2]1162,虞预“雅好经史”[2]2147,名士刘殷“博通经史”[2]2288,陈寿“锐精《史》《汉》”[12]184,大臣戴邈“尤精《史》《汉》”[2]1848,名士张华“善说《史》《汉》”[2]1232,大臣刘隗“雅习文史”[2]1835,甚至少数民族统治者也是如此,如匈奴人刘元海“《史》、《汉》、诸子,无不综览”[2]2645,鲜卑人慕容皝“雅好文籍”[2]2826,慕容儁“雅好文籍”[2]2842。
在此学术背景下,史学获得蓬勃发展。梁启超先生云:“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17]21史书数量多、史书种类多、私人修史多,是魏晋时期史学兴盛的标志。范文澜先生指出:“东晋南朝士人在学术上所走的路不外儒、玄、文、史四学。史学既是士人事业的一种,私家得撰写史书,又还没有官修的限制,因之东晋南朝史学甚盛。”[18]196据李颖科先生初步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断代史来说,同一种史书每每多达二、三十家。如这一时期编写的东汉历史有十二家,三国历史二十余家,晋史二十三家,十六国史三十家,南北朝史十九家”[14]97。考查两晋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主要有陈寿《三国志》、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王沈《魏书》、束皙《晋书》、王隐《晋书》、虞预《晋书》、朱凤《晋书》、谢沈《后汉书》、袁山松《后汉书》等。这些纪传体史书,在体例上采用司马迁《史记》首创的纪传体,在叙事写人上学习《史记》列传写人的方法。
随着史学脱离经学而逐渐走向独立,司马迁与《史记》的史学地位得以提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士大夫家多有其书,《史记》得以广泛流传。当时的文人学士乃至大臣、名将、绿林好汉,以及少数民族统治者,或对《史记》进行考证与注释,或学习研读《史记》,或从不同角度对司马迁与《史记》进行精彩评论,或讲授《史记》,共同为《史记》的传播做出贡献。《晋书·孝友·刘殷传》云:“(刘殷)弱冠,博通经史,综核群言,文章诗赋靡不该览。性倜傥,有济世之志,俭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颓然而不可侵也。……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2]2288-2289刘殷七个儿子,个个贤能,其中有五个儿子分别学习《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另外两个儿子学习《史记》和《汉书》。所以《晋书》称其“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当时学者还对《史记》著名人物的优劣进行比较评价,其中张辅《名士优劣论》最有名。《名士优劣论》所论名士主要有管仲和鲍叔、曹操与刘备、乐毅和诸葛亮等。其论管仲和鲍叔曰:“管仲不若鲍叔,鲍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三归反坫,皆鲍不为。”[2]1640高度赞扬鲍叔的忠贞与智慧。其评论乐毅和诸葛亮曰:“乐毅诸葛孔明之优劣,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国之兵,以破强齐,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此则仁者之师,莫不谓毅为优。余以为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19]1114认为从仁义、忠贞、智谋、爱民等方面比较,乐毅不如诸葛亮。可谓见仁见智。
当时的文学家也从不同角度学习、接受司马迁与《史记》。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对司马迁与《史记》有着浓厚的兴趣。司马迁曾作《悲士不遇赋》,抒发自己不幸的遭遇和满腔的悲哀与愤慨。陶渊明也有《感士不遇赋》。其《感士不遇赋并序》云:“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20]145明确表明自己此赋是受司马迁影响而作。其《读史述九章》云:“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20]179《读史述九章》是一组专咏《史记》人物的诗歌。诗中所歌咏者依次为伯夷与叔齐、箕子、管仲与鲍叔、程婴与公孙杵臼、孔子七十二弟子、屈原与贾谊、韩非、鲁二儒、张长公等历史人物。不仅体现出陶渊明对司马迁《史记》的接受,也表现了陶渊明的政治理想与人生最求。特别是《咏荆轲》诗,作者借古喻今,通过赞扬荆轲刺秦王的壮举,抒发自己对实现的憎恨。在晋代,还有一些咏史诗从《史记》中取材。挚虞的《赞黄帝》,赞颂黄帝的美德,抒发自己的仰慕之情。吴隐之的《酌贪泉诗》,赞美伯夷、叔齐的高洁,表明自己的廉洁。傅玄的《何当行》,歌咏管仲和鲍叔的真挚情谊,抒发自己的向往之情。左思的《咏史八首(其六)》,歌颂荆轲傲视天下的英雄气概,表明自己鄙视权贵、怀才不遇的情怀。卢湛的《览古》,歌颂蔺相如的机智勇敢和无畏精神,表明自己的敬慕之情。以诗歌形式歌咏《史记》人物,不仅使人物形象生动、深入人心,而且使人物身上富有了诗的意味。但相对来说,人们更多的是从史学角度研究《史记》,提升了《史记》的身价,而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的则寥寥无几。到了唐代,人们才真正从文学角度去研究、欣赏《史记》。
晋人对司马迁与《史记》的关注与传播,还体现在对司马迁祠墓的营建上。据《水经注·河水卷四》记载,司马迁祠墓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310)。“陶水又南径高门南,盖层阜堕缺,故流高门之称矣。又东南径华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阳城西北四里许。故司马迁《碑文》云:高门华池,在兹夏阳。今高门东去华池三里。溪水又东南径夏阳县故城南。服虔曰:夏阳,虢邑也,在太阳东三十里。又历高阳宫北,又东南径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太史公自叙》曰:迁生于龙门。是其坟墟所在矣。”[21]47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离经叛道的“谤书”。殷济崇拜敬仰司马迁,他“瞻仰遗文”,以卓越的见识、大无畏的精神,率先给司马迁修庙立祠。这不仅提升了司马迁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而且使后人能够瞻仰司马迁的遗迹,为宣传司马迁与《史记》,弘扬司马迁精神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殷济为司马迁修庙立祠,从侧面也反映出司马迁与《史记》在晋代知识分子心中的位置。
不仅如此,当时学术界考量史学家和史书常常把司马迁与《史记》作为标准。如《晋书》称赞葛洪“著述篇章富于班马”[2]1913。华峤《汉后书》完成后,当时的中书监荀勖、太常张华、侍中王济等人,认为该书“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并建议“藏之秘府”[2]1264。《文心雕龙·史传》评论陈寿《三国志》云:“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22]189荀勖、张华认为《三国志》可以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相媲美,刘勰赞同此观点“非妄誉也”。《晋书·陈寿传》论赞云:“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自斯已降,分明竞爽,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2]2159认为《三国志》是次于班马之后的著作。这些都说明当时史学界对司马迁与《史记》的肯定与高度评价。
综上所述,相对于两汉来说,两晋时期传播与接受司马迁与《史记》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阅读层面来说,还局限于上层社会,普通老百姓还没有成为阅读的主体;从研究层面来说,两晋时期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从评价角度来说,基本上都是从史学方面进行评价,且大多是只语片言、零星段落,鲜有真正从文学角度论及《史记》文学成就的。虽然如此,这一时期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给后代学人留下了许多疑案,而后代学人正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深入,取得了新的成就,推动了史记学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