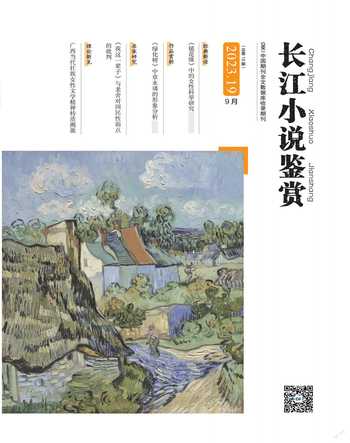论《达洛卫夫人》中的对立统一
[摘 要] 对立统一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创作的核心理念。《达洛卫夫人》作为伍尔夫将“对立”与“统一”结合得最为精妙的小说之一,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生命意识三个方面都贯彻了这一理念。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塑造了一组异体同质的人物形象——克拉丽莎·达洛卫和赛普蒂默斯,他们看似相反、实则同一。作者在刻画人物时有意通过平行相交的叙事结构使两个形象形成对应关系,两者在对比中完善了自身形象。这种对立统一背后传达出的是同一种生命意识,即对自我生命的超越。
[关键词] 弗吉尼亚·伍尔夫 《达洛卫夫人》 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9-0031-04
《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1925)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2)的代表作之一,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达洛卫夫人一天中的漫游经历。伍尔夫运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不断切换视角,通过现实与回忆的交织呈现人物的现实处境和精神世界。《达洛卫夫人》的人物塑造与叙事结构在意识流的催化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部小说是伍尔夫创作风格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达洛卫夫人》以女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卫(Clarissa Dalloway)为核心,以晚宴为线索,塑造了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人物形象——克拉丽莎·达洛卫和赛普蒂默斯(Septimus)。这种对立与统一的理念不仅出现在小说的人物塑造中,还是小说叙事结构,乃至核心价值的根基。弗吉尼亚·伍尔夫将对立统一的创作理念贯穿小说始终。换言之,对立统一不仅是《达洛衛夫人》的创作手法,更是其灵魂所在。
本文旨在通过文本细读分析克拉丽莎·达洛卫与赛普蒂默斯两个主要人物之间异体同质的特性,通过人物塑造的对立与统一进一步揭示小说叙事结构的平行与相交,探索两者之间相互推动的内在关联和其背后所蕴含的超越生死对立的生命意识。
一、异体同质的人物形象
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是《达洛卫夫人》中一组相互呼应的人物形象。表面上,他们之间只存在一种擦肩而过的间接关系;实际上,他们在意识层面有着更深层次的同质性。他们之于彼此,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看似完全相反,实际上分享着同一个精神本源。
克拉丽莎·达洛卫是典型的英国资产阶级贵妇人形象,她是理性的代表,斟酌利弊后嫁给了议员理查德·达洛卫(Richard Dalloway),而非恋人彼得·沃尔什(Peter Walsh)。婚后达洛卫夫妇相敬如宾,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也灵巧可爱。达洛卫夫人每天只需要关心买花、缝补衣裙、操持晚宴之类的琐事,她虽已年近中年,但依然优雅美丽。表面上看,达洛卫夫人的生活是资产阶级贵妇生活的理想范式,但实际上,克拉丽莎·达洛卫并不享受这种生活,她时常被恐慌和不安袭击,萌生死亡或人生重来的想法。她自我认知中的克拉丽莎与外界所看到的达洛卫夫人并非完全一致,以克拉丽莎(敏感孤独)为生命基调的达洛卫夫人,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在试图排解生活的空虚,寻找自己生命的出路。
与达洛卫夫人不同,赛普蒂默斯来自社会的底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存,却因目睹长官埃文斯(Evans)的死亡而痛苦不堪,以至于精神错乱,看见死者的幻象,听见不存在的声音。赛普蒂默斯是非理性的代表,战前,他因为缥缈的爱情和文学作品中的人文主义理想而志愿入伍,为保卫英国而战;战后,战争的残酷和战友的死亡使其丧失感受的能力,他在惊慌之下草率地娶了意大利姑娘卢克丽西亚(Lucrezia)为妻。冷漠对待战友死亡的罪恶感、人生的虚无感和无法回应爱的无力感始终包围着赛普蒂默斯,他无法排解,遁入癫狂是他得以喘息的唯一方法。然而,本该承担拯救职能的医生却成为赛普蒂默斯死亡的直接推动者。霍姆斯医生(Dr Holmes)和布雷德肖爵士(Sir William Bradshaw)作为绝对理性的化身,为强迫行为披上拯救的外衣,他们将“平稳”(proportion)和“感化”(conversion)视为女神,按出诊时间和距离收费,让病人与家人隔离,住进自己的疗养院“恢复”平静。“平稳”和“感化”疗法背后是赤裸的功利主义和对生命的漠视。赛普蒂默斯可以在自由和爱中忍受孤独和疯狂,但他无法忍受漠视人性者对自己的肉体约束和精神入侵,他在医生迫近的那一刻选择了自杀,以毁灭性的身体暴力对抗生命受限的压抑。
伍尔夫在为现代图书馆版《达洛卫夫人》的序言中写道:“赛普蒂默斯是作为达洛卫夫人的替身创造出来的(Septimus is intended to be Clarissas double)。”[1]小说的最初构想中没有赛普蒂默斯这一角色,只有达洛卫夫人走向死亡,赛普蒂默斯的出现和自杀代替了达洛卫夫人原本的结局。作者的意图进一步强化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表面上,他们处于无处不在的对立之中,性别、身份、性格、结局等完全相反。克拉丽莎·达洛卫是身处上流社会的贵妇,以她为中心的世界是明媚而充满生机的。赛普蒂默斯则是隶属于平民阶层的普通士兵(战前是一位普通职员),以他为中心的世界是阴郁而疯狂的。但实际上,他们拥有相同的内核,包含对孤独与虚无的对抗和对生命的渴望。正因如此,克拉丽莎才会对赛普蒂默斯的死感同身受,在完全不认识他的情况下,本能地将医生之流视作扼杀灵魂的恶的化身,认为是他们逼得赛普蒂默斯自杀。这种精神层面的同质性使两人的生命线在小说叙事层面上发生交集。
二、平行相交的叙事结构
《达洛卫夫人》是一部以人物动向为线索的意识流小说,人物的情感意图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情节的走向。两位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卫与赛普蒂默斯就外在的身份而言,可谓层层对立,他们的生命线本该没有任何交集,但两人高度同一的精神内核却直接促成他们的相遇。小说的前半部分,克拉丽莎·达洛卫与赛普蒂默斯的行动构成了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达洛卫夫人去花店买花然后经由邦德街回家准备晚宴;赛普蒂默斯与妻子从邦德街经过,在摄政公园闲坐,随后赴12点与布雷德肖爵士的诊约。直到结尾,两个人才在这一天的最后时刻——晚宴——相会。由于达洛卫夫人第一次听说赛普蒂默斯的名字时他已自杀去世,所以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行线相交。尽管两人的交点没有落在实处,但赛普蒂默斯的死亡直接推动了达洛卫夫人生命的延续,两者的生命线在那一刻合二为一。
瞿世镜先生将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中联结复杂人物、复杂意识、复杂人生的方式称作“立体网状结构”,他认为相同的客观时间、客观地点、客观事件,布雷德肖爵士,莎士比亚剧本《辛白林》中的诗句构成了连接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的三座桥梁[2]。在此基础上,达洛卫夫人与赛普蒂默斯之间存在着三个层面的联系,而且这三个层面的联系并非简单的平铺关系,而是层层递进的。它们连接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促使平行发展的两条线索相交,最终使得两个相对的人物形象发生重叠。
首先,相同时空的客观事件构成了两人之间的事实联系。如邦德街上汽车爆胎引发了整条街人的关注,达洛卫夫人与赛普蒂默斯分别展开自己的联想;摄政公园上空飞机喷气写字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通过目光的焦点将叙事视角从达洛卫夫人转向赛普蒂默斯。这种事实联系表面上强调了两人之间的陌生感和无法逾越的距离感,但同时,它也像一根无形的线把两个人的命运缠绕在一起。
其次,人物构成了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之间的精神联系。如布雷德肖爵士,他既是达洛卫夫人晚宴的客人,又是赛普蒂默斯的医生,正是他将赛普蒂默斯自杀的消息传递给达洛卫夫人。赛普蒂默斯的死亡以布雷德肖爵士为中介造成了两人之间的精神共感,达洛卫夫人与赛普蒂默斯分享了同样的感受:对布雷德肖爵士(戕害人性者)的厌恶,对生的恐惧和对死亡的认同。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的形象因为其深层的同质性开始发生重合。
最后,重复出现的意象构成了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的生命联系。如钟声、莎士比亚的诗句和楼对面的老者。第一,钟声作为《达洛卫夫人》的锚,它在人物大段的意识流动中标记了客观时间,成为故事发展的节奏点。钟声每一次敲响既勾连起人物与现实的关系,又宣告死亡的迫近。赛普蒂默斯跳楼后,丧钟响起。达洛卫夫人在斗室为赛普蒂默斯抛弃自己的生命而高兴,决定振作精神时,大钟又一次敲响,成为归返生命的号角。钟声将达洛卫夫人与赛普蒂默斯的生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第二,莎士比亚戏剧《辛白林》中的诗句“不要再怕骄阳炎热,也不怕隆冬严寒(Fear no more the heat o the sun, nor the furious winters rages.)”①是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常念的两句诗。赛普蒂默斯自杀前躺在沙发上告诉自己不要再怕了,随后他与妻子一同打闹取笑,获得了人生鲜有的快乐。他在跃出窗户前一刻想道:“他不要死。活着多好。阳光多温暖。”[3]知道赛普蒂默斯自杀而死后,达洛衛夫人脱口而出“不要再害怕火热的太阳”[3]。莎士比亚的诗句在小说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不再害怕死亡;二是指不再害怕生活,生与死在此处合二为一。赛普蒂默斯的死和达洛卫夫人的生重叠在一起,表达相同的含义。第三,老者的形象在小说中可以看作是死神的化身。赛普蒂默斯跳窗的时候,对面楼梯上一位老者停下来瞪着他。达洛卫夫人在斗室独自一人思索赛普蒂默斯的死亡时,也有一位老妇人盯着她,但这位老妇人立刻熄灯上床。就像是死神在赛普蒂默斯跳楼时凝视着他直至死亡,却在克拉丽莎·达洛卫思索死亡时转身离开。这个场景预示着达洛卫夫人在赛普蒂默斯生命的终点停顿,然后继续向前。两人的生命线路由此交叠在一起,达洛卫夫人的生命即赛普蒂默斯生命的延续。
《达洛卫夫人》平行相交的叙事结构与其异体同质的人物形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叙事结构的对立统一实则是人物形象对立统一的另一种体现。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表面的对立感和精神的同一性决定了小说的总体结构,而平行相交的叙事结构也反过来促使两人形象由对立走向重合。
三、重叠合一的生命意识
对立元素在《达洛卫夫人》中无处不在,它构成了小说的细节,也成为小说内核的一部分。克拉丽莎·达洛卫与赛普蒂默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立”的化身,性别的对立、身份的对立、性格的对立等,而他们身上的一切对立最终都指向了生与死的对立。而弗吉尼亚·伍尔夫正是通过达洛卫夫人的生和赛普蒂默斯的死表达了她的生命意识——一种对生死的统一和超越。
生和死是人表达人生态度最为直接和激烈的方式。一般意义上,我们将继续生活看作是对于生命的积极接受,而将死亡视为对于生命的消极逃避。然而在《达洛卫夫人》里,生和死的界限不再分明。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作为精神世界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人物,他们的生命线在小说的结尾融为一体。因此,他们的生之选择和死之选择事实上在表达相同的含义,即完成对自我生命的超越。
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的生命意识并不指涉生活与死亡本身,而是一种对于生命现状的抗争。正如小说中重复出现的莎士比亚戏剧《辛白林》中的诗句“不要再怕骄阳炎热,也不怕隆冬严寒”[3],它既是在说“不再害怕生活”,也是在说“不再害怕死亡”,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最终的选择中同时包含两者。正因如此,从小说开篇就念叨着要自杀的赛普蒂默斯才能够在最后重拾感受力,看到自然的美好,有能力与妻子欢笑打闹,体会到久违的生活的乐趣。也正因如此,在以霍姆斯医生为代表的危险迫近时,赛普蒂默斯能够毫不犹豫地选择死亡。克拉丽莎·达洛卫也是一样,她为赛普蒂默斯的死亡而高兴,认为那个青年虽然死亡却“保持了生命的中心”[3]。而她自己面对“生之恐怖”,也有勇气将“生的意义”注入到达洛卫夫人这一空洞的外壳之中,重新回到晚宴的人群中间。
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生命意识的核心,实则是对生命受限的抗拒。达洛卫夫人每天被困在资产阶级贵妇人的无聊生活中,赛普蒂默斯则被困在精神病人的失语处境中。他们均是被主流话语规定,被社会中心边缘化的存在。因此,他们都在自我身份的规范下失去了行动的主动性,使自己的生命不断受到限制,失去原有的光彩。赛普蒂默斯在疯狂中的妄言正是超越生命的真理:“第一,树木有生命;第二,世上没有罪恶;第三,爱和博爱。”[3]只有保持生命力、感受力和爱人的能力,才能够掌握生活的主动性,将自己从孤独感和虚无感中解脱出来,不被陈旧的生活所困,从而超越自我。正因如此,赛普蒂默斯无法忍受重获活力的生命有再次受限的可能,死亡是他对抗冒犯生命的外部世界,超越现有生命的方式。他的死亡也为达洛卫夫人带来启示,她重新回到晚宴,其内在的克拉丽莎与外在的达洛卫夫人合为一体,去完成她尚未结束的“奉献(an offering)”,通过有限的活动创造新的价值,将其他孤独、无谓地消磨时间的人们聚拢起来,创造一个能够使他们突破生命局限的场域,达洛卫夫人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超越旧有的自我。
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生死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恰恰是对于生活至高无上的热爱,从中也能够窥见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对于生命的态度,与达洛卫夫人和赛普蒂默斯一样,伍尔夫选择死亡正是由于她热爱生活。
四、结语
《达洛卫夫人》如同一块竖立在桌面上的硬币,达洛卫夫人与赛普蒂默斯构成硬币相反的两面,精神与生命的同质性促使伍尔夫通过平行相交的叙事结构让其真正由对立走向统一,他们以一种超越生死的生命姿态面对现实世界。《达洛卫夫人》的人物塑造、叙事结构,生命意识无不体现着对立统一的思想观念。
《达洛卫夫人》中的对立统一并非个例,实际上它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生涯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从《夜与日》(Night and Day, 1919)中以黑夜与白昼为代表的真实与表象的对立统一,到《海浪》(The Wave, 1931)中六个全然不同的声音的合唱,再到《奥兰多》(Orlando,1928)中的雌雄同体等,都蕴含着对立统一的思想。它所反映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二元对立模式的反思和消解,是对男与女、生与死、理智与疯狂等一系列对立的消解,也是对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的消解。伍尔夫希望借助对立统一完成一种容纳万物的小说形态,描绘出一种超越个体生命、关乎人类整体的一般性印象。《达洛卫夫人》正是她实践这一理想的重要尝试。
注释
① 出自莎士比亚戏剧《辛白林》第四幕第二场第258—259行,此处选用孙梁、苏美在《达洛卫夫人》中的译法。
参考文献
[1] Woolf V.Mrs Dallowa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2] 瞿世镜.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3] 伍尔夫.达洛卫夫人[M].孙梁,苏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 伍尔夫.海浪[M].曹元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袁欣,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