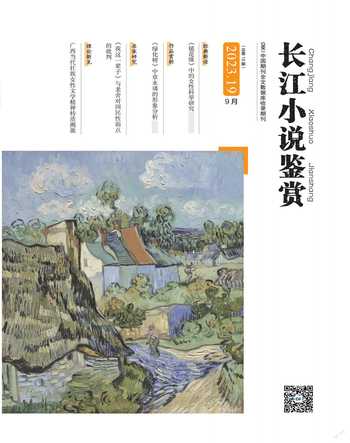论双雪涛笔下的“边缘人”形象
[摘 要] 近年来,东北文学重回大众视野,80后作家双雪涛即东北作家代表之一。双雪涛因其作品精妙的叙事手法、深邃的历史意识、真挚的人文关怀在文坛大放异彩,屡获大奖。其小说大多聚焦20世纪末“东北下岗潮”,叙写普通大众父辈与子辈之间寻常而又令人深思的故事。双雪涛笔下的人物形象以普通人为主,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作家书写的背后蕴含着文学与现实的双重价值。
[关键词] 双雪涛 边缘人 尊严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9-0012-04
“边缘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于1908年提出“陌生人”理论,进一步扩充了“边缘”的内涵。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在此基础上展开更深入的探究,从种族意义上对边緣人作出解释;帕克的学生斯通奎斯特对边缘人含义的界定深入到心理、文化、信仰等因素;后继者格林则从边缘性程度与主导群体的关系对“边缘人”进行阐述。虽然这些理论缺乏系统性,但这些探索仍为“边缘人”概念的界定做出了贡献。至今,文学领域虽无关于“边缘人”的明确范畴,但文学史上关于“边缘人”的书写从未停歇。
从郁达夫小说中孤独敏感的“零余者”,鲁迅小说中绝望反抗的“孤独者”,到刘震云笔下的李雪莲,池莉笔下的小市民,毕飞宇作品中的盲人推拿师……弱势群体始终是作家们书写的对象。双雪涛的小说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他的目光始终聚焦于“边缘人”这个群体。在他的笔下,“边缘人”是相对强势群体而言的弱势群体,亦是试图站在社会中心却无可奈何的失意人群。
一个好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1]。从一个失败者身上,可以看到更多东西。在此意义上,本文试图以双雪涛小说中的“边缘人”形象为切入点,从“自我尊严的捍卫者”“生命本真的坚守者”“爱与正义的救赎者”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以完成对其作品中“边缘人”形象的评价。
一、精神边缘:自我尊严的捍卫者
双雪涛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一个人把一种东西做到了极致,就接近了某种宗教性,而这种东西是人性中很有尊严的东西。”[1]在双雪涛的小说中,“奇人”形象多次出现,他们或是下岗工人,或是叛逆少年,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社会地位低下,但却对某一事物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们坚持自我,因个体与社会格格不入而陷入苦苦挣扎,由此成为社会上的“边缘人”。
在《大师》中,双雪涛塑造了“父亲”这一形象。父亲本是有编制的仓库管理员,虽然工作十分枯燥,但在那个年代却代表着一定的身份和地位。父亲平日里酷爱下棋,甚至到了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程度,工作之余或参加单位的象棋比赛,或去城里的棋摊下下棋,生活安稳又平静。但个人的生存总是难逃时代的掌控,突然下岗、母亲离开、爷爷去世,一系列的打击导致父亲一蹶不振,慢慢变成一个“傻掉”的人。生活越来越拮据,父亲终日穿着“我”肥大的校服,或喝酒捡烟蒂,或泡在棋摊上,四处游荡,伴随着工作的失去,父亲的尊严也随之失去。但幸运的是,象棋成为父亲唯一的精神寄托。
在象棋的世界中,父亲从不与人赌棋,恪守君子之交,即便棋艺精湛却从不把下棋当作谋生的工具。棋局是父亲纯粹明净的精神世界,一盘盘棋局中游荡的是父亲为人的尊严,以及面对人生的释然与坦荡。父亲之所以被称作“大师”,不仅仅因为他那出神入化的棋艺,更因为父亲的人生哲学和精神境界。“我”10岁那年母亲出走,父亲告诉我人可以没有文化,但做事情要善始善终;狱警与瘸腿和尚下棋,和尚愚弄狱警,双方僵持不下,父亲主动上前破局为瘸腿和尚解围;父亲一生从不赌棋,却在一场明明可以获胜的棋局中主动认输。在众人眼中,父亲从工人变成了“傻子”,生活窘迫甚至负担不起“我”的学费,但父亲传授给“我”的人生哲学,却成为激发“我”奋力前进的强大精神源泉。父亲通过一盘盘棋局找回自己的尊严,更捍卫了他人的尊严。于父亲而言,下棋是纯粹的精神享受,无关世俗,无关利益,棋局是父亲的精神“避难所”。
短篇小说《冷枪》中的“老背”同样也是一位有着独特手艺的“边缘人”,他在射击游戏中战无不胜,叱咤风云。无论现实还是游戏中,老背一直坚守着“公平”的原则,这是他的世界里“正义”的标准。老背凭借过硬的游戏技术射中无数“尸体”取得胜利时,能感受到自我生命的蓬勃向上,以及对自我尊严的强劲捍卫。而一旦这种公平的环境被破坏,即有人在游戏世界作弊时,老背就会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捍卫自尊。在这里,双雪涛并非鼓吹暴力,而是旨在呼吁人们关注边缘人面临的精神困境,边缘人也需要自尊、公平和正义。
从双雪涛的个人经历来看,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他有着一份父母亲戚都认可的稳定职业——银行柜员。但其在接受采访时却坦言,这份职业并不是他喜欢的,每月拿到的工资好似精神损失费。于是,他毅然辞职来到北京追寻自己的写作梦想。成为职业小说家后,双雪涛遇到了诸多困难:生活窘迫、家人不理解、稿费无法按时交付……然而这些困难并未将其压倒,他从未想过放弃,而是暗暗和自己较劲,默默捍卫着心中的文学梦。显然,这些经历无形中影响了其作品人物的塑造。不管是《大师》中的“父亲”,还是《冷枪》里的“老背”,抑或是双雪涛自己,他们都一度成为社会上的“边缘人”,但一旦进入到自己的场域中便成为强者。双雪涛书写这些“边缘人”,剖析边缘人群的生活环境与精神世界;站在“边缘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不刻意去描写他们生活上的失意与落魄;从客观的视角娓娓道来他们精神世界的困境,为“边缘人”发声,引导人们关注这个特殊人群。双雪涛用文字记录这个被边缘化却依然迸发强大生命力、保持着尊严的群体,作品触及现代人普遍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的无所依托,反映出他对现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二、成长边缘:生命本真的坚守者
双雪涛曾多次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段话,“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遺忘。”①这一理念始终贯穿双雪涛的小说创作。其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少男少女形象,他们有的是病态家庭成长起来的“叛逆”少年,在社会的疏离中一步步沦为“边缘人”;有的是应试教育体制下无所适从的“另类”,因不被理解而与社会隔绝。
在《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双雪涛塑造了一个在应试教育体制中游荡的人物形象。“安德烈”是班级里最特殊的同学,他无视课堂秩序和学校制度,入学首日即与老师发生冲撞,坚持自己叫“安德烈”而不是点名册上的“安德舜”,初中三年从未调换座位,并被“放逐”在教室最后一排,要求脱稿演讲《祖国在我心中》却拿着稿子讲“下水井盖为什么是圆的”……在学校的教育体系下,安德烈被视为“异类”,被老师多次打压,但安德烈的精神世界却永远充沛。然而,过盛的自我意识却使安德烈在生活中找不到自我的定位,现实的迷茫和精神世界的理想相互交织,每次的自我尝试都会遭受现实的碾压。因此,安德烈被社会“边缘化”,在精神病院中孤独地度过余生。但当安德烈知道学校不公平的暗箱操作时,他不考虑后果,只在乎好友被不平等对待,勇敢地揭露“我”的名额被人顶替的真相;作为重点初中的学生,安德烈身上也有独特的潜质,他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在试卷上乱画,但却可以准确估算出班主任每次到达的时间,还能侃侃而谈宇宙知识。边缘人“安德烈”身上流淌着生命最本真的态度:不趋炎附势,不妥协退缩,勇敢善良,敢于反抗。
不能遗忘被世界抛弃、被时代掩埋、被主流放弃的“边缘人”,是双雪涛在小说里传递的文学精神。在刻画这些青春期的“边缘人”时,双雪涛不仅书写个人命运,也聚焦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光明堂》中的柳丁一直处于病态的亲子关系中,成为病态家庭中的边缘人;《大路》中的“我”被送到工读学校,16岁拿上一把刀闯入社会;《安娜》中,安娜在控制欲极强的母亲的阴影下成长,极度敏感叛逆,缺乏安全感;《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当安德烈的父母被叫到校长室时,安德烈的父亲并不了解事情的原委却直接一脚把安德烈踢倒。学校秩序和家庭教育模式化的僵硬和教条式的僵化,无疑是导致这些少女少男边缘化的主要原因。《聋哑时代》中的刘一达和霍家麟同是有着天才特质的少年,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虽然二者结局不同,但指向的却是相同的社会问题。作为小说家,双雪涛的创作充满温度,其关注个体的生命价值,亦坚定地肩负反映社会现实的责任。
三、生存边缘:爱与正义的救赎者
耶鲁学派著名学者米勒曾经提出:“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或是与其他重复形式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2]也就是说,在一个小说家的创作中,相同的符号、相同的意象往往会重复出现。在双雪涛的作品中,“救赎”便是重复出现的主题,这一主题意蕴在一些边缘角色上体现更甚,即便被排挤在主流之外,他们仍旧渴望爱与浪漫、爱与自由、爱与正义。
《平原上的摩西》中的傅东心是双雪涛笔下为数不多的母亲角色,与传统的母亲形象不同,她并不关心儿子庄树的生活和学习成绩,在母子关系中表现得非常漠然,并且将这种态度延伸至婚姻乃至工作中,常常一个人安静地与书本为伴。但在对待老邻居家的孩子李斐时,傅东心却回归到传统意义上的“母亲”角色,她带着李斐学习知识,在承担“老师”责任的同时为李斐带去母亲般的关怀。傅东心将自己的心血付诸在李斐身上,指引李斐走出“平原”,完成“摩西”的使命。成年后的李斐同样继承了这种“摩西”色彩,将关爱给予照顾她的孙天博。在傅东心和李斐身上体现的是善良美好的底色,是对人性的坚持、对生命的抗争、对爱与正义的笃定。而在这种救赎中,最无限接近“摩西”的是“李守廉”。
《平原上的摩西》讲述了一个悬疑故事,由七个人不同的叙述视角构成,而李守廉则是隐藏在这七人话语下的真正凶手。卖了珍藏的邮票给女儿凑学费,为卖苞米的小贩出头袭击城管,因去“艳粉街”被警察误认成嫌疑犯,下岗导致生活拮据和尊严丢失……李守廉成为一个彻底的“边缘人”。但七个不同的叙事视角却呈现出李守廉形象的另一面:对待工作,李守廉恪尽职守,厂里的人都尊称他为“李师傅”;对待朋友,李守廉推心置腹,即便生活拮据仍将存款借给急需用钱的孙育新;对待陌生人,李守廉心怀善念,为被城管误伤的母女伸张正义。虽设置了情节上的巨大冲突,但双雪涛并未给李守廉安排一个“摩西”的结局。现实是残酷的,没有人能够是“摩西”,李守廉救赎不了自己也救赎不了别人,但他和他们是值得被铭记的,因为人人都在努力扮演“摩西”的角色。“坚持了一点自我的人,很多都沦为了失败者。当世界丧失正义性,一个人怎么活着才具有正义”[1],在渴望救赎和追求正义的平原上跋涉,永远具有意义。
“边缘人”被困于社会环境,孤独焦虑,但绝不妥协堕落,处于弱势的他们无法进行轰轰烈烈的反抗,“出逃”就成为渴望救赎的另一种形式。《飞行家》中的二姑夫不被众人理解慢慢处于社会边缘,自制热气球飞行器逃离艳粉街;《跛人》中的刘一朵在高考后一心要去北京放风筝;《光明堂》中的三姑跟随牧师出逃南方,柳丁付出一切要去北京寻找母亲。从小说的时代背景来看,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正经历着国企改革的阵痛,人们承受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压力,无所适从,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踱步,却迟迟找不到身份认同,这给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社会变革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但人们却始终牢牢坚守着内心的洁净与善良。对爱与正义的苦苦追寻,对救赎与被救赎的深深渴望,是双雪涛挖掘出的“边缘人”身上的坚定意志,并使之成为可以践行与传承的文学精神。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双雪涛对“边缘人”形象的塑造展示出“被遗忘的人”和“被遗忘的城市”。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科技水平日新月异,历史会记录那些做出过伟大贡献的人,但“边缘人”群体永远存在。双雪涛随父母从繁华的商业街搬到棚户区,对原来生活的环境而言他是边缘人,对艳粉街的孩子来说他也是边缘人,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能够更好地观察和体会边缘群体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边缘化的人并不是无用的,他们的人生并非毫无意义。他们经历苦难但不被苦难打倒,他们捍卫自我尊严,坚守生命本真,救赎爱与正义,他们是社会历史发展洪流中渺小的角色,却迸发出强大的能量。作为80后作家的代表,双雪涛担负起作家的社会责任,其笔下的“边缘人”形象凝聚着文学匠心,亦丰富了整个文学谱系上的边缘人群体。
注释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转引自双雪涛,《天吾手记》题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参考文献
[1] 走走.非写不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2] 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3]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
[4] 双雪涛.聋哑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5] 双雪涛.飞行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6] 双雪涛.天吾手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7] 张丛皞.青年新锐作家创作的叙事学维度—以双雪涛的小说为例[J].山东社会科学, 2020(11).
[8] 双雪涛,走走.写小说的人,不能放过那道稍瞬即逝的光芒[J].野草,2015(3).
[9] 张志平,王雪力.论双雪涛小说意象叙事彰显的人民情怀[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3).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段天赐,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