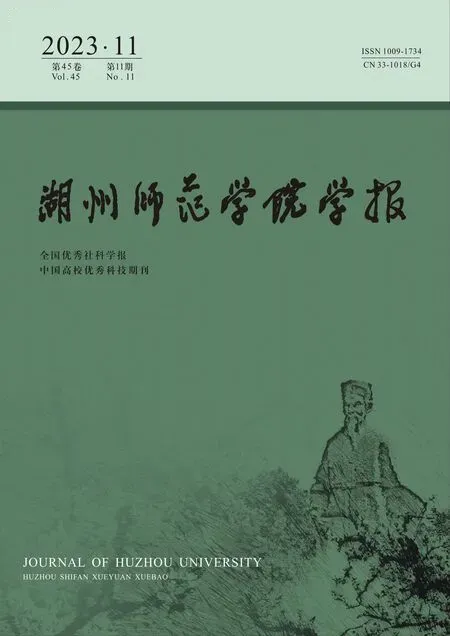“湖桑”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问题考述*
祝玉芳,李学功
(1.湖州师范学院 图书馆,浙江 湖州 313000;2.湖州师范学院 湖州发展研究院,浙江 湖州 313000)
论及蚕丝,翻检史志文献,自明清以迄近代,享誉中外“紫光可鉴”[1]206的湖丝几乎成为中华丝绸的代名词。湖丝因其细、圆、匀、坚、白、净、柔、韧的特点,远超其他地方蚕丝,形成“湖丝遍天下”[2]之局。如所周知,蚕丝所系在桑树、桑叶。在历史研究的回溯中,“湖州、嘉兴一带,土地肥沃,地势高爽,肥力与排水条件均较优越,最宜桑树种植。”[3]5至秦,湖州桑树的种植已经是“有地即栽,无一旷土”。(1)(明)王继祀:《重修永宁禅院记》,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一,《物产》。因此讨论的话题不妨从一个小切口介入,谈一点儿不成熟的认识。
一、问题缘起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力驳中国文化西来说。在是文中,李济先生曾举出三件无可辩驳的史实,其中之一就是蚕丝的发明。认为“在殷代文字中,蚕字和丝字也都多次发现。……正如骨卜术一样……始终是一种地道的中国式的文化复合体。”[4]508由此出发,我们将话题讨论的方向和关注点放在与蚕丝相关的“湖桑”身上。
从种植技术的角度来看,蒐览相关科技史著,发现有一个问题颇为有趣,即说到“湖桑”种属,目今所及的许多著述和研究文字,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湖桑源自鲁桑。如《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即谓:“湖桑原是南宋时由鲁桑南移至浙江的杭、嘉、湖地区,通过人工和自然选择,而成为公认的新桑种。”[5]331《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亦云:“湖桑是鲁桑南移至杭嘉湖地区后,逐渐形成的‘鲁桑的新类型’。”[6]434《补农书校释》作者认为:“湖桑是宋以后‘由嘉、湖人民通过提高嫁接技术和异地定向培育逐渐创造了一种新类型’。”[7]14《浙江农业文化遗产调查研究》谈及浙江湖桑也称:“湖桑,为鲁桑移植于杭嘉湖地区后通过自然和人工选择形成,故称湖桑。”[8]284《桑树高产栽培技术》亦谓:“江苏、浙江的湖桑都属于鲁桑系统。”[9]29《蚕业史话》亦云:“‘湖桑’的‘娘家’是在山东,也就是说它确实是鲁桑的变种。”[10]217
如此看来,所谓“湖桑”在人们一般的认识中,似乎不姓“湖”,而是姓“鲁”(按,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迄今犹在),原系宋代由“鲁桑”南移至浙江的杭、嘉、湖地区,经过人工和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个新种属,是谓“湖桑”。
于是悖论或曰困惑皆由此产生,即经考古发掘,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杭嘉湖所在地区已发现有人类养蚕缫丝的史迹,并有重要的出土遗物,最典型者莫过于考古工作者于1958年在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发现的距今4 700年之遥的珍贵绢片(绸片)。如果说“湖桑”乃是迟至宋代才藉由“鲁桑”之桑种所赋,那么早在新石器时代杭嘉湖地区蚕宝宝所赖以生栖的桑树,岂非成了“无本之源”“天外来客”?
真正的实相,到底是怎样的?这是我们的困惑,也是问题的指向所在。看来,“湖桑”这个本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还真值得下一番功夫,考索厘辨一二。
二、“湖桑”之辨
考诸历史文献,“湖桑”作为一个专有名称较为晚出,大致应在明清时期。徐光启《农政全书》论及蚕桑,虽未专门提及湖桑之名,但于蚕桑之事,有谓:“今天下蚕事疎阔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夥,取给于湖茧。”徐氏书中言及“湖茧”,称誉湖州“茧丝遍天下”[11]。迄清,“湖桑”之谓频出。(2)按,“湖桑”称谓散见于清人著述处甚多,如陈恢吾《农学纂要》、方濬颐《二知轩文存》、葛士濬《清经世文续编》、何德刚《抚郡农产考略》、卫杰《蚕桑萃编》、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等。
其实,围绕“湖桑”冠名产生的悖论性现象,已有学者注意到,如浙江湖州著名的地方志学者嵇发根等。嵇发根先生的研究前后有所变化,最初他认为“湖地之桑与‘鲁桑’无分先后,它们同样源远流长”。“湖地之桑北输,‘鲁桑’南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同等的意义。‘辽川无桑’,适与晋通好,自然‘求种’而去;北人南迁,也自然丢不下桑树这一‘衣食之本’,随带桑种在所必然。”“就湖地这个局部区域来说,土桑先而‘鲁桑’后。只不过其后‘本籍’桑与‘客籍’桑同荣同茂而已;而且二者都是‘野桑’。”[12]15反思所谓“鲁桑为桑之始”的说法“站不住脚”[12]15。随着学界对湖州钱山漾文化认识的深化,特别是学界对湖州丝绸之源地位的新认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传统看法。如嵇发根在之后的研究中就认为:“北宋时,湖州民间普遍使用桑树嫁接技术,以更换、优化桑树品种。土生野桑与引进鲁桑等培育为嫁接桑(家桑),逐渐形成优良桑树种群——湖桑。”[13]240翻检《十六国春秋》《晋书》和《通志》,均记载有“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一作辽州)之桑,悉由吴来”(3)(南北朝)崔鸿:《十六国春秋》卷四十六,《后燕录》四。参见《中国基本古籍库》,原据版本:明万历刻本;(唐)房玄龄:《晋书》卷一百二十三,《载记》第二十三;(宋)郑樵:《通志》卷一百九十一,《载记》。参见《中国基本古籍库》,原据版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显见,宋代以前确乎存在一个南桑北上的物种交流前史。
之所以人们会产生对湖桑认知的种种误读、误释,究其因盖在于:一是基于近现代以来农学界对既有桑树、桑种的研究和分析。二是鉴于历史上出现的三次“衣冠南渡”,北人南下所带来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物种南移的历史事实。三是缺乏对环太湖流域考古遗址中古桑树、蚕茧遗存材料的深入挖掘与分析。而其中第三点原因,窃以为是最为关键处。
就“湖桑”的知识发现与知识建构而言,有必要厘清一个认识,即关于“湖桑”,事实上存在一个湖桑的原生形态——“野桑”,或名之曰“土桑”,到次生形态——嫁接桑,即后世文献所称之“湖桑”(按,系鲁桑与原生形态的湖桑人工嫁接后之改良种属)的传承与创新转化过程。鉴此,后世典籍包括《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农业史籍文献,以及近今学者研究中所触及之湖桑种种,其所经眼者皆不过是“湖桑”的次生形态而已。
如所周知,湖桑是从人类文明进程初阶之原始时代最初的野桑或曰土桑发展而来,经由春秋战国时期(4)按,当其时太湖流域所处吴越之地,历春秋战国大分化、大变革之巨变,受吴越文化和楚文化之交互影响,原生形态期的湖桑——野桑或土桑,亦复名之越桑、吴桑或荆桑、楚桑等。延至两宋时代,原生形态的湖桑伴随着历史上“衣冠南渡”及其技术与物种南移的脚步,经过人工嫁接和改良,转变为次生形态的湖桑。也因此,次生形态的湖桑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北地桑种——鲁桑等的遗传基因与特点。清《抚郡农产考略》即谓:“湖桑,叶圆大多津而甘,然枝条柔脆不高挺;鲁桑,叶圆大丰厚,结葚少津润……湖桑、鲁桑宜饲大蚕。”[14]
就知识发现而言,“湖桑”的历史与太湖流域古人类的蚕桑生活同样古老。根据孢粉分析,环太湖流域距今6 000至5 300年的崧泽文化期植被组成就有桑树的发现。据考古发掘,在新石器时代,环太湖区存在许多野生桑林。原始先民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也会采摘桑椹以充饥,因而有可能发现桑树上野蚕所结的茧,从而逐渐注意将野蚕茧丝加以利用,继而有意识地加以保护,饲养野蚕,进而驯化成为家蚕。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1件牙雕即刻有“蚕纹”图样,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有“蚕纹”样饰。当然,这种纹饰不排除其为野蚕的可能。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正定县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2件陶蚕蛹,长2厘米,腹径0.8厘米,灰黄色。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鉴定,此陶蚕蛹系为对原“实物”仿制的家蚕蛹。[15]40凡此,不难看出人类植桑养蚕的历史悠久而邈远。
从考古的实际物证看,较为可靠的实物资料,是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经人工割裂过的半个茧壳,茧长15.2毫米,幅宽7.1毫米,李济先生并称之为“一个有趣的发现”[16]178。当然,最重要的发现当系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湖州潞村钱山漾遗址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发掘探方13个,总面积为341 。正是在这一次发掘中,发现了一批盛在竹筐内的丝织品,包括绢片,丝带和丝线等。据《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第二次发掘时,在探坑22出土不少丝麻织品。麻织品有麻布残片、细麻绳。丝织品有绢片、丝带、丝线等。大部分都保存在一个竹筐里[17]。经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所和浙江丝绸工学院多次验证鉴定,原料是家蚕丝,绢片是“由长茧丝不加捻并合成丝线做经纬线,交织而成的平纹织物”,时限距今4710±100年,“证实钱山漾出土的丝织物是由桑蚕丝原料织成的”[18]。这是长江流域目前出土最早、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实物形态的丝织品。
此外,值得书录的是,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2017年和2019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发掘出土了距今5 300至5 500年庙底沟文化时期的碳化丝织物[19]。由此可见,至迟在上下5 000年左右,在“中国之中国”(5)按,梁启超曾将中国史划分为三段,其中第一段为“上世史”,时限“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提出此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参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1页。区系内,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从而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丝织的国家。与之相应,湖州钱山漾遗址绸片、丝带的发现也带来了一个新的知识史发现,即湖桑的历史是悠久而古老的。这也是湖桑的原生形态——野桑或曰土桑时期。随着文明史的展开,太湖流域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处于吴、越、楚此消彼长的控御与影响之下,湖桑之原生形态——土桑,彼时亦名之以“越桑”“吴桑”“楚桑”或“荆桑”之谓(6)按,南浔所在的太湖之州,先秦时期因着吴越争霸,曾有属吴和属越的时光,随着越灭吴,以及楚灭越,地属楚,故湖地土桑(一称“野桑”),亦谓越桑、吴桑、楚桑或荆桑。明人徐渭《野蚕》诗有:“越桑虽云盛,不及吴中繁。”宋人沈与求《蚕》诗亦有:“吴桑成绿茵,吴蚕盈翠箔。”宋人沈括《长兴集》则有:“楚桑旖旖”诗句。参见《中国基本古籍库》之《徐文长集》卷四,明刻本;《沈忠敏公龟溪集》卷二,四部丛刊续编景明本;《长兴集》卷十三,四部丛刊三编景明翻宋刻本。。
据史记载,唐宋时期中国经济地理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经济重心南移。彼时江南经济区基本形成,中国蚕桑业的中心,至宋代业已转移到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据《宋会要辑稿》对各路租税和上贡的丝织品统计,长江下游各路约占当时全国的半数,其中两浙路就占全国总数四分之一左右。在历史的转形移步间,蚕种在演化中改良。同样,原生形态的土生湖桑——野桑,或曰土桑、楚桑、荆桑,在宋代以降,物产的互鉴融汇和交流演化中,也经历了一个桑树种系由“未接”(不接)到“接”,即嫁接技术与改良培育提质升级的过程。此即宋至元明清的湖桑演化之路,也是湖桑由原生形态演化至次生形态的重要时期。需予以说明的是,进入次生形态期,原生形态的湖桑并未彻底退场。据载,虽然彼时土桑或曰楚桑“叶薄而小且易瘪”[20]30,但由于其在春季发芽比嫁接桑早5~6天,故蚕农仍多用作稚蚕饲喂。同时,原生形态的湖桑还有一个重要用途,据清汪曰桢《湖蚕述》记载,“(湖)桑之种不一”,其中有“蜜眼青”者,“此种桑葚最美”。论其因,盖在于传统野桑(按,湖桑之原生形态者)于次生形态湖桑桑葚果实之丰厚颇有作用。具体做法是:“采取野桑之葚紫黑者,搓碎于箩,入水中捏淘,不必淘净,脂皮浮者去之,用其沉者,以稻秆灰拌匀,晒一日……将灰拌葚,匀匀撒下。”[20]300-301
在桑树种植环境与桑树种系选择、融合的过程中,太湖流域的人民逐渐积累形成了丰富的经验与认知。据《湖蚕述》记载:“桑地,宜高平,不宜低湿。高平处,亦宜培土深厚。”并特别指出:“蚕桑随地可兴,而湖州独甲天下。不独尽艺养之宜,盖亦治地得其道焉。”[20]300《湖蚕述》并对原生形态湖桑(按,野桑)、次生形态湖桑(按,家桑)两者之特征与区别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宋(代)以前“接过,谓之家桑,未接者,谓之野桑。家桑,子少而大;野桑,子多而小。子名葚,俗名桑果,可啖。……家桑,叶圆厚而多津,古所谓鲁桑也;野桑,叶薄而尖,古所谓荆桑也。野桑若任其长,肥者成望海桑,瘠者成鸡脚桑,蚕家贱之,故莫不用接。接成家桑,经数年,高与檐齐,粗如杯、如碗,是名嫩壮桑。过十余年则老,渐稀渐薄,以此添种而删易之。”[20]300-301

综上,太湖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桑树的培育、生长,此即湖桑之原生形态期(按,野桑、土桑、越桑、吴桑、荆桑、楚桑之谓)。本论题之厘辨思考置于中华文明进程的时空背景下,从中华文明人文开化时代蚕桑业的情况来看,其在中国的大两河流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基本上是同时起源的。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从湖桑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的视角观察湖桑演进的路线与轨迹,当不会是无的放矢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