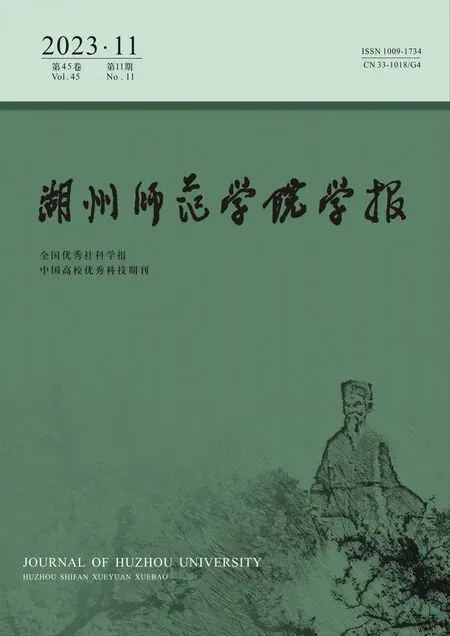从政统与道统的关系看儒学道统意识及其嬗变*
樊智宁
(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道统是儒学颇为重视的概念,儒家认为自上古的“二帝”“三王”开始,历经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人,皆传递着延绵不绝的大道。一般看来,韩愈以对抗佛教的法统学说,首次明确提出儒家的道统传承。而道统一词的真正使用,以及道统学说的确立则是到朱熹那里方才完成。然而,这绝非意味着韩愈与朱熹之前的儒学不存在道统意识。譬如朱汉民即认为自孔子删述六经开始,儒家即“从经典文本,同时也在授受脉络、思想内涵等多个方面,为后来的道统论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础”[1]79。诚然,朱熹之前儒家关于道统的讨论虽然称不上为学说,但亦可称为意识。德国学者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对朱熹之前道统的用法进行过考证,认为道统意识最早兴起于孟子,并且在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已经有相关的讨[2]82-88。遗憾的是,当前学界对先秦儒学道统意识的研究仅涉及孟子,并且忽视了汉代儒学的贡献。鉴于此,重新梳理历代儒学关于道统意识的论述,进而明确道统意识之嬗变对其最终确立的影响,乃是必要的研究工作(1)本文涉及之“政统”乃是指政治统绪的传承及其合法性来源。现代中国政治哲学的语境之中,牟宗三最早论及“政统”的概念。牟宗三认为“古人言‘正统’,是就得天下正不正说,无言‘政统’者。……‘政统’一词,意指‘政治形态’或政体发展之统绪言,不单指‘民主政体’本身言,是通过客观实践中政体之发展而言今日民主建国乃理之所当然而不容己,且是历史的所以然而不可易。在客观实践之发展中言今日民主建国,而客观实践是前所由自,后有所继,而垂统不断的,故曰政统。”参见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64页。将牟宗三关于民主政体的内容剥离,则是普遍的“政统”概念,亦与本文“政统”的概念接近。。
一、道统的原生及其与政统的融贯:先秦儒学的道统意识
道统意识在先秦儒学那里已然开始萌发,以孔子、孟子以及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皆探讨过传道谱系与内容的问题。关于先秦儒学的道统意识,大多数学者将重点置于孟子,对孔子的道统意识则缺乏足够的关注。至于荀子对道统谱系与内容的论述,学界的研究更是乏善可陈。事实上,如果对先秦儒学的文本及其思想理路详加考察,那么可以发现孔子、孟子以及荀子关于传道谱系与内容的论述不仅充分体现了儒学的道统意识,同时亦系出同源,并且呈现出逐渐成熟与完善的趋势。故而孔子、孟子以及荀子所展现的道统意识,其文本源头乃是《尚书》的经文,所遵循的传道谱系乃是“二帝”“三王”之体系。
道统意识之滥觞最早可以溯源自孔子。审视整部《论语》,孔子虽未明确提及道统,但亦有多处展现出传承道统的意识。譬如孔子周游列国,途经匡地而被匡人所围困。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此处即言西周圣王之“文”皆载于其身。何谓“文”?刘宝楠曰:“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游,以所得典籍自随,故此指而言之。文在兹,即道在兹。”[3]328由此可见,“文”虽然指代典籍,然则已然有圣王之道的含义,孔子俨然以传道者的形象自居。而在《论语》之中,孔子亦完整地以“二帝”“三王”为核心,陈述道统传承的谱系。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论语·尧曰》)
以上是孔子陈述传递的道统谱系及其内容。同时,在道统传递的过程之中亦包含政权合法性的转移。张文江认为,此章乃是“由概括《尚书》而来,整部《论语》以此奠基,可看成全书的后序”[4]15。故而此章意义重大。
此段文字的内容乃是阐述“二帝”“三王”之道,可分为五段来理解。自“尧曰”至“在予一人”为前四段,孔子通过这四段文字分别勾勒出四部分道统的传承谱系。首先,首段文字描绘了尧舜之间相授受的道统,其内容乃是“允执其中”。其次,第二段又描写舜对禹的道统传授,其内容亦复如是。然而,自第三段开始道统的内容为之变化。自“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乃是成汤革命的宣言。何晏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5]302夏桀昏乱,违背天心民意,成汤受命于天而行吊民伐罪之举,此亦是道统的内容。自“周有大赉”至“在予一人”为第四段,此为周武王伐纣灭商的誓言。何晏曰:“周,周家。赉,赐也。言周家受天大赐,富于善人,有乱臣十人是也。……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5]303周武王以德为先,亦以德性教化万民为己任,奠定周王朝所传承之道与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前四段梳理“二帝”“三王”的传道谱系,而末端文字的内容则是孔子总结“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政策与方法。质言之,即修礼乐、行公义、重民生。而无论是礼乐、公义还是民生等,显然更倾向于制度这类外王层面的内容(2)尽管孔子亦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说法,表明制度层面的事物绝非仅停留在制度本身,而是具有更加深层次的内涵。然而,孔子的论述仍是从制度这类“外王”层面入手展开讨论,并未直接从道德修养等“内圣”层面进行探究。故而孔子此处的道统意识是倾向于外王的。。通过对以上文字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所描绘之道统谱系是较为完整的,而从内容而言,道统则与政权的合法性息息相关。换言之,孔子此处论述的“二帝”“三王”之受命于天,以及相互授受的道,皆体现儒家的外王之法,而与内圣的关联则不甚紧密。故而孔子此时关于道统的意识,带有较强的政统更迭交替的意蕴(3)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孔子在《论语·尧曰》中关于道统的论述并非意味着其忽视内圣。如果结合《论语》的整体结构,可以发现其自《学而》开始已然有大量关于内圣之道的阐释,故而末章不必再次赘述。质言之,整部《论语》乃是自“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以修内圣为始,而此章以通外王为终”,形成前后呼应、贯通内圣与外王的完整结构。参见张文江:《〈论语〉析义之孔子评论古人》,《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6页。。
道统意识在孟子那里则得到进一步昭示,孟子关于道统的论述亦是后世儒者以及当代学者关注的重点。与孔子相似,孟子亦曾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孟子在离开齐国之时面有不豫之色,弟子以君子不怨天尤人问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在此处提出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论断,亦为后世道统的接续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并且,孟子亦将这种观点运用于其道统意识之展现。孟子曰: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
以上文字是孟子所详述的道统传承谱系,其同样是以“二帝”“三王”为线索,将道统的谱系依次展开。孟子与孔子不同,其并未详细说明“二帝”“三王”所传承道统的内容,但是在道统传承谱系的描绘方面,孟子则比孔子更为详尽。
首先需要阐明的是,孟子之道统意识为何要以“五百有岁”为区间。赵岐注曰:“言五百岁而圣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迟速,不能正五百岁,故言有余岁也。”[6]480赵岐以“五百岁”为天道之常,将道统传承的规律程式化,这显然未能触及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论断的本义。事实上,孟子此段以“五百有余岁”来划分道统传承的区间,根本目的乃是“孟子欲归道于己,故历言其世代也”[6]481。这种解释与孟子“舍我其谁”的自信态度亦可前后呼应。因此,孟子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论断,其目的与孔子的“文不在兹乎”具有相同的思想内核,两者皆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将自身纳入道统的谱系之中。故而其具备道统意识,可谓如日昭彰。其次需要明确的是,孟子在道统谱系的构建方面是如何推进孔子学说的。孟子在道统的谱系之中加入“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相区别的内容。赵岐注曰:“见而知之,谓辅佐也。通于大贤次圣者,亦得与在期间。……闻而知之者,圣人相去卓远,数百岁之间变故众多,踰闻前圣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6]480孟子此处将圣人与贤人进行了划分。“见而知之”乃是与圣人相同时代的贤人,其位次虽不及圣人,然亦可辅佐圣人施行大道、传承道统。“闻而知之”则是指道统的圣人,尽管与先代圣人相隔的时间甚为久远,然亦可直接闻知先代圣人的大道,并传承与施行之。由此可见,孟子一方面在道统的传承谱系之中增添贤人,用以辅佐圣人传道;另一方面又表明,仅有圣人能直接承续道统,然而其又暗示无贤人辅佐,圣人的大道亦难以施行,这亦是其与孔子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总而言之,孟子所展现出的道统意识,虽为明确具体的内容,但从其所言的诸位圣王与贤臣的例子,以及孔子与自身面临的现实困境来看,其更多亦是倾向于政治层面的内容。故而对孟子之道统意识而言,道统与政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荀子作为先秦儒学的后劲之辈,亦有道统意识。然而,荀子的道统意识通常被后世儒者所排斥,当前学界亦鲜关注荀子对道统的论说。如果详细考察荀子论说道统的文字,能够发现荀子之道统意识表现比孔子与孟子更为强烈。并且,与孔子、孟子相比,一向侧重外王之学的荀子则在展现道统意识之时体现出浓厚的内圣思想,呈现出比孔子与孟子更为明显的打通内圣与外王之特色。荀子曰:
尧让贤,以为民,泛利兼爱德施均。辨治上下,贵贱有等明君臣。尧授能,舜遇时,尚贤推德天下治。虽有圣贤,适不遇世,孰知之?尧不德,舜不辞,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万物备。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贤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亲,贤者予。禹劳心力,尧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举舜甽亩,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谷殖;夔为乐正鸟兽服;契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天乙汤,论举当,身让卞随举牟光。(《荀子·成相》)
以上文字是荀子论说的道统传承谱系。可以看出,“二帝”“三王”体系亦是荀子展开论说的基础。并且,从此段内容来看,荀子乃是通过韵文的形式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尚书》之《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经文之内容(4)《荀子》的文本与《尚书》经文有不少相互借鉴之处,对此需要进行必要的分梳。伪《古文尚书》大量参考《荀子》之中的“《书》曰”内容。譬如,“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王。”(《尧问》)被《仲虺之诰》简化而袭用;“独夫纣。”(《议兵》)被《泰誓》改写而袭用;“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君道》)被《胤征》袭用;“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臣道》)被《伊训》袭用;“维予从欲而治。”(《大略》)被《大禹谟》袭用。此外,《大禹谟》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亦从《荀子·解蔽》所引之《道经》而来。因此,《荀子》可谓伪《古文尚书》部分篇章经文之来源。然而,此处的引文则不同。除去描写成汤的文字之外,《成相》的主要内容皆为《尧典》《皋陶谟》《禹贡》之改写。此三篇属于《今文尚书》,乃是源自孔子整理的百篇《尚书》。故而此处之引文可以被视为源自《尚书》经文。。
荀子关于道统的论说对孔子与孟子的理论皆有所扬弃。荀子之道统意识基本继承孔子关于道统乃政权合法性来源的论述。纵观《成相》此段的内容,其所言之事皆为尧、舜、禹、成汤如何意图治理天下,又如何意图将天子之位禅让于贤人。换言之,《成相》此段的内容乃是阐述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统治者的道德,仅有道德卓越之人方能获得前代圣王的认可而获得天下。这种更加凸显内圣层面的论述,对孔子侧重外王之道统意识进行了补充。譬如“尚贤推德天下治”“尚德推贤不失序”“民知孝弟尊有德”皆是此意。并且,荀子之道统意识亦吸收了孟子的观点,认为圣王传承与施行道统,亦需要贤人辅助。譬如舜举于畎亩之中而任天子之位,其需要后稷、夔、契等贤人辅佐方能施行大道,使得天下大治;禹平水土,以功业受禅得天子之位,其亦离不开益、皋陶、横革、直成,这些贤人皆是禹得道、传道以及施道的重要助力。此外,荀子对道统的内容亦有所论,其曰:“尧问于舜曰:‘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荀子·尧问》)荀子认为“执一”与“行微”是道统的内容。王先谦曰:“执一,专意也。行微,行细微之事也。言精专不怠而天下自归,不必致也。”[7]547依照王先谦的解读,荀子的“执一”与“行微”在含义上与《尚书·大禹谟》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意思相近,亦即孔子在《论语·尧曰》之中所言的“允执其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先秦儒学之道统意识进行总结。首先,“二帝”“三王”乃是先秦儒学道统意识之核心,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其关于道统的论述皆以“二帝”“三王”为线索,而与“二帝”“三王”相同时代的贤人,则被视为道统传承的辅助。其次,先秦儒学以“允执其中”为道统的内容,这在孔子与荀子那里体现得较为明显。再次,先秦儒学的哲学家们在展开自身道统的意识之时,亦将自身纳入道统的传承谱系之中,孔子与孟子则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最后,先秦儒学的道统意识呈现出偏重外王之学的特征。在先秦儒学那里,道统的传承与政权的传承是相互交融的,道统传续之正意味着其政权亦具有相应的合法性。换言之,道统乃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此外,先秦儒学之道统意识固然注重外王之法,但这种外王之法绝非抛弃内圣而独立存在着,其需要通过与内圣贯通方能实现。譬如孔子在论述道统之时,即有诸如“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与“百姓之过,在予一人”这样体现圣王反求诸己的仁恕之道;荀子之道统意识,亦反复提及“尚德”与“推贤”。故而先秦儒学之道统意识绝非独尊外王之法,而是贯通内圣与外王、结合道统与政统的综合性理论。
二、道统的转型及其与政统的割裂:汉唐儒学的道统意识
汉唐儒学之道统意识较为复杂,由于治学方式的差异,汉唐儒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汉至唐初,这段时间的儒学以经学为主,其道统意识亦蕴含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之中。然而,自韩愈与朱熹以来的道统学说则往往将这段时间的儒学排斥在道统体系之外,即所谓的道统断绝时期。后世学者亦研习韩愈与朱熹的观点,认为这段时期的儒学思想偏离正道,此举恐有未安之处。第二阶段为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儒者发动儒学之复兴运动为其标志。儒学开始跳出经学的范式,并且重新探求道德性命的议题,用以抗衡佛老的哲学思想。自此开始,道统意识亦呈现转型之势。因此,探讨汉唐儒学与道统意识问题,必须从这两个阶段入手,分别阐明各自阶段道统的意识及其转变,方能展现道统意识在汉唐儒学发展的全貌。
第一阶段的代表是公羊学。公羊学宣扬“大一统”学说,其基本内涵乃是彰显王者受命改制的作用。“因为唯有改制,才能体现王者受命的合法性及其更化之责。”[8]52故而董仲舒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公羊学所言及的王者受命改制,与《论语·尧曰》描述的“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以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说法有共通之处。换言之,公羊学与孔子在《论语·尧曰》之中的观点相似,皆陈述了王者相授受之道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关系。那么王者受命改制与王者相授受之道,又有何关系?董仲舒曰: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度,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尧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欤?(《春秋繁露·楚庄王》)
以上文字充分体现了公羊学之道统意识。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以董仲舒思想为代表的汉代公羊学已经将道统与政统区分开来,其不仅阐明了道统与政统的内容,亦厘清了道统与政统两者的关系。
董仲舒开宗明义,阐述了王者受命改制而不易道的观点。在董仲舒看来,新任王者受命改制的原因在于更化,即与先代的政治相区别,亦表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是受命于天而非受命于人。对此,何休亦曰:“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9]10由此可见,这种观点已然成为公羊学的共识。而在公羊学家看来,“制”与“道”的区分亦是相当明确的。所谓“制”者,乃是指王者的居所与称号,奉何月为正朔,使用何种服色与旗帜,以及使用何种牺牲祭祀等,这些与礼仪典章相关的形式性因素主要起到象征王者权威的作用。而所谓“道”者,则是指在人伦日用之中应当操持与遵循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等,这些皆是涉及人之根本的要素。并且,在公羊学家看来,“道”不仅万世不易,其亦是由历代圣王薪火相传而来。董仲舒在应对汉武帝的第三道《举贤良对策》之中,即对“道”的传承体系进行阐释。董仲舒曰:“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此处亦强调“道”乃是万世不易、无所缺弊的,这是由于其本原乃是完满与至善之天。尧、舜、禹之受命于天而为天子,其所传授与守护的即为此“道”。质言之,公羊学认为道统的内容恒常不变,所变者乃是政统。政权合法性的外在表现是改制与更化,而其实质来源则是天“道”。此外,公羊学所言之“道”乃由尧、舜、禹“三圣”相授受,其亦在“二帝”“三王”的体系之中。综合看来,公羊学之道统意识可谓明矣。
公羊学在汉代之后逐渐式微,公羊学关于道统的论说亦随其式微而被湮没。然而,唐代的经学则将道统意识传承下来。其中,《尚书》学对道统意识之发挥最能够体现这一时期的特色。《尚书》与道统的联系极为密切。就道统的谱系而言,《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科,其与“二帝”“三王”的体系高度吻合。并且自先秦开始,利用《尚书》经文阐述道统的论说亦是儒学的常态,譬如《论语·尧曰》以及《荀子·成相》的文字即是典型的案例。由于这种先天的契合性,唐代的经学家在诠释《尚书》的过程之中亦呈现出道统意识。孔颖达乃是其中的代表,其曰:
古之王者事揔万机,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勋、华揖让而典、谟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先君宣父,生于周末,有至德而无至位,修圣道以显圣人,芟烦乱而翦浮辞,举宏纲而撮机要,上断唐、虞,下终秦、鲁,时经五代,书揔百篇。[10]4
以上文字乃是孔颖达《尚书正义》的序言,基本陈述了《尚书》的由来、作用以及孔子整理与编撰《尚书》的目的。其中能够窥见孔颖达将孔子视为圣王之道的传承者,并且亦能够发现孔颖达对道统谱系的勾勒。
一方面,孔颖达陈述了《尚书》的由来及其作用,在其陈述之中蕴含着孔颖达对道统内容之理解。《尚书》的经文自诞生之初即为教导君王在政治生活之中当谨言慎行、合乎法度。伪孔安国《尚书序》亦有《尚书》乃是“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10]12-13的论断。可以看出,《尚书》所载之道既包括君王自身道德修养的内容,同时亦以归正君王的政治活动为目的。故而从孔颖达对《尚书》的由来及其作用的描述可以窥见,其对《尚书》所载之道的认识已然偏向内圣。另一方面,从“勋、华揖让而典谟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的表述来看,其亦基本围绕“二帝”“三王”,勾勒出道统的传承谱系。“勋”乃是指尧,“华”乃是指舜,《尚书》之典、谟、誓、诰之文体,分别代表从尧舜至汤武的载道方式。而到了孔子那里,《尚书》所载之道为其所总结深化,最终得以完善。作为圣人的孔子,此时亦成为道统的传承者而被纳入道统的谱系之中。诚然,孔颖达之道统意识与先秦儒学以及公羊学相比较为微弱,其言说内容亦略显粗糙。然而,其能够自觉地体现道统意识,这在佛老甚嚣尘上、儒学逐渐式微的时代则显得弥足珍贵。
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则是韩愈。中唐时期,儒家思想地位进一步受到佛老之学的挑战,由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主要目的就是抗衡佛老而复兴儒学。对此,陈畅认为韩愈关于道统的论述乃是“针对佛老思想压力而提出的竞争理论。韩愈发展出一种以‘破’为主的对抗性思想”[11]6。因此,韩愈力图以儒家的仁义为本位思想,驳斥佛老之学的道德理念。韩愈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12]253所谓道与德为虚位乃是指道德的概念仅是框架,其中的内容方为思想的关键。而在韩愈看来,儒家的道德即是仁义。韩愈亦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延伸道统学说。其曰: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处而不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12]261-262
以上文字首先将道统的内容概括为先王之教,亦即韩愈所言的仁与义。换言之,韩愈以仁义作为儒家道德概念的本质,使得儒家得以与佛老之道德区分开来,而以仁义为本质的道德,乃是儒家道统的内容。
在确定道统的内容之后,韩愈又阐述了道统的内容具象化后的事物,即儒家经典、礼乐制度、百姓身份、伦理关系,以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诚然,韩愈这段话所提及的道统具象化后的事物,亦是针对佛教与道教的人伦日用而言。即通过对道统具象化的描述,阐明儒家倡导的基本生活方式,从而树立儒家文化的主体性。简而言之,韩愈将道统视为儒家思想的本质,以及儒家文化能够具有主体性与本位性的来源。故而在韩愈这里,道统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道统并非仅仅体现于百姓的日用伦常之间,政治生活领域亦是如此。佛老提倡君王之治心,然而却造成“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12]259的局面,韩愈对其持批判态度,认为这显然有悖于施行君王良善政治的初衷。因此,韩愈认为应当将道统的内容贯彻于政治生活的领域之中。而所谓的“以之为己”“以之为人”“以之为心”以及“以之为天下国家”,实际上即是儒家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亦表明韩愈之道统意识乃是以治心为本,以祈求内圣为起点,进而将先王之道推及家、国与天下等外王层面。此外,韩愈之道统意识在描绘道统的传承谱系之时,同样以“二帝”“三王”为核心,并且已然延伸至孔子与孟子。至于荀子与汉代儒家的思想则被忽略,此实为韩愈道统意识之一大缺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汉唐儒学之道统意识进行总结。首先,儒学的道统意识在汉唐儒者这里呈现出割裂与转型之势。所谓的割裂乃是指儒学的道统意识与政统意识开始分离,这在汉代公羊学那里已然初现端倪。而所谓的转型则是儒学道统意识开始从侧重政权合法性等外王因素,转变为强调治心的内圣之学,其中的标志即为韩愈对道统的论述。并且,道统意识之割裂与转型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关系。换言之,将道统与政统割裂开来,原本包含在道统之中的外王之学被规划至政统之中,而道统之中的内圣之学则成为道统的内容,故而道统亦由此转型。其次,道统意识之所以在汉唐时期发生割裂与转型,亦有外部因素的影响。譬如汉代儒学被统治者所利用,用以论证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这必然使得受命与改制等要素得以突显,修身正心等要素则被忽略。而到了唐代,由于佛老之学的冲击,使得原本注重政治哲学的汉唐儒学在人自身的安顿问题上无法与佛老相抗衡。因此,以韩愈为代表的儒者便选择跳出当时儒学范式的掣肘,从道德性命之学的层面加强儒家道统的意识,并力图以此消解佛老之学流俗于世的弊病。此外,韩愈之道统意识开启亦纯粹的心性为道统的内容之先河,此亦为程朱理学之道统意识提供了思路。总而言之,汉唐儒学之道统意识,虽然结构复杂,研究范式的前后变化亦较大,但却成为承接先秦、肇启宋学的枢纽。
三、道统的确立及其与政统的复归:朱熹的道统学说与蔡沈对道统学说的拓展
宋代儒学在其早期的治学方法上,皆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儒者为滥觞。诚如钱穆所言,其评价宋学之源头曰:“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13]1。研究儒学道统意识及其嬗变的过程更是如此。宋代的学者至朱熹之前,其道统意识基本沿袭韩愈的学说。赵瑞军认为,“宋初学者在阐述道统论时,融贯了唐宋古文革新运动中‘文’与‘道’的关联性阐述,有以孟子心性说对抗佛教心性说之意,推动了宋初儒学的转型发展”[14]138。而自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之后,以程颐为代表的理学家亦围绕韩愈的道统传承谱系,陈述自己的道统意识。譬如程颐曰:“‘轲之死,不得其传。’似此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是。”[15]232此即表明程颐赞同韩愈关于道统谱系的论述。然而,程颐亦曰:“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宋史·道学传》)程颐将程颢列为孟子之后的道统传承者,其不仅拓展韩愈之道统的谱系,亦将从自家精神体系而出的理学列为儒学之正统学说。
南宋时期,以心性论为基础的儒学道统意识不断受到理学人性论与工夫论的影响,最终在朱熹那里得到大成(5)自宋初至朱熹之前,诸如柳开、穆修、赵湘等古文复兴运动之学者皆参考韩愈的学说论述道统的问题。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儒者则对韩愈之道统意识进行过较为辩证的评价。介于篇幅所限,并且此段亦非论述的重点,故而本文不再赘述。相关内容可参见赵瑞军:《宋初的道统论研究——兼论宋初之尊孟》,《现代哲学》2018年第3期,第136-138页;路鹏飞:《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51-52页。。事实上,朱熹是在儒家圣王传道意义上使用道统之词的第一人。儒学道统意识亦是以此为标志得以确立,正式成为具有理学特色之儒家道统的学说。朱熹关于儒家道统的论述首发于其《中庸章句序》之中。朱熹曰: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16]14-15
以上文字乃是朱熹对理学道统的盖棺论定,其主要的贡献在于确定道统的谱系以及道统的内容。一方面,朱熹所构建的理学道统传承谱系,基本架构亦是“二帝”“三王”,这是其对前人的继承之处。另一方面,朱熹亦将道统的内容确定为中庸之道,此则为理学道统学说的创见。
关于理学道统的传承谱系,朱熹的论述与先秦儒学、汉唐儒学皆无差异。从朱熹对道统谱系的描述即可看出,其将道统的传承者以君王与辅臣的身份进行区分。尧、舜、禹、汤、文、武乃是直接传承道统的圣王,至于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则是辅助道统传承的贤臣。朱熹的这种划分模式显然继承自孟子,其与荀子的观点亦有诸多相似之处。并且,朱熹亦高度评价孔子作为道统传承者的作用,认为孔子有德无位却能继往开来,此功德当在尧舜这类圣王之上。相比之下,孔子在韩愈那里亦仅为普通的传道者,身份与地位虽然崇高,但亦无法企及“二帝”“三王”的程度。
关于理学道统的具体内容,朱熹在论述时未取先儒的受命改制、仁义道德等观点,而是直接溯源自《论语·尧曰》的“允执其中”,亦即中庸之道。就来源而言,朱熹认为中庸之道乃是“继天立极”而来,这与董仲舒的“道之大原于天”相似,然其内容又有所区别。董仲舒的“道”乃是万世不易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行为准则。朱熹的中庸之道则指“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16]17,其亦有规范与准则之义。然而,朱熹的中庸之道并非一成不变,其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质言之,董仲舒所谓的“道”自尧舜得之于天即恒常不灭,而朱熹的中庸之道则在传承过程之中不断地增添新的内容,即以一种更为详尽的呈现方式体现中庸之道。譬如尧授之于舜本为“允执厥中”;舜授之于禹增益为“十六字心传”。这使得道统的内容不断丰富,更加具有活力。
此外,朱熹的道统学说亦包含了政统又复归至道统之中的含义,这亦是容易被后世学者所忽略的要义。朱熹反复强调,圣王之间的道统传承非惟治心之法,而是“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在朱熹看来,儒家的道统学说从来都是沟通内圣与外王的综合性理论。在孔子与孟子那里,道统的传承即是与政治的合法性及其来源息息相关的。而自汉唐儒学开始,道统与政统渐渐开始割裂。到了韩愈那里,道统的内容已然完全成为道德性命之学的代名词,这种观点一直持续至程朱理学的早期阶段。譬如程颐即曰:“道外无物,物外无道。在父子则亲,在君臣则敬。有适有莫,于道已为有闲,又况乎毁发而弃人伦乎?”[15]1169由此可见,即便是对道统与道的理解,亦未能完全脱离韩愈的影响,即通过心性论来阐发自身之道统意识。因此,朱熹力图将代表儒家外王学说的政统复归至道统之中,以展现儒家道统的本然面貌。
遗憾的是,恢复道统本然面貌的工作朱熹并未完成。从《中庸章句序》的论述可以看到,作为道统内容的中庸之道见诸经文乃是“允执厥中”,后又增益为“十六字心传”。而“十六字心传”则出自《尚书·大禹谟》,因此,若要理解儒家道统的本然面貌,《尚书》经文之诠释乃是关键。朱熹本人并无《尚书》学专著,而是授意其弟子蔡沈撰写《书集传》。考察蔡沈《书集传》的道统学说能够发现,政统复归于道统的问题在蔡沈《书集传》这里得到了解决。蔡沈曰:
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治乱之分,顾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心;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书何以哉?[17]13
以上文字乃是蔡沈《书集传》的自序。从这段自序来看,蔡沈的道统学说基本继承了朱熹的思路。一方面,关于道统的谱系,蔡沈亦以“二帝”“三王”为脉络;另一方面,关于道统的传承内容,蔡沈所谓的“精一执中”“建中建极”以及“德”“仁”“敬”“诚”等,皆为中庸之道的变体。然而,蔡沈对朱熹道统学说的拓展更在于阐明君王求心的道理。
蔡沈认为《尚书》乃是君王求心之作,道统的根本亦在于“此心之妙”。故而所谓的“精一执中”“建中建极”,甚至是朱熹所言的中庸之道,其皆本于君王之心。需要注意的是,蔡沈所言的“此心之妙”并非陆九渊的那种心学,而是指人的本身即存有,且本之于天理的道心。蔡沈认为儒家圣王历代相传的道统,其本质乃是君王自身道心的复现。至于君王在政治实践之中施行的礼乐教化、设置的典章文物,皆由道心所发著而成。然而,蔡沈又认为君王复见道心并非目的,而是通往良善政治的手段。换言之,在蔡沈看来,历代圣王相传的道统,乃是告诫继承者应当以求其道心为手段,进而在政治实践的层面达成善政[18]28。而政权的合法性亦在于君王能否秉持道心之正,祛除人心之偏。并且,《尚书》之经文所承载的正是“此心之妙”,亦即儒家的道统。如若后世君王意图实现良善的政治,则必须发掘出《尚书》之中的道统意蕴,进而求得“此心之妙”。总而言之,蔡沈通过以《尚书》为中介的方式将君王之治、君王之道以及君王之心贯通合一。作为道统内容的“此心之妙”属于内圣之要,作为政统内容的良善政治则属于外王之机,两者互为其根,使得政统与道统重新融合成有机的整体,这即是道统的本然面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程朱理学之道统意识进行总结。首先,儒家的道统自宋代开始正式完成从意识到学说的蜕变,其标志则是朱熹《中庸章句序》对道统传承谱系的论述以及对道统内容的界定。其次,在程朱理学早期,道统的意识依旧局限于心性论,这种偏颇的理解使得道统的本然面貌隐而不发,道统亦容易被后世视为单纯的心法传承。然而,亦是从朱熹开始,道统与政统的关联被重新重视起来。最终在蔡沈《书集传》的道统学说之中,政统又复归于道统之中。这种道统学说与孔子之道统意识相符合,亦是儒家道统的本来面貌。最后,朱熹与蔡沈的道统学说之核心在于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见诸《尚书》之经文则又存在多种变体,在历代圣王的传承之中亦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19]48-56。这些变体与历代圣王的形象以及社会历史相结合,共同彰显出儒家哲学在时代变迁之中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四、结论
通过对儒学道统意识及其嬗变过程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儒家的道统与政统是相伴相生、互为支撑的关系。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讲求沟通内圣与外王,即在展现自身道统意识之时更侧重外王的层面,但本质上亦是在道统之内融合政统的要素。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道统意识在汉唐儒学那里发生割裂与转型,公羊学与韩愈分别使得道统的内容呈现外王与内圣的特点,其固然有现实的意义,但却背离了道统的本然面貌。直到宋代理学兴起,道统意识才正式蜕变成为学说,其标志则为朱熹《中庸章句序》之中对道统谱系的重建以及对道统内容的确定。以朱熹与蔡沈为代表的理学家,虽然亦以理学重视心性的方式构建道统体系,然而亦强调君王的寻求“此心之秒”乃是手段,而实现良好的政治、保障政权的合法性才是最终目的。自此以后,政统复归于道统之中,理学道统学说亦使得儒家道统重现其本然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