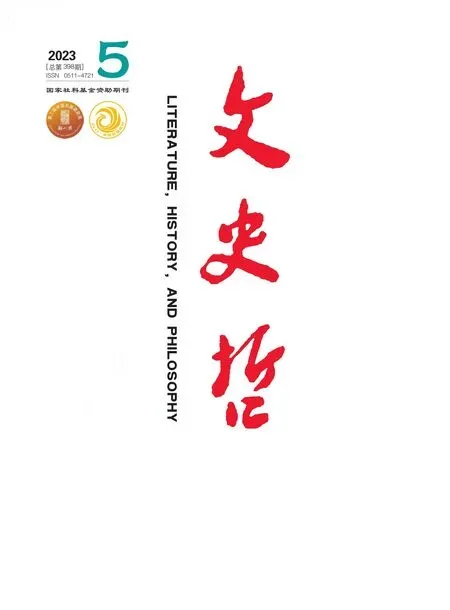“坑术士”新证
白效咏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发生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的“坑术士”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然而关于“坑术士”到底坑的是什么人,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认识。传统的观点认为“坑术士”就是坑儒生。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传统“坑儒”的观点有所质疑,特别是国际汉学界,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即认为“有充分的根据把它(笔者按:指坑儒)看作虚构(颇为耸人听闻的虚构)的资料,而不是历史”(1)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7-88页。,甚至断言司马迁用来撰写《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原始记载中并无坑儒之说,要么是司马迁取材于半杜撰的资料,要么为后人窜改添加。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李开元也认为“坑儒是伪造的历史”,并指出这一说法的源头为《说苑·反质》所载的坑方士的故事,司马迁未加辨析,据此写进《秦始皇本纪》。他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把术士想当然的理解成方士,认为“坑术士”“杀术士”就是坑方士、杀方士(2)李开元:《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第46-48页。。国内不少学者与这一观点遥相呼应,如马执斌(3)马执斌:《“焚书坑儒”辨》,《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24日第15版。、张子侠(4)张子侠:《“焚书坑儒”辨析》,《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41-48页。、王立群先生(5)王立群:《王立群:“焚书坑儒”说法有误》,《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5月11日,第6版。,他们都认为《史记》《汉书》最初记载坑儒这件事时均作“坑术士”,而术士乃是指欺骗秦始皇的方士。这一派学者的观点遭到王子今先生的驳斥,王子今一方面强调汉代典籍关于坑儒的记载是得到历代学者认可的,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所谓‘术士’‘方士’和‘儒生’,文化资质有某种相通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谓所坑乃“方技之流”,非“吾儒中人”,盖未省“术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根据当时语境,可以知道这里说的‘术士’就是‘儒生’。”(6)王子今:《“焚书坑儒”再议》,《光明日报》2013年8月14日11版。学术界持这一观点的也不乏其人,李景明引许慎《说文解字》“儒者,柔也,术士之称”一说,认为术士既可指儒生,也可指方士,被坑者儒生方士兼而有之(7)李景明:《中国儒学史·秦汉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页。。其他学者的观点不一一列举。
考察两派观点,其所据史料近乎一致,得出的结论却迥乎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于两派对“坑术士”之“术士”理解不同。认为坑儒事件基本可信的学者,均把术士理解为既可指方士,也可指儒生,或者说儒生、方士均可称术士;而认为坑儒事件不可信的学者,则坚持“坑术士”就是坑方士,也即把术士等同于方士,与儒生不同(8)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在叙述坑儒事件中,更是直接把引发坑儒事件的两个方士侯生和卢生直接称为“术士”,可见作者认为方士就是术士(参见该书第87页)。。因此,准确理解“坑术士”是判断整个坑儒事件是否可信的关键,不仅事关儒学史的书写,还关系到对秦帝国思想文化政策及秦始皇本人的评价,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研究。
一、两汉时期所谓“术士”就是儒生
关于“坑术士”或“杀术士”的记载,《史记》《汉书》共出现四次:一是《史记·淮南王列传》所载伍被劝谏淮南王刘安之语:“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9)《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086页。二是《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10)《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6页。三是《汉书·儒林传》:“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11)《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2页。四是《汉书·伍被传》:“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杀术士,燔《诗》《书》,灭圣迹,弃礼义。”(12)《汉书》卷四五《伍被传》,第2171页。这也是否认坑儒事件是历史事实的学者们用以论证坑儒不可信的重要论据。但仔细分析这四段话中的“术士”,不可能是指方士,而只能是儒生。伍被之语,“昔秦绝圣人之道”,此处圣人毫无疑问就是孔子,“圣人之道”就是儒术,所谓“绝圣人之道”,就是禁绝儒术,其后所言“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说的是禁绝儒术的具体措施和表现。如果这里的术士作方士解,“杀术士”就和“绝圣人之道”没有关系了,出现在这里,从逻辑上讲不通。同样的内容,在《汉书·伍被传》中被表述为“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杀术士,燔《诗》《书》,灭圣迹,弃礼义”,这里的“灭圣迹”就是“绝圣人之道”,而“杀术士,燔《诗》《书》”则是灭圣迹的具体施为。
至于《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中两段话中的“术士”,更不可能是指方士。首先,《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所记载的内容实际上是从先秦到汉代的儒学史,这里面不可能收入和儒学无关的方士的事情。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对汉武帝之前的记载,大都承袭自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而稍加损益。这里的“六艺”和“六学”,显然都是指六经。司马迁把“焚《诗》《书》,坑术士”视为六经残缺的原因,班固因而不改,也说明“术士”就是儒生。古代儒生传习六经,首先要背诵下来,“焚《诗》《书》”而不“坑儒”,六经仍有可能凭借儒生的记忆重建。秦始皇所坑的这460余位儒生,都是他招来欲以兴太平的,从常理来讲,应该属于儒生中的佼佼者,不然也难以入秦始皇法眼。这460余位儒学精英被坑杀,使得经典重建的可能性大大减小,导致汉兴后典籍重建时未能完整地恢复,这也是司马迁把“坑术士”作为六经残缺原因的依据。
公子扶苏是“坑术士”事件的亲历者,并在此事上劝谏过秦始皇:“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1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他的这段话对理解“术士”的身份特别重要。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将儒家的特征概括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14)《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28页。,在儒者尊奉的先圣中,无论尧、舜,还是周文王、周武王,都没有著述流传下来,儒者所传的尧舜文武之道都是靠孔子整理阐释的。故《论语·子罕》载孔子自我评价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1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8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和“宗师仲尼”在实践中都是指学习孔子传授的六艺。扶苏在提到被坑者时说“诸生皆诵法孔子”,“诵法孔子”也即“宗师仲尼”,是儒生最主要的身份表征,这也说明被坑杀者是儒生而非方士。
其实,在两汉时期所谓的术士就是指儒生,而非方士。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儒”时说“儒者,柔也,术士之称”(16)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66页。,便是最好的证明。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载,许慎博通五经,深得马融推许,誉之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并撰有《五经异义》,是东汉治学严谨的经学大师,其言必有所据,但现在学术界多以许慎之说孤证难立,不予认可。
事实上,明确地把儒生称作术士的,许慎《说文解字》并非孤例,《汉书》中还有一处比较隐蔽的证据,见于《宣帝纪》和《夏侯胜传》。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夏四月,全国有49处发生了地震,造成民众死亡6000余人。为应天变,汉宣帝下诏求谏,班固在《汉书·宣帝纪》中收录了这份诏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17)《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5页。
在西汉,人们都或多或少地信奉天人之际说,认为“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18)《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498页。。因灾异下诏求谏,这是西汉诸帝通常的做法,求谏的范围就包括群臣及儒生。这里的“经学之士”显然是指儒生,在汉代,经学就是儒家的六艺经传之学,其他学派的著述均不得目为经学。而天人之际本是经学题中应有之义,故董仲舒对策时,汉武帝策问的内容即有“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19)《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496页。、“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20)《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3页。,要求“明先圣之业”的董仲舒对这些问题做详细的说明。董仲舒对曰:“《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21)《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0页。“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22)《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15页。这说明,宣帝因地震之灾而访问儒生咨询消弭之道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件事《汉书·夏侯胜传》也有记载,说辞却有不同:
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吊问吏民,赐死者棺钱。下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托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术士,有以应变,补朕之阙,毋有所讳。”(23)《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第3158页。
比较这两个版本可知,《宣帝纪》中的诏书是班固据原文抄录而成,而《夏侯胜传》中关于诏书的内容,则是班固根据诏书原意做了删削的,但班固不可能篡改诏书的原意。在这里,“经学之士”被改写作“术士”,足以说明“经学之士”和“术士”是同一概念,都是儒生的另一种称呼。如果说许慎“儒者,柔也,术士之称”证明术士可以被称为儒生,那么班固将宣帝诏书中的“经学之士”改写成“术士”,则说明“术士”与“经学之士”所指的完全是一类人,只能是儒生。否则,如果“术士”还可以指称儒生之外的其他学派学者和方士,那么班固在《夏侯胜传》中就扩大了“经学之士”的外延,篡改了宣帝诏书原意。对于班固来说,这么做不仅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显然这种可能性不大。
值得注意的还有颜师古为《汉书·儒林传》“杀术士”所作的注:
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此则闵儒之地,其不谬矣。(24)《汉书》卷八八《儒林传》颜师古注,第3592页。
张守节在为《史记·儒林列传》“坑术士”作正义时,又引了颜师古的注。在注中,颜师古给出了坑儒的具体地点,又引卫宏关于坑儒的另一种说法。尽管卫宏的说法比较离奇,未足深信,但可以看出唐代学者们对“杀术士”或“坑术士”的理解就是坑儒。
二、“术士”作为“方士”的称呼始于三国时期
《剑桥中国秦汉史》为代表的一方把方士等同于术士,想当然地认为所谓术士乃是“方术士”的简称,在秦汉时期找不到任何文献依据。“术士”一词最早见《韩非子·人主》篇:“且法术之士,与当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25)韩非撰,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64页。这里的“术士”是对前文“法术之士”的简称,亦仅此一例,也有可能佚一“法”字(26)据松皋圆、太田方、陈奇猷等学者意见,《韩非子·人主》篇为后人增益,且文词颇多舛误,不出于韩非之手(韩非撰,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第1162-1163页)。。
典籍关于方士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封禅书》,第一个方士当是苌弘:“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貍首。貍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27)《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4页。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期,燕齐海上方士集团兴起,以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为代表。司马迁将他们的特点概括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28)《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8-1369页。,他们误将春夏之际燕齐海滨出现的海市蜃楼现象当作海上神山,因而造出蓬莱、瀛洲、方丈三神山及不死药说,这也是他们“为方仙道”的主要内容。自齐威王时始,燕齐海上方士集团即游说人主,发起入海寻三神山求不死药的活动,一直绵延至汉武帝时期,秦始皇与方士的故事即是这场持续近三百年的活动中的一部分。《封禅书》称“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29)《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0页。,秦始皇自称“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时期入海寻三神山求不死药活动的总结。
此后,到了汉武帝时期,方士的活动又达高潮,代表人物是李少君、史宽舒、谬忌、少翁、栾大、公孙卿等。《史记·封禅书》关于他们的记载如下:“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主方……其游以方遍诸侯……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30)《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5-1386页。“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31)《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6页。“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3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7-1388页。“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奄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33)《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9-1390页。
从以上司马迁在《封禅书》中对方士的记述可以看出,方士之所以被称作“方士”,和“方”有关,因为他们掌握或懂得一些“方”。苌弘以方事周灵王,擅长役使鬼神诅咒不尊奉周室的诸侯。兴起于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期的燕齐海上方士擅长“为方仙道”,致力于为人主入海寻三神山求不死药。汉武帝时期的方士李少君擅长“祠灶、谷道、却老方”,并将其方传授于史宽舒;方士少翁擅长鬼神方,能招徕鬼神;栾大与公孙卿均是燕齐海上方士集团的传人,其方以入海寻三神山求不死药为主。从“方”的内容来看,多是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却老、诅咒、祭祀神灵、祈祷鬼神、求不死药的方法。这些“方”的程式多是固定的,如谬忌所奏祠太一方,其内容为“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苌弘致诸侯之方,“设射貍首。貍首者,诸侯之不来者”,《史记集解》引徐广说:“貍,一名‘不来’。”(34)《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4页。以貍诅咒诸侯之不来者,与后世以土木偶诅咒的方式方法几乎一致。综上可知,方士指称通晓却老、诅咒、祭祀神灵、祈祷鬼神、求不死药之方的人,不可能与术士混称。
术士作为方士的称呼,据目前文献,当始于三国时期。牟子《理惑论》:“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35)周叔迦辑撰,周绍良新编:《牟子丛残新编》,北京:中国书店,2001年,第1页。这里的“道家术士”,指的就是“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的方士,也就是司马迁在《封禅书》中所谓“为方仙道”者,但此处“道家术士”似为一词,与“方术士”同,尚不能断定以“术士”称方士。明确以“术士”指称方士者为曹植《辩道论》:“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诸术士咸共归之。”(36)《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79-480页。这里的术士,是指修炼行气导引、房中术、辟谷之类的方士。此后,术士作为方士之称才比较广泛地使用开来。西晋张华《博物志》载:“魏武帝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之术士如左元放、华佗之徒无不毕至。”(37)张华撰,范宁校正:《博物志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1页。这里术士与方士已是同一概念。
另外,三国时期刘邵《人物志》中也有术士一词:“故烈士乐奋力之功,善士乐督政之训,能士乐治乱之事,术士乐计策之谋,辩士乐陵讯之辞,贪者乐货财之积,幸者乐权势之尤。”(38)刘邵撰,梁满仓注译:《人物志》,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3页。这里的“术士”,指的则是善于谋划的谋士。把人物分成烈士、善士、能士、术士、辩士、贪者、幸者七类,是刘邵的首创,每一类人物的含义,也是刘邵赋予的。他的这种分法并未被后世广泛接受,也无助于对“抗术士”的理解。
三、从秦始皇政治实践的内在逻辑看,所坑之“术士”为儒生无疑
学术界之所以将“坑术士”理解为坑方士,很大程度上缘于坑儒事件是由侯生、卢生两位方士所引发的,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记叙“坑术士”事件时,又是从秦始皇对方士的痛斥开始:“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3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遂以为秦始皇下一步必然坑杀方士,作为对方士骗钱逃走、求不死药不得和诽谤自己的惩罚。然而考诸史籍,卢生、侯生已经逃走,虽欲坑杀而不得,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尚有关于方士徐巿的记载:“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4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3页。秦始皇不仅没有惩处徐巿,相反,还根据徐巿的要求,亲自带领人马去捕杀大鲛鱼,“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4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3页。,这已是“坑术士”两年之后的事了。又,《史记·封禅书》载:“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史记集解》:“服虔曰:‘疑诈,故考之。’瓒曰:‘考校其虚实也。’”(4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0页。秦始皇去世于三十七年,以此推之,“考入海方士”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也就是“坑术士”之年。综上可知,秦始皇虽然对徐巿等入海求不死药的方士有所不满和怀疑,但对他们只限于考校虚实,并未将他们置于被坑杀之列,其原因在于秦始皇招揽方士的目的是“欲练以求奇药”,临死尚“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可以说,秦始皇对不死药的迷恋和由此引发的对方士集团的依赖,至死都没有醒悟过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秦始皇虽然对方士们花费巨资未能为他至蓬莱求得不死药很失望,但并未完全绝望,故而仅限于考校虚实,不是坑杀。因为如果把这些方士坑杀,就再无人能为他入海寻三神山求不死之药。秦始皇所坑之术士如是方士的话,那么被点了名的徐巿肯定应该在列,也就不可能在秦始皇三十七年还能欺骗秦始皇去捕杀大鲛鱼。
与方士相比,秦始皇和儒生的关系一直就很紧张。儒生就其学术趣旨来讲,他们崇尚的是王道,推崇尧、舜、禹、汤、周文武那套治国理念与方式。又,据《礼记·礼运》所载孔子对理想社会的描绘,最理想的是尧舜时期“大道之行”的大同之世,那时的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其次是“三代之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他们治理下的小康之世,模板就是周王朝前期的成康之治。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是儒家崇拜的圣人,也就是他们经常称颂的“古圣先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乃至成王治理下的分封制模式,在儒家看来是最理想的治国模式。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即以法家的政治理念构建国家政治体系,被视为“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43)刘向撰,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36页。、“虎狼之秦”,与儒家的政治思想相悖。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自以为功过三皇、德迈五帝,立尊号曰皇帝,废止谥号,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4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83页。,这些措施也与儒家的学术旨趣格格不入,思想旨趣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儒生集团在社会政治层面与秦始皇发生全面冲突。秦始皇即帝位的第三年,欲封禅泰山,从齐鲁征召七十名儒生,讨论封禅礼。儒生们认为“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被好大喜功的秦始皇视为“乖异,难施用”,并“由此绌儒生”(45)《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6页。。秦始皇先于泰山顶刻石颂德,又采取秦国在上雍祭祀上帝的礼仪举行封禅。“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46)《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7页。秦始皇三十三年,在咸阳宫举行的宫廷宴会上,仆射周青臣面谀秦始皇,儒生淳于越当场指责周青臣阿谀希旨,不是忠臣,并攻击郡县制:“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4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4页。这是淳于越从儒家学术思想出发,对秦帝国政治体制及政治理念的全面否定。淳于越建议秦始皇宜效法殷周,封子弟功臣为诸侯,作为中央帝国的屏藩枝辅,实际上是企图以儒家的思想学说重塑秦帝国政治,由此激发儒家与秦帝国政治理念的正面冲突。秦始皇将淳于越的意见交给群臣讨论,丞相李斯对淳于越的意见做了严厉的批驳,并由此引发焚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斯对淳于越等儒生的批评“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4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5页。,以及他给出的焚书的理由“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4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5页。,都说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儒者和秦帝国中央集权“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治体制严重地不兼容。儒生承袭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自由讲学的风气和思想自由的潮流,对朝政和政治体制的批评有削弱中央权威的危险,更与秦帝国“天下无异议”的政治追求背道而驰。故而焚书虽及百家语与史记,其重点打击的无疑是儒生。
焚书的举措势必引起儒者的反弹,他们对秦始皇及秦帝国政治的批评只能更厉害,这些批评之声又被汇报给秦始皇,这才引发了“坑术士”。再回到“坑术士”前秦始皇所说的一段话:“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5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这里秦始皇责难的对象虽然包括“文学方术士”两类人,但前已辨析,秦始皇对方术士也即方士仅仅限于考校,并未坑杀。而所谓的“文学”就是儒生,《史记·平津侯列传》:“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51)《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列传》,第2949页。前言文学,后言儒生百余人,说明两者所指为同一类人。故“焚《诗》《书》,坑术士”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也记述为“焚《诗》《书》,诛僇文学”(5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1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对诸生的指责与李斯对儒者的批评近乎一致,都认为他们的言论蛊惑人心,不利于帝国的稳定。因此,可以肯定,坑儒的发生绝不是偶然,乃是为了达到“别黑白而定一尊”“天下无异议”的特定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政治肃清行动,矛头直指的就是与秦帝国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发生全面冲突的儒生,是继焚书后对儒生的第二次重拳出击,也可以看作焚书政策的延续,目的在于“使天下知之,以惩后”(5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从“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5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8页。这句关于“坑术士”最原始的记载来看,御史案问的是诸生,传相告引的也是诸生,故而下文公子扶苏救护的也是诸生。正如王子今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司马迁笔下,‘诸生’称谓都明确直指‘儒’‘群儒’。”(55)王子今:《“焚书坑儒”再议》,《光明日报》2013年8月14日第11版。
众所周知,秦帝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就是按照法家学派学术思想建构的,而儒者一直是法家学派重点打击的对象。韩非子在《五蠹》中,将儒生与游侠、商人、游士以及依附于权贵的游民视为国家的五大蛀虫,视儒者“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56)韩非撰,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第1122页。为乱国之俗,必欲除之而后快。与此相应的是,从学术趣旨而言,法家学派的学者与秦帝国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包括焚书在内的一系列施为,本身就是法家学派政治思想的题中之义(57)据《韩非子》卷四《和氏》载:“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撰、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第275页)又,《韩非子》卷一九《五蠹》:“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撰,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第1112页)。黄老学派与法家学派趣旨有相通处,法家学派焚书的思想就是本于黄老学派“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58)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16页。的愚民理论。《史记》中韩非与老子同传,并称申不害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59)《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46页。,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60)《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46页。,这都说明法家学派和黄老学派在学术旨趣上有内在的联系。加之黄老学派的学者大都恬退,不可能与秦帝国发生激烈的冲突,没有坑杀他们的必要。墨家学派的学者,秦之世近乎绝迹,其他学派并没有形成气候。所以,从历史逻辑上来讲,这次坑杀的460余人,也只能是儒生,虽然不能排除有牵连进去的个别其它学者。
小 结
综上,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称“焚《诗》《书》,坑术士”,在《封禅书》称“焚《诗》《书》,诛僇文学”;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称“燔烧《诗》《书》,坑杀儒士”;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称“燔《诗》《书》,坑术士”,在《五行志》中称“燔《诗》《书》,坑儒士”,在《地理志下》中称“燔书坑儒”,以及伍被所言“杀术士,燔《诗》《书》”,这些记载其实并没有任何冲突。这些说法都明确表达了秦始皇坑杀于咸阳的460余人就是儒生。在秦汉时期,儒生可称术士或经学之士,术士即儒生的别称;而方士则是指掌握一些特殊的、神秘的“方”的人,这些“方”包括却老、诅咒、祭祀神灵、祈祷鬼神、求不死药等,方士可以被称作方术士,但在秦汉时期没有被称作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