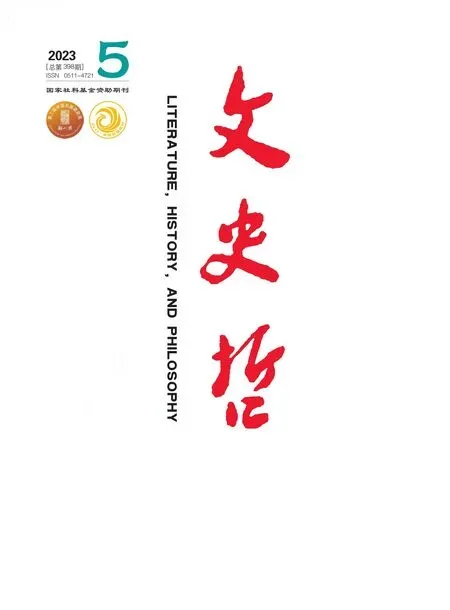帝、黄帝、黄老与帝道
——战国“帝道”说的兴起及其演变
孔祥来
引 言
在战国中后期及秦汉时期的文献中,散存着“帝者……王者……霸者……”或“……者帝……者王……者霸”等类似的说法。“王者……霸者……”或“……者王……者霸”的说法分别代表了当时流行的王道、霸道说的主张,与之对应,我们不妨将“帝者……”或“……者帝”等类似的说法称之为“帝道”说。“王道”说在儒家有系统论述,“霸道”说在法家有系统论述,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虽然“帝道”说缺少系统论述,但既然为一些学者所鼓吹,便证明它在当时的思想学术中亦必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因而颇有研究的价值。罗根泽先生很早就注意到战国学术中流传的“帝道”说,曾专文考证过霸、王、帝等作为政治学术语的形成过程(1)罗根泽:《古代政治学中之“皇”“帝”“王”“霸”》,《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5-129页。。后来杨兆贵进一步讨论了“帝道”说的“师臣”思想,并认识到“帝道”说的兴起和战国中后期的政局密切相关(2)杨兆贵:《先秦“五至”论与帝道、王道、霸道说——由〈鹖冠子·博选〉篇说起》,《古代文明》2009年第3期,第66-74页。。近年来,曹胜高、郑开、叶树勋又探讨了“帝道”说与黄老道家的学理渊源,并试图将“帝道”说建构成黄老道家的理论体系(3)曹胜高:《帝道的学理建构与学说形成》,《哲学动态》2015年第9期,第54-61页;郑开:《黄老的帝道:王霸之外的新思维》,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十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91-525页;叶树勋:《“帝道”理念的兴起及其思想特征》,《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1期,第23-31页。。毫无疑问,这些研究使我们对战国“帝道”说有了一个初步认识。但是,战国中后期的政局到底如何催生了“帝道”说,以及“帝道”说的学派归属,尤其是它与黄老道家的关系,都不是可以简单判断的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实际上,相对王道和霸道,“帝道”说的兴起和演变都要复杂得多,我们必须充分结合战国中后期之际的政治与学术发展,才能厘清它兴起和演变的历史脉络。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结合战国的政治与学术发展推断“帝道”说兴起的时代;二是结合稷下学术考察“帝道”说之内容的多元化思想渊源;三是考察战国后期“帝道”说的演变与黄老学派的密切关系。通过三个方面的探讨,以期尽可能真实地再现战国“帝道”说兴起及其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一、死谥、生号与帝、王之别——论“帝道”说的兴起
(一)王帝:从死谥到生号
人王称帝,已是殷代晚期的事情。对于“帝”字之本义,学术界存在着四种观点:一是指花蒂,二是指女性生殖器,三是“禘”之古字,四是指主宰万物的天神。其中以取“花蒂”之义者为多。但不管“帝”字的第一义是什么,它之作为人王的称号,直到殷代晚期才出现。胡厚宣根据对甲骨卜辞的研究指出,“从武丁到帝乙,殷王对于其死了的生父都以帝称”,所以武丁以后的卜辞中就有了“上帝”的称谓,祖庚、祖甲以后的卜辞中又有了“王帝”的称谓,以分别至上神与人王(4)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下)》,《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第109页。。《礼记·曲礼下》曰:天子生时称王,既葬,“措之庙,立之主,曰帝”(5)《礼记正义》卷四《曲礼下第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260页下栏。。而人王死后谥帝,可能和“帝”作为至上神的意义有关。郭沫若说,“帝”是宇宙之真宰,“人王乃天帝之替代,因而帝号遂通摄天人矣”(6)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4页。。
周人没有沿袭殷王死后谥帝的传统,《史记·殷末纪》曰:“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7)《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08-109页。但周人仍以“帝”指称古代的王,在西周和春秋的文献中,不仅有殷王帝乙、帝辛,还出现了帝夷羿、帝舜、帝尧、帝喾、黄帝和炎帝等名号。至孔子为宰我陈五帝德,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遂成为先秦文献中具有共识性的五帝系统(8)孔祥来:《先秦文献中的“五帝”说新考》,《九州学林》(香港)总33期,2013年,第3-19页。。此时帝与王只是古今之别,狐偃云:“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9)《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六《僖二十五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20页下栏。按照公羊家的理论,王者应存前代二王五帝九皇之后。这个二王五帝九皇是一个动态的系统,随着朝代的更替,后面的朝代不断加入,前面较古的王依次贬为帝,帝再贬为皇,皇则贬为民。所以,“今之王”将来也会成为“古之帝”。《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10)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98、202页。武王克殷,“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11)《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第126、127页。。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仍封微子启于宋以奉殷祀。《礼记·乐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公羊家以《春秋》当新王,则存殷、周为王者后,绌夏改号帝禹,贬黄帝归入九皇。
生王称帝发生在战国后期,公元前288年秦、齐的称帝运动是生王称帝的第一次尝试。秦国称帝的野心萌于惠王之世,时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魏王曰:“请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效河外!”(12)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74页。复说韩王,韩王亦曰:“客幸而教之,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13)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第1492页。“称东藩,筑帝宫”是奉秦为帝,己为藩属,筑宫室供秦帝巡狩以居。苏秦游说秦惠王时亦以“称帝”为辞,曰:“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14)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第139-141页。但秦惠王并没有将称帝的意愿付诸行动,秦、齐称帝运动发生在昭王之世。秦昭王十九年(前288),即齐湣王十三年,秦约齐并为西帝、东帝。但齐用苏秦之计,表面上答应秦一起称帝,实际上却合纵三晋与楚、燕共同伐秦。最后,秦迫于诸侯的压力,十月为帝,十二月复为王。《韩非子·内储说下》曰:“穰侯相秦而齐强,穰侯欲立秦为帝而齐不听,因请立齐为东帝而不能成也。”(15)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54页。虽然秦、齐的称帝运动以失败告终,但此后“帝”号成了诸侯王的追求,“帝王”也逐步成为一流行概念。
按照周礼,“王”已是有天下之号,秦、齐皆已称王之后,为什么又执着于追求“帝”的称号呢?如果帝、王在内涵或象征意义上没有重大区别,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
(二)尧、舜、黄帝与帝、王之别
秦、齐称帝,最直接的原因是“王”号的贬值。至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诸侯已相继称王。“王”本是有天下之号,只能有一个,“由于各大诸侯已经称王,王号不那么尊贵了”(16)杨兆贵:《先秦“五至”论与帝道、王道、霸道说——由〈鹖冠子·博选〉篇说起》,第74页。。所谓“不那么尊贵”,就是它不再是天下宗主的标志了。“王”号既已贬值,就需要另外找一个名号,以昭示凌驾于诸侯王之上的地位。“帝”号之能成为超越“王”号的首选,则是因为“帝”号的象征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帝”与“王”不再是死谥与生号的关系,而是“借用了它原有的神圣意味”(17)叶树勋:《“帝道”理念的兴起及其思想特征》,第25页。,成为高于“王”的尊号。这一变化始于儒家对尧、舜的表彰,进而借由田齐的“高祖黄帝”催生出了“帝道”说。
“帝”之象征意义的强化,或曰“帝”与“王”之间关系的变化始于春秋之末,首先归功于孔子对尧舜政治的推崇。孔子亟称尧舜德政,将尧舜作为最高的政治典范,修撰《尚书》断自《尧典》,认为尧舜的时代是“大道之行”,夏商周则是“大道既隐”(18)《礼记正义》卷二一《礼运第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14页上栏、中栏。。虽然孔子清楚由“公天下”到“家天下”的演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并自觉地选择“从周”(19)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八佾第三》,《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5页。,他的政治理想也是在对尧舜三王之制度因革损益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但他对尧舜政治的称颂却凸显了“帝”相对于“王”的优越性,并因答宰我问“黄帝三百年”事提出了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代表的“五帝”系统(20)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7-125页。,将其与以禹、汤、文、武为代表的“三王”系统分别开来。在儒家文献中,五帝与三王的区别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德行和治理功效方面,还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传承制度方面。尤其孔子对尧舜“公天下”的赞扬,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战国中期风靡一时的禅让思潮和禅让学说。当然,孔子及其之后的儒家仍然只是将尧舜治道看作“王道”政治的内容,并没有另外发明一个“帝道”说出来。
真正推动“帝道”说产生的契机,是田齐政权“高祖黄帝”的国家战略(21)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二)》,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第464页。。虽然孔子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但儒家并没有太多地推崇黄帝,这可能和黄帝以兵戈王天下的传说有一定的关系。但正是黄帝传说的这一特点,契合了战国中期田齐政权的需要。齐国从春秋之末到战国前期,一直处于权力斗争的泥淖之中,国势日衰,不仅受到三晋的攻伐,还受到鲁、卫小国的侵扰,当时“齐号为怯”(22)《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第2164页。。所以,田齐桓公午夺取政权之后,便励精图治,一方面设立稷下学宫,招徕天下学者,一方面定下“高祖黄帝,侎嗣桓文”的战略,以期复兴霸业,进而像黄帝一样统一天下(23)周生春、孔祥来:《田齐“高祖黄帝”考辨》,《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第132-142页。。桓公午的儿子因齐(即齐威王)继位后进一步推进“侎嗣桓文”的战略,经过桂陵和马陵两次大战,彻底打败了当时的霸主魏国。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与齐威王徐州“相王”,田齐崛起为东方霸主。于是,“高祖黄帝”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随之提上田齐的议事日程,成为宣、湣两世的奋斗目标。稷下学者“不治而议论”(24)《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第1895页。,专职工作便是为田齐的内政外交提供政策咨询和理论阐发。当田齐“侎嗣桓文”时,他们就整理管子治齐的经验,阐发争霸诸侯的方略。现在田齐转向“高祖黄帝”的战略,他们的研究重点也随之转移到整理黄帝的史料,阐发统一天下的方略上来。黄帝以征伐统一天下的传说契合了诸侯兼并的战国形势,所以田齐不效法儒家德政的圣王典范尧舜而“高祖黄帝”。稷下学者因应田齐的政治需要,便提出一些“帝者……”或“……者帝”的说法,以区别于儒家的“王道”主张。
推断“帝道”说兴起于稷下,不仅是基于战国政治与学术发展的逻辑,也有一定的文献依据。稷下学者的“议论”结集于《管子》一书,而《管子》正是称述“帝道”说最多的战国文献,分别见于《乘马》《幼官》《幼官图》《兵法》《势》和《禁藏》诸篇,其中一些篇章也是称述“帝道”说最早的文献。稷下学宫建于田齐桓公午,“历威、宣、湣、襄,前后五世,垂及王建,终齐之亡”(2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69页。,大约在公元前374年至前265年之间,历时一百多年。《管子》中除“轻重”以外的部分,应该就写成于这段时期。其中,“经言”部分写成时代最早,一般认为是威、宣之世的作品,不会迟于湣王。威、宣之际正是田齐由“侎嗣桓文”转向“高祖黄帝”,诸侯竞相称王的时期。《乘马》《幼官》和《幼官图》都在“经言”,它们鼓吹“无为者帝”,“尊贤授德则帝”,就是稷下学者向田齐提出的治道建议,是“帝道”说的最早表述。《乘马》《幼官》和《幼官图》的形成时代,早于其它称述“帝道”说的战国文献——《战国策·燕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庄子·天道》《鹖冠子·博选》及《吕氏春秋》。除此之外,《逸周书·谥法解》涉及“皇道”,《太子晋解》强调帝、王功业之异,相关内容亦必形成于“帝道”说兴起之后。
既已推断“帝道”说是田齐“高祖黄帝”的产物,那么它的产生必在田齐“高祖黄帝”的战略提上议事日程之后,甚至在诸侯“相王”之后。因为只有当“王”不再是有天下的象征时,才有必要去寻找另外的称谓,于是“帝”号才借由五帝的声望成为优选。所以,“帝道”说的出现不可能太早。《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见秦孝公,先后说孝公帝道、王道,当是法家后学的附会——孝公招贤“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商鞅不会傻到以“邑邑待数十百年”方见成效的学说去自荐。但“帝道”说的产生也不可能太迟,既不可能迟到秦、齐称帝运动之后,更不可能迟到战国之末,而必发生于生王称帝之前,亦即在秦、齐称帝运动之前已有相当程度的传播,是秦、齐称帝运动的先行观念。“帝道”说的兴起,可能只是战国中后期之际十几年间的事情。
二、稷下学术与“帝道”说多元化的思想渊源
“帝道”说兴起于稷下,所以《管子》也是称述“帝道”说最多的一部战国文献。根据我们的统计,《管子》称述“帝道”说的内容共有六条,分别见于《乘马》《幼官》《幼官图》《兵法》《势》和《禁藏》诸篇。《乘马·大数》云“无为者帝”(26)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4页。,《势》篇是对“无为者帝”的解释(27)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82-883页。。《幼官图》本是《幼官》的图解,故而二者文字相同,皆云“尊贤授德则帝”。《兵法》云“察道者帝”,虽没有上下文可以判断“道”的具体涵义,但我们认为与“无为”有关(28)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39、184、316页。。《禁藏》所谓“以情伐者帝”(29)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027页。,讲诸侯兼并中的用兵之道,“帝”者是善于征伐用兵的典范。这六条称述不妨概括为三项内容:无为、尊贤授德、征伐用兵。无为与尊贤授德、征伐用兵显然是不同学派的思想主张,反映了稷下学术的多元化面貌。
(一)征伐用兵与黄帝传说
《禁藏》曰:“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是将帝、王、霸都塑造成了善于征伐用兵的典范,只是在征伐用兵的谋略上存在着高下之分。“以情伐”“以事伐”和“以政伐”指的是敌国之间在情欲、内政、外交等层面展开的斗争,是通过不同谋略破坏敌国的内政和外交,使其国家自行坏乱,然后再用兵兼并之。因为谋略不同,斗争的层面不同,兼并战争消耗的成本和取得的功业也不同,便有了帝、王、霸的分别。但无论“以情伐”“以事伐”,还是“以政伐”,帝、王、霸之有天下,无不是通过征伐用兵、通过兼并战争来实现的。用兵征伐以兼并诸侯,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情形,也反映了传说中黄帝时代的情形。五帝之中,唯有黄帝是征伐用兵的典范。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30)《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第3页。唯炎帝与蚩尤不服,于是黄帝又征服炎帝,擒杀蚩尤,才最终取代神农氏有了天下。《管子·地数》附会有伯高教黄帝控制矿山制造兵戈以兼并诸侯的传说。黄帝问伯高如何能“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伯高教他封禁蕴藏着黄金铅锡铜铁等金属的矿山。“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3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354-1355页。《禁藏》所谓“以情伐者帝”之语,应该是兵家学者总结的战争谋略。在兵家著作中,黄帝是一个善于用兵的典范。《孙子兵法·行军》篇载有黄帝伐“四帝”的传说(32)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2页。,《孙膑兵法·见威王》云“黄帝战蜀禄”,《势备》又云“黄帝作剑,以阵象之”(33)“蜀禄”即“涿鹿”。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第48、63页。。孙膑在齐时,稷下学宫已初具规模,他与稷下学者之间不可能没有交流。
用兵征伐以取天下,最符合传说中黄帝的原始形象。黄帝传说最早见于《逸周书·尝麦解》,云蚩尤逐赤帝(赤帝即炎帝),赤帝求助于黄帝,于是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34)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33页。,以兵鼎定天下。李学勤推断《尝麦解》是周穆王初年的文献(35)李学勤:《〈尝麦〉篇研究》,《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7-95页。,所以这个传说应该有着最远古的史影。到了春秋中期,文献中又出现了黄帝与炎帝相征伐的传说。《国语·晋语四·文公在狄十二年》云黄帝与炎帝“成而异德”,故“用师以相济”(36)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37页。。《左传·僖二十五年》晋卜偃占卜勤王之事,“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37)《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六《僖二十五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20页下栏。。孔子为宰我陈五帝德,云黄帝“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38)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第118页。。而《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魏二·五国伐秦无功而还》和《庄子·盗跖》中,皆有提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传说。《史记·五帝本纪》对黄帝事迹的记载,实际上是综合了先秦文献中的各种不同说法。
周武王克殷之后,封“帝舜之后于陈”(39)《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第127页。,田齐的祖上陈完是陈厉公之子,于陈宣公时避祸奔齐,“以陈字为田氏”(40)《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第1880页。,所以田齐实际上是帝舜之后。帝舜是儒家“王道”政治的典范,但田齐政权不效法帝舜,盖因帝舜乃通过禅让继为天子,其德治模式无法适应战国兼并战争的需要。黄帝列五帝之首,又是通过兼并战争统一天下,是用兵征伐的典范,其治道更能适应战国的形势,故而亦欲通过征伐兼并统一天下的田齐,选择黄帝作为效法的榜样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稷下学者要为田齐“高祖黄帝”的国家战略进行理论上的阐释,那么征伐用兵也就成为“帝道”说必不可少的内容。
(二)从“尊贤授德”到“师臣”之说
《幼官》《幼官图》曰:“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4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39、184页。尹注“尊贤授德”是“师臣”之义,实际上只解释对了一半。“尊贤”和“授德”并非同一意义的重复,而是表达的两个意思——“尊贤”可以理解为“师臣”之义,但“授德”强调的则是帝位传承,不授子孙而授有德。并且,这句话主要还是在强调“授德”。因为“尊贤”并不是帝与王、霸的根本区别,文献中的王、霸之君以及任何有作为的君主,无不尊贤。帝之所以有别于王、霸,乃在于他们能将“尊贤”的思想实践到极致,即不仅选贤与能,不仅“师臣”,还将帝位传于贤德之人,实行“禅让”。战国“帝道”说兴起的时候,也正是“禅让”说流行的时期。郭店简《唐虞之道》曰:“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授贤”与“尊贤授德”组词略有不同,表达的意思则完全一样。又曰:“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42)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5、96页。上博简《容成氏》则按照“授贤”与“授子”的不同将古史划分为两个时期,自舜以上的古帝“皆不授其子而授贤”,所以政治清明,天下太平;自禹而下的三代之王改“授贤”为“授子”,于是天下政治陷入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43)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8-293页。。帝、王之优劣,正在于“授贤”与“授子”的不同。《幼官》《幼官图》中“尊贤授德则帝”的说法,应该就是渊源于当时正在风行的“禅让”说。
帝者“师臣”的说法最早见于《战国策·燕一》,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44)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第1684页。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郭隗谏议他招贤纳士时如是说。“帝者与师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是说帝者师事贤者,故能吸引百倍其贤的人前来辅佐。尊贤的程度不同,吸引到的人才水平就不同,最后在功业上也就表现为帝、王、霸的不同。这实际上反映了战国士人傲骄的政治心态。但“帝者与师处”的说法并非郭隗独创,杨兆贵考证它实际上渊源于《尚书·仲虺之诰》(45)杨兆贵:《先秦“五至”论与帝道、王道、霸道说——由〈鹖冠子·博选〉篇说起》,第68页。,只是《尚书》中只言王、霸而不及帝。《荀子·尧问篇》载楚庄王闻之中蘬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46)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48页。中蘬即仲虺,又作中,成汤时贤臣,“汤归至于泰卷陶,中作诰”(47)《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第97页。,《尚书》有《仲虺之诰》。《吕氏春秋·恃君览·骄恣》亦载庄王引仲虺之言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48)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74页。《吴子·图国》篇佚文、《韩诗外传》卷六、《新书·先醒》《新序·杂事》《说苑·君道》皆有此语,可见此说源远流长,出自儒家经典无疑。
存在着一类以君臣问答形式阐发治道的先秦文献,曹峰将它们统称为“帝师”类文献,认为它们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49)曹峰:《道家“帝师”类文献初探》,《哲学论集》(台湾)第49期,2018年,第33-59页。。这确实是一种很有启发性的视角。不过,即使不考虑文献的学派归属问题,这类文献中为君主答疑解惑的大臣是否皆有“帝师”的性质,也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方面,从这类文献中的君臣对话来看,很难说君对臣的礼敬皆达到了“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的谦逊程度。另一方面,这类文献不只附会了黄帝、高阳、尧、舜等帝者问治道的事迹,还附会了禹、汤、盘庚、武丁、文王、武王、成王等三代之王,以及吴王阖庐、齐威王、秦昭王等春秋战国霸主问治道的事迹,固非对“帝者与师处”的诠释。事实上,到了战国后期“师臣”说已不再囿于“帝道”。《吕氏春秋·孟夏纪·尊师》曰:“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尧,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孙叔敖、沈尹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句践师范蠡、大夫种。此十圣人、六贤者,未有不尊师者也。”(50)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91-92页。不仅五帝“尊师”,三皇、三王、五霸也无不是“尊师”才立功成名。
《幼官》《幼官图》认为齐桓公九会诸侯乃成帝者之势,曰“九举而帝事成形”。而成“帝形”之措施与所成之“帝形”,亦皆体现出儒家特色。曰:“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官,发之以力,威之以诚。”所谓以道、以惠、以仁、以义、以德、以信、以礼、以乐,无不是儒家治道。九会诸侯之后,帝事既已成形,则“大命焉出”,诸侯朝聘以时。曰:“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内,诸侯三年而朝,习命;二年,三卿使四辅;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来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内,诸侯五年而会,至,习命;三年,名卿请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礼义;五年,大夫请受变。三千里之外,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为廷安,入共受命焉。”(51)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39、159、184、186页。这个“帝形”的安排,应该就是《周礼·司寇·大行人》《礼记·王制》和《聘义》中那套朝聘体系的综合。
(三)“无为者帝”与老子、黄帝类政论
《乘马·大数》曰:“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贵而不过度,则臣道也。”(52)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4页。《乘马》综论国家政治措施,多有三晋儒家遗意。唯此节概论为君之道,曰“不自以为所贵”,曰“无为”,曰“为而无以为”,曰“为而不贵”,显然出自《老子》。帛书《老子》第38章曰:“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53)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页。帝是“上德”之人,王是“上仁”之人,《逸周书·谥法解》曰“德象天地曰帝”,“仁义所在曰王”(54)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628、630页。。所以,“无为者帝”即《老子》所谓的“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为而无以为者王”也即《老子》所谓的“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为而不贵”或“不自以为贵”,在《老子》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表达,但它反映了《老子》贵柔守雌的思想,却毋庸赘述。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无为”,“无为者帝”之“无为”是否即《老子》所说的“无为”呢?很多学者认为,《老子》的“无为”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就是追求一种“可以减少冲突并能达到更高效果的‘为’”(55)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修订版)》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16页。。我们不认同这种说法,我们认为要理解《老子》的“为”,首先需要厘清它所追求的“更高效果”是什么。我们认为《老子》追求的“更高效果”就是它在第六十七章所描绘的那幅世界图景,即“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基于这样的社会理想,《老子》的“为”其实就是“无为”。这与上述很多学者对“无为”的界定并非一种简单的同义反复,而是厘清了《老子》的“为”确实是一种不同于诸子积极创制的“无为”,或者说它的“无为”确实不是一种积极建设的“为”。《老子》第六十三章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其准确涵义就是“为以无为,事以无事,味以无味”。所以,它主张“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主张完全回归“道”,放任天地万物自然地演化和生灭。曰:“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地将自正。”(56)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第131、132、150、153、154、421、426、427页。
如果“无为者帝”亦是《老子》意义上的无为,则“帝道”说又如何说服热衷于兼并战争的战国君主呢?《老子》的“无为”思想当然不符合田齐“高祖黄帝”的战略目标,也不符合战国君主兼并诸侯的战略目标。我们认为,“无为者帝”的表达形式虽然渊源于《老子》,但帝者“无为”的内涵已不再是《老子》的一任万物之自然,而是成为一种效法天地阴阳五行变化之规律,以更有效地统一天下的积极手段。《管子·势》篇解释了“无为者帝”的涵义,曰:“夫静与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知静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从,每动有功。故曰:无为者帝,其此之谓矣。”(57)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82-883页。强调的就是君主施政不能任由自己的主观好恶,必须静作以时,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才能收到最好的功效。所谓静作以时,就是要效法天地阴阳五行变化之规律。“帝道”说导源于田齐的“高祖黄帝”,黄帝自然也就成了践行“帝道”的典范(58)叶树勋认为黄老学者“沿用了早期流传下来的黄帝形象,并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将黄帝塑造成历史上曾实践帝道的主要代表,希望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说明帝道的优越性”。参见叶树勋:《“帝道”理念的兴起及其思想特征》,第25页。。《五行》云“黄帝泽参”,亦是说黄帝能够效法天地阴阳五行变化之规律,立六相以治天地,作五声“以政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59)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865页。效法天地阴阳五行变化之规律,从而取得治理之极效。这样理解帝者的“无为”,才更符合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也更符合田齐“高祖黄帝”的现实政治需要。《乘马》《势》和《五行》非一时一人之作,但所论之“帝道”,归根结底都是效法天地阴阳五行变化之规律。
“无为者帝”的说法反映了稷下的黄老思潮。曹峰认为战国黄老思潮的特色就是“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作为思想的基础,将以黄帝为代表的‘天道’作为行动的法则,而贯穿着本与末、道与术相对应的思维”。所以,在黄老的思想结构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道论和政论,“老子类型道论和政论”强调道的本原性以及它对人事的决定性意义,而“黄帝类型道论和政论”则强调君主应“法天地以尽人事”,从“天地人贯通的宇宙秩序中”总结出治世的方法(60)曹峰:《出土文献视野下的黄老道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141、143页。。从《老子》的“无为”到《管子·势》篇的“无为”,正是“老子类型道论和政论”向“黄帝类型道论和政论”的转变,“帝道”说之“无为者帝”的内容体现了“黄帝类型政论”。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测《管子·兵法》所谓“察道者帝”的“道”,应该也是指“黄帝类型道论”,而非“老子类型道论”。“黄帝类型道论”与“老子类型道论”有着深刻的渊源,但“黄帝类型政论”则主要吸纳了其他学派的治道。
稷下学者是一个学术群体而非一个学派,所以稷下学术的思想十分复杂,《管子》的各个篇章实际上是不同学派的学者为田齐政权提出的国家治理策略的汇编,而不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所以,兴起于稷下的“帝道”说,在思想内容上自然也体现出不同学派的色彩——不仅不是某一个学派的独创,甚至各项内容之间还存在着一些龃龉,比如那些主张“尊贤授德”和“无为”的学者,应该都不会鼓吹用兵征伐。因此,早期的“帝道”说并不存在一个理论体系,而只是稷下学者为了区别王道、霸道创造的一个习语,兵家、儒家、黄老等都可以用它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三、战国后期“帝道”说的演变与黄老学派
我们通过考证“帝道”说内容的多元化思想渊源,阐明了它并非某一学派的独创。但是,可能因为以黄帝为典范的缘故,“帝道”说在演变中与黄老学派的关系愈益密切。《管子·势》篇对“无为者帝”的解释已体现出了这一特点,而《管子》以外的文献,尤其是《庄子·天道》和《吕氏春秋》一些篇章对“帝道”说的阐发,皆主要发展了帝者“无为”的内容。战国后期,“帝道”说逐渐演变成一种有别于王道、霸道的治国之道,与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不再有必然的联系,即与最高统治者称王或称帝不再有关系。这一演变与黄老学派不断强化“黄帝类型道论和政论”的趋势相辅相成。
在“帝道”说的演变中,《庄子·天道》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献。《天道》篇是庄学“融合派”的著作(61)刘笑敢根据《庄子》外、杂各篇反映的思想内容,将之分为述庄、无君和融合三派。参见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其实就是黄老一派的著作,不仅是唯一出现了“帝道”一词的先秦文献,也是阐述帝道“无为”的内涵最系统的一篇文献。《天道》曰:“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帝道、圣道所以运转无所积滞,皆是效法天道,不以万物“铙心”,虚静无为。曰:“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者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帝王无为,故无忧患,可以“年寿长”。然则帝王无为养生何以治国?曰有“任事者责矣”,即上无为而下有为。“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上、下不能同无为,也不能同有为,而是上无为而下有为,曰:“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62)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57、465页这正是典型的“黄帝类型道论和政论”,阐明了无为何以治国的问题。
《吕氏春秋》也是一部颇有黄老色彩的文献,尽管不能完全将之划归于黄老学派。它也是战国晚期称述“帝道”说最多的一部文献,共有三条。其中《慎大览·下贤》强调帝、王皆尊贤以为治,并非区别帝道与王道。《有始览·应同》阐发“物之从同”的思想,认为“类固相召”,其所同者大,所召者亦大。故引黄帝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所谓“与元同气”,就是同于“元气”。这个“元气”是指作为天地万物总根源、总规律的“气”,既是物质的,又具有精神性。黄老学派认为万物都是从“气”生出来的,都是“气”之运行变化的产物,“气”就是道。所以,同于元气也就是同于道,就是同于天地万物的总根源,顺应天地万物的总规律。帝者同于气,同于道,那么其治所召者亦大,必致最高的太平。“故曰同气贤于同义,同义贤于同力,同力贤于同居,同居贤于同名。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则薄矣,亡者同名则觕矣。”又曰:“成齐类同皆有合,故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63)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287-288页。所以,《恃君览·行论》引鮌之言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64)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568页。
不过,黄老学者在《吕氏春秋》中更多的是直接依托“黄帝言”阐发“黄帝类型道论和政论”的(65)郑开统计“帝”字在《庄子》中出现了70余次(郑开:《黄老的帝道:王霸之外的新思维》,第504页),其中有许多是有关黄帝的寓言。但黄帝在《庄子》中基本上是一个问道者的角色,甚至是被揶揄的对象,而非践道的典范,所以那些寓言绝不是在阐发“帝道”说。。《季春纪·圜道》引黄帝言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并解释说:“以言不刑蹇,圜道也。”所谓“圜道”,就是天道。天象运行,四时变化,万物生灭,周而复始,“无所稽留”。处,居也。帝者遵循天道,所以无所留居,亦即“无所稽留”,无所踬碍。俞樾曰:“然则不刑蹇者,不踬碍也。”《季冬纪·序意》引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大圜”即天,“大矩”即地,天圜地方,黄帝告诉颛顼,能效法天地之道,便能有天下而治万民。《孝行览·必己》云神农、黄帝法道德,“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物物而不物于物”(66)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80、273-274、348页。。《士容论·审时》引黄帝之言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67)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第701页。实际上亦皆是强调顺应天地变化的规律。《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集天下学者编撰而成,其时稷下学宫已散,参与编撰的学者应有来自稷下者。
黄老学派的“黄帝类型道论和政论”主要反映在战国及秦汉之际出现的各类黄帝书中。《汉书·艺文志》所录各类黄帝书有20余部,很多学者认为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种古佚书即《汉志》所录的《黄帝四经》,或泛称为《黄帝书》。但从内容来看,这四篇文献应该不是一部书,裘锡圭认为“它们大概是帛书的主人为了学习黄老言而抄集在一起的”(68)裘锡圭:《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黄帝四经〉》,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其中,《道原》论道之原,《经法》并称“帝王”,《称》有“帝者臣,名臣,其实师也”一句(69)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1页。,是抄自其它文献。唯《十六经》依托黄帝君臣的对话,根据太史公对黄老道家的定义,应该是一篇典型的黄老作品。《十六经》的形成年代也存在争议,叶山(Robin D. G. Yates)认为它可能是一些不同时期的文章的节选抄辑(70)叶山(Robin D. G. Yates):《对汉代马王堆黄老帛书的几点看法》,傅海燕译,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16-26页。,我们根据《立命》中的官爵体系及《五正》《正乱》反映的政治形势,推断它最后写成于汉初。《十六经》反映了兴盛时期的黄老治道,主张亲民、尊贤、刑德相用、征伐兼并,但归本于清静无为,因顺天地之道。《观》曰:“圣人不巧,时反是守。优眛爱民,与天同道。圣人正以待天,静以须人。”(71)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第111页。这个宗旨,正是“帝道”说所鼓吹的效法天道的无为思想,但《十六经》完全没有以“帝道”标榜自己的思想主张。
根据上面的考察,应该可以这样来概括“帝道”说与黄老学派的关系:一方面“帝道”说与黄老学派不能等同划一,即“帝道”说不是黄老学派的独创,而从现有文献中,也未发现黄老学派以“帝道”作为其理论体系之标榜的直接或间接证据。另一方面,“帝道”说又与黄老学派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尤其在演变中与黄老学派的关系愈加密切,“无为者帝”的内容即渊源于黄老学派,而这一内容的内涵也随着黄老学派“黄帝类型道论和政论”的不断阐发而日益深化,甚至可以说战国后期的“帝道”说与黄老学派在效法天道无为的思想层面上达到了统一。因此,从“帝道”说发生和演变的实际历史脉络来看,我们不能用“帝道”说指称黄老学派,也不能认为黄老学派的思想体系就是“帝道”说。
结 语
“帝道”说的发生与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的产生有着现实的政治和学术背景,在学术上是学者们“托古”的产物,更具体地说是受到了儒家宣扬尧舜之道的启发,在政治上则受到了田齐“高祖黄帝”的直接影响,进而受到诸侯相王之后继续追求统摄天下之政治发展的影响,因而它以五帝,尤其以黄帝作为典范,强调帝之于王、霸的优越性。但“帝道”说从产生伊始,就不是一个被精心构建的理论体系,而只是稷下学者从各自的思想主张出发,结合现实的政治需要创造出来的一种类似习语的说法,因而其内容有着多元的思想渊源——不仅有黄帝原始传说的史影,还有兵家、儒家、黄老道家以及“禅让”说的思想因素。战国后期,在“帝道”说的演变中,它与黄老学派的关系愈加密切,即它效法天道无为的主张随着黄老学派“黄帝类型道论和政论”的阐发而不断得到深化,二者可以说在效法天道的层面达到了统一。但“帝道”说仍不能等同于黄老学派,不仅“帝道”说不能涵盖黄老学派的全部思想内容,从现有文献中也未发现黄老学派以“帝道”说标榜其理论体系的证据。本文仅仅是将“帝道”作狭义的理解,如果将它与五帝治道对应起来,那它就更不能是黄老一派所能独占的了。到了战国后期,当“帝道”说还没有形成一个像王道、霸道那样完备的理论体系时,它已被另一种新治道模式“皇道”所超越。